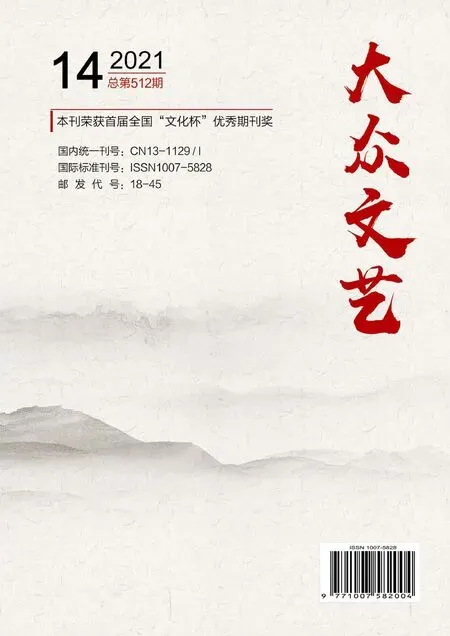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父权与生育问题研究
——以《1984》和《使女的故事》为例
李知行 吴燕飞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000)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有关女性地位与权利的讨论更加深入,两性之间的种种问题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密切关联也日益得到揭示。此外,女性作家的作品改变了往日男性笔下女性的固定形象,创作出更富有生命力的女性角色,传达出对陈腐错误的两性观点之讽刺和抨击,以及对更健全的人类社会之思考。作为两部公认对于女性主义问题有所启发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和《使女的故事》建构了两个略有不同的未来极权社会,用不同的情节与叙事对女性问题和人类社会的走向进行了探究。本文从父权与生育问题入手,以两部反乌托邦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极权政治环境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所经历的困境,具体而言包括父权意识形态施于女性的不公平和极权政治制度强加给女性的荒谬生育制度与生育重负。把反乌托邦文学与女性主义探究进行结合是本文的新尝试,希望为文学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新视角。
一、父权
父权指男性在社会中某些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所特有的权威,它好似一只无形的手,使男性获得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从而通过强力、习俗、法律、礼仪等来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使之处于男性统治之下。父权制是社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种不公平制度,关于其形成的原因有种种猜想,最被广为认可便是由于男女两性之间的体力差距。在早期的农耕社会,通常拥有更大蛮力的男性可以进行更多更久的农耕或畜牧,从而掌握了更多的物资,逐渐发展为权力。迄今为止,全世界半数以上的文化都形成了父权制,这一跨文化现象给女性群体造成了许多阻碍。1970年凯特·米利特首次在其著作《性政治》中将“父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当中。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也在其生态女权主义中表示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由此,父权制对于女性的不公可见一斑,其影响之深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或带有性别歧视主义的强烈色彩,或带有对于父权制的强烈反抗。
反乌托邦文学与父权:
欲了解反乌托邦的含义,首先要了解它的反义词——乌托邦。乌托邦源于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同名作品《乌托邦》,作品中有一个理想的共和国,如先哲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一样,乌托邦中人民地位平等,财产归为公有,社会资源按需分配,构成一个欣欣向荣的繁荣社会体系。而反乌托邦虽然从基础政治原则上承袭了乌托邦的影子,发展结果却与乌托邦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反乌托邦思想从相反的方向出发,带着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的悲观性理解进行建构。这一点可见之于拉塞尔·雅各比对反乌托邦主义的定义:“它着重于描绘一个不理想或反理想的社会,且一定与堕落、枯竭、沦丧、沉沦、迷惘、无聊、无助这类暗示性极强的字眼相联系。”由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占支配地位,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着重要作用,二元对立这一概念充斥于西方哲学思想之中。在两性间造成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在反乌托邦主义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强势与弱势之间的冲突。因此,在女性被称为是“客体”的父权制社会环境下,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自然地远离了权力中心,成了弱势群体。正如文中的两部作品一样,女性在反乌托邦社会中无论是任何方面都深受着来自父权制的野蛮挤压。
(一)反乌托邦视角下不同父权形象的体现
在《1984》中存在着“老大哥”这个角色,他是大洋国社会体制的缔造者,权力的拥有者。老大哥所具有的力量感与威严,是父权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反乌托邦体裁下,这种压迫感走向极端,老大哥掌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将威严建立在人民的恐惧之上。他企图成为国家的精神图腾,于是又把自己可怖的微笑挂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着对民众的洗脑教育,抹杀掉他们眼中最后一丝对于自由的追求。同样的,在《使女的故事中》中,年迈的“大主教”们也带着父权的威严统治着整个国家,他们拥有自己的豪华别墅,私人卫兵,还有象征着地位的旋风牌轿车。与《1984》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大主教们虽然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与老大哥有所不同。虽然基列国的大主教们将用以立国的圣经烂熟于心,他们却在背地里背叛着自己的信条。无论是弗雷德大主教用来藏违禁用品的办公室,还是大主教们集体龌龊的下流场所,都彻底颠覆了男性掌权者所理想的威严形象。聪明如制定基列国国法的大主教,还是会在孩提般的拼字游戏中落败给一个没有任何书籍可以读的使女。在阿特伍德的笔下,父权失去了男性主义者眼中的光泽,代之而来的是一具空壳。由此可见,不同性别作者笔下父权形象的体现,也带着不同的主观色彩。在奥威尔笔下,登峰造极的父权形象是其作为男性最为理想化的表达,而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则转变为了女性对于父权制度的批评与反抗。
(二)父权在思想上对于女性的压迫与控制
企图对于女性实现精神控制是父权的重要提现。在《1984》中,温斯顿在第一次见到裘莉娅时,表现出了对她极度的厌恶,甚至在脑子里进行了对她变态的虐待幻想。然而在裘莉娅与他秘密通信后,他对裘莉娅的态度又发生了逆转,奥威尔笔下的裘莉娅也由原来的积极分子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颇具女性幻想的角色,在结识温斯顿之后,裘莉娅甚至为其穿上了连衣裙、丝袜、高跟鞋。笔者认为,这是奥威尔作为男性作家将他对于女性的种种幻想杂糅于其小说中。从温斯顿的内心独白“认识裘莉娅之后的那个月里,他对于她的欲望性质改变了。”以及“她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必须物,他不仅想拥有她,而且觉得有权拥有她。”可以看出,此时两人之间出现的不再是爱情,而是男性对于女性变态般的占有欲,而这便是对于父权制最赤裸裸的诠释。阿特伍德在作品中同样描绘了相似的场景,大主教偷偷地邀请他的使女奥芙弗雷德到他的房间里玩拼字游戏,想通过一次次的接触使奥芙弗雷德对其产生感情,改变他们在荒唐的生育仪式时的尴尬氛围。他带奥芙弗雷德到基列国上层男性们专属的“地下俱乐部”,实则是这群卑鄙之徒囚禁女性用之招待外宾或是自我享乐的地方。这位大主教所做的一切,表面是看起来是试图对奥芙弗雷德交心,本质上却同样是为了满足他的一己私欲,即让奥芙弗雷德真正屈从于他,再次燃起他早已不在的男性欲望。只不过,阿特伍德作为故事的缔造者,没有令这一可耻行径成功,反而赋予了奥芙弗雷德不为所动的反应来讽刺这一大男子主义的荒唐幻想。纵观两部作品,尽管父权制的影子无处不在,二者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奥威尔并没有有意对于父权制作出批评与抗议,而是流露于他本人对于书中女性角色的种种描述之中,这与其作为男性的个人立场与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反观阿特伍德笔下的父权制,女性角色拥有着对于父权压迫明显的厌恶与反抗,并且不以男性意志为转移,这是阿特伍德对于现实世界男权压迫有意的警告与反抗。二者包含的对于父权制的流露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二、生育
生育是一个自然过程,其旨在繁育后代,为社会注入新的血液。生育的过程离不开男女两性的参与,两性在自然选择的安排下获得了不同的生殖功能,男性排出精液,女性提供卵子并在体内供养受精卵。亚里士多德曾言:“胎儿是通过精液和月经相遇而产生的,在这种共生之中,女性仅提供被动的物质,男性的本原才是力量、主动性、运动、生命。”然而这位希腊先哲的设想并不客观公正。事实上,在整个生殖过程中,精子和卵子之间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女性主义论著《第二性》中写道:“重要的是要指出,在相遇时配子中的任何一个对另一个都没有特权,两者都要牺牲它们的个性,卵子吸收了它们的全部物质”。女性作为生产者,往往承受着生育过程中最多的痛苦,然而纵观历史长河,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生育的自主权,主动权往往被男性所支配。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对于女性生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他们将自己作为生育过程的掌控者,漠视了女性本该拥有的权利。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新的思想浪潮出现,天赋人权,男女自由平等,生育自由才被逐渐推崇起来,政府不再干预个人生育问题,逐步形成了平等的生育自由观。二战过后,女性主义思潮蓬勃发展,女性地位再次被推上一个更高的地位,生育权利之于女性,也再次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一)反乌托邦作品中女性因生育问题受到的压迫
在《1984》中,凯瑟琳曾说道:“如果能够,他们必须生出一个小孩,所以要继续有房事,得有规律的每星期一次,除非是在不可能怀孕期间。”而温斯顿对此嗤之以鼻,原因是在此过程中他不能享受到任何爱人之间应有的情绪。在他眼里,凯瑟琳是一具没有感情的躯壳,麻木地遵守着老大哥定下的规矩,她的这种被洗脑思想,是反乌托邦极权社会下对于女性生育职能严重压迫的一种体现,它表现为偷换生育的概念,对女性灌输错误的思想。在另一部作品《使女的故事》中,对于女性生育受到压迫的描写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负责生育的使女们被套上了宽大的红色袍子,仅仅是从穿着上就昭告众人她们已经不再是一个自主的女性,而是国家的生育机器。在使女履行自己义务,即“授精仪式”时,她们将自己的身体袒露在一个与自己毫无交集,年老色衰的大主教面前,却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逃离这一令人作呕的过程,实在是一种非人般的虐待。在这里,使女甚至不再是他者,而成了“第三性”,她们生下的是流着自己的血液却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使女们不仅从精神方面收到来自嬷嬷们的洗脑教育,同样受到强力的制约。层层把守的眼线,寒冷彻骨的机关枪,都是基列国用来给女性施压的工具。这些反乌托邦作品内女性角色在生育问题上收到的种种压迫,离不开作品外真实社会里人们对于女性生育话题的种种偏见。
(二)荒谬的生育制度与反乌托邦的主题
如果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暂时不考虑女性在生育压迫中受到的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反乌托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生育计划是否是一个荒谬的存在?在苏格拉底构建的理想国里,经过选拔的优秀女性被强制分配给在战场上有出色表现的男性,并且要求他们多生多育,为社会提供优良基因。然而这一效益最大化的方案,具有极为苛刻的局限性,即建立在一切最理想的条件之下(苏格拉底在论述的最后也强调了这是不可能的),如在完美的社会分工下,社会拥有充足的资源来供养数目庞大的新生儿,或是在周到的法律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下生养者能够以给予婴儿需要的保护和教育,因为对于后代的良好教育是能否维持完美社会机器良性发展的最根本因素。理想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就在于其“理想”二字,即一切都是理想化的,并不能真正实现。反观反乌托邦社会,在生育被奉为圣旨的情况下,其他环节却不能够提供应有的条件。大洋国里那些冷冰冰的食物以及粗制滥造的杜松子酒充分表明了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孕妇和婴儿不能得到什么像样的食品。而就算婴儿能够成长,他们也只能是像帕森斯太太的两个侦察队队员似的给本就令人窒息的国家带来更多的恐惧和不安。同样的,在基列国里新生儿们除了无法受到良好品德教育与喂养,他们还要承受着核泄漏之后糟糕的自然环境,而每日在教堂草坪上的处决仪式想必会成为他们日后制定更多泯灭人性的制度的灵感来源。反乌托邦主题下的生育制度背离了生育的本质,忽略了支持其良性发展的一切社会因素,在这样的错误理念下,其存在永远是荒谬的。
三、被父权胁迫的生育
父权与女性生育问题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如今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将生育视为女性义务的男性仍不在少数。这正是由于父权制在经年累月的发展中男性不断地强调自己与女性地位不同所带来的结果。他们既对女性的能力,如力量,智力等提出质疑,又使女性处于繁育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所以当男性在父权社会中掌权时,生育便成了女性理所应当的任务,她们被灌输以生育为荣的思想,而忘记了自己本该拥有的权力。这解释了为什么在《1984》里凯瑟琳对于生孩子有如此巨大的渴望,她坚信着国家对她的教导,执着地要求温斯顿与她进行每星期一次毫无夫妻间乐趣所言的房事。同样的情况也在《使女的故事》中由使女和大主教及其夫人三人荒唐的生育仪式里一览无余。父权对于女性生育的胁迫已经存在长达几千年,错误的思想烙印也随着时间一次次地由男性群体施加给女性。一直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人们才开始大规模地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并做出改变。即使如此,在如今世界的许多不发达地区,女性生育问题仍然深受着来自父权主义的压迫。
结语
父权制以及女性生育权是女性主义者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但纷争仍未消除。生育既是人类的希望,也是对女性的胁迫,父权已然是人类社会成熟的权力形态,也是女性解放道路上最大的阻碍。从《1984》和《使女的故事》所建构的反乌托邦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摒弃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立场,使是两性都拥有同等的权利,分配同样的社会资源,使生育的选择和制度更多出于女性自主,是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应当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使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