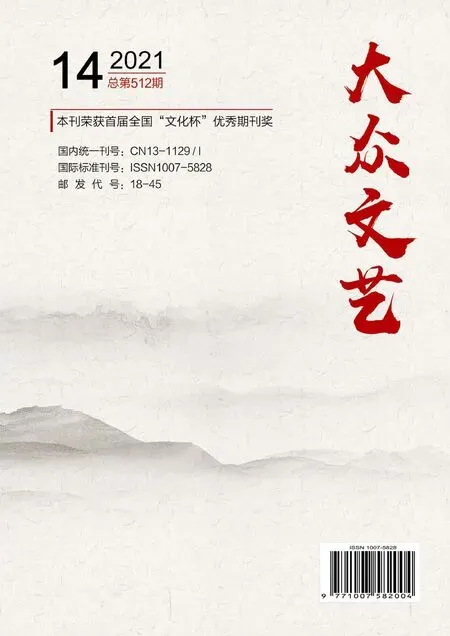浪漫时代的壮举
——论《光荣》中火车与道路的象征意义
李怡帆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光荣》是纳博科夫第五部俄语小说,最初取名为Voploshchenie(某个梦想的实现),后改为《浪漫时代》。之后作者倾向于更精炼的词“荣耀”,它意指英勇的壮举。马丁只身跨越俄国封锁的边境,别人认为他的行为令人困惑,但纳博科夫却要向人们证明,这个过着乏味的外在生活、死得又轻若鸿毛的年轻人却有着内在的光荣。
评论家们不理解马丁的行为。采特林(М.О.Цетлин)表示他没有感受到独特的、宿命般的人类命运。奥索尔金(М.А.Осоргин)称他的壮举没有任何目的,缺乏充分动机,只反复提到这个即将到来的远方探险,要去往一个被想象成充满混乱与野兽的国度。无疑,壮举的意义和目的是神秘的。这份神秘背后隐藏着纳博科夫对故国的怀旧之情与乡愁意识,这部作品也被纳博科夫赞叹为提升到了一种充满忧郁与极度纯情的艺术境地。
在《光荣》中作者大量运用象征主义手法,生动描绘许多意象,其中火车与道路是揭开这层神秘面纱的关键,它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使小说充满怀旧气息,提醒着主人公内心对周围环境的疏离,映衬出作者重回故土的愿望。这两个主题意象贯穿整部小说,构成了现实与非现实世界之间的空间联系,其他意象与象征细节也优雅地交织于其间。
因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光荣》深刻的思想内涵,解读火车与道路的象征意义,从传递作者情感的角度探究其文学功能,以期对该作品的艺术价值有更全面丰富的认知。
一、情感映射:浪漫时代的壮举
小说讲述了俄国青年马丁离开故土、流亡至西欧生活,逐渐成长并最终服从浪漫激情的指引做出一项壮举——非法跨越封锁的苏俄边境。纳博科夫所有俄语作品都与“失落的家园”主题相连,他对祖国和对自己有着冷静而忧伤的审视,有时在其小说中冲破出俄罗斯的呐喊——《光荣》。在1943年给威尔逊的信中他承认:“《波尔塔瓦》是一首绝美的诗,但爱国主义精神过于强烈。而《波尔塔瓦》在普希金文学遗产中占据的地位如同《光荣》之于我”。
关于俄罗斯的描写串联成对往昔与故国的回忆。俄罗斯这个词本身就像交响乐中的旋律,起初听起来很遥远,接着越来越强烈,成为主旋律。马丁渴望通过一种绝望而冲动的方式表达自我,这是对流亡者命运的浪漫挑战。他需要牺牲来履行职责——回到俄罗斯。即使注定死亡,也不是在思想和意志的沉睡中死去,而是要以清醒的意识向时代和人民传达即将消亡的、纯粹深刻的忏悔之声。后来纳博科夫在其文章《普希金,或真实与似真实》中写道:只有那些安于一隅的庸人才认为旅行不再揭开任何秘密;事实上,山风一如既往地搅动着血液,冒着高尚的危险而死亡一直是人类的荣誉法则。一种神秘又不可抗拒的对俄罗斯的追随、对危险与救赎般死亡的渴望构成了《光荣》的情感基础。
“光荣”一词在小说中出现两次。第一次是马丁驳斥二十世纪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让人极度厌恶的“黑色小兽”的想法,他认为没有一个时代有这样的辉煌,这样的豪勇,这样的工程。这是对作为二十世纪特征的“光荣”的概括性判断,表明马丁热爱着他的“浪漫时代”。第二次是在小说最后形容马丁。因此,主人公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他所处时代的俄国侨民总体思潮的表达。正是在马丁前往俄国边境后,每个人才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真正的人格尺度,意识到他做了一件英勇的事。显然,他的个人举动已成为集体愿望的实现。
作为流亡作家的纳博科夫,在其早期作品中不断流露出返乡的冲动和对祖国未来命运的关切。随着创作时间推移,他逐渐告别现实层面的主题,转而探索形而上,借助“审美狂喜”打造自己的“时间之狱”。乡愁流淌为对永恒而纯粹的时间的追求。
而在《光荣》创作时期,纳博科夫饱尝流亡滋味,用诗性动人的语言表达出对故国的深深追忆。只有实际的回乡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治愈乡愁的病痛。他以想象性的创作补救心理上的缺失,借主人公的壮举完成重返故土的心愿。正如儿时一段乘坐火车的经历对当时年幼的纳博科夫而言成为一场还乡的预演:不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衣锦还乡的预演,而是在我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不断出现的还乡梦的预演。
主人公浪漫时代的壮举在于他完成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俄国人于现世分散中都渴望回到俄罗斯的愿景,尽管这项事业充满了不切实际与致命危险。因此,小说中出现了乐观的悲情:青年人的壮举如同一道金光冲破了俄国侨民普遍无望与忧愁的层层乌云。而《光荣》的情感呐喊映射在这道光芒中透出耀眼的色彩。
二、火车:精神进化的马
火车与马丁各种旅行联系在一起,承载着揭示主人公成长变化与诠释主题的作用。它具备一种神秘特质,与马丁探索未知的精神与挑战自我的勇气相通。因此,对火车意象的语义情节分析能更加阐明小说的深刻情感。
纳博科夫主要运用隐喻的手段塑造火车形象。其中最典型的隐喻是火车-马。
小说刚开始马丁母亲想象儿子在内战最激烈时回到圣彼得堡,在想象中看到了“нанеизвестнойстанции разорвалсяснаряд,паровозвсталнадыбы(一发炮弹落在某个不知名的车站里爆炸了,把火车头掀翻在地)”。“встатьнадыбы(前蹄腾起)”多用于描述马的行为,该语境下火车像一匹受惊的马。此外,“надыбы(直立)”亦有词意“顽强反对”,这种反对不仅来自火车本身(它已有自己的性格意志),也来自主人公,马丁宛如驯马师:尽管他不理解周围环境,其行为也似乎无意义,但在小说最后他仍然试图制服火车,将其引向俄罗斯。
纳博科夫将火车看作马也体现在对其运动与声音的隐喻性描述:“погодяпоезддвинулс я,новскорестал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издавдлинный,тихосвистящи йвздохоблегчения(火车开始动弹,却又马上长叹一声,夹着一声咝咝的轻响,松了口气)”“поездидётплавнее,развязнее,словноприноровился к бытромубгу(火车开得更为平稳顺畅,仿佛已适应了快速奔跑)”。火车运行被喻为跑步,刹车和释放蒸汽的嘶嘶声被喻为叹息。在“вздох(叹气)”后加入“облегчения(轻松)”,表达了这种叹息的主观原因——长途旅程后的疲劳;用“развязнее(毫不拘束地)”修饰“идёт(行驶)”使得到休养后的火车更自由地行进,并体现出“развязнее”的内在形式:“бытьразвязанным(被解开)”。这使人再次联想到卸下枷锁的马与自在行驶的火车。
马丁最早乘坐火车前往海边与父亲有关,因此在小说的童话语境中,可理解为从父亲那里收到一匹神奇的马作为礼物。父亲在故事开始前就已去世,只存在于主人公的记忆,所以他被视为来世的捐赠者,其礼物具有神奇魔力。正是童话般的马(火车)将马丁送往远方,甚至成为从一个现实世界渗透到另一个现实世界的手段。而这样的现实世界就是俄罗斯和欧洲,从另一视角也可将两者任何一个看作是彼岸世界。
夜间神秘灯火也与童话般的马有关。马丁只能透过火车窗户看到这些山丘上的灯火,当他跳下火车试图走近它们时却无果。马丁停留了几个月的莫利尼亚克并不是这些灯火的源头。作者暗示了只有马丁能看见这些奇异的灯火,它们只在火车行驶时存在。在童话语境下,这些灯火就是火花,热情似火的马(火车)载着马丁飞奔而来,将身上的火花洒落四周。
马丁渴望通过一系列考验学习驾驭这样一匹马。驾驶火车是他童年起就有的梦想,在这梦想的思潮中他沉入了梦乡:闭眼想象到自己驾驶的特快列车,他的内心就会依然安宁,仿佛被净化了。他儿时不止一次玩起控制火车的游戏:窗边可折叠的坐板让他能控制火车的布带。此处“布带”即为驭马的缰绳。
马丁并不像达尔文那样让自己的马止步:达尔文庄重地拉下紧急刹车索,火车发出疼痛的呻吟后停住了。达尔文也让自己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止步了;让生命进程、如他名字所言的进化止步了。纳博科夫甚至强调了他的退化:在马丁远赴边境前去拜访达尔文时,他得意扬扬,口中都是取得的成就与薪水,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可见,马(火车)的止步会导致一个人停滞退化,使其沉浸在物欲享受中。然而,纳博科夫用“止步”一词意味着达尔文这种状态是暂时的。在获知马丁的壮举后,达尔文逐渐从精神停滞中走出:起初他心里难以平静,这种感觉近来在他身上少有,几天后他感到一丝诡异的震惊。飞驰的马洒落的火花能够点燃人们灵魂中即将熄灭的火。马丁正是带着这种能赋予生命的力量进入死气沉沉的俄罗斯,他的壮举承载着复活祖国精神的意义。
小说结尾马丁终于掌控了马(火车)并将其引向俄罗斯。在他与达尔文的最后通话中两次出现“我的火车”,强调了马丁对自己的马和对命运的控制权,这种权力是他成长蜕变、突破自我的结果。
火车-马的隐喻诠释了马丁的内心成长与对使命的坚定追求,同时驳斥了马丁行为无法被称为光荣的肤浅观念。火车在马丁的生活轨迹中如影随形,他从童年的自娱自乐、控制布带到青年时期驯服这匹“马”、孤身闯入佐尔兰德,从无知无觉到听从内心召唤,火车象征流亡者的精神进化,壮举的发生有迹可循,他无畏死亡,义无反顾回到俄罗斯,去寻找光荣,爱,对大地的温情和千万种相当神秘的感觉。
俄罗斯文学中火车的意象意义有着显著的演变轨迹。19世纪创作中的火车多被用于“灾难”“怪物”“地狱”等负面形象,以《安娜·卡列尼娜》中象征闯入俄罗斯的欧洲文明、光明与希望的对立统一的火车为代表,传递出西方先进文明与俄罗斯宗法田园的紧张冲突。20世纪初火车承载着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流亡异乡的俄国侨民对故国的温情回忆与浓重乡愁,《光荣》中引领主人公踏上返回故土路程的火车实现了流亡者的精神进化。近现代文学中火车形象转向正面,它书写了通往新世界、新社会的理想之路,如在列昂诺夫《贼》一书中火车象征着新的乌托邦社会,它带领人们逃离痛苦,奔向更美好的未来,社会的进步与人们乐观的生活态度流淌在字里行间。
纳博科夫将独特的火车意象嵌入流亡生涯的创作中,传达出难以返回故国的乡愁意识与对“失落的家园”的诗性想象。
三、道路:奔赴使命的人生历程
《光荣》中道路象征主人公奔赴使命的人生历程。它连接了现实的三个层面:主人公不仅奔跑在梦想之路,也在现实世界的旅途中穿行,最终走向儿童房墙上的水彩画里带有童话色彩的蜿蜒小径。
马丁的这条人生道路不断向上,他克服障碍如同征服高峰。山作为神圣之地,象征信念、坚守与不可摧毁的生命力量。主人公三次上山,情节递进反映出其精神变化。征服高峰的过程也是他直面恐惧、改变生活态度并找寻使命的过程。第一次尝试登顶,岩石不理会马丁的抱怨软弱,深渊朝他发出邀请。几天后他忍不住又去攀爬,但在那道悬崖面前又退缩了。决定远赴佐尔兰德时,他想到还有一笔良心的债务要清偿,达到那块熟悉的岩石后,他像在执行心中一项坚定的命令,移动脚步并安全返回。人生旅途的艰辛和非法探险的准备使其性格变得坚韧,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山终于接受了他。对高峰的勇敢征服成为主人公的精神启蒙。
这条道路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画般神秘蜿蜒在树木之间,沙沙作响,它缓缓展开,引诱着马丁,使他胸中涌起神奇而迫切的冲动,只要有了它,就觉得自己不会虚度此生。祖国,是主人公命运的定向标。他沿着这条路走,没有选择的自由,并有时会问自己是不是有天夜里真的从床上跳进了画中,这段经历是不是他那充满幸福和痛苦的人生旅途的起点。最后马丁决定逃往俄罗斯,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童年梦想的实现。在画有那条诱人小径的婴儿床上探险的念头萌芽迸发。马丁的人生从对道路的描述开始,整部小说也以这条幽暗的小径结束。
道路充当两个空间的纽带,连接起马丁安逸的国外生活与“失落的家园”,连接起想象的世界与现实。同时它见证了马丁的人生历程,见证他逃离流亡生活的空虚,认识到返回故国的使命。主人公如同一列快车,沿着这条道路克服重重阻碍,努力奔向心目中最后一站——曾经被遗弃的俄罗斯。而纳博科夫的乡愁情怀也被安放在这条延伸向久别故土的小径,随它奔赴远方。
结语
与纳博科夫其他作品相比,评论界对《光荣》研究态度冷淡,几乎无人问津。然而《光荣》虽缺少作者成熟时期小说的复杂细节与精妙技巧,但其文学魅力恰在于纳博科夫以想象性的艺术形式,借主人公越过俄罗斯边境的壮举完成返回故土的愿望。
是什么力量吸引马丁越界而死,纳博科夫没有直接解释,而是用细小的暗示与完整的意象系统传达。火车如同一匹见证了马丁精神进化的马,被赋予童话般的色彩与探索未知、勇于挑战的意义,马丁驯服它的同时也完成了内心自我成长。道路则象征主人公奔赴使命的人生历程,展示其神秘的浪漫世界和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理想追求。在解读其象征意义后,马丁为了祖国与信念、坚定履行自己的职责——返回俄罗斯的壮举就在这浪漫激情中闪耀出在文学高度上应有的荣光。
与其创作后期走向形而上的、自我放逐式的精神流亡相比,此时的纳博科夫仍处在远离故土的深思愁绪与追忆往昔的乡愁情怀里。在《光荣》的艺术创作中,主人公最终完成了崇高的使命,实现了纳博科夫回到故国的深切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