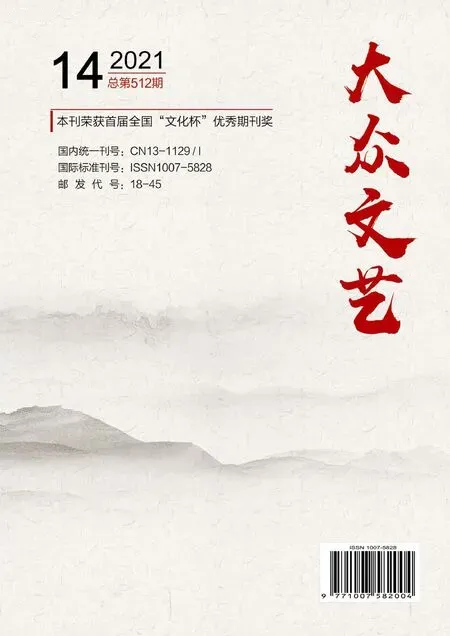失落与重建:论《宠儿》中的色彩隐喻
杨 涵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00)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性,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通过作品让黑人得以发声。《宠儿》是她的第五部作品,并夺得了1988年的普利策奖。这部小说重述了那段沉重而屈辱的黑奴历史,将沉痛的创伤记忆以三代黑人女性的故事展开叙述,直面那段蓄奴制的历史。许多学者对《宠儿》中的记忆、文化和历史也进行了研究,安妮·科宁(Anne Koenen)认为宠儿是黑奴鬼魂的回归,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肯定了小说作为创伤文学文本的研究价值和地位。色彩作为小说中不可忽视的要素还并没有太多的被提及和研究,但结合文本细读可以看出色彩在小说叙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谈道了小说中色彩的重要性,如谢丽尔·霍尔(Cheryl Hall)把《宠儿》中颜色的使用看作是重复主题的一部分。小说中所描绘的许多细节都能看出文本主题与颜色紧紧缠绕。在这些复杂的色彩运用中,红色是使用最为连贯和频繁的颜色。本文以解读小说中的红色为主,结合对其他颜色的阐释,来理解黑奴创伤记忆的失落与重建。
一、色彩隐喻、创伤理论与《宠儿》
戴维·洛奇曾指出,“所有的声音、颜色、形式,或者因为它们固有的力量,或者因为丰富的联想,都能激起那种虽然难以言喻但确实无误的感情。”也就是说,色彩作为绘画中的主要部分,具有隐喻性。莫里森的《宠儿》中色彩的隐喻基本上遵循了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语言隐喻性用法在文本中的两种模式,意义上使用象征手法,结构上使用重复或相同类型的色彩词汇促使小说主题不断再现。比如不断出现“红心”“白色楼梯”等带有颜色的词汇,这些词汇所包含的隐喻性让小说中对蓄奴历史的描写更为鲜明,并且在重复色彩的同时也是在重述这段美国黑人不愿提及甚至刻意忘却的沉痛记忆,为被掩埋的历史与记忆发声。
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将创伤定义为一种没有经历过的事件而只是简单地被记录下来的事件,因为创伤对发生者的影响是压倒性的。并且她认为这一现象的典型反应是有一种重复的强迫行为,一种不断回到创伤事件的冲动。这与《宠儿》中的人物行为相符,如贝比·萨格斯在临死前也在不断想要找不同颜色的东西,“既然她认识到死亡偏偏不是遗忘,她便用残余的一点精力来玩味颜色。”“给我来点淡紫,要是你有的话,要是没有,就粉红吧。”以及保罗·D不断回忆起和说道“‘红心、红心,’一遍又一遍。”巴里·科恩(Barry Cohen)在他对创伤经历阐述中提到,受创伤的个体渴望通过隐喻和意向来理解他们的世界。在前人对隐喻和创伤的研究基础上可以看出,色彩隐喻与创伤记忆有着显著的联系。因此,对《宠儿》中色彩隐喻的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小说主题和挖掘其中蕴藏的巨大能量。
二、猩红之色:血淋淋的创伤记忆
红色作为《宠儿》中最为频繁出现的颜色,在小说中以直白的流血场景或其他各种形式出现,象征着奴隶制及与种族主义暴力相关的创伤记忆。小说中对红色血液的描写占据了大部分暴力场景。如对塞丝背上的红色“樱桃树”的描写,“是棵树。一棵苦樱桃树。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你背上有一整棵树,正开花呢。我也挨过鞭子,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样子。”这是白人女孩爱弥·丹芙帮助塞丝时看到她背上被鞭打后的带着血迹的伤痕所发出的感叹。这些伤痕是在“学校老师”和他的两个侄子将塞丝强暴后,塞丝把他们的恶行告诉了奴隶主加纳夫人,当“学校老师”知道后气急败坏用鞭子将怀孕中的塞丝毒打了一顿留下的。以及当塞丝最终成功逃离甜蜜之家来到辛辛那提的124号房时,贝比·萨格斯注意到“鲜血的玫瑰盛开在塞丝肩膀的毯子上。”“通红通红”的“樱桃树”和“玫瑰”都是塞丝受到种族主义暴力以及奴隶制压迫后留下的骇人印记。遭受侵犯后的塞丝以为能通过告知奴隶主受到庇护和得到正义的支持,然而迎来的却是更加残暴的毒打。
红色在这中间被用来记录和放大奴隶制期间美国黑人受到的痛苦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能够传染到其他角色,引发他们共同的痛苦记忆。除了贝比·萨格斯为塞丝清理伤口时感受到的苦楚,还有保罗·D和塞丝的丈夫黑尔。黑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强暴,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崩溃,“我的丈夫蹲在搅乳机旁边抹牛油,抹得满脸尽是牛油疙瘩。”保罗·D在看到和听到塞丝背上“树”的故事后,也陷入了对自己遭遇的沉思。瓦莱丽·史密斯(Valerie Smith)认为,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深深地收到奴隶制经历的影响,时间无法将他们与它的恐怖分开,也无法消除它的影响。塞丝和其他几个人物都是残暴奴隶制的共同经历者,深受这种创伤经历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以红色为特征的创伤记忆。
小说将表现残酷奴隶制情节的地点设定在乔治亚州,这个地点不仅位于南方深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其土地的颜色——“红土”。如在叙述保罗·D到达战俘营时,文中指出在夜间作为囚犯牢房的盒子被放置在“五英尺深,五英尺宽”的“红土”沟,“匣子有道栅栏门...打开后就能看到三面墙和红土做成的屋顶。”对保罗·D和其他无数的黑人奴隶的虐待行为就发生在“红土”上,红色成了奴隶制在精神和身体上暴行的象征。被奴役期间,保罗·D对“先生”这只鸡的红冠格外在意,“冠子有我巴掌那么大,通红通红的。”“‘先生’它看起来那么样自由,比我强,比我更壮实,更厉害。”甚至他将自己的心脏与鸡冠对比,“在他胸口埋藏的烟草罐里,曾经有一颗鲜红的心跳动...而知道他的胸膛里没有一颗像‘先生’的鸡冠一样鲜红的心在跳荡。”保罗·D的经历中,红色代表着屈辱和不自由。他将人性的“红心”与动物性的“红冠”对比,并且认为自己甚至没有一只鸡强大和自由,可以看出他深受奴隶制的压迫和影响,而他和众多美国黑人的创伤记忆已经内化表达为红色。
奴隶制的记忆和历史带着血红的印记,作者在小说中给了太多的例证。保罗·D在黎津河岸抓住的“红绸带”,“系着一缕湿淋淋的卷发,上面还粘着一小片头皮。”这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血腥场景,就像塞丝在给小女儿丹芙讲故事时所说,“我相信这孩子的太太将会在俄亥俄河血腥的岸上,在野葱中间一命呜呼。”“他希望她紧抓住蓝色、黄色或者绿色,就是别盯上红色。”红色作为血腥的印记成了他们——奴隶制受害者共同的创伤记忆,并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他们,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对这一记忆的抵触和刻意遗忘。
三、无言之色:失落的创伤记忆
在鲜红的创伤经历中,黑奴对于自己的惨痛遭遇处于一种无声和被动的失语状态。在塞丝被困木棚到她杀死自己孩子一系列情节中,整个黑人群体都陷入了主动和被动的沉默状态。当猎奴者、“学校老师”和侄子出现在124号房附近,他们遇到了六七个黑人,但黑人社群中没有人向塞丝一家人通风报信,大家都选择了沉默。在面对施暴者时,塞丝也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抓住自己的孩子们,跑到木棚里想要杀死他们。而在这一无声场景中,不仅仅是塞丝的无声,还有范围更广的沉默。“一个帽子上戴花”的黑人“也一动不动地站着”,“侄子和猎奴者和他一起退了出来……顶着烈日骑马走了。”整个场景陷入无声,不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压迫的黑奴们都被血红的场面所震惊,“黑鬼小姑娘的眼睛在血淋淋的手指缝里瞪着,那只手扶助她的脑袋,好让它不掉下来。”红色成了死亡的象征,也是黑奴在奴隶制压迫下做出极端选择——为了让后代不再受奴隶制的折磨宁愿亲手将其杀死——的缩影。从此124号房便与婴儿鬼魂相缠绕,并与红色紧密相关。文中多次提到保罗·D在进入这座房子时“迈进门,跌入一片颤动的红光”。血红的杀婴行为牵动着每一个经历了奴隶制压迫的黑人的心,让人感受到沉重和抑郁。
芭芭拉·斯佩曼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在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后,由于人类心理的保护机制,受害者的创伤性记忆会被压抑到意识层面以下或被扭曲,使人很难回忆起来,但是这种记忆也在发挥着作用,影响着当事者的行为和情绪。塞丝在亲手杀掉自己的女儿后,为了让雕刻师把女儿的名字刻在墓碑上,她只能选择出卖自己身体,“她女儿墓石上的粉红色颗粒是她记得的最后一样颜色”“仿佛有一天她看见了红色的婴儿的血,另一天看见了粉红色的墓石的颗粒,色彩就到此为止了。”从红色到粉红色颗粒的过渡,塞丝不愿再面对这段记忆并且感知不到其他颜色,其实也是她逃避和刻意忘却这段记忆和惨痛历史的表现。
小说中保罗·D被囚禁在“红土”乔治亚州期间所表现出的行为也展现了他失语的状态。早上被点名时,他们不允许说话,“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说话。”面对看守的问话时,也只能简要回答。“‘想吃早餐吗,黑鬼?’‘是,先生。’”“‘饿了,黑鬼?’‘是,先生。’”他们被剥夺了语言的权利,处在了沉默的境地,一切所遭受的灾难都由这一代人默默承受着。红色的创伤记忆让美国黑人处于失语的状态,进而使他们选择了刻意遗忘然后内化为自身不断受压迫的形象,失去了为民族沉重记忆和历史发声的力量;同时,压迫者也希望将自己的罪恶行径掩埋而选择噤声,最终导致了这段历史的暂时失落。
四、希望之色:记忆的传递
作为唯一没有经历奴隶制度压迫的角色,丹芙承担起了治愈创伤和重构种族身份的部分。她没有在甜蜜之家待过,但她依然接受着上一代人的影响。通过塞丝包含色彩隐喻的记忆讲述,丹芙了解到关于奴隶制的历史以及黑人所遭受的经历,这是一种创伤记忆向下一代的传递和转移。她与上一代红色记忆的连接还在于“丹芙就这姐姐的血喝了妈妈的奶。”这是一种不可能断掉的延续和传承,她也形成了创伤跨代传递的集合体。在了解到关于母亲杀婴的故事真相后,丹芙失去了听力,这也是她接受和消化带着血红色记忆而造成的创伤。多米尼克·卡拉普(DominickLaCapra)提出,重复性地体验创伤,创伤将逐渐被记忆消解。因此,丹芙在与宠儿的交流中不断重述母亲和祖母讲述给自己的话,来重构记忆和身份。
色彩对于丹芙来说也代表了一种治愈和重建的可能性。比如丹芙对被子上两块橙色补丁的关注,并且迫切希望宠儿也能注意到。在宠儿花了三天才注意到橙色补丁后,“丹芙非常满意”,因为那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在124号房这个缺乏色彩和充满苦痛回忆的地方,丹芙渴望颜色,“橙色的补丁显得野性十足——好像伤口里的勃勃生气。”而宠儿在丹芙的概念里就是她去世的姐姐,承载着过去血红色的创伤记忆,她希望宠儿能够看到世界上美好而有活力的部分来消解过去的抑郁与沉默。在塞丝跟丹芙的讲述中,提到了白人姑娘爱弥对塞丝的帮助,以及爱弥对红色天鹅绒的向往。说明在创伤记忆的代际讲述传递中,红色的隐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色彩不仅代表那段创伤记忆,还代表着未来的生命与希望。这是新旧两代黑人对种族未来命运寄予的希望——创伤能够被治愈以及黑人能够为自己经历过的苦痛历史勇敢发声,重建失落的创伤记忆。
结语
《宠儿》中的色彩描写有着深刻的隐喻,与美国黑人的创伤记忆紧密联系。通过对小说中颜色的解读,可以进一步理解小说所蕴藏的深刻主题以及托妮·莫里森为黑人种族发出的强有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