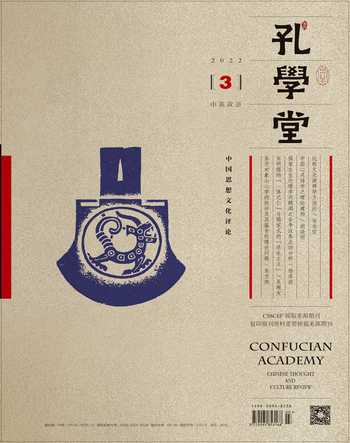“两头明,中间暗”
摘要:朱子对象山之学的批评所涉范围甚广,其中一种重要的说法则认为象山说话常常是“两头明,中间暗”,并以此指象山之学为禅学。对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朱子所谓的“两头明,中间暗”具体所指为何?象山之学毕竟如何表现为“两头明,中间暗”?假如朱子的批评有所针对,则由其针对所透露出来的象山之学的理论问题又是什么?审如是,我们有必要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说明朱子批评的含义,二是顺朱子的批评而呈现象山学之教法上的特点,最后是提出一点拓展性研究,亦即站在当今哲学的立场显示象山之学所可能存在的理论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反省。
关键词:朱子 象山 “中间暗” 知识 确定性
作者东方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朱子对象山的批评所涉范围甚广,存留的文献繁多,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难以计数,其中,常为学者所征引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说法,便是朱子认为,“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应该说,朱子的这种批评指义清晰,偏重于理论上的剖析,谓其“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然而,朱子对象山的批评还有另一种说法,谓象山说话“两头明,中间暗”,“暗”就是不说破,不说破“便是禅”;又说“陆子静说道理,有个黑腰子”。很明显,朱子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偏重于学问性质和教法上的判定,故直指陆象山之学为禅学,而此一种说法似乎尤其吃紧,我们从牟宗三不厌其烦的辩难中不难看出。对此我们要问,朱子所谓的“两头明,中间暗”具体所指为何?象山之学毕竟如何表现为“两头明,中间暗”?假如朱子的批评有所针对,则由其针对所透露出来的象山之学的理论问题又是什么?审如是,本文的目的有三,一是说明朱子批评的含义,二是顺朱子的批评而呈现象山学之教法上的特点,三是提出一点拓展性研究,亦即站在当今哲学的立场显示象山之学所可能存在的理论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反省。
一、为何是“中间暗”? [见英文版第57页,下同]
朱子批评象山之学“两头明,中间暗”的原文如下: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或问:“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
此条为辅广所录,时在甲寅亦即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朱子65岁以后,另一条谓象山说道理“有个黑腰子”,其原文是这样的:
“极高明”,须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则将流入于佛老之学。……某尝说,陆子静说道理,有个黑腰子。其初说得澜翻,极是好听,少间到那紧处时,又却藏了不说,又别寻一个头绪澜翻起来,所以人都捉他那紧处不著。
此条为黄义刚所录,时在癸丑亦即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朱子64岁以后。以上两条可断为朱子晚年所论,而且皆指象山之学为佛禅之学。因此,以“两头明,中间暗”“有个黑腰子”来比喻象山之学在教法上为禅学是朱子所以如此立说的关键理由。
今案,朱子谓象山之学近禅或是禅乃是其一贯的看法,但其中又大体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朱子早期目象山似禅可以“鹅湖之会”为中心,鹅湖之前,朱子只是在传闻中得象山之学近禅,淳熙元年甲午(1174,朱子45岁),朱子有《答吕子约书》,云:“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竞相祖习,恐误后生。恨不识之,不得深扣其说,因献所疑也。”鹅湖之会后,朱子经由对象山之接触,在赞赏其气象的同时,对其学也深致疑虑。淳熙二年乙未(1175),时象山三十七岁,《年谱》记云:“吕伯恭约先生与季兄复斋,会朱元晦诸公于信之鹅湖寺。”是年,朱子有《答张敬夫书》云:“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而不自知耳。”由此看来,朱子早期虽对象山之学不满,但似尚未坐实其为禅学,且有融通之意。晚期朱陆交恶乃以淳熙十年癸卯(1183)朱子为曹立之作墓表为契机,而以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朱子57岁)《答程正思》第十六书为分界,朱子对象山学的态度已不复唯阿,变至如王白田所谓的“诵言攻之”,朱子云:“盖缘旧日曾学禅宗,故于彼说虽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说得遮前掩后,未尽见其底蕴。……去冬因其徒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自此乃始显然鸣鼓攻之,不复为前日之唯阿矣。”朱子自此以后至晚年对象山之学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云:“若陆氏之学……此煞坏学者。某老矣,日月无多。方待不说破来,又恐后人错以某之学亦与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说破。某道他断然是异端!断然是曲学!断然非圣人之道!”
朱子晚年断言象山之学是禅学,是祸害学者的“异端”“曲学”,其间所涉问题繁复,非本文所欲一一辨明者。然而,平实地说,朱子之攻象山虽语词、气态刚厉凌逼,但其如此主张实非说象山之学之本质为禅学,多是指其在为学教人的方式上似禅。今以“中间暗”“有个黑腰子”喻说象山之学,前者谓其“不说破”,后者谓其“藏了不说”,意思大体相同;但“两头明”究竟所指为何,朱子似未有明确的说明。牟宗三谓:“实则所谓‘两头明只是一方挥斥闲议论之失,一方令归朴实之得,这得失两头甚为分明。”又谓:“至于‘两头明则是指孟子见道的这一头,与朱夫子不见道的那一头。朱夫子也承认陆象山对他的批评,所以他认为陆象山批评他的那一面,以及令人所归到的那一面,都很清楚,这就是他所谓的两头明。”牟宗三此说乃其自己站在象山立场所作的解释,非朱子之意。今观朱子著述,“两头”一说多有,俱為比喻描状之词,如《论语集注》卷五对《子罕》篇“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句,朱子注云:“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由此推论,朱子谓象山“两头明”大意当指象山学之本原与目的说,本原指的是四端之心,目的是成圣成贤,此两头象山言之凿凿,朱子亦无能置疑;而所谓“中间暗”“黑腰子”乃就如何借由恰当的方法、确定的传达途径以表现由本原到目的的过程而言,亦即象山“不说破”的“非分解”的表示方式,朱子于此斥之为禅,此从朱子《文集》和《语类》卷一百〇四、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四等诸多论述中不难看出。朱子对此的相关言说甚多,今以《语类》卷一百二十四《陆氏》为例,朱子谓象山学之“暗”和“黑”的意思大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象山之说“无定常”,无定常乃所以“暗”。所谓“定常”是一个总说,包括多层含义,而重心在于认为成德之学当有确定的传达途径,有必要的次第、规则,故朱子云“圣贤教人有定本”,而象山之学则似禅家教人无定,“子静之说无定常,要云今日之说自如此,明日之说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可知是他所学所说尽是杜撰,都不依见成格法。他应事也只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当然,今日之说如此,明日之说如彼,并不一定是杜撰,盖本心之发,如水银洒地,随遇随应,随应随润。然而,朱子谓象山之学“无定常”毕竟包含什么内容?具体所指为何?依朱子,其一是不著言语,排斥分解性言说。朱子云:“陆子静不著言语……陆只鹘突说过。”“鹘突”即模糊、疑惑不定之意,象山不以清晰确定的语言表达成德之方法、路径,此乃所以“暗”和“黑”也。朱子又云:“吾儒头项多,思量着得人头痹,似陆子静样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书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说我这道理,从头理会过,更好。”象山无心细看圣贤文字:“凡说未得处,便将个硬说辟倒了,不消看。”其二是“跳踯”,意即教法上躐等跳跃,不落阶级,泯除难易远近,无法示人以确定的循序的阶梯和轨道。其实,在朱子,“跳踯”和“鹘突”可以理解为一个钱币的两个方面。朱子云:“近来一种议论,只是跳踯。初则两三步做一步,甚则十数步作一步,又甚则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学之者皆颠狂。”朱子又云:“陆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举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得?”此处朱子仍是用比喻性的说法,所谓“那人既无资送”非谓人无成德之资、之本,而是指经由修养有效地到达目的的途径和方法,此处若“无”,即朱子所谓的“中间暗”“黑腰子”。最后,与象山攻击朱子一样,朱子也认为象山立说乃是“假借”,所不同的是,在象山看来,朱子是假圣人之言以说己意;而在朱子看来,象山则是假己意以说圣人之言。朱子云:“陆子静之学,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看是甚文字,不过假借以说其胸中所见者耳。据其所见,本不须圣人文字得。他却须要以圣人文字说者,此正如贩盐者,上面须得数片鲞鱼遮盖,方过得关津,不被人捉了耳。”朱子此说,意指象山之学为了防人耳目,乃假借圣人之言,说自己的意见。
其次,象山之学以悟代证,拒斥一切议论和意见,导致“默然无言”“寂然无思”。无言无思、默然寂然乃让人不得其意,不明所以而为“暗”。“暗”是对着“明”而言的,而此处所谓“明”依朱子的功夫教法,乃在于借由认知、讲说、议论、辨明(主要是对着圣人之经典而言)达成客观、公共的道理和节次以便让人有所持循,盖若只任单个人之直觉体悟,则其体悟固然可直趋本根,涤除阶级、不着言诠以至瞑迹显本,但此个人所体悟者究竟是“廓然”之本心抑或是“懵然”之私意?如何防止妄拟情缘为妙用?又如何识别参情识、荡虚玄于本心本体?此类问题似尚需讲究,而依朱子,象山教人“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若识得一个心了,万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如是者,象山乃排斥一切议论、意见,“今陆氏只是要自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若别人说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别人说出,便指为义外”。故朱子云:“某向与子静说话,子静以为意见。某曰:‘邪意见不可有,正意见不可无。子静说:‘此是闲议论。某曰:‘闲议论不可议论,合议论则不可不议论。……‘他之无意见,则是不理会理,只是胡撞将去。若无意见,成什么人在这里!”“既不尚议论,则是默然无言而已;既不贵意见,则是寂然无思而已。圣门学问,不应如此。若曰偏议论、私意见,则可去,不当概以议论意见为可去也。”又云:“某谓除去不好底意见则可,若好底意见,须是存留。……圣贤之学,如一条大路,甚次第分明。……今只理会除意见,安知除意见之心,又非所谓意见乎?”依朱子,若去除一切思索讲论,群疑胸塞,都没分晓,其学则不免“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堕而为“陷溺人之深坑”。
朱子对象山学之“中间暗”的批评无疑是从其所理解的“圣门学问”出发的,且其所涉论旨林林总总,非上述简说所能尽,但约其核心则主要在不着语言,主直觉之悟,排斥一切议论和意见,在作用和表现方式上有类于禅。
然而,我们说过,牟宗三曾在数本论著中对朱子斥象山之学“中间暗”而为禅作了全面的辯护,其中又尤以《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为详。围绕朱子“中间暗”的批评,综合牟宗三的相关说法,我们大体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牟宗三在区分朱陆之学之“端绪得失”的前提下认为,朱子说象山之学“中间暗”“不说破”指的是象山“非分解”的表示,而非分解的表示不是禅。象山继承孟子,走的不是分解的路,他用非分解的方法表达,分解的义理在孟子,他的假定都在孟子,但因象山取“非分解以指点”的方式,“遂令朱子误想其为禅。其实这与禅何干?”所谓“中间暗”“只是因为于朴实之得以‘非分解方式来指点,指归于孟子,令人就实处来理会,便足够,故不须再从事于分解,盖孟子已说破,已分解地言之矣,何须再分解?又何暗之有?”“所以在此,孟子的分析就是他的分析,孟子的那些分别说,就是陆象山所肯定的分别说。”
其二,“陆象山在某一方面虽然用非分解的方式,可是在某一方面,仍然用的是分解的方式,这与禅宗所用的方式还是不同。”禅家之风格是当我们一旦归于朴实之途,进一步想把本心即理之“本心”不起一毫作意与执着,如如地呈现之时,便有禅之风格,此即禅家所谓“无心为道”,亦即是作用义的无心,不是存有论的无心。要说禅,只有在此作用义的无心上始可说,但此义可在明道、阳明及龙溪、近溪处见,且此作用义之无心的境界乃是共法,非佛家之专利;即便如此,象山也尚未进至此义,尚未有这种禅的表现风格,“故朱子说他是禅根本是误想,而且是模糊仿佛的联想”。
其三,是挥斥“闲议论”。象山讲学宗旨在发明本心,去除一切虚说浮论,归于道德实践而不在追求知识,盖实事实理顺本心自律而发,本就坦然明白,读书讲论或分解的表示若不相应于本心的发明,则为粘牙嚼舌,徒增葛藤,“知识本身自有其独立意义,但不必与道德实践有直接而本质的相干”,“象山之挥斥议论不是挥斥此种知识本身,乃是挥斥依知识之路讲道德。依知识之路讲道德,即成为‘闲议论,不是知识本身为‘闲议论”。
总之,牟宗三认为,在象山那里,若能就本心即理之第一义处实落下手用功,则“其语言不待分解亦自明”,因为“分解无论如何重要,总属第二义”。故象山以启发、指点、训诫、遮拨的方式来豁醒人,“因为他一眼看到孟子所昭显者皆是实事实理,坦然明白,只须吾人以真生命顶上去,不落于虚见虚说,不落于文字纠缠粘牙嚼舌之闲议论,便自然能洞悟到那坦然明白之实事实理而内外洞朗,进而更能真切相应地呈现之而挺立吾人之人品。”
二、如何是“中间暗”? [60]
不难看到,牟宗三力辩象山“非分解”的表示不是禅,而只是朱子的“模糊仿佛的联想”;此种“非分解”的表示非但不“暗”、不“黑”,反而是“坦然明白”。牟宗三之如此辩护乃基于一重要的理论判断前提,此即朱陆之间有关第一義或“端绪”上的“正当”与“不正当”之分,这无疑是另一个独立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即便“端绪”或第一义已明,分解地展示,认知、讲说、议论是否还有必要?是否可以一概加以挥斥?即便象山的义理在孟子处已分解、已说破,至象山教人时是否即可以无需分解、无需说破?倘若如此教人,其是否即能使人得其“坦然明白”?
即便就着牟宗三的疏解而言,议论、讲说之分解地表示相对于第一义而言虽落第二义,但却依然不可忽视,依然为第一义之内在要求,说其为第二义乃只是比较之权说。对象山心学而言,此处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象山主脱落习染,直悟本心,功夫固是直截简易,然亦会因此简易而驯至下半截之无危无惧,乃至落于指情缘为妙用,簸弄精魂,玩弄光景;另一是本心之理虽亭当活泼,圆满自足,当恻隐自恻隐,当羞恶自羞恶,是非在前,自能辨之,但若无分解地表示,则此本心之理仍不足于应众机以适情境、时代变化之需,因情之不同,时之不同乃至所因应的具体的人、物、事之不同,则必当有对此情、此时、此人、物、事之认知之分解以呈现此心此理,以泛应曲当,此理之易明者,亦为牟宗三所意许,而象山对此亦非无所知觉。《语录》记象山云:“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然此心此理,万世一揆也。”依象山,若千古圣贤同堂而坐,其议论作为也必不能尽同,然其安身立命之理,必无毫发之差。象山强调此心此理万世一揆,此端绪上必当先立者,故一切功夫、一切议论和分解必当在发明本心上实落下手,凡外于此者则为闲言闲议论,即此而言,象山自无排斥议论、分解之理,亦无拒斥读书、讲说之理,盖象山已明确认识到,即便“圣贤”同堂合席,必也无“尽合之理”。然而,何故万世一揆之心之理,即便圣贤也不能尽合?象山于此虽在理上认识到读书、讲论的必要,然其教人多在扭转朱子上用心用力,更多地强调本心之“同”,强调当恻隐“自”恻隐,是非在前,“自”能辨之的“自”,而对于为何不能“尽合”的原因和道理欠缺足够的、必要的条陈和说明;不仅如此,象山教人多诉诸当事人自己的体悟,或以当机指点的方式让当事人豁醒,而对于成德过程中的节目、次第、规则,对于各主体心灵间确定的传达渠道亦即形式型知识的确立等等并不着力关心,以致常使学者“每闻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
其实,在象山在世时,便因其教人“空腹高心”,脱略文字,主简易直绝,直趋本根而被时人目之为禅。牟宗三虽力辩象山“非分解”的表示非禅,但牟宗三也不得不承认“陆象山是有这个姿态,他不说破,就很容易令人误解为禅”。又云:“当然,朱夫子批评陆象山是禅,并不正确;但在某一层意义上,朱夫子的联想也不完全没道理。”象山在教人讲学上有“不说破”的“姿态”,这种“不说破”在《陆九渊集》中有许多记载,最重要的是表现为象山教人排斥分解的展示,诉诸当机指点以期于学者对本心的自悟与自成。
象山立言,本孟子主“先立乎其大”,所谓“大者”即是本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故“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然而,对于此人所固有的本心的把握,在象山和心学家看来,并不是通过知识性的、能所对立的分解方式来实现的,而主要诉诸当事人的体悟和体证来获得,对此熊十力先生说得很清楚:“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所谓内外、物我、一异,种种差别相,都不可得。……哲学家如欲实证真理,只有返诸自家固有的明觉。即此明觉自明自了,浑然内外一如,而无能所可分时,方是真理实现在前,方名实证。前所谓体认者即是此意。”基本上,象山教人也并不是不资用经典,然而,在象山处,经典顶多只是一种引发,关键在于是否存乎人的自我体证,此从杨简扇讼之例中可见,据《年谱》记载:
四明杨敬仲时主富阳簿,摄事临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阳,三月二十一日,先生过之,问:“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曰:“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讼至于庭,敬仲断其曲直讫,又问如初。先生曰:“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觉,始北面纳弟子礼。
此一案例常为学者所引。杨简问“如何是本心”当包含本心的概念义和活动义,即什么是本心?本心如何表现?象山原封不动地以孟子语作答,且再三之而不易,似乎侧重从概念上作答,但这并未解答杨简的疑问,及至扇讼毕,经由象山的当机指点,杨简“忽大悟”。当机指点则侧重于从本心的作用表现上以明本心为何,象山并没有用自己的分解性的语言以让杨简明白何谓本心,毋宁说,象山是用本心“怎么样”来代替本心“是什么”。在象山看来,此本心之分解的表示孟子已经说过,不必再次劳攘,而象山所以不厌其烦地重复孟子之语,目的则在于引发杨简返诸本心,令其在事上自悟自得自成。象山虽言必称孟子,但在明端绪得失之外,孟子之语似乎也依然只是一种引发,一种假手和方便法,关键还是在个人的体悟体证。
与此相联系,在功夫修养方面,象山教人也不免鹘突。《语录》记:
伯敏问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无寸进。”先生云:“如何要长进?若当为者有时而不能为,不当为者有时乎为之,这个却是不长进。不恁地理会,泛然求长进,不过欲以己先人,此是胜心。”
此处伯敏困于年来修身无长进而有以问之,象山答谓要理会当为不当为的本心之理,否则便是求胜之心,象山之答可谓有针指。但接下来的对话却不能让人释怀。
伯敏云:“无个下手处。”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处。”伯敏问:“如何样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须是隆师亲友。”
伯敏疑于功夫无下手处,象山如回答杨简之问一样,先原封不动地大段铺陈《大学》的原文,最后仍归结为要明本心之理。伯敏之疑原在此本心之理在日用常行处如何寻着下手,蕴含由近及远、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的階梯、次序和规则等等,但象山回环一圈,依然返回到原点,认为此理不解自明。我们有理由相信,象山的回答并没有有效地化解伯敏的疑问。但象山此处提出“理不解自明,须是隆师亲友”,似乎在告诉伯敏,功夫的下手处在“隆师亲友”。象山教人的确重视师友,象山尝言:“道广大,学之无穷,古人亲师求友之心亦无有穷已。以夫子之圣,犹曰‘学不厌,况在常人,其求师友之心,岂可不汲汲也!”师友之间的切磋、提点、讲论乃至榜样固有益于明道,不过,象山对此依然保持警惕,认为一方面师友聚会不可必得,还是要依恃个人随分用力,另一方面若遇非真实的师友,反相眩惑。故象山认为,功夫之下手处依然在发明本心,而此发明本心之关键则在“自得,自成,自道”,在“不倚师友载籍”。《语录》又记:
徐仲诚请教,使思《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一章,仲诚处槐堂一月,一日问之云:“仲诚思得《孟子》如何?”仲诚答曰:“如镜中观花。”答云:“见得仲诚也是如此。”顾左右曰:“仲诚真善自述者。”因说与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诚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说了也。”少间,仲诚因问《中庸》以何为要语。答曰:“我与汝说内,汝只管说外。”
象山让仲诚思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一章,象山显然并未解说《孟子》此章何意,我们或可理解为在象山看来,此章之意在反身自证、自求,而不在语言之解说。仲诚思之一月,乃以“镜中观花”喻其心得,象山称仲诚“真善自述”,盖依象山,唯有透过镜子,乃可知万花皆映照在镜中;亦惟有透悟此心,乃可知万物皆在此心中。除却心,如何见得自然世界之枝叶扶疏?故镜中观花即喻了万物皆备于我,而了解《孟子》此章的根子在自家心上,不在向外他求万物。象山教人汲汲于在心上立根,亦常常以“不说”来说明“已是分明说了”,反身自求是为学的大关节,故当仲诚问《中庸》以何为要语时,象山以为类似之问落于概念、语言之解说,皆是枝叶、歧途,学问之道唯在自家本心上用功,这便是他所说的“知学”。
象山尝言:“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又云:“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学者每闻此言,不免下自警策,倏然而兴,骤然而动。象山教人,亦每对学者言:“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故为学者当打扫心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依象山,主体自我完具作道德实践的天赋和能力,关键在于自立和立志,“道非难知,亦非难行,患人无志耳”。因此,为学之要,首在立志,“得其门,有其地,是谓知学,是谓有志。既知学,既有志,岂得悠悠,岂得不进”。凡此皆果决刚实之言。不过,当伯敏问“如何立”的时候,象山则一仍如旧地强调在本心田地上用功,并以禅宗棒喝的方式说道:“立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须把捉。”象山谓“立是你立”于理上固然亭当,然而,伯敏是经象山之开诱已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但却苦于无路头可入;常思量不把捉,又苦于无下手处。故伯敏“如何立”之问的实质原在于求得一个人为学进德的确定方法和轨道,目的在于要象山提供某种可传达的、形式型的知识和途径,然而,象山却并未回答伯敏之疑,反而责伯敏方法上为异端。顺此而下,象山乃大段引经据典说要在学问根源上理会此心,谓“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可当伯敏问“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时,象山断然斥之为“枝叶”,是只求解字,不求血脉,认为“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问者之意在于,即便端绪已明,毕竟情、性、心、才有何不同?但象山却取鹘突模糊的方式,将不同概念做打合的、浑沦的处理,并认为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可问题是,若情、性、心、才不须分别,又何以要有情、性、心、才的分别?何况这种分别不也来自《孟子》吗?何以孟子有此分别而象山却认为“不须得说”?这正是伯敏不明而求有以明之之处,但这种知识上的讲求和分辨,象山将其认为是碍道的闲议论。然而,“知识上的分辨”与“依知识之路讲道德”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便理会得“自家实处”,此“自家实处”仍有情、性、心、才之分别,仍需讲求,否则,自家实处仍不易得、不易明,而象山却常常混而为一,或不事讲求,故有学者问“如何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时,象山则云:“吾友是泛然问,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与吾友说,皆是理也。穷理是穷这个理,尽性是尽这个性,至命是至这个命。”问者是问怎样或什么才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问得似乎并不泛然,象山却通通用“这个”加以鹘突地回答,什么样或如何样的“这个”?答得倒委实有点泛然。我们不禁要问,即如前之孟子、后之阳明,他们不也有对尽心、知性,对情、性、心、才等概念的讲说和分别吗?莫非他们也是多此一举,也是“平地起土堆”?若谓象山取非分解的表示是为了扭转朱子之失,那么,何以同样是为了扭转朱子之失,阳明却采取了分解的表示?若上述疑问如理,则象山自己何以不示之以分解地立义,以便有效地接引学者?显然,凡闻分解之问即斥为枝叶、闲议论,必有言之太过处。审如是,象山千言万语,只教人在自家本心实处理会体证,而对于此本心实处所当含的言语讲说则不加理会,《语录》记:“曹立之有书于先生曰:‘愿先生且将孝弟忠信诲人。先生曰:‘立之之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说且将。”假如作为德行规范的孝、悌、忠、信不能说,也不必说,只是作为达到究竟境界的个人的体证方式,那么,儒门中作为成德的共同规范也就无从建立,但无论如何,主体心灵的道德自我意识的确定的传达,乃是建立共同规范必须满足的条件,除非儒家的道德哲学不必有此共同规范。
三、“中间暗”蕴含的问题是什么? [62]
综上可见,象山为学汲汲于教人在本心上自我体证,以为路头对了,则功夫之本全在自家切己自反,故而象山教人特别突出一个“自”字,象山云:
“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暴谓“自暴”。弃谓“自弃”。侮谓“自侮”。反谓“自反”。得谓“自得”。“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圣贤道一个“自”字煞好。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上看,人但凡认识到自己内在的良知良能深广不竭,不可胜用,则成就一个人德行的着力处乃取决于意志的自我决定,故做人“不可自暴、自弃、自屈”,学问之根在“自得,自成,自道”,在“自作主宰”,凡抛却自家田地兀自外求者,则是自我戕贼。强调主体自由意志的自我决定乃是成就道德的前提和道德责任赖以落实的基础,象山于此断之甚明,持之甚坚。然而,象山似乎并未认真考虑意志之“展示”与意志之“完成”的不同。《年谱》乾道八年记:“先生所以诲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于学者,数人相与讲切,无非此事,不复以言语文字为意。”象山教人所以“不复以言语文字为意”,强调单个人的自得自成,原因在于每个人的本心皆含具先天的道德原则,而此先天道德原则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自我明证性。象山重言“自”,其意既在自作主宰,也在自悟自证。不过,尽管象山不事语言讲说,不喜格套条规,善于从血脉上感动学者,以期学者自悟自明,然而,不可否认,学者也常有“无下手处”的窘境以及认“枝叶”为“根本”的陷落,以致象山自己也不免有“某有积学在此,惜未有承当者”的遗憾和慨叹。如是,我们要问,何以象山教人旦旦然谓“坦然明白”,却又依然让人有“茫然不知所入”之“暗”?何以心体亭亭当当,而悟之者却似是而非?牟宗三对此已有他自己详细的解说,今且不论。然而,面对象山诸学生的诸多疑问,我们依然心有疑惑的是,学者对本心之理的体悟所得毕竟是随“仁守”而有的“充实”?还是只随“智及”而来的“觉照”?学者所体悟的“自明”,果真如此“自明”吗?抑或只是当事者自己觉得“自明”,而旁人却是“茫然”?我们又有何途径和方法既让当事者“自明”又让旁人或他者亦“分明”,以便成就儒家道德哲学的共同规范理论?
无疑的,类似疑问已然涉及对道德的主体性哲学的根本性的反省,不过,在此脉络下它们却的确是经由朱子“中间暗”的批评被显题化出来的。这些问题涉及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看,是所谓“玩弄光景”问题。象山主“自”,强调个人对本心的自我体悟,但其体悟所得究竟是真实的本体呢,还是体悟者“只是因智光之悟及而将其(指心之本体)横撑竖架,投射于外而为影子”?从外部看,是所谓议论讲说所涉及的规则规范问题。虽依牟宗三所说,象山是因端绪之辨而挥斥一切闲议论,以非分解的方式启发学者,但牟宗三以扭转朱子之失而推述象山排斥言说讲论的正当性却并非是一好的、充分的理由,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象山所言之本心本体本就无法言说,端赖乎学者的自悟自证。然而,学者间对同一本体的体悟体证又必有不同,如是者,若一道德哲学理论仅仅局限于单个主体的“自悟、自道”,则作为道德哲学的共同规范将如何建立?各主体心灵间如何获得确定的传达?我们又有何办法来判定各人的体悟所包含的此是而彼非?上述内外两方面所涉义理繁复,我们在此只作简单的提领和点示。
先说光景问题。其实,牟宗三对心性之学在践履功夫上可能流于“玩弄光景、簸弄精神和气魄承当”有严肃的觉察,而且认为在陆王的心学一系中此三病尤为易显:
故自陆王以后,犯此者众,而觉此亦严。真伪疑似之际,不可不辨。盖陆王讲学,脱落习染,直悟心体,以立其大。简易是其主征。但简易是就透悟心体以立大本而言。中有存主,心体流行,直而无曲,自是至简至易。……但透悟简易心体,而不能知险知阻,正视险阻,在“必有事焉”中而落实,则因心体之简易而将“事”亦简易,驯至下半截全部放弃或荒废而不关心,则心体吊挂,形同隔绝。
牟宗三强调直悟心体,必当有笃实功夫在“必有事焉”的无限过程中一隙不断地践履,如是则无光景可玩,此当是心学之所以立之“法体”所必包含者。然而,象山教人却不无因重体悟而流于猜测卜度、因主简易而流于气魄承当者,致使其弟子也不能分辨自己所悟是真正识得本体,还是只窥见本体之光景。《语录》曾记詹阜民“下楼之悟”:
他日侍坐无所问,先生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詹阜民)因此无事则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窃异之,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某问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
“占眸子”语出《孟子·离娄上》,原意是说观察一个人的心正还是不正,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因为眼睛不会遮盖一个人的丑恶。詹阜民下楼“忽觉”心已澄莹,但此所忽觉之澄莹究竟是本心实理还是智光投射出去的影子?颇难判定;象山则通过观察詹阜民的眼睛来判断他是否真正悟得本心之理,尤不免出玄入妙,此即难怪后之学者会有“茫然不知陆子之学为何如”之叹。明儒罗整庵则站在性学立场,对杨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以及詹阜民安坐瞑目,“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之悟,不惟斥之为禅家机轴,且直认为“二子之所见,即愚往年所见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误而究言之,不敢为含糊两可之词也”。整庵还对象山教人“眩于光景之奇特”深致慨叹,而谓:“象山以英迈绝人之资,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虚心易气,舍短取长,以求归于至当,即其所至,何可当也?顾乃眩于光景之奇特,而忽于义理之精微,向道虽勤,而朔南莫辨,至于没齿,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
另一方面,象山教人固然简易直截,但简易而没有着实紧汲的功夫作前提,即不免沦为气魄承当。象山常有启发语、点示语、警策语,说得煞是动人,让人广广然,跃跃然,故朱子认为“近世所见会说话,说得响,令人感动者,无如陆子静”。但不可否认,象山也有不少虚夸语,大话头,易于让人誤会为只此一念之间便可一了百当,直与天地相似,如象山尝言:“吾于践履未能纯一,然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试想,若忽视践履功夫的纯一,则其所谓“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鲜有不落于玩弄光景,气魄承当者!故朱子云:“他(象山)是会说得动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会使得人都恁地发颠发狂。某也会恁地说,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坏了人。”
再说言语讲论问题。象山为学重个人的自得自悟,故不事言说讲论,这与其认定的作为形上本体之本心的特点密切相关,此一点前引熊十力之语说得甚明。其实,在心学一系中此一特点尤为突出,如作为明代心学的前期代表,陈白沙即认为:“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君子奚取焉。”阳明亦云:“心之精微,口莫能述。”又云:“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象山挥斥闲议论,但自己教人也多不著言语、著述,不主与人辩说讲论,象山尝言:“辩论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责也。不与之论,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强说,自加惑乱耳。”又云:“日享事实之乐,而无暇辨析于言语之间,则后日之明,自足以识言语之病。急于辨析,是学者大病。虽若详明,不知其累我多矣。”不与辩说,期于学者于自家本心实处默而识之,默而成之,故云:“吾之深信者《书》,然《易·系》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处深可信。”盖道不难知,也不难行,总在立志以自悟其是,非能宣之于笔舌,故云“平生所说,未尝有一说”。如是,为学进德全在个人的觉悟和顿悟上,没有“如何”的过程,不注意客观理论的建构,更不能示人以确定的轨范和规则。朱子所以对此心存耿耿,正在于象山无形中缩减甚至消解了儒家为学进德中必要的“过程”和“知性”,无法满足建立哲学理论的基本要求,故而其力主的讲说、议论、经典研究等可以被理解为朱子对“心”的内容意义和关联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的反省,他不取直觉的方式而是取客观化的方法来理解心之为心。
而牟宗三则对复其本心之本质有一详细的说明:“说到复其本心之本质的关键并无巧妙之办法。严格说,在此并无‘如何之问题,因而亦并无对此‘如何之问之解答……知一切巧妙办法,到紧要关头,皆无用,然后始正式逼出此觉悟、顿悟之说矣。”牟宗三基于心体之作为形上本体原不可作言语的分解的表示,故对此本体之知便无“如何”之问,因其本身便无“如何”的过程。审如是,凡试图对此本心本体作言语之分解、确定的传达途径的寻求、清晰而具共识的共同规范的建立等等,皆不可行。“这个方法之所以不可行,最重要的理由在于此一本体或本心逻辑地不可能构作任何方法程序。由于此一本体或本心是形而上的、超越的实体,它不可能建立有实践性的发生程序;又由于此一本体或本心是无对的、无分别的,它亦不可能提供有内容性的本质程序。”无疑的,若依此逻辑推论,则所谓个人体悟体证意义上的“见道之真”,在根源上、本质上便不是本心本体的自明自了,最多只是体道者后天的“自我得之,自我言之”(陈白沙语)的诠释与玄想,而这种单独的个人体证意义上的“诠释、玄想”,即便它仿佛可以与本心本体相合,也只是一种没有必然性的“巧合”或“偶合”。在此一意义上,象山虽力辟闲议论,但象山自己的议论仍不免于闲议论,而朱子谓“安知除意见之心,又非所谓意见乎?”乃可以获得其批评的正当性理由,其批评象山说话“中间暗”也必有其说。
盖体悟本心落于“自得”“自言”(象山说为“自道”),在逻辑上等同于将个人的“见道之真”看作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自我宣称(self-claim)。然而,假如一种理论能够成立,其重要的理由之一乃在于它能夠被人所理解;而一种理论若要被人所理解,其预设的条件之一,则必须诉诸一些关于使用语言及传达意义的共同规则。在此意义上,“自我得之,自我言之”的自悟自明、自得自成固可以有其单独个人的“自我受用”,但这种类似于私人语言的喃喃自语,却不能充当证立理论本身的有效性理由,盖基于对本心本体的体证意义上的语言亦即“自言”“自道”式的语言乃是一种形上学的语言,这种形上学的语言只是表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故有其个人“受用”的意义,但却并不能带给我们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因而它无法建立一种有效的、可沟通、可传达的哲学理论。牟宗三顺康德来疏解象山并证立象山,假如撇开其间繁杂的异同不论,至少康德以后的众学者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反省和不满,抑或可以为我们理解朱陆之争带来某种启发。
无疑,康德以后,围绕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反省涉及诸多头绪,不是一篇简短的文章所能处理的,但扣紧我们的主题而言,则如何从先验主体的意识哲学发展到互为主体的语言哲学显然是一条极为突出的线索。大家知道,黑格尔是站在“伦理”的立场来批评康德的“道德”的形式主义,黑格尔认为,康德把不受制约的意志的自我规定作为义务的根源,但却未使之向伦理过渡,致使其自身成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把道德科学贬低为关于为义务而尽义务的修辞或讲演”。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在康德那里,“所谓道德律除了只是同一性、自我一致性、普遍性之外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形式的立法原则在这种孤立的境地里不能获得任何内容、任何规定。这个原则所具有的唯一形式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同一”。黑格尔批评康德的伦理学为形式主义的伦理学在理论上是否公平,学者自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黑格尔批评康德伦理学的形式的立法原则“没有任何内容和规定”,只是“为义务而尽义务”,使自身局限于“孤立的境地里”等等,可以说既是构成哈贝马斯批评康德伦理学为“独白的伦理学”(monologue ethics)的原因,也是促使哈氏着力于借助沟通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来重建康德式的伦理学的理由。哈氏特别重视黑格尔对康德囿于意识哲学的批评,主张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过渡。依哈氏,康德把每一单个的主体(every single subject)当作理性的存在者,自己为自己给出道德法则和命令,然而,康德并没有从他人的立场、依据对话和理性讨论的共识来建立道德法则,如是,在康德的这种道德准则之下,本来道德哲学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消解成单一而自足的主体的活动(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s dissolved into the actions of solitary and self-sufficient subjects)”。哈氏进一步认为:“就自律的观点而言,意志是由能够成功通过普遍化检验的格言所担当的。因此一个人的意志,是由应该对其他人同样有价值的理性所规定(当其他人被视作同一道德共同体的成员时)的。”因此,“自律不是一个分配的概念,而且无法个体地实现……康德用自律概念,自己已经引出一个只有在交互主体的框架下才能完全展开的概念”。哈氏明显不同意那种出于单独个人的意志决定的所谓道德行为,不论这种意志决定是如何地秉承于可普遍化的先天的定言命令,因为自律无法个体地实现,相反,真正的道德行为是一种主体间的沟通行为。沟通离不开语言,“沟通行为概念预先把语言设定为达到某种理解的媒介,在此一过程中,参与者借由自己与某一世界的联系,相互间提出可接受或拒绝的有效性要求”。而哈贝马斯所发展出来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正是要处理一种沟通行为何以可能的普遍、必要的条件。依哈氏,若语言理论不再从语义学的角度讨论对某一命题的理解,而是从语用学的角度建构一组使得语言符号之所以有意义的规则,那么,各行动者相互间达成共识的表述便构成了彼此间同意的有关什么是对的行为规范,人们使用语言以达成沟通的行为即是理解和应用规则或规范的行为,因为语言是由规则所管辖的,而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也是一种被规则所管辖的行为。因此,哈氏认为,语义学的真理观和语用学的真理观并不相同,一旦人们接受了语义学和语用学有关真理问题上的区分以后,就会追问,对于规范正当性的话语为何是重要的。审如是,则道德实践就已不再是单独个人“知道如何做”的体悟,而是“知道是什么”的知识,由这种知识所组成的规则即是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乃是基于认知、讨论和行动者彼此同意的结果,不是也不能是单个的理性存在者自我决定或自我体悟的宣称,否则,这种自我宣称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是类似于“我的痛”那样的“私有的”感觉。哈氏所主张的交谈伦理,跳出了单个的主体性的自我意识的自明性宣称,将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建立在主体间认可的基础上,而且这种认可又具有程序性的说明和证明。某人应当做某事,意味着某人有好的理由做某事,而这个好的理由是由理性论证而来的,是人们公认的标准,而人们之所以会同意这个标准,乃是因为这个标准具有且符合清晰、明白、确定等形式条件,因此,支持这个标准的理由要比支持别的标准的理由要好。
无疑的,如何评价哈氏对康德伦理学的重建,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是情理中事,同时,我们引述哈氏的主张也并非意味着我们完全赞同他的所有看法。就当今哲学研究的视野而言,伴随着20世纪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由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我们看到,西方许多学者的讨论,似乎皆不约而同地指向康德式的先验主体所包含的个人意识的明证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皆与我们反省象山之学之“自言”“自道”为何是“中间暗”的问题息息相关。我们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假如我们仍然期待传统儒家心学在未来,有一个可预期的、能为现代道德哲学理论所认可和接纳的健康的发展,那么,如何克服“中间暗”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固然可以说,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问题意识,儒家哲学的研究不必随西方哲学起舞,我们完全可以“汉话汉说”。不过,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特色”论的主张足于证成和捍卫我们的“特色”,这也是我们所以不惮以最简陋的知识作此拓展性研究的理由。
四、简短的结语 [65]
作为朱子对象山心学的某种特定批评,在朱子的观念中,“中间暗”的主要含义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谓象山之学不著言语,在教法上躐等跳跃;一谓象山之学以悟代证,拒斥一切议论和意见。如是者,虽象山欲“鸳鸯绣出从君看”,然而却终未能把“金针”度与人;“道理固是自家本有”,可象山却只要自得,但“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此中朱子的担心既包含判定“是”与“非”的标准和方法,也包含“为何”之疑问、“如何”之思辨,凡此皆构成了我们反省的理论问题。
站在当今哲学的立场,我们想着重指出的是,现代哲学的发展给儒家传统的心性理论尤其是心学本体论提出了值得我们正视的挑战。不必讳言,假如象山的本心本体确如熊十力所认定那样,乃是泯除了“内外、物我、一异、种种差别相”,那么,我们对“本心”也就只剩下返回到单个人的自我“明觉”一途了,而这样一种依恃“明觉”的体悟,又由于“本心”此一形上的超越实体的“无对”“无分别”,故其结果乃不出两途:一是体悟者的体道之真顶多只是体悟者个人的自我宣称;一是体悟者的自我宣称亦如牟宗三所说的并无“如何”之问,亦无“如何”的过程。如是,所谓主体的“体悟、体证”也便从根本上取消了认知、讲说和讨论的必要,而其“自言、自道”的说辞虽然充满自信,但却并不能满足自我解释和理论解释的需要;虽悟者“深信”他与本心本体觌面相呈,但却不能说明他是如何与本心本体觌面相呈,由于其并不能提供客观的理据,无法建构一套形式型知识,因而也便无法说明自己的悟道的陈述何以为真,最终或不免陷入如劳思光所说的“特权的谬误”(fallacy of entitlement)。审如是,真正的问题似乎就转变成为,一个人的道德意识和决断已经不在于其究竟是如何出于本心,如何出于权威、典册,抑或是如何出于议论和意见,而在于如何确保由主体发出的当下呈现的意识,具有主体间共认的普遍性和公共性之效力。假如我们同意哈贝马斯所说的“自律无法个体地实现”,同时赞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个人“不可能‘私自遵从规则”,或更进一步,假如我们把道德规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看作是一个众道德行为者之间借由理性讨论而共同接受的问题,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指出,象山所言的单个人的“本心的决断”所包含的内容本身必定是一个在主体间待检验和可辩论的问题,并不能直接以道德真理的方式进行自我宣称,因为我们无法借此获得确定的传达途径、清晰而具共识的共同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同责任。也因此,就建立具有确定性的道德理论而言,象山“自得、自成、自道”的形上学本体论似乎已成明日黄花。
不过,尽管如此,谈道德哲学却始终离不开主体意志的自由自决,此乃道德之所以为理想、为崇高以及道德责任所以赖以落实的前提,同时,也是批判意识所以能够安立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角度,象山之学即便在今天仍所以有其大用而呈其高致者,由此则可反显出哈贝马斯重建式理论可能存在的不足。哈氏的交谈伦理配合着20世纪哲学的转向,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方向和设想,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动向,但也正如学者指出的,哈氏常常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将问题本身加以取消,而且哈氏的重建式理论也不免有混淆民主正当性原则与普遍主义道德原则之嫌。李明辉便断言,哈氏交谈伦理学的普遍化原理在本质上应当只是民主的正当性原则,当他将这项原理也视为一套道德原则时,必然会陷于两面为难的窘境,“因為一切道德原则均表示一种道德意义的‘应当,亦即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与现实条件之间永远有距离,永远有‘如何落实的问题。但是一项程序性的正当性原则即是一项应用的原则,它不能显示一种道德的理想。”哈氏的普遍化原理是否仅只在寻求道德原则或规范的程序正当性,抑或可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然而,李明辉的质疑却透露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亦即道德的“应当”最终必系乎意志的自由自决,劳思光便在肯定哈氏所作努力的基础上敏锐地发现,哈氏的交往伦理,“只强调交互主体性,对主体性的内在世界便了解得太少。看他的道德哲学理论,似乎他对意志本身的状态问题完全未加注意。我则认为如果要以交互主体性为根据来建立一个沟通理论下的道德哲学,则顺着他的理论模型说,至少也得提出‘道德语言的特殊语用规则,来安置有关道德意识的特殊性问题,只讲一般性的语用规则是不够的。”劳氏批评哈氏未着力注意到自由意志本身的重要,此一批评蕴含着道德哲学的思考必须预认自我意识及自主性,虽劳氏并未对“道德语言的特殊语用规则”作出详细的说明,但劳氏的此一看法在理绪上既与李明辉的质疑相映成趣,也与阿佩尔(Karl-Otto Apel)不同意哈氏的主张有不谋而合和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在形式上阿氏与哈氏同主交谈伦理学,但与哈氏建立的普遍语用学不同,阿氏则特别重视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阐明其所主张的交谈伦理学的特色,也因此,阿氏特别重视对主体自我反思的“终极奠基”。要而言之,阿氏认为,假如我们要建构一套具共识的共同责任的伦理学,那么,我们就必须保存个体在道德上自由自主的良知决断,以及随之而来的伦理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和道德的一致性。
我们想指出的是,此间争论繁复,只能点到为止。但显然,将这种争论和探索的成果与我们反省象山心学乃至儒家的心性理论建立起某种富有意义的“自我关涉”,抑或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责任编辑:陈 真 责任校对:杨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