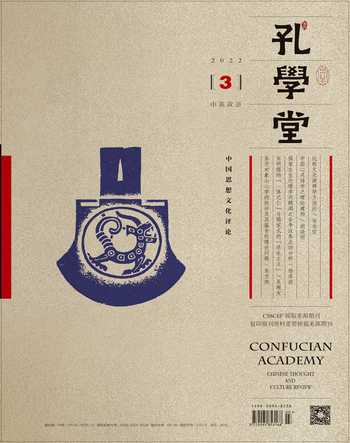戴震与荀子心性论之差异
摘要:戴震思想虽与荀子有相近处,但他们的心性论架构存在明显差异。荀子将性、心、欲、情视为一源,戴震则把血气心知拆分成人性的两部分。二人虽都提出心具有认知、情感、思辨、统御感官的能力,但对心是否必然成善的判定不同:荀子认为心虽有向善的资质,但心也好利,“可以”为善不等于“能”成善;而戴震主张心喻仁、心好理义,心知必然成善。荀子认为心能认识理,但自身不具备理,而戴震指出心自含理义。二人都反对寡欲,主张发挥心的作用以理制欲,但荀子认为心既能管控情欲,也会为情欲所驱使,戴震则主张情中包含大共理,因此要以情絜情。在修养论上,两人都注重以解蔽、学问修为和遵循礼法之方法养护心灵,但区别在于戴震反对心斋坐忘工夫论,因而戴震思想近于荀子性恶论的说法不能成立。
关键词:戴震 荀子 心性论 理 欲
作者李慧子,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66)。
清代思想家戴震效法韩愈,以传续儒家道统为己任,标举孟子思想的重要意义,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著作。他从理气论、人性论和理欲论等层面批判程朱理学,力图还原先秦儒学本意。戴震对孟子的诠释与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皆不遗余力,并提出:“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尽管戴震大力崇孟抑荀,但其思想却被批评为近于荀学。比如清代学者程瑶田批评戴震:“不知性善之精义”,“不能不与荀子《性恶》篇相为表里”。章太炎直言:“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钱穆也说:“孟子书中亦明明分说两种境界,而东原必归之于一;又不归之于仁义,而必归之于食色,是东原之言近于荀子之性恶,断然矣!”既然戴震在论著中极力批判荀子,那为什么他的思想会引发违背孟子而近于荀子性恶的批评呢?戴震思想又是否如章太炎、钱穆所言近于荀子呢?要想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个公正的评断,就必须深入荀子和戴震的思想体系,比较两者思想异同。而切入这一问题除了从人性论角度着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就是人心问题。因为“心”在戴震和荀子思想体系中是关联人性、天理、欲、情等问题的枢纽,两位哲人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而学界目前对此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关注。因此如要判断戴震思想是否与荀子相近,就要从比较两者的心性论入手。
一、荀子与戴震论心与性 [见英文版第91页,下同]
在对心之功能的理解上,戴震与荀子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心具有天赋的认知能力,能够认识和思考天地的规律和宇宙的奥秘,并且能根据天道制定人间的伦理法则。两人都看重心的辨识能力。荀子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识能力不仅体现在能够判断事物种属与性质的差别,还体现在善恶是非的判别上。戴震将孟子“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解释为:“心能辨是非,所以能辨者智也;智由于德性,故为心之能而称是非之心。”心能辨夫理义并不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而是“自具之能”。两人也都认为心是人形体与精神的主宰,心不仅能控制身体的行动,还能统领情感与欲念。“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尽管戴震与荀子对于心的论述有诸多共同之处,但是戴震对于人心与人性的关系、心之善恶等问题的理解与荀子颇为不同。
第一,人性与人心关系的架构不同。在荀子思想里,人心与人性是一源的。心的认知能力来自血气。“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与孟子把“大体(仁义礼智)”与“小体”(欲望)二分的构架不同,“荀子则将性、情、欲三者看作是同出一源”。人性就是由阴阳二气“精合感应”和合而生,是“不事而自然”。人心的属性也是由人性所决定,是“生之所以然者”。人心与人性是一体的。心必须以人性为基础,不能脱离人性而活动。人心与人性是双向互动的:人心不仅能调动人性的资质,人性也能够发动心的能力为其服务。人心区别于人性的特质就在于,人心具有自主决定权。“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戴震将孟子的“四端之心”说与荀子“凡有血气必有知”的说法相结合,提出了“血气心知”说。他把人性分成血气和心知两部分:心知产生仁义礼智,而血气产生欲望、情感。他分析了血气心知的天道基础:“血气心知者,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谓性。”戴震从气化宇宙论的角度说明心知要以血气为基础,心不能脱离气而独立运行。但他更强调心对于血气之性的主宰能力。“况气之流行既为生气,则生气之灵乃其主宰,如人之一身,心君乎耳目百体是也,岂待别求一物为阴阳五行之主宰、枢纽!”心虽能统领感官,但并不能取代感觉器官的功能。尽管心知与根于血气的欲望都属于人性,心知也会受到欲望的影响,但心知本身不产生欲望,也没有欲望,欲望只来自血气。这与荀子“心好利”的观点不同。
第二,两人对心之可以为善与能为善的判断不同。荀子人性论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如果任由人性好利的特质自然发展,人就会作恶;另一方面,如果把人性中“仁义法正”的资质通过后天的教化与修为而实践出来,人就可以成为圣人。荀子区分了道德的资质与道德的结果,强调“可以”并不等于“能”。这一点也是孟荀心性论的一个核心分歧。在孟子看来,四端之心是人与生俱有的“良知”“良能”,“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而荀子认为人性之中虽有可以成善的资质——“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也具有可以实现仁义的能力——“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但“可以”成善的資质并不必然等于道德本身,“可以”也并不一定能转化成善的结果。
相比于孟子对人必定能为善的判断而言,荀子强调人既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因此荀子强调隆礼重法,意图用礼法规范制约人性。与此同时,从个体修为的层面来说,荀子重视发挥心的能力去为善去恶。他用“心意之于善”论来解释人何以能行善。“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唐君毅曾指出,荀子所谓的心有向上之能,其人性中蕴含有自我向善的能力。如此看来,荀子肯定心有向善的资质能力,但不承认心本身就是善。
戴震不赞同荀子对心可以成善的判定,而是延续孟子思想,主张心知皆善。孟子虽说“心之官则思”,但是并没有解释心何以能思考。而戴震从气化宇宙论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证:“曾子言:‘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盖耳之能听,目之能视,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为也,所谓灵也,阴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辄通,魂之为也,所谓神也,阳主施者也。”正是由于人心禀赋了阴气之灵与阳气之神,心才可以感知人情的冷暖,认识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建立人世间的政治与伦理秩序。“心之精爽”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孟子的“良能”“良知”彰显的是“弗学而能”的“乃属之性”;而荀子的人性论是显明“学而后能”的“不得属之性”。“属之性”就是人性之必然的“能”成善,意味着一种必然的成就美德的能力。因此戴震强调心知全善。
第三,两人对心是否具有道德内容持相反意见。荀子虽然认为心有善质,但也指出“心好利”。荀子用人性之“本始材朴”来说明人性本身不具有道德内容。人天然喜欢能满足欲望的事物,就如耳口鼻舌喜欢美好的声色嗅味一样,心也天然喜欢利益好处。这些特性是与生俱来的,是“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人性本身如果不经过后天的学习与教化,就不能自然而然成善。“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因此仁义道德与礼仪法度是化性起伪的结果,并不是人性本身就具有的。
与荀子观点不同,戴震明确提出“心之所喻则仁也”。心所包含的就是天地之德,就是仁。不仅如此,戴震还注意到人心具有一种天然爱好理义的特性,这种特性与感官喜欢美好的事物是一样的。“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至是者也。”当人看到他人做了顺应规律、体现仁义、符合礼法的事情,内心就会欢喜满足;反之内心就会沮丧、难过。心的这种“好理义”的天性并不是个别人的心理感受,而是大家都有的,是心之所同然。正是由于心具有好理义的特性,人们才能好善憎恶、为善去恶,社会才能向积极良善的方向发展,仁义才能得以实现。
戴震反驳荀子将仁义归功于圣人的观点,认为礼义出于人性本身。“知礼义为明于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极则,适以完其自然也。”荀子只看到制度规范的必然性,但是没意识到必然法则也是出于自然人性。社会伦理规范虽是人必须遵守的,但它的制定是基于普遍人性,其目的也是呵护与制约人性。戴震彰显“必然乃自然之极则”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外在的礼法规范一定要基于人性之自然。他由此批评荀子只把欲望视为人性,是“举其小而遗其大也”,赞扬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人性内容的看法是“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由此可见,尽管戴震与荀子对于心的功能的理解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二人对人心与人性关系的架构方式不同,导致他们对心本身是否具有仁义,心是否必然能成善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别。荀子认为心好利,心就有向善的资质,但心本身不具有道德内容,心的活动也不必然成善。而戴震主张心知皆善,“心好理义”,心知的扩充必然成善。两者心性论的分歧还体现在他们对于心与理的关系理解不同。
二、荀子与戴震论心与理 [95]
对于理的看法,戴震与荀子有一致性。其一,理是规律,是事物的文理、条理。荀子说人通过了解“物之理”就可以理解天道规律。戴震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其二,人性是天道赋予的,人性本身是天理的体现,因此灭杀人性就是违背自然规律。荀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戴震说:“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贤圣所谓理也。”其三,仁义礼智是天理的体现,也有可以遵循的理路。荀子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戴震说:“若夫条理之得于心,为心之渊然而条理,则名智。故智者,事物至乎前,无或失其条理,不智者异是。”尽管戴震和荀子都认为心能认知世界的规律和万物的法则,但是两者对心与理关系的理解有所差异。
荀子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分成两个层次。其一,天人之分。天是客观实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二,“天人不分”。人的感官、情感与认识能力是天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天君”“天官”“天养”“天情”也都是“天”的一部分,人与天关联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内在之天与外在之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基于此,人才可以认识和把握天的运行规律,并且通过了解天的自然规律而做出适当的判断和行动。
荀子把心叫作“天君”。人只有发挥心之天君之职能,调控人的感官按照天地规律行事,才能完成属于人的使命,才能养护情性。只有发挥心知之能辨识天理,才能判断是非善恶。而“知天”就是发挥心的能力。“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只有发挥心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和理解天道,才能喜欢与渴求天道。在此基础上,人才能持守与护卫天道,并且禁止一切不符合天道的事情发生。个体内心安宁、社会稳定的核心关键是要治心。“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如果人心都能渴求天地之道,并且按照天地的规律去生活,那么就会身心和畅、百姓康宁。
由此可见,荀子对于天人关系的构架与理心关系的构架是一致的。一方面,理是客观实存,不以人心为转移;另一方面,人心之中具有理之则,人心可以认识和运用理。荀子在心与理的关系上,并没有直接说心本身就具有理,只是说心具有认知天道的能力。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认识能力,乃在于天官之能是天所赋予的。但是能否运用天官之能把天道实践出来,还是要靠心的自主选择权。因此,荀子对于人性的理解与对人心的理解是一样,即人有成善的资质,并不等于人性、人心本身就是善。人有认识天理的能力,也并不等于人心就具有天理。
在心与理的关系上,戴震的论述分为三层。其一,心能通于理义,就如五官能通于声色气味一样,是人性本然具有的能力,并非后天赋予的能力。“孟子明人心之通于理义,与耳目鼻口之痛于声色臭味,咸根于性而非后起。”戴震从气化宇宙论的角度分析心之所以能通达理义,乃是因为心也是由阴阳五行构成的:“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因為心与天地在形质上是相通的,因此人心才能通理义——“理义也者,心之所通也”。
其二,之所以心能通于理义,是由于心具同然之理、大共之理。理是普遍共理,是万事的准则,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他将孟子“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概括为“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他解释“同然”的意思是:“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在戴震看来,人心具有普遍性的天理,即“大共之理”。所谓“大共”就是善。“大共之理”就是“有根于心之德”,是“所以衡论天下之事,使之协于中,止于至善”的根据。
其三,每个人都同然具有认识理与实现仁德的心知能力。理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知晓与把握的,每个人都能明理、得理,因此圣人与普通人的心灵能力没有差别。不仅如此,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心之功能,“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使“仁义礼智无不全”,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在这一点上圣愚也无差别。
戴震认为荀子意识到了人心之同然,所以荀子才会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但他批评荀子没有意识到人不仅“可以”成为圣人,并且“能”成圣成贤。也正是由于心具有同然之理,人才能用普遍法则去衡量事物和言行是否正当、合理,人才能不会为偏私所误,才不会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迷惑不定,世界才不会也因为主观私意而走向混乱。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荀子认为人有认识天理的能力,并不等于人心就具有天理,而戴震主张人心本身就自含天理。
三、心与欲、情的关系 [96]
(一)心与欲 [96]
荀子和戴震都肯定欲望的合理性,反对寡欲和去欲。他们都主张仁政要满足人的基本欲求。荀子说:“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圣人制定的礼法规范就是在充分考虑人性实情的基础上,既能满足人的基本欲求,又能限制人的过度欲望。圣人制礼作乐的依据就是理。戴震指出王道之治都能呵护体察人民的情感需求,恰当满足人们的欲求。“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
荀子和戴震也都主张运用心之能力满足人性的诉求。荀子说:“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戴震认为要“以心遂欲”。而心之仁德的实现就是使身体的欲望得以恰当满足,二人也都注意到无节制的欲望会导致恶,因此要以理制欲。荀子云:“心也者,道之工宰也。”虽然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心是道的主宰,可以决定是否遵行天道。如果心用道来节制欲望,欲求不仅能得以满足,行为也会合于礼法,心灵也会获得安乐。如果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而违背天道与人道规律,内心就会焦虑困惑。“以道制欲”的关键在于心,因此心能决定欲望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被满足。
戴震不赞同荀子“欲为蔽”的观点,提出遮蔽心知的不是欲望,而是私欲。“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戴震虽肯定欲望的合理性,但他也主张“性之欲之不可无节也”。天理的实现就是对人欲的正确处理,要使得欲望的表达合于中道,就要“依乎天理”。而依乎天理、达乎天理就需要发挥心之作用。
戴震主张要发挥心通理义、辨理义的理性能力,让欲望得以节制,使其分寸适当。“人有欲,易失之盈;盈,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心达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夺之。”心对于欲的控制要如大禹治水一样,要疏导而不能堵塞。戴震还认为,人应当基于心之大共理去换位思考他人的感受与需求,不能以自己为中心。“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
(二)心与情 [97]
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性”就是天所成就的禀赋,情是性的内容。这里的“情”字并不指情感,而是实际情况的意思。“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欲望对人性实情的显现。戴震对于“情”字的理解与荀子有一致性,他认为孟子所言“乃若其情”的“情”并非情感之情,而是指实际情况、本来的样子。“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情,犹素也,实也。”即如若按照心的本来样子去做,人就会为善。
戴震与荀子在心与情之关系的论述上存在差异。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悲”“心伤”“心淫”“心庄”等心的情感活动是由人性决定的,心也会根据人性需求而考虑、谋划。因为心好利,所以心的活动未必皆善。而戴震认为:“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征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人由二气五行构成的,有血气就会有欲望,有了欲望的喜好与厌恶就会推动不同的情感。人作恶并不是因为心知不善,而是由于不良的欲望与情感遮蔽了心知。
戴震认为,人除了喜怒哀乐等情感之外,还有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与《大学》中所说的“所恶”,皆是“人之常情”,而“常情”中包含着常理:“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人之所以会有“所不欲”“所恶”的“常情”,皆是因为遇到违背“常理”的事情。宋儒后学所主张的“舍情求理”不仅不能体民之情,还会伤害民心。“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那么如果使得情欲有节,又能呵护民心民情呢?戴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以理节情”的同时,也要“以情絜情”,而“以情絜情”的关键乃在于心。
心能对外界的刺激产生知觉反应,而这种知觉反应是人所有的感官能力中最强大的。“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曰觉,思之所通曰知,百体皆能觉,而心之觉为大。”正是由于心具有知觉能力,人才会怀生畏死,人与人之间才能彼此共情与理解,关心和帮助才得以可能。戴震分析人的情感具有感通之能:“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基于此,人与人之间才能彼此同情與理解、彼此体谅与安慰。人之所以当看到他人处于危难、苦痛时而心生恻隐、怵惕,就是因为心有知觉、有情感,能觉知冷暖悲欢,能换位感受他人处境。这种觉知能力是心本然固有的,并非心外别有一物操控着人的想法与言行。“然则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焉藏于心也。”因此,心的知觉感通能力是人与人、万物发生关联的基础,也是道德产生的基础。
由此可见,在理制欲的思路上,戴震与荀子有一致性。所不同的是,戴震认为人心自含仁义之德,人情之中体现着常理,因此发挥心知的通理义和感通能力,用心之大共理去絜矩他人。
四、戴震与荀子的心性修养论异同 [98]
在心性修养工夫上,戴震与荀子的思路有不少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二人都注重解蔽。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偏见和带有局限性的认知会让人的思想受到禁锢,从而无法全面认识真理。而彼此相反的现象与意见,也会让心灵困惑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解蔽的目的就是要客观全面认识世界,使人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能够“主其心而慎治之”。只有发挥心以理制欲的作用,使得“心意至于善”,人才能“兼陈万物而中县衡”,才能做到“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
戴震提出“解蔽,斯能尽我生”的宣言,将解蔽与充分实现生命意义相关联。在他看来,解蔽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其一,解除私欲对心知的遮蔽。戴震并不用程朱气质之性的理论去解释人何以会作恶,也不认为人性本恶,而是将人作恶的原因归结于私欲。但他说明去除私欲并不是让人无欲,而是使心无私慝。“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只有去除私欲对心知的干扰,心才能明辨理义,从而实现仁义。其二,解蔽还要清除各种主观偏见、成见对心知的干扰。人们有时会把主观意见当作真理去评断他人与事情,并因此造成误判与伤害。戴震将这种自以为是叫作“蔽而自智”。因此,他呼吁人们在评断事情之前,先要全面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先要“自求其情”,对他人的处境给予换位思考与同情的理解,不要盲目地做道德审判,避免因各种误解与误判而造成的人祸。
第二,注重学问对于心知的提升作用。荀子认为君子和小人的人性是一样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心知之能出于人性,因此人们的心之能力也是同样的。造成君子与小人之别的原因就在于后天的化性起伪。而学习是最有效的改善人性、提升心知,实现仁义的方式。普通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圣人乃在于学习与修为。
在戴震看来,孔子说的“性相近”的“性”并不是程朱所理解的氣质之性,而是指心知之性。心知之性的差异是由于后天不同的努力程度造成的。不能认识和实践善的人,并不是由于先天的心知不足,而是由于没有进行足够的学习和教化。上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智力水平的差别,但并不是善恶的差别。愚人也有血气心知之性,也有认识善和行善的能力。即使是愚钝之人,只要对仁义礼智怀有敬畏与渴望,同时不断勤勉精进,心智就能被开启,因此戴震主张下愚可移。因此戴震强调“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
第三,戴震与荀子都注重通过遵循礼法规范以养心。荀子认为礼法之中体现仁义,遵循礼法的过程,也就是行道的过程。因此,养心最好的方法就是遵循与实践礼法。“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戴震认为,礼法是根据天地的规律而制定的,因而体现着天理的秩序。因此人遵循与实践礼法的过程,也就是将外在的规范条理内化为身心秩序的过程。设立礼法的目的是“治天下之情”,使人的言行变得恭敬、谦让、谨慎,让情感的表达恰当、适中。“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在遵循礼法的过程中,心灵也能获得一种秩序,从而让欲望与情感的展现皆能发而皆中节,适中而不过度。
尽管戴震与荀子在心性修养论有不少共识,但是他们在修养方法上也存在差异。荀子主张通过“虚壹而静”的方式去通晓天道,“虚”和“壹”是实现心静的前提。“虚”就是让心保持一种虚空、敞开、容纳的状态,不让自身已有的感觉、认知、意志、思想妨碍未知。“壹”就是心以天道为原则,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不迷惑彷徨。荀子强调“虚壹而静”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人们意识到天道是运动变化的,因此人要用虚怀若谷的心态去感知和认识道,不能僵化守旧,更不能用已知阻挡、遮蔽新知。只有保持“虚一而静”,才能保持内心的大清明,人才能认识道(“知道”)、实践道(“行道”)和体会道(“体道”)。“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
戴震认为主静存养工夫是佛老修行之法,批评朱子的心性修养论是“非六经、孔、孟也”,强调儒家的修养工夫之目的是“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及“德性资于学问”的方式,不断实现扩充四端之心,使得“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因此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并非主张使心复原到虚明之本体,“非‘复其初”。
此外,荀子所倡导的“美善相乐”是通过乐教的方式得以实现的。他认为乐教具有改善人心、引导人心向善的作用。雅乐能使人变得庄重沉稳,也会避免心灵被不良的欲望、情感所搅动。不仅如此,荀子还认为乐教能使人和悦团结,有助于社会的移风易俗,能促进“王道之治”的实现。而乐教对人心的改善与提升作用在戴震的著作中罕有提及。
五、结语 [10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以“心”作为关键词分析比较戴震与荀子思想体系之异同,可以明晰两位哲人心性论架构模式的差异。在荀子思想中,性、心、欲、情是一源的,人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人心亦然。而戴震则把血气与心知拆分成人性的两个部分:欲望和情感根于血气,而仁义礼智来自心知,心知必然为善。
尽管两人都认为心具有认识、情感、思辨和统御感官的能力,但他们对心是否包含德道内容的判断存在分歧。荀子认为人性中具有仁义的资质,心也有向善的能力,但是心也好利,因此不能说人心本身就是善。而戴震主张心喻含仁义、心好理义,而且心中包含普遍的大共理,因此心知本善。在心与理的关系上,荀子认为心有认识理的能力并不等于心本身就是理;而戴震主张心中自具理义与大共之理。在心与欲、情的关系上,二人都肯定欲望的合理性,反对去欲寡欲,也都主张发挥心的作用以理制欲,但荀子认为情是性之实际情况,欲望是人性的显现与反应,心既能管控欲望,也会为欲望所驱使;而戴震主张人之常情之中包含常理,因此倡导以情絜情,让人与人之间彼此体谅与互助。在修养论上,两人都注重运用解蔽、学问修为和遵循礼法规范的方式养护心灵,但区别在于戴震批评荀子所说的“虚壹而静”的修养方法近于佛老,而且他也没有谈及乐教对于改善心知的作用。
由此可见,戴震思想的核心基调是孟子性善论,但他在建构自身哲学体系时,不仅继承与发展了孟子思想,也吸收融合了荀子思想。由于戴震与荀子对人性与人心关系的架构模式不同,所以二者在心性是否具有道德内容,心性是否必然成就善,以及心与理、欲、情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与分歧。因此,章太炎、钱穆等人对戴震思想近于荀子性恶的批评不能成立。
(责任编辑:陈 真 责任校对:禹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