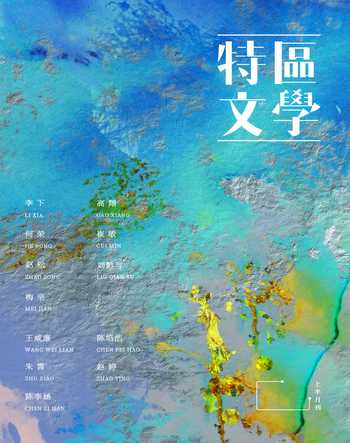分辨“同”与“异”的迷宫
开门见山,在我看来,管季的新书《性别意识、文化症候与情爱叙事—80后女性写作研究》是一部很有新意和锐度的文学研究著作,给我带来了一次新视野的启发。
我在这本书里,更好地理解了我的同时代写作者,尤其是女性写作者。我比较深入地见识到了她们在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才华、勇气与超越。以往,我不仅以“异”的方式去看待她们,也是以“异”的方式看待她们彼此。我觉得她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是那么大,她们之间的共性被我所忽略。准确地说,是站在自己狭小的立场上,失去了发现能力的那种忽略,是一种本质性的盲目。但管季让我看到了她们之间“同”的面向。我发现,这种“同”的确基于她们都是女性这个基本事实,从而让她们在“异”之外有着“同”的隐秘联系。我更是基于这种“同”,还发现了男作家的那种局限性。很多男作家非常强调写作是个体化的精神行为,仿佛都处于“异”的一面,置身其中,浑然不觉。但是,我忽然意识到,男作家对“异”的一面的格外强调,在女作家的“同”作为参照系的时候,就越加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换句话说,男作家的“异”正是在女作家的“同”的观照下,显示出了更加本质化的“同”。似乎有点绕,但如果想清楚这点,会发现性别话语对于文学的那种不可回避的重要性。女人需要自我觉醒,男人难道就不需要从某种幻觉中自我觉醒吗?
因此,管季对男作家是提出了批評的。她说,女性形象的类型化,往往出现在男性作家笔下,而在女性作家笔下一般很少出现类型化的女性形象。像《简·爱》《傲慢与偏见》或者《呼啸山庄》这样的作品,其女主人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着独立和特殊的性格。而以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来说,排名前列的长篇小说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活着》《废都》《秦腔》《芙蓉镇》等,里面对女性角色的塑造跟《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一样,逃不开男性那种“类型化”的审美。
她甚至决绝地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有效”女性形象,大部分都是女性作家来建构的。除了鲁迅笔下的子君、祥林嫂,老舍笔下的虎妞,曹禺笔下的陈白露等,或可一提,但与张爱玲、萧红、丁玲、冰心、凌淑华、冯沅君、庐隐等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相比,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
我本想为男作家们辩护几句的,但好像又无言以对。如果从某种女性的立场来看,的确如此。男性要彻底跳开自身的男性立场,何其艰难。
回到这本书的那些主角身上,她们于我而言,是让我惊异的同时代的“异”,她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书写,尤其是对于那种生活方式的自省,有着我难以企及的锋利。比如,管季以情感书写为线索,找出她们在文学题材上的一些共同场域:“在生活层面,这种低欲望社会,表现为女性的不恋、不婚、不育倾向。孙频、笛安、张悦然、文珍、蔡东、马小淘、颜歌、春树等大量80后女作家都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提到了爱情与婚姻的没落,以及当代年轻女性对于两性关系的失望。剩女、离异者、宅女、丁克等人群的产生及增长,也在文学作品中被如实呈现。这些现象既代表了女性对于自我理想的追求,也是这个特殊时代对于女性独立设置的某种障碍。”自我理想的追求与所处时代的障碍,是一种普遍的人生困境,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是身为女性和身为男性的人生,至少让这个普遍性可以一分为二,然后再在每个作家的笔下去细分。她们中的每一个在现实世界之外的写作中,都生出了坚韧不拔的诗意,如管季所说,让人看到了“80后”这一代女性灵魂中的翅膀,这是我深以为然的。
管季还用“阿尼玛原型”理论解读批评了我的作品。她没有事先告诉我,也许是想试探我的反应。
男性将自身的心灵力量,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并且将其压抑在无意识领域,在荣格的心理学说中,这种女性形象就是“阿尼玛原型”。我得承认,我差点看成“阿诗玛”,那是小时候见父辈男性常抽的一种香烟,现在似乎不怎么流行了。“阿诗玛”的香烟盒上,确有一个美丽的女性形象。
她说,阿尼玛不仅是灵感之神,也是男性对于美好的想象,从《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到《雪国》,那些美好的女性形象基本脱离不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审美想象;同样,在中国,从《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的“双美合璧”,到《边城》中的翠翠,到《黑骏马》中的索米娅、《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以及《废都》中的唐宛儿等,都体现了这种男性对女性的美好想象。
幸亏有了这些铺垫,她这才说我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将阿尼玛形象融入作品的创作规律,且更为符号化。她说我虽然塑造出各种女性形象,却并不注重女性心理过程的写实,说我在描述女性的过程中,其实是将女性作为一种象征物和男性思想的引领者,在两性互动的过程中,去完善某种哲学性的思考。这跟巴赫金所谓的“对话”异曲同工,女性人物往往成了男性主人公的另一个自我,他们互补和缠绕着,完成了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她也指出,我的小说跟前辈男作家相似,也是父权制的影子若隐若现。
她的解读和批评于我来说,是新颖的,不乏刺痛,从侧面迫使我要面对自己对于性别书写的某些观念。那些观念也许是习焉不察的,也许是刻意改造的,也许是文化塑造的,在这里便趁机简单梳理一二。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说,好的写作者应该是雌雄同体的,这个说法流布很广。在我看来,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在个体身上需要具备对于异性的理解与容纳;其二,男女对彼此的理解整合在一起,方能构成完整的人类。这和当代文学的伦理关怀是一致的。当代文学的精神指向便是必须写出他/她的深层的存在境遇,必须写出男性和女性所共同面对的人类命运。很显然,这是超越性别差异的。
因此,我觉得能不能先不要预设一种性别差异(想想看,性别差异是天然存在的,是想摆脱都很难摆脱的),而是要在一个超越性别的大视野中对男女一视同仁。只有站在人的基本立场上,男性才能真正理解和洞察女性的独特生存经验,女性也才能把男性从那个庞大的权力体系中分离出来,发现男性被遮蔽的性别经验。男作家写女性如果只是为了描摹得“像”,其实是远离了真实的女人,并在继续塑造着某种想象性的性别差异。只有以人的深层价值为尺度,忘记性别的差异,才会在写作的具体细节中发现因为生理的不同而在女性身上呈现的不同困境,才会发现历史、文化乃至经济对女性的束缚存在于哪些具体而微的地方,而不是徘徊在大而空洞的概念周围。我们不能忘记,从不存在抽象的男人和女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当然,由于女性在历史中长久处于被压抑的处境,女性的声音曾经是虚弱的,因而我觉得现代以来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有其非常重要的价值。为了使弱者的发声得到回应,即便偶尔夸张和刺耳也是必要的。女性主义文学不仅仅彰显了女性的意识,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改变和塑造了男性的意识。正是女性的崛起,才让男性从大而无当的历史概念中逐步回到了身体的存在。但我想,我们的写作还是得在性别差异中超越性别差异。书写女性经验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止步于建立一个性别经验的乌托邦是狭隘的,最终还是要超越性别的边界,对一切的男人和女人发声,对一切的强者和弱者发声,这才是雌雄同体的真义和力量。
我的这番想法,当然也是暂时性的,也注定是过于理想化的,是漏洞百出的。但我在这里不惮写出来,也是想回应管季的批评。我不是在自我辩护,而是想构造一个话语场域,让更多的视野获得敞开。尤其是面对未来,生物学技术一定会让性别超越原本的神秘前定,成为一种人的主动选择。到那时,性别话语不是会消失,恰恰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选择需要更加鲜明的“同”,需要更加鲜明的“异”,需要更加充分的生命诠释。
再闲笔几句。
管季是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为人谦和率性,性格中不乏豪爽。我对她的这点了解,实不相瞒,只是因为她也是谢有顺老师的学生,是我的同门师妹。在师友聚会中,酒量让我等男性望而生畏。我也知道,她嘱我给她的这本新书写序,显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我和她研究的这些女作家大多数都认识,有些还比较熟悉,是朋友,她想借助我这“异”的目光去看待她对她们的研究。无可否认,这也的确是一件颇有意趣的事情。从中也可以证明管季性格中的幽默和好玩。离开了幽默和好玩的学术研究,是一点儿也不好玩的。
不要忘记哲学家赫伊津哈说的,游戏才是人的本质。
但是何为人类存在的真正游戏?
我想,“同”与“异”算一个。
(责任编辑:朱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