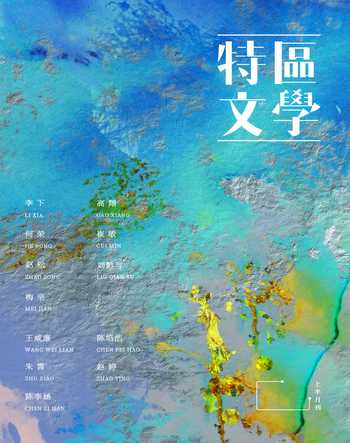夏日在雨后终结
高翔,生于1988年,辽宁人。小说散见于各文学期刊,曾获第38届香港青年文学奖。
他们来的那天,外面在下雨,一男一女,一人擎一把紫伞,小孩则披一件黄色的雨衣,远远看,如同两朵下降的愁云和一颗明星。
雨水顺着灰色的房顶淌下来,每到那种连雨季,旅馆入口的棚顶就会漏雨,总是没法彻底修好。我当时倚在旅馆的玻璃门前,打算把身边两个装满垃圾的巨大塑料袋送到街对面的垃圾箱,可是雨太大了,我一手只能拎一袋垃圾,无法打伞,会被浇透。我踟蹰在门边,罕见地消磨着时间。三个人走过来。我当时没有对他们问好,大概只是苦笑。这其实不是我分内的工作。
那对男女收起伞,对我颔首。披着黄雨衣的小孩则仰起头,雨水顺着雨衣的帽檐滑落,是个小女孩。她的父母走向前台,说他们有预订房间。而女孩跟我交谈起来。
“这里一直下雨吗?”女孩问我。
“也不是,最近才这样。”我说,“你不喜欢下雨?”
“不喜欢。”女孩噘起嘴,好像很委屈。她的眼睛很细,脸肉嘟嘟。“一下雨,夏天好像就结束了。”她说。
“哦。”我应了一声,觉得她这话很有意思。我对她说,我也不喜欢下雨,下雨让我没法出去倒垃圾。
“天气预报说下午才有雨。”男人在前台边抱怨。他人枯瘦,黑,显得有些焦躁,抽出一根烟想要点着。
“啧。”女人看了他一眼,男人把烟放了下来。
“没关系,我可以把雨衣借给你。”女孩说。我对她笑了笑,我很感激,但我告诉她,我太大了,会把雨衣撑破。
服务员很快帮他们办好入住,女人转过身,对女孩说:“妮妮,我们一会儿睡一觉,睡醒了,如果天好起来,我们再出去玩,好不好?”女孩点点头,有一种对待陌生人的客气。那对男女于是牵起女孩的手,一起走向客房的电梯。
直到中午,他们才再次从房间出来,眼睛都有些浮肿,穿戴的仍是来时的那套行装。那对男女说要带女孩出去吃饭,问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我告诉了他们一家餐馆,位置离这里较远,俄餐,餐馆二楼的露天阳台有俄罗斯人在上面拉大提琴。他们听后向我道谢,随后离开,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去了那里。
他们离开后,我拿着门卡,第一次进入了他们的房间,里面的光景我到现在还依稀记得,因为后来我又进去过很多次,它始终没有太大改变。
房间很暗,拉着纱帘,我把廊灯打开,屋子才亮了一些。门口的换衣镜前摆着三双拖鞋,其中两双是旅馆提供的,另一双则小小的,上面镶着棕色的卡通熊。我把那双鞋捡起来,拿到眼前端详,我看到鞋里还有底部都粘着一点沙粒,有股沙滩和海洋的味道。我猜想他们来这里之前去过海边。
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没将它视为自己的领地。背包整齐地码在置物架上,行李箱塞在电视柜与桌子之间的空档,除了白色被子的一角被折叠,上面布满褶皱,像蠕动的白色肉虫,为房间增添了一点生动,其它全部是拒绝的姿态。它仿佛身体的免疫系统,对于一切外来物保持着警觉。
环顾一番后,我回到门口,关上廊灯,准备出去。就是在那时候,我透过纱帘后的残光,看到一件被丢在盥洗台下面的东西。我走过去,俯身将它捡起来。
从他们的房间退出去后,我将门把手上“请勿打扰”的牌子重新翻正过来,接着去完成我那些未完成的活计。我来到杂物间,将那只搁置许久的铁桶拿到一楼,放在门口漏雨的地方,又拿拖布,将地砖仔细拖了一遍。地面终于不再湿漉漉。
两个小时后,三人回来,我与他们打了招呼,像什么也没发生。女孩对我说,她没有听到阳台音乐会,音乐家们好像今天不上班。我安慰她说总会看到的,只要她在这里待得够久。
女孩有些自来熟,接下来的几天,每次外出回来,她都会跑来找我聊天,有时只说几句,有时很多。我仍能记起她对我讲过的话,她讲她吃了两种口味的马迭尔冰棍儿,但她更喜欢香草味;讲她在长得像面包一样的石板路上摔了一跤,她以为膝盖会磕破,但是却没有;她还对我说起美丽的教堂,钟楼顶部像圆圆的洋葱头,还有广场上的鸽子,她的父母给她买了一包鸽食,她在广场上喂了很久。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喜欢跟陌生人交谈的孩子,毫无保留。我想那也许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她应该对许多陌生人这样做过。
他们入住后的第二天,傍晚,我正要去二楼的杂物间取东西,看到女孩一个人在走廊踱步,手里攥着一支矿泉水瓶,目光四处打量四周的空间,墙壁、地毯、楼梯,仿佛在寻找什么。我联想到,也许她是在找我在盥洗台下发现的东西,我将它藏在了门口的鞋柜里。我想,如果这东西对女孩来说是重要的,她应该会去找它。
因为过于专注,女孩起先没有发现我。后来我拍拍她的肩膀,她才转过头。看到我的那刻,她立刻将拿着矿泉水瓶的手别在身后。
“在找东西?”我蹲下来,装作疑惑的样子。
女孩摇摇头,隔了一会儿,又点点头。她问我,阿姨,你知道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吗?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环顾四周,想到一家漏雨的旅馆能有多安全呢?我问她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地方,女孩抿抿嘴,似乎困扰了一阵子,然后将背过的手伸到我的面前。
我从盥洗台下发现的是一枚钥匙扣,上面绑着一只粉色的小猪,圆滚滚,戴着一顶黑色礼帽,骑着扫帚,仿佛会魔法。这枚钥匙扣应该用了很多年,小猪原本的眼睛已被磨损,消失不见,它的主人用圆珠笔为其重新描画了一番。它有了一双新的眼睛,一只是蓝色的,一只是绿色的。我把它藏在了门口鞋柜的深处。
空瓶里爬着几只蜘蛛。一只看起来大一些,剩下的兩只体型较小。因为女孩的动作,三只蜘蛛各自沿着瓶壁爬行了一段。女孩看我没什么反应,似乎松了口气。她说她以为我也讨厌蜘蛛。我摇摇头,问她,为什么要捡这些蜘蛛回来。女孩回答我,因为它们很危险。
女孩说,蜘蛛是她在游船的时候看到的。那时候她坐在靠近船舷的一个座位上,她的头顶上架着一盏小小的灯笼。那艘船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悬挂着一只,船上别的灯笼都亮了,只有她头顶的这一盏没亮。女孩很沮丧,她希望自己头顶的灯笼也亮起来,于是不时抬头看,希望它只是暂时坏掉。可直到游船结束,她都没能看到它亮起来,倒是意外发现几只在灯笼架附近随风飘摇的蜘蛛。
“外面风很大,它们的网被吹坏了,只能在一根蜘蛛丝上走来走去,它们可能会被吹到水里,会被淹死。”女孩说。
“所以你想给它们找个安全的地方,是这样吗?”我问。
女孩用力点点头。我站起身,试图帮助女孩找到一个她所说的安全的地方。
“那边是什么?”女孩用手指向走廊尽头的那扇窄门。我看到那是杂货间的位置。
我将女孩领到那间杂货间前,点上灯,小小的屋子立刻亮起来。屋里面紧凑地摆着两排置物架,上面堆满清洁工具和一些很少用的杂物。朝东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女孩立刻喜欢上了这里,她对我说,这里很安全。她走到那个小小的窗前,将瓶盖拧开,试图把里面的蜘蛛倾倒出来,但它们紧紧地趴在瓶子里。没办法,我只好用剪刀把瓶子裁开,将蜘蛛们抓出来。
“别弄伤它们。”女孩叮嘱我。我将自己的动作幅度放缓,将蜘蛛一一放在窗台上。它们在窗台上停留片刻,便立刻四散逃窜,有的钻进柜架与墙壁的缝隙,有的顺着墙向上爬去。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我说,“它们很安全,这里只有我和另外几个女工会来。它们无聊的时候还可以看看窗外。”
“嗯。”女孩高兴地答应着,说谢谢阿姨。紧接着,她给了我一个拥抱。
那是一个小小的拥抱,女孩的手只够环着我的腿,头则勉强贴在靠近我腰部的位置。我微微躬着身子,一时手足无措,呆呆地站在那里,姿态非常古怪。
上个拥抱是多久之前?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去年八月的時候,我辞掉旅馆的工作,离开老家,来到这座边境城市。我有个亲戚在这边的一家物业公司做副经理。我只带了少量的行李,其中之一是从那个女孩的房间捡来的小玩意。
一开始我被安排在酒店工作,后来公司承包了政府业务,我又被调去政府大楼。都是做保洁。政府大楼是日本人建的,几十年了,外面是砖红色,后来被漆成了墨绿,它的里面像个迷宫,有很多房间。除了保洁人员的休息室和卫生间,其它的我一间也没进过。
在旅馆工作之前,我没上过班,在家带孩子。我的儿子有自闭症,三岁的时候去医院检查出来的,情况比较严重。医生说你就养着吧。回家后,我向我男人复述了医生的话。我男人说,那就养着吧。
儿子长到七岁,看起来已经很老了。有时候我看着他,就像看到未来的自己,我想我最终也会得那种痴呆的病,这是遗传吧,儿子发病早点,我发病晚点。
像全天下的母亲一样,我不能完全了解他,他经常独自缩在床上,目光呆滞,怔怔地看着墙角,忽然嚷一句什么。
世界在此后的每一天都收缩一点,如同敏感的软体动物,在触碰之后,变瘦,变小。我巴掌大的生活,只有儿子和那间西偏的旧房。那里夏季闷热,冬季阴冷,日子望不到头。出门就像放风,回去则像越狱犯人被重新逮捕。墙上布满粪便、尿液、彩笔、酱油的痕迹,我没再粉刷过,我以为还会有新的痕迹。
我不是没想过逃离这种生活,我也会设想新的孩子,新的家,房子的墙壁要粉刷成雪白。这令我惭愧,因为它如此自然。但我太粗心大意,一直以来,我从没想过,旧日子会以何种方式结束,一次也没有。等到它终于戛然而止,我才知道,生活跟想象、直觉、预感,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是突如其来的旋风,到来时只管将一切席卷。
终结的那天傍晚,我从母亲家回来,她摔断了腿。浓重的煤气味像鬼魂一样缠住我。我捂着鼻子,打开门,看到餐桌上摆着空酒瓶,半碟花生米。里屋的床上,儿子乖巧地躺着,丈夫仰在沙发上。他们都像睡着了一样,神情淡漠。我把煤气关掉,把他们拖到大门口,随后像个咿咿呀呀的聋哑人,将一些自己都听不懂的音阶从嘴里吐出来。那一刻我失去了语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打开了煤气。儿子,丈夫,还是,我?我出门前曾烧过一壶开水。我想不明白。这是生活留给我的另一个谜团。在梦里,有时候我会变成我的丈夫,在那个煤气环绕的房间,一切堕入沉沉睡意前,他已预感到危机,生命行将结束,却不想呼救,只是把原本闭上的眼睛,闭得更紧一点。
他们死后,我来到那家旅馆,老板给了我一间屋子住,在旅馆二层,我不必再回到原来的住处。我一直在那里生活,工作,直到遇到那个小女孩和那对男女。
因为蜘蛛的缘故,女孩常来找我,让我带她去杂物间,仿佛那些蜘蛛是她的宠物。我们不总见到它们,它们会爬上窗户,也会藏在各种堆积物之间,叫我们无法找到。有时候,我去晾晒床单、被罩,女孩在一旁帮忙。真是一个乖巧的孩子。我将床单的一头交给她,另一头攥在自己手里。我告诉她,我们要把这张皱皱巴巴的床单拉扯平整。她点头,表示明白,她愿意做我的助手。可当我们真的开始抻床单的时候,她却总不可自抑的大笑,仿佛这个行为触发了她身体的某个穴位。她小小的身子蹲下来,因为怕床单掉落弄脏,手还拽着那头,笑得咯咯咯咯,我于是也开始跟着她笑。我们乐此不疲,不断重复。“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她说她一抻床单的时候,就觉得浑身痒痒,手立刻没劲了。“阿姨,我费了好大劲才没让床单掉下来!”“那我还要感谢你喽?”我笑着说。等晾晒完床单,我们会在院子里待一会儿。院子的角落,有一辆废弃的白色吉普车,不知道是谁的,轮胎早就完了,座椅也变形的厉害,但我们总会到里面坐一坐。她坐驾驶位,我坐副驾驶。我从兜里掏出糖果或者瓜子递给她。她便一本正经地说她在开车。有时候,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真的以为自己在一条公路上,女孩开车载着我,我们一起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你愿意跟阿姨单独出去旅行吗?你敢吗?”有一次,我问她。她说,那有什么不敢的,阿姨是好人。
院子里传来女人的声音,她在喊女孩的名字。我原本以为时间被上帝点了穴,它已经停止了呼吸,但那声呼喊让我意识到它仍在流动。有时候,我们谁都不会吭声,仿佛在跟女人做一个游戏,假装我们真的开车去旅行了。我又变成了我丈夫。
我将车门打开,然后拉着女孩的手,将她带出废弃汽车。女人看到我们,立刻跑过来,将女孩的手扯过去,随后,她给了我一个难看的微笑,笑容消失时,眉头立刻蹙了起来。
我总时不时想起那孩子,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那时候我躺在旅馆的床上,眼前就会浮现出她那张圆嘟嘟的小脸,她的笑容足以驱走夏天的溽热,我感到幸福、宁静、满足,好像重新活过来。我自己的儿子始终抗拒与我交流,甚至对视。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这样做,但那确实会伤害我。我有时候会在别人的孩子那里寻求一点安慰,地铁、市场或者公园,那些孩子静静注视着我做鬼脸,看我将自己隐藏在一尊雕塑或者一棵大树后,然后再次出现。他们的眼睛微微放大,随后嘴巴咧开,爆发一阵口齿不清的笑声。我也对他们回报微笑,然后转身离开。与陌生孩子的互动令我满足,却意味着对儿子的背叛,我因愧疚而从不让这种互动过久。只有他死后,我才能稍微放纵自己。
从那时开始我不断进入女孩的房间,试图寻找她的影子,吮吸她的味道。那个房间自始至终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它和衣而卧,一派拘谨,物品摆放的位置也没有太大变化,只多了一些速食商品和一些零碎的渣滓。每次进去,我都会查看那枚钥匙扣的位置,看到它仍在原来的位置,我便很放心。我想我注定无法带走这个女孩,但有天他们离开,我会把这枚钥匙扣装进自己的口袋,作为纪念。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将那女孩作为了某种替代品或者是安慰剂,与那女孩相处的短暂的日子,令我感到愉悦,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她父母的反感,他们似乎对我与孩子的接触很介怀。二楼的走廊上,或者院子里,一度充斥他们呼唤女孩的声音。他们戒备女孩和我亲近,故意将呼唤的声量放大,做出焦急的情态。他们明知道女孩跟我在一起。我不是不能理解他们的反应。即出于安全考量,会想要替孩子提防陌生人的无故接近,或者担忧孩子跟我这样的人接触,会生出什么可怕的陋习。我与女孩只能见缝插针地见面。有一天,走廊又传来那个女人的呼喊。女孩忽然对我说,他们不喜欢阿姨。我装作镇定,但应该脸色十分难看。我对女孩说,没关系,我不能让所有人喜欢。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也许事情要比我想的严重。
后来发生的事,证实了我的预感,我本该在我们假装开车的时候就从女人的神色上有所察觉,并且及时收敛。
男人找我谈话那天,我正清理一间刚刚办理退房的房间,他单独朝我走过来。没有女人,也没有女孩。他先对我打了声招呼,然后对我说,他很感谢我的好意。
“什么?”我放下手中刚刚拆卸下来的床单。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额外地照顾,你帮我们照看妮妮,还帮我们收走屋里的垃圾,更换浴巾,我们很感谢,真的。但我想,你应该没注意我们门把手上的门牌。我们一直挂着请勿打扰。”男人说。
“很抱歉我没有注意到门牌,你知道,有时候我会注意不到这些细节。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这些都是我分内的。”
“我只是提醒你,我知道你做这些对我们有益,也很辛苦,一天之內,你会清理我们的房间不止一次。”男人干笑了声,“有些事情我们不说,不证明我们不知道。所以还是不麻烦你费心了。如果你再这样,我保不准我会干什么。”
我注视着男人的眼睛,对他说:“好的,下次我会注意。”
我在那间被退掉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男人的话让我汗流浃背,不得不思考他话中的含义。我担心他发现了什么。他们也许是那种会在旅馆自行安装偷拍设备的住客。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干过,一些不负责的清洁工,将擦完马桶的抹布擦拭杯子,被他们偷拍后,曝光于网络。他们也许同样看到了我,独自在房间中逡巡。我想他们也许已经掌握了我的证据。
我得说,旅馆的工作我一直干得不错。在保洁方面,我拥有其它旅店的员工所不具备的自觉。这一自觉源自我的服务意识,它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做到,但很少有人真的愿意为之—在打扫房间时,我一直尽最大可能消除保洁人员作为人的痕迹。这么说有点别扭,我是说,我会尽力在保持房间原样的基础上做清洁工作,如同罪犯离开作案现场前清理罪证。我尽量不让房客在回到房间后,发现这里像一片新天新地。
我预想的场景是这样的:当住客们回到房间,第一时间还来不及发现什么,他们感到一切如同他们出门前一样。他们将在房间里放松下来。随着与这间屋子发生更多互动,比如换衣服、洗澡、丢垃圾……他们又会发现房间有所不同地面被拖过,桌面的垃圾被一扫而空,旅馆配备的物品被归位……往往他们注意到这一切后心里会相当舒适,而且感到自己的隐私仿佛从未被打扰过。他们认为我叫他们宾至如归。
“真是麻烦你了。”他们说。
但我并非完美无瑕,我有小小的癖好,你可以因此否定我的人品,认为我下作、卑劣、手脚不干净。不过这就是我—我喜欢从住客的房间带走一些东西,一些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东西。最初的时候我能够克制这种欲望,可后来这成为一种习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那些被我从房间带走的东西,包括奶嘴、跳绳、夹在杂志里的枫叶、旧邮票和贝壳手串……还有,那枚钥匙扣,我因无法衡量它对女孩的重要性,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归女孩所有,所以暂时没将它带走,而是藏了起来。这些东西大多来自住客们敞开的行李箱、没有拉上拉链的背包,或者被直接搁置在床铺的表面。它们的姿态像是一种邀请,一切暴露在空间的事物对我都构成一种诱惑,仿佛希望我把它们带走。它们与各自的主人了断,却又保留着主人的印记,记载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所有一切都将成为回忆,再长久的,也会成为回忆。我试图把它们留下来,成为他们新的主人,仅此而已。
虽然这在我看来无伤大雅,可如果公之于众,我想那会对我的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不仅会成为罪犯,更会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疯子。我不想坐以待毙,如果他们手中真的掌握着我的一些证据的话,那我必须做些什么来挽回,而不能因为那个男人几句不咸不淡的话便自行远离,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得干干净净—那等于承认自己犯下了错误,陷于更加被动的地步。
那次谈话之后,我想到一个方法,或者说策略,那就是,我将以更加殷勤的态度面对他们,以此显示我的坦荡和磊落。在接下来的日子,我确实一直按照这一策略行事,我照旧与他们接触、攀谈,毫不退让。男人一开始对我的这番态度抱有敌意,充满怀疑,也许他更希望我会对他们敬而远之,不过后来我想他欣然接受了,我看出他有所缓和。
城市进入汛期后,那对男女和女孩基本没有外出,一直待在房间内。雨水不仅让旅馆前厅原本漏雨的棚顶更加难以为继,甚至还淹没了外面的街道,行驶的车辆犹如船只。不过那对男女在这里似乎有朋友,总有人冒雨前来旅馆看望他们,有时候是一对夫妇,有时候只是一个人。他们那些出入宾馆的朋友,都不太喜欢登记,让他们出示证件似乎是一件为难的事。我有时会帮着疏通一下,将他们放行。我对他们说,我跟他们的夫妻朋友很熟。我想我的这番举动应该会让他们得知。而我也适时增加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几率,碰面后神色如常地与之打招呼,自然、温和。与此同时,我减少与女孩的交谈,也不再踏入他们的房间。
有几次,女孩想找我说些什么,也许是希望向我传达新见闻,我都借口有工作,躲避了,或者只说很少的几句。最令她失望的一次,是她在杂物间的门口碰见我,央求我带她去里面看望她的几只蜘蛛朋友。我没有答应她,因为我看到她的父亲站在不远处。我只能当着她的面,将杂物间的门上了锁。看到她小小的、落寞的背影,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恐怕伤了那孩子的心,不过我告诉自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天终于放晴,是三人登岛的那天上午。雨水退去后,阳光凶猛,热气沸腾。那座小岛位于沿江对面,它此前被新建成一座公园,上面不仅有长颈鹿、鸵鸟之类的动物,摩天轮、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还有一片俄式的建筑群落。坐船或者搭缆车,十分钟就能到。
那天上午,我正在大堂打扫卫生。女人自己站在前台,正询问服务人员那座岛的情况,她本不想去,并且显得很不耐烦。“没什么意思,估计会有很多游客。我们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服务员听后,连忙推荐了另一处自然景区,但女人嫌太远了,她将手中的墨镜不断敲打著前台的桌面。
我试图再一次表达我的善意。我停下手中的活计,告诉女人,那个岛上有个地方,人少,他们也许可以去那里。女人立刻表现出兴趣,让我把话说下去。我发誓我说那些话的时候丝毫没有想过它可能带来的后果。
“是个湿地,平时很少有人去,上面有许多夏季迁徙过来的候鸟,我以前去过,可以告诉你位置。”我说。
“太好了。”女人说,她认为那个地方妮妮会喜欢。我将位置画在一张便签纸上,交给她。女人看后,塞进包里,又传了简讯,叫男人和女孩下楼。至于她自己,则率先走出旅馆大门,她拨通了一个电话,交谈起来。
因为天难得放晴,老板在当天找了一位做防水的师傅来,漏雨已经让门厅前的棚顶略微有些发霉,被水洇湿的部分,像一块不大干净的尿布。可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快中午,也没见到那位师傅的踪影,倒是那对男女带着女孩回来了。我以为他们会回来得更晚,因为那个岛很大,可以玩赏的地方很多。
女孩被男人抱着,头埋在男人的肩膀,发丝凌乱,看起来仿佛病了,病得很重。
“这附近哪里有药店?孩子不舒服。”女人对我说。
“她怎么了?”我问。
“热伤风吧,”女人一头汗,“孩子心情不好,她说她丢了幸运符。”
“那是什么?”
“一个小猪,钥匙扣,之类的东西,我之前见孩子拿过,现在找不见了。孩子非要闹着回来找。”
我忽然感到一阵轻松,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仿佛从我身上松绑。他们没能找到钥匙扣,或许证明了,没有人发现我将钥匙扣从盥洗台下拾捡起来,又藏在了鞋柜。他们没有我行为的记录,或许也压根没有针孔摄像头那类东西。一切都是我自己杜撰,自己吓唬自己的把戏。
“你们找过了吗?什么时候丢的?”我还是问了一句,以防万一。
“我也不知道,孩子也不知道。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昨天,也许早就丢了。说不清。谁能告诉我药店在哪儿?”女人问,旁边的几个服务员凑上来为女人指路。
我告诉她别着急,我知道药店在哪儿,让他们先把孩子送上去,我替他们买退烧药。
“在旅馆很容易丢东西,你们找找床与床垫之间的缝隙,垃圾箱,还有,”我说,“鞋柜,人们经常把东西落在鞋柜里。”女人点点头,对我千恩万谢,她说她会好好找这些地方。
“也许你能再帮我买一点安眠药。”女人说。
去买药的路上,我悬空的心终于放下。我既轻松,又有些沉重。轻松是因为危机解除,而沉重,则因为毕竟那孩子的发热有我一半的原因—我把她的幸运符藏了起来。而我最近对她的态度,也一定让她失望透了。我想着一定要尽力弥补一些,也许给她买几根香草味的马迭尔冰棍,或者多带她去看看她在杂物间的蜘蛛朋友。
再次站在那对男女房间的门口,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我没有掏出卡片径直进入,而是叩响了房门。
那对男女一起出现在门口,他们并排站立,入口因此显得十分拥挤。我将药品交给他们,他们表现出一副感激的样子,但并不打算让我进去。
“妮妮怎么样?”我问他们。
“睡了,等会儿我叫醒她,喂她点退烧药。让你费心了。”女人说。
“别客气,这孩子我也很喜欢。对了,东西找到了吗?之前我说了几个地方,鞋柜、床头……”
“都找过了,找不见,我们想可能是丢在湿地了。没关系,只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女人说。
“怎么会?如果是丢在旅馆……”我下意识说下去,但立刻制止了自己。我看到地面上停着几个纸团,上面一团红色,仿佛是血。
那对男女似乎并没有听出什么,他们坚持说,应该是丢在了湿地。我只好点点头,将身子向后退了退,告诉他们,如果有需要,随时找我。男女俩人连连点头,随后将门缓缓关上。
在517房间的门口,我站了一会儿,我没办法解释地面上红色的纸团是什么,女人为什么要我买安眠药。我只能怀着莫名的心情离开房间。随后我去杂物间待了一会儿,试图寻找那几只被妮妮放生的蜘蛛,但是我一只都没看到,它们似乎知道我来,都躲了起来。
下午一点,维修棚顶的师傅才匆匆赶来,我们为他找了一个梯子,让他爬上去,打开棚顶的盖子。他查看了一番,认为这工作很棘手。
“得弄很久,我后面还好几个活儿呢。”他啰啰唆唆,试图增加一点费用。我们没吭声,老板不在,我们没有办法擅自做主。他见没人回应,便从梯子上下来,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打起了电话,一会儿联络找人,一会儿又叫人带一些工具和材料。
“你们这管饭吗?我中午没吃饭。”过了一会儿,他说。
早餐时间虽然早就过了,但厨房还剩一些米粥、煎蛋、香肠和面食。服务员问他嫌不嫌弃,他便站起来,说:“在哪儿,我得先吃饭。”
服务员让我领着那位师傅去餐厅。我打开门,将他让进餐厅,那时,正好看到那对男女穿戴整齐,重新抱着妮妮来到大厅。
“抱歉,我们这儿维修,你们躲着点走。”旅馆的服务员对他们说,“这是要出去?”
“对,上午在岛上丢了东西,我们再去找找,你们忙吧。”女人说。
女孩正趴在男人的肩头,眉目低垂,仿佛仍在熟睡。既然孩子病着,为什么还要带出去?我正想出去问问,却被维修的师傅叫住。他冲我嚷,你瞅啥呢,还让不让人吃口饭了?我向他道了几句歉,随后跑去后厨帮他要吃的,等我热了饭菜,重新回到餐厅,男女俩人已经不见。
棚顶维修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那位师傅此后又叫来两个人,三人合力,才勉强做好了上面的防水,将棚板扣好。至于到底做得怎么样,只能等下一次雨天才能验证。几个人怨声载道,觉得收钱少了,第一个来的师傅问我们旅馆晚上有没有饭,他们在这对付对付吃了。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们悻悻离开。
我将掉落在地面的碎片、残渣清理干净,又拖了几遍地,才结束工作。我无心吃饭,心脏闷得厉害。外面气压很低,似乎又在憋着一场大雨。我于是回到楼上的房间休息。
其间,我睡着了一会儿,仿佛还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女孩一同坐在江边的观光船上,外面下着小雨,头顶的灯笼随着波涛摇摇晃晃,我们也摇摇晃晃。可是没过一会儿,那盏灯笼嗞嗞啦啦响了几声,忽然熄灭了。
“阿姨,灯笼上的蜘蛛哪去了?”女孩在梦中问我。
我醒过来,发现自己的对讲机在响,服务员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姐在吗?517退房,你过去给看一下。
我从床上坐起来,将床头的对讲机拿过来。收到,我马上过去。我说。
讲完我才意识到,517是女孩和那对男女的房间,他们要退房了。我连忙跑过去,刷卡,开灯,发现房间里一片凌乱。行李被带走了,床上堆满浴巾、塑料袋、衣架。地板湿漉漉的,有明显杂乱的脚印,带泥。卫生间的门开着,那里悬挂着女孩那件橙黄色的雨衣。我又去检查鞋柜,发现那枚钥匙扣,还静静地躺在那里,骑着扫帚的小猪,将脸对着我。眼睛一只蓝色,一只绿色。
“你们太大意了,妮妮的东西忘记带了。”下楼后,我对那对男女说,语气一如往常,亲切、自如,说完,我将女孩黄色的雨衣递过去。
“没关系,帮我们处理掉吧,”男人说,“外面不下雨了,这种一次性的雨衣穿几次就够本儿了。”
我对他笑笑。他们正在办理退房,我没看到女孩的身影。“妮妮呢?”我问他们。
“妮妮被她妈接走了,知道孩子病了,她妈下午赶过来了。现在他们应该到火车站了,一会儿我们也过去跟他们汇合。”女人说。
“啊,我以为你们就是妮妮的父母。”我感到惊诧。
“是亲戚。”男人说,说完立刻将目光从我身上收走,重新看向前台的服务员。
我点点头,将手伸进口袋:“对了,妮妮的幸运符……”
“那个我们下午在湿地那里找到了,就掉在草丛里,之前着急没看到。妮妮高兴坏了。谢谢你还记得。”女人对我说。
我原本伸进裤袋的手,在听到女人的话后,只得紧紧攥着。那枚钥匙扣,差点被我捏碎。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形同此前某一时刻我突然的失语。
办理完退房手续,女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是还给我此前为妮妮垫付的药费,见我没说话,将钱塞进我的口袋。男人这次终于点上了一支烟,女人没有责怪他。他们的心情似乎都不错。
我离开旅馆的时候,棚頂还是没修好,雨天时依旧向下淌水,仿佛无休止的哭泣。我将妮妮的那只骑扫帚的小猪,还有那件遗落的、橙黄的雨衣塞进行李箱里,那些来自其它房间的、不属于我的物品。我都把它们拿了出来,放进前台遗失物品存放处。我查询了那对男女的住房登记,他们都姓乔,身份证信息显示他们所在的城市是一座边境城市,对面就是朝鲜。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在那里见过他们。
后来我回过一次老家,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下葬那天,我跟家人一起吃了顿饭,我吃得很饱。饭后,我想出门走走,就出了门。那天天又下雨了,我在地铁站出口买了一把伞。我不知道要去哪。我先是走到了我原来的家,之后又走到旅馆,接着又不知怎么地走到了江边。我很久没来这些地方了,它们还是老样子。我在江边坐了一会儿,上空的观光缆车正沿着轨道,缓缓下行,它们在雨中闪着五色的光,像一簇簇小小的烟火。
一艘大船正慢慢在岸边停靠,一批游客下了船,新一批又上了去,即使下雨,他们的兴致依旧很高。售票员在船上喊着,“游江,游江,十块钱一位,还有座儿!”我想了想,站起来,对女人说,我没有零钱,能找吗?她说多少钱都能找,上来吧。我于是登上观光船。船篷雕龙刻凤,上面还挂着古香古色的灯笼,我看到其中有一盏不亮的灯笼,走过去,坐下来。
船客满了之后,大船缓缓开动,它先靠着江岸行驶,之后又转了一个弯,向对岸的灯火靠拢。是那座小岛。我手里攥着那枚钥匙扣,注视着江面,江水被江浪搅扰,又被砸落的雨滴激起水花,雨在水面上留下了自己的形状。这让我想到那个夏天,一个在雨中消失的夏天。
不知道旅馆里的那些蜘蛛怎么样了,刚才路过的时候应该进去看看,我想着。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即使是毫无用处、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不该由我评判。我不是它们的主宰。我应该尽早明白这些,我为此深深忏悔,在许多夜晚夜不能寐。
一个波浪,船震动了一下,身边的人们发出阵阵喊叫。我一惊,钥匙扣从我的手中滑落。
“咕咚。”
周围的大人和孩子再次爆发一阵叫嚷,似乎在为自己刚才的惊慌失措感到可笑。我看到那只小猪在水面留下自己的形状,之后转瞬下沉,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和那个消失在雨中的夏天一样。
(责任编辑:王建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