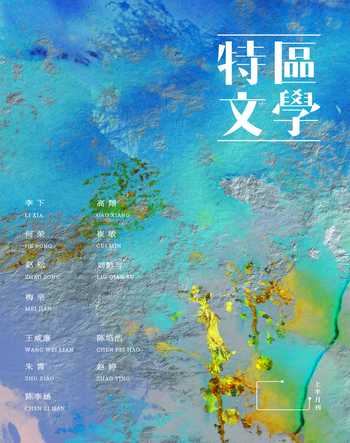葬礼
赵松,作家、评论家,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曾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小说《等下雪》入选2021年“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著有《伊春》《隐》《空隙》《抚顺故事集》《积木书》《被夺走了时间的蚂蚁》《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等。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还是二十六年前。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始终记得他。尤其是那个最后的场景:公司宣布解散的那天下午,他就坐在我原来的位置上,搂着那泡满茶叶的大玻璃杯,手里夹着根旱烟,笑眯眯地看着窗外。主任拎着一袋私人杂物站在门口:“老黄,你不走吗?”他慢慢转过头:“去哪呢?”主任一时语塞,尴尬地抖了下肩,就来到了走廊里。“走吧?”他递了根烟给我,然后点上那半根原本掐灭的烟,抽完。
其实,这些并不是我记忆里的,是我想出来的。真实的,是那个时间点。当然,我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这种虚拟的过去,对于你我来说,也还是需要的,总好过不知该说点什么。其实,看到你从那辆车里出来时,我多少有些意外。不是意外你也来了,而是你的头发都花白了。半年前你在朋友圈里发的那张照片里,你的头发还是染过的,全黑的。现在你戴着墨镜,再加上这身黑西装,要是再染黑头发,那真就没谁了。可是现在这头花白的头发,在这样的场合里,很让人唏嘘。
这个葬礼,我是前天下午登机时才知道的。手机关机前,收到了一条短信:今天凌晨,老黄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后天早上九点,将在北山殡仪馆五号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人敬请您到场。
我当时都没想起来这个老黄是谁。手机早就换过几次了,老家的朋友手机号只有少数还留着,前同事的都没了。我这次回来,跟这事没有关系,我只是回来看看,并无具体的事。在殡仪馆里,夹在来宾的松散队列里,我转到老黄的遗体旁,把手里那朵小白纸花放在旁边。有位前同事拉着我,对老黄的家属说:“这位兄弟是从上海赶回来的。”那个瞬间,我确实有些尴尬,但又不好说什么,只能默默地接受家属们紧紧握着的手,嘴里重复着“节哀顺变”。
来的人不多,我认识的,只有你跟那位前同事。我跟你说:“老黄的样子,我都认不出来了。” 印象里的他,不是这样的。现在看到的这个安静地躺在那里的人,是已然瞑目的陌生死者。你点了下头:“都这么多年了,估计他要是活着,也认不出你了,你看他的孩子们,都是三十几岁了。”后来,我们靠着告别厅门外回廊的护栏抽着烟,看着广场上的人。很多人在来,很多人在离开。焚化炉那高耸的烟囱正冒着黑烟。这里有二十个告别厅,每个都有不同的名字,里面都是人,放着哀乐,传出哭声,留下很多纸扎的小白花。结束一场,就换掉背景,再来新的一场。
我钻进你的车里时,你已想好了去处,是临近河堤的一座大厦顶层的日料餐厅。开车去那里,要个把小时。“这次回来,”你说,“你怎么都不说一声呢?”我就解释,回来的计划早就有了,可是这几月里,你也知道的,行程只好一推再推,光是机票就退了三次。只是,我并没有告诉你,最近这段时间,我主要是忙于应付公司破产的事。这是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所以,当你随口问我的公司怎么样了,我就说:“还行,老样子。”你点了点头:“那就好,现在这环境,能说还行,就是不错了。”你一直都没摘下墨镜,我也就看不到你眼神的变化。你降下车窗,把那包烟递给我,而我正做出犯困的样子,其实不是困了,是我忽然有点尴尬的感觉。算起来,我们至少有半年多没说话了。
在我们之间,累积了二十七年的时间。最近这五六年里,你我说话的频率,保持在每年两到三次的样子。跟早期那十来年里的密集交流相比,你我都会承认,确实有太多的空白。没见面时,这种空白感倒也并不明显,就好像那漫长的时间本身就会自然稀释它们。可是等坐到了你这辆车里,面对如此近的距离时,它们就忽然都冒出来了,估计你也能感觉到,不是那么容易填充的。比较方便的,还是让话题回到老黄这里,不然的话,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老黄呢,我刚调到公司时,他还在农场开半截子,就是那种小型货车。每到周末,他都会出现,车里满载土鸡蛋、新鲜蔬菜和活的土鸡。他拎着那个大玻璃茶杯,叼着根烟,晃到办公室里,找个角落坐下,就不再出声了。晚上下班后,他就开着那辆半截子,跟着主任把那些东西送到领导家里。主任没空的话,就是我带着他去。他这人,永远是笑眯眯的,话极少。有一次我就问他:‘你怎么话这么少呢?他握着方向盘,注视着前方,慢悠悠地答道:‘一个开车的,要什么话呢?话多招人烦的啊,车豁子,一身的土气,没事就该把嘴巴闭上。”
听到这里,正表情严肃地开车的你忽然就笑了:“车豁子,这个说法倒是真够久远的了,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对老黄也没什么印象了。”你說着,就把车窗又升了起来,这样说话就清楚多了。“要不是我妈提示,”你继续说着,“我也想不起来老黄还给我爸开过车呢。再有就是,我爸去世时,他是最早到的,忙前忙后的,也不怎么说话,直到所有的事都结束了,他才不声不响地走了,挺实在的。那时他也就四十出头吧,就是长得比较老,黑黑的,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不少。现在能想得起来的,也就这些了。哦,老黄好像也是当过兵的,跟那个农场的场长,叫什么来着,据说还是一个连队的。”我说他应该是姓贺。你也想起来了:“对,是姓贺。”你摇了摇头:“好多都想不起来了。”
“他们两个,”我接着你的话头继续说,“都保持着部队的作风,喜欢穿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胡子永远都是刮得光溜溜的,走路时腰板永远笔挺。”你就笑道:“对,练出来的,肌肉记忆。”
“老贺属转业干部,老黄则是退伍兵,所以老贺是干部编制,而老黄则只能按集体职工安排,差别还是挺大的。”
你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前天晚上去老黄家里了,在西郊那边一幢特别老的破楼里,他家里也是破破烂烂的,那日子过得……他那两个儿子也都是开车的。说实话,从他家里出来,我有点时空错位的感觉,就像刚从另一个时代又穿越了回来。据他老婆说,他这人就是脾气不好,开过几年出租,经常莫名其妙地跟人起冲突,什么事都看不惯,跟年轻时没啥两样。有一次还把乘客打了,那是个喝醉酒的家伙,上了车就骂骂咧咧的,最后他把车开到河堤路上停下,就把那人打了。人家就报了警,他被带到了派出所里,最后还是老贺把事情摆平的。”
你说的这些,我也是知道的。不过由你说出来,感觉还是不大一样,至少,这些往事似乎能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你我的距离。趁着你意犹未尽,我就接着说了下去。“我到公司第二年的夏天里,公司决定去北戴河玩两天,你爸跟黎书记,以及三个副经理,都去了。但是很多细节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到达时天还亮着,离晚饭还有段时间,你爸要去酒店房间里休息,黎书记则拉了几个人打麻将。那年我才二十三岁呢。后来,第二天吧,老黄的车坏了,刹车片的问题。主任就安排我陪老黄去最近的修车厂,等修好了,估计也是周日了,我们就直接回抚顺了,没跟主任汇合。”
你忽然笑道:“你的记忆力还可以嘛,这么遥远的事情了。”我说:“记忆力这事,也挺难说的,你看那次去北戴河,别的没记住,就记着我跟老黄去修车的事了。”
我和老黄是周六下午出发的。那辆车还可以开,但只能以最慢速度行进,跟自行车差不多了,稍一快,就刹不住。老黄还给我演示了一下。这破车早就该大修了。当时天很热,车里空调也坏了,只能开着车窗,有点风进来,不至于让我们中暑。我们也没什么话。他抽的是自己卷的旱烟,不抽卷烟。我抽的是红塔山,是主任在临出发前塞给我的两包。这烟其实是主任带着给你爸抽的,据说你爸当时只抽这种烟。
你开着车从山里转出来,过了半个多小时,就又看到了不远处的那些连绵的山丘。此时车已驶上了河堤路,我陷入了沉默。其实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老黄开车的场景,而是你爸抽烟的样子。我想告诉你,当时我是有些怕他的。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氛围里并不适合说这些。山在河的北岸,连绵起伏的,好像后面还有很多山,实际上并不是。它们是长白山的余脉,要是看谷歌地图上的图片,确实就像个尾巴。我十几岁的时候,曾跟人去过山里,不到半个小时,就走出去了,发现后面都是平原。要是想看更多的山,就得朝东走,在十几公里外,才有逐渐高起的群山。在父母辈的话语里,有个“东部山区”的概念,指的就是这些山汇聚的地方。我从没去过那里。
你侧过头,瞄了我一眼。我就继续说了下去。“当时老黄那车啊,不能再慢了。我发现,他也是够有耐心的,以这样缓慢的速度行进,也没见他有丝毫急躁的意思。有时看着他,甚至还有点老僧入定的感觉。他是看得开的,急又有什么用呢,老话怎么说来着,既来之,则安之?我点头称是。他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种车况,是不能走国道的,被交警发现就麻烦了,只能走便道。”
这种狭窄的路上,经常会遇到农民赶着羊群,或是几头牛,就在马路上走着。有时还能遇到成群的鸭子。道路两侧都有高大的白杨,在盛夏的骄阳下轻微地摇晃着,很多叶子翻转出有些发白的那面。老黄似乎没有意识到,当时我其实是挺享受那种坐在车里什么事都不需要想的状态的,他甚至会觉得我肯定是有些无聊的。后来他就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其实,你是不需要来陪我的,就这么点事,我挪到地方,把车修了,就没事了。”我说没事的,反正我在那边也是没事的,陪你出来,也有个照应。他笑了笑,就不再言语了。前面延伸中的柏油路面,感觉都被太阳晒软了。树行后面的田野上,只有茂盛的庄稼,偶尔还有几块绿油油的菜地。当时我就觉得啊,这种感觉真挺好的,有种正在远离现实世界的感觉,也不需要说话。
你开着车子穿过那座老桥,转了几转,就到了那座大厦门外的停车场里。从车里出来,到坐电梯,直到那大厦的顶层,我们都没有说话。我感觉之前建立起来的那种没有什么距离的感觉又渐渐瓦解了。你订的位置,在那个圆形餐厅的西侧窗边,你能看到北面的山,我能看到南边的河面。你说过一会儿,就能看到落日了,就在河转弯的那里,你指了指。现在,那里还只有在西斜的日光下白亮亮的河面,河堤路那里也是白花花的,树林的绿色都是发白的。天空中有层非常轻薄的云气,让强烈的日光变得更加耀眼了。
我仔细想着,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年你爸去世时,我有没有去参加葬礼,甚至都想不起当时我是不是已经在南方了。主要還是想不起那是哪年发生的事了。我只能想起很多年前曾经参加过你爷爷的葬礼,或是你姥爷的。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一起去送葬的,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但具体是谁我也不记得了。最近这十来年,我跟他们都是失联的状态。有时我也能想起几张面孔,只是想不起名字。
你从洗手间回来,表情轻松了许多。没有了墨镜的遮掩,你那温和的眼光也让我觉得亲切。你为我倒满啤酒,然后自己也满上,我们碰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啤酒冰凉,深褐色的瓶壁上缀满了水珠。就在我犹豫是否要继续说跟老黄一起在路上的故事时,你点了根烟,然后说道:“这里的好处,就是可以抽烟。”我们都笑了。
“这是我今年参加的第四场葬礼了,”你继续说着,“前面三场,都是老朋友,只有老黄算是不熟的。不过听你讲起来过去那些事,感觉还是挺复杂的。你讲那些事时,其实我是有点走神了,也不是说没兴趣,而是不太能共情,毕竟我跟他也不熟。说实话,我现在不像你那么喜欢回忆往事,半年多前,你跟我在微信里说起一些我们年轻时的事,我之所以没回你,不是因为觉得那些事不重要,而是觉得太遥远了,不知该怎么回应才好……我现在就是活在当下,不想过去,也不想未来……这是适合我的状态。”
“这样确实是挺好的,比较踏实。” 我附和着。
你把烟灰弹到烟缸里,恢复了那种对一切都有些漠然的神情。“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吧,”你又说了起来,“平时我基本上不大能想到过去的老朋友们,也包括你了,这么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出我自己的真实状态……你是知道我的,我从来不会为了刻意维持关系而没事聊上几句。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活得真实才是对的,不需要勉强自己。过去的那些记忆,不管说起来多么美好,都像宴席一样,最后都散掉了。是不是听着有点绝情?当然,每当听到朋友们,比如你,在外面都发展得挺好的,我还是会为你们高兴的,大家都走在各自的路上,走得安好,就好。”
我们碰杯,干掉了一杯冰凉的啤酒,像在庆祝什么。
我只能在脑海里回想我们过去的那些美好时光了。你在说你掌管的文化馆里的事情,最近策划的社区音乐活动,邀请来了一些本地著名音乐人,效果非常地好,还来了很多重要的人。这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很久以前的那个冬天里,我跟你去一个玩摇滚乐队的朋友那里,在那个只有五平方米的小仓库里,我们都没地方站着,只能坐在地上的板凳上,我面前就是那套架子鼓,那把电吉他就在我头上摇晃着,而在你头上的则是电贝斯……当时是傍晚五点多,气温是零下十几度,我的下半身都是冰的,可脑袋里却起了火,被那强烈的音响效果冲击得就像马上要炸裂开了似的。后来,我们就跟乐手们去喝酒,那种最便宜的白酒,也能喝得兴起,我跟你都是超量发挥。
那时你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你还曾带我去一位电台主持人家里玩,说是去验证一下以说话为生的人在业余时间里几乎是不怎么说话的状态。你说得没错,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确实就是不怎么说话的,但她喜欢听别人说话,那些不爱说话的人,她是不欢迎的,说是只有跟话多的人在一起,才能让自己心理恢复平衡。你还带我去拜访过一位老中医,其实并不算老,也就五十几岁的样子,只是留着长长的胡子,看着像个老头……你想让我见识的倒不是他的医术,而是他还是个太极高手。我还跟你去一位住在远郊的开小酒坊的朋友那里,去品尝新酿的玉米酒,也是在冬天里。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他们家的酒,而是在那幢小楼顶的露台上吃酸菜火锅的场景,晚上七点多了,我们吃喝正在兴头上,忽然下起了雪,鹅毛大雪。主人说,咱们继续啊,多好啊,这大雪。
在你说起最近见过的一些重要人物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当年你发现的那家杀猪菜小馆,那里的五花肉血肠炖酸菜锅,直到现在也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还有那位漂亮的女主人做的腌黄瓜也是一绝,清脆得能让人落泪。当时我说出这太过夸张的赞美话时,你还笑我意不在此。现在,我尽可能做出正认真听你说那些重要人物的事,同时也为自己的游离多少有些歉意。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这张摆满酒菜的餐桌,而是很多年里累积的空白,我沉湎于过去,而你呢,只在乎现在,就像暮霭沉沉的城市上空,飘浮的两只大型气球,相距几公里。
伴随着你的说话声,我保持着不时点头的状态,为了显得真实,我不得不尽量放慢点头的速度,偶尔还会屏住呼吸,以配合你讲到重要细节时的那种庄重的感觉。让我有些奇怪的是,这个日料餐厅今天客人很是稀少,这偌大的空间里始终都处在某种过于安静的状态里,即使是播放着音乐。尽管每份菜量都不多,但菜还是点多了。空盘子撤下,又有新上的菜占据了空位。你似乎意犹未尽,又叫来服务员,要了份盐烤秋刀鱼。我完全能领会,你这貌似不经意间点的最后一道菜里所隐含的心意,这是当年我们在北京第一次吃到日料时点的唯一一道菜,当时看着菜单上的价格,我们只点了两碗拉面,还有那道盐烤秋刀鱼。
其实,你之前讲的那些,与之相关的图文,我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都看到过。听你以如此严肃的口吻又讲了一遍,会觉得有些怪异。而我的眼光在碰上你的眼光时,估计呈现出的,是那种能跟秋刀鱼记忆相匹配的光泽,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感觉。就在此刻,颇为应景的是,日落出现了。你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缓慢地往后靠去,侧过头,点了根烟,然后就默默注视着,那正在低处云霭上短暂停顿的、那轮依然明亮的红日。
我略微侧过身子,注视着它,那炭火般通红的落日。可是,就这种天然的容易引发抒情状态的氛围里,我却想到了老黄的遗容,一个我不能认出的面孔,被殡仪馆里的专业化妆师精心修饰过的,像是涂了层微微有些发黄的油彩,跟蜡像馆里的人像面孔有些相似。当年,我坐在他身旁,在那辆以极慢速度前行的小货车里,也遇到了落日时刻,当时刚好经过一段没有树木遮挡的地方,落日余晖从我这一侧的窗口射进来,让我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火星般的红色。我转过头去,发现老黄的脸已是暗红的。他喃喃自语道:“你看啊,这个时候,你要是没跟车出来,就在跟他们吃饭喝酒啦,然后还可以打打麻将,到海边转转……你跟我又不一样,你是在领导身边的人。”
后来,天黑了,我们仍然在路上。他说不远了,再有一个来小时,我们就到了。
我跟老黄怎么回抚顺的,是完全想不起来了,就像跟那次北戴河之行相关的其它记忆一样,都被抹掉了,只剩下灰茫茫的空白。哦,我还记得一个场景,就是那破车终于开到能望见修理厂大门那里的灯光时,老黄忽然笑道:“那个门口啊,原来有个花坛的,据说曾有人深夜里开车过来,没开大灯,结果就直接撞了上去。是那种大解放货车,司机踩了急刹车,可还是撞上了,他旁边那个副驾驶的脑门直接撞到插着车钥匙的地方,结果,钥匙尾部插进他的眉骨里,险些插瞎了眼睛。”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这个副驾驶,就是我。”
你端起啤酒杯:“咱们碰下酒吧。”我这才回过神来,坐直了身体,跟你碰了杯。我又一次看了看这个餐厅里的那些空着的座位,终于还是问了出来,为什么这里人这么少呢?“他们家周末是订不到位的,”你拢了拢头发说道,“但平时就很清静了,我经常来这里,为的就是这份清静……这里适合招待你这样的贵客。”说完他就大笑起来:“可以随意说说话,也没人在旁边吵吵闹闹的……我呢,现在别的都无所谓,就是喜欢清静些。有时间你可以到我办公室来坐坐,喝喝茶,我那里是在文化馆的最顶层,视野开阔,特别清静。”
不知不觉间,已是晚上八点多了。你看了看手机,说:“我送你回去吧,反正我也没别的事。”我本想自己打车走的,见你并不是客套,就不好推辞了。我们乘电梯下了楼,走到露天停车场,就在你的那辆车车灯闪了闪时,我抬起头,看到天空中有一弯淡淡的新月。你叹了口气,钻进了车里。我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系上安全带。
你发动车子。“唉,时间过得还是太快了……前面你说到我爸时,我忽然就有些恍惚,就感觉他不是离开这么多年了,而是不久前才走的。他那个时候,知道咱们是哥们儿的,对你印象还是不错的,觉得你人老实,当然也比较内向,有时看不出来领导的意图,可是那时你才多大啊,很多事也是要学才能会的。不过你出去这么多年,变化也是挺大的,几乎就是变了个人,挺好的。你是做事的人,不像我,没什么追求,就喜欢守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过自己的小日子,悠闲惯了。一个人一个活法,各有各的道理。”
不胜酒力的我,就这么几瓶啤酒,已经让我晕晕乎乎的了。我把头往后一靠,面带微笑地听着你说话。你看了我一眼,笑道:“你这酒量,这么多年了,还是没练出来啊,看来这是你唯一没变的。”
其实你不知道,此时此刻,我正在缓慢地滑入伤感里。你同样也不会知道,就在你讲到你爸对我的评价时,我的某段遗失的记忆又意外地浮现了,让我有些猝不及防。
那次在北戴河入驻酒店之前,我们都站在大堂门口,平时很少发火的你爸,出人意料地爆发了,为了我疏忽了安排入住的几个细节。“那我们让你来这里是干什么呢?”他大声说道,“既然你连这些细节都想不到,那我们为什么不让其他人来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需要你。你现在就可以问问这里的所有人,有人需要你吗?”我呢,就像被閃电击中了,整个人都烧焦了。我的眼睛模糊了,完全说不出话来。后来只听到主任在替我解释,表示责任在他,这件事并不是我负责的。可是你爸仍然在气头上,继续大声说着:“他这样怎么能在我们身边做事呢?!那还不如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回炉再造,造好了再回来!明天不要让我再看到他,你看着办吧。”
就这样,那天深夜里,主任找到我,语重心长地宽慰了半天,让我理解领导的良苦用心。最后,他说:“明天啊,你就陪老黄去修车厂,这样也就没事了,你也不是没做事,等回去了,领导气也消了。根据我的经验,他是被别的什么事气到了,就是借你发泄一下而已,咱们作为领导身边的人,挨骂是正常的,不挨骂,倒是不正常的了。骂你,说明他没把你当外人,不用顾忌什么。”
我想起来,那天坐在老黄那辆破车里,我几乎是闷了一路,总共也没说过几句话,关键是直到回抚顺,都没能从那种深重的挫败感中缓过来。我甚至都忘了后来有没有跟你说起过这件事,在潜意识里,我应该是把与此相关的那些记忆统统抹掉了,只是我没想到,其实没有什么记忆是真的可以抹掉的,只能是被遮蔽了,被掩埋了,在大脑皮层的那些褶皱深处。时隔这么多年了,忽然重新回想起那个场景,我还是有种被瞬间击中的感觉,尽管那种随之而来的痛感无法跟当年相比拟,但仍然是足够强烈的。我降下车窗,把手伸到了外面,让它随着外面气流上下浮动。你开得太快了。
你伸手点了下播放器:“给你听听这个吧。”是大提琴曲。
我听了听:“巴赫的?”
你笑了:“对。”
“罗斯托罗波维奇?”
你又笑了:“你还真记得。”
“应该是那个在一座大教堂里演奏的吧?”我继续表现出默契的状态。你摇头,“这个倒是真不清楚了。你还能想起最早咱们是在哪里听到这支曲子的吗?”
我想了想,想不起来了。你就平静地说:“是在咱们厂工会那个喜欢古典音乐的老兄家里,听的还是唱片呢。”哦,我点了点头,可是,我甚至连这位老兄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他呢,”你继续说道,“我上一次参加的葬礼,就是他的。那天在殡仪馆里,遗体告别的时候,没放哀乐,放的就是这支曲子,无伴奏大提琴。”
车子还在河堤路上飞驰。你把音乐声调到了最大,让我有种被淹没了的感觉,也让我有种重新回到现在的感觉。“他那么洒脱的一个人,”你沉默了片刻后又接着说道,“到最后却是百病缠身,才五十二岁,就走了……他临终前,我去医院看他,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点了下头。那双眼睛啊,我到现在也没法忘掉。他整个人都瘦得不成样子,那双眼睛,原来是多么的精神,可是当时看上去,却像小小的两汪浑浊的水,几乎看不出光泽了……其实我现在特别想忘掉这个场景,甚至彻底地忘了他这个人。”
在到达我住的地方之前,最后那十几分钟里,我们都没再说话。你表情冷漠地注视着前方,好像是在凝视着远光灯扫射照亮的那些忽然从黑暗里浮现的景物。从某种气息里,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距离感的出现,那种此前跟着大量空白一起在不断累积的距离感。我已经接受了这种必然会出现的状态,甚至已经想好了下车时要如何跟你道别。我让自己处在某种诡异的放空状态里,觉得任何事都无需再想了。车窗不知何时关上的,音乐声也消失了。我能听到的,只有车子飞速前行时发动机发出的那种轻微的响声,跟车身摩擦空气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车子停下了。你递给我一支香烟,举着打火机,为我点燃了。你自己却并没有抽烟。你看着前面,手搭着方向盘,等了等,你才又说话了:“那天,你在微信里,跟我回忆几段美好往事时,我正在外面开会……当然也不是没法回复你,只是,当我看到你又说到你连续两次梦到了我,还描述了梦里的场景时,我其实想回你的,是一句你想不到的话……當然,不是我说的,是弗洛伊德说的,原话我也记不清了,只能复述大意:当你反复梦到一个人时,说明那个人正在遗忘你。”
(责任编辑:胡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