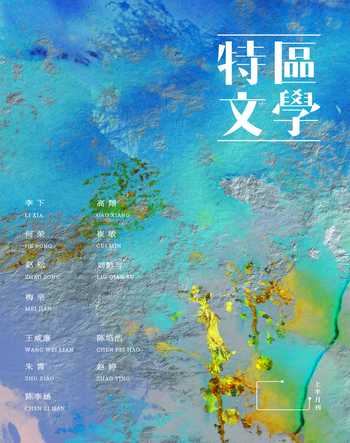藏身
“好的,你可以走了。”警察收了笔,点头示意。
赵安萍试图站起来。左腿伤还没好,她下意识觉得右腿也有些软。
慢慢才出了门,外面的阳光洒在包裹的石膏上,映出一个奇怪的形状。已经是九月份,地上铺陈着铜钱大的碎光,南方夏天的余温还没有消散的迹象。路上有小孩在飞跑,父母跟在后面笑。四处都暖融融,很难不舒服。
她捏着手里的车票,忽然想起自己的孩子来。
一
结婚那天,赵安萍没请一个人,单方面免了场酒席。李峰顺对此大为不满,连着嘴碎了好几天。赵安萍就挑着眼,把银行卡余额递给他看。这人噤了声儿,讪讪地瞅她脸色,心里有些不甘。所以转身就瞪了赵忠宁一眼。
赵忠宁是她儿子,正读市里的高中,但和李峰顺没什么关系。赵安萍结婚不请人吃酒,也有点二婚的原因。离开县城好些年,赵安萍却仍然下意识觉得,人们都不太待见二婚女人。她的第一任丈夫沉默寡言,除了发工资的时候,决不主动同人讲话。有次她不在家,儿子要家长给试卷签字,简直让男人大为受惊。他单位不在体制内,薪酬微薄,赵安萍那时常常对此胆战心惊。所以,丈夫去世那天,除了悲痛,她还隐隐约约松了口气,自此不必担忧他失去工作。
相比起这一个,李峰顺要灵活得多。饭桌上极少有他插不进的闲话,自己还特别喜欢编扯哄人。因此,赵安萍一边盼望他找到个靠谱工作,还私心想着最好能包食宿。
两个人原本没什么交集。那时丈夫才去世几年,赵忠宁刚升了高中。因为学校离家有些远,每周不一定能回来。日子一长,赵安萍就干脆退了城里的房子,一个人搬进了城郊的廉租房。她平日里在居委会打下手,偶尔还会去学校看儿子。李峰顺当时是个大巴车司机,线路正好经过市高中。一来二去,两个人在车站上熟起来。这附近圈子小得很,后来经几个闲人撮合,就搭在一起过日子。
赵安萍对此始终感到恍惚。一年间,她看着李峰顺从三号线换去了五号线,几个月后又被撵出来,在隔壁修车店干了几天的活儿。兜兜转转,如今的李峰顺待在家里已经快半年。赵安萍不再看着他出门,只能盯着他整日吧嗒着嘴,露出逐渐泛黄的牙齿,还有额头上愈来愈深的一道褶子。
那牙齿上腻出一层膜来,却不完全覆盖,所以眼见着越来越黄。
赵安萍感到恶心。
他们结婚没费什么周折。男人没有房子,赵安萍也不大在意,就直接叫他搬了进来。省城的廉租房是标配的一室一厅,还算是健全,但因为多了个人,一下子变得拥堵起来。李峰顺自己买了张床,放在客厅里,正对着门。赵安萍就从卧室里搬出来,和他一起睡客厅。儿子平时不在家,但就此有了自己的房间。
一进门就是客厅。来人能看见桌子和床紧挨着,桌子挺干净,还齐齐摆着几本书。屋里没有沙发,只能在床边围坐一圈。居委会的人有时来串门儿聊天,几个认识赵安萍的女人就笑,对这个男人露出几分轻蔑来。李峰顺每次都嬉笑着扯开话题。但这样的事情一多,他就会躲出去,口里念叨以后会买大房子,但往出走的步子却丝毫不停。
这一片区的人都挺同情赵安萍。结婚前李峰顺倒是规矩,估计是忙打工不着家,但后来一直没有工作,人就像是变了。很多人亲眼见过他在超市里偷摸拿些零碎,被逮住了也决不承认。就算是老板从他兜里把东西拿出来,他都只是面不改色地溜达出来。这导致他的风评越来越差。一旦李峰顺进了店铺,周围人都会不自觉地盯着他看,这人也就仿佛完全感受不到。最严重的时候,连赵忠宁回家都能听见有人在背后指点,叫他回去找他妈来给男人结账。赵忠宁扛不住这种目光,对李峰顺的态度越来越差,甚至有意减少了回来的次数。
小区几个肉菜铺子多少都被占了便宜,连着对这一家人都很有意见。大多数人都等着女人来收拾李峰顺的一堆烂账。
但赵安萍一次也没有出现。
二
隔壁的女人又在哭了。
赵安萍在床上翻了个身,眼睛怎么也合不上。那声音细细碎碎,从四处往她的耳朵里钻。哭声断续着,还伴着些咳嗽,几乎能想象出那女人压抑的表情来。
小小的县城,如今也有了省城的味道。
先是剧烈的摔门声,哭声才慢慢响起来。此前还有东西落地的闷声,以及来去推搡的摩擦。赵安萍盯着屋顶,分了点神,心里怨这老房子隔音太差。邻里的秘密一点也藏不住,单叫人尴尬麻木。
她不清楚隔壁住了什么人,只是偶然见过闹剧里的主人公。一男一女,估计也就三十多岁,记不清脸。赵安萍刚搬过来时,夫妇关系还算是正常,但短短一年里吵架次数却越来越多。
她对此并不关心,只是声音实在恼人。
小城的十二月,气氛颇有些剑拔弩张。这与赵安萍的记忆相差很大。她从小住在这里,长大又离开多年,从未想过小城也会有后来。南方的省城柔化了赵安萍对冬天的感觉,偏北的家乡就给她一记重重的耳光。临近年末,风越是呼啸凛冽,人们也越是冷漠嚣张。为了一朵小小的花菜,几个女人能原地对着掐起来。
夜里的小城不再极静,而是热热闹闹。母亲留下的房子在老城区,是人流来往最多的地方。城管整日在这一带巡逻,小贩们清早就来回奔波,倒不是会被赶走,而是忙着做整个老区的生意。赵安萍一个人住在这里,早上出门买菜,回来后一整天也很少出去。要等晚上邻居们闹起来,屋子里才像是有了人气儿。
老式的住房楼,赵安萍最能听到的动静,就在隔壁和上层人家。
隔壁的哭聲还在继续,只是更低了些,几乎快要听不清。头顶上的一家人应该是已经睡下了,今晚动静小得很。这是两个老人住在一起,子女偶尔会回来看看,他们平时也少有声音,最多便是碎个碗杯,从未出什么大事。
赵安萍起身披了件衣服,她看见对面楼里的灯灭了大半,只是星星点点的几处亮着。有的窗户甚至能从外面看到人影,这多数是有孩子念书的家庭。过去赵忠宁也是在这种地方长起来的,只是如今隔着许多里路,赵安萍对这些家长也逐渐淡了念想。
第二天,她破天荒地起得迟,没能赶上第一拨菜市。早上八九点,第二拨换来的小贩们都站疲了,才见她过来。这些人都互相熟悉,基本上撤了摊就会撒进周围的居民楼里,算是社区的邻里关系。但因为赵安萍不大和人接触,小贩们也就只是随便掰扯些闲话。
赵安萍挑拣着青菜,日头已经升得高了,菜看起来也并不新鲜。她随意掂了一把,一边看秤,一边听人闲聊。
各地的小贩们聊天大都相似,相比十几年前离开小城时,这些内容也没有什么变化。听得乏味,赵安萍接过袋子,正准备付钱离开,说话声突然就停了。
她抬起头。
来者裹着厚厚的围巾,口罩挡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额头和眼睛,是个女人。这是小城居民冬天特有的装扮。问价的声音很柔和,但人的眼睛红肿着,像是哭了一宿。一片突兀的青紫横过眼角,看样子甚至蔓去了脸颊。她伸手去握西红柿,赵安萍瞥见她手背上还有几道擦伤。
小贩最会看眼色,也不再做声,麻利地给人称好算钱。赵安萍拎着袋子就离开了。那女人神色仓皇,步子却很快,虽然来得晚,却渐渐走到了她前面去。
赵安萍落在后面。
看着女人进了自家的隔壁。
三
早上家里来了个电话,李峰顺中午就嚷嚷着要吃肉。
那电话里的声音很急,缺人,来。
李峰顺当即出门理了发,就等着第二天入职。碰巧赵忠宁回了家,赵安萍就做了几道菜,三个人围坐半桌,听李峰顺侃大山。
半年来,这日子都像是这么过。儿子的筷子很少动,大半的菜进了李峰顺的嘴。那张嘴分作两用,一边上下翻飞着讲话,一边时刻不停地咀嚼。赵安萍觉得有趣,也不去听内容,专盯着人脸瞧。赵忠宁刻意坐得远,恨不得捂住耳朵。经历了连续几次的店铺奚落,他简直猜不透继父的想法,心里觉得丢脸至极,同桌吃饭都逐渐难以忍受,只是心里常常企盼李峰顺改掉毛病,免得家里以后菜都买不到。
李峰顺把筷子伸到最远的盘子上,敲了敲盘沿。赵忠宁当作没看见,他又讪讪地收了回来,自行点了根烟,叼在嘴上。
他们默默听着李峰顺吹嘘自己的工作,又给邻里人家编排几段艳情历史。桌上的饭菜逐渐混杂了一股烟味儿,儿子停筷,赵安萍别开了脸。
五月份,窗外阳光正好,气温舒适。似乎正等着一个家庭复苏过来。
第二天,李峰顺就去报到。这工作比以前体面得多,是给一个小公司的老板当司机,平时还帮忙接孩子。因为他开过大巴,人家着急才看上他。要接的老板女儿正上高中,和赵忠宁在一个学校,只是不同年级,放学时间也不太一样。最初他跟赵忠宁提,倒受了个白眼儿,暗地里气得牙痒痒。
自此,李峰顺像是走了运。老板没发现这人的德行,反而欣赏他开车稳,干脆就长期聘了他。李峰顺在老板面前夹着尾巴,背后却得意起来,主动去以前欠账的几个店铺晃悠。店里的人都瞧着他,简直就是变相鼓励他从头吹到尾。即使最后还是没还钱,东西也没买,李峰顺却哄得人一愣一愣的,最后又全须全尾地溜出来。
他甚至在赵安萍面前也挺直了腰杆。以前没有收入,还住着赵安萍家的房子,很多时候都要看女人脸色。如今倒是不同了。他做司机的收入远远高于赵安萍在居委会的工作,再不用靠赵安萍给的定额过活。工作时间越长,李峰顺对赵安萍的态度就越硬气。
赵安萍对此不置一词。
车开了半年,李峰顺在老板跟前也混熟了脸。开着老板的宝马车,他着实沾了不少光。出门谈生意,有时作为司机也能接支烟。见多了人家的光鲜,李峰顺心里也开始打算盘,等着有一天在熟人面前出风头。
生意场上酒局多。这老板的身价明显不足保全自己,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李峰顺得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把他送回去。老板娘看起来温温柔柔的,李峰顺把人送到手里,自己才开车回去。
深夜,车一路开进高档小区,大半的楼层都彻夜亮着灯。这里隔音好,红男绿女们的狂欢很少影响到别人。但老板很重,手劲也足。李峰顺每次都得费很大的力气,扛着人往电梯里走。这时候的男人烂泥一滩,乖顺得很。
老板往屋里扑进去,老板娘会习惯性地来扶。人已经站不直,女人缓几口气才能接过手去。李峰顺常见不同的女人跟在老板身边,平时不敢过问这种家务事,后来都把人放下就走。这种酒局一周能有两三次,每次都看到老板娘温和地笑,像是并不在意男人喝多。这反让李峰顺忍不住嘴,但怕丢了工作,还是加快脚步离开。
日子慢慢地过着,李峰顺手里握稳了工资,说话有底气了不少。他不再去小區里的超市,更多时候开始使唤赵安萍。赵安萍下了班才能买菜,社区事多,经常没法按时做饭。李峰顺就挑三拣四,还嫌做的不如饭店里好吃,话里话外都在炫耀见过的世面。
这天儿子在家,赵安萍还没能回来。李峰顺当日没有工作,就坐在床边看赵忠宁翻书包,嘴里闲闲地说几句话,也没有指望他回答。大概是等得有些饿了,口气逐渐恶劣起来。李峰顺来回诉说自己的辛苦,讽刺赵安萍连一个家庭主妇的事都做不好,连在外时挂在嘴边的脏话都顺了出来。
赵忠宁的书包落到地上,书散了一地。他蹲下去捡,连头也没回。
“几个月前,你不还成天自己去偷吗?”
这话声音平淡,语气也冷漠。李峰顺盯住他的后背,一下子停住。结婚后的种种回忆涌上来,仿佛完全压住了他刻意的体面,时时提醒着过去。脑中浮出赵安萍的脸色,赵忠宁的抗拒,一直到想起上周送老板回家,女人开门时温温柔柔的脸。
男生瘦弱的脊柱因为动作的伸展而耸动着。
李峰顺一脚踩了上去。
四
“这是老家亲戚带来的马铃薯,太多了,我给你送些过来。”
赵安萍接过张琳手里的袋子,掂着还挺沉。她笑起来,请张琳进了屋,放下马铃薯,又倒了杯水递过来。
张琳就是隔壁的女人。三十多岁,眉眼淡淡的,扔进人群就找不出来了,她情绪很少激烈,难以联系半夜摔门的行为。赵安萍至今没有同她谈起过家事,两个人的交往不深不浅,时间很短。
说来莫名。一日,赵安萍如往常一样,早晨回来,回头就发现张琳跟在后面。这和第一次见刚好相反,赵安萍当时就发了怔,但明显张琳在这里住的时间久,也更熟络,主动就和她打招呼。赵安萍被迫点头,又注意到她的目光停了一次在自己腿上,转瞬即走,什么也没问。
这举动很能博人好感。赵安萍慢慢接受了生活的异客。
张琳很热情,从马铃薯就能看出来。赵安萍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她不只是送东西,简直乐于服务整栋楼。此前她不与人打交道,到现在才发现,这楼里的人大多都不太客气,凡事都能找上张琳的门。
本来起自头顶住的老人一家,有段日子兒女出国,一时没人去管,张琳好心上门送饭,倒叫人逮住了机会。她没有工作,平时就在家里待着,有邻居又太忙,连饭也吃不上,就常常请她帮忙照料家里的事。往日最多是浇浇花之类,如今有些人还偶尔请她帮忙接次孩子,说是要给钱,张琳又不好意思要,就一直搁着。
听说的人都劝她别犯傻,但张琳总是尴尬地笑过去。赵安萍明白那种面上无法拒绝的感受,从不和她提。又因为赵安萍独居,屋里安静,张琳也常常会来坐一会儿。
然而,每次赵安萍见张琳,她都带着点伤。
很少出现大的伤口,基本都是淤青堆在皮下。不一定都在脸上,赵安萍亲眼看见她抬手取东西,衣服滑下来,胳膊上也纵横着红印,还略有隆起,明显是新鲜的伤痕。
这回刚坐下,赵安萍就看见她眼角破了条口子,延到眼睑上面,眼睛都不大能睁得开。张琳握住水杯,还没开口说话,就窸窸窣窣地哭出了声。
长久以来避开的话题终于被强行扯了出来。赵安萍扶住她的肩膀,感觉张琳轻微抖了几下,了然地松了手。
明眼人早就能猜个大半。赵安萍起身给自己续了热水,沉默地看着她。张琳没有说话,只是哭。昨晚隔壁的声音很杂,但也能听出不只是男人回来,尖利的女声打破了往日低低的抽泣。不像是年轻女人,估计是婆婆一类的人物。那音调高昂,穿透了薄薄的墙壁,整栋楼的人都被迫听下去。连楼道里常有的小孩打闹声都没了,被大人关在屋里。晚上四周静悄悄,赵安萍躺在床上,用被子捂了脸。
婆媳关系差,男人脾气爆,本来是小城里挺平常的事情,她也以为忍忍就过了。直到事情愈演愈烈,甚至不得不每天戴着口罩出门。
赵安萍没作声,只默默地喝水。她去开了电视,正播着下午的电视剧,空荡荡的屋里回响着男演员敦厚的声音。
直到有人敲响了门。
五
连着一周,李峰顺都主动回来做饭。
赵安萍看着他在厨房里忙,心里慢慢有些松动。
那日赵安萍回来得不巧。书散了一地,自己儿子正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李峰顺似乎还意图再补上几脚。
她还没有继续反应,身体已经扑上去把李峰顺推开。赵忠宁呻吟了几声,脸涨得通红,羞愤难堪,又因为腰腹太疼,折腾半天坐不起来。
李峰顺也并不比赵忠宁冷静。他胸腔呼呼地喘着气,拳头捏得很紧。已经到了夏天,短袖早已上身。赵安萍看着他的胳膊鼓起青筋,额头硬是多挤出了两条深痕。
看到她,李峰顺像是忽然醒过来。男人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才意识到屋里的现状,不自觉出了一后背的冷汗。
客厅墙上挂着的钟响了一声。
他连连解释,事情也了结得很快。赵安萍没能继续做饭,赵忠宁当天就回了学校。少了个人,屋里安静不少。赵安萍去卧室里睡觉,晾得李峰顺心里发毛,又莫名地憋火。他坐在客厅的床上,心里杂乱,熬了半宿才睡。
这就僵持了一周。
李峰顺正在厨房里忙活,今天还买了肉回来。赵安萍在外面听他叮叮当当,那嘴还在一如往常地闲扯。
似乎是有东西落地,她走过去看,悄悄倚在了厨房门边。李峰顺没察觉,背对着门炒菜,身上还系了条围裙。
厨房能容下一个灶台,又勉强放置了桌子,剩下允许活动的空间很小,每次赵安萍做饭,都会下意识打开窗子,似乎能扩大点范围。住来不过几年,灶台上贴着的报纸已经被熏得干黄。没有油烟机,赵安萍自己给安了个小风扇,作用不大,噪音却整日轰鸣,显得碍手碍脚。扭在一起的电缆从头顶的风扇处绕下来,一直伸到地上拖拽着的插板上。它们早已分不清颜色,看起来油腻泛光,不注意还容易被绊倒。角落里塞着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有些里面还装着出芽的蒜苗。
李峰顺翻炒着锅里的菜,刻意低着头。正对着脑袋的墙上,被赵安萍钉着个铁钩。原先两个人住,赵忠宁不进厨房,她也并不是很高,这钩子位置显得恰到好处,平时还能用来挂围裙一类的东西。但李峰顺显然要高出许多,稍不注意,那颇为锋利的钩子就会戳到自己。
李峰顺炒了一阵就放小了火,回头准备放点酱油,抬眼就看见她。
脸上蒸着汗,他呲牙笑起来。
赵安萍忽然就软了。
“端三碗吧。”
话没说完,李峰顺却懂了,这是说今晚继子也会回来。他乐得很,毫不避讳地表现出来。当晚忙前忙后,像根本不在乎赵忠宁的目光。
赵忠宁之前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这时始终狐疑地看着他,也没说什么话。整个饭桌上只有赵安萍和李峰顺的声音,氛围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每一天。
吃完饭,男人头一次主动起来收拾桌子。最后还剩个盘子没能一起端走,赵安萍拿起来进了厨房。
里面开着窗,没有白天闷热,碗筷摞在一起,李峰顺正忙着拆解,也没注意到她过来。
赵安萍目光越过他的头顶,听见外面有蝉在鸣叫。
六
这是赵安萍头一次见张琳的丈夫。
看起来是个身形文弱的男人,还戴着副眼镜。下巴有些尖,让人没来由地想起昨晚尖利的女声。这人身上套着件窄皱的西装,看起来薄,估计不会穿来出门。
果然是找张琳的。
听完来意,赵安萍垂下目光,不去看他的脸,又几不可察地放小了门缝。她余光瞥见张琳,正不自觉地往沙发里面缩。
“她待会儿回去”,赵安萍补充,“不会耽误很久。”
丈夫却很执着地站在那里,要让张琳快点跟他回家。
赵安萍犹豫了一瞬,毕竟并没有立场拖着人不放,她又下意识回头往屋里看了眼。
张琳拼命摇头。
赵安萍松开了门,但还是没来得及。男人趁机逮住机会,连推带搡地挤了进来。
张琳被粗鲁地拽下了沙发,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赵安萍没能想到这一步,眼睁睁地看着张琳的头发被揪住,她踉跄了几步,膝盖直直磕在茶几上,痛得吸了口气。丈夫却完全没有理会,拖着她就往外走。
张琳长得小巧,即使是个文弱的男人也完全能拉得动。赵安萍挡在门口,试图劝说这人放开,但自己也被推了一把。她未曾想到,在小城里竟然还能见到这样的事。门在墙上回弹了一下,大张开来,人就这么被强行带走。
赵安萍追出去,隔壁摔门发出了巨响。
不到晚饭时间,各家各户的人基本都还没回来。楼道很安静,还有管道敲击的声音。听起来空洞又惨然。她往隔壁迈了两步,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闷闷的钝响。
缠绕多个夜晚的哭泣声又开始了,这次还加上了男人的吼骂声。赵安萍就站在门口听着。男人从她生不出孩子,伺候不好婆婆,一直说到今天没能按时做饭。其间掺杂着各种小城独有的脏话,无论如何无法和刚才站门口的男人联系起来。
这丈夫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人,声音越来越高,情绪几乎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很快,赵安萍听到了一声清晰的巴掌响。
哭声愈来愈大,她有些发抖。
已经是一月份,年关渐近,赵安萍的家里却很难寻着年味儿。她不去超市,不赶市集,对过年也没有兴趣。但比起她,隔壁的张琳就常常提着东西回家,赵安萍偶尔也跟去她家里,帮忙打扫卫生。那房中干干净净,张琳却反复地擦拭着物件,即使它们可能当晚就会被打碎。
赵安萍觉得冷。她进屋,拖出了来时的箱子,翻找起衣物。住在南方省城的十几年,充斥着冰冷的记忆,却没能给她留下一件厚衣服。手机里的通讯录很久没有打开,和儿子赵忠宁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半个月前。她猛然间发觉,她又走进了过去的生活,小城与想象完全不同。
今晚的事情同以往过于相似,梦里都紧紧扼住她的喉。
七
这周末,老板女儿被老师留了堂,一直拖到高三下课。李峰顺在学校门口等着,老远就看见赵忠宁出来,冲他拼命招手。赵忠宁犹豫了一瞬,还是走了过来。李峰顺挤挤眼,让赵忠宁赶快上车,好不容易在继子跟前露脸,李峰顺兴奋得很。
女孩儿出来,就看到车里多了个人,扬了扬眉毛,坐进来询问李峰顺。他就谄媚地笑,说顺便带儿子回家。赵忠宁不大清楚这中间的弯绕,见有正主上来,尴尬得手也沒地方放。
女生举止很大方,没有再问下去,安安静静地靠在车窗前。李峰顺见她不讲话,自己倒是得意起来,举手投足都像是车主。他要先送人回去,再开车带赵忠宁走。两个人都没什么异议。
和往常不一样,李峰顺有意在赵忠宁面前找回面子。以往偷鸡摸狗的事情始终横在这小子眼中,他心里也老大不愿意。
两个学生都沉默着,李峰顺话却很多。先是恭维老板一家人,夸人家女儿漂亮,见没人回应,他又把话题扯到了自己家里。
赵忠宁早就如坐针毡。不可否认,这车里的座椅很舒服,但他始终感到局促,尤其是在李峰顺谈到赵安萍的时候,这种尴尬达到了顶点。
他被迫听着赵安萍与老板娘之间的对比。赵安萍在李峰顺的口中,不年轻也不漂亮,更没有老板娘贤惠。那女生笑起来,似乎还转头问他是不是真的。
血撞着耳鼓膜,赵忠宁没能听清楚她的话,却听见李峰顺继续讲着。恐怕是为了逗那女生开心,这男人越发口无遮拦,一直讲到了赵安萍的工作,笑嘻嘻地说,不过是个给居委会扫地的,估计没了他连饭也吃不上。
有东西被猛然甩到了前座,直冲着李峰顺的脑门儿而去。李峰顺没能闪过去,车拐了个小弯。他回头见是赵忠宁的书包,禁不住破口大骂。
“婊子养的臭玩意儿,竟然还敢打老子……”
李峰顺把车往路边上开,滑了几米就停下来。赵忠宁喘着粗气,像是要冲到前座打人。女生早就吓呆了,坐直了身子,扶住了车门把手。
车刚一停,赵忠宁书包也不要了,“砰”地就摔了车门。
李峰顺积了一肚子气,面子上还下不来。他只能呵呵干笑着,把老板女儿先送回去。这一路比先前更沉默,连李峰顺都不再讲话。他气得发昏,满脑子都是回去要怎么收拾赵忠宁。
学校离得远,开了快四十分钟的车才到小区。女生下了车,却没像往常一样跟李峰顺说再见。
她冲他挥了挥手机:“叔,把车停到地下停车场吧。”
李峰顺笑,说明天早上还要开来接人,就不停了。
女生也没继续说下去,点点头,转身就走了。
回去的路上,手机振动着响起来。李峰顺手里还握着方向盘,也不忙去接,先是开了车载蓝牙,才慢悠悠地点开了接通。
“明天不用过来了,自己去公司结一下工资。”
声音不算陌生。曾经急着叫他去上班的电话里也是这把嗓子,但那时他满心的欢喜,没察觉那嘴里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李峰顺有些发愣。
……
晚上,男人回到家里前,破天荒地又去了趟门口的超市。
拎了把菜刀出来。
八
赵安萍紧紧锁住了门。
搬回来的第一年,她没有交这个季度的供暖费。平时觉不出什么,这时却似乎逐渐有寒气渗进来,从四处弥散在小小的居室。
隔壁的闹声还在继续,她就扑过去拉窗帘。冬天昼短,不到七点就黑透了天。外面早已亮了路灯,各家各户的人也都回来,楼层逐个开了灯。窗帘合上了外面的世界,房中显得更昏暗。赵安萍环视着这地方,忽然有些茫然。
今天一整天还都没有吃饭。早上买来的东西照例堆在门口,下午只是当着张琳的面放了袋马铃薯。厨房冷锅冷灶。她许久不曾用过这里,今晚却是主动进来。张琳笑她怪毛病,厨房的灶台闲着,非要在客厅接个电磁炉。
赵安萍也跟着笑,随口说能省下天然气的钱。
当日同她玩笑的女人正在隔壁惨叫。赵安萍头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那声音离得远了些,她退出厨房,贴在墙根绕着走。
墙面冰凉。赵安萍摸到了距隔壁声音最近的地方,慢慢靠着坐下来。她听见易碎物品清脆的破裂声,还有沙发被推动后沉闷的响动。刚落地的碗,可能今早才被张琳细心擦过。沙发推出来的灰尘,明天又要扫半早上。简直都能想象出她的动作。
隔壁令人心惊的动静,彻底把赵安萍魇在里面。
她至今不清楚拳脚能达到的力量。但左腿确确实实被李峰顺连续踹到骨折,到现在落下毛病,始终不太利索。几个耳光打得她眼冒金星,耳朵嗡嗡直响,话也听不太清。那日前,赵安萍从未想过,李峰顺能有这样大的力气。她想起头一次在车站见他,看起來老老实实,身边还有卖票的人跟她说,那司机叫李峰顺。他当时的手舒展着,搭在方向盘,正等着人上车。赵安萍多看了两眼,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手也能握成拳头。
记忆里当然不止这些。李峰顺亮出菜刀的时候,赵安萍还能想起赵忠宁的表情。她捂着腿坐在地上,眼泪大颗大颗地掉,整个人急得失声。李峰顺的嘴没停,来来回回重复着一两句脏话。赵忠宁慌了,但这空间过小,他慌不择路,竟往厨房蹿去。赵安萍挣扎着起来挡住李峰顺,眼角瞥见了厨房的冷光。
隔壁,张琳已经全然是在哭了。尖叫声不再,似乎也没了力气驳斥。
暴行像是停了,赵安萍默默地听着。
她也不再去想,兀自发抖。
九
四月,县城的叶子终于盈满了各个巷口,小孩子呼啦啦地跑过去,能落一地的绿色。过去几个月很少开门的店铺都张罗起来,超市冰柜里的雪糕也终于有人光顾。阳光甚至辨不出来时的方向,直让人感觉处处温暖亮堂。冬天一点即燃的氛围松懈下来后,整个小城就变作了书里的插画,人们说话也逐渐温和,无论认识与否,都能在路上拉扯几句。
年轻人们开始陆续离家,随着温度变化的曲线一路南下。一时之间,往日热闹的场所都收敛不少,茶馆之类的地方反而兴旺起来。
赵安萍也收拾了东西,在潮流中搬离了这间老房子。
她还记得张琳的目光,清澈的眼神里是明显的羡慕。两人最终也没能再说些什么,张琳沉默着帮她抬箱子下楼,微笑着给了她一个拥抱。
赵安萍仰头去看这栋小楼。县城的春天少有下雨,多有风吹。楼上铺着层灰扑扑的颜色,白天也没有人从里面出来,看起来阴森难挨。
但明明是个晴天。
十
身边蹦过去几个小孩儿,有人落了串钥匙在地上,转身来捡,抬头就瞧见个女人。步子略有些跛,那张面容却出奇沉静,嘴唇抿得很紧,柔和的眼神映着凌厉的眼角。孩子原本是有些惊奇,但前面有同伴叫喊起来,很快又转移了注意力,笑嘻嘻地抛着钥匙,朝着前方奔过去。
踩住地上丢弃的生锈铁钩,赵安萍顿了脚步,垂下眼帘。
像是看到钩子上淌着鲜红的血。
朱霄,女,零零后,暨南大学文学院在读学生。作品曾获“感受岭南”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征文比赛特等奖、全国大学生“新作新评”比赛特等奖、第15、16届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二等奖、“丰湖杯”全国小小说大赛三等奖等奖项。曾在各大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并有作品被选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