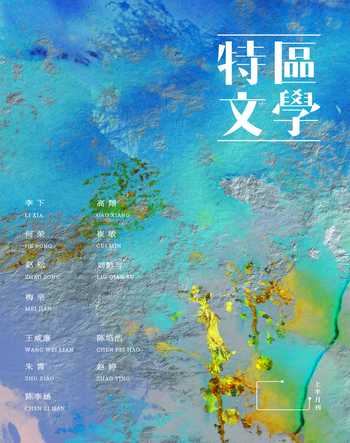寒冷是一种生活的痛觉
作为一名零零后写作者,朱霄开始小说创作的时间并不很长,但难得的是,她的叙事极少见刻意的修辞,初出手便奠定了简洁的风格。从《惧鬼》到《取暖》,再到《藏身》,这种风格被延续下来,逐渐凝成一股萧索的冷气。这或许和朱霄的出身有关,她来自一片拥有漫长冬季的土地,而这种寒冷流淌在她的血液里,也成为刻在她的文字中难以被抹灭的基因。
朱霄的小说创作多为现实主义,事实上,她的作品也都呈现出了现实主义作品应该有的品质,不论是人物的刻画、细节的填充,还是情节的布置,她往往能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织起一张关于生活的细密的网,从而还原出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为青年写作者,朱霄在小说中也体现出过人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透着一股既清澈又老练的力量,也让她笔下的文字具备了一种冷峻的气质。从朱霄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来看,她所选择的题材其实并不新鲜:《惧鬼》写不实舆论如何一步步将人逼上绝境;《取暖》写少年王家辉因家贫无法继续学业,只能到农贸市场充当劳工的故事;而此次的《藏身》聚焦的话题则是家庭暴力。在小说《藏身》中,女主人公赵安萍带着儿子赵忠宁,与司机李峰顺结合为一个重组家庭,此后便断断续续地受到丈夫的家庭暴力。当丈夫在一次冲突中挥刀向自己的儿子时,赵安萍却在反抗中意外地杀死了丈夫。小说所触及的题材似乎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踪迹,但正是由于这些故事距离现实太近,其内在隐含的暴虐力量也往往为人所忽视。朱霄则通过小说,揭示出生活这一层寒冷的底色,让人在生活的麻木中感受到真实的战栗。
朱霄小说中的冷意并非仅仅是一种氛围感,而是由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含蓄生发出的凝练和准确。正因如此,《藏身》的语言描写就像一组组短暂又简洁的镜头,清晰地勾勒出了故事的轮廓。没有办酒席的婚礼、为了几朵花菜便争得面红耳赤的女人、饭桌上侃大山的男人,琐碎的细节还原出生活的本真模样,平凡的场景构建起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有隐忍的女人、好面子的丈夫、自尊心正盛的儿子。然而,在这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组合中间,压迫也无处不在。丈夫李峰顺泛黄的牙齿、饭桌上的一根烟,这些邋遢的习惯成为终止一顿饭的理由;李峰顺偷窃的毛病惹来了邻里商户的非议,让赵安萍和儿子赵忠宁在外都抬不起头来;李峰顺重新工作之后,在家里便对赵安萍颐指气使。这样混沌的生活还能安稳地行进,所依赖的是无数的隐忍和沉默。
生活虽轻描淡写地向人们施压,人与人之间的天平却也不可能始终保持平衡。当赵忠宁撕下继父苦心经营的体面,甚至让他丢掉引以为傲的工作,李峰顺终于显露出残暴的本性。但《藏身》从未真正着笔写矛盾爆发的场景,也没有对情感的冲突加以渲染,而是用一把菜刀、一个铁钩点出泛着寒意的事实。对于同样遭受暴力的女人张琳,文本中的描写也只有一次次深夜的哭声,和皮肤表面泛起的伤口。文字的克制埋伏在小说的每一处,平静表面下的暴力,是小说之“冷”的真正来源。而叙述层上的理性,给故事层上激烈的情感冲突做出留白,既让小说具备了一种内敛的美学,又给理想读者的接受留下充分的空间。克制的语言与残忍的伤害之间形成极大的张力,构成了文本的裂隙。
生活之“冷”在《藏身》中不仅作为语言的克制而呈现,更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在朱霄的小说中,常常能见到小区或居民楼这种集体居住的空间:一栋容纳众多住户的大楼,兼具了私密和公共两种属性。人们的私隐看似被封锁在一个个被称之为家的房间中,最终却都无法避免地在公共空间中传播,成为邻居们茶余饭后流行的谈资。如在《惧鬼》中,小区居民因为虐杀动物的事件频发,便开始相互怀疑,捕风捉影地生成许多中伤他人的流言。在《取暖》的工人集体宿舍中,同事们趁主人公王家辉离开,便越过界限翻找他的东西。如果说,《惧鬼》中人与人的互不信任成为了一种精神攻击的利器,《取暖》中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是动荡生活下的疏离,那么《藏身》所呈现出的邻里之间的冷漠,则更在暗处助长了实质性的暴力。在《藏身》中,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听到了张琳遭遇丈夫暴力时的呜咽、婆婆尖利的咒骂,却每每在他人遭遇暴力时选择各自紧闭门户,漠然地忽视周遭正在进行的暴力。家的私密性与小区的公共性、邻居们在空间上的距离之近与情感上的冷漠,共同构成了两组二律背反的关系。
对他人遭遇的苦难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是现代社会环境下普遍存在的症候。而在冷漠的语境之下,《藏身》中人与人之间时刻处于对立的关系中,隔膜使人物只能成为孤独的个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作为对照人物的赵安萍和张琳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特殊。赵安萍和张琳同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二人虽有来往,在面对彼此的困境时却都无力给予对方救助。这也意味着,赵安萍与张琳在经受伤害的同时,也无奈地充当了暴力的旁观者。这组特殊的“看”与“被看”的关系,实际上是被以“家庭”为名的界限所区隔开的。当同样的暴力行为发生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暴力便是一起公共事件,将遭到群体的共同谴责;但当暴力发生在被冠名为家的场域之内,残忍的行径也被合理化为家庭的内部矛盾。小说中,赵安萍时常隔着一堵墙,听着隔壁的张琳遭遇暴行时发出的呻吟,此时,这堵墙所隐喻的并非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指向了被家庭的概念所掩蓋的暴力行为。
从外部看,“家庭”沦为了美化“暴力”的修辞,而从内部看,家庭作为人生存的最小单位,原本应该成为一种归宿,但《藏身》中,赵安萍的家却始终是一个并不温馨的处所。李峰顺回到逼仄狭小的所在,卸下在社会生活中的伪装,换上了一副易怒的面孔。这个重组家庭积年来的龃龉就如同厨房层层叠叠的油腻,却冒不出热腾腾的烟火气。张琳家虽打扫得很干净,却同样缺少了一个家应该有的温情。家让冷漠的家人不得不保持亲密,便也成为了暴力滋生的温床。
朱霄的小说多写苦难,尤其是底层人的苦难,而寒冷在这些作品当中往往成为了指向苦难的意象。苦难在《取暖》中体现为寒冷对瘦弱的少年王家辉的侵袭,在《藏身》中,则化为了一个有寒风无孔不入的冬季。在没有暖气的冬季里,赵安萍目睹了儿子的死亡,又意外杀死丈夫李峰顺,两个生命的消逝造就了她生命中的寒冬。但在极寒之处,小说又无一不涌现出了救赎的光芒。《取暖》中的王家辉遇见了对他十分照顾的刘忠伟,他因此得到了一个有热水袋的被窝和一口小小的电热锅,这成为被迫辍学的少年艰苦生活中的一丝慰藉。而《藏身》中李峰顺的死亡,也意味着赵安萍终于结束一段压抑的婚姻,重新获得了走向新生的能力。但同时,随着《取暖》中的刘忠伟的离开,王家辉的生活似乎再次回到原点,原本计划用于复学攒下的钱,也只能花费在父亲的病上;《藏身》中的女主人公再次搬离老房子,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只有寒冷作为一种痛觉,始终烙印在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当中。但生活的真相就是如此,即便被凛冽的寒风冻伤,也依旧要挣扎向前,正如《藏身》的结尾处,赵安萍的小城披着灰色的冷气,却也终于步入了春天。
陈李涵,现就读于暨南大学,曾获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征文比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新作新评”比赛三等奖等;作品见于各文学刊物;曾参与创作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探案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