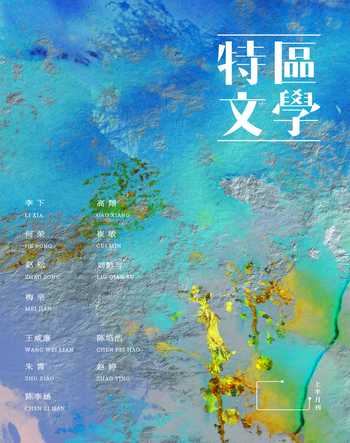侏儒
何荣,女,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各文学期刊发表散文及小说,作品入选“岩层”书系、《小说月报》创刊35周年“小说新声特集”。短篇小说集《断头螺丝》即将由后浪出版社出版。
他盯上他很久了。
超市排班表贴在员工休息室门上,他偷拍过一份。一共五个收银员,剔掉三个女名,只剩下“黄杰”和“王建国”。大概率是“黄杰”,他听到有人叫他“小黄”。名字不重要,结账的时候扫一眼,最矮的那个就是。两台机子同时结,七天里三天都能碰上。他把最近结账的小票摊开,有口香糖,有牙膏,最多的还是矿泉水,两块钱一瓶,便宜、低调,可以天天买。连着买了两星期,侏儒终于跟他说话了。
大哥,这个牌子最近有活动,一箱七折,要不要搬一箱?
他笑一笑,摇摇头。侏儒也笑,表示理解。一箱水24瓶,那得多重?搬起来累死人。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
我老家安徽。
安徽?好地方。
他的老家也是个好地方,但不是侏儒的那个好地方。上午九点,超市没什么人,照明充足,物品摆放整齐,像一只巨大冰箱的内部。几条拉花彩带凌空交错,是上次大促销留下的残骸。他跟自己说:就到这,不要急,来日方长。出门左转是菜市场,他买了份凉皮,外带。凉皮圆圆一张,半透明,被切成条,拌上麻酱、黄瓜丝、绿豆芽,慢慢变得像食物。他看着,悄悄咽口水。不要急。大婶帮他把凉皮装进纸碗,冒了尖,用塑料碗盖压下去。他用一根食指拎着塑料袋,一路悠回来。坐下,拧开瓶盖,喝口水,在键盘敲下今天的收获—
“二十年前,安徽的一个小村里,一群小孩在打谷场上玩‘抓鬼子。打谷场的角落,蹲着被他们剔除在外的‘土行孙。土行孙,大名黄杰。虚岁九岁,个头只有五岁。他早上刚喝了爷爷求来的苦药,爷爷说喝完他就會像河坝上的小白杨,蹿天长。话虽这么说,王建国他们还是不肯带他玩。一!二!三!他跟着跑又跟着喊,硬朝人缝里钻。‘鬼子根本看不见他,直接从他身边溜过去。他像个成了精的矮树桩,一会儿移到东,一会儿移到西,肚里的药汤撞得咣咣响。苦味混着酸液,漾到喉咙口。土行孙喷水啦!孩子们吓得全跑光,他还在吐。最后爷爷拾起他,软软一条,驮在背上。手脚抻长,看着比之前高了些,一搁到地上又恢复原样。此时,他满脸土,泪汪汪。他还不知道,二十年后,他会跑到另一个小镇上,避开父老乡亲,体体面面穿着超市员工服、用扫码枪一件一件‘毙货。”
二十年前是新千年,这个节点很好。旧千年里的小矮子,迈开短腿跨世纪。二十年后,中年矮子;再过二十年,老矮子。碗底的凉皮浸饱酱汁,变成黄泥色。卖相丑、滋味美,读者一定会像他这样,唏里呼噜,嗦完这个故事。刚开个头,他就在咂摸余味了。王俐打来电话,说今天看了万达广场附近的二手房,一平才两万不到,你觉得怎么样?他点点头。王俐说你表个态呀,他说挺好。王俐说你在吃饭?这都几点了!他说我有个电话进来了,你等会儿啊。挂断后他马上打给张龙应,因为王俐会回拨,看他是不是真的占线。
龙应太好约了,跟小时候一样,在他家楼下喊一声就会出来。以前一起喝汽水,现在一起喝啤酒,喝到肚皮浑圆,再一起放尿。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他老婆变成了前妻,两个女儿一个也没跟他。结婚生子的流程走一遍,从烧烤摊到大酒店再到小饭馆,你发小还是你发小。
好东西呢?给我看看。
他掏出手机,出示了一张偷拍的侏儒照片,挺糊,看不清脸。
这谁啊?
一个矮子。
矮子怎么了?
他说不出口。就好比,你泡了个药酒,刚封口,总不能再扒开吧。走气了,酒就废了。
不说是吧?那你把我弄这儿干什么来了?
你等下,我接个电话。
他打给王俐,两声就接了。我现在在外头。还能跟谁?放心,没喝多。马上就回去了。挂了电话,他跟龙应说王俐今天又看房子去了,这是要逼死我。两百万!我卖血都挣不到两百万!
你少给我打岔,我还没醉呢。你今天叫我出来,说你有个好东西,必须马上跟我聊一聊。
我先写,写好了再跟你说。
去年那个好东西呢?写出来了没?
那篇还没找到感觉,先放着。
龙应点点头,把一次性塑料杯举高,跟他碰一碰。跟龙应在一起最像独处,比独处还像独处。如果王俐是高压水枪,龙应就是感应水龙头。他不说,龙应就不问。龙应搬出那个被他们骂过很多遍的黑心老板来救场,他仍像第一回听说那样,一拳砸在墙上。
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把这狗娘养的写出来,给你报仇!
他知道这些话挺假,不过要是别人,他不会冲水泥墙来这么一下。他手背破了皮,钻心疼,这疼是真的,专门献给龙应。
“初二那年,班上转来一个小胖子,叫张龙应。张龙应很快就跟同学们打成一片,倒是侏儒,更像个插班生。总有人踩他鞋带,他蹲下去系,大家就在他身后助跑,两腿分开,撑着他的背跳山羊。龙应不拦着别人跳,也不肯跟着跳。很快,龙应也不合群了。俩人一块被关在老教学楼的废厕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龙应从怀里掏出一个乒乓球拍,酱红;再从屁兜挖出一颗球,蛋黄。来,试试!来嘛!他俩轮流对着墙打,球落地了就换人。看不出来,他个头不高,悟性挺好,上手快。小球在拍子跟墙之间横跳、拉丝,似乎忘了往下掉。之后,龙应把他带到米厂家属区,仓库里有几张水泥球台,没有拦网就用砖头拼。上旋、下旋、拉弧圈,乒乓球细巧,没有身体对抗。他们不太聊天,话都在乒乒乓乓里了。他经常喂高球给龙应抽,龙应也不把球抽死,等他退得远远的,在球桌下一捞,救回来,龙应再抽。小球极敏感,手腕力道的改变、球拍倾斜的角度、球桌上的一粒沙,都能让它瞬间改变路径。胜负很明显,两个少年合力赢了这颗狡猾的小球。龙应家开五金店,他像他爸那样,见人先笑,很小就知道‘点到为止。某次打完球,他们往河坝走,桥下一个岔路口,两边的小白杨蹿天长,两人被夕阳照得红彤彤。龙应突然说:你知不知道,邓亚萍个子就不高!
邓亚萍个子就不高!
这句话简直可以裱起来,挂上墙,与‘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并排。十五岁的龙应,讲出他人生中第一个金句。时隔多年,他依然敬佩这句话。这句话很十五岁,但包含的智慧足足有五十岁。”
他又来买水了,侏儒不在。他在另一个柜台结了账,问:小黄今天不值班?胖乎乎的女收银员朝门外一努嘴。超市对面是个小公园,有个简易的篮球场,侏儒抱着球在球场上跑,没穿工作服,远看像个初中生。头发少,脑袋比身子大一号,两腮红艳,像戴着扭秧歌的大头娃娃头套。
他折回去,又买一瓶水,走过去观战。侏儒看见他,笑一笑,把球运过来,一脚踏住。这时他才发现,侏儒光着脚。
两人坐在小公园假山上,晒着太阳,把矿泉水喝出酒味。他偷偷看侏儒,皮肤粉里透白,一只人畜无害的仔猪。侏儒问他信不信主,他說不信。侏儒说那你信佛吗?他说我只信人民币,侏儒笑得呛了口水。进度条艰难地前进了一格。他牢牢记着龙应身上特有的松弛感,那是多年来让他信任的东西。松弛得像草垛、羽绒被,像被暮霭稀释了的淡紫色炊烟,像家。他必须习得它,并让侏儒感受到它。“邓亚萍个子就不高!”只要有个家伙把你当正常人看待,你就会马上正常起来。
侏儒说他信主,因为奶奶信主,他信奶奶。奶奶说主会保佑你,就算你爹妈不要你,就算以后奶奶死了,主会永远在你身边。这世上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但主是真的。你小时候最亲的那个人,就是你的主。我奶奶就是我的主。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想要一个不死的奶奶,就这样,每人出一份心意,供出一个大家的奶奶,就是主。主就像这马路,这公园,是公用的。你说你不信主,其实你也在这马路上走,你也在这公园里休息。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些人不信主,那我们心里就有很多事情过不去。这么多人心里有这么多过不去的,天下就会乱。所以说,信主的人捐钱修了路,建了公园,让不信主的人也有个清净的去处。你要是愿意,你也可以加入我们,信主的人越多,马路越宽,公园越大。
侏儒的声音很静,语调有凉意。皮囊是老人的,身体是小孩的,套上去之后富余太多。脑门有抬头纹,眼角有鱼尾纹,腮上有法令纹,整个人皱巴巴。烈日当头,树伞被风摇破,漏下许多大洞,地上有白有黑,花成一片。侏儒坐在一块平整的太湖石上,两边各有一株绿植护体,看起来像个巫童。他突然生了敬畏之心,想跟这位高人求个签,问问他这个赌局胜算如何。你觉得你是在人道主义关怀,其实是人家在关怀你。
他起身,说自己还有点事,先走了。走了几步,才想起来伸出右手,举到肩膀上方,朝身后摇出一句“再会”。牌全乱了,他得推翻重来。他刷了一辆公共自行车,不骑,沿着302国道推。车把被很多人握过,脏黑黏腻。他在这些看不见的手上,覆上自己的手。这边靠近物流园,一路都是大货车,沉默、笨重,开起来轰隆轰隆。货厢方方正正,是临时集装箱房,被匆忙铲起,从此处逃往他处。道路指示牌有蓝有绿,清一色的白字,有的面朝他,有的背对他。荒地荒着,一架丝瓜藤彻底干朽,野鸽子在搬迁后的厂区宿舍门口起起落落。天地灰蒙蒙像一潭污水,一颗夕阳投入,沉底,尾部溶开一缕红。
他推着车,自觉像行者牵着马。这行者穿着优衣库卫衣,袖口都洗旧了。马也非马,马身是高碳钢,马鞍是人造革,马蹄是实心胎。如果不是王俐通过中国移动找到他,把他揪回市区,他可能会一直走到太湖边。他的终点是一人一湖一车,剪影浓黑,烟波起伏。但现在,他在1号线入口处倒腾健康码。
“咚咚咚,马戏团动物表演马上开始。石头剪子布!龙应输了,让他踩着肩膀先看。一只大铁笼子,几只小狗穿着背心在跳圈。耳朵打在眼睛上,叭叭响。龙应说到我了,侏儒说我还没看够呢。接下来是秃毛猴翻跟头、小猪赛跑,还有抓着铁杆、怎么晃也晃不下来的大公鸡。之后出场的是一个小丑,顶多一米高。戴假发,涂白粉,帽子一摘,口哨四起。侏儒直接从龙应身上跳下来,掉头就走。”
他在麻雀咖啡馆靠窗的位子坐下,打开手机备忘录,写了一小段。王俐还没到。这里的灯全是暖光,琥珀色,一走进去人就被冻住,手轻脚轻,动作消音。这里简直就是小人国,到处都是精致的障碍物。咖啡杯白瓷描金边,杯柄幼细,一不小心就捏断了。耳挖子大的小金勺,勺柄磨砂,手感滑腻,像沾了油污没洗干净。脸盆大的小圆桌,玻璃台面,二人座,头抵头聊天,很挤,感觉是大清早在卫生间抢洗手池。花瓶巴掌大,花手指粗。凳子还会转,转狠了可以直接掉个头,加入邻桌。他很久不来这个地方了,腾挪不开,憋屈得很。可是王俐喜欢,刚认识的时候他总陪她来。一米八三的大男人,在亚麻钩花布艺小沙发上练缩骨功,看上去温驯极了。
你还记得我只喝拿铁呀。
这个语气不太妙,他换成比较保险的老爸爸口气:快喝吧,都凉了。
王俐就是不喝,下巴内收,盯着他。她看上去像个正在参加面试的女演员,眨眼都有声音,吧嗒吧嗒。又来了,他想。他等了一会儿,她并没有在座位下用脚蹭他的小腿。她把小金勺伸进棕褐色的液体,一圈又一圈,耐心地搅动。他这杯快没了,不能再喝了。他抖动杯身,把这点珍贵的咖啡底子旋起来,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一滴都没漏。他感觉自己在操纵一台洗衣机,滚筒里转着洗脏了的黄泥汤。
王俐的咖啡,他的咖啡,都在转。他觉得,就这么转一晚上也不错。王俐声称,有时候她就是希望两个人一起发个呆,什么也不用说。他知道没那么简单,她的内心一定进行了一番复杂的加减乘除,正数很大,负数也不小,结果两相抵消,变成了“什么也不用说”。一只冰凉的手伸过来,帮他理了一下衣领,他一个激灵,王俐噗嗤一声笑了。
你看看你,都快三十了,还毛毛躁躁的。
她的口气听上去是个老妈妈,老妈妈配老爸爸,准老夫老妻。三十不到,就这样了,再下去就是一对骷髅,连体的,互相嵌进对方骨骼。王俐放下勺子,叹口气。
你这个死样子,怎么当爸爸?
你说什么?
王俐只是笑,把搅过咖啡的手收回去,摸一摸肚皮。四下突然响起尖锐的、只有他能听见的啸音。老妈妈慈爱地拍拍他的头,向他出示了一张照片。照片看起来没什么杀伤力,就是普普通通的两道杠,他还是感觉被抡了两棍。果然,之前的暗示她压根儿就没听进去,她以为那只是抱怨。
俐俐,咱们不是说好了,这事儿过两年再说吗?
对,那是两年前说好的。
不是啊,我这边不是还在影视公司混着嘛。你也说了,我这个死样子,怎么当爸爸?
你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我现在手头有个好东西,关注小人物的,写出来准能火!
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你说等好东西写出来,你就自由了,再也不替人打杂了!后来老板给你发奖金,你又变成了一条狗!
你以为我想拿那个奖金?那个奖金后来花哪儿了,你不比我清楚吗?
黄泥汤直接冲他的脸泼过来,温热的,醇香的。她狠狠地哭了,留他一个人在座位。服务生眼疾手快,在他手边递上一包纸。他摸索着,把自己细细擦了一遍。四周的花瓶、瓷摆件、水晶球、绿萝、方糖罐、香薰烛台、手摇八音盒静静地目睹了这一切。出了门,天地一宽,一条顺滑的馬路,缀着灯链。去哪儿?去太湖。出租车司机看着他,他知道自己现在就像刚从泥里爬起来。不打表一百。行。车窗大开,夜风挟着黑,抽打他的脸。他知道,他接下来的行为,全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他会找个地方躲起来,变着花样,用酗酒、失眠、暴走等方式,尽可能地把自己搞得像只流浪动物—瑟瑟发抖、毛发凌乱、眼神湿漉漉。直到她担心他,找到他。他会声称自己已经无药可救,劝她别费心了,“你把我忘了吧”逐渐升级到“你就当我死了吧”。这一套,他们都腻了。他使着暗劲,把她往世俗那边推。其实一开始他就知道,她跟他不是一路人。那又怎么样呢?课间休息的时候没人想继续研究课本。网红奶茶、园林年卡、老字号小馄饨、时鲜菜馆、胶片机、手冲咖啡,他在海面漂流太久,渴望伏在世俗的碎片上休息。这些多孔的、轻材质的日常,摁下去,又会顽强地浮起。人民路和干将路两大主干道切割了市区,大道生出分支,分支里藏着小巷,小巷尽头是一分为二的小天井,天井里有树,树上有鸟窝,鸟窝里有鸟,扑棱一声跃入海蓝的天空;随机选一条街,照着美食APP,一家一家吃过去;每个月去一次拙政园,在同一角度拍同一棵树;夏天去西山农场摘杨梅,冬天去东山农家乐吃白切羊肉。这几年,他们在万花筒里迷了路,很快乐。但他始终觉得,这是一座细节拼成的鹊桥,让他俩得以相会。脚下踩着密密麻麻、蠕动的边角料,充满不安的液态感。
这次跟以往不同,有异物入侵。如果他纵容它,胚胎就会长成怪兽,用触手缠住他,撬开他的颅腔,痛饮脑浆,吃掉里面未成形的侏儒。在接近西环岔路的时候,他让司机掉头。计价表开始跳动,计算他思考的里程和费用。
“那是一场结结实实的恶斗。
王建国喊他‘土行孙也不是第一回了,侏儒一直在心里计数。他有自己的积分制,虽然他也不知道具体数目是多少,但这个下午,他出手了。等上铺的张龙应把脸从漫画上移开,侏儒已经把一只小拳头捣在王建国肚皮上。
王建国一愣,笑起来。他的笑显然抄自黑帮片里的老大,一抽一抽地往外冒,像打嗝一样,压不住。突然,他脸一寒,笑从脸上跌落。王建国出手很利索,他像他爸揍他那样,先是给了侏儒一个嘴巴,接下来又是一个。如果侏儒是一个陀螺,一定会滴溜溜顺时针转起来,而不是涩重地停在原地,难堪、滑稽,浑身都是懒骨头,呼唤着更解痒的暴力。张龙应在高处看着侏儒,没有要帮忙的意思。他看出来了,侏儒是在故意找打。光喊绰号哪能过瘾呢?显然是拳脚的触摸更亲密。除了打架,平时没人愿意碰他,侏儒病毒会传染到你身上,让你看起来永远像个从福尔马林溶液里逃出来的巨婴标本,背影可爱,正脸可怕。揍我吧!你看,这一拳下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跟你所有揍过的人一样皮实,我没有一碰就散架,像你们谣传的那样。使劲揍!别偷懒!侏儒死死抱着王建国的大腿,一口下去,咬得他嗷嗷叫。王建国这才认真起来,一把揪住侏儒的头发,在他后背狠狠捣了几拳。这几拳手感奇特,好像是什么东西断在肉里,他把它打得更碎了。王建国有点怕,换成用脚踹,两下就把侏儒撂倒在地。侏儒弓成虾形,王建国没头没脑一顿踢,嘭嘭嘭,声音沉闷,像在踢一只小号沙袋。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王建国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踢。踢一脚,它就动一下。一停下,就死气沉沉。得连着踢,感觉才像个活物。终于,沙袋蠕动起来。大家一起看着,包括王建国。它一节一节捡回四肢,慢慢拼成侏儒的形状。他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样血淋淋,他看起来甚至没什么伤,就是睡了长长一觉,浮肿、呆滞。好几次他想站起来,但没有成功,只好坐着,小小一尊。王建国得了解脱,啐了句‘土行孙,掉头就走。没想到侏儒从身后扑上来,死死抱住他的脚。王建国想拔,拔不动,干脆站着。站了一会儿,脚猛一抽,侏儒吧嗒一声掉下来,软绵绵一截,皱巴巴的。这时,张龙应才下床,打了盆热水,拧了毛巾,一点一点地,帮侏儒擦脸、擦手。此后,‘土行孙三个字销声匿迹。
很多年后,王建国仍然记得那个下午。他俩打得投入、磊落,惊心动魄。此后,他辍学、学修车、做生意,他再也没有跟别人用这种方式合作过。”
出租车停在河畔天园小区东门,司机说,加上刚才没打表的那段,一共五十块,怎么样?他点点头,翻出一张纸钞,递到司机肩膀上。司机接了钱,对光弹一弹,摇下车窗,摸出打火机。他坐着不动,咖啡渍干在脸上,紧绷着,像是被烫伤后长了一脸新皮,还没撑开。司机吐一口烟,回头看他一眼,他说,去苏通花苑。
龙应刚洗完澡,裹着条破破烂烂的大毛巾。他绕过龙应,直接去冰箱里拿了罐红乌苏,抠开,仰头干了一大半。不行,才4度,太慢。他走进厨房,开始翻库存。运气不错,他找到半瓶红星二锅头。很好,50度。解忧口服液,马上见效。
你干什么?你给我放下!
哥们儿帮帮忙,帮帮忙好吧?
这是老子的酒,你想独吞?
两人僵持不下,对视一眼,突然笑了。龙应在冰箱深处掏到几个青椒,洗了洗,分他两个。一小碟食盐,白粉似的。把青椒拦腰撕开,蘸一点点盐,咬一口,辣得嘶哈嘶哈;再抿一口酒,另一种辣,嘶哈嘶哈,就像在喝火,两种火。这是龙应他三舅的喝法,他三舅写一手好字,会画画会刻章,就是小时候生了病没钱治,一只脚跛了,终身未娶。他俩读小学那会儿,跛子经常在路灯下摆个小板凳,自斟自饮。永远是黄泥汤一样淋下来的昏暗灯光,永远是六块一瓶的洋河大曲,永远是伛偻的背、颧骨深陷的脸。龙应跑,他追,绕着跛子转。跛子是掩体,可以用来躲机枪。现在掩体不在了,他们自斟自饮、满身弹痕。
你到底怎么想的嘛?你表个态。
你口气怎么跟王俐一模一样?
天王老子摊上这事儿,都是这个口气。
我不知道。
不行,你不能不知道。
过了今晚再说好吧,帮帮忙。
龙应顿了一下,点点头。过了今晚,他就没有退路了。龙应从床底拖出一只黑色旅行袋,让他猜是什么。他说这还用问,碎尸呗。龙应一掌拍泼了他的酒,拉开拉链,掏出一把吉他。还留着?留着呢。没传给你闺女?她俩一个钢琴一个古筝,我传给谁?你们组个乐队嘛!父女三人组。龙应不吭声,他笑着拍拍龙应:喂喂,跟你说话呢!键盘手吉他手都齐了,组一个嘛!龙应还是不吭声。你看看你,又装死!当年律师叫他装定位雇人跟踪那对狗男女,他不吭声;前妻骂他挣不到几个臭钱天天就知道搞花架子,他也不吭声;女儿问爸爸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他还是不吭声。不吭声的中年跛子抱起老吉他,翻出手机里的原唱,来了一段:
哥哥你今回的北游
觉悟了生命的充实
领略了友情的真挚
领略了友情的真挚
社会阵场上的勇将
在轰烈的炮火中间
别忘却身心的和睦
别忘却身心的和睦
奋勇呀然后休息呀
完成你伟大的人生
奋勇呀然后休息呀
完成你伟大的人生
他也一起唱,两人都尽量不看对方。这种时候就像光着身子,怪不好意思的。他的外套跟墙一个颜色,他起身,一小部分墙就跟着走。就这样,两个“醉犯”把房间拆成无数块。眼看二锅头一寸一寸矮下去,他们决定来个彩排,以迎接明天“轰烈的炮火”。没开口就笑场,一会儿拍大腿,一会儿拍桌子,NG了十几回—
哎哟你用点心好不好!再来再来!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怎么可能?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不听!你就是不想要!
你看你,又发脾气!老发脾气对孩子不好!
你都不想要它了,你管它好不好?
不是啊俐俐,咱俩都没备孕,对吧?我这烟酒不离手的,孩子萬一不健康怎么办?
还没产检呢!你凭什么咒它不健康!
他一时语塞,心下暗惊,龙应的演技简直炉火纯青,绝对是源于生活、原汁原味。酒精把另一个龙应诱了出来,他再也不像他三舅了,他就是王俐本人:
我不管!只要我想生,谁也拦不住!
我不是不想生!我是不想现在生!
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我没权利吗?我不是孩子爸爸吗?
你现在知道你是孩子爸爸了!孩子爸爸的权利就是不要孩子?
它现在是个孩子吗?
它以后是!
对,它以后是!它现在只是个细胞!
你不是一个细胞长的吗?你爸妈当年可没有不要你!
我宁可他们不要我!我宁可我没生出来!
咱们能别玩中学生这套了行吗?
咱们能换位思考一下行吗?你觉得孩子愿意在这个时候被生出来吗?
孩子愿不愿意,轮不到你放屁!你去打听打听,现在多少人想怀还怀不上呢!喝中药,打排卵针!好好一个孩子,你非要杀了它,小心天打雷劈!你天天说要写个好东西,孩子就不是好东西?碍着你了?孩子生出来,老人家会帮你带,不费你什么事儿!那些大作家,个个都不要孩子?你就是在逃避!你这么多年都没孩子,写出什么来了吗!你没有!你马上就三十啦!你想过没有?有了孩子,你踏踏实实当个爹,说不定就写出来了!你想想,老天爷为啥现在给你这个孩子,这是天意!你看看你浑身上下那个矫情劲儿!孩子就专治你这一身病!再说了,人家铁了心要生,你还能杀了她,一尸两命?干脆痛痛快快的,赶紧领个证,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省得这么被动!你要是真让王俐把孩子打了,这事儿传出去,你以后别想找对象了!人家姑娘跟你好几年,图什么?你看我干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胳膊肘朝外拐是不是?你信我,就一个孩子,天塌不下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哥们儿,咱俩一块长大,真不是我说你,这事儿没得商量了,只能这么办,死心吧!
伴着再次响起的尖锐啸音,一行字过了他的脑子:
“他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他现在看上去很矮,像个侏儒。”
(责任编辑:费新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