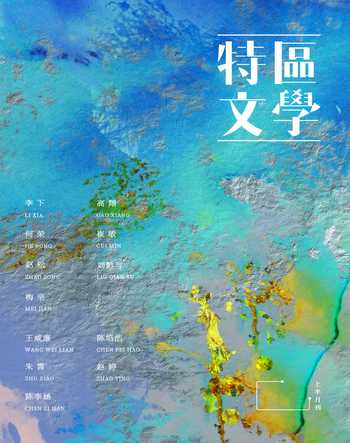野草在大地上蔓延的诗意
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倒立生活》等,随笔集《无法游牧的悲伤》等。作品被翻译为英、韩、日、俄、意、匈等文字。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首届“文学港·储吉旺文学大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雨花文学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金奖、第三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阎晶明先生的《箭正离弦》一书事关《野草》全景,标题的意象已传达出鲁迅创造出的那种奇崛的紧张感—从情感、语言到存在本身的紧张感。从写作《野草》时期的细微的人事处境,到诗与哲学的隐喻飞升,乃至版本与传播,《箭正离弦》为我们完整呈现出了鲁迅的“精神野草”:地下的根须脉络如何长成了地上的繁茂茎叶,又如何在大地上蔓延攀越,以至生生不息。
在这里,先简述《箭正离弦》的结构,它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野草》本事考,也即充分还原鲁迅写《野草》时的人生状态以及物质环境。我深深感受到了鲁迅写《野草》时的心境。他喜欢在夜晚写作,处于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正因如此,我们在《野草》中看到了那么多的暗夜和死亡。理解《野草》所诞生的现实背景,才能理解文中的景观是如何呈现的。比如,从一棵枣树到另一棵枣树,从院内到院外,他的目光犹如摄影机的运动,逐步将外在的世界呈现出来,这也提醒了我们《野草》这部散文诗集所具备的视觉艺术特征。书的第二部分对《野草》做了诗学和哲学上的阐发,但这种阐发是相当克制的。对《野草》的阐发特别多,有时不免有过度阐释的嫌疑。阎晶明的阐述是小心谨慎的,在本事考的基础上往前推了一小步:从鲁迅当时的心理环境和物质环境出发,但又不拘泥于这种局限。他让我们深入到“虚妄”“过客”等关键词的内部。在他看来,鲁迅的“虚妄”应该是一种悬置的精神状态,一种处在临界点上的心灵感受,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全部《野草》的核心。第三部分聚焦于《野草》的发表、出版与传播,这涉及到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复杂关系。比如鲁迅写《野草》时已经和周作人失和,却全部发表在周作人当主编的《语丝》上,这其中的微妙非常值得探询。另外,阎晶明也对一些涉及《野草》的污蔑文章进行了辩驳,比如说日本学者秋吉收认为鲁迅的《野草》受到了同时代一个年轻诗人徐玉诺的“极大影响”,导致鲁迅试图抹去跟徐玉诺的交往。阎晶明犹如侦探,用历史的材料证明鲁迅从未逃避与徐的交往,而《野草》也谈不上受了徐的影响。第四部分,阎晶明对《野草》的每一篇文章都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述,文字也如散文诗一般优美,呼应着《野草》的基调。
这本书对我的触动极深,我必须承认,我受到新批评的一些影响,曾是一个“文本主义者”,觉得作品完成后,就离开了它所在的土壤,进入到了一个纯粹的艺术世界。如果说,我是一个纯粹的读者,一个消费社会的消费者,持有这样的态度,也许是可以的。但是,我已经认识到了自身的浅薄,那就是这世上哪里有纯粹的读者,而一个彻底的消费者跟文学的精神难道不是相违背的吗?我寫作,我必须要面对我的时代土壤,要把这土壤带到写作当中去,这样的写作也许才是有价值的。
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读这本书,家人在说话,智能音箱在播放音乐,突然,孩子说:“我想听梅花鹿的音乐。”智能音箱马上响起了另外一首曲子的旋律,那是梅花鹿在奔跑的脚步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土壤。我悄悄关上了门,一个人好像获得了某种释放。我想到鲁迅写《野草》时都坐在他的“老虎尾巴”里。何为“老虎尾巴”?就是在后院加盖的一个小房间,如果放在今天,也许还会被当作违章建筑。但你会迅速意识到,“违章”与“野草”这两个意象之间有着深层的关联,《野草》中充满了“违章”的诗意和思想,包括它的散文诗的形式也是中文首次,也属于“违章”。这关乎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今天如何来理解诗意?
现代汉诗早已不像古代诗一样有格律,有平仄,有押韵……今天一个诗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分行,可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而去除了束缚,如何来直接表达诗意便成了愈加困难的事情。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以诗咏物或是以物言诗,是一种抒情的常态模式,其借助于对事物本身某种状态的呈示,从而反映出人与之相对应或相关联的某种状态与心境。借助物而表达情感,可以将情感那不可言说者进行充分传递。由此,事物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占据着主流地位。月亮、夕阳、春风、菊花、河流、美酒……这些构成了一个基本恒定的古典诗歌元素,一直沿用了下来,因为它对应于古典文化当中那个相对稳固的自然世界。但是进入近代以来,在鲁迅所生活的世界当中,这种自然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睁眼看世界”,看到的便是迥异于古典的一个现代世界。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边,不仅仅是有汽车,有飞机,有电话,连带着对于自然事物的象征价值也有了新的引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审美运动。
鲁迅将自己谦称为“历史中间物”,不得不说,《野草》在很多方面确实有种“中间物”的状态。《野草》对于意象的运用,跟鲁迅古典诗歌的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野草》中的主要意象已经远远偏移古典诗学的意象体系。从古典诗学的角度来说,“野草”并非是一个适合抒情的意象,在漫长的历史中,即便它出现在文本中,也常常代表了某种负面的东西:比如芜杂,比如遮蔽,比如丑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在鲁迅这里,“野草”忽然间获得了热烈而奔放的生命力,那让我们厌弃的丑陋之物,焕发出了令人动容的精神力量。《野草》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悖论空间。如果我们不把这种审美嬗变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来看,就不会惊异于这种创造的开创性是多么巨大。
我们看到鲁迅在《野草》当中使用了那么多奇怪的意象:野草、猫头鹰、蛇、刀、风筝、蒙汗药……这些东西在古代很难入诗,但鲁迅让它们闪烁出了奇异的诗意。我之前特别好奇鲁迅的想象力的生发方式:怎么会有赤练蛇、猫头鹰这样古怪的物象进入他的生命隐秘体验呢?这是我作为写作者特别关切的问题。我会想:鲁迅读过了很多外国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受了国外作家的影响,才会这样去写?就像中国古代不把玫瑰和爱情联系在一样,玫瑰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意象。《箭正离弦》这本书回答了我的这个隐藏在心底多年的疑问。在阎晶明的考证下,原来这些意象活生生地存在于鲁迅的生活空间当中。有几个小细节我印象特别深,《箭正离弦》书里写到,鲁迅他平时居然在床下放一把刀,那是防身的。鲁迅是属蛇的,所以他的邻居小姑娘给他起个外号叫“野蛇”。还有《腊叶》,确实是跟他与许广平的爱情是有关系的,但这里面又有很多爱情之外的对于人生况味的隐喻表达。阎晶明对鲁迅当时生活的环境进行深入追索与绵密复原,让我遽然发现,鲁迅所使用的意象并非是凭空而来,而是与自身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从而我更好地理解了艺术中的现实元素,更好地理解了鲁迅使用这些意象所具有的那种本原性的冲动。我领悟到意象之于真正文学创作的价值:意象的塑造与作家的创作之间注定有着时代与生命之间博弈的那种深刻烙印。
今人重复使用古人的意象,文学便会失去生命力。如果没有对这种现代诗意的理解,我们的文学还是停留和局限于“风花雪月”那一套符号系统里面,我们就没有真实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感受,从而我们便是没有真正接纳自身所处的时代。鲁迅的意象是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又走向了一个极为幽微深远的艺术空间。理解这点后,我们才能理解阎晶明《箭正离弦》通过对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的研究,像一道明亮的探照灯光,为我们照亮了鲁迅的那已经逝去了的但依然丰沛的世界。这关乎作家写下的作品跟作家生命之间的深层关系,提出的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发生学,是为我们时常忽略却极为重要的。
鲁迅及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高度自觉精神的生命美学,这种生命美学有着令人炫目的内在能量,也让我们认识到离开生命温度的“纯文本”的意义终归是有限的。我们还是得回到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那种“理解之同情”的模式当中。正如人工智能时代,程序APP都可以写诗一样,但这样的诗句只是对语言符号的模仿、编码和生产,与人类精神的表达以及对人类生存图景的观照是毫无关系的。
将《野草》生长的土壤带到读者的阅读视野当中,实际上正是为我们还原一个相对完整的鲁迅,而不是那个已经被时间反复冲刷、各种话语透镜扭曲的鲁迅。类似植物的移植,根须一定要与土壤同时储存,而不能清洗过于干净而伤及根须。莫若说,根须与周围的土壤已经浑然一体了。将作家及其生活的时代同时审视,尤其是辨析贴近于作家身体的部分生活,我们才能发现写作是如何生发,而又如何超越局部抵达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我想起法国诗人博纳富瓦的一句诗:“必须给语言本身赋予一种智力。”写作便是不断地给语言本身赋予智力,赋予情感,最终赋予人类的精神世界以生命。
写作这个过程意味着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从而获得了一种与世界对峙的勇气。—你虽然渺小,只是一个个体,但是你面对庞大的世界的时候,你依然是有话可说的,是可以评判的,是可以创造出一个平行世界的,这充分体现了生命的尊严。在今天这个“泛写作”的时代,每个人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表达机会,其实我们要冷静想一想,写作到底怎样生发出来的,文章是怎样来构成的。把当代的经验以及物象,化入文学的溶液当中。作家阿来经常举美国诗人桑德堡的一句诗:“美国,它已经长出了钢铁的身体/但我们诗人还没有长出钢铁的牙齿/来消化它。”我举桑德堡的例子,还有一层意思,桑德堡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桑德堡出生于1878年,比鲁迅大三岁。在鲁迅的时代,中国可没有长出钢铁的身体,而是,更加混乱、失序、充满绝望,是鲁迅的牙齿在消化着那时的中国。因此,鲁迅的写作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根基。
我不禁想起,有段时间我没有读鲁迅,几乎遗忘了他。有一次,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文章时,他提到鲁迅,这让我有些意外。大江健三郎写道,他的母亲问他:你写了那么多东西,但是你读过鲁迅的《故乡》吗?你读过鲁迅的《希望》吗?大江健三郎觉得很惭愧,赶緊找来读。在大江许多作品的译者许金龙的文章《“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中,提到大江于2009年1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文章也得出结论:“在大江的整个创作生涯期间,鲁迅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根据这个参照系所进行的五十年调整,使得大江文学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
该惭愧的是我,对鲁迅的重读应该是一个当代写作者必需的参照系。而细读《箭正离弦》,提醒着今日的文艺创造,要像鲁迅那样,凝视身边的物象,凝聚当代的经验,让它们经过思想的锻打与语言的溶解,成为我们精神审美与内在体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