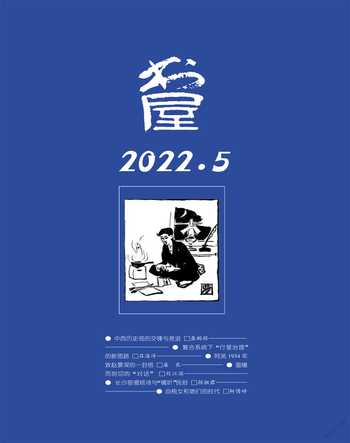史景迁与《王氏之死》
赵旖璇
史景迁作为美国汉学“三杰”之一,写下了十余部有关中国明清和近现代的历史叙事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美国众多读者的喜愛,也为他赢得了很多荣誉,他还一度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体现了美国历史学界对他的肯定。而在史景迁的所有作品中,有两部争议最大,其中之一就是《王氏之死》。此名字乍听就会有一股小说之感,实际上人们对于《王氏之死》的争议正是集中于它的史料选取与写作技法上,这种争论也代表着国内外读者对于史景迁“异数”的文学化写作方法的质疑。
在回答卢汉超的访谈时,史景迁对自己写作风格的一段概括给了我们理解史景迁大门的钥匙:
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
《王氏之死》一书的中心思想在副标题便有展露,而在前言中则有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解释:“把这些说成是‘小事是因为相对于整个历史背景而言,而对于那些实际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这些事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史景迁谈到他将镜头转向1668—1672年间的一个叫郯城的小县城:“所聚焦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老百姓:农民、田间佣工,以及他们的妻子,这些人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社会的帮助,也没有强有力的家族组织的支持。”这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以往史学家只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与之联系的重要人物、地点的惯例,将视角聚焦于中国山东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郯城和生活于其中的一个无名女人王氏,关注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底层农民的命运,可以说是开创了小人物叙事的先河。围绕“小人物与大历史”这个主题,史景迁从四个小而具有冲突的事件上去考察他们:第一,土地耕作和税收;第二,寡妇保护她的孩子和遗产的努力;第三,地方恩怨而带来的暴力;第四,王氏妇人的决定,她不再愿意面对一个不可接受的现状而逃离她在郯城的家和她的丈夫。
毋庸讳言,史景迁的作品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史实差错,本文在这里浅谈两点:
第一是有些地方对史实把握不准确。比如,第一章讲蒲松龄在十八岁中秀才后,直到七十一岁时,才经由特别的恩赏获得了举人的头衔。实际情况是,蒲松龄并没有中过举人,他十八岁即取得了生员功名,但其后在科举上没有斩获,直到1710年,才因岁贡成为贡生,但贡生并不是举人,两者不能混淆。岁贡生是按资历递升的贡生,按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研究》一书中的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以前,全国每年的岁贡名额不多于一千名,因此蒲松龄因岁贡成为贡生,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贡生虽然地位高于生员,但要成为举人,则必须经过乡试,而一旦乡试中举,其势力和地位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改变。因此,很多贡生也像生员一样,汲汲于参加乡试,冀图中举。
第二是书中有些记述对清代的相关制度的理解有误。例如,第三章讲寡妇李氏有两子,一子力田,一子读书,“读书的儿子通过了乡试,后又通过省一级的‘举人考试”。这里的表述混乱且错误。按说考中举人的考试才是“乡试”,“乡试”之前的考试应是获得生员功名的县、府、学正主持的童试。清制,要取得生员功名须通过县、府、学正主持的三级童试;通过县试为俊秀,仍属于无功名的平民,通过知府主持的府试和学正主持的院试者,才能获得生员功名。生员可以参加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再比如,写黄六鸿接到任某及任父投县诬控高某杀死王氏之案后,第二天即审判高某,第三天才到高某家中勘验王氏尸体。我们不知道这是黄六鸿的记述有误,还是史景迁的笔误,总之这并不符合清代处理人命案的法律程序。清代刑科题本的无数案例告诉我们,知县在接到命案报告后,在程序上应是立即赶往现场勘验尸体,然后才是审问犯人。
史景迁有错误很正常,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本身就不如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汉学研究在过去的美国是非常边缘的,汉学研究资料也是极为有限的。在如此学术环境下,史景迁能在图书馆书中对王氏的偶然接触中,抓住郯城甚至是中国晚清中国县城中妇女处境的核心问题,已是相当令人敬佩。
在前言中,史景迁已自我披露了此书所使用了三大史料——第一个资料是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第二个资料是官绅黄六鸿于十七世纪九十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第三个资料是散文家、短篇小说作家和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美国汉学界使用史料的传统是利用档案材料如地方志、官绅笔记及官方档案等,史景迁也遵从这一传统,首先关注的是地方志和官绅笔记。由卸任知县冯可参纂修的《郯城县志》有较多的历史统计数据,在还原郯城这个“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数据匮乏”小地方的历史图景时,对其多有借鉴之处。郯城知县黄六鸿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在退休后著有《福惠全书》,记述了相当多较详尽的事例,《王氏之死》中的事件大多来自黄六鸿的记述。史景迁除了运用传统史料以外,最为大胆的就是大量使用了时空上与王氏基本重合的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中的材料,用以构建小人物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用以描摹小人物的欲求和念想。
在研究方法上,史景迁运用多学科视角对小人物生活的环境进行多维度的诠释。简单来说,小人物生活世界的场景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部分,其中静态的部分,如郯城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场景,诸如地震、蝗灾,落后的农业经济,以及税收压力等,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眼光来叙述;而动态部分,如小人物他们自身的生活世界中的一些场景,诸如日常生活、收入消费等经济生活,乃至家庭家族等伦理道德生活等,则用动态的法学和社会学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
对于史景迁走入汉学研究的殿堂之路,用两个短语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在象牙塔中培养兴趣”“从菜篮子里看形势”。出生在英格兰书香世家的史景迁从小就接触到了优秀的中国文化。他说:“我觉得非常惊奇,中国画与我以前接触到的艺术形式都截然不同,加上当时正处在二战期间,中国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英雄,我对中国的兴趣就在那时候产生了。”从温彻斯特公学到剑桥克莱尔学院,再到耶鲁大学,史景迁的求学之路顺风顺水。在耶鲁,他受到芮玛丽的赏识从而踏入了汉学研究之路。然后又受房兆楹的悉心栽培,投身于清史的研究当中。同时,他又是一位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反叛传统的史学家,他一改传统史学家只注重上层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与之联系的精英人物的固化思想,转而把目光聚焦到下层社会,学者卢汉超形象地将其概括为“菜篮子里看形势”。
这是单单从史景迁的个人求学经历来讲,而对史景迁的观察还应该放在美国中国学这个大背景中观察。首先,史景迁的学术历程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他的史学训练、学术成长都离不开美国中国学的大环境。一方面,他是在美国中国学大师芮玛丽和芮沃寿的引领下走上学术之路的,接受了严格的史学训练。他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费正清、芮玛丽等前辈的提携和帮助,费正清为他的多部著作撰写了书评,不吝嘉奖之词,他也经常参加费正清在家中举行的学术下午茶会。另一方面,他与美国中国学的整个学术圈密不可分。史华慈、孔飞力、魏斐德等人与他互相写书评,他所获的各种奖项及任职也代表了美国中国学界对他的认可。他的许多学生如韩书瑞等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大家。可以说,史景迁本身就是美国中国学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他独树一帜的写作手法也丰富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
——以明代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