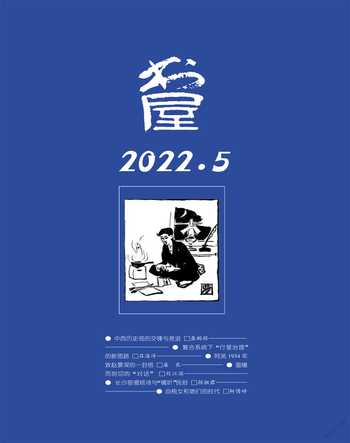胡适的日语学习
杨华波
胡适的留学经历和研究需要使他很看重外语的学习,他本人就学习过多门外语,除英语外,还有拉丁语、德语、法语和日语。英语、拉丁语、德语和法语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的正式课程,但英语显然是重中之重,其他几门则多是一般性的课程,胡适在毕业后便未再对此多费时间和精力。让人诧异的是,胡适在求学时期并未系统研修过的日语却成了他此后坚持学习的外语。他不仅购藏了众多日语教科书和辞典,还在其日记中留下了相关的学习记录。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可以了解胡适不为人知的外语学习经历,并探寻他学习日语的动机和目的。
胡适起意学习日语在其留学美国期间。1915年1月24日胡适在《纽约时报》中读到日本人T. Iyenaga(家永丰吉)的文章“Jap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War”(《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他惊异于作者在中国中立问题上的“肆无忌惮”,深受刺激。胡适认为:
……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日本者,完全欧化之國也,其信强权主义甚笃。何则?日本以强权建国,又以强权霸者也。
吾之所谓人道主义之说,进行之次宜以日本为起点,所谓擒贼先擒王者也。
且吾以舆论家自任者也,在今日为记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
据上两理由,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
吾其为东瀛三岛之“Missionary”乎?抑为其“Pilgrim”乎?抑合二者于一身欤?吾终往矣!
此时的胡适已经将促成中日两国间的相互理解作为其重要的使命之一,而其前提便是要掌握日语,至少应达到利用日语演说写作的程度。
同年5月2日的日记中,胡适再次重申了他学习日语的动机,还记述了购买教科书的过程:
吾前此曾发愿研究日本之文明,偶以此意告叔永,嘱叔永为购文法书应用。叔永转托邓胥功,告以余所以欲习日文之意。邓君寄书二册,而媵以书,略云:“日本文化一无足道:以综而言,则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则男盗女娼。”又注云:“此二语自谓得日人真相,盖阅历之言。”嗟乎!此言而果代表留日学界也,则中日之交恶,与夫吾国外交之昏暗也,不亦宜乎?
1915年正是日本加大对中国的侵略之时,在中日两国国势日异的背景下,胡适想探求日本文明的发展,并在这一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决定学习日语。由于远在美国,他委托好友任鸿隽代购日语文法书,任氏继而转托正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四川同乡邓胥功,最后才为胡适买到他想要的教材。经查,胡适藏书中出版于1915年前的日语教科书有《东语正规》(1905)、《中日文通》(1905)、《日语新编》(1906)、《文法适用东文教科书》(1906)、《汉译日本口语文典》(1907)和《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1913)等数种,其中1913年由松本龟次郎编著、日本东京国文堂书局出版的《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即是胡适在美期间藏用的。该书目前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扉页有胡适题记:“民国四年五月一日,邓君胥功赠,胡适之。此余所有日本书之第一部也。适。”胡适后来又得到该书作者的签赠本,为1926年的重印本,扉页有题记:“胡适先生赐览,著者松本龟次郎拜赠。”签赠本中夹有胡适学习日语的七页笔记,可证胡适使用过这本书。同年松本重印的《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也曾签赠给胡适,题词与前一著作同。胡适还藏有该书1919年的版本。可见,在得到著者赠书前,胡适已自行购藏。赠书者松本龟次郎(1866—1945)是日本近代教育家,辛亥革命前曾在北京的京师法政学堂担任日语教习,后返回日本创办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并编纂了专供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教科书数种。1930年,他还曾来中国考察教育。胡适和松本订交的时间不详,但到1934年松本出版他的《译解日语肯綮大全》之时,两人似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因之胡适为其书题词:“学得一国语言,好像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该书多次再版,1942年已发行至第14版,胡适所藏为1934年的初版本,应为著者所赠。
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后仍坚持学习日语,其1929年4月9日日记记载:“这几天开始读日本文,用葛祖兰兄的《日语汉译读本》,颇感觉兴趣。”查《胡适藏书目录》知,此书全名为《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出版于1928年,是由著者葛祖兰赠送给胡适的,封面有作者的题记:“适之学长,祖兰。”该书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内有胡适朱笔批注圈画的痕迹共八页。葛祖兰(1887—1987),字锡祺,慈溪人,1905年赴日留学,1909年毕业后任教于广州和上海,曾任上海澄衷中学校长和商务印书馆编辑。因胡适留美前曾就读于澄衷,是该校校友,因此两人少不了联系。除这一读本外,葛氏还曾赠送其编著的《日本现代语辞典》(1930)和《日语文艺读本》(1931)给胡适。
此外,胡适回国后购藏的日语教科书还有《日本语读本》(1926)、《日语会话》(1927)、《表解现代日文语法讲义》(1935)和《日华对照日文翻译着眼点》(1935)。其中,后两书都由著者汪大捷所赠,书的扉页有其赠书给胡适的题记。
全面抗战期间,胡适于1937年赴美,此后忙于外交事务和考证《水经注》,很少有时间学习日语,其日记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要掌握日语的夙愿,在台湾的胡适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避居台湾期间购置了《实用日语文法》(1957)、《日本语法精解:英文法比较研究》(1957)和《日语之门》(1960)等教科书。其中,《日语之门》由台北启明书局出版,列为“日语自修丛书之一”,书内夹有一张胡适红笔练习日文字母的字条。可见,即使七旬高龄,胡适仍然没有放弃学习日语。
除了教科书,胡适还购藏了数种日语辞典,除了上述葛祖兰赠送给胡适的《日本现代语辞典》,还有《英和双解熟语大字汇》(1902、1905)、《俗语辞海》(1909)、《汉译日本辞典》(1913)、《新汉和大辞典》(1917)、《熟语集成汉和大辞典》(1925)和《大汉和辞典》(1933)。
如果说胡适留学期间立志学习日语的动机是增进中日了解,那么,其后他的职业需要和学术兴趣使他萌生了新的动机,即读懂日文文献,追踪日本汉学界动态。在现存胡适藏书的外文书刊中,日文书刊的数量仅次于英语书刊,包括图书近三百种、期刊三十余种。胡适回国后与日本学界保持着较为频繁的往来,他的《胡适自传》和《中国哲学史》等著作被翻译成日文,他与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入矢义高、室伏高信、吉川幸次郎、诸桥辙次、桑原骘藏和铃木大拙等人时有来往。由于日本汉学家大多熟悉汉语,至少可以和中国学者笔谈,他们的汉语书写能力令胡适艳羡,也让胡适为自己无法用日语写作感到遗憾。1920年胡适在回复青木正儿的信中便说:
你的白话信,我全看得懂。偶有一两处很微细的错误……我若能把日本文学到这样通顺的地步,我就真要高兴极了。
对于日本汉学界研究的禅学史、小说史和水经注研究,胡适也时常追踪,藏有《佛教研究》《中国文学报》《东方学》和《东方学报》等日文刊物。由于胡适不精通日语,收到的日文信件或著述,往往只能求助于翻译。1953年在美期间,胡适还请杨联陞代为寻找译者:
想请你将日本《东方学报》第三册的森鹿三的《戴震之〈水经注〉校定》一文,作photostat一份,寄给我。其费用务乞示知,当照缴。若有精通日文之人,肯将此文的结论译成汉文或英文见寄,我也愿出翻译之费。
总之,学习日语是胡适在留学期间即立志达成的愿望,但他终究没有余力实现。不过,他自始至终都未曾放弃,不管是回国后身居北京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六十年代初生命结束前困居台湾的日子,他都曾自学日语,这可以从他的日记和藏书笔记中得到证实。虽然胡适的日语能力并没有阻碍他与日本学者的正常交往,中日两种语言间的渊源也没有阻碍他部分阅读日文书刊,但无法利用日语交流和写作对胡适而言是终生遗憾,早在1935年他在回复室伏高信的信件中便感叹“可惜我能读的是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