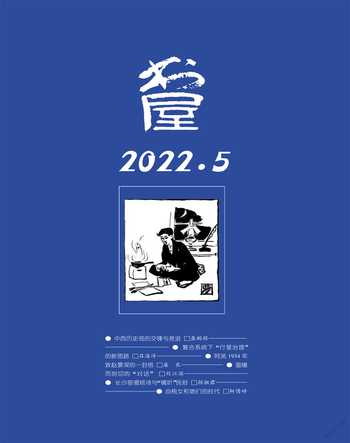不能忘记的一个诗人
张建智
毕奂午,原名桓武,后改奂午,曾用笔名毕篥、李福、李庆、鲁牛等。1909年生于河北井陉县贾庄,一个太行山东麓矿区的小山村,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以挖矿为生。毕奂午父辈和家庭出身已不可考,零散的资料基本都只写到他的童年是与祖母一起度过的。祖母知书识字,给毕奂午很好的启蒙教育。毕奂午小小年纪便已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祖母给他讲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的故事,也给他埋下了文学创作的种子。想来,辛亥革命前的河北山村,大量的妇女受教育程度相当低,这位知书识礼的祖母该是位世家闺秀,由此推测毕奂午家在当地可能也是乡绅书香之家。而贾庄的地方志文献载,毕氏是当地的望族,明嘉靖年间,贾庄毕氏始祖毕扶由井陉七狮窑迁居贾庄村西高埠处,建造房屋“毕家台”。毕家台至今依旧在贾庄老街,而毕家累世文脉绵延,出了不少贡生、监生。
毕奂午在贾庄当地的新式小学念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历史悠久,老舍便是这所学校早期的毕业生。毕奂午就读北师时的校长是王西徵先生。王西徵是位卓越的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
这位不凡的诗人因各种原因出版作品不多,我收藏的毕奂午的诗集,只有《掘金记》,1936年7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所版,属于全面抗战前夕“文学丛刊”系列丛书之一。
“文学丛刊”自1935年底至1949年初由巴金主编,陆续出版达十集,每集十六种,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评论。可谓是民国期间出版时间持续最久、内容丰富广泛、思想艺术水平很高的一套系列丛书。其在书装上自始至终都采用三十二开本,一式的封面设计,素白封面,全无装饰,只印上书名、丛刊名、作者名和出版社,极其朴素,却自有一种简洁大方之感。
“文学丛刊”每集十六种,诗集并不多,仅一种或两种,但被“文学丛刊”选中出版的诗集,往往都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如第一集卞之琳的《鱼目集》、第三集臧克家的《运河》、第四集胡风的《野花与箭》、第五集曹葆华的《无题草》、第六集邹荻帆的《木厂》和王统照的《江南曲》、第十集陈敬容的《盈盈集》等。
《掘金记》是“文学丛刊”第二集中唯一的一本诗集,该集另有长短篇小说九种、散文五种、剧本一种,作者阵容包括靳以、萧军、沙汀、芦焚(师陀)、荒煤、周文、柏山、蒋牧良、欧阳山、陆蠡、丽尼、悄吟(萧红)、何其芳、巴金和李健吾。
其中,萧红的《商市街》和何其芳的《画梦录》都是两位作家的散文处女集,且日后皆成为新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可见主编巴金的敏锐文学嗅觉和扶持新人的独到眼光。
尽管诗人毕奂午和《掘金记》今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诗集甫一出版,在当时新诗界便激起一阵浪花,好评如潮。诗集刚一出版,京派评论家李影心就在1936年8月30日《大公报·文艺》发表书评给予高度评价:“我们缺乏那种气魄浓郁的好诗。两年前诗坛出现了臧克家,我们极感悦快;现在,《掘金记》的作者又重新燃起我们对气魄浓郁好诗的期望……博大雄健与绵密蕴藉同为新诗开拓的广大天地,诗人尽可依据自己禀赋环境,跋涉任一适合自己脚步的路程……我们不大清楚毕奂午先生在《掘金记》外是否另有诗作,不过仅读《掘金记》那一首诗,便可见出这位新晋诗人奇拔的气魄,恰是歌唱了诗人自己进展前程的序曲。”
除李影心外,同为诗人、当时以《画梦录》在文坛享有盛名的何其芳对毕奂午的诗也十分欣赏,1938年他在“成属联中”执教时编的《新文學选读》就选入了毕奂午《春城》《村庄》两首诗,数量与闻一多、徐志摩等相同,仅次于卞之琳,而郭沫若只入选了《地球,我的母亲》,戴望舒只入选了《我的记忆》而已。
何其芳认为毕奂午的诗有臧克家现实主义的张力,且他的诗“笔力粗强似甚于臧克家”。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作为新诗理论家的闻一多编《现代诗钞》时,《掘金记》已被列入“待访”诗集,当时毕奂午身陷日军监狱,闻一多以读不到毕奂午的诗为恨。
《掘金记》分为两辑,第一辑收十首诗,第二辑则包含四篇散文,书中没有诗的写作时间,但作者在书前的题记中写道:“这里面的文字,一大部分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写的……四篇散文,写的时期略微靠后,是两年前吧。我从中学毕业了,趁暑假回到我那位置于一个大矿山附近的故乡去一趟。在那里我看见不知有多少的人是遭遇着像《冰岛渔夫》里面所描述的人物的同样命运——潘堡尔壮丁们的生命是都被大海吞噬了……于是我便描了这样几幅小画。但它们并没有把河泊山下居民的哀愁的万分之一申诉出来。”
由此可见,诗集的两辑恰对应诗人两段人生经历,由纯真懵懂的文学少年,到进入社会更深刻思考社会痼疾的青年文人,而细读两辑中的文字,也会发现诗人文风从轻灵变得雄浑。第一辑中除了与诗集同名的《掘金记》一首,多是短小的诗,我最喜欢的是《春城》和《田园》两首,均来自诗人初中课堂的习作。新诗历史上,中学生的习作收入诗集的例子并不少见,如汪静之的《蕙的风》、陈敬容的《盈盈集》中都有数首中学时的习作,但课堂作业直接作为成熟的创作公之于众倒并不多见。而且,毕奂午这两首诗的语言、意象、韵律,都堪称完美,如果不是诗人在题记中言明,绝难想象是出自稚嫩学生之手。《春城》一首,以一句“也是春天”的极短句开篇,既点出了全首的季节背景,又给读者留下了一点悬念:又一个春天来临,该是勾起诗人年年岁岁春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之后,作者则以洗练而灵动的笔触,通过一连串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勾画出一幅初春的城市风情卷:赶马车进城的车夫、游荡在城街间寻营生的人们、缕麻编草鞋为生的鞋匠。“永不带〔戴〕手套的乡下人”“带着菜色的黑眉男子”“摸索于人类之足底”这几个细部描写,寥寥数笔,底层人民饥寒挣扎的卑微生活,便毕见纸上。然而,诗的色调又不尽是灰暗,“冒着杏花雨”“没有一棵苜蓿花,没有一棵金凤花”,让人读后感受到春日花开的亮色,但慢慢回味,却又涌起一种莫名的哀伤和凄婉,全诗以“向炎夏走去”结尾,恰与开篇呼应。整首诗,景与人物交融,意象生动,明暗色交织,情感流畅而细腻。
毕奂午诗中意象的营造颇为大胆,也独具特点。如《田园》中,诗以“新的鞋子/踏着旧泥土”起首,新与旧对应,鞋子与泥土两个意象,虚实间似有无穷的隐喻;后两句“到五月的海洋/眺望田间的麦浪”,海洋和麦浪形成一种自然的互喻,舒畅而繁荣的气象油然而生;而紧接着诗人又以芜菁、石榴花和晚霞比喻农女厨边通红的火焰,火光绚烂,把整首诗饱满的情感推至顶峰。
又如在《牧羊人》中,诗人写道“黄金色的米粒,价值/等于几瓣残红”“三月的太阳/空照银齿的镰刀”“春雷,如失意的老人/在阴沉的天空/隐隐呻吟”,这些意象的营造,使整首诗弥漫一种优美而萧索的徒劳感,使读者深陷其中,仿佛走进了诗人营造的村庄和田野。《秋歌》一首,诗人写催征的喇叭响彻田间的紧张感,却用了一种十分诗意闲适的笔调,结尾处“赤臂的苦力,肉搏/西风,落叶,黄花”,这两组反差极大的意象,产生惊人的张力,让人不禁想到:这些征战的人们在浴血奋战,而终将如黄花落叶般灰飞烟灭,随风而散。
毕奂午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深沉思考和悲悯,也体现在他的诗中,使他的写景和抒情诗有了思想的深度。他在《村庄》中写道:“我们曾把自己的谷子/一大排,一大排的〔地〕割倒,我们曾换得一个钱票/小而又小。”在《牧羊人》中他写道:“可怜的岁月是如此凋零”“汗水与尘土/再不能塑成/美丽的幻梦了。”诗人对社会不公与黑暗的控诉在《掘金记》这首长诗中达到顶峰,整首诗九十多行,不分节,酣畅淋漓,一气贯注。全诗记述了太行山民的一次掘金狂潮。
1934年,太行山區山洪暴发,随之传闻金矿大量流失,千千万万饥民怀揣侥幸的希冀,成群结队,背井离乡,疯魔一般地涌向太行山掘金,不分男女老幼,都用最原始的工具,拼命地希望哪怕挖到半点金沙。诗人用强健的笔力,描绘出这既魔幻又现实的场景:“随急风在天空飞起白云,随锹锄在地面流着石火。随着人堆上的劳作怒潮,每一颗心都想收获新果。”人们为了争夺一星半点的金沙,以命相搏,杀伤流血:“太行山的空气,整日里像不够人们呼吸,每个人都用方言叫骂,恼懊,焦灼,往往为一粒细沙,不惜用铁锹爆溅血花。”诗人准确抓住在掘金狂潮中各色人等的特点和心态,他们中有多年在塞外贩马的来客,有平山草地田野劳作铸就铁骨的农民,有凶顽野蛮的山民,有盲从发财梦的城市居民。但最终真正得利的是一些城市内的银楼业老板,他们精于算计,散布流言,乘机压低黄金收购价格,大大地捞了一把,而付出血与汗甚至生命的掘金者们,到头来只是被流言欺骗,白白做了一场梦,只剩痛苦的回味。
这首《掘金记》奠定了毕奂午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诗人通过这一并不知名的社会事件,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底层人民迫于生计的无助和愚昧,无良奸商唯利是图,最终陷入人吃人的怪圈。不同于前几首轻灵的小诗,长诗这种形式适合表现宏大的叙事和壮阔的感情,也更显诗人的功力,诗人投枪匕首般锋利的语言和深沉的悲悯融合得恰如其分。诗人选用这首诗为整部诗集命名,说明他对这首诗的看重。尽管,我更偏爱诗人早期的短小诗作,但不可否认,《掘金记》一诗在现代诗歌中更有地位。
毕奂午在题记中有言:“对于什么是诗或怎样写诗等类的文字,在那时自然有些看不懂;但我也总没有留心过。幼时对于几种玩具,如木马,布老虎……是那样渴望地想知道它们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对文学理论则从未发生半点兴趣。”由此可见,诗人对新诗理论并不感兴趣,也并未下功夫。相较于与他同时期的卞之琳、戴望舒等诗人在新诗理论上的着力,毕奂午的诗更多是自然的流露,而较少雕琢。诗人的目光紧紧地注视着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在艺术风格上,他也不盲从于当时新诗坛流行的新月派唯美主义,也不附庸于现代派的象征主义,而形成现实主义的诗风。毕奂午对自己的诗风并没有太多的描述,但从何其芳的一段文字中,我们可窥得一二。
何其芳与毕奂午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共事,何其芳在《梦中道路》一文中写道:“有一次我指着温庭筠的四句诗给一位朋友看……我说我喜欢,他却说没有什么好。当时我很觉寂寞。后来我才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实在有一点分歧。他是一个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分意义;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欢……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
何其芳文中所说的“一位朋友”即是毕奂午。何其芳在南开中学度过的岁月并不愉快,其时的他正处于对自己文学道路的彷徨之中,尽管凭《预言》《夜歌》,他已成为诗坛新星,但他有时“厌弃自己的精致”,而寻求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嬗变。何其芳曾读到毕奂午的《火烧的城》一诗,诗中有这么几句:“是谁被抛弃于腐朽,熟睡/如沉卧于发卖毒液的酒家/在那里享受梦境无涯?欢乐的甜蜜,吻的温柔谁不期待?但那带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指/将推你醒来……”何其芳读后,曾感慨地对毕奂午说道:“是的,我们不能再做梦了,而应该如诗中所言,让戴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把我们推醒、摇醒了……”
《掘金记》第二辑中的四篇散文《人市》《下班后》《溃败》和《幸运》所描写的皆是矿区人的生活日常,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更接近于微型小说。如《下班后》中在矿里工作十个小时的苏保,却无法让妻子吃上饱饭,而妻子为生计只能成为暗娼,苏保受不了工友的冷嘲热讽,但望着空空的米缸和饿得哀号的儿子,只无可奈何地嘟囔一句“长大,还不是得提安全灯,背拖钩……钻黑洞去”。作者用极短的篇幅,没有设置太多的故事情节,只是白描式地展现一系列小人物在艰难困苦中求生的场景。诗人笔下的矿区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像一个巨大的轮回,埋葬一代代矿区民众的希冀与生命。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毕奂午对太行山矿区,对那些山民、矿工、家庭妇女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写得非常真实,力透纸背。而创作这一系列短篇的缘起,可能是他与王洛宾在哈尔滨流浪的三个月里,两人住进了高尔基笔下那种《夜店》式的鸡毛小店里,房间是地下室,窗户比马路还低。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当时最底层的生活和最下层的人物:卖苦力的、无家可归的逃亡者、小偷、乞丐、下等妓女,等等。这些亲身经历为他后来写作储备了素材。令人不免惋惜的是,《掘金记》之后,毕奂午的创作几乎中断了。
1937年,巴金将毕奂午的一些新诗和小说编辑成《雨夕》,同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原书作者后记已辗转丢失,所以巴金亲自为书补写了后记。而诗人那时正身陷囹圄,巴金也不知老友在何处,只觉得有义务把这本存在他处的稿子付梓出版。《雨夕》初版本稀见,之后也没有单独重印。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将《掘金记》与《雨夕》合为一册,命名为《金雨集》重印了两百册。除了两本诗集,毕奂午再也没有出版任何作品。以毕老坎坷波折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位大师的交谊,从年轻时便显露的文学才华,他本可留下更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今老诗人离世已几十个年头了,武汉大学樱花掩映的小楼里,曾经陪伴凌叔华、苏雪林直至毕奂午的青灯早已熄灭,那些曾经来赏花的老友们都已离开人世,真似李辉所说的,“遥想当年,毕奂午先生清晨走出牛棚,牵着牛,穿过草丛,向远处走去。头上,漫天星辰……”
——兼及一类史料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