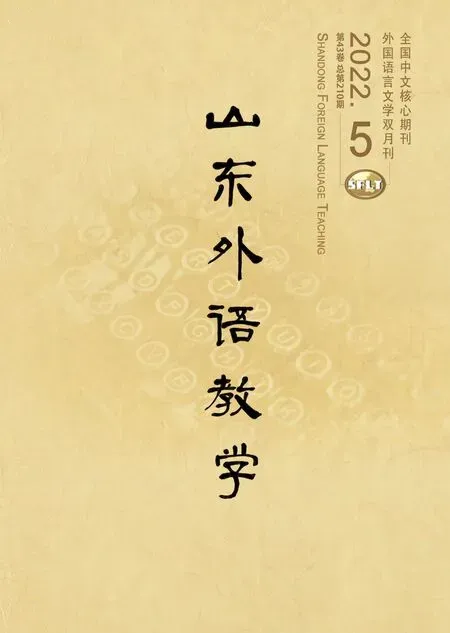《儿子与情人》中的工人阶级共同体
程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1620)
1.引言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曾在《自传简述》(“Autobiographical Sketch”)一文中推荐读者阅读小说《儿子与情人》(SonsandLovers, 1913),因为“第一部分都是自传”,“我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并在工人阶级中长大”(1968:300)。劳伦斯的创作与他的成长背景息息相关,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中,他像“社会主义者”(socialist)那样刻画了真实的工人阶级生活(Kazin, 1962:vii)①。
有评论家着眼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对作家的影响,将这部小说看作反映工人阶级普通家庭的一部“个人历史”(a case-history)(Holderness, 1982:135)。国内批评家或将主人公保罗的婚恋困境归因于资产阶级工业化困境下“畸形的母爱”(张礼龙,2000:47),或强调其中的“阶级认同危机”,认为莫瑞尔夫妇阶级观念(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冲突导致了保罗的困境,而劳伦斯对“性爱”的赞美正是他自己阶级认同危机的反映(庄陶,2001:146-148)。本文认为,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儿子与情人》中的作用固然值得探究,从文化层面对小说中工人阶级的考察更为重要。本文将在英国文化批评的视野下,运用“共同体”概念分析莫瑞尔家的工人阶级生活和莫瑞尔家庭悲剧的根源。本文认为,共同体“集体”“团结”和“具体”的观念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中心,小说对“超越”共同体的书写是双重的。莫瑞尔夫人和威廉试图跨越工人阶级生活,追求中产阶级物质文化,最终导致家庭成员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和差异,家庭分崩离析。与之相反,小儿子保罗对艺术的追求和探索是“超越”共同体狭隘之处的积极途径。他的艺术创作扎根工人阶级文化,保留了共同体核心的认同感,帮助他最终摆脱母亲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积极拥抱生活。
2. 劳伦斯和“工人阶级共同体”
在论述20世纪英国文化传统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小说家劳伦斯作为第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家,主要由于劳伦斯终其一生批评工业革命的实践和精神,积极寻找革新社会的途径,深入思考工业革命精神中机械化和物质主义思想状态。劳伦斯反复强调,工业制度导致物质主义的思想,并且是以破坏人类直觉及其对生命的感悟能力为代价。这些思考和威廉斯文化批评思想的核心不谋而合。在威廉斯看来,虽然劳伦斯对工业革命的批判和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认识并不系统,在他身上却存在一种“共同体的本能”(the instinct of community)(1961:219),这种精神正是威廉斯所倚重和赞许的。
那么何为“共同体”?事实上,共同体精神为我们了解劳伦斯思想提供有效的途径。要了解共同体,需得从威廉斯对“文化”概念本身颠覆性的论述开始。威廉斯的文化批评与阿诺德(Matthew Arnold)、利维斯(F. R. Leavis)等文化精英论者的最大差异便是对文化范围的扩展。阿诺德将文化定义为“这个世界被思考和被解说的最好的东西”(2006:5);利维斯注重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号召通过普及大学教育,提升英国民众的文化素养。而威廉斯则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物质、智性和精神各个层面的内容(Williams, 1961:16)。既然文化包含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工人阶级文化也成为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最重要领域。那么下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工人阶级文化相比中产阶级文化有何优越之处?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提供的答案是:“共同体”精神。②
在威廉斯看来,“共同体”精神正是工人阶级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尤其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关键。相比以“个人性”为特征的中产阶级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具有独特的“社会性”。③具体地说,工人阶级文化把个人价值的实现置放于共同体之中,将共同利益认同为个人利益。他们之间这种团结的情感来自于对环境和经验在现实生活中的认可。而处于共同体理想核心的“团结的观念”(the idea of solidarity)是潜在的“社会真正根基之所在”(Williams, 1961:318)。威廉斯还强调,为了在当今分工更为细致,利益更为多元的社会中实现共同文化的理想,工人阶级应当严格遵循民主的进程,并且构建一个物质上的共同体。共同体中具有责任感的个体应该积极参与集体活动,逐步深入地融入共同体中。这种集体民主的机制是工人阶级文化的精髓,而工会、互助运动或政党团体则为这种精神的体现。可见,“共同体”不仅描绘了精神上的蓝图,还应当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其中所包含的集体、团结的观念是工人阶级文化的精髓,也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正是因为“共同体”的观念,工人阶级文化才得以独享生命和活力。
劳伦斯出身并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童年的经历让他获得了对共同体“集体”、“团结”精神敏锐而直接的体验。工人阶级生活中的客观环境和经济条件拉近了家庭成员间的距离,使得工人阶级家庭成为权利责任共享的紧密整体。他在《儿子与情人》中刻画的工人阶级共同体便是这样一个热情真诚、真实可靠的团体。但和威廉斯不同,劳伦斯同时意识到工人阶级生活同时也有缺点,比如思想狭隘、父权中心。因此在小说中,他虽然以饱蘸感情的笔墨描述工人阶级共同体,但绝非毫无保留地赞扬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他曾从工人阶级的父亲和出身下层中产阶级却身为矿工妻子的母亲之间的矛盾着手,分析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文化的矛盾。事实上,他认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各自的优缺点:前者“知识丰富”但“思想狭隘、感情贫乏”;后者虽然智性阅历有限,还存在一些偏见,却胜在“感情深厚、强烈”,具有强烈的生命活力(Lawrence, 1968:595)。
3.“团结”的共同体集体
霍加特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之一《识字的用途》(TheUsesofLiteracy)中意味深长地指出:“某些小说使我们可以真正近距离地触摸到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如《儿子与情人》,而非某些更为流行或者更具无产阶级意识的作品。”(Hoggart, 1958:6)如果我们对照霍加特对早期矿区工人阶级共同体图景和《儿子与情人》中的工人生活方式,就可以对“共同体”的优越之处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霍加特看来,典型的工人阶级具有如下的特点:居住在边远地区;街区特点鲜明,房屋结构为“背靠背”或“巷靠背”式,通常为租赁(不拥有产权);生活来源为一周一付的“工资”(wage),而非固定的“薪水”(salary);工人多数只受过小学教育,不论是否具有特殊的技艺,工作都需要付出体力劳动;工人从重音、口音、说话习惯到地方方言有一套独特的语言方式。与之对比,小说开篇的贝斯特伍德矿区处于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农田和矿井、铁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莫瑞尔一家刚搬到“底层”矿工宿舍。房子是“背靠背”式:街区间的房子内部相对,中间是一条巷子,巷子两边是掩埋粪便的灰炉坑。
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写莫瑞尔一家的情况,和霍加特的介绍也是不谋而合。对霍加特而言,工人阶级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因为这种文化体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人们时刻可以直接感受、触摸到工人阶级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成员间彼此关怀和爱护,培养出一种“小集体的意识”(a sense of the small group);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十分亲密,人们的生活局限在几个熟悉的街区之间,共同参与复杂而活跃的集体生活(Hoggart, 1967:32)。家庭和街坊在工人阶级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放射出的直接而强烈的归属感。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就是这种集中体现于他们对“家庭”和“街坊”看法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具体有形的、属于特定地区的意识”(同上:38)。
在《儿子与情人》中,我们可以找到劳伦斯对共同体“团结”、“集体”核心观念的生动描述。巷子是社区生活的重要场所,“孩子们在这里玩耍,主妇们在这里聊天,男人们在这里吸烟”(Lawrence, 1958:2)。④矿工家庭之间互帮互助,莫瑞尔夫人和先生生病的场景就很有代表性。莫瑞尔一家搬到矿工宿舍不久,丈夫不在,莫瑞尔夫人便要生产。她敲击壁炉,邻居克尔克太太就立刻扔下手中的家务在产妇身边陪伴;另外一个主妇则帮忙请来接生婆。后来莫瑞尔先生得了头疼病,整个社区伸出援助之手。邻居们帮莫瑞尔夫人做家务、看小孩,送来慰问品;工人俱乐部抽出矿井利润中的福利金。就连心高气傲的莫瑞尔夫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邻居和工友的慷慨帮助,莫瑞尔一家不可能支撑下去。
在《儿子与情人》的工人阶级世界里,社区、邻里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精神潜移默化表现其中:社区生活丰富多彩、邻里间和气相处、工友间热情互助。在矿区,人们喜欢集体活动,莫瑞尔一家刚搬到矿工俱乐部,就迎来了“教区节或义卖集市”(the Wakes, or fair)。在这一年一度的欢乐场所里,不光有各种吃食还有游戏,欢乐温暖的节日气氛十分具有感染力。矿工俱乐部和其他酒馆是矿工们最常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聊天、喝酒、赌博,莫瑞尔先生还在矿工俱乐部主持舞蹈班。随着莫瑞尔夫妇矛盾逐渐升级,莫瑞尔先生在酒馆里重新找到归宿感。那里虽然空气污浊、人声喧闹,但气氛温暖友好。莫瑞尔夫人不太喜欢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但也加入了一个小型的“妇女俱乐部”(the Women’s Guild),每星期在固定时候集会,阅读报纸,讨论通过互助可以得到的实惠以及社会问题。通过协会,妇女们培养自己的是非标准,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地位。透过对这种荣辱与共的亲密、活跃、封闭的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刻画,劳伦斯展示了世俗化的工人阶级世界,人们彼此亲近友爱,体现着共同体集体、团结的精神。
众所周知,贝斯特伍德矿区的原型是劳伦斯的家乡诺丁汉。在《儿子与情人》出版十六年后,流放在外的劳伦斯发表《诺丁汉和煤矿乡》(“Nottingham and the Mining Countryside”, 1929)。在这篇散文中,他不仅以社会学调查报告的客观态度追溯了19世纪初诺丁汉郊区的伊斯特伍德镇(Eastwood)的起源、1820年煤矿工业的初兴和发展,还以更为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在工业革命影响下矿区生活的变迁。生活在农业化和工业化时代交界地段的人们,几乎全靠本能行事。矿工在“分包合同制”(the butty system)下劳动,彼此间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共同体:“他们常常赤身裸体在地下劳作,相互之间有一种奇特的亲近感。同时,因为矿下十分黑暗,离地面也很遥远,他们还必须面对时刻可能出现的危险,矿工之间结成了一种肉体的、本能的、直觉的强烈而真实的联系”(Lawrence, 1936: 135-136)。这样的共同体让人们可以带着尊严和骄傲团结起来。但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个人主义思想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二十世纪初,随着属于农业社会的原始采矿方式被现代工业的机械作业所取代,更大的矿井取代单个独立的小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老式小排的矿工公寓被推倒,新建了两大排“新楼”;商铺、酒馆和各式各样的教堂出现。共同体的本能被打破了,留下的只有对物的欲望。城市只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聚集体,而在真正的城市中,市民是和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母亲本应是家庭的中心,用霍加特的话说“实际上家庭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她,而非父亲,保持着家的整体性”(Hoggart, 1967:22),但现在矿工妻子身上体现着赤裸裸的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但劳伦斯批评矛头的指向并非是女性,而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工业思想:“工业革命的真正问题在于其是建立在一种促使人们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对物质占有的竞争思维之上”(Lawrence, 1936:136)。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劳伦斯对英国社会的批评和自我流放并非源于他对共同体精神的疏离,他所拒绝的正是导致共同体精神分崩离析的工业社会。
4.共同体的分裂和超越
正如劳伦斯在另一篇《自传简述》(“Autobiographical Sketch”)中所说,人类交流的障碍并非因为“中产阶级”本身,而是“中产阶级物”(middle-class thing),也就是“中产阶级文化”(Lawrence, 1968:595)。小说把莫瑞尔一家放置在工人阶级共同体中,刻画在中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下家庭成员所经历的变迁,更好地体现了共同体精神在工人阶级文化中的作用。家庭是共同体的核心部分,是工人阶级文化集体性最突出的体现。莫瑞尔一家居住在底层矿工宿舍,是这个工人阶级社区的一份子。而矿工妻子、主妇莫瑞尔夫人始终向往中产阶级社会。大儿子威廉在母亲的影响下,试图超越工人阶级跻身中产阶级行列,却是以生命作为代价。共同体面临分裂的危险。劳伦斯告诉读者,正是莫瑞尔家庭成员对共同体意识认识上的差异导致了其家庭悲剧。
在莫瑞尔先生身上,劳伦斯刻画了典型的工人形象。在肯定工人阶级的感性、自然、朴实的同时,也展示了其缺陷。莫瑞尔出身工人阶级(祖父是法国难民,祖母是酒吧女招待),魁梧健壮,快活健谈;他本性是“纯感官”的,喜欢跳舞、喝酒,热爱手工活,全靠本能行事(14)。莫瑞尔一家生活贫穷,莫瑞尔夫人常常为生计发愁。可是在这个工人阶级家庭中,中产阶级的语言(而非工人阶级的方言)“解读和证实着”孩子们的经历(Kiely, 1990:94)。与此同时,莫瑞尔脾气暴躁,思想比较狭隘,还存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经济上的困难和生活理想上的差异,让莫瑞尔一家矛盾重重。
事实上,莫瑞尔夫人与丈夫的矛盾是后者堕落的重要原因。丈夫男子气十足,驽钝粗陋,而妻子娇弱、品味高雅;丈夫举止粗鲁喜欢饮酒作乐,妻子注重礼仪,杜绝一切感官享受;对孩子的过失,丈夫不管对错一律使用武力,妻子却倾向说服教育;丈夫希望孩子以后成为矿工,妻子决不允许孩子靠劳力吃饭;丈夫需要在家庭树立绝对的权威,但妻子不满足于“侍候”男人。劳伦斯通过妻子和丈夫的对立告诉读者,中产阶级重视精神性、个人性的文化破坏了“共同体”团结、和谐的精神。丈夫在家里被孤立,得不到属于“集体、社会的”归宿感。家人的疏远让他不得不到外面寻找集体生活,从此他酗酒、自暴自弃,逐渐放弃自己。莫瑞尔夫人生病之后他惊慌失措,“看起来就像一个遗弃的人,没人要他一样”(375)。莫瑞尔生在工人阶级中,无法超越工人阶级共同体。
莫瑞尔夫人出身于一个名声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她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纯正英语,颇有上流妇女的风度。她笃信宗教,性情清高,生活严谨;求知欲强,喜欢智性思维。从一开始,莫瑞尔夫人就与矿区共同体格格不入。她不愿主动参与集体活动去接受工人阶级文化,其他妇女也因为其淑女风度对她嗤之以鼻。她和莫瑞尔相识在舞会上,却对莫瑞尔主持矿工俱乐部舞蹈班一事,感到“羞辱和痛心”。她不喜欢教区节的喧闹,禁止孩子们喝酒,也看不起工人阶级妇女的手工劳动(28-29)。在工人阶级的共同体中,她感受到的是孤立、寂寞和疏远。如《识字的用途》中构想的那样,作为工人阶级的妻子和母亲,莫瑞尔夫人理应是家庭的中心,为丈夫和孩子营造一个友爱、温暖、团结的家,但她自己却找不到归宿感:“我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我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甚至我将要生下的这个孩子!我好像是个局外人”(6)。劳伦斯告诉读者,莫瑞尔夫人在思想上缺乏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实际上又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她的人生悲剧是她自己造成的。
莫瑞尔夫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步入中产阶级,实现自己没有完成的心愿。她害怕威廉走上父亲的那条路,成为一个出卖劳力、地位低下、沉溺享乐的普通工人,因而把中产阶级的理想赋予他身上。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威廉变得野心勃勃。他白天在“合作社”办公室做文员,晚上到夜校学速记,后来又在夜校教书,连交往的对象也是小镇上的中产阶级。后来威廉从诺丁汉去往伦敦谋到一个拿年薪的职位,决心成为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但莫瑞尔夫人看得出他的困惑:“生活中的变化让他失去了重心。他并没有站稳脚跟,在新生活汹涌的水流中被冲击得头晕目眩”(90)。
威廉的婚恋选择更明确地说明超越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困难所在。他追求“吉普赛”女郎露伊莎,图的是其淑女风度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当路易莎正式拜访莫瑞尔一家时,他又为她高人一等的小姐派头感到羞愧和愤怒。他意识到了她的浅薄和虚荣,却没有勇气否定自己一直追求的中产阶级生活。正如侯德尼斯(Graham Holderness)所说:“一旦工人阶级共同体被抛弃,剩下的什么都没有;在现实中,没有地方可以去。作为一个个体进入中产阶级永远不是贝斯特伍德(或莫瑞尔一家)困境的解决途径”(1982:147)。在工人阶级共同体中成长起来的威廉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根深蒂固,和露伊莎有本质的区别。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和我们不同。那些人,她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些人,他们有与我们不同的生活准则”(118)。他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共同体,但却无法真正接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两个世界之间找不到归宿感,只有孤独地死去。因此,劳伦斯在批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工人阶级文化共同体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是给予充分肯定的。莫瑞尔夫人和威廉试图在阶级框架内超越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做法必然以失败告终。
如何“超越”共同体的狭隘之处获得救赎?通过小说中二儿子保罗的艺术追求,劳伦斯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同威廉一样,保罗上过寄宿学校,如母亲所愿到办公室做文员,但他并不像威廉那样一心一意向往中产阶级的生活。他虽然跟牧师希顿学习法语、德语、数学和绘画,喜欢旅行、看书、绘画;后来还利用工余时间去艺术学校上课,绘画获得了“诺丁汉宫冬季展览”一等奖。但保罗自己并不真正想要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的雄心壮志,只要这个世界还在转,就是在家附近的某个地方工作,一周安安静静地挣30或者35先令,然后,等他父亲去世后,与母亲同住在一间乡村小屋里,画画,如果高兴就出去散步,从此幸福地生活……他想着或许他还可以成为一名画家,一个真正的画家”(89)。保罗爱好艺术,他的构想是理想化、浪漫派的。但保罗将艺术追求扎根于真实、具体而又丰富的工人阶级文化,同时寻求建立一个超越阶级局限的“乌托邦”。他的理想居所是乡村茅屋,他对工人阶级有天生的亲近感:“我最喜欢我们普通人。我属于普通人”(256)。他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在阶级,而在他们本身”,“从中产阶级那里,人只能得到观念,而从普通人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和温暖”(298)。
实际上,劳伦斯当时的理想社会也带有几分乌托邦色彩。1915年他在写给威利·霍普金斯(Willie Hopkins)的信中提到,“我想召集大概二十个人,然后离开这个满是战争的肮脏的世界,寻找一个小小的聚居地。在那里,不使用金钱,实行某种共产主义,只要满足生活的必需品,过一种真正正派、高尚的生活”(Lawrence, 2002:259)。艺术追求是保罗保留共同体的归宿感、又超越其狭隘之处的途径,也是他摒弃母亲的中产阶级文化影响、勇敢拥抱生活的动力。与保罗一样,劳伦斯为了艺术追求离开了家乡,但始终感到自己的根与家乡的普通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唯一能够强烈打动我的人,让我感到我的命运在冥冥之中与之相连。正是他们,在某些特有的地方,是我的‘家’。我离开了他们,但是我始终对他们怀有强烈的思念”(Lawrence, 1968:264)。简言之,劳伦斯探询的不仅是个人从社会体系中得到解救的途径,他的艺术创作也并非威廉斯所说的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和“逃避”。正是在工人阶级文化中,劳伦斯汲取了创作的素材和激情,他对活跃、团结、丰富的工人阶级共同体生活的描写与构想赋予其作品永恒的魅力。
注释:
① 批评家阿尔佛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在1962年版《儿子与情人》的序言中指出,尽管劳伦斯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并曾在一家外科器械工厂工作,但并不属于工人阶级。他与工人阶级有天生的联系,但缺乏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本文赞同卡津前半部分的结论,但倾向认为劳伦斯在看到工人阶级缺点的同时,对工人阶级存在认同感。See Kazin, 1962, p.vii.
② 在《关键词:社会与文化的词汇》中,威廉斯列举了“共同体”在英语中的五种含义。他对“共同体”的考察是从其与“社会”(society)的区分开始的。他指出社会是“更直接的、更完整的、更具有功能性的国家关系或是具有现代意涵的社群关系”,而共同体则是“更具形式的、更抽象的、更功能性的国家关系或是具有现代意涵的社会关系”。See Williams, 1976, pp.79-80, 203-206.
③ 对于“共同体”的内涵,威廉斯认为存在两种不同解释:中产阶级将其解读为“服务的观念”(the idea of service);与之相对立的是工人阶级“团结的观念”(the idea of solidarity)。See Williams, 1961, p.313.
④ 引自D. H. Lawrence,SonsandLover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8. 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