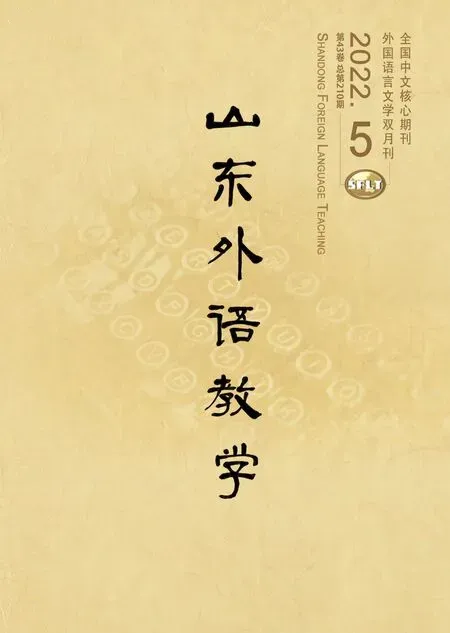阐释与脱节博弈中的古诗“名词语”英译探赜
钱屏匀
(上海电力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6)
1.“名词语”的名与实
“名词语”,顾名思义,是指完全由名词或名词词组构成的诗句。这种句子由南北朝时期的谢朓和庾信首创,在后世的近体诗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鹏飞, 2010:72)。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对汉语句法做出如下评述:“在散文里,宁可没有主语,不能没有谓语;诗句里却常常没有谓语,只一个名词仂语①便当做一句的用途”(王力, 2005:273)。据此可知,汉语诗中名词词组单独作一句用的现象并不罕见。
“名词语”可根据其包含的意象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类。有的“名词语”中两个或多个意象并置,例如“梦泽三秋日,苍梧一片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等。有的“名词语”中意向相互叠加构成“定语+中心词”结构,例如“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等。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将影响英译策略的选择。
2.“名词语”的句法功能和诗学功能
从上述定义、分类、举例中可以看到,“名词语”是一种形式不完整但语意完备的诗歌破格现象,作为一个隐形完整句中的核心成分,具备贯通整个文意的强大功能。
从句法形式而言,“名词语”浓缩凝练,其释义要求增补句子成分。由于读者的个性化理解,增补的成分可能显示出差异,增补成分之间的不同排列组合也可能使诗句呈现出意义的错落。由此可见,“名词语”句法功能上的不确定性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召唤读者参与,激发读者对诗意的想象和补充。
从诗学功能来看,“名词语”由于不包含除名词和名词词组以外的成分,首先可使字数有限的诗句容纳更多的意象,其次也令各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变得模棱含糊,从而拓展了诗意空间。以李白《送友人》一诗的颈联“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为例,出句中“浮云”与“游子意”、对句中“落日”与“故人情”的无缝衔接模糊了意象间的逻辑关系。若读者在每句的前后两个意象之间建立比喻关系,则整联可被理解为“浮云如游子意,落日似故人情”;若读者将每个意象视为独立的成分,则整联可被理解为“浮云飘荡、游子神伤,落日残照、故人惜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意象的并置或叠加令诗句凝缩而产生视觉和弦,留下了“不定点”(indeterminacy)和“空白”(gap)(Iser, 1978: 72),或如中国水墨画中的留白手法一般使读者对诗意产生含蓄的想象,或如电影中的剪辑镜头制造蒙太奇效应。由此可见,“名词语”意象密集、语意朦胧的特点,不但没有减损诗句的整体语意,而且“激发了文本本身隐藏的、需要读者深度参与和解读的审美效果”②(同上)。
3.“名词语”常见翻译路径
通过对句法常规的适度背离,“名词语”营造出汉语古诗词在语言形式上简洁凝练、在诗学审美上模棱多义的特征,然而这些特征却为汉诗英译带来巨大障碍。英语是形合语言,通常需要在句子间、短语间甚至词语间使用连词、介词表达逻辑关系,语意的确定更少不了谓语动词。在翻译“名词语”时,部分译者选择顺应英语习惯,采用阐释策略对汉语诗句进行句法上的补充和语意上的限定;部分译者则倾向于保留汉语结构,采用脱节策略创造不连贯的译文。下文将分别讨论两种翻译策略的得失。
3.1 阐释翻译
阐释翻译的思想在现当代译论中十分常见,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翻译同时也都是解释,“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译者对所给定的词语进行的一个完整的解释过程”(Gadamer, 1975: 346)。纽马克也指出,“当文本语意模糊,且在时间、空间和认知上相隔遥远时,其中的语言便超越了比喻而成为象征,这时译者就应进行充分阐释,除非打算将问题留给读者”(Newmark, 2001: 142)。然而,诗歌翻译在策略的考量上较之其它文学翻译更为复杂。在“名词语”的英译中,如果译者为使译文更加连贯达意而选择增加句法成分和个人阐释,则不仅诗句会失去简约浓缩的语言形式,诗句中意象叠加或并置赋予诗作的多义性和模糊美也将不复存在。
试以杜甫《旅夜书怀》中的首联做一分析。该联中出句“细草微风岸”和对句“危樯独夜舟”均由多个意象组合而成,“草”“风”“岸”和“樯”“夜”“舟”的空间和主次关系呈现出不确定性。如果诗句可以构成画面,那么在这幅画面中各个意象的位置、显隐、色度都是模棱的,读者在想象时拥有极大的自由度。例如,若突出静态描写,则可将诗句理解为“细草摇曳(之)微风岸,桅杆矗立(之)独夜舟”,诗中情绪淡然平和;若侧重动态描写,则可将诗句理解为“细草摇曳(于)微风岸,桅杆独矗立(于)夜舟”,句中蕴涵情绪的起伏;若立足动静结合的描写,则可将诗句理解为“岸边,微风轻拂、细草摇曳;夜中,孤舟独行、桅杆矗立”。原诗允许几种理解并存,但英语重形合、重逻辑的特点使得译者在进行阐释时必须添加原文没有的句法成分,这样一来,译文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译者发挥其主体性的某一种解释,文本空白带来的想象空间骤缩。这种变化在白之(Cyril Birch)、王红公(Kenneth Rexroth)、许渊冲及许明的译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白译:Reeds by the bank bending, stirred by the breeze, / High-masted boat advancing alone in the night...(Birch, 1965: 238)
回译:微风轻拂,岸边芦苇低垂 / 高桅小舟独行夜中……
王译:A light breeze rustles the reeds. / Along the river banks. / The Mast of my lonely boat soars. / Into the night. (Rexroth, 1965: 33)
回译:轻风摩挲芦苇 / 沿岸 / 桅樯高耸孤舟 / 入夜
许译:Riverside grass caressed by wind so light, / A lonely mast seems to pierce lonely night. (许渊冲、许明, 2009: 251)
回译:轻风拂岸草 / 孤舟穿独夜
形式上,三段译文选词精到,但都增加了不少逻辑标记(如“by”“alone”“in”“into”)以及阐释性的动词成分(如“bend”“stir”“advance”“rustle”“soar”“caress”“pierce”)。语意上,译文用客观描述代替了原文意象并置带来的多重心理暗示,分别描绘了三幅清晰而各异的画面,诗句的朦胧感消失了。
“名词语”让诗歌以形象化的方式自我表现,其重点不在于逻辑陈述,明确的逻辑和清晰的语意或许正是原诗力避之处。从这个角度来看,阐释翻译有违原诗的句法功能和诗学审美,因添加过多逻辑标记减缓了原诗简洁明快的节奏,弱化了原诗的音韵特质,增加了叙事感。无怪乎闻一多先生认为“浑然天成的名句……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禁不起翻译的”(中国翻译编辑部, 1986:40),并在谈及小畑薰良将李白诗中“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译为“The smoke from the cottages curls / Up around the citron trees, / And the hues of late autumn are / On the green paulownias”时感叹中文的“浑金璞玉”移到英文中去,竟变得“这样的浅薄,这样的庸琐”(同上)。
不难看出,“名词语”营造的朦胧境界与功能词语密布的英语句法之间确实存在天然屏障。若处理不当,英语句法的约束对翻译“名词语”必将是一种致命伤。毕竟,文化典籍的翻译不仅“要忠实于传递原文的文本信息,还要尽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诗学特征和美学传统”(朱振武, 2016: 83)。尽管阐释翻译有利于译者在遣词造句上发挥创造性、表现诗意之美,但在翻译“名词语”这种具有特殊语言形态和诗学功能的诗句时如完全采用英语句法,不仅无助于异域读者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本来面貌,还可能阻碍汉英诗歌的深层次交流与相互吸收,因此不可全盘采纳。
3.2 脱节翻译
脱节翻译的概念由国内学者蒋骁华提出。蒋骁华(2003: 75)认为脱节翻译可以“实现原文的多值性”,这种见解主要源于“名词语”对英美意象派诗歌创作的影响。意象派诗人从“名词语”罗列意象的写作方法中获取灵感,以中国古诗的句法形式入诗,不仅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更推动了汉语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其中美国意象派代表性诗人庞德(Ezra Pound)采用意象并置(juxtaposition)和意向叠加(superposition)的方法翻译中国古诗、创作英语诗歌,而不做任何解释或评论,让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去感知、探讨意象之间的关系。例如,周红民认为庞德将“荒城空大漠”译为“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Pound, 1915:16)具有开创性意义,因为“这种只呈露意象,不做定性和定量描述的策略,立足于汉诗的本质特征,在英语文化中违背了语言逻辑,给人突兀、陌生的感觉,但是它符合翻译本质,较为本真地传递了古诗歌的形态,充分展示了汉诗空灵简洁、含蓄凝练、多重暗示之美”(周红民, 2012:76)。又如,庞德《诗章》第49章的开头“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Pound, 1998:244)就是模仿中国古诗“名词语”之避用述词、连接词的写法,试图让诗句中的意象感染读者而非以作者的评述影响读者。
采用脱节策略翻译“名词语”的译者不乏他人。例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将贾至《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一》诗中的“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一句译成“Bright moonlight and autumn’s wind, / Waters of lake Tung-t’ing, / A lone goose, the falling leaves, / A single tiny boat”(Owen, 1981:251),没有添加任何述词或连接词,基本保留了原文意象并置的形式。应该看到,脱节翻译在此处的运用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原诗“名词语”中的各意象本就属于并列关系,以并置的方式还原,能够最大程度地制造空白和意象间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保留“名词语”鲜明的视觉效果和模糊多义的审美特征。
诚然,隐去的成分一经补足,诗就散文化了;与其解释词与词、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倒不如保持原诗的形式,留待读者自己想象。这样看来,脱节翻译法似乎是“名词语”翻译的不二法门。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脱节翻译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3.2.1 脱节翻译与“名词语”的语意差异
意象派诗人庞德、弗林特(Frank Stuart Flint)和休尔姆(Thomas Ernest Hulme)在1912年发表的意象主义原则中曾声明要“删除一切无助于呈现的词语”(转引自常耀信, 1994:221)。该原则的本意在于提倡诗的简洁精炼,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导致了意象派诗歌纯粹为呈现意象而呈现意象、无视英文句法习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名词语”的英译中一旦走向极端,会瓦解译文的逻辑性,令诗意晦涩难解甚至可释意性趋近于零。这样一来,汉诗原来的含蓄多义不仅无法得到转存,诗句的意义反而会导向不可知。这种现象多出现于时空和思维跳跃巨大的“名词语”诗句中。
试以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一诗的颈联为例进行分析。杜诗向以时空和感情上的极大跳跃性而著称,前人对杜诗有“气俊思活”的评价(萧涤非, 2004:1087)。在“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一联中,出句摹写雨中人家,对句描述晴空晚照,两句之间存在时间范畴的跳跃,而且单句中意象间的关系也很不明确。原诗中该句主要是通过不同时空景物的描写,抒发作者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古今之慨。若采用脱节策略依样画葫芦地罗列意象,恐怕只能使英语读者莫名其所以然。如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将这一联译作“Deep autumn, screens, a thousand houses, rain; / Setting sun, towers and terraces, a single flute, wind.”(Frankel, 1976: 149),译句意象割裂,诗意支离破碎,趋向无解。
这种现象主要是由“名词语”中意象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在前例“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中,虽然各种意象在方位上呈现出不确定性,但都存在于同一时空中且相互之间有所关联,足可构成一幅完整统一的画面,读者可借助想象体悟诗句的整体意境。因此,运用脱节翻译不仅不影响画面的关联性,还能保留空白和引发联想。但是,此法并不适用于如杜诗这样含有隐性不确定性的诗句。因为在这种“名词语”中,各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松散,意义关联往往在心理、逻辑、时空或语意上经过了几重跳跃。汉语的意合特征允许诗人打破时空局限,在广阔的背景上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古诗中的对偶句法恰能将处于不同时空的意象连接起来。对偶句“让人看了这一面习惯地再去看另一面……意象之间虽有跳跃,而读者心理上并不感到是跳跃”(袁行霈, 2002:61)。尽管英语中也有所谓的“对句”(couplet),但那只是长度相当、韵脚相同的诗行,难以构成语意的互文。因此,翻译“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寒食看花眼,春风落日心”“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类意象松散的“名词语”时,译者如果使用脱节法直接呈现意象,极易导致诗意无解。
相对而言,适合以脱节法翻译的“名词语”,其各意象之间一般存在并列、修饰、判断或陈述等逻辑关系。当各意象处于同一时空中时,意象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位置、顺序、大小、显隐等物理层面,足以让读者产生统一完整的画面感。即便有多种排列组合,意境也大都统一,使读者与诗意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样的诗句有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昨夜星辰昨夜风”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绿杨芳草长亭路”等。
3.2.2 脱节翻译与“名词语”的诗学差异
笔者认为,从诗学审美而言,英美意象派诗歌虽借鉴于中国古诗,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意象派诗人倡言的“意象”是鲜明具体、能够直接感知的形象,这种意象局限于知觉经验,属于浅层心理学范畴。而中国古诗中以“名词语”方式呈现的意象组合是作者主观情感与外在景物结合的产物,这种“景中情”即王国维所称之“无我之境”(王国维, 2009:4),它不以单纯意象呈现为终点,而以整体意境营造为旨归。这种诗学上的审美意识来源于老庄之“道”,折射的是个人对宇宙、对人生本原的深层次生命体验,因此中国古诗中意象的出现都带有浓厚的情绪,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同上:80)。英美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诗的借鉴放大了意象的表层视觉感受,却没有深入挖掘中国古诗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基础,他们孜孜以求的意象缺少了朱光潜先生所强调的诗歌之情趣,这正是脱节翻译与“名词语”最大的分别。如果不了解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化背景,脱节这种异化翻译策略所保存下来的意象“未必能取得很好的诗学效果”(蒋骁华, 2003:116),普通的西方读者会觉得虽新奇却难以理解,很难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因此,不加分辨地使用脱节翻译易导致译者过度依赖外在表象而忽视诗歌的情感肌理,缺乏对原作的深入思考和探究,甚而走入机械模仿的误区。正如翁显良先生在《译诗管见》中所说:“倘若采取庞德译《击壤歌》③的办法,一天译十首,一年三千六百五,岂不快哉”(翁显良, 1981:2)。
由此可见,即便脱节翻译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保留“名词语”的模棱多义,译诗依然很难臻至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毕竟前者只是单纯呈现意象,而后者呈现的意象群却共同营造出一种意境。译诗或可实现原诗的蒙太奇效应,却很难再现原作意象互通的诗意境界。
4.阐释与脱节的博弈
对于存在破格现象的“名词语”而言,句法上的剑走偏锋本身即是为了实现独特的形式功能和诗学价值,因此,翻译应在不以消解诗意为代价的前提下适当保留句法上的特异性。事实上,如以阐释法翻译“名词语”,诗句会变为透明,以脱节法翻译“名词语”,有时又会令诗句完全不透明,而“名词语”给人的感受是半透明。这就要求译者在这两种策略中筹谋平衡,既没有必要译得纤毫毕现,亦不可令逻辑割裂,而应各取所长。诚如柳无忌与罗郁正在《葵晔集》前言中所说,“汉语言的非曲折性和简练紧凑在20年代令许多美国意象诗人爱不释手,由此衍生出一种舍弃介词、冠词的接近于洋泾浜英语的翻译风格”,但他们认为“对源语结构的保留应当置于目标语言的掌控中,不能以牺牲理解为代价”(Liu & Lo, 1975:2)。两位先生以李商隐《小桃园》中的“坐莺当酒重”一句为例,指出如果以极端的方式来译,就可能出现如“Sit oriole like wine-heavy”这样令人如堕五里雾中的译文。因而,此处适当地“补充一个动词或隐含的主语,不见得就会令诗意无存”(同上)。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略的取向:“名词语”的翻译是介于阐释和脱节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一方面,应采取脱节的思路,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尽量避用英语功能词汇,在句法上采取适度的陌生化,在语意上保持一定的模棱性;另一方面,由于英语的隐喻性和暗示性均不及汉语,翻译中应借鉴阐释翻译的长处,在不乖违原诗深层含义的基础上,将“名词语”不言情而情意自现的特点适当显化。对于原诗含蓄的风格,许渊冲先生的看法是,若用含蓄的译法能引起英美读者的共鸣,那自然应该保存原诗含蓄的风格;如果不能,那就只好舍风格而取内容了(许渊冲, 2005:15)。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目标语读者获取与源语读者相近的心理感受和审美体验。
试以司空曙《喜见外弟卢纶见宿》一诗的颔联为例进行分析。“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前后对偶句中“黄叶树”与“白头人”两个意象存在类比关系,而“雨中”和“灯下”两处景语有起兴之效,烘托了整个诗行的悲凉气氛。该联简洁自然、比兴兼顾,直击人心且极富艺术感染力,读之思绪悠悠,慨叹黄叶飘零,韶华自流。译诗既要再现原诗的意象直陈之妙,又要微露原诗的言外之意,势必需运筹于阐释和脱节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试看曾炳衡、刘师舜、徐忠杰的译文:
曾译:Under the rain there were yellow-leaved trees; / In the lamplight were seated grey-haired men. (吴钧陶, 1997: 447)
刘译:In the rain stand trees with yellow foliage, / Under the lamp a man grown hoar with age. (Liu, 1967: 58)
徐译:With rain, leaves yellow, falling before their time. / By lamplight, my hair is white—long past my prime. (徐忠杰, 1990: 196)
曾译是典型的阐释译法,枝节繁多芜蔓,句法上失去了“名词语”应有的灵动简洁,审美上给人的感受更流于单纯景物描述,译文本身很难让人体会到原诗苍凉的气氛。刘译吸收了阐释翻译对意境营造的长处,选词精雅,更以“foliage”和“age”之对应含蓄地暗示出“黄叶树”与“白头人”意象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名词语”余意不尽的审美效果,但功能词汇的使用过于频密,诗句的散文化痕迹比较明显。相对而言,徐译处理得最为均衡,不仅有意识地将前后意象以逗号分隔开,干预诗歌的审美构建,而且省略了完整句所需的若干衔接词汇,且丝毫不损理解,同时以“time”与“prime”之情语诠释出原诗年与时驰而功业无着的精神主旨,使原诗的句法功能和诗学意义都在译文中得到了有力体现。
依笔者拙见,若能适当删去徐译中只起功能作用的人称代词“their”和“my”以及系动词“is”,得译文为“With rain, leaves yellow, falling before time. / By lamplight, my hair white—long past prime”,则原诗“名词语”之妙会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转存。依照这样的博弈原则,笔者试将前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一句翻译为:“Deep autumn, rains croon—curtains drooped—hundreds of houses cold. / In setting sun, towers steeped, wind—floating—a flute song, as of old”。
5.结语
“名词语”的翻译从深层次反映出中国古典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保留“有我之境”的问题。作为新时代的外语人,译者首先应清楚地认识到“在加强双语文学文化学习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土文化”(高静, 2018:3),时刻秉持民族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特质。其次应该在言与不言之间、畅言与寡言之间谋求一个平衡点,以尽可能周全“名词语”在句法和诗学上的双重功能。一般说来,“名词语”中各意象关系在时空、逻辑、心理上越是疏离,平衡点离阐释翻译越近,离脱节翻译越远;反之,各意象之间关系越是紧密,则离脱节翻译越近,离阐释翻译越远。但无论如何,“名词语”的翻译应以不散文化和不造成理解障碍为前提。同时,译者还应考虑“名词语”诗句景语含情语的重要特征,对原诗营造的情感、氛围、意境等象外之致与言外之意悉心揣摩,翻译时略微地化隐为显,适当深化原诗的精神主旨,方能激发译语读者的心灵共振,助力中国古典诗词在异国他乡觅得更多知音。
注释:
① 仂语即词组。
② 文章中对英文文献的直接引用均为笔者所译。
③ 击壤歌原文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庞德译文为“Sun up, work / sun down, rest / dig well, drink of the water / dig field, eat of the grain / imperial power, and to us what it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