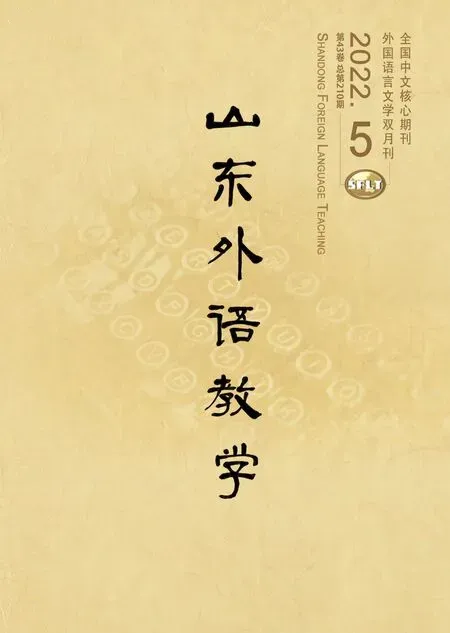挪用“弹震症”:《士兵的回归》中的失忆、怀旧与共同体难题
程汇涓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1600)
1.引言
弹震症(shell shock)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对新型机械化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描述。在有关一战的文学表现中,弹震症占据了极为显著的位置,小说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关于弹震症及其后果的文学呈现”(Dodman,2015:12)。历史学家特蕾西·洛克伦(Tracey Loughran)认为,“自一战停战以来,弹震症就被包含进战争想象”,从彼时到当代,有关一战的小说都表现出“对创伤的彻底的现代迷恋”(2012:97)。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 1892-1983)在一战尾声时出版的小说《士兵的回归》(TheReturnoftheSoldier, 1918)常被视为最早将罹患弹震症的士兵形象引入虚构创作的尝试之一(Baldick,2004:338;O’Malley,2015:92)。受到有关弹震症经典话语的影响,以及战后审美意识形态的浸染,当代批评家倾向于将这本小说中的“弹震症”与战争创伤表征关联起来(Kavka,1998;Bonikowski,2005;Pinkerton,2008;Pividori,2010;Pulsifer,2013),小说男主人公克里斯仿佛与伍尔夫笔下标志性的弹震症受害者“赛普蒂默斯”一样,受困于机械化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而细读之下,《士兵的回归》对克里斯罹患弹震症后状态的表现,存在违背常理之处。小说的核心事件是克里斯因弹震症失去了十五年的记忆,他忘记已婚的事实,也不记得早夭的儿子,只牵挂十五年前的旧情人玛格丽特,并强烈地渴望与后者重修旧好。尽管失忆在有关弹震症症状最早的医学记录里就占据一席之地(Myers,1915:316;Rivers,1918:173),但它无疑是与失眠、焦虑、听嗅味视觉受损等情况并发的(Smith,1917:4-6)。相较之下,克里斯的弹震症有两点违背医学经验:一是其症状仅限于失忆,其余可能造成负面情绪的并发症均不存在,失忆反倒使他在情绪上走到医学病例的反面,表现出积极、幸福的状态;二是他记忆缺失的时段(十五年)过于特殊,事实上,由弹震症诱发的逆行性失忆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与意识丧失并发的完全失忆,另一种是失去受伤前后不久形成的记忆(Mott,1919:84-91)。也就是说,由弹震症诱发的失忆具有明显的创伤属性和事件关联性。
那么,为何《士兵的回归》中的弹震症表现得如此远离真实?韦斯特对它做的去现实化的处理蕴含了怎样的批评眼光?本文认为,若仅在战争创伤表征的逻辑上理解这种错位,就可能忽略小说对特定时代情绪的回应,也会错过深入探究失忆所诱发的田园怀旧以及共同体问题。
2.被挪用的“弹震症”与嫁接的失忆
《士兵的回归》是最早将弹震症作为主要情节的小说之一,它与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版且在接受史中被经典化的文本不同。它诞生于弹震症医学观念和大众观念形成的早期,生动地反映出共识达成之前流动不居的形式自由。在学术研究、评论文章和文学教育的共同作用下,对英语国家当下的阅读群体来说,表现弹震症的经典文本是被不断筛选出来的,它们逐渐在审美意识形态上走向统一,继而影响后继的创作。凯特·麦克唐纳德(Kate Macdonald)曾就1914至1918年战争持续期间英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和杂志刊登的短篇小说,做了一整套基于文本库的研究(2017:43-44),并雄辩地指出,当代读者对一战经验,特别是“弹震症”作为其核心要素的理解,“更多来自战后文学”(2017:38)。从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 1925)到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 1873-1939)的《队列之末》四部曲(Parade’sEnd, 1924-1928),再到帕特·巴克(Pat Barker, 1943-)的《重生》(Regeneration, 1991-1995)三部曲,有关弹震症的文学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也自发地与看上去不够真实或者说不够“痛苦”的写法拉开距离。
《士兵的回归》创作于书写范式达成之前。在这个阶段,从作者到读者,远离前线和战地医院的公众对弹震症只有模糊的认识,由此也给弹震症在文本中的挪用和拼接创造了条件。弹震症的源头叙事通常被追溯至英国皇家陆军医生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 1873-1946)于1915年2月13日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文章《一篇关于弹震症研究的文稿》(“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hell Shock”),但迈尔斯并不是第一个使用“shell shock”来描绘这类症状的医生,吉尔伯特·巴林(Gilbert Barling, 1855-1940)比他早一个月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MedicalJournal)上已使用该说法。军队医生在学术刊物上专文探讨这一病理现象,反映出患病士兵的表现和人数对军方来说已不能忽视。然而,前方的医学观察传播至后方公众,不仅会有必然的时间差,也存在信息的过滤和择选。从“英国报纸档案库”(The British Newspaper Archive)的检索结果来看,有关弹震症的报道在1916年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它主要出现在伤亡将士名册的简短说明中,或是以乐观主义精神报道的个别士兵康复案例里。事实上,身处大后方的公众即便能够从报纸杂志中窥见一鳞半爪,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其认识往往停留在纸面上,因为“重症患者通常被直接送进战地医院,公众在后方的正常生活里遇见患者的机会有限”(Macdonald,2017:48)。在《士兵的回归》中,克里斯·鲍德里的旧情人玛格丽特前往他的宅邸,告知其妻克里斯的状况,但她琢磨半晌却不知如何描述,“我不知该怎么说……他不能严格说是受伤了……炮弹爆炸了”,她的说法仿佛是在“提供一个她长期以来苦苦思索却无法理解的术语”,最终她口中蹦出了一个词“弹震症”,但克里斯的妻子和堂妹对这个词并未产生任何恍然大悟的反应(West, 2010:55)①。此处韦斯特用后方女性听闻弹震症的困惑,模仿了彼时大众对弹震症一知半解的状态。
在这样的话语关系网中,弹震症成了一个文本楔子,它与新型战争方式和当下士兵境况的关联,自然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关切,但同时后方公众与它的距离又使作者享有部分挪用的自由,免除了情感和道德压力之下的表征趋同。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小说将克里斯的弹震症症状压缩至单纯的失忆,剔除了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其他表现:他从医院被送回家后,热情地与人打招呼,高兴地哼歌(64);待人有礼,情绪平稳(70);得知自己失去十五年的记忆后,也并不在意——只要能找回玛格丽特,他就能沉浸于幸福的过去(79)。事实上,克里斯的“失忆”确实源自其他故事灵感。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在《丽贝卡·韦斯特传》(RebeccaWest:ALife, 1996)中披露,小说受到医学杂志上一篇文章的启发,“该文描写了一位上年纪的工厂雇员从楼梯上摔下来,头部着地,醒来后认为自己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拒绝痛苦的妻子,一心要找曾经的情人”(1996:69)。这个病例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嫁接到了克里斯的弹震症失忆上,只是将病因做了替换。
从文本效果的角度来看,病因的替换无疑解释了《士兵的回归》中弹震症那种不合时宜的纯粹表现,但更重要的是,其嫁接的“失忆”悄然转变了小说聚焦的核心议题。它将士兵可能受到的伤害搁置,转而以“失忆”唤醒人物和同时代读者对记忆断裂前时代的怀旧。小说中克里斯“人生大事”的相关年份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他在战场受伤的时间是1916年,失去十五年的记忆,则记忆倒退至1901年——对英国人来说,这个年份是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爱德华七世继位的节点,是回忆中更令人骄傲、值得怀念的历史时段的终结处。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就指出这部小说“部分带有爱德华时代的特性”,那是“英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是维多利亚主义与现代主义浪潮遭遇的狭窄通道”,彼时“工人问题、妇女问题和爱尔兰问题同时存在;政治与社会权力转移;紧接着就是战争的大麻烦”(1998:ix)。因此,克里斯的“失忆”很容易唤起身处一战之中的英国读者的怀旧共情——若能瞬间就摆脱十几年动荡不安的记忆和凭借后见之明已知的战争后果,这何尝不是彼时英国社会的共同情感向往?
来自有产阶级的克里斯与美貌妻子基蒂于1906年结婚,他们的儿子奥利弗于1911年夭折,孩子的夭折自然隐喻着婚姻的无果,而这两件人生要事以五年为间隔,标记了克里斯因弹震症失去的记忆与爱德华时代近乎完整的重合。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失忆是对不愉快经历的主动压抑,事实上《士兵的回归》也是“最早描写精神科医生的英语小说之一”(O’Malley,2015:92),文本后半段引入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师吉尔伯特·安德森这样评估克里斯的失忆:“他的无意识自我,拒绝让他恢复与正常生活的关系,因此就造成了现下的失忆”(108)。该点评不仅适用于克里斯这位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也同样呼应了战时动荡不安的环境下英国人的某种共同情感倾向——重返过去、重返田园,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分析“怀旧”出现的时机时指出的,“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2021:7)。对彼时的英国人来说,怀旧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择,而《士兵的回归》恰以“失忆”诱导出克里斯和玛格丽特十五年前在猴岛(Monkey Island)上的一段带有黄金时代色彩的回忆,复现了“怀旧”的运作机制,传递出一种渴望用纯真替换物来消除“麻烦”的共同意识。
3.猴岛:召唤田园怀旧
在小说中,猴岛是属于克里斯和玛格丽特的共同回忆,也是被弹震症失忆所召唤的怀旧想象,有关它的描述均带有强烈的田园牧歌特点(O’Malley, 2015:95-105)。失去十五年记忆的克里斯返回家宅,在堂妹珍妮眼中,他的一举一动均显得与现实脱节,然而克里斯只强调“猴岛是真的,你不知道老猴岛,我来告诉你”(72)。通过想象和叙述的运作,“怀旧”将怀旧客体带至当下,置换真实感。从克里斯的讲述中,一处理想的、孤立的田园乌托邦出现了——这个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小岛绿树成荫,风景秀美,玛格丽特和她的父亲在猴岛上经营着一家远离尘嚣的旅店。对克里斯来说,少女玛格丽特身上有着属于田园的宁静气质,在他的记忆中,猴岛上最重要的景观是“白山楂树”(72,76)。“山楂树”作为爱情的象征符号,从中世纪起就在西方文学中占据显著位置,它是“爱情寓言的常量之一”,没有山楂树的园地就仿佛“熟睡且感觉安心的宫廷情人一样不可思议”(Eberly,1989:41)。小说里每当克里斯对“白山楂树”的回忆出现时,少女时代的玛格丽特也必然身着“白色的裙子”(72,76)以最纯美的模样浮现于记忆之中,用克里斯的话来说,“她就是慈善和爱本身”(72)。将过去时空中的具体意象与抽象道德和高尚情感联系起来的做法,是怀旧逻辑中普遍且必要的一环。
正是借助“白山楂树”在克里斯和玛格丽特心中独特的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印记,象征时空中的标记物对怀旧主体的价值被揭示出来——它是召唤共同情感依附的符号,隔离令人不安的现实。在小说中,堂妹珍妮代表在后方受到前线战况报道影响的大众,她时常做“近期英国妇女常做的噩梦”,将战争宣传电影里的情景投射到梦中,梦见克里斯穿过西线战场的“无人区”(No Man’s Land),四处是被炸得血肉横飞的士兵(48-49)。而当她听闻克里斯和玛格丽特对白山楂树以及猴岛记忆的描绘时,也产生了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梦幻感,“真奇怪,他们俩都那样细致地描绘渡口边杨树林里的一棵白山楂树”;“真奇怪,克里斯和她讲起那里,仿佛那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魔法状态”(84)。这种隔绝感正是怀旧在认知层面为心理需求所建构的舒适区。“环境断裂或剧烈冲突会否定人类维护自我连续性和统一性的根本需求”(戚涛,2020:96),而怀旧情感正是主体应对连续性危机的产物。在空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不论对克里斯这样的遣返士兵,还是玛格丽特和珍妮这样的后方平民,猴岛空间都成为理想化的隔绝地。他们为猴岛和白山楂树赋予的光晕不仅将自身置换进没有痛苦的田园世界,也用施魅的话语把听者带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叙述者的珍妮摹仿了每一个听到田园诗般讲述的读者,而讲述的过程则应和了彼时英国社会和群体意识中愈发清晰的重返田园的呼声。
事实上,重返田园的乡村怀旧贯穿于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只不过每一次促使呼声走向嘹亮的动因有所差别。在一战爆发前的爱德华时代,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立足于“英国状况”且以田园作为“他处的神话”(Mackenzie,2013:108),提供有关秩序的暗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乡村的心脏》(TheHeartoftheCountry, 1906)和E. M. 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End, 1910)都在这条道路上做了尝试。而爱德华时代的关键文本之一,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 1859-1932)的《柳林风声》(TheWindintheWillows, 1908)更是将河滨田园生活作为动物故事的框架结构,以“怀旧的笔调构建了一个传统绅士共同体”(陈兵,2022:24)。这些文本的共同特点是面对转型期的困顿以某种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怀旧,寻求解决工业和城乡问题的可能性。如果说爱德华时代的英国问题是复杂纠缠的(工人问题、妇女问题、爱尔兰问题和政治与社会权力转移等),那么随着一战的爆发,这些问题上又叠加了新型机械化战争的暴力。对战争作出反应的“田园怀旧”也成为战争爆发后不久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中的显性声音。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其一战文学批评经典《大战与现代记忆》(TheGreatWarandtheModernMemory, 1975)中指出,萨松(Siegfried Sassoon)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人作品中的田园理想是“夹在暴力与恐怖之间的时刻”,它们作为“插曲”或“绿洲”在战争回忆中“短暂重现”(1975:236-237),这种模式为叙述的推进提供了情绪动力,通过并置诱使读者谴责现代世界的混乱与苦难,向往阿卡迪亚式的世外桃源。
从文本的章节安排上来看,《士兵的回归》似乎也使用了类似的叙述模式,涉及猴岛的两章被夹在整个文本六章的中间部分(三、四章),其前后分别以患弹震症士兵回归后方和治愈返回战场为主要事件,这就使田园怀旧成为名副其实的绿洲,夹在暴力的背景和前景之间。田园作为退守之处所蕴含的逃避和隔绝意义,同样嵌套于文本设计之中:猴岛是田园的象征符号,其与小说人物最早的瓜葛就始于逃避和疗愈,玛格丽特和父亲之所以搬去猴岛经营旅店恰是因为母亲的逝世,那里与外界的“断然差别是种疗愈”,他们“在绿色的寂静中安顿了下来”(85)。十五年前克里斯与玛格丽特在猴岛的梦幻相恋,同样起始于克里斯因躲避家族生意的散心(86-87),十五年后,猴岛的再次出现又与压抑战争不愉快经历的失忆和逃避重合。小说有一处关于玛格丽特在猴岛房间陈设的描写,她的“小房间暮色沉沉,只有桌子上的缝纫机和壁炉架上她母亲那放大了的照片,以及用红色毛绒相框摆设起来的丁登寺之景”(77),封闭房间里封闭相框中被当作心灵幽居所观赏的景色,其田园怀旧的隔绝意味呼之欲出。隐居、退守的安全感是这种风景和怀旧背后的伦理,它往往为经历危机和怀疑的群体提供某种基于共同审美取向和情感需求的认同,让人产生归属感的快乐。
4.田园怀旧的美学与共同体难题
共同的审美取向确实能够制造出精神上的共识,但对20世纪初至一战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英国人来说,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田园怀旧背后有着怎样的心理诉求,其美学表象下的伦理暗语为何,它是否能够成为共同体所必须的“共识”的纽带?事实上,田园风光在文学书写中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反映,它是被反复编码的风景,其美学既受到时代思想和情感结构的影响,也在风景与人的关系中透露出书写者的摇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CountryandtheCity, 1973)中追溯了历史沿线上的数个时期,指出人们面对旧秩序的破坏时所自发求助的习惯,即“把过去,把那些‘过去的好日子’当作一种手杖,来敲打现在”,但不断后退的历史(怀旧)和田园书写的结合“其实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运动”,“对于每一种回顾……都需要进行准确的分析”(威廉斯,2013:15)。在对田园诗传统中“精心挑选的意象”之流变的考察下,威廉斯发现“不受干扰的乡村快乐和安宁”以及“黄金时代的回复”都是选择性的建构,是建立在“关键张力被删除”的基础上的,其结果就是“诗中不再有真相”,“田园诗变成一种极其造作和抽象的形式”(同上:24-27)。
韦斯特在《士兵的回归》中借由弹震症失忆所插入的猴岛片段,模仿了这种抽象造作的形式,但经由士兵被弗洛伊德式心理暗示所刺激恢复的现实记忆,小说又对田园怀旧摆出了反叛姿态。克里斯究竟应该沉浸于失忆的后果,还是应该被唤醒、正视现实,这实际上是从爱德华时代到一战的英国社会在面对现代性问题和战争暴力的“麻烦”时,所感到困扰的选择。伯纳德·施韦策(Bernard Schweizer)认为,小说中三个女性人物关于是否应唤醒克里斯记忆的争论让“这部小说在主题和结构上都被设定为对整个怀旧观念的公投”(2013:30)。当精神分析医师与她们探讨恢复克里斯记忆的方法时,玛格丽特认为“谈话疗法有什么用呢?你无法治愈他……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法让他快乐,你只能让他变得普通”(110)。她们的争论再现了愉悦与真相之间的艰难选择,小说最终给出的答案是“真相就是真相……他必须知道”(116)。尽管这本小说从出版伊始,就不断受到责难,人们认为其结局提供的解决太过仓促,似乎把弗洛伊德式的精神治疗推到了荒诞的极致——玛格丽特用克里斯夭折儿子的遗物唤醒了他对现实的记忆,而这个过程仅用了一个自然段的篇幅。但这一不够精巧的安排隐含了某种针对田园怀旧的道德判断——它的美好代替不了残酷却必要的真相。
实际上,尽管玛格丽特和克里斯拥有共同的猴岛记忆,但两人回顾的细节却有所不同,这些微妙却重要的差别破坏了田园怀旧作为共同体归属感的基础。对克里斯来说,田园怀旧从最开始就被当作审美消费品。真正在猴岛上定居并从事养殖生产的是玛格丽特和她的父亲,他们豢养家禽和兔子(74,76),访客因这番辛勤的养殖劳作得以享用白鸭蛋等食物(85)。相较之下,克里斯的来访是富裕阶层到田园寻访野趣的消遣活动,其游览的性质与猴岛在现实中的历史亦颇有关联。猴岛并非韦斯特生造的世外桃源,它原本和丁登寺一样为僧侣使用,后于1723年被第三代马尔伯勒公爵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r, 1706-1758)购买,经建筑改造后用作贵族享乐(Over,2012)。韦斯特熟谙猴岛历史,小说亦将猴岛旅店的修建史概括如下:“第三代马尔伯勒公爵把它建成‘大而无用的怪异建筑’……它有一种属于18世纪的优雅和愚蠢”(73)。对韦斯特时代的作家来说,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大王后时常到猴岛度假的传闻也并不陌生(Over,2012)。可以说,贵族按照自己的品味对田园做出美学加工并消费调适后风景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田园风景的消费者从贵族扩展到了有产有闲阶级,但不变的是他们外在于土地的关系。
与依赖田园土地而生存的“内部人士”相比,这些生活在田园外部却希望间歇寻访野趣的人所采用的是“外部人士”的视角(Relph,1976:49),这种视角差异决定了以田园怀旧作为共同体情感基础的可疑性。克里斯来自有产阶层,不仅拥有偌大的宅邸,还有相当规模的与英帝国海外利益密切相关的家族生意。他与玛格丽特的相恋不是田园内牧羊人与牧羊女的爱情,而是外部的风景观赏者与想象中牧羊女的关系。堂妹珍妮分别倾听了克里斯和玛格丽特讲述对猴岛的记忆,我们可以发现,在前者的故事中,田园怀旧就像猴岛上的希腊神龛那样遥远神秘,“只有美”,就像他的爱一样“永恒不变”(78);但从玛格丽特的讲述中,我们才知道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克里斯目睹玛格丽特同他眼中的“俗人”嬉笑——尽管此人是玛格丽特从小的玩伴,那一刻玛格丽特才意识到“他不像信任同阶级的女孩那样信任我”(86)。他们争吵的当晚,克里斯与父亲聊到很晚,“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前往墨西哥,保证他们的矿业在当地革命中不受影响”(87)。可见,对于寻访田园野趣的“外部人士”来说,即便其审美欣赏并非出于猎奇,但当现实秩序受到威胁时,作为娱乐对象的田园风景是可以割舍的。而玛格丽特后来的人生轨迹显然证明田园“景框”中的内部人士,并不像游客那样“享有从景色中离开的自由”(Cosgrove,1998:19)。借由两人猴岛记忆叙述的微妙差别,内在于田园怀旧美学的断裂被揭示出来,被忽略或删除的“关键张力”重新进入文学文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士兵的回归》反思的是现代场景下基于怀旧的情感团结和共同体冲动。尽管田园怀旧作为一种普遍的情感,可能出现于任何时间和空间,但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来说,它无疑形成了一种热潮,并在战争的“大麻烦”下被推向了高峰。在这一时期,各行各业似乎都涌动着“往回看”的暗流,“市场营销者、建筑师和作家都在小说、广告、住房和社区设计中唤起怀旧欲望,贩卖怀旧形象”(Outka,2013:255)。乡村怀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营销也大致始于此时,创刊于1897年的《乡村生活》(CountryLife)杂志一跃成为英国最受人欢迎的读物之一——《士兵的回归》甚至灵巧地抓住了这个细节,让鲍德里庄园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如饥似渴地阅读《乡村生活》(95)。战争爆发后,堑壕与后方之间频繁传递的明信片和书信更将田园怀旧在“两条战线”上一并推进(Roper,2011:421-432)。不论对前方士兵,还是对后方平民来说,个体在危机下寻求田园怀旧作为情感慰藉并不新奇,但倘若其美学基于消解真实性的想象,且无法在共同生活中实践,那么它曲折隐含的道德引导对共同体而言是不可靠乃至危险的。
5.结语
《士兵的回归》对“弹震症”的挪用具有历史的特异性,其创作时间恰处于“弹震症”开始从前线军医的研究进入后方报道的过渡期,公众对其既有耳闻,又缺乏实感。对当时的创作者和读者来说,“弹震症”包含真切的当下性,但同时仍未成为显性的文学主题,不至诱发陈陈相因的心理习惯。因此,当代读者摆脱后见,再审视这部作品中的“弹震症”时就会注意到,小说悄然将前线的危机与社会深层的情感结构和共同意识联系了起来。韦斯特借用“弹震症”内含的休克元素,把它与“失忆”故事的素材嫁接,使田园怀旧这一凸显的共同情感倾向进入小说图景。而文本中不和谐的细节暴露出田园怀旧美学所隐含的共同体难题:它若脱离客观性,仅提供看似美妙、可消费的共同体验,那就难免遮蔽复杂的现实,倒退着将过去的秩序理想化为被情绪裹挟的共识。
注释:
① 本文对《士兵的回归》的引用均出自West(2010),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