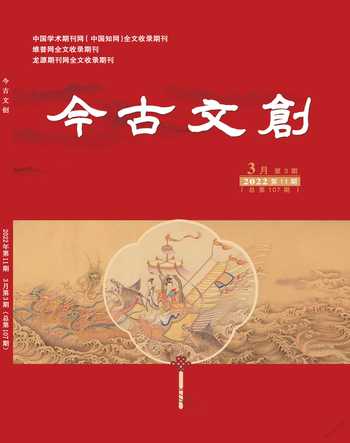从传统文化中探寻勇德继承的意义
荣延庆 谢超凡
【摘要】 中国文化中的勇德主要体现在儒家经典中,“勇”的内涵意指勇必有义、勇必有礼、勇必有为,勇德的三境界是,北宫黝与孟施舍式的守气,子夏与曾子式的守约,孟子之善养浩然之气。当今的和平年代,现代人常常会遭受价值理性的没落、自我认同的危机的折磨。需要一份从安全的混沌状态抽身而出的勇气,这种勇德是推动社会各方面良性进步的动力源泉之一。
【关键词】 勇德;礼义;浩然之气;心灵秩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1-0111-03
勇,最早见于金文。《说文解字注》曰:“勇,气也。从力,甬声。”[1]段玉裁注:“气,云气也,引申为人充体之气之称;力者,筋也;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即人敢作敢为不畏惧的一种气魄。在包尔生看来“勇敢是出于保持基本的善的需要而抵制对于疼痛和危险的本能恐惧的道德力量”[2] 。
一、儒家经典中“勇”的内涵
儒家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仁”也是最高的道德范畴,“勇”是这一范畴中的子概念。《论语》载:“刚、毅、木、讷近于仁”,即刚毅的精神接近于“仁”。《荀子》载:“刚毅勇敢,不以伤人”,具有刚毅勇德的人能践行“仁”道。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是践行“仁”德过程中的勇敢行为。勇德是一种指向“仁”的道德实践。“勇”在《论语》中出现了16次,大多以“礼”“义”“仁”等同时出现: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子曰:“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勇”总是关乎仁德中的“义”与“礼”,儒家强调“知行合一”,“义”与“礼”之知要达至勇不可缺少“为”之行。
(一)勇必有礼
“礼”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因素之一。《说文解字》曰:“履也。”“礼”由一种祭祀礼仪发展成为一种做人的准则、规矩、制度。“礼”指导个体人文化、道德化,从而整合为社会的一套仪式规则,在道德方面成为一种行为规范。“礼”和“仁”是《论语》的两个核心概念,“礼”是通向“仁”的重要途径,“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就是培养“仁”之德。“仁”和“礼”是体和用的關系:“仁”是道德品质,是理想人格;“礼”是约束人行为的具体道德规范,具有外在仪节的规定性,是国家的法律或者地方的法规或者是部门的规章,“礼”具有调控人的行为、为人个体进行定位的作用,约束和规范个体的行为,在社会规范上,起到一种维序作用。笃守“礼”的规范让个体在道德践履中不失相应的度。也就是说,“勇”要循“礼”而行,以“礼”制勇。《国语·晋语六》曰:“勇以知礼。”可见“勇”中必有“礼”的制约和规范。子曰:“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这段话可见君子之“勇”与小人之愚蠢鲁莽的界限。也就是说“勇”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勇”就不合道德之要求,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因此,“勇”必有“礼”。
(二)勇必有义
《说文解字》释曰:“义,己之威仪,从我从羊。”中庸曰:“义者,宜也。”朱子解释为“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义”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宜的、合理的道德准则。“义”在孔子看来,是君子人格最根本的品质。《论语·卫灵公》写道:“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学而》篇第十三章首次出现“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对它的解释是:“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3]也就是说,“义”是衡量一个人的品行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社会价值的一种行为准则,是一种恰当、合宜的具有一定外在强制性的准则。《论语·阳货》记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勇”没有“义”的制约就可能产生“乱”的结果。勇作为一种善德,应包含“义”的成分,正如孟子所言:“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认为要靠正直来培养浩然之气,即要与正义、正道相辅而行。荀子认为士君子有真正的“勇”,因为士君子“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4],从儒家伦理来说,“义”是道德践行的最高准则,“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5],体现道义的原则,勇中有义,才是真正的勇德。君子之“勇”不是意气用事的鲁莽冲动,见“义”才可以“勇”为。“勇”中有“义”才是一种善的力量。勇敢中含有道义,符合“义”的要求,“勇敢而协于义,谓之义勇”[6]故,“勇”以“义”为规范,“义”是“勇”是否合宜的关键,有勇有义,见义勇为,才能称得上勇德。
(三)勇必有为
义,勇之源头;礼,勇之规则基石;为,勇之落实点,为即做,即孔子说的“行”。“勇”不仅是义礼之上的不惧不恐,还是理性指导下的果敢决断。《礼记·乐记》载:“临事而屡断,勇也。”在思考之后,迅速做出正确的抉择,有所行动,才是“勇”。《荀子》所谓“折而不挠,勇也。”勇敢的人在困境中能承受痛苦,坚持到底。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知道是正义的事,没有勇气去执行,是没有勇气、怯懦的表现。“勇”的核心要素是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鉴于此,在遭受痛苦时仍然能够笃定信念采取行动。“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君子当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君子在言行上从不苟且。《宋史·欧阳修传》中有一段关于“见义勇为”的评价:“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见义勇为的人,天赋其刚健勇猛,不管前方是地雷陷阱,还是万丈深渊,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为”包含着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故能称得上于社会有益的勇德。“勇”落地为一种对抗与自我肯定相冲突的因素而“敢于”行动的能力。
二、勇德三境界
先秦儒家经典中“勇”者的代表人物:北宫黝与孟施舍、子夏与曾子,还有孟子。本文尝试用这几位经典勇士来解释分析儒家经典中勇德的三重境界。
(一)守气
北宫黝是勇士中最直观的代表:“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7]这表明北宫黝是为了维护道义,威武都不能使之屈服的人。孟施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具备勇士的勇敢无惧。朱子说:“北宫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动心。”[8]这两人的勇就是强制自己不惧,主要凭借一种外界约束力,死守住一股气,表现出无惧与必胜的气势,并以此威慑敌方,“粗”在于其主要是一种生理上的锻炼,心里没有义理的支撑。孟子的“勇”与“气”紧密相连,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的“气”是志气、气节,是一种精神风貌,需要长期的、艰苦的道德积累和道德践行,凝聚道德之善的长期自觉的过程,是一种意志内省。自春秋战国始,好勇之风在儒家道德规范的社会体系中盛行,勇敢受到高度推崇,齐庄公甚至设“勇爵”以待勇士,《左传》记载:“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身为贵族却被人视为无勇,是莫大的耻辱。《礼记·檀弓上》记载了一则以死来证勇的故事:“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这一阶段的勇主要是憋住一股气,展示出一份“气壮”(但是还没有“理直”),所以权且称之为“守气”。
(二)守约
子夏在回击北宫黝时说道:“所贵为士者,上不摄万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是士之所长而君子之所致贵也。若夫以长掩短,以众暴寡,凌轹无罪之民,而成威于闾巷之间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恶也,众之所诛锄也。”[9]相较之下,北宫黝对待平民百姓与君主,都是采取粗暴无礼的方式,只是“你不给我自由,我就游离于律法礼制之外去暴力争取自由”的侠客[10]。子夏以“义”为前提,以“礼”为规范,以“礼”视君,以仁爱之心待民,将“勇”之为与“义”“礼”结合起来,具备了义礼的勇就不再仅仅是勇“气壮”之“虚”,填补了“理直”之“实”。朱子把曾子的“缩”解释为“理直”。孟子曰:“……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公孙丑上》)赵岐解释“缩”为“义”也,“自反而缩”即通过自省觉得自己的行为符合“义”,从而无所畏惧[11]。曾子的“勇”是用“理”主宰了“气”,“理”是内质,“气”是顺势的外显,这一阶段的勇“气”不需要憋,不需要守,需要守的只是“自缩而反”的过程。福林把“缩”解释为“实密”:“缩之意蕴当有实密之意。若形容心理,缩是一种踏实、不空虚之态……这与理直气壮的状态应当是接近的或者一致的……”[12]故孟子把曾子的“勇”称之为“守约”。
(三)大丈夫养浩然之气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即儒家之理想人格。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既是理想之人格,也是勇者之最高境界:“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为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现实世界不管是困顿还是通达,都不能改变大丈夫行正道的志向,无所畏惧。这一境界的勇建立在对义理深刻认同的基础上,已成为一种道德力量。“血气之勇已化为道德之勇”,不仅在于战胜敌人,而是身心的充分统一并觉醒,面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所畏惧[13]。孟子说:“我善养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志”指人的志向、信念与追求,“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气”指人有了志向与追求以后所展现的一种精神状态。“气”与“志”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孟子认为,人只有做到“明道不移,集义(行每一件当为之事)既久”,浩然之气应运而生,因此孟子自称“吾善养浩然之气”,在孟子看来,人的精神世界是“养”出来的。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大丈夫”所具有的一种信念和意志互相交融的心理状态,或说是一种精神境界。大丈夫善养浩然之气即是儒家勇者的最高境界。
三、勇德的现实意义
“勇”由孔子提出时,只是说“勇者无惧”,“无惧”未必是一种品德,更不是一种肯定性的品德,是中性的。勇在此时只是一种本真性的存在,一种个人气质状态,本质上尚是一种“为己”的儒学精神,属于修身养性的范畴。所以孔子的言论中并没有对“勇”的赞颂,或者说孔子并没有单独言“勇”,《论语·阳货》中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勇”在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上升为一种暗含当时政治价值标准的正面的德性,与使命感、社会道统以及民族大义等相勾连,“为己”不再是勇德的关注重点。礼义等古典行为规范成为“勇”之美德的支撑性内涵。中国当今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古人用以支撑“勇”的礼、义在某些方面已不适应社会的转型发展,或者说今天不能完全沿用经典内涵标准来规范当今社会的勇德。
古人所知,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在今日看来,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愚昧的。建立在认知体系之上的礼、义带有的封建等级色彩,有些是与当今社会价值体系不相容的。对于勇德之经典内涵的批判性继承,应当结合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客观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内涵及判断标准,也需要为勇德确立新的价值方向。这也是一个呼唤勇德的时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价值多元化,“勇”更多地指涉追求价值认同的坚毅与耐力。勇气体现在内心的成长过程中,在价值自我的建设过程中,勇德向“为己”的回归可能正当其时。
当今的和平年代,勇德似乎已经沦为故纸堆里的名词。“对于很多人来说,作为道德的勇不过是一种过时的骑士精神式的历史残留物,在文明社会派不上用场的军人品质。对于某些人来说,勇德不仅不是一种品德,还暗示着暴力、战争或主宰他人的令人不愉快的状态,是与粗鲁相关的概念。”[14]但是,和平的多元发展的年代,或许是一个更需要勇德的时代,只不过这种勇德不主要是用来应对威胁,更多地涉及个体追寻个人认同、价值理性的坚毅。和平年代,人们不用为贫困、生存危机所困,然而,现代人常常会被价值理性的没落、自我认同的危机所折磨。这样的状态中,需要一份从安全的混沌状态抽身而出的勇气,打破周遭安全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精神世界,人生归属感与责任感也由此生发。这种勇德是推动社会各方面良性进步的动力源泉之一。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01.
[2](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系体系[M].何怀宏,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13.
[3]荀况.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1822.
[5]潜苗金.礼记译注[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282.
[6]董莲池.说文部首形义新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4.
[7]许维遹.韩诗外传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0:225.
[8]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0:123.
[9]杨伯俊.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56.
[10]韩云波.侠与侠文化的自由理想——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五[J].天府新林,1996,(1):58.
[11]赵岐.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4.
[12]福林.孟子“浩然之氣”的探论[J].文史哲,2004,(2):38.
[13]黄俊杰.孟子思想史论[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346.
[14]Dennis Walton.Courage:A Philosophical[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18.
作者简介:
荣延庆,男,湖北仙桃人,讲师,医学学士,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教育与医学教学。
2047501705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