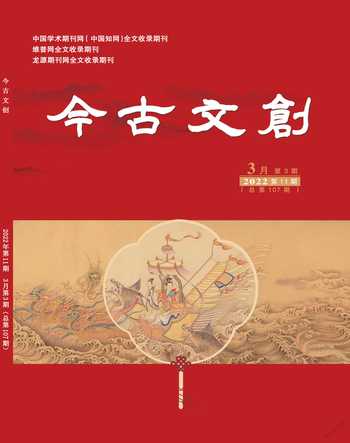重重枷锁下的底层女子像
邵国茹
【摘要】 《生死场》是萧红创作的一篇中篇小说,作品描述了一系列底层女子悲惨的生活状况。文章没有直接表达对男权的反抗,反而以沉着冷静的笔端述说一个个女子的命运悲剧,这实际上是作者对于女性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的血泪控诉,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之时,大家在悲叹之余,更应该理性思考其中缘由。本文试图分析《生死场》一文中造成女子悲剧的原因,在更好地理解文本、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之时,也更充分地理解女性,尊重女性。
【关键词】 萧红;《生死场》;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1-0004-03
一、一重枷锁:时代的残酷
《生死场》里的各色女子,她们生存背景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形成了一种新的尚未形成、旧的又还未完全消退的尴尬局面。虽然飘来了民主与科学的新风尚,但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乡村民众,他们生活以及思想不仅没有因着民主科学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反而受到来自各方的更沉重的压迫。而自古以来都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女子,在社会转型交替之际,所受到的压迫显然更多。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言:“在战争或是社会变革面前,作为受害者,女人永远首当其冲。”
在社会转型之际,当时各方有志改变国家现状之士,都在奔相呼救。力图在思想上启迪人们,开掘希望的曙光,改变旧社会的风貌。《妇女杂志》作为为女性发声的刊物,其思想都依旧封建固执,在编辑思想和编辑方针上,主要倡导如何叫女子做旧礼教下的贤妻良母。
在《妇女杂志》创刊号发刊辞中,有着非常明晰的阐述:“人生天地间,不可一日无所养,即不能一日无所教。吾国女子,自姻皇至今五千年,大抵养而弗教,禽息兽世,如浑纯未开之天地。一部廿四史中,女子之流芳百世者,曾不数十百人,如一线之曙光。近二十年中外大通,形见势细,乃知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舰炮利也。实由贤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起视吾国妇女以来依赖成性,失养失教,能不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耶。”这与晚清以来秋瑾所倡导女子“无论贫富贵贱,幼而事父母,壮而事舅姑,长而育儿女,其本分之事……”有着一致的追求。便是恭谨孝顺,为人母,为人女,却始终不能做自己。王宇对此有深刻剖析:“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论述中最重要的性别符码依旧是贤妻良母晚清‘女子救国的倡导并不要求女子直接介入国家、民族事务,而是要求女性做好现代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即具有强健体魄和现代科学知识(好孕育体魄强健、智慧、适于现代竞争的后代)。”[1]
从这本刊物的发言来看,话语权掌握在执笔的男子手里,他们将遭受欺压的旧中国之原因,单纯归结在女子的无教养、愚蠢、软弱上,没有找到真正根本的原因,不过是寻着以往的老路子,将女性归为红颜祸水之类,女子再次成了替罪羔羊,文章再次强调女性的本分是顺从而非独立,要有教养而非学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放女子的生活,反复强调起到的作用不过是旧时女子之习性的加强版,起不到改变社会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妇女杂志》这本打着为女性发刊的杂志尚且如此,其他的杂志也可见一斑。正如王宇所分析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上紧接着《易卜生主义》一文后面的便是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剧作《娜拉》。这无疑为娜拉形象在中国读者中的接受做了一个前瞻性的意义设定:中国妇女应该像娜拉一样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发展自己,贡献社会。但实际上,易卜生剧作中的娜拉的形象是易卜生所謂‘孤立的人的代表,要表达的恰是对压迫个人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法律以及建基其上的所谓的责任的反叛精神,并不包含个人、女性对社会的责任。胡适对娜拉形象这样的改造事实上根源于五四关于‘个人思想的内在逻辑中。”[2]
无论是刊物或者是译文,并不能做到真正为女子发声。由此可见,当时之社会风尚,并未将女性个人的解放放在迫切位置,没有意识到压迫在女性身上的重重枷锁之根源,或者当时所提女子解放实际上让女子背负了更多的家庭和国家责任,究其原因:“晚清以来关于性别的现代性话语的立根基础是民族主义,尽管这一话语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契机,但是女性作为性别主体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独立与自主并没有进入这一话语主体的视野。这一话语并无意于让妇女先‘救出自己然后再对家庭、国家负责,而只是强调妇女对于家庭与国家的责任。在要求女性与男性一同分担家庭外的民族国家事务的同时,却未曾要求男性与女性共同分担家庭内的劳作。因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性别分工这一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有所触动,但也更加重了女性的负担。”[3]这里所要求的解放实际上并未真正地使妇女独立起来,唤醒的并不是女性的个人意识、独立自主意识,而是将女子解放与责任、民族之义混同在一起,实际上要求的还是女性付出与承担更多,也就不能起到革新女子之思想、开创社会之新风尚的作用。
那么作为女性,并真正为女性发声的萧红,她的文章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女子悲惨命运,深究之下,更能窥见女子悲苦命运之原因。萧红所写的《生死场》一书中真实地揭开了在日军侵略之下的女性惨景图:年轻的媳妇、女学生、十三的小女孩、大姑娘无一幸免于日军的蹂躏。一位十九岁就开始守寡的老婆婆,唯一的儿子参军惨死,最后带着三岁的孙女菱花上吊自杀。主线人物金枝被迫流亡到哈尔滨的都市里去,为了在陌生的都市中生存,出卖了自己的肉体。麻面婆一家被日军杀害。
这些或软弱或坚强的女子,她们熬过了挨饿受冻的日子,却在日军的铁蹄下了此残生。地主的剥削、日军的践踏,底层女子因所处时代的大悲剧下,寸步难行。当物质上无法赖以生存,精神上又失去了寄托时,等待她们的也只有死亡。
当时之社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没有任何生路,即使生存下来,身心也是千疮百孔,备受煎熬。封建地主、日军、糟粕的思想无一不是杀人凶手,正是这些构建了压迫女性的密网,将女性置于水深火热的悲惨时代。
二、二重枷锁:俗成的桎梏
中国自古以来信奉儒家的传统学说,儒家正统学派鼓吹男尊女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天指向男性,坤指向女性,天尊地卑,即男尊女卑,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固守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认为女性就是弱的、愚的。这种自古以来对女子的践踏蔑视,钱虹所著《文学与性别研究一书》,特意从汉字构造看女性的命运沉沦:“许慎的《说文解字》,也以‘服训‘妇字:‘妇,服也,从女持帚扫也。而‘妇所‘服与‘伏的对象自然是、也只能是‘夫,夫尊而妇卑的地位差异赫然可见。”[4]于是他们一方面鼓吹女性的低下与愚笨,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他们对女性的性格定义为柔顺与服从,加大对女性在行为准则上的规范与限制。
《礼记·内则》里专门叙述妇女在家庭中的行为规范:“妇事舅姑,如事父母”,谨慎侍奉父母公婆飲食起居,“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5]
这里面谈到了女性在生活起居方面需谨慎勤快,为人处世则要谦逊听从,不可偷懒懈怠,在人际交往之时不可违逆反抗。对女子各个方面进行了行为规范,实际上,也是对女子的层层束缚和限制。
在《生死场》中,每个女性需要不停地劳作:开篇人物麻面婆在炎热的环境下做家务,做到豆大的汗滴昏花了老眼,还要继续洗衣。但迎来的却是丈夫二里半习以为常的吼骂。金枝大着肚子、临近产期,每天也是做不完的活计,丈夫成业回来不是骂她,就是要求性爱。全然不顾怀有身孕的妻子。其他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要求一刻不停地做活,他们没有说“不”的权利,做事是她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除此之外,还要忍受丈夫无端的、无休止的责骂。
她们地位低人一等,是约定俗成的桎梏。每个女人都是如此,她们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她们自觉地遵守一套已然形成的规范,就是女主内,做不完的家务,挨不完的骂。一切是那么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女人在长此以往的儒家思想熏陶下,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仿佛天性。这里面的女子没有丝毫的反抗性的举动,也没有任何的“大胆”的想法。
男人,更具话语权的男人们,给予女人各种规定和规范,只有合乎他们的规范才能称作好或者贤能,这其实一种规则谋杀,在这套话语体系下,千百年来,女性遵守着种种规范,不敢有任何逾越,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口诛笔伐。女性主义的先驱学者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发出这样的呼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6]
三、三重枷锁:他者的禁锢
《生死场》里的众多女子,往往以悲剧结尾。这些女子的丈夫,一种被称作男人的物种,是造成女子悲剧的主要推手。女子是活在他人眼中的女子。她们是自己丈夫眼中的她们,她们必须活成丈夫眼中的样子,才是正确的,才有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而在他们眼中,女人不过是性欲的发泄对象,不过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在波芙娃的《第二性》中显露无遗:“女人吗?这很简单,喜欢简化公式的人这样说:女人是一个子宫、一个卵巢;她是雌的,这个词足以界定她。在男人嘴里,形容词‘雌的像侮辱一样震响;然而,他对自己的动物性并不感到羞耻,相反,如果有人谈到他时说:‘这是雄性!他会很骄傲。‘雌的一词是贬义的,并非因为它把女人植根于自然中,而是因为它把女人禁锢在她的性别中。”[7]
在男性眼中,他们天性带着优越感,理直气壮的鄙视女性,在他们眼中,女人不过就是一个子宫,一个生育机器,一个性的发泄口。而一旦作为妻子的不能满足丈夫的性要求时,男人丑陋的面孔就会如撒旦般暴露。钱虹在关于“妻”和“嫁”详细分析了女性地位和命运的沉沦:“古时候,‘妻又可称为‘奴,古字写作帘,从‘巾' ‘奴声。《左传·文公六年》疏曰:‘帑,妻子也。这‘帑字另有一义,指聚藏金钱之处。《说文解字》说得很清楚:‘帑,金币所藏也。那么,这‘妻怎会与藏金之处扯到一起呢?原来,这正反映了买卖婚姻制度把女人视为金钱财宝的劣迹。在婚姻可以自由买卖的社会里,娶妻纳妾都是以钱财作为等价交换物的,所以,丈夫一旦有了钱财之需,便可将妻妾转手倒卖他人,‘妻不就等于一座‘芝麻开门的藏金窟了吗?文字研究专家经过考证,认为它与‘贾‘沽‘购不仅古音接近(至今在某些方言中仍念‘嫁为gu音),而且词义相仿。因为古时候嫁女娶妻跟商品交易无异,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女人)。在先秦,‘嫁字就有‘卖的意思,《战国策·西周》中有‘以嫁之齐也,就是卖给齐国的意思。这足以说明在战国时代,女人等同于钱财货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发、买卖的悲惨命运。”[8]当种女性等同货物的观念在男人心中根深蒂固之后,一旦作为“货物”的妻子没有利用价值,等待女人们的,也只有来自丈夫的冷漠和残忍伤害。
村里最美丽的女子月英患病了,她的丈夫起先会去求佛烧香,觉得是尽到了做丈夫的义务,其实是希望妻子好起来满足性需求。最后用砖头围在月英身上,恨月英不早死。当五姑姑的姐姐生产时,虽然是大户人家,也必须在柴草上面生,因为压柴和不能发财有着迷信的关联。当这个赤身裸体没有任何尊严的女子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生产时,她的男人吼叫着要生产的女人拿靴子,得不到回应之后,大骂女人装死,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因为难产而失去气力如同死尸的女人,之后举起大水盆向女人扔过去。李二婶子因为小产而死。还有其他因为生产遭受痛苦、甚至死亡的女性,她们无法言说,只能沉默,不能有任何反抗,只是默默地忍受生产的痛苦,忍受来自夫权的压迫。
金枝临近生产之日,还要整日做家务,以及忍受丈夫的性发泄。金枝形容这种痛苦如同灾难一般。生孩子之后,丈夫成业因为米价落了,整天吼骂还不解恨,听着孩子因饥饿而啼哭的声音,烦躁之下将才一个月的小金枝摔死。王婆不满丈夫的冷酷无情,选择服毒自杀,服毒之后尚有一丝气息,丈夫赵三看到此情此景,不仅不去设法营救,却等老婆死去等得不耐烦,直接靠墙打瞌睡。当看到王婆紫色的脸变成淡紫,似乎渐渐活过来的时候,赵三想到的死者化成了鬼,于是用他的大红手贪婪地将扁担压过去,如刀一般扎实地切在王婆腰间。
这些女子的生命悲剧,与和她们一起生活的男人息息相关,性爱本是夫妻间和谐逾越促进情感的亲密接触,但在这里,仅仅是男人发泄欲望的工具,而当妻子无法满足性欲时,男人残酷无情就暴露出来了,只希望妻子死掉。
女人被男人看作是附庸,是活在他人眼光之下的生物。他者的眼中,女子是绝对的付出和服从,波芙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人面对的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絕对,而女人是他者。”[9]鲁迅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儿性,而没有‘妻性,妻性完全是后天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这一观点的真理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家庭的论述中可以找到理论依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生死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惨死在夫权制度下;王婆被丈夫打死,月英被丈夫害死,金枝刚满月的女儿被丈夫摔死,这些惨死悲剧与男性的残酷剥削有着直接原因。他者之下生存的底层女子更显得举步维艰。女性的生存困境在丈夫的压迫剥削下,更加无立锥之地。
四、结语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生死场》中底层女子受苦受难的原因,力图更加全面深刻地解读萧红笔下底层女子生存的不易和悲哀。同时也给予现代人理性思考两性关系,正如韩立群在分析“丁玲时代的萧红”所言:“《呼兰河传》对原始宗教与男性法权相结合的封建社会乡村文化的批判,便具有上述理论意义。因为它的目标正是:‘撕碎男性法权和宗教神权这两条锁链上的花朵,使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公众摆脱幻想和愚昧,直面苦难现实,作为‘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充分显示了作者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思想的深刻性和在女性主义艰难实践时代的实践价值。”[10]
参考文献:
[1][2][3]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0,31,20-21.
[4][8]钱虹.文学与性别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21,21.
[5]戴圣.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30,336,338.
[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9.
[7](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
[10]韩立群.现代女性的精神历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