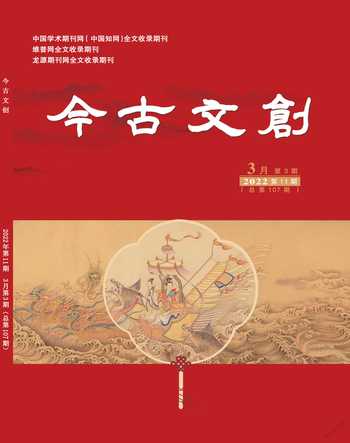论《一小时的故事》中露易丝 · 玛尔拉德的女性意识
【摘要】 19世纪,美国对于妇女的家庭角色以及社会身份提出诸多规定,女性的大部分权利因此饱受拘束。彼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民众关于女性传统观念的蒙昧思想逐步觉醒,女性文学创作成为研究热点。其中最著名的文学作家为同时关注女性的传统思想和解放思想的凯特·肖邦,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一小时的故事》广受关注,人们对于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对作者经历以及作品的研究,分析婚姻中以露易丝·玛尔拉德为代表的女性的被动地位,以及其对于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渴望,以期展现女性意识的变化轨迹。
【关键词】 女性意识;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1-0007-03
一、引言
凯特·肖邦被誉为美国“20世纪女性解放运动先驱作家”,1951年出生于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具有法裔克里奥尔人血统,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其女性意识逐渐凸显。四岁丧父,凯特·肖邦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外祖母和曾祖母三位女性抚养成人,期间一直受到曾祖母所讲故事的影响,因此开始关注女性对传统道德枷锁的反抗与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与奥斯卡·肖邦结合的婚后,她仍然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个性,对于吸烟、喝酒、骑马、独自散步的热情与19世纪中产阶级传统女性的性情相悖。
塞耶斯特德曾指出:“肖邦同时关注传统女性和解放了的女性。她常常创造出成对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就在几周的时间里,先写传统女性,紧接着就写解放了的女性,而这表明,就女性的命运而言,肖邦一直和自己保持着对话。”即便如此,观其女性思潮追求的一生,肖邦从未公开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也从未加入或支持过类似组织(肖邦曾加入圣路易斯周三女性俱乐部,但后来主动退出),因而并非为字典定义的女权主义者。
《一小时的故事》是凯特·肖邦最知名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患有心脏病的露易丝·玛尔拉德在一小时内,经历丈夫失事丧生又再度出现的情感起伏。该文以女主人公为第一研究对象,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客厅的三个视角出发,探讨整个时代背景下女性意识的禁锢、追求与陨灭。
二、露易丝·玛尔拉德传统婚姻的桎梏
露易丝·玛尔拉德夫人的婚姻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和谐且幸福的。一方面,对于玛尔拉德夫人本人而言,“她知道,当她见到丈夫那双温柔、亲切的双手变得僵硬,那张从来都不会对她吝啬爱意的脸变得毫无表情、灰白如纸的时候,她肯定还会哭的。”丈夫对她的爱得到了她自己承认——这是一种温柔的关爱,无微不至的照料。另一方面,对于小说中其他人物而言,即姐姐朱赛芬或是丈夫的朋友,后段中,姐姐约瑟芬因担心她而跪在紧闭的门外,嘴唇对着锁孔,苦苦地恳求着让她进去:“露易丝,开开门!求求你了,把门打开——你这样会得病的”,朋友理查兹的反应是立刻动身,赶在那些粗心大意、考虑不周的朋友之前把這个不幸的消息带了回来。亲朋好友关注到玛尔拉德夫人的心脏病,为了顾全她的身体于是不得直言悲剧。通过这些语段,可以从侧面看出,玛尔拉德夫人的生活是令人艳羡的,在婚姻中享有丈夫的细心呵护,拥有亲朋好友的体贴照顾,对于每一个社会女性而言,这样的婚姻生活无疑是值得追求的。
然而,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会发现其中的蜿蜒曲折。不需为生活操劳,有丈夫的疼爱,又有朋友关心爱护,在这样一种完美幸福的环境中,玛尔拉德夫人却感受到婚姻生活的抑郁。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宠爱才让玛尔拉德夫人内心痛苦无比。第一段中,“她的姐姐朱赛芬告诉她的,话都没说成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她丈夫的朋友理查德也在她身边。”对于具有社会身份的每一个人而言,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普遍情况下大众会认为女性存在于男性的存在。类似此处玛尔拉德夫人姐姐的劝导,无一不在宣示着,在婚姻生活中,女性是完全依靠男性而存在的“附属品”,离开了所谓“顶梁柱”的丈夫,女性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等待着她们的必然是身体的日渐憔悴和心灵的干枯崩溃。
由心理环境建构以小见大,此处只言片语直接折射出了社会中已婚女性的处境。即使生存的外在条件看似备受推崇,但丈夫和朋友所给予的一切并非是当事人内心真正渴望得到的,而备受束缚的环境也让她们绝无实现自己愿景的机会。在一个公共领域,即文中的“客厅”这样一个众目睽睽的场景里,一个接纳外来者的地方。她们言行举止都必须得尽其所能地符合已婚女性的形象,必须让人直视已婚女性的身份标签。她们完全受到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和约束。在美国,无论是宗教还是法律都对女性提出了诸多的要求,进行了严苛的规定,在政治上,她们无法享有选举权,因而无法发表自己对于政界人士或者现状的看法,甚至无法申诉女性应当具有的权利;在道德上,她们被要求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一方面无法接收到正规的教育,只能从事最基本的家庭活动,另一方面必须做到忠诚顺从,时时宽容忍让等等。甚至,美国许多州明文规定“已婚妇女无权签订合同,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不能支配自己的收入。无论什么原因,如果夫妻双方离婚,妻子无法获得孩子的监护权”。那么,对于已婚女性而言,自己的真实想法,若无法奴颜婢膝地迎合,那么毋庸置疑会受到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性的质疑与否定,不平等的话语权直接造成了两性关系的不平衡。待情绪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是传统意义的金丝雀,而婚姻则是镣铐,囚禁着她们最真实的诉求。
三、露易丝·玛尔拉德女性意识的觉醒
露易丝·玛尔拉德夫人的女性意识从第一部分的描述中便略有显现,其中“要是别的妇女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手足无措,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她立刻一下子倒在姐姐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块恰好说明了玛尔拉德夫人与众不同,她并非流露出和传统女性一般的感情,或者做出与他们一般的举动,此处为读者留下了悬念,也昭示了具有女性意识的人物的多舛命运。
其中,玛尔拉德夫人女性意识最为突出的部分则是发生在“房间”。与前文中人物角色直白敞开于外来者面前的“客厅”相对,“房间”是封闭的、排他的、放纵的、自由的,是一个能够赋予人们独立思考权利的空间。若说“门外”的“客厅”是公共世界,玛尔拉德夫人佯装哭泣,那么“门内”的“房间”则是私密世界,玛尔拉德夫人真实哭泣。
在“房间”里,凯特·肖邦的写作视角从叙事视角转化为了人物视角,直戳玛尔拉德夫人独处时的女性意识觉醒过程中的挣扎、收敛与爆发,尤其是通过停滞时间的环境描写——“窗”来充实了她的部分觉醒和对完全觉醒的渴求。文章中这一部分共出现三个“窗”,其一,“正对着打开的窗户,放着一把舒适、宽大的安乐椅。全身的精疲力竭,似乎已浸透到她的心灵深处,她一屁股坐了下来。”其二,“她能看到房前场地上洋溢着初春活力的轻轻摇曳着的树梢。空气里充满了阵雨的芳香。下面街上有个小贩在喝着他的货色。远处传来了什么人的微弱歌声;屋檐下,数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对着她的窗的正西方,相逢又相重的朵朵行云之间露出了这儿一片、那儿一片的蓝天。”其三,“她正透过那扇开着的窗子畅饮那真正的长生不老药呢,在纵情地幻想未来的自由美好岁月,春天,还有夏天以及所有各种时光都将为她自己所有。她终于站了起来,在她姐姐的强求下,打开了门。她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激情,搂着姐姐的腰,一齐下楼去了。”这三个窗无一不在昭示着玛尔拉德夫人因女性意识觉醒而引发的兴奋之情,而“当她放松自己时,从微弱的嘴唇间溜出了声音。她一遍又一遍地低语:‘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她的目光明亮而锋利,她的脉搏加快了,循环中的血液使她全身感到温暖、松快”,这一句则直接宣示了玛尔拉德夫人的兴奋巅峰。
这也正好符合凯特·肖邦一贯作品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推崇,展示了另一种形式的女性意识觉醒。在肖邦的笔下,类似玛尔拉德夫人,大多数女性在与大自然的接触过程中实现觉醒,但是最后被迫或者自愿选择在大自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正好伴随着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经历种族矛盾、南北战争和废除农奴制等一系列动荡后的美国女性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绝大部分人们,尤其是女性开始对自己的传统身份提出质疑,以期冲破传统女性社会地位的束缚,实现真正意义的女性意识觉醒。
四、露易丝·玛尔拉德自由选择的幻灭
露易丝·玛尔拉德的女性意识的陨灭伴随着她自己生命的陨灭,本来是一件令人无尽感伤的事情,按照作者的叙事视角应当对此加以描述,将读者的情绪直接推到顶峰。但是,在此处,作者并没有按套路写作,而是笔锋一转,在文章中通过一种客观的口吻对这样一个场景进行叙述。 “医生来后,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说她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这种反讽的写作手法直接立体化了整个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表面上来看,众人必将为之长吁短叹,或为玛尔拉德夫人心脏不适造成的英年早逝而悲伤,或为玛尔拉德夫人对于完好归来丈夫的乐极生悲而遗憾,或为玛尔拉德夫人对于丈夫深情厚谊而震慑。人们对于玛尔拉德夫人的死因绝对不会多加思考,而是只会按照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使其能够符合集体潜意识所要求的社会习俗和伦理道德。
由此,无人会猜中,玛尔拉德夫人是因获得自由后的狂喜和现实的严重反差形成的强烈刺激而亡故,面临再度降临的恐惧,她直接受惊吓而死。原本,当她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时,即使在人前表现出了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但是内心对于自由的渴望已经溢出。当她想要面向未来重新开启只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时候,当她想要融入窗外的世界,永远与拥有的丈夫的生涯告别时,她的丈夫破门而入,正如文中所说“进来的是布兰特雷·玛尔拉德,略显旅途劳顿,但泰然自若地提着他的大旅行包和伞。他不但没有在发生事故的地方待过,而且连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一切又回到了既定的轨迹,而她又要重新回归婚姻继续所谓的令人艳羡的幸福生活。于是,在一切希望幻灭的时刻,绝望的情绪直接吞噬了她的内心,而唯一等待着她的就是死亡。
这正如弗洛伊德关于自我和超我理论的解释,即“当本我和超我出现嚴重冲突的时候,自我如果不能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人就会失控混乱。”正沉浸在“门内”“房间内”“窗边”的“本我”世界中的玛尔拉德夫人,在面对“超我”对于“本我”的再次压制,“自我”的意识失控,直接造就了自由选择的幻灭。其中,文章中共出现了六次“门”的踪影,最后一部分的“门”,和前面五次隔绝“客厅”与“房间”的门不同,指的是丈夫打开的大门。这是那个本来传递自由消息的“希望之门”,但无奈转变成了真相水落石出的“绝望之门”,而象征着本我世界的“门”以及美好愿景的“窗”则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无论是在婚姻生活中的“单身自由”,还是在社会体系内的“权利自由”,对于处于彼时社会的女性而言,实现美好愿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五、结语
文章中女主人公在一个小时内的三个阶段的变化,暗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走向。18世纪以前,社会对女性卑微的传统地位存在固化看法。1789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英美法妇女先后获得了选举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潮为当时的妇女带来平权的曙光。19、20世纪,由于家庭、婚姻和男权的压迫,女性权利再次受到控制。本文立足于西方传统女性角色的转化以及蒙昧意识的觉醒,通过讲述基于故事情节展开的场景变化,分析女主人公的行为逻辑,呈现女性思想在觉醒过程中的变化轨迹,对丰富女性意识的研究方向以及指导女性作品的创作逻辑具有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於晓丹.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对女性文化的影响[J].芒种,2016,(02):97-98.
[2]张沛.凯特·肖邦作品的叙事文本与美学意义[J].作家,2015,(22):70-71.
[3]熊蕾.婚姻与枷锁浅析《一个小时的故事》[J].语文学刊,2013,(2):59.
[4]苏秀玲.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凯特·肖邦作品分析[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5):59.
[5]柳欣.面具下的阴影:痛苦与死亡中觉醒——以荣格原型理论分析《一小时的故事》[J].名作欣赏,2015,(24):59-60.
[6]田园.《一个小时的故事》双重主题阐释[J].语文学刊,2015,(3):12.
[7]胡月.《一个小时的故事》中的女性意识及社会背景[J].史苑杂谈,2014,(18):23.
[8]董雪飞,田静.旧南方的新主体——凯特·肖邦内战小说的创伤书写[J].外国语文,2020,36(01):85-91.
[9]张胜男.十九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意识觉醒的根源探究——以凯特·肖邦本人及其作品中的女性为例[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33):72-73.
[10]曹晨.尼采哲学下的凯特·肖邦[J].科教文汇(下旬刊),2018,(07):160-161.
[11]王亚萍.凯特·肖邦短篇小说中的双重种族观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8.
[12]王庆勇,张梅.从婚姻看凯特·肖邦的女性意识——以《一小时的故事》和《暴风雨》为例[J].名作欣赏,2017,(36):77+79.
[13]王海莉.探析凯特·肖邦笔下新女性觉醒的社会根源[J].现代交际,2017,(23):78+77.
[14]秦圣洁.凯特·肖邦短篇小说的功能文体分析[D].江苏大学,2016.
[15]李新梅,张谡过.论肖邦短篇小说女性意识的矛盾性[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6,(12):78.
[16]王哲.凯特·肖邦的女权主义文学创作探究——从《一双长丝袜》谈起[J].出版广角,2018,(04):82-84.
作者简介:
冯璐,女,汉族,上海人,东华大学,翻译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翻译和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