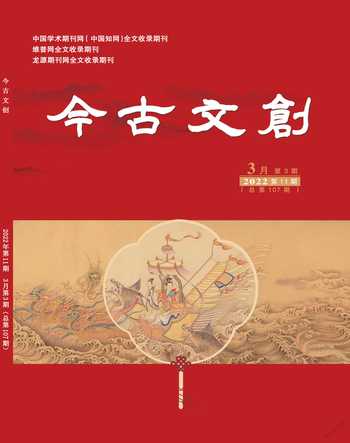《金陵十三钗》的女性主义解读 : 战争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女性
汤小丽
【摘要】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反映了战争中的女性除了会和男性一样被剥夺生命以外,还会遭受性别的压迫。战争暴力下男性和女性都可能面临死亡,但死法上却存在差别。男性往往可以死得“干脆利落”,而女性却在死前经受折磨。在战争暴力面前,女性所受的压迫被凸显。而女性所受的压迫在小说中一直存在,贯穿始终,好比容易被忽视的幕布。战争暴力犹如一束灯光赤裸裸地打在了这幕布上,引起了读者对战争中女性的同情,对一直以来女性所承受的压迫的反思。
【关键词】 《金陵十三钗》;女性主义;战争;性别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1-0019-03
一、“暴风雨来临前”的性别压迫
人类创造文化,文化创造人类。小说中的人物符合实际地被置于男女不平等的父权制文化中。无论是男性对女性明显的性别压迫,还是女性在文化塑造下内化了男性意识对自己的压迫,都在小说中时时浮现。如果把日军比作一场“暴风雨”,在它席卷威尔逊教堂前,教堂里的性别压迫早已存在。
(一)被贱视的秦淮河女人
《金陵十三钗》中作者把13个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下用女人代替)和金陵大学的女学生置于同一个环境里,两个社会身份完全不同群体,从一开始就针锋相对。在女学生眼里,这些女人是社会的败类,她们寄附在男人身上,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才得以苟活。女学生们态度鮮明地要和这群女人划清界限,认为她们同自己讲话的资格都没有。“呸,我跟你说话了吗?你也配搭我的腔?”孟书娟拿出抬手专打笑脸人的态度[1]。在教堂里,女学生们住的“阁楼”和女人们住的“地下室”也在空间上象征了社会身份的悬殊,暗含着“高贵”与“低贱”的区别。
英格曼神父和法比副神父对这群女人的歧视和压迫更多体现在冷漠的态度上,而非语言上。在他们心里,这群低贱女子甚至连人的资格都不具备。当女人们潜入教堂的阅览室取暖时,英格曼神父的反应足以表明他冷漠的态度。他认为这些女人不配听他的愤懑指责,便把法比·阿多那多从卧室叫来。“法比,怎么让这样的东西进入我的阅览室?”[1]在故事的结尾,英格曼神父不假思索地打算用这些“贱命”去拯救女学生的命,是法比拆穿了他,“那就是你向日本人供认的时候,已经想好要牺牲这些女人了。”[1]诚然,英格曼神父在故事结尾不再那么厌恶这群女人,但依然没有尊重她们作为人的基本生命权利。在这位神父心中,存在着强大的偏见,生命并不平等。在灾难面前,他代替上帝行使了选择权,把“诺亚方舟”给了女学生们。
除了女学生和神父这些人对女人们明显的鄙夷外,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男性对这群风尘女子的态度才是最令人深思的。第一个是张世祧,这个最后一次让赵玉墨对男人抱有幻想又幻灭的男人。张世祧看中了赵玉墨“淑女其表,娼妓其内”的气质,认定她为理想型的妻子。却在赵玉墨的名妓身份被揭穿,觉得“她的小打小闹不再那么可爱”后,给了她“一根金条和五十块大洋”,回归家庭,甚至在妻子的安排下,远走美国。在这之前,赵玉墨经历过多次由希望到失望的恋爱,让她摆脱不了这个死循环的,显然是她秦淮河女子的身份。张世祧使她陷入绝望,也认清了现实,通过男人来救赎自己,是行不通的。第二个是陈乔治,英格曼神父收养的孤儿,教堂的厨师。为了姐妹们能每天多分得三个洋芋,红菱心甘情愿地让他占便宜。第三个是戴教官,受伤后是这群女人们给他以慰藉和照顾,从温柔乡醒过来后,却懊悔自己作为一名军人和一群“胭脂水粉”厮混在一起。在这几位男性的眼中,这些女人是被需要又被厌弃的客体。她们被视为“低贱”的人,永远处于底层,遭受唾弃;而与之发生关系的男性,却可以被认为是“一时糊涂”,而得到原谅。在这暂时安宁的教堂里,她们是避难的难民,但也是被压迫、被贱视的女人。
(二)被“灵肉分离”的女大学生
正是这些女人们无法颠覆社会对自己的刻板印象——“低贱”,女学生们才会竭力维护社会对自己的刻板印象——“纯洁”。她们强调自己与这群女人们的不同,把自己置于其对立面,却矛盾地对这群女人的身体入迷。因为在这些女人身上,她们看到了自己身体的可能性。而女学生们在“刻板印象”的“袈裟”下,永远不会让这种可能性公开地发生在自己身上,她们要维护自己的形象。因此,女性从婴儿到少女,直至成年,始终都摆脱不了这种形象对自己的束缚,始终囚禁在精神牢笼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从而变成弗洛伊德所称的“被阉割的人”。[2]小说开篇描写孟书娟初潮来临时的身体经验。她对自己秘密器官的“复活”,感到恐惧,并为自己的经血感到耻辱,认为它是招致邪恶的源泉。孟书娟对自己的身体缺乏认识,或是错误地认识不仅是她缺乏相关知识的结果,也是权利对女性身体规训的结果。女性的子宫是女性所独有的,其特殊性在于它是“没有男性身体对应物的唯一的女性器官”。爱丽丝·杨在《正义与差异政治》中指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会将其他群体显露的差异塑造为“缺陷和否定”,以使其成为“他者(Other)”。从生理方面,女性的子宫赋予女性生育权方面的主动权。即从现实可行性而言,女性实际上享有生育决定权。而正是因为男性认识到自己不具备这种权利,企图把生育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父权制文化下,子宫才被塑造成恐怖的、黑暗的深渊;经血被认为是肮脏、邪恶、耻辱的源头。掌握不了的东西就贬低它、妖魔化它,这是父权制社会常用的戏码。由于深受父权制文化的影响,孟书娟认为自己的初潮招致了血腥的屠杀,而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厌恶感。
正确认识自己的途径被切断、被误导的结果是女学生身上体现出“灵肉分离”般矛盾的身体意识。孟书娟痛恨自己的身体,却对这群女人的身体无比着迷。女人们曼妙的身姿让女学生们看得如痴如醉。女学生们会在暗地里讨论这群秦淮河上的女人们的长相和身材,并给她们排名。因而,这群女人们成为被“凝视”的客体和欲望投射的对象。被教化的女学生把自己对身体可能性的幻想,投射到这些女人们身上,让她们代替自己实现这种可能性,又在清醒时,厘清了自己与幻想的界限。这种“灵肉分离”现象体现了女学生思想被束缚,本性被压抑,进入一种被“阉割”了的无能状态,在年龄上和行动上都成了弱者,需要被保护。
总之,无论是女人还是女学生,在“暴风雨”吞没这座教堂前,她们都受到了不同形式的性别压迫。
二、战争环境下凸显的性别差异
玉墨心里发出一个惨笑:难道她们没听说?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都成了日本畜生口中的“花姑娘”。[1]战争可以抹除女性在年龄、地位、声誉、职业等等方面的差异,却无法忽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这种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地对他国女性的侵害,体现了女性柔弱、不具威胁性的刻板印象在两种文化里的相似性。讽刺性地反映了受压迫女性群体之大。在日军所建的慰安所里,充当慰安妇的不仅有中国的女性受害者,还有日本妇女。战争是男人的游戏,女性在战争中诸如粮食、汽油、古玩等一样属于“战利品”。在作品中,男性被日军视为具有威胁性的敌人而被杀死。他们虽死得惨烈,但也算得上干脆利落,往往是一枪或一刀毙命。而女性不一定会死,但一定会经历非人的、“战利品”般的折磨。十四岁的豆蔻被日本兵暴打、蹂躏、还被拍下照片,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赴会救人的女人们要么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要么被囚禁在慰安所染病而死、要么必须整容才能重新活下去。“战利品”的待遇在日军那里就是被分享、被炫耀、被玩弄、被折磨,或者被摧毁。战争中的女性,依然是女性,她们因自己的“性”特征遭受更多的折磨,既受战争的摧残,又受男性的虐待。而承受双倍痛苦的原因,仅仅因为她们与男性的生理差异。她们的力气不如男性大,属于弱者。在战争环境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被反复践行。在战争中,与男性遭受不同的“待遇”,暴露了女性的性别劣势,在不同文化里有着共通的部分,女性从属于男性,是次等性别。男性可以与敌人一决高下,可以自己终结生命,具有主动性,属于主体。女性是待宰的羔羊,她们的生死不由自己决定,十分被动,属于客体。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始终存在,在战争的聚光灯下,这种压迫被凸显出来,变得更为直白,更加显眼。无论在何种文化里,这种性别优越感来源于暴力崇拜。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是全盘占领的。[3]可事实上,男性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钢筋铁骨,他们在泄欲后,经历“贤者时间”,把对自己的厌恶,马上转嫁到女性身上,轻者变得冷漠,重者变得暴力。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小说中,会出现“剖开肚子的赤身女人” [1]。战争暴力犹如一束聚光灯光,让性别差异和性别压迫赤裸裸地凸显出来。
三、被消失的“英雄”
并不是所有秦淮河女人们都大义凛然,要去保护弱者,因为她们中的一些人和女学生年纪相仿。她们也畏惧死亡,也珍惜自己的生命。她们最终舍弃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同胞的性命,并非被赵玉墨故意刺激其他同伴所说的那样,“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留着有人疼有人爱吗?”而是“不能看着日本人把那些小丫头拖走去祸害!”[1]这不是保护处女的行为,这是保护弱者的勇为;这不是对贞操的保护,这是对生命的拯救。
赵玉墨能第一个站出来,代替女学生去赴生死会,固然离不开她的善良,但也和她清醒的意识有关。她深知自己的社会阶层无法通过男人来改变,也知道她所处的社会对她们这类人的偏见有多大,来自社会的鄙夷一刻也没有放过她,久而久之,她们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救人的同时她们想赎罪,尽管罪不至死。没有天生的女人,更没有天生的妓女。正如红菱所说,她们扮谁都像,却唯独扮不像自己。可是社会却认为她们是天生的“害人精”。赵玉墨深知她改变不了社会对她们这群人的看法,而拯救女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带了对自己的“拯救”。把自己从世人的鄙夷下“拯救”出来。显然,对女学生的拯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对自己的“拯救”,付出的代价过高。除赵玉墨以外的女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赵玉墨也只能通过整容,成为另外一个人,才能活下去。小说结尾问道,赵玉墨为何要整容?或许是为了摆脱残酷的记忆,忘掉被折磨过的自己,摆脱世人的唏嘘也好,可怜也罢,问心无愧地重新开始。试想,如果男人从敌人的眼皮下死里逃生,那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啊,也可能是他很多年后炫耀的资本。可是女人,同样是拯救别人的英雄,从敌人的铁蹄下逃脱,却不得不改头换面,隐姓埋名。这一群拯救了同胞的女人,却只有通过“消失”(死亡或整容)才能拯救自己。而她们也热爱自己的生命,热爱生活呀!正如《二十二》里面的一位老奶奶所说:“这世界那么好看,我吃野菜也要看下去。”说到底,这场救赎,救了别人,却没能救了自己。
妓女们对女学生的拯救却不仅限于生命上的拯救,还有思想上的解放。孟书娟等人在后来一段时间里,都会说被认为只有妓女才能说出口的话,吵架也觉得用妓女的口头禅,骂人才过瘾。她们渐渐懂得男女之间的事儿,是很正常的生理需要,“谁还不撒不拉?”过去,在父权社会下,对女性贞洁的过分要求,导致她们对把男女性事看得过分神秘莫测,不敢提及。而与妓女相处的一周,对她们而言是思想上的解放。性需求像人对食物、水、空气和睡眠的需求一样,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只有剥开这层神秘面纱,女学生才会把注意力放到更高的需求上,而不是把自己束缚在贞洁的牢笼里。初出茅庐的女学生和历经人间疾苦的妓女,在小说的需求,有相似也有不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生理上,她们渴望食物,女学生会因为妓女的到来,分走她们的食物而懊恼,妓女会为了几个窝窝头,出卖自己。在安全上,她们都惧怕死亡,需要庇护。在爱与归属感的层面,女学生们和妓女们各自的内部都存在着友谊,然而,妓女却没有家的归属感。在尊重需求层面上,妓女們显然比女学生们更加渴望得到尊重。她们一直处在社会底层,被人鄙视,来自别人的尊重显得更加奢侈和稀有。所谓欲盖弥彰,赵玉墨等人缺乏来自别人的尊重,就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可终究发现奢华的外表无法改变世俗的看法。在小说末尾,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自己那被人唾弃的形象。
小说把战争环境下,人们缺衣少食的状态到精神上的追求都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们不禁感叹时势造英雄。妓女们希望通过牺牲自己,来拯救女学生的生命,她们成功了,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与此同时,企图通过自己大义凛然的行为,来颠覆人们对自己“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因为人们对她们的英雄事迹,唏嘘多于赞美。这是为什么赵玉墨不得不改头换面,忘记自己的名字,才能重新活下去。因为社会进步的速度,大众对一个观念的接受度,有时依然太过缓慢。人性的阴暗面,告诉了她,人们可能会同情她的遭遇,感叹她的壮举,但这种同情和感叹,把她也排除在外了,她会成为大家私下的谈资,比起那些华而不实的感叹唏嘘来,她更愿意被大众无差别化的接纳,反而这样,她才能平平淡淡地活下去,否则别人一个异样的眼光,都能迅速把她送回可怕的深渊,无论过去多久都是如此。本是救人的英雄,也不敢邀功,只能选择默默无闻地活下去。
四、结语
《金陵十三钗》揭露的不仅是女性做为人被战争压迫和践踏,更是作为女人被剥夺尊严。作者对战争的直接描写,所用笔墨远不及对父权社会下被降级的女性的描写。而这种性别压迫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直白。对理想型女性的要求——“娼妓其内,淑女其表”,其实是男性利己主义的表现,而女性是不可能同时真正具备这两点的。
小说把被社会划分开的两类女性都拉了进来,无论是秦淮河女人,还是女学生,她们都遭受到了性别压迫。战争会结束,而女性所受的精神折磨却从来没有结束。而这种折磨从根源上讲,是长久以往,人们固有的偏见强加的,不过在演进过程中,被女性内化了,成为自己跨不过去的一道坎,救人英雄却只有沉默,只有消失,只有逃避,才能活下去。
战争已经过去,思想得到解放,再回首去看这部作品,依然可以从里面挖掘一些有益于人们当下生活的思考。第一,在极端环境里,不要高估人性。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在战争环境里,人类可以对自己的同类做出无异于动物一样的行为,人类文明在此时此地荡然无存。第二,女性意识的觉醒始于正确地认识周遭的事物。正确的认识,意味着借助生物学的知识认识自己,认识男性,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女性地位的变化,才能理解自己当下所处的位置,追根溯源的同时,探索更多促进性别平等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2](澳)杰梅因·格里尔.女太监[M].欧阳昱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3]傅守祥,陈然然.国殇叙事中的女性创伤书写——以《金陵十三钗》与《南京安魂曲》为例[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02):59-66.
[4]Stein E,Kim S.Flow:the Cultural Story of Menstruation[M].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9.
2583501705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