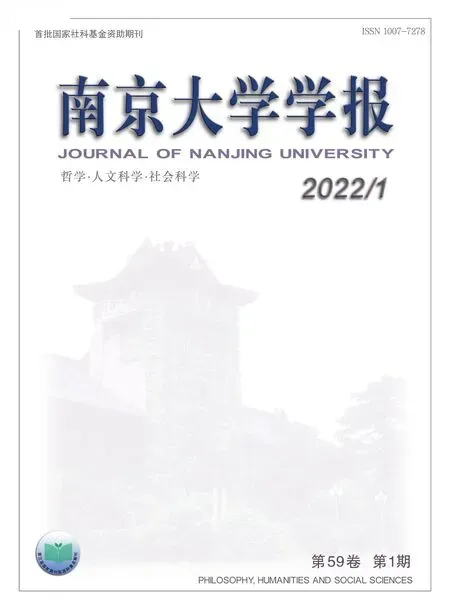何谓现象学的心理学?
倪梁康
(1.浙江大学 哲学系, 杭州 310058;2.浙江大学 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 杭州 310058)
引 论
1925年夏季学期,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做了题为“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的讲座。他在其中对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讨论,给这一已经延续了1/4个世纪的问题以一个当时看来是了断、现在看来是小结的回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塞尔在这里既非第一次处理这个问题,也非最后一次阐述这个问题。他从起初的任教资格论文《论数的概念》(1887年)开始,直至最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6/37年)期间,都需要一再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在“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讲座中的讨论与阐述仍然是胡塞尔本人给出的对此关系最为详尽、最为系统的说明。只是胡塞尔在他生前并没有发表这个讲座稿。直至1968年,该讲座稿才由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组织,经瓦尔特·比梅尔(Walter Biemel)编辑,连同胡塞尔于1925—1928年期间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现象学”条目以及1928年以“现象学的心理学”为题的阿姆斯特丹讲演等几个内容相关的文本一起,作为《胡塞尔全集》的第九卷出版(1)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8. 中译本见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心理学:1925年夏季学期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下面对该书的引述参考了这个译本,偶尔有一些修改,不再一一标明。。
事实上,不仅在胡塞尔那里,而且在他去世之后,直至今日,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一种不得不一谈再谈的老生常谈。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现象学和现代心理学产生以来的100多年时间里,它们各自都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随着这些发展而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一再以新的面目出现,一再受到重新理解和解释。无论是在胡塞尔所处的时代,还是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它们都一再地被提出并一再地被思考,无论是在现象学这一边,还是在心理学的另一边(2)这里所说的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讨论,首先是指一种为了向起源回溯而进行的关于胡塞尔本人在这两者关系理解上的思想发展之讨论,例如:Elisabeth Ströker,“Phänomenologie und Psychologie. Die Frage ihrer Beziehung bei Husserl,”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37(1), 1983, SS.3-19。其次,这个讨论也会涉及一些可称作现象学的心理学家或一些可称作心理学的现象学家的工作,这些工作会在现象学与心理学之间的间域进行,并为它们的相互关系添加新的内容并为新的讨论提供素材,例如:Aron Gurwitsch,The Collected Works of Aron Gurwitsch (1901-1973), Volume Ⅱ: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y,Dordrecht / Heidelberg / London / New York: Springer, 2009.最后还会包括对在现象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自就此关系所做的不断延续和不断更新的讨论,例如:Carl Friedrich Graumann,Grundlagen einer Phänomenologie und Psychologie der Perspektivitä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0; Herbert Spiegelberg,Phenomenology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eter D. Ashworth, Man Cheung Chung,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 Springer, 2006; Ian Rory Owen,Phenomenology in Action in Psychotherapy: On Pure Psych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Psychotherapy and Mental Health Care,Heidelberg / New York / Dordrecht / London: Springer, 2015,等等。。
一、现象学与出自经验立场的意向心理学
胡塞尔本人是在现代心理学形成的初期进入哲学领域的,并从一开始便受到几位重要的心理学家的影响。他的两位哲学老师布伦塔诺和施通普夫都是现代心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对胡塞尔的影响要远甚于他的另外两位数学老师:魏尔斯特拉斯和科尼西贝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胡塞尔在其哲学思考的初期,即《算术哲学》时期,试图用心理学来为数学—逻辑学奠基的做法。但理论上的困难迫使胡塞尔在此后的《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开始检讨和批判自己原先的所谓“心理主义”的观点,并转向其对立面“反心理主义”的立场,这个立场被冯特误解为某种意义的“逻辑主义”。不过《逻辑研究》第二卷对意识体验的大量讨论以及描述心理学与意识现象学观念的提出,又使得胡塞尔看起来仍然无法摆脱与心理学的纠缠,利普斯甚至认为有必要再讨论一下《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的心理主义”问题(3)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 Bd. Ⅱ,The Hagu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S.121.。
这两方面的误解都与现象学在心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的特殊位置有关。这也涉及学科划界的问题。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对现象学与心理学和逻辑学的关系理解可以在如下概括表述中找到:
纯粹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一方面,纯粹现象学为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做准备。它分析和描述(特别是作为思维和认识的现象学)表象的、判断的和认识的体验,心理学应当对这些体验进行发生上的说明,应当对它们的经验规律关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现象学打开了“涌现出”纯粹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泉源”,只有在把握住这些基本概念和观念规律的来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赋予它们以“明晰性”,这是认识批判地理解纯粹逻辑学的前提。(4)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 Ⅱ/1,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4, A 4.
后来在《逻辑研究》1913年的第二版中,胡塞尔的这个理解也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提出于1901年的说法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胡塞尔在1905年提出现象学还原并完成超越论转向之后的某些因素: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心理学,现象学借助于本质直观或本质还原从而是本质科学、先天科学,是本质心理学,也是反思的心理学。由于意向性是意识的最普遍本质,因而本质心理学也可以被称作意向性心理学。而相对于作为本质科学、先天科学的逻辑学(形式逻辑),现象学借助超越论还原从而可以是反思的逻辑学、主观的逻辑学,也是超越论的逻辑学。
现象学在此意义上可以为心理学和逻辑学做两方面的奠基。一方面是先天的奠基:事关经验心理学如何可能,如何奠基于本质心理学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超越论的奠基:事关形式逻辑如何可能,如何奠基于超越论逻辑学中的问题。
然而,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与其说是随《逻辑研究》的发表而得到了回答,还不如说这个问题随《逻辑研究》中现象学观念的倡导而刚刚被提出来。因为在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上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尤其是在前一个奠基方向上,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版发表之后很快就做了一些自我批评和自我修正。例如在1900年的第一版中他将现象学等同于“描述心理学”,但在1913年第二版中则收回了将现象学标示为描述心理学的“误导做法”(5)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 Ⅱ/1,A 18、B ⅩⅢ.。他承认对现象学运作的阐述没有能够正确地评价“现实地被进行的这些研究的本质意义和方法”(6)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 Ⅰ,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75,B ⅩⅢ.。潘策尔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的《编者引论》中指出:早在1902/03年冬季学期关于“认识论”的讲座中,胡塞尔就已经对描述心理学和现象学的关系做了重新反思,而且还在其研究手稿中明确表明:“心理学—客体化的兴趣将现象学转变为描述心理学……但现象学可以并且应当被视作纯粹本质学。从观念来看,它不是心理学,也不是描述心理学。”(7)胡塞尔文库手稿编码:Ms. F I 26/12a.
胡塞尔究竟是基于哪些在此期间新获得的明见性才发现了这里的问题并做出这个修正,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转变一方面与他对描述方法的新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作为描述方法之对立面的发生方法的新理解有关。这意味着,在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上,胡塞尔从一开始,甚至在《逻辑研究》前的《算术哲学》时期,就强调现象学不同于心理学的关键在于本质直观、范畴直观、观念直观、先天直观或形式直观,无论是以意识现象学的名义,还是以直观逻辑的名义,或是以直观数学的名义(8)E. Holenstein,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Teil.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SS.ⅩⅩⅩ-ⅩⅩⅩⅠ. 这里需要一再强调,胡塞尔所说的作为现象学“一切原则之原则”的“直观”概念是“Anschauung”,它原则上有别于“直觉”(Intuition),无论是在直觉逻辑的意义上,还是在直觉数学的意义上。尽管胡塞尔偶尔也将两者等同使用,但它们在德文和中文中所表达的根本不同的含义是需要随时留意的。详见笔者的文章:《关于几个西方心理哲学核心概念的含义及其中译问题的思考(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只是在对本质直观方法的具体展开解释上,他的观点才有所变化。
首先就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来看,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版发表之后不久就不再将现象学称作“描述心理学”,并在这点上偏离了他的老师布伦塔诺,也偏离了他后来结识的狄尔泰。
胡塞尔不再使用“描述心理学”的原因是他在此期间注意到,描述的方法也可以被经验心理学运用,因而它无法将本质现象学区别于心理学。在此之前,布伦塔诺于1874年发表他的代表作《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强调心理学的方法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方法(9)Franz Brentano,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I,Hamburg: Felix Meiner, 1955, S.39 ff.,而后他首次在1887/88年讲座中阐释“描述心理学”,即“一门对我们的现象进行分析描述的心理学”;他在1888/89年的讲座中还将“描述(deskriptive)心理学”等同于“描述(beschreibende)现象学”(10)Franz Brentano,Deskriptive Psychologie,Hamburg: Felix Meiner, 1982.。因而在布伦塔诺那里,正如他的另一位学生,也是胡塞尔的激烈批评者奥斯卡·克劳斯(Oskar Kraus)所说:
描述心理学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经验的”,因为它建基于内经验之上;唯有描述心理学才需要对心理进程的经验与统觉,其目的也在于借助包含在这种经验中的直观而上升为更普遍的表象,完全类似于数学的情况,它要想获得对它的公理而言最基本的概念也不能缺少直观。……在如此获得的普遍概念的基础上,描述心理学直接地达到普遍认识,而且是“在无须任何归纳的情况下一举获得”。(11)Oskar Kraus,“Vorwort des Herausgebers,”Franz Brentano,Deskriptive Psychologie,S.ⅩⅦ f.
对于这里表述的布伦塔诺心理学基本立场,胡塞尔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逻辑研究》期间也的确这样做了,不论是以“描述心理学”的名义,还是以“本质现象学”的名义。但这恰恰与克劳斯对他的两位师兄胡塞尔与迈农(Alexius Meinong)的一个批评有关,即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以“复归”(wiederkehrt)的方式出现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与迈农的对象理论中;他以此暗示这两种学说并未提供比布伦塔诺心理学更多的新东西。但克劳斯同时又不无矛盾地指出:布伦塔诺与胡塞尔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布伦塔诺并不承认“观念的、无时间的、普遍的对象”是真实的存在;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对于布伦塔诺来说只是一种“臆想”(Fiktion)。至于胡塞尔与迈农都承认的先天对象的“先天性”或“本质性”,在克劳斯看来都仅仅涉及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而不涉及一个特殊的认识领域(12)Oskar Kraus,“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Franz Brentano,Deskriptive Psychologie,S.ⅩⅨ ff.。
就此而论,布伦塔诺意义上的“描述心理学”是经验心理学。这对于克劳斯来说,而且对于胡塞尔来说也意味着:如果胡塞尔接受这个概念,他就继承了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而如果他将现象学理解为本质心理学,那么他实际上就背叛了布伦塔诺,因而不应该再使用这个概念。胡塞尔显然在《逻辑研究》第一版出版后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克劳斯是在20多年后(1924年)编辑出版布伦塔诺的《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第一卷时才在《编者引论》中表达了这个观点。由此看来,胡塞尔不应当是因为受到克劳斯批评的影响才中止使用“描述心理学”概念,而更可能是出于自己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和做出的决定。
然而,由于这个概念的使用与布伦塔诺及其学派有关,因此可以确定一点,在概念使用上的校正与胡塞尔对自己以及对布伦塔诺及其学派的重新理解有关。他在1901年7月7日致师兄马尔梯(Anton Marty)的信中还将“现象学的”等同于“纯粹描述心理学的”;但在1902年5月11日写给他的老师兼师兄施通普夫的信中就已经对自己刚出版的《逻辑研究》自我批判地写道:“在表述中令人感到有所干扰和有所不足的地方在于,在各种‘普遍性意识的形式’的关系上没有做出最终的澄清,而为了区分这些形式所需进行的描述分析则可以说是完全缺失。”(13)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 Bd. Ⅰ,SS.78、169.
由此看来,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版发表之后自己就立即注意到,从布伦塔诺那里接受过来的“描述的方法”没有被或不能被有效地运用在对意识体验的本质把握或观念抽象上。在这里讨论的于1/4个世纪之后的“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讲座中,胡塞尔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布伦塔诺及其学派的成熟看法:
虽然几世纪以来心理学已经是奠定在内经验基础上,并且有时候也意图成为一门关乎纯粹意识给予性的描述心理学。在此,我甚至不能把布伦塔诺及其学派排除在外,虽然他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引进意向性以作为心理之物的描述性根本特质。于此,他呼吁将经验心理学的构成奠定在一个系统而首先是纯粹描述的意识研究之上。但纯粹意识分析的真正的意义及方法却始终对他隐而不显。(14)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309.
当然,除此之外,在这里也可以考虑霍伦斯坦提到的影响因素,即与布伦塔诺及其学派无关,但与纳托尔普的新康德主义学派有关的影响因素。他认为胡塞尔的这个自我校正与他的超越论现象学还原有关:
胡塞尔在1903年就已经不再同意用描述心理学来标识他的认识体验的现象学分析。这个做法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描述心理学将它所研究的体验和体验类理解为人的体验和体验类,即是说,理解为在客观—时间上可规定的自然事实,而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分析则将任何关于心理体验的心理物理的和物理的依赖性的假设连同对物理自然的实存设定都悬置起来。(15)E. Holenstein,“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Teil,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S.ⅩⅥ.
不过,即使承认这个将胡塞尔潜在的超越论转向提前了几年的观点有其一定的道理,它也只能是导致胡塞尔放弃“描述心理学”概念与方法的一个次要原因:对实在设定的排除要求。而对经验事实的排除要求是导致胡塞尔放弃描述心理学概念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描述方法,而仅仅意味着他放弃经验的描述方法。他仍然会使用本质描述的方法,并在此意义上使用“描述现象学”的名称(16)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320.。
二、现象学与精神科学的理解心理学
在现象学与心理学关系问题上,1905年与狄尔泰的结识是另一个影响胡塞尔思想发展的重要事件。虽然狄尔泰与布伦塔诺一样,都倡导描述心理学的观念与方法,但他们之间看起来并没有相互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他们都使用“描述心理学”的概念,但他们对描述的方法与描述的对象的理解都不尽相同。
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讲座的历史回顾部分是从狄尔泰开始的,而后才在讨论《逻辑研究》时涉及布伦塔诺及其学派。这也说明狄尔泰在此问题上对胡塞尔的影响有多么大。
比梅尔在“编者引论”中已经对此开端做出说明:
讲座开始于对狄尔泰的讨论。这件事之所以合理,原因不在于胡塞尔是透过狄尔泰找到了通向心理学的途径,在这方面布伦塔诺和施通普夫更有贡献。当我们看到胡塞尔将《逻辑研究》一书献给卡尔·施通普夫时,它并不只是表面功夫而已。从本册的讲稿我们甚至得知,胡塞尔原本是未曾阅读过狄尔泰的著作的,这是受到艾宾浩斯的负面批评的结果。但狄尔泰本人却架起桥梁,与胡塞尔建立起联系(17)比梅尔的这个说法现在需要得到修正,并非是狄尔泰与胡塞尔建立起联系,而是他开设了《逻辑研究》的讨论课,胡塞尔得知此事后去柏林拜访狄尔泰并随即建立起两人之间的联系。,因为在狄尔泰看来,胡塞尔同样在他所追求的精神科学奠基工作方面下了功夫。从历史的回顾来看,该重视的是狄尔泰,而非施通普夫,因为胡塞尔总结说,狄尔泰曾在对抗实证论上面做出巨大贡献,尤其是就将心理学视作精神科学这点来看,贡献更是显著。(18)Walter Biemel,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ⅩⅥ.
比梅尔在这段话中集中概括了胡塞尔在讲座中就自己所受的两方面影响的回顾阐述: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心理学与布伦塔诺的出自经验立场的意向心理学。但这里还有几个要点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展开说明。
首先,狄尔泰对胡塞尔的影响是在独立于布伦塔诺的情况下发生的。他在1894年发表的《关于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长文中,提出并论证了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奠基的任务以及这门心理学的方法基础(19)Wilhelm Dilthey,“Ideen über eine 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 Psychologie,”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vorgetragen am 22. Februar und am 7. Juni 1894, Berlin.。他在这里并没有也无法去诉诸布伦塔诺或马赫的描述心理学的观念,而是自己在这种描述和分析的方法中看到了划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关键所在。由于自然科学连同各种将心理当作“自然”来研究的心理学学科,如物理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化学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其所诉诸的无一不是因果解释的方法,例如通过外部的物理刺激或内部的生理反应来解释特定的心理活动和意识行为;而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则将精神视作不同于自然的现象,强调需要通过自己特有的方法,如在反思、理解、“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中“描述和分析”心理现象和精神现象,因而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由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而需要在基本方法上各行其道。因此,胡塞尔对狄尔泰的这篇长文评价说,它是“针对自然主义心理学的首次抨击;是一项天才的,即使尚未完全成熟的工作,是在心理学的历史中始终不会被忘却的工作”(20)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6.。在胡塞尔这里所做的有所保留的评价中,包含了多重的含义。它们主要涉及精神科学心理学的描述方法和经验性质。
首先要提到的是,海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在狄尔泰的长篇论文发表两年后,从自然科学的实验心理学方面对狄尔泰进行反驳回应,他在自己主编的《心理学与感官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对狄尔泰的批评长文《论解释的和描述的心理学》(21)Hermann Ebbinghaus, “Über erklärende und beschreibende Psychologie,”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und Physiologie der Sinnesorgane,9, 1896, SS.161-205.。这里最主要的批评在于,狄尔泰将描述的方法视作精神科学特有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中,在经验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中早已得到了有效的使用。艾宾浩斯本人便同样使用描述的方法创立了记忆心理学。他以自己为主试者和受试者进行的记忆力实验以及借此而确立的“遗忘曲线”使他成为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因而并非如狄尔泰所说的那样仅仅依据因果解释的方法,而是同样也使用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从今天的视角来审查这场争论,那么一方面当然可以说,艾宾浩斯在记忆心理学案例中实施的实验方法,并不能算是自然科学的客观心理学的实验方法,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科学的主观心理学的实验方法;这里姑且对此置而不论(22)笔者在《意识问题的现象学与心理学视角》一文中对这场争论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倪梁康:《意识问题的现象学与心理学视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而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描述”概念本身的定义在狄尔泰那里始终模糊而不确定,故而难以成为他倡导的精神科学心理学的方法基础。总的说来,描述的方法既可以是经验的和实证的,也可以是反思的和实验的,甚至可以说,描述的方法既可以运用于“主观心理学”,也可以运用于“客观心理学”。这可能是狄尔泰后来放弃对艾宾浩斯进行反驳和回应的打算,从公共讨论中归隐,回到对自己的精神科学的观念与方法的专注思考与研究中的原因之一。因而这场争论给世人留下的印象可以说是“艾宾浩斯曾严厉批判过《描述的与分类的心理学》,而狄尔泰不知道如何应对他的批判”(23)鲍伊斯·吉布森:《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1928年弗莱堡日记节选》,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25页。。
因此,可以想象狄尔泰在读到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时的兴奋之情。应当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他主张的“描述心理学”的理想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心理学”中的实现。用胡塞尔在1925年讲座中的话来说,“尽管《逻辑研究》是在与他(狄尔泰)自己的著作极不相关的情况下产生的,他却看到了他自己的‘关于描述的与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首度具体地展示在《逻辑研究》中”(24)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34.。
然而如前所述,胡塞尔于此期间(1901—1905年)已经发现用“描述心理学”来标示“现象学”带来的问题,并计划对它做出修正。胡塞尔必定于1905年在柏林拜访狄尔泰时已经向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因而按照胡塞尔太太马尔维娜的回忆,狄尔泰在随后于哥廷根回访胡塞尔时曾对她说:“仁慈的太太,《逻辑研究》是哲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引导。这部著作还会经历很多次再版,您要运用您的全部影响,使它不被修改,它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碑,必须始终将它如其在被创造时的那样保存下来。”(25)马尔维娜·胡塞尔:《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平素描》,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第22页。
事实上,在与狄尔泰初识的这段时间里,胡塞尔不仅将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的观念,而且也已经将自己《逻辑研究》中的“描述心理学”的观念视作“尚未完全成熟的”了。因而即使有狄尔泰的忠告在前,他对《逻辑研究》的修改也仍然势在必行。
不过胡塞尔从狄尔泰那里的确获益良多,不仅是在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观念和方法的总体构想方面,而且也在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以及“理解心理学”概念对发生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的推进方面。
胡塞尔在1925年的讲座中指出:狄尔泰所设想的精神科学可以分为历史的和系统的两个部分。构成系统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主要是“描述的分析的方法”,而历史的精神科学所使用的方法则被称作“理解的和说明的方法”,它涉及在精神生活中展现出的个体性与历史性。与此相对应,为精神科学奠基的心理学也可以分为两种:描述心理学和“理解心理学”(verstehende Psychologie)。这里的“理解”,也是在狄尔泰与约克(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的通信中一再讨论的“理解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 verstehen)意义上的“理解”,而且它也构成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解”(Seinsverständnis)思想的主要来源。胡塞尔在1925年讲座中对此予以充分肯定:“狄尔泰的阐述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他针对作为一个体验整体的心灵生命之整体提出正面说明,并在于提出一个纯粹直观创造的描述心理学之相关的要求:也就是一种尽管只是‘单纯’描述的,却仍然能够完成一种特有的最高说明成就的心理学,即狄尔泰用理解一词来表达的那种说明成就。”(26)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10.
狄尔泰在“理解和说明”的心理学方法上对胡塞尔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它推动了胡塞尔后期在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方向上的思考和研究。值得留意的是,这个推动早在1905年就已经发生。到1910年胡塞尔撰写《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长文时,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历史理解方向和方法已经在胡塞尔思想中有了相当成熟的结果,他在这里对狄尔泰在此思考方向上的功绩做了总结性的阐释:
如果我们通过“内心直观”(innerliche Intuition)而生活到一个精神生活的统一中去,那么我们就可以“追复感受”(nachfühlen)到那些制约着精神生活的动机,并且因此也可以“理解”各种精神构形的本质和发展,理解这些构形对精神的统一动机和发展动机的依赖关系。以此方式,所有历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在其“存在”特性中“可理解的”“可说明的”,这种存在就是“精神的存在”,就是一个意义所具有的各个内部自身要求的因素的统一,并且在此同时也是那些根据内部动机而合乎意义的自身构形和自身发展的统一。即是说,以此方式也可以对艺术、宗教、道德等进行直观的研究。同样也可以对那个与它们相近并在它们之中同时得到表达的世界观进行直观的研究,一旦这种世界观获得科学的形式并以科学的方式提出对客观有效性的要求,它便常常被称作形而上学,或者也被称作哲学。因此,在这些哲学方面便产生出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透彻地研究(精神生活的)形态结构、它们的类别,以及它们的发展联系,并且通过最内在的“追复生活”(Nachleben)而使那些规定着它们本质的精神动机得到历史的理解。狄尔泰的著述,尤其是最新发表的关于世界观类型的论文表明,在这方面有多少极为重要的事情,并且事实上也是值得赞叹的事情有待完成。(27)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1-1921,The Hague &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86, S.42.
尤其是胡塞尔在这段引文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值得注意,它是胡塞尔的由衷之言,也涉及胡塞尔在随后几十年里一再去努力完成的工作。十多年后,他在1927年12月26日致曼科的信中甚至说:“但从这一部分(《观念》第一卷)就可以看出,对我来说,现象学无非就是这门普全的‘绝对的’精神科学。”(28)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 Bd. Ⅲ,S.460.进一步看,胡塞尔在这里尚未说出的是他已请埃迪·施泰因编辑完成但还无意出版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以下简称《观念》)第二卷和第三卷,它们更应当被视作现象学哲学作为精神科学的自身宣示。
应当说,《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三卷本标题中的“纯粹现象学”与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和“理解心理学”的功能相似,而“现象学哲学”则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并行不悖。
比梅尔曾指出,对于“现象学与心理学”这个论题而言,胡塞尔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具有重要的意义(29)W. Biemel,“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ⅩⅦ.,后面笔者会阐释他为此给出的具体理由。但这里先要对此说法给出一个其他的理由:如果说胡塞尔在狄尔泰的“描述和分析的心理学”中看到的是系统的(静态结构的)精神科学的基础,那么他在狄尔泰的“理解的和说明的心理学”中看到的便是历史的(变动发生的)精神科学的基础。现象学与心理学在心理结构与心理发生两个方向上平行而行。这里要预先说明:这两个方向原则上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二阶系统”,与它们相对的一阶系统是“自身反思”或“自身思义”的总方向。
就狄尔泰所说的精神科学心理学的“理解和说明”方法而言,它与对动机的追复理解与动机引发线索的追踪说明有关。胡塞尔后来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提出的静态现象学的描述方法与发生现象学的说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批判性继承(30)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 Bd. Ⅺ,S.340.。在这里,心理学的认识方法的差异导致心理学类型的差异;而且在相同的意义上也可以说,现象学的认识方法的差异导致现象学类型的差异。
在结束这一节之前还有必要做两方面的简要说明:其一,描述与理解作为精神科学心理学的两种方法并非各行其是,互不干涉。无论在狄尔泰那里还是胡塞尔那里,它们都可以互补地既运用在意识结构或精神系统的研究上,也可以运用在意识发生或精神历史的研究上(31)胡塞尔在哥廷根和弗莱堡的学生、后来博士论文以《约克的历史哲学》为题的弗里茨·考夫曼在跟随胡塞尔学习之前曾在莱比锡学习,他回忆说:“在莱比锡,由于狄尔泰的学生施普朗格的引导,我是按照‘理解的描述’(verstehendes Beschreiben)的视角来熟悉现象学的。”考夫曼:《回忆胡塞尔》,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第44页。。如胡塞尔所说,描述也可以是“对在每一个被发展的人类心灵生活中,那个以相同形式出现的组成部分与脉络的描述”。他借用狄尔泰的话说:“我们解释自然,但却理解心灵和精神生命:进行理解乃是所有历史与系统精神科学之任务,这些精神科学因此正是可回溯到那个描述的,即分析的心理学去而作为理解的基本科学。”(32)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 Bd. Ⅸ,S.14.
其二,狄尔泰与胡塞尔所说的“理解与说明”方法中的“说明”(Erklären),也可以译作“解释”,但它不是艾宾浩斯在其批评论文中所说的“解释”(Erklären),即不是自然科学心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解释”,而是历史的精神科学与发生现象学意义上的“动机解释”。前者意味着通过因果法则来解释一个心理现象产生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外部原因,例如荷尔蒙的分泌对人的情感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或解释一个心理现象会引起或导致的各种生理物理数值的变化,例如撒谎的意识行为所导致的脸红和心跳加速等。后者则是在纯粹的直觉的内心经验中、在普遍有规律的心灵生活与精神发展脉络中被追踪和被解释,例如一个表象如何会引发一个审美享受,对他人痛苦的同感如何会引发自己的怜悯意识,如此等等。
三、现象学的特质:相对于布伦塔诺和狄尔泰的心理学
这里需要回到前引比梅尔的说法上,即《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对于理解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个说法在他那里得到了补充说明:“诚然,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胡塞尔在现象学的构造阶段特别重视将他自己的工作与其他人的工作划清界限,而且恰恰是与他看来非常接近的人的工作。《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篇‘逻各斯’论文就是胡塞尔的一篇论战文章,是这位哲学家在找到自己的道路之后将别人的道路揭示为歧途的论战文章。”(33)W. Biemel,“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ⅩⅥ.所谓“别人的道路”,主要是指胡塞尔在文章中批评的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心理学的“历史主义”道路。正是通过胡塞尔对自己与他人的差异的标明,他的现象学与他人的心理学的差异也随之得到了揭示。
如果前一节揭示的是胡塞尔如何在狄尔泰影响下转向历史的精神科学的方向,或者说,转向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方向,那么这一节要阐述的就是胡塞尔如何在这个方向上发现狄尔泰的不足以及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来加以弥补的过程。以此方式,现象学与心理学一般以及与特定类型的心理学的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彰显。这个情况在第一节讨论胡塞尔现象学与布伦塔诺的意向心理学时已经出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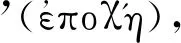
因此毫不奇怪,在《现象学心理学(及阿姆斯特丹讲稿)》(1928年)中,他直截了当地将现象学称作“描述现象学”,它的第一阶段是本我论的描述现象学(37)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320.,而在此之前于1923/24年所做的“第一哲学:现象学还原理论”的讲座中,他已经说明,这门“本我论(egologisch)的描述现象学”,或“超越论的本我论”,或“唯我论(solipsistisch)的现象学”,接下来会过渡到第二阶段的交互主体的描述现象学领域中(38)Edmund Husserl,Erste Philosophie (1923/4), Zweiter Teil: Theorie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56,S.173 ff.。可以看出,胡塞尔在此期间一直致力于对同样以描述为方法的现象学与其他心理学之间的关系的梳理辨析。在1925年讲座中,胡塞尔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理清他自己的描述现象学与狄尔泰和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的关系。在划清了它们之间界限的情况下,胡塞尔可以说,“经过几个部分的说明之后,我所引入的并非带着狄尔泰印记的心理学,而是,如同我已经宣告的那般,一门现象学的心理学”(39)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35.。
胡塞尔对狄尔泰的批评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文章开始,到1925年的讲座为止,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缺失:
其一,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心理学的经验科学性质及其在本质观点方面的缺失。
与对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立场的批评相似,胡塞尔对狄尔泰的批评也在于后者的精神科学的经验立场。
狄尔泰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的赞赏,是因为他看到的是作为描述心理学的现象学的成就,但他并没有看到作为本质科学的现象学的成就,而后者“谈论的是感知、判断、感受等本身,谈论它们先天地、在无条件的普遍性中作为纯粹种类的纯粹个别性所拥有的东西,谈论那些只有在对‘本质’……的纯粹直观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明察到的东西”(40)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 Ⅱ/1,B1 18.。因此,胡塞尔在1925年的讲座中将本质观点的缺失视作“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所包含的极大缺陷”,因为“他仍未见到基于直观、但也是本质直观的理由而来的一般本质描述之类的存在,犹如他也还没看到底下的事实,那个构成心理生活的极端本质──与意识对象的关系──乃是系统性的心灵分析由其作为本质的分析之本有而无尽丰富的主题”(41)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13.。
早在1910年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中,胡塞尔在批评了自然主义哲学之后进一步转向对包括狄尔泰在内的“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的批评。他在一个脚注中说明,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经验立场出发无法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性和客观有效性,而且最终只会导向历史主义的怀疑论,因为“一门还是经验的精神科学既不能对某个提出客观有效性要求的东西提出反对的论证,也不能对它提出赞成的论证”(42)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1-1921,S.45, Anm. 1.。而他在正文中的说法更为直白和激烈:“从历史根据中只能产生出历史的结论。从事实出发来论证或反驳观念,这是悖谬——用康德所引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从石中取水(ex pumice aquam)。”对于胡塞尔来说,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在历史事实中发现的“流动的起效用”过程以及建基于其中的文化现象的经验科学,另一方面是哲学家在历史发展脉络中把握到的“本质和客观的有效性”以及建基于其中的有效理论体系的科学(43)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1-1921,SS.45、44.,前者必须以后者为理论基础,否则它的归宿只能是历史主义的相对论和怀疑论。
而从狄尔泰这方面来看,胡塞尔的这个批评带有过于浓厚的柏拉图观念论与康德的先天论的烙印。他在此之前就强调:“康德的先天是僵死的,但我理解的意识的现实条件是活的历史过程,它们具有其历史,而这个历史的进程是它们对越来越精准地以归纳的方式被认识到的经验的杂多性的调整适应。”(44)Wilhelm Dilthey,Grundleg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Geschichte,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7, S.51. 关于心理学是经验科学的观点和主张尤其可以参见他的全集第21卷中收集出版的讲座“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第一部分“心理学与人类学讲座”。而在读到胡塞尔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后,他的反应可以在他于胡塞尔这篇文章页边所做的批注上看出:“真正的柏拉图!先是将变化流动的事物固定在概念中,然后再把流动这个概念补充地安插在旁边。”(45)Gerog Misch,“Vorbericht des Herausgebers,” Wilhelm Dilthey,Die geistige Welt: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Hälfte 1, Abhandlungen zur Grundlegung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0, S.CXII.
在胡塞尔这方面,他在前引脚注中继续写道:“如果将这种旨在经验理解的经验观点换成现象学的本质观点,那么事情自然就会是两样的,而这似乎正是他思想的内部活动。”(46)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1-1921,S.44.现在看来,这个对狄尔泰“思想的内部活动”的想象只能算是胡塞尔带有良好愿望的揣测。狄尔泰持有的一个明显的成见在于,他对观念、先天、本质的理解始终是柏拉图式的或康德式的,即将它们理解为僵死的和固定不变的,而历史、发生、精神是活的,流动不息的,因而与本质、观念、先天等无关,仅仅与杂多经验的丰富性和鲜活性有关。狄尔泰没有读到胡塞尔1905年便已讲授过的,但于1928年才由海德格尔编辑发表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也没有读到胡塞尔1929年出版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胡塞尔在这两部著述中都在尝试对在纵向本质直观中展现出来的历史发生之“本质和客观的有效性”进行本质描述:或者是对时间意识的三位一体形式的本质有效性,或者是对普遍意识结构与意识发生之超越论逻辑的本质有效性。
其二,狄尔泰缺乏对意向性的本质认识,更确切地说,缺乏对作为纵意向性的历史性的直观与理解。
狄尔泰的这个缺失与前一个缺失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狄尔泰在本质观点方面的缺失,他才无法看到意识最基本的本质特征:意向性。胡塞尔自己说:“狄尔泰似乎并未被布伦塔诺影响。他毋宁完全被他自己,特别是自己的精神科学兴趣领域支配而来到对于纯粹描述的要求。意向性的核心意义在他身上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47)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33.
事实上,狄尔泰没有注意到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其著述中虽然对布伦塔诺有所提及,但并无特别的关注。布伦塔诺对他的影响更多地是通过胡塞尔来完成的。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好友约克一再要求的“理解历史性”也没有在狄尔泰那里产生特别的效应。至少可以说,狄尔泰在“理解历史性”的方法思考与实施方面始终没有获得充分的自觉与自信。
不过,显然狄尔泰最终还是在胡塞尔那里看到了描述心理学的成就,即胡塞尔在布伦塔诺的描述的意向心理学影响下取得的成就。但他并未将此理解为对意向性的本质描述的成就,也不会将它与他和约克的意义上的“理解历史性”联系在一起,发展出在纵意向性方面的本质描述心理学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在胡塞尔那里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所谓的“历史性”,无非是指贯穿在历史进程中的规律性与意义的有效性,无论这里的历史是精神史还是自然史。在精神科学的历史现象学中,它是指胡塞尔自1905年起就开始关注的历史意识中的纵意向性,也是胡塞尔在后期《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所说的“超越论的历史性”(48)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S.213.。“理解历史性”在现象学中可以改写为:对历史意识中的纵意向性的纵向本质直观以及理解的本质描述。
其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心理学在“同感”或“交互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方面的缺失。
胡塞尔在1925年讲座中所确定的狄尔泰的第三个缺失在于:“狄尔泰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一个个体的心灵关系如何进入到其他的心灵关系之中,它们如何能够联结成一个结构关系。”(49)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548.他以此来批评在狄尔泰那里一门同感心理学的缺失。
狄尔泰并非没有思考和讨论过同感问题,并非没有考虑过个体的历史意识与集体的历史意识的关系问题,例如他在《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之建构》中便有“对其他各人及其生命表述之理解”的论述,讨论“理解”的各种类型——“设身处地”(Hineinversetzen)、“模仿”(Nachbilden)、“追复体验”(Nacherleben),等等(50)Wilhelm Dilthey,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Stuttgart: B. G. Teubner Verlagsgesellschaft, 1958, S.205 ff.。不过这些思考大都只是以手稿的方式记录下来,且在胡塞尔的时代还难以为他所知悉和了解。因此胡塞尔会认为:“狄尔泰在这一方面却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究竟在只是内经验或者只是对他人精神生命及群体生命的阐明的基础上如何能够产生一个比个人的理解更多的描述?”(51)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13.
胡塞尔在1905年,即在结识狄尔泰的这一年,已经开始在特奥多尔·利普斯的影响下思考和研究同感问题,后来同感问题被改称为交互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是横意向性研究和横向本质直观的一个分支。到1925年“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讲座时,胡塞尔对这个问题已经有20年的思考,并且已经培养了以《论同感问题》为题完成博士论文的埃迪·施泰因;而且在1925年期间,按耿宁的说法,在胡塞尔那里,“交互主体性理论第一次获得一种自成一体的、在内容上得到透彻加工整理的形态”(52)Iso Kern,“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Dritter Teil. 1929-35,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73, S.ⅩⅩⅩⅣ.。因此可以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对狄尔泰的发难和批评在当时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将自己的意识现象学的第一阶段称作“超越论的本我论”或“唯我论的现象学”,这也是狄尔泰的心理学所处的阶段,即他讨论内感知、内经验、自身思义等时所处的阶段。而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还原则为“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打开了通道,在这里,对其他个人的“同感”就意味着“对他们的动机的理解”(53)Edmund Husserl,Ideen zur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Bd. Ⅱ,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52, S.226.,这是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心理学尚未到达的阶段(54)不过,在狄尔泰和雅斯贝尔斯的“理解心理学”的具体实施者戈鲁勒那里,动机理解意义上的“同感”已经出现。Hans W. Gruhle,Verstehen und Einfühlen,Berlin / Göttingen /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1953, S.283.。
如果在狄尔泰那里,系统的精神科学采用的是“静态理解”(55)这是戈鲁勒引述的雅斯贝尔斯的说法,Hans W. Gruhle,Verstehen und Einfühlen,S.283.的方法,并且如前所述,在施普朗格那里是所谓“理解地描述”(verstehend beschreiben)的方法,而历史的精神科学则采用“历史理解”的方法,那么狄尔泰意义上的交互主体的精神历史、精神社会历史的方法就应当是“理解地同感”(verstehend einfühlen)的方法(56)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审核报告中提到:“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里的“了解之同情”若翻译为德语,基本上就是“理解的同感”的意思。这是否是陈寅恪在他两次留学德国期间(1910-1914年,1921-1925年)所受狄尔泰及其后学“理解心理学”影响的表露,目前尚不得而知,还有待进一步查究。。
四、现象学与经验论心理学、自然科学心理学、精神科学心理学的差异
通过与自然科学心理学、精神科学心理学以及布伦塔诺经验心理学划清界限,胡塞尔便对自己的现象学与种种心理学的关系做出了理清和说明。尤其是在现象学与心理学的相同性与差异性的各个层次方面,胡塞尔也表达了明确的态度和立场。
现象学与自然科学心理学、实证的和实验的心理学的差异已经十分了然,就像普莱斯纳在1914年便已经确定的那样。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对象上,现代心理学都已经放弃了那些如今由现象学来坚守的东西:对意识体验和意识权能在结构与发生两个方向上的反思和本质直观。早期现象学家如普凡德尔曾将他所理解的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区别等同于“主观心理学”与“客观心理学”的区别(57)Alexander Pfänder,Phänomenologie des Wollens. Motive und Motivation,Leipzig: J. A. Barth, 1900, S.6f.,并与他的现象学同道如胡塞尔和盖格尔等人一起为在客观心理学面前维护主观心理学的权利而耗费心力。此前十多年,在冯特、施通普夫、艾宾浩斯、詹姆斯等现代心理学的开创者那里,这两种心理学都还以互助互补的方式共处于一室。而此后十多年,各种类型的主观心理学与各种类型的客观心理学已经彼此分离、另立门户,既不再为彼此间的合作而费神,也不再为相互间的混淆而担心。
然而,现象学与各种主观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在此期间反倒成为这个特殊心理学群体内部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胡塞尔需要面对的是他的现象学与布伦塔诺心理学的关系问题。后者的意向的和经验描述的心理学一方面脱离了与哲学心理学有关的思辨哲学,另一方面也脱离了与生理心理学或心理物理学有关的发生心理学。在这两个方面,胡塞尔都无条件地予以接受。除此之外,他也采纳了布伦塔诺经验心理学的本质内核,即意识的最普遍的本质特征——意向性,但同时排斥布伦塔诺的经验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主义立场。胡塞尔在1925年讲座中对此有清晰的表述:“布伦塔诺对意向性的指明突破了在意向性方面的普遍盲目状态;但尚未克服自然主义,现在可以说自然主义是强占了意向体验并阻断了通往意向研究之真正任务的道路。”(58)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310.
胡塞尔不再将“描述”仅仅视作经验描述。他赋予现象学的描述以本质刻画的性质,从而可以谈论一门本质学说意义上的“描述现象学”。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实际上就是胡塞尔谈论得更多的、意义也更为宽泛的“本质现象学”或“现象学的心理学”。因为按照胡塞尔和盖格尔的理解,描述的基础是直观;本质描述的基础是本质直观。在直观与描述之间的关系与在意识现象学和语言现象学之间的关系都是平行的。而“本质描述的现象学”最终必须以“本质直观的现象学”为前提条件,因而这里存在着一种奠基关系。
除此之外,布伦塔诺指明的作为意识本质特征的意向性最终只是“横意向性”,即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的关系。但胡塞尔通过时间意识分析和意识发生分析而将意识的本质特征的概念扩展到纵向的维度:发生的和历史的维度。因而在胡塞尔这里,“发生”不再像他在《逻辑研究》第一版时期那样,意味着原初布伦塔诺意义上的生理心理的因果发生,而是指内在的心理发生、意识发生。通过纵向本质直观来把握在意识发生中的纵意向性和超越论逻辑,这是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不同于其他各种形式的发生心理学(包括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59)Eduard Marbach, “Two Directions of Epistemology: Husserl and Piaget,”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Vol. 36, No. 142/143 (4), 1982, pp. 435-469.)的地方。
其次,胡塞尔现象学与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关联是在纵意向性方面。胡塞尔应当是从狄尔泰那里接受了历史意识的向度,并且将它与此前从布伦塔诺那里获得的时间向度结合在一起。
然而,现象学在纵意向性的认识和把握方式本质上有别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描述心理学和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的描述方法。可以作如下概括:如果说胡塞尔现象学与布伦塔诺经验心理学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是用描述的方式来揭示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意向性或构造性(横意向性),那么胡塞尔现象学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心理学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在尝试用理解的方式来解释意识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流动性或历史性(纵意向性)。而后可以进一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求用横向本质直观和静态理解的方式把握横意向性,因此有别于布伦塔诺的心理学;同时要求用纵向本质直观或追复理解的方式来把握纵意向性,因而有别于狄尔泰的心理学。胡塞尔始终认为:狄尔泰与布伦塔诺在纵横意向性方向上的思考没有脱出经验论的巢穴,因而最终会在这两个方向上导向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
因此,无论是横向上的意向性描述,还是纵向上的历史性理解,现象学都必须——正如胡塞尔在1913年的《观念》第一卷中已经确定的那样——是“一门意识体验的描述本质学”(eine deskriptive Eidetik),即一门“现象学的本质学”(60)Edmund 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logie und phänomenlogischen Philosophie, Bd. 1,S.148 f.。而在这里讨论的1925年“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讲座中,胡塞尔更是明确地指出,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最终还会涉及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以及现象学与认识论的关系。即是说,这个意义上的本质学与数学、几何、逻辑意义上的先天科学相似,它是心理学领域中的本质学,必须实施一种“新型的、先天运行的心理学分析”,并构成“一门从纯粹内向直观中汲取的心灵科学”(61)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41.。
这里提到几何、数学等并非偶然。它们与现象学(现象学的心理学或纯粹心理学)一样,都是观念科学。这里可以看到胡塞尔的数学背景始终在起作用,看到莱布尼茨的普遍数理模式的潜在影响。无论是在《观念》第一卷中,还是在“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讲座中,他都一再指出,现象学的心理学与经验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应当类似于几何学、运动学、年代学、力学等与自然科学物理学的关系。尽管他认为,现象学的本质论不同于作为形式的本质科学的数学、算术等,而更应当像几何学、运动学等一样是质料的本质科学或质料的数理模式,因而或有可能讨论是否可以或必须“将现象学构造为一门意识体验的‘几何学’”,但现象学与几何学仍然在方法和对象上彼此有别,例如现象学诉诸本质描述,而几何学则主要以演绎的方式进行;现象学讨论体验的本质,而几何学揭示的是空间的本质,如此等等。无论如何,现象学与几何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探讨和处理的都是可能性问题,而非实在的事实。在此意义上,“现象学本身不是心理学,就像几何学不是自然科学一样”(62)Edmund 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logie und phänomenlogischen Philosophie, Bd. 1,SS.149 f、5.。这里的“现象学”,当然不是经验现象学或经验心理学,而是“现象学的心理学”或“纯粹心理学”。它们不依赖关于心灵生活的经验事实科学,但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基础。
现象学为心理学提供理论解释与论证的观点还可以在胡塞尔于1903年为埃尔森汉斯《关于逻辑学与心理学的关系》(63)Theodor Elsenhans, “Das Verhältnis der Logik zur Psychologie,”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109),1897, SS.195-212.撰写的相关德国逻辑学著作报告中发现,他写道:“显然,被排除的心理学统觉随时可以插进来,让现象学和认识批判的结果可以为心理学所用。因此,现象学分析获得了描述心理学分析的特征;它充当了对心理学这门关于精神显现的自然科学进行理论解释的基础。”(64)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Rezensionen (1890-1910),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9, S.207.此后他在1917年又写道:“每个现象学的确定作为关于意识和被意识之物的本质确定都可以被重新评价为心理学的确定。……纯粹现象学的每个结果都可以被转释为先天心理学或理性心理学的一个结果。”(65)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Rezensionen (1911-1921),S.117.
而由于心灵生活的流动性和历史性,因而现象学在这里面临双重的任务:不仅要在横向上对意识体验的结构进行本质描述,而且要在纵向上对意识体验的发生进行本质解释,即“建立起一门先天纯粹心理学,它具有类似于几何学等对于经验物理学所具有的那种功能。在其中包含的一个重大任务就在于对历史的以及对在它的独一性中包含的普全‘意义’的现象学诠释”(66)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252.。从这段出自1927年《不列颠百科全书》条目草稿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胡塞尔在这一年便已经有了一门关于历史意识的本质现象学的构想。在这里可以看到胡塞尔与狄尔泰的同行和分离的大致轨迹。
最后,胡塞尔的现象学首先是认知现象学和理性现象学,而非心理学一般。这是由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理解的意识最基本特征决定的,他们的心理学的最原本形式必定是意向心理学或表象理论和对象理论。用胡塞尔的话来说:“情感生活与意愿生活的现象学连同其特有的意向性是奠基在自然经验和认识的现象学之中的,它涵盖了在其必然的和可能的本质构形方面的全部文化以及属于社会性的本质形式的相关先天。”(67)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252 f.因而现象学在这点上也有别于一般心理学。即是说,现象学承载的首先是认识论奠基的使命,而后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才会朝向对情感行为、意愿活动等与文化社会相关的意识生活的描述分析。
在前引普莱斯纳的回忆录中,他记载说当他于1914年来到哥廷根时曾注意到,胡塞尔现象学始终还持守在认知现象学或理性现象学的范围内,尽管他的现象学同道已经各自在情感、意欲等领域展开工作。他回忆说:
讨论题目被紧缩在认知行为范围上,尽管莱纳赫、普凡德尔、舍勒、莫里茨·盖格尔已经突破了它,但胡塞尔却还并不懂得如何去摆脱它,因为他是在七十、八十年代的心理学与认识论上成熟起来的,而且不得不为了与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作战而付出其半生的心血。伦理学的、美学的、法哲学的问题离他甚远。感觉、感知(他向我特别推荐沙普和黑德维希·康拉德-马悌乌斯的典范研究)、错觉、抽象、判断和事态主宰着整个课程,尤其是讨论课,而且——如《观念》所表明的那样——还不仅仅是课程。(68)普莱斯纳:《于哥廷根时期在胡塞尔身边》,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第54页。
普莱斯纳的这个回忆虽然基于表浅的印象,但的确是对哥廷根当时现象学阵营活动状况的写实描述。而如今随着大量胡塞尔遗稿的编辑出版,人们已经可以了解胡塞尔本人在现象学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情感现象学、意愿现象学、生活世界现象学等领域(69)对此尤其可以参见新近出版的《胡塞尔全集》第43卷,其中第1卷讨论知性与对象,选自1909-1927年的手稿,第2卷讨论情感与价值,选自1896-1925年的手稿,第3卷讨论意欲与行动,选自1902-1934年的手稿。)中长期耕耘的状况以及业已收获和尚待收获的丰富成果。在这点上,现象学与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并无原则性差异,只是视角和方法不同而已。
五、现象学的各个分科之间的关系
胡塞尔在1925年讲座中主要讨论的是“现象学的心理学”,而在1927年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现象学”条目草稿中则首先论述作为“纯粹现象学”的“心理学的现象学”,而后论述与“心理学的现象学”相对应的“超越论的现象学”。最后,在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讲演中,胡塞尔开宗明义地标示了“现象学的双重意义”:心理学的现象学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就第一个标示而言,“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主语是“心理学”,指一种关于心灵生活的科学,而前面的定语“现象学的”则与这门心理学采用的方法有关,即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它们在两个方向上进行:对横意向性的横向本质直观与结构把握,以及对纵意向性的纵向本质直观与发生理解。“现象学的”在这里意味着运用本质直观和分析方法。现象学的心理学意味着一种描述的和理解的心理本质学。如前所述,现象学的心理学具有对心理学的理论奠基作用,“现象学的心理学既对心理的自然研究而言是奠基性的,也对人格科学和相应的科学而言是奠基性的”(70)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217.。现代心理学是在两端之间活动: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一端,生理学的心理学的另一端。前者为心理学提供意识的理论基础,后者为心理学提供生理物理基础。
此外,“现象学的心理学”的标示在当下的语境中还有另一重含义。“现象学的”在这里是指它的原初含义:“意识显现的”,即“有意识的”。“现象学的心理学”随之也就意味着“关于有意识的心灵生活的科学”。由于心灵生活分为有意识的(被意识到的)和无意识的(未被意识到的)两个部分,因而各种形式的“有意识的”或“现象学的”心理学,包括上述胡塞尔使用的意义上的“现象学的心理学”,就构成关于前一部分的心灵科学,而各种形式的“无意识心理学”则构成关于第二部分的心灵科学。目前在意识哲学方面影响较大的心智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的著作《有意识的心灵》(71)David John Chalmers,The Conscious Mind: 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以及现象学哲学家伽拉戈尔(S. Gallagher)与扎哈维(D. Zahavi)的著作《现象学的心灵》(72)Shaun Gallagher and Dan Zahavi,The Phenomenological Mind,London: Routledge, 2008.都属于前一部分的心灵科学。关于后一部分的心灵科学在胡塞尔那里(在他的许多手稿中)相当于不显现的、未意识到的意识权能意义上的现象学,而在现代心理学中也被涵盖在机能心理学或功能心理学的范畴下(73)对此可以参见笔者的论文:《意识现象学与无意识研究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意识分析的两种基本形态——兼论通向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莱布尼茨道路》,《学术月刊》2021年第8期。。
接下来,就后面提到的两种现象学标示而言,它们的主语都是“现象学”,在这里主要涉及关于意识现象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而它们的定语“心理学的”和“超越论的”则是对这里的对象和领域之性质的进一步刻画。
按胡塞尔的说法,“必须以最清晰的方式将超越论的现象学与心理学的现象学分离开来,它们在其基本意义上是各不相同的。不过,即使通过观点的改变,这一个可以过渡到另一个之中,因而在两方面会出现‘相同的’现象与本质明察,但可以说是伴随着原则上改变它们的意义的不同符号”(74)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247 f.。胡塞尔自己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现象学”条目和“阿姆斯特丹讲演”中曾尝试以最清晰的方式区分这两者,即指明这两种现象学是对两种相互平行的现象的探讨:超越论现象学的对象是纯粹意识现象,现象学心理学的对象是人的心理现象。在它们之间隔着一个超越论的还原。通过对这个还原的实施和放弃,这两种现象以及两种现象学彼此可以相互过渡。同时,对这两种现象学的关系的澄清也会附带地解释:为什么带有深刻的康德烙印的“transzendental”在胡塞尔这里不能被译作“先验”,而应当选择“超越论”这一更为确切也更不易造成误解的译名。对此笔者会另文专述。
这里的思考和阐释还是集中在这一卷的书名所标示的“现象学的心理学”上。它与众多“主观心理学”或“内省心理学”的差别也在于一个还原的施行和放弃:本质现象学的还原。它在胡塞尔那里更多被称作“本质直观”或“观念直观”。
除此之外,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心理学》这一卷的内容还需要强调说明一点:从1925年的“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讲座,到1928年的“现象学的心理学”阿姆斯特丹讲演,在胡塞尔这几年的思想道路旁既可以安放精神科学的路碑,也可以安放历史哲学的路碑。在这些路碑上不仅应当刻有胡塞尔的名字,也应当刻有胡塞尔的两位前辈狄尔泰与约克的名字,最后还可以刻有胡塞尔的两位弟子的名字:弗里茨·考夫曼和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他们两人于1928年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九辑上同时发表了他们各自的历史哲学论著,即考夫曼的任教资格论文《瓦尔腾堡的约克伯爵的哲学》和兰德格雷贝的博士论文《威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由于这两部论著与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刊登在同一辑,因而这个第九辑完全可以说是专门献给历史哲学的一辑,而这一年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现象学的历史哲学年,它在1925年随胡塞尔在“现象学的心理学引论”讲座中向狄尔泰的回溯就已经默默地开始了。
结 语
在本文引论中已经提到,胡塞尔从起初的任教资格论文《论数的概念》(1887年)开始,直至最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6/37年)期间,都需要一再面对和处理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关系问题。笔者在这里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依据“现象学的心理学”(1925年)的讲座稿。但因胡塞尔的思想变化,不仅需要涉及最初的《逻辑研究》(1900/01年),也需要涉及《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0年)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即使在集中讨论这个关系的《胡塞尔全集》第九卷中,胡塞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表述也有略微的变化,它们主要体现在1927—1928年期间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现象学”条目以及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讲演”中。
如果回到《逻辑研究》最初的意向上去,那么对于胡塞尔来说,对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与逻辑学的关系的思考与讨论自始至终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寻找、发现并把握意识的静态的和发生的逻辑,即寻找、发现并把握主观性中的“客观性”:心的逻辑或心的秩序,或者说,心智本身、“对思想的思想”(νησζ νοσεωζ)的逻辑与秩序。
在术语上可以作如下总结:胡塞尔所说的“纯粹心理学”“本质心理学”“先天心理学”“现象学的心理学”,其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如果它们仍然想要“普全地研究作为在世界中的实在事实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的心理学”,它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科学。这个意义上的纯粹心理学必定是“超越论的心理学”,它与“超越论哲学”无异:“只有一门超越论的心理学,而它与超越论的哲学是一回事。”(75)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S.261.一言以蔽之,经过双重纯化的纯粹的超越论的意识学。
这里最后还要引述胡塞尔在1908年12月23日致纳托尔普的信中的一段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的话:
我在1903年的逻辑学年度报告(参见:贝格曼、贡佩尔茨、耶路撒冷等)中就已经放弃了现象学作为“描述心理学”的偏斜的标示,尽管我在这些年里——在讲座中——已经能够做出更好的阐释。我寄希望于今后几年的更大的著述发表。我还要说明一点,我的——以任何方式都不是心理学的——问题与马堡学派的问题并不相合。而我的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不是心理学的方法——既非发生心理学的也非描述心理学的方法)在目标与本质上都是一种不同于您的意义上的超越论逻辑学的方法。(76)Edmund Husserl,Briefwechsel, Bd. Ⅴ,S.103.
不言而喻,这段引文的前半部分尚未超出这里讨论的现象学与心理学关系的论题范围,但其后半部分则已经过渡到另一个论题上去,它已经属于胡塞尔所做的将自己的现象学与各种超越论哲学划清界限之努力的另一章节了。因此,对胡塞尔与康德各自的“transzendental”概念的不同意义的澄清已经迫在眉睫。
——专栏导语
——兼论现象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