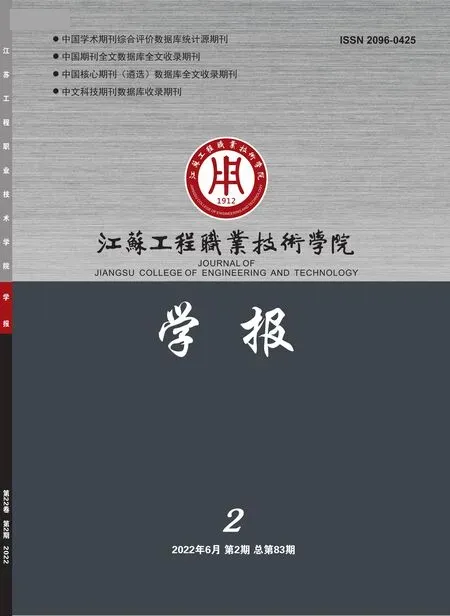高空抛物罪的理解与司法适用
董 寅 辉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近年来,高空抛物案件屡见报端,人们“头顶上的安全”问题亟待解决,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修(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3月至9 月,全国以高空抛物罪提起公诉的人数已达222 人。①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2021 年1 月至9 月公布的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网址为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10/t20211018_53 2387.shtml#1。司法实务领域在本罪行为模式、“情节严重”的标准以及与相近罪名的界限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立足实践中既有的高空抛物案例,从高空抛物罪的条文规定出发,以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为立论根基,对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详细解读,以期有助于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能规范化适用此罪名。
1 《刑修(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的法益之重申
刑法解释应该确保条文之间所得结论的一致性[1]以及个罪在刑法体系中地位的和谐性,个罪所欲保护之法益的认定应服从于该罪名所处章节保护的同类法益。《刑修(十一)》将高空抛物罪最终置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所欲保护的法益也应是社会公共秩序。我国通说观点认为,社会公共秩序是“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并依靠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制度、社会公共道德规则、风俗习惯来建立和维持的,有条理的正常的社会运行状态”[2]。其中,“公共”侧重于行为的公开性和社会性,“秩序”则强调的是一种有规范、有条理的状态。因此,增设高空抛物罪所欲保护的秩序限定为维持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秩序较为妥当。但是,公共秩序只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并非公共利益本身。本罪作为预防性刑法观的产物,强调对危险的前置化预防的同时,也存在侵害国民行动自由的可能,为避免过分依赖刑法的社会治理作用,有必要对此处的公共秩序进行限制性解释。《刑修(十一)》颁布前,司法实践中的高空抛物行为常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置,本罪在立法修订之初也被规定在第114 条中。受到学界广泛质疑后,在最终公布的修正案中,立法者将本罪调整至291 条之二。回顾修法过程不难发现,立法者增设本罪的初衷在于将刑法的介入时间进一步提前,实现保护的前置性,以公共秩序维护之名,行公共安全保护之实。故本罪保护的公共秩序也应限定为与公共安全有关的秩序,即本罪在维护必要的公共秩序之余,还保护公众对自身财产、人身安全的信任感。如此认定,可将诸如单纯因看热闹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排除出刑法保护的范围,避免出现部分学者所担忧的“过分强调社会风险,而忽视刑法风险”之法治悖论现象,防止价值错位引起的犯罪圈不当膨胀。[3]
2 高空抛物罪属抽象危险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高空抛物案件数量急剧增加。随着《刑修(十一)》的生效,此类不当裁判势必会减少,但是考虑到既有判决中存在大量机械适用法律的现象,有必要释明高空抛物罪成立之结果要求,依笔者之管见,本罪应为抽象危险犯。
1) 这一理解切合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意图。抽象危险犯作为一种法益前置化保护措施,此处的“危险”是立法者根据一般社会经验而预先设定的一种类型性危险。[4]基于对既有案件的调研考察,立法者考虑到高空抛物行为自身的危险性以及出现实害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意图通过增设本罪,以提前规制高空抛物行为。如此一来,也可以将根本不会对不特定人身或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或者威胁极低的高空抛物行为排除出犯罪圈。相较于行为犯,将本罪作为抽象危险犯理解,在入罪时增加了一次出罪的可能性。
2) 将本罪作为抽象危险犯对待具有规范依据,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行为人所受之刑罚应与其所犯罪行相当,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将“以刑制罪”贯彻在定罪活动过程中,即在对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具体解读时,应确保解释结论与相应的法定刑相适应。[5]本罪第二款规定了当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时依照重罪处罚,这意味着第一款规制的仅是侵扰社会秩序的高空抛物行为;同时,鉴于社会秩序这一法益较之人身、财产和公共安全等法益更加抽象,不宜处以较重的法定刑。倘若将本罪的成立结果理解为足以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等法益受侵害的具体危险,则会出现本罪与《刑法》第114 条等条款刑罚严厉程度的不相适应。
3) 将本罪理解为抽象危险犯也并不意味着模糊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一方面,我国向来坚持“既定性又定量”的犯罪概念,只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虽然,此处“一定程度”的概念本身较为模糊,但考虑到出罪与入罪本质上的一体两面关系,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刑法》第13 条但书,将“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在高空抛物罪中规定“情节严重”其实就是典型的定量限制,立法者有意提示我们在进行罪与非罪判断时要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实质考量,避免罚重于罪的情形出现。另一方面,在刑事程序中,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虽然并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但是并非完全不允许被告人反证,[6]立足于所保护的法益,完全可以将在荒无人烟的郊外别墅中任意抛掷物品等并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确保定罪结论的实质合理性。
3 厘清“高空抛物行为”模式
立法者对高空抛物罪采用了简单罪状的规定模式,为避免此罪名在实践中被滥用,有必要立足本罪法益,对法条的具体内涵进行限缩解释,避免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
3.1 关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的理解
基于本罪是抽象危险犯的理解,回溯本罪的增设历程,本罪的“高空”应当满足:依据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法则,从该高度向下抛掷物品具有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抽象危险,足以引起周边不特定公众对于自身财产、人身安全的紧张与恐慌。有学者将此处以地面为判断基准的“高空”概念扩大解释为“高处”,并根据《高处作业分级》规定,将高空理解为距离基准面2 米及2 米以上。[7]出于对处罚实质合理性的追求,结合我国建筑物中地下分层众多的现实,笔者赞同将“高空”扩大解释为“高处”,即一种相对高空,强调行为人抛物地点与物品坠落地点存在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抽象危险的高度差。
为贯彻罪刑法定,理应对此处的“高空”进行最低限度的限定,但是以2 米作为判断标准的合理性存疑。一方面,《高处作业规定》是以保障劳动者的工作安全为价值导向,与高空抛物罪所欲保护社会公共秩序的价值追求相距甚远;另一方面,实践中高空抛物案件常发于城市的居民区,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颁布的《住宅设计规范》中对住宅层的一般高度要求都是不少于2.8 米,采纳2 米的结论有所不当。考虑到生活中商务办公楼的层高往往高于住宅楼,“高空”限定解释为行为人抛物地点与所抛物坠落地点的高度差不得少于2.8 米即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二楼抛掷一切物品均能成立本罪,还应该结合抛掷物的重量、物体形态等因素实质判断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性,将符合《刑法》第13 条但书的行为予以出罪。
3.2 关于“抛掷”的理解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抛”有扔、投掷、丢下之意。[8]抛掷一词实为同义反复,强调的是行为人有意识地扔、投掷一定物品。讨论“抛掷”的主要目的在于将高空抛物与高空坠物进行区分,后者主要是指物品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或者意外事件从高处坠落的情形,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换言之,强调“抛掷”的意义有助于实践中通过考察物体的下落轨迹,推定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存在。但是,“抛掷”的形式并未限定为作为,事实上不作为形式也可能成立本罪,如有高层住户明知窗台上放置的物品有坠落风险,却不将物品搬离,放任危险发生,亦可认定为本罪。
3.3 关于“物”的范围
本罪作为一种侵犯公共秩序的抽象危险犯,要求足以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自身财产、人身安全的紧张与恐慌,所以并非从高空抛掷任何物品都应入罪。例如,在住宅楼上向小区内部人行道上抛洒羽毛的行为就难以构成本罪。因此,有必要立足规范目的结合抛物的高度以及抛物内容对所抛之“物”是否足以引起公众对自身人身、财产安全的危惧感进行类型化分析:①参见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皖0191 刑初144 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1)渝0105 刑初320 号刑事判决书。自身具备一定杀伤力的物品,如玻璃瓶、管制刀具等尖锐或者坚硬物品,此类物品即使是从非高空抛出,也能造成不特定群众对于自身人身、财产安全的紧张或者恐慌;②自身杀伤力有限,但于高处积蓄一定重力势能之后可能造成人身、财产安全受损害的物品,例如,在2 楼扔下1 枚螺丝钉并不足以致人伤亡或财产损失,但在20 楼扔下1 枚螺丝钉则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③无论在何种高度抛出,通常都难以致人伤亡的物体,如瓜子壳、无毒无害的液体等。当然,第三种情形并非一概无罪,还应结合具体抛物场所考察是否足以引起不特定公众关于财产、人身安全的紧张与恐慌来判断能否认定为“情节严重”。如前例所述,从高空向小区内部人行道上抛洒羽毛并无危害公共安全的风险,也不会引起不特定民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但是,如果在高空向车流量较大的机动车道抛洒羽毛,则完全可能引发公众的紧张与恐慌情绪,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理应构成本罪。
3.4 “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之建构
“情节严重”是立法者有意制定的模糊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既要考虑增设高空抛物罪所欲保护的法益,也应考虑高空抛物罪的客观方面、主体以及主观方面,以期建构的具体认定标准实现对模糊条款的实质解释。虽然《意见》第六条立足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从量刑情节的角度规定了“情节严重”判断标准,但不能因此否认《意见》对本罪“情节严重”判断标准的借鉴意义。纵观本罪增设过程,不难发现,《刑修(十一)》是在对《意见》吸收借鉴的基础之上增设的高空抛物罪。因此,仍可选择性地借鉴《意见》中的有关内容。《意见》中指出判断“情节严重”,应当从抛物场所和时间、抛物高度、抛物内容、实际造成结果、行为人主观目的以及实施次数等方面综合考量。但空谈综合对司法实务指导意义着实有限,这也是为何大量判决文书中仅陈述高空抛物事实本身,而忽视对“情节严重”进行具体说理。①本文尝试立足典型案例,遵循从形式到实质、客观到主观的基本思维规律,构建体系性的判断思路,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补益。
1) 考察抛物的场所和时间。高空抛物罪所欲保护之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在判断“情节严重与否”时应首先考虑抛物场所和时间来考察高空抛物行为侵犯秩序的“公共性”与否及程度。实践中高空抛物案件常发于居民聚居区,坠物地点大都为小区内外公共道路,抛物行为在侵犯公共秩序的同时能够引起居民对个人财产、人身安全的危惧感,具有规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是,不能将秩序的“公共性”简单理解为公共场所,还需考虑抛物时间、抛物地点的基本环境以及人流量大小。例如,冬天的6 时与夏天的6 时,冬天北方的22 时与冬天南方的22 时,相似场所的秩序“公共性”程度却有不同。在既有案件中,不少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直接或间接释明了“抛物时间”以及“抛物地点的人流量或者基本用途”,但仅以此来论证“情节严重”显然难有说服力。①参见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吉0104 刑初430 号刑事判决书、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2021)吉0802 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2 刑初901 号刑事判决书、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2021)辽0104 刑初312 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0 刑初235 号刑事判决书等。
2) 关注抛掷物的性质、抛物高度和次数。在通过判断抛物场所和时间明确所侵害秩序的“公共性”之后,再以社会一般人的标准衡量抛掷物是否具备毁损财物或致人伤残的风险,进而得出是否会引起社会公众的恐慌。若得出肯定答案,则无须实质判断抛物的高度,只需抛物地点与坠物地点之间存在2.8 米以上的高度差即可,以避免突破罪刑法定原则设定的底线;倘若单独考察抛掷物品本身尚不足以判断能否引起民众的恐惧感时,则有必要结合抛物高度,通过侦查实验等方式,进一步判断情节严重与否。例如,在李洪兰高空抛物一案中,其将装有废弃玻璃瓶、快递外包装等垃圾的透明塑料袋从阳台扔至楼下,②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2 刑初901 号刑事判决书。考虑到玻璃瓶从高处坠落后崩碎四溅的高度盖然性,将该行为认定为高空抛物罪也并不会违背社会一般人的基本常识,无须再对抛物高度进行具体测量。但是,在李岩高空抛物案中,③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 刑初1616 号刑事判决书。鉴于其所抛掷的是吸食笑气的瓶子,体积一般较小,仅凭该物品本身难以断定行为的危险性,有必要结合其抛物高度(16 楼)形成的重力势能来整体判断。倘若行为人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实施多次抛物,应该将数次行为一体化视之,整体考量其行为的危害性。此时,若连续行为的危险性达到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则成立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想象竞合。④参见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5 刑初139 号刑事判决书。
3) 重视实际损害结果和潜在损害后果。将实害结果作为“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符合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但本罪作为抽象危险犯,不能仅考察实害结果,还需立足具体时空条件,站在普通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研判高空抛物行为潜在风险的高低,将确实难以引起公众恐慌的行为予以出罪。以卢某高空抛物案为例,虽然抛物行为并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但考虑到坠物地点当时人流量较大,造成危害后果的盖然性较高,实际上也确有老人与从高空抛下的手机擦头而过,险些酿成实害结果,⑤参见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2021)湘1002 刑初145 号刑事判决书。足以引起公众对自身安全的危惧感,认定为高空抛物罪并无不妥。
4) 考虑行为人主观恶性。我国传统观点认为,“情节严重”的考察应涵摄所有能够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高低及行为人之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主客观各种要素,具有复合性。[9]因此,在对高空抛物罪中的“情节严重”标准进行认定时,除主观罪过外,还有必要考察行为人的犯罪目的、犯罪动机、是否有预谋以及其他能够反映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虽然现在不少学者提倡“情节”要素的客观化,但这并不符合本罪新增之初所预设的引领社会道德的功能定位,鉴于道德的抽象性,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纳入“情节”严重与否的判断较为合理。此外,实践中也不乏行为人不连续地实施多次高空抛物行为的案例,倘若先前的高空抛物行为已经构成高空抛物罪,则应考虑是否存在构成累犯的情形,并单独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倘若前行为未达到犯罪程度或者未经处理,理应将前行为纳入“情节严重”的判断范围。在周言昌高空抛物案中,⑥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1)川0112 刑初51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行为人周言昌连续3 天多次实施高空抛物行为,虽然所造成的损失有限,但是其连续多次实施行为本身就已经反映了其主观恶性之严重,理应受到刑罚惩罚。
4 高空抛物罪竞合犯的处理
修法之后,除了明确本罪的犯罪构成之外,有必要在《刑法》第291 条之二第二款的基础上厘清相关罪名的界限,科学地适用处断规则,以免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
4.1 高空抛物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
《意见》的颁布导致实践中大量的高空抛物案件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由此产生了一些量刑不当的判决。高空抛物罪设立后,在恪守本罪构成要件边界的基础上,明确“高空抛物行为原则上就不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10],促进实务界对“公共安全”实质判断的理性回归,减少不当判决的出现。
“公共安全”的解释向来是公共安全犯罪争议焦点,相较于张明楷教授将其限定为“不特定人的安全”[11],通说观点将其作“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12]理解,在确保刑法保护周延性的同时,也较为切合一般人的正义观念。鉴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在对具体行为进行定性时,应立足所保护的法益,对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理解。同时,出于同类解释体系性的要求,还应发挥例示条文对解释兜底条款具有的平行制约作用。[13]具体而言,在判断某一危害行为是否符合以危险方法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应符合以下两点:一方面,需要以“多数人”为中心来理解“公共安全”,实质衡量该行为是否有威胁现实或潜在的多数人安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应判断该行为是否同时满足“导致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直接性、迅速蔓延性与高度盖然性”[14]。基于此,不难发现,高空抛物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难度较大,仅在于人口密集处的高空抛掷煤气罐、炸弹等自身有危害扩大性质的物品,或者较短时间内连续多次抛掷物品等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夏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中,夏某某为宣泄个人愤怒,于人流密集的场所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多次从高空抛下电水壶、菜刀、玻璃茶几及易拉罐啤酒等物品。①参见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5 刑初139 号刑事判决书。考虑到玻璃茶几的体积较大,行为人高空抛出后难以控制落地的位置;而且玻璃茶几的特殊材质决定了其自高空抛下后,必定会四处溅射,具备潜在结果范围的蔓延性,社会危害性极大,将该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无不妥。相比而言,黄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的判决结果就值得商榷,判决书中仅提及行为人多次在晚上拿苹果、梨子、砖头等物品扔向一楼正在营业的重庆麻辣烫消夜档及周边,威胁到正在重庆麻辣烫消夜档及周边店铺消费的顾客安全,②参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2020)粤0310 刑初438 号刑事判决书。强调的重点在于次数多,而非抛物行为在短时间内的连续性,加之所抛掷之物自身不具有结果蔓延的可能性,将黄某某的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做法显然是罚过于罪,有所不当。然而,黄某某案绝非孤例,实践中仍有大量罪刑不相适应的判决,③参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6 刑初161 号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 刑终484 号刑事判决书。此次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在顺应民众需求的同时也给司法裁判留下了实质考察危害公共安全与否的空间,实现对实质罪刑法定的价值回归。
4.2 高空抛物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竞合
寻衅滋事罪包括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4 种行为类型。其中,殴打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直接身体接触,不仅包括行为人对被害人直接施加暴力的情形,还包括行为人利用工具对被害人进行攻击的情况,由此,高空抛物攻击他人完全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同理,恐吓行为的本质是强调行为人造成不特定民众的恐慌,并未对其手段形式进行限定,因而具备二罪竞合的空间。但此类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罪的案件较少,这主要是因为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性较之普通的殴打、恐吓行为要高,司法机关更倾向于将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务中最为常见的是高空抛物行为与任意损毁公私财物型寻衅滋事罪的竞合,在李某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李某酒后滋事,无故多次自7 楼扔出锅碗、衣服、石块、花盆等物品,造成他人热水器太阳能板及该单元的公共车棚玻璃毁损,④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1 刑初1021 号刑事判决书。鉴于财产损失的有限性,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刑修(十一)》出台之前,部分并未造成实害结果的高空抛物行为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以实现刑法覆盖面的完整性,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随着高空抛物罪的增设,有必要划清两罪的界限,减少寻衅滋事罪这一“口袋罪”的适用,避免高空抛物罪的虚设。 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参考寻衅滋事罪中“情节严重”的标准,限缩高空抛物罪中“情节严重”的范围,实现二者之间罪刑的梯度化,使之与各自法定刑相协调,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定罪的指导意义。[15]例如,考虑到高空抛物罪的法定刑较低,理应减少“多次”在本罪“情节严重”认定中发挥作用的比重,形成与寻衅滋事罪中“多次”认定的差别化。再如,综合全案事实,高空抛物罪中的“情节严重”只要求引发不特定人对自身财产、人身安全产生恐慌的程度即可,但是寻衅滋事罪由的“情节严重”应达到“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程度。
5 结语
高空抛物作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应当坚决予以抵制;刑法积极介入是出于风险防控的客观需要,以严厉的手段惩办社会危害性较大的陋习。在修法后阶段,还需要戒除情绪性司法,在教义学内部对高空抛物罪进行解释,在明确高空抛物罪是抽象危险犯的基础上,厘清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寻衅滋事罪的关系,根据具体时空情况、手段方式等所造成的情节严重程度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准确定性,注重刑法重塑公众基本的道德观念、引领正向社会价值功用的同时,还应该避免不当压缩公众自由行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