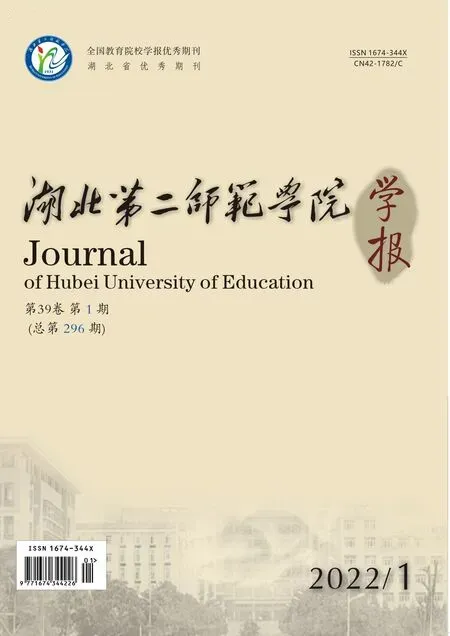超自然性和精神人格解构的融合
——再谈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叙事手法
李晓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广州 510420)
引言
中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给黑暗腐朽的神权和宗教极度的禁欲主义统治下的黯然时期,带来了一次壮烈璀璨的天启式曙光。这场运动的触角伸及欧洲各国,揭开了历史的一番新帷幕,信仰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媒体就能得到上帝的救赎,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进行信仰沟通。神权已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突然间被告知他是自己命运和世界的主宰,无需遵循教条信义,他有能力并因天附于其选择的恩赐。
人一时间赖以生存的宗教礼仪原则被抛弃,一路原设铺定的救赎道路不再有它的路迹,“人”被文艺复兴者利用“人文情怀”加以凝练,他不用再相信上帝,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这在当时是一件多么惊讶可怕的事情。如今世界的寻常观念意识在当时却是极其陌生甚至令人彷徨的。到了19世纪至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依然思考上帝和人的关系:“人类不必期望从仁慈的上帝那儿得到任何帮助。人们心中期待的社会秩序只是一场幻梦,人类必须认识到在这样的世界自己是无足轻重的。不管多么让人难以接受,人类还是要认清这一点,才能够适应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命运,人类全部的付出也因此徒劳无功,留下的只有绝望。死亡使人类所有的努力和成就都将归于灭亡。人的一生是短暂脆弱的,而注定走向毁灭的命运将无情降临整个人类。”①罗素劝诫人们相信自己,带有一种悲观的人生奋斗论,倡导人不可信任神帝,要依靠自己,要有“绝望的勇气”去面对生活。而这种“重压下的优雅”的精神在美国作家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人物中可得斑驳显现。
由于文艺复兴打开了人的意识,莎士比亚对当时人的思想意识状态进行了一次韬光养晦的凿探,对人的精神状态进行了人格解构。他透过长期黑暗宗教统治,看到了作为人的基本意识和欲望,认识到了人的先天本能才是推动人前进觉醒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倘若莎士比亚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他自然不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文学家。他与易卜生不一样,易卜生《玩偶之家》讨论更多的是社会现实问题、家庭冲突、女性经济地位等等;而莎士比亚却是站在了“是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维度,去探究人的自我意识的抗争和人在善恶两极不可平衡的状态下如何选择、如何剖析自我、如何毁灭创造自我的哲学性问题。
因而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在确立了人为主体后,神权依然丝丝不去地发挥着影响下,我们可以利用超自然叙事手法去解读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非现实因素,在莎士比亚自身对人的意识精神分割中,我们也可以将他超自然的叙事手法和佛洛依德的人格结构论去探析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和文学世界。
一、叙事前进的动因——女巫的超自然意象
在莎士比亚近四分之一戏剧作品的中,鬼魂、凶兆等直接或间接出现的超自然描写俯拾皆是。尽管大诗人歌德早在19世纪初,就已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文中述及,但之后数不胜数的莎剧研究文献中,却很少有对此问题做出深入探讨的。在莎士比亚艺术宝库里,超自然描写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考究及分析它们在戏剧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悲剧总是以意象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确定作品的叙事走向,“意”是指作者的情绪情感、主观意识和客观对象的有机统一。“意”(思想观念)和“象”(具体物象)是天然有机融合。作品中的“意象”联系着具体的现实世界,又表征为作者心灵的精神世界,是女巫、幽灵、鬼魂、勃南的树林等,似乎具有古希腊悲剧影响的痕迹。莎士比亚笔下的凶兆、女巫、幽灵、鬼魂、仙女和精灵等,有效地渲染了悲剧的神秘气氛,在叙事中构建作品的悲剧结构。歌德指出:“使莎士比亚伟大的心灵感到兴趣的,是我们这世界内的事物;因为虽然像预言、疯癫、梦魔、预感、异兆、仙女和精灵、鬼魂、妊异和魔法师等这种魔术的因素,在适当的时候也穿插在他的诗篇中,可是这些虚幻形象并不是他的主要成分,作为这些著作伟大基础的是他生活的真实和精悍。因此来自他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显得那么纯真和结实。”②事实证明,莎士比亚剧作的写实力量并没有因超自然描写的出现而被削弱,反而是得到了大大的强化。
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位”的意识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与张扬,感性的欲望得到人们重视。莎士比亚在“神为中心”向“人为中心”的转化过程中,看到了人潜在的本能欲望是推动自己生命前进的动力。《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最短的一部悲剧作品。这部剧作讲述了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征服叛乱后班师回国,在路上遇到三个女巫。女巫预言:麦克白将成为未来的君王;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也没有任何一个妇人生的孩子能伤害到他。在这三个预言及其夫人的煽动之下,麦克白先后杀死了国王邓肯和大将班柯等人,最终众叛亲离,被敌人杀害。《麦克白》中的女巫,充当了作为叙事的一个预言者,可能让读者好奇地想去探清故事未来的走向,给整个戏剧蒙上了一股悄然的命运意识和隐藏的跌宕转折。
在麦克白主动寻求女巫解惑的时候,女巫的预言作为麦克白坚定阴谋下去的强心剂,即挖掘出麦克白内心的欲望已经深不见底,也推动着叙事的前进,整个戏剧的叙事情节基本都是围绕着女巫的预言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抛开女巫作为叙事燃料的视角,把女巫从整个麦克白的戏剧中抹去,整个戏剧将无从谈起,麦克白的自我解构、自我毁灭,自我完成的形象将不会存在。
《麦克白》中女巫这一角色正是起到了功能性叙事的作用,对戏剧情节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影响。“女巫”和“鬼魂”等角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并不少见,比如《哈姆雷特》中飘荡在殿堂里的老国王的鬼魂。女巫的角色在《麦克白》中频频出现,但不同于《哈姆雷特》里老国王鬼魂的是,从第一幕女巫的出场,到第五幕麦克白夫妇的死亡,莎士比亚用女巫的预言在其中构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叙事圈套,这使得读者包括主角麦克白本人,都陷入到了这个叙事迷宫里,也就是说,女巫在这个故事里对功能性叙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莎士比亚总是把这些超自然的元素植入在他的作品中,女巫代表超自然的力量,超自然力量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父亲亡灵的出现,是引领哈姆雷特走向生存还是毁灭的源动力,他得知克劳狄斯杀父夺位的真相后,人性的挣扎终得以显现。在克劳狄斯忏悔的一幕,哈姆雷特把握住了最佳的报仇机会,但他拿起的匕首刀挥下去却又收回来,伴随着宗教的思考,如果杀一个忏悔的人,他的灵魂会升入天堂。亡灵、女巫、天堂的宗教概念,这些超自然的元素融入,实际上是文艺复兴时期对神权冲击,是神权和人权斗争下人的困惑和思想混乱的一种状态在作家的笔下的显现。超自然元素的加入,让哈姆雷特或是麦克白在选择相信自己还是相信上帝的纷扰上,时刻都是对自己信念的考验。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女巫的加入实质上是本我欲望本能的潜在体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论中指出,“人的行为动机是潜意识的本能,并把本能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前者代表着一种生存、发展和爱欲的本能力量,代表着人类潜伏在生命自身中的一种进取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驱力;后者表现为一种生命发展中的对立力量,代表着人类潜伏在生命中的一种破坏性、攻击性、自毁性的驱力。它们的作用方向相反:一个建设性的或同化的过程,另一个是破坏性的或异化的过程。”[1]他把人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格的核心,是原始的、无意识的、不合逻辑的,是先天本能和欲望的贮存库,体现着动物性的、本能的一种冲动。而这样的冲动,恰恰是通过女巫的话语来体现的,女巫这个超自然元素实际上就是麦克白本我意识的客体化、具体化的意象。女巫的话:“祝福你,葛莱密斯爵士;祝福你,考多尔爵士;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在女巫说出了自己的预言后,班柯立马反应:“将军,您为什么这样吃惊?好像害怕着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2]16莎士比亚从侧面的角度去揭示麦克白心底的欲望被外在暴露的慌张,而麦克白自身也故作伪装地说:“考多尔爵士现在还活着,他的势力非常煊赫;至于说我是未来的君王,那正像说我是考多尔爵士一样难于置信。”[2]16等麦克白的话说完,女巫立即隐去。这实际上是麦克白压抑住自己欲望暴露的体现,否则,莎士比亚为何不让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女巫继续为其解释这预言的由头。
试想若这预言真是预言,真是上帝派女巫向麦克白告知这天赐的惊喜,这帝王的命运,那么麦克白为何不坐享其成,享受命运对自己的眷顾,何须要费尽心思,安排一场天衣无缝的弑君的宴席,白白让自己走向了叛国的道德沦丧。他深知考多尔爵士即将带来不堪的判决,此外他击败挪威军队的保卫国家的无上荣耀为何不能开启他的野心。另外,女巫对班柯的预言:地位低于麦克白,但比他更伟大,虽没有麦克白那样幸运,却比他更有福。虽然不是君王,但你的后代将有君王之份,在叙事上,为麦克白登上王座后要铲除这最后的疑虑埋下伏笔,把握了一定的叙事走向,为麦克白登上王座的道路上的转折突发事件作了预告。同时也是麦克白欲望中,死本能的体现,是在生存竞争中,班柯表现为麦克白发展道路中的一个对立力量,班柯也是和他在战斗中,立下血汗功劳的人,自然是他道德和名声上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在对班柯的预言中,隐藏了麦克白本我中的破坏性和攻击性。在这样的超自然元素把握叙事走向,并融入了人格精神结构,作为莎士比亚的一个重要的戏剧手法,给整个故事增添了命运色彩的同时,也有了作为“人”本位的思考,深刻地剖析了人内心潜动的欲望自身的涌动焦灼以及在外因下的变化,从而成为整个叙事的风向标。
二、超自然叙事元素融入——麦克白超我与自我的挣扎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面。自我既联系着本我和外部世界,也扮演着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调节角色,它调标了常识与理性,依照现实原则来行动。麦克白作为自我,其现世的思考带有一定的伦理价值,这些体现在他要行刺邓肯国王时的犹豫“可是我为什么说不出‘阿门’两个字来呢?我才是最需要上帝垂恩的,可是‘阿门’两个字却哽在我的喉间。”[2]40麦克白想说“阿门”,体现了他对上帝将信将疑的态度,痛苦之时,他也想对上帝忏悔,也想从上帝那里寻求到一点帮助,可他哽咽了,或许他认为自己所犯下的恶行不可能被上帝宽恕,或许他从根本上就觉得求助于上帝是无用的。无论怎样,基督教的影响总归是难以磨灭的。这是自我意识在度量着即将要行刺事件的道德性,是自我在现实规则下对行为的理想辩证判断的过程。而超我是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追求完善的境界,它处于最上层,压抑和控制了本能的冲动,根据至善原则来指导个体的行动。班柯则是麦克白意识中一个超我形象的具化。班柯在麦克白整个起落转折中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是作为麦克白罪行的无言诉说者以及他精神失常的一个因素。
班柯和麦克白一样,征战沙场,在战斗中功不可没,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他对王上的称赞十分谦虚,“如果我成长起来,收获的将是陛下本人。”他和麦克白一样听了女巫的预言,却没有动心,不似麦克白一样起了杀心,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开一条王座的康庄大道而把麦克白和邓肯铲除。在麦克白款待国王邓肯的夜晚,班柯思考,“慈悲的神明!抑制那些罪恶的思想,不要让它们潜入我的睡梦之中。”[2]36显然,女巫的入梦让他刚到这个夜晚有些许异样,他不愿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便要去寻剑作为防备,不料碰到未入睡的麦克白,感到了些许女巫的预言有几分真实的影像,“昨天晚上我梦见那三个女巫;她们对您所讲的话倒有几分应验。或说这是初步的试探,接着他用自己的原则去作隐约的暗示和提醒:为了觊觎富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不干的;要是您有什么见教,只要不毁坏我的清白的忠诚,我都愿意接受。”[2]37
此时,班柯作为超我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去点醒麦克白即将失控于本我的自我,这点作用微乎其微,主要体现在麦克白对行刺的犹豫和惊忧上:“那打门的声音从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怎么一回事,一点点的声音都会吓得我心惊肉跳?这是什么手!嘿!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2]43此时麦克白的迟疑体现了本我和超我的调节过程,体现的是以超我的伦理度尺丈量本我潜在欲望和丰富的心理感受。
班柯是忠心的,即便麦克白继位后仍然起誓为新王效忠,惟命是从。班柯是麦克白的良心体现。在宴会上麦克白看到的班柯的灵魂。所有在座的宾客都没有看到班柯血淋淋的灵魂,而只有麦克白一个人看到。和《哈姆雷特》的老国王灵魂不同,老国王的灵魂不止哈姆雷特一个人可以看见的,所有人都能看见老国王灵魂,这暗指了一个必须要复仇的不安的灵魂控诉,一场天大谋杀的愤怒,是要人来挥起复仇的烈火,烧尽所有不可饶恕的罪恶的野草。而班柯的灵魂只对麦克白可见,是带有麦克白的自我意识呈现。班柯一直作为忠心的臣士,一直对女巫预言的无行动,这或多或少也影响着麦克白的思考:该是像邓肯那样怀着仁慈善良的道德才可攀上巅顶,摘得王座的桂枝。女巫的预言加上班柯的良心,最终鬼魂的出现,都是在无形中拷打着麦克白的罪行,更是莎士比亚将超自然叙事元素融入人格精神解构中的一个十分有趣的手法,时刻让故事涌动着神秘和变化的色彩。这种超我的显现,莎士比亚把它设计成了让麦克白去追问质疑本我的本能和欲望。麦克白去找女巫问话的情节,生动有趣地展示了麦克白对自我否定、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意识变化过程。麦克白质问女巫:“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些什么?”[2]83作为在班柯鬼魂出现后对本我的严厉拷问。不料的是,他面对的是自己的欲望,自然还是会被欲望所牵动,他这次无法完成转变正是因为面对的是本我而非直面超我。他这次找女巫的谈话无非只是强化他稳固王位及继续铲除不利因素的野心。
班柯作为超我的形象以及他鬼魂出现的超自然元色素,在整个叙事过程中二者水乳交融,既是个人精神意识的突变,又成为故事走向更深的外延发展的动因,给整个叙事舞台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三、复调叙事——自我意识的剖析
巴赫金1963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列举并分析了当时评论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并从正反两方面对这些观点进行评述,丰富了复调对话理论。
巴赫金提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的意识被当成“一种‘他人意识’,是‘自身的、直接具有意义的话语之主体’,主人公相对作者是独立的,同时各个主人公之间也是相对独立不相混合的。各种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各种有充分价值的声音之正的复调”,[3]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并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统一意识来操纵的,人物的形象、命运以及情节的发展并不根据这种统一意识来展开,小说呈现的是价值统一、意识却不同的世界。此外,巴赫金还认为复调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与主要人物的声音相比,作者的声音并不带有任何的优越性,主人公的独立自我意识是复调小说艺术特色的一个主要体现。[4]
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赋予了麦克白自我独立意识的设置,隐去了作者主观意识的干扰,使得麦克白自我意识的剖析以及麦克白夫人作为本我人格的客体化形象更为深刻。作为麦克白野心强大的推动者——麦克白夫人,在杀害国王邓肯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读到麦克白来信的话语:“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2]25与其说她是丈夫的不可思议的同谋者,倒不如我们将她看成是麦克白野心的人格化,而她对麦克白的回信,更是本我对自我的怀疑和拷问,因而要实现麦克白的夺位阴谋,本我必须坚定自己的目标和立场,所以在谋杀邓肯的过程中,麦克白夫人的表现是那样的直接和没有罪恶感:我手上的颜色和你的手一样了,但我心却耻于变得苍白。麦克白夫人作为本我意识的具体化,表现为惊人的野心和道德的沦落,与自身女性的特点没有一点吻合之处。在整个故事叙事上,比超自然元素女巫更能推动麦克白朝着帝王位上前进,更能让叙事节奏加快步伐,充当着道德压抑下的欲望的完全体,即便杀害了国王邓肯,也没有一点的愧疚和自责。而麦克白夫人的精神失常以及最终走向死亡,也预示着麦克白本我已经消失,他也将在人格失去平衡的状态下面临毁灭的命运。在这里,自我和本我的邪恶思考体现得非常的精彩,莎士比亚善于从不同的人格视角将看似矛盾的人格融为殊途同归的一体,从而影响整个叙事的走向。麦克白夫人(本我)的直接残忍的野心欲望,和麦克白(自我)在刺杀国王邓肯的犹豫实质上是本我邪恶逐渐占上风的过程。面对本我的强大直接夸张的野心,自我渐渐失去了调节功能,他迟疑犹豫的思考实际上并非良心在作怪,而是为了让邪恶的计划更加无缝和周密,从而避开可能发生的道德谴责,这是在降低超我的引导能力,加强本我的入侵,使自我失去中间介质调节的功能,让自我的思考更加地本我。这样,在整个人格的挣扎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以人物的思想斗争变化来预示叙事的节奏和走向,到最后麦克白对妻子的死去完全无感的时候:反正她日后也会死,迟早总会有这么一天。实质上也影射了麦克白本我消失,以及代表道德度量的超我也全然散去,等待的将是他自我的毁灭。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充满着复调叙事的色彩,根据自我意识人格的分解,从麦克白夫人的本我毁灭到麦克白自我的消亡,体现着剧本的叙事逻辑,作为复调叙事自我意识分解的结果。
四、结语
文艺复兴是带给在黑暗深渊和宗教禁锢下的人们的一场光的洗礼,在有人告诉我们最真的事实是你不是你,世界不是世界,真理并非真理的时候,人将会处在怎样的思想意识状态,尤其是选择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信仰的对抗者,是如此的陌生和可怕。莎士比亚从中捕捉光影,把人的矛盾、混乱、朦胧的状态记录在了他的文学作品里,无论是从叙事技巧到其中道德伦理和人本能欲望的挣扎,还是叙事语言的诗意性和丰富性,都体现了莎士比亚剧本的独特无法超越的魅力,他站在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角度去命题他的剧作,从而达到了一场又一场灵魂盛宴的高度。
注释:
①转引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2008:156-157),这原是20世纪初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在《一个自由人的信仰》(罗素,1903)中的一段话。
②出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 4页。《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本介绍国外古典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古代文学流派及重要作家相关资料的不定期刊物,前后共出过11期。
——他者形象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