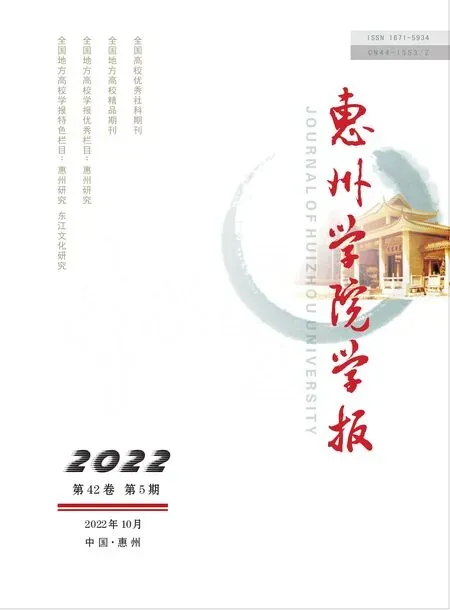“迫成隐士”与“开卷有益”
——“论语派”小品文的现世性
李茜烨
(中山大学 中文系(珠海),广东 珠海 519000)
论语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品文创作的重要流派,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为中心。论语派小品文最显著的特点是性灵与幽默,在历史上最受人诟病的也在于此。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主导下,论语派小品文在新的价值标准下获得了肯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庄钟庆的《论语派与幽默文学》正视了论语派对幽默、闲适、性灵文学的倡导;俞王毛的《论〈宇宙风〉杂志的近情文学》关注到了《宇宙风》对于小品文“近情”风格的重视;杨剑龙的《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系统地分析了论语派小品文性灵、幽默、闲适的创作特点。然而,在这些肯定性的评价里,论语派小品文逐渐成为性灵与幽默的标志,研究者也似乎遗忘了他们曾提出的“迫成隐士”与“开卷有益”。《论语》第一期的《缘起》中说:“我们无心隐居,迫成隐士”[1]1;《人间世》的《发刊词》里对来稿提出这样的期待:“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也已”[2]2。“迫成隐士”与“开卷有益”一为出发点,一为落脚点,显示了论语派对小品文创作中真诚性、现世性、批判性内容的期许,以及避免小品文成为玩物丧志之物的努力,这可以说是该派在性灵、闲适、幽默之外的创作态度。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在性灵、闲适、幽默之外,“迫成隐士”与“开卷有益”如何体现了论语派对小品文现世性和批判性的关注,以及他们对小品文内容的扩展所做的努力;这些创作态度是如何被消解又如何被试图阐释与达成;在消解与试图阐释、达成中纠结着创作者怎样的心态与立场。
一、性灵幽默与现世正经的双重变奏
1932年《论语》创刊,第一期上的《缘起》边玩笑边正经、半虚构半真实地道出了他们办刊结社的由来,但其开篇几句却常为人所忽视:“《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1]1。此处可见其办刊之目的起初并非为了轻松与玩笑,所谓“聊抒愚见”也蕴含着自由表达的性灵之光,而这里的“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和“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则明确提出了指向现实社会的创作内容。可又“无奈泰半少不更事,手腕未灵,托友求事,总是羞答答难于出口;效忠党国,又嫌同志太多;入和尚院,听说僧多粥少;进尼姑庵,又恐尘缘未了”[1]1。这段话中玩笑颇多,但联系论语派的惯常姿态也不难想见他们是不甘与国民党握手言和,亦不愿与左翼同为激进,而且还无法舍弃市井现世,因此他们才“迫成隐士”。既然他们是“迫”成隐士,也无心隐居,必定无法真正超脱于社会,才有了《论语社同人戒条》中所谓“不反革命”。“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3]1等一系列有着功利主义和启蒙主义色彩的创作倡导。然而,评价者对《论语》的印象却多是关乎幽默,或是如左翼文人对其堕入笑话式的低劣作品的批评,或是如郭晓鸿的《现代市民话语的文化形态——<论语>杂志研究》延伸出的“市民文学”“商业文学”等概念,虽然这些评价都有中肯之处,但也逐渐忽略了论语派小品文“迫成隐士”时的锋芒。
一年多以后创刊的《人间世》,因其直截了当地打出提倡“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的闲适小品文旗号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唱和事件的导火索而招致左翼的猛烈批评,世人关注到了《人间世》上性灵、闲适的小品文与名士气的姿态,但“开卷有益,掩卷有味”的内涵与避免小品文“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的努力,以及小品文应具备实质性、现世性的创作原则却为大多数人所忽视。这样的现象,或许源于论语派本身对性灵、闲适、幽默的呼喊过于盛烈,并有意塑造言志派的自我形象;可能也由于批判者的矛头指向的正是他们性灵、闲适、幽默的小品文,从而产生了价值过滤;也可能是论争中所缠夹着的政治身份和文学场占位等因素所造成。
论语派对言志派形象的塑造源于周作人。周作人在1926 年的《陶庵梦忆序》中公开提出关于明清名士派文章与现代散文的一致性问题,后来经《杂拌儿跋》(1928 年)、《<燕知草>跋》(1928 年)、《<近代散文抄>序》(1930 年)、《<枣>和<桥>的序》(1931 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年)至《<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年)的集大成,形成了他的“言志派”文论。在这个文论体系中,周作人借用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信腕信口”的文学特质来凸显他对表达个性的文学的肯定,同时也借用这样的思想资源把论战的矛头指向他所谓的“载道”文学——左翼。周作人成为言志派文学的精神导师,在这样的号召之下,林语堂融合晚明的性灵因子、老庄的道家思想和他所欣赏的克罗齐等人所代表的西方表现主义,在完成中西方文化的对译后,创办了提倡幽默小品、性灵小品的刊物,并形成了论语派,与北方的苦雨斋文人群体共同作为言志派小品文的两大重镇。
论语派立足于言志,把性灵视为小品文之灵魂。林语堂在读过沈启无的《近代散文抄》后,借鉴袁宗道《论文》上下两篇,在《论语》上发表了同名文章《论文》。他在此文中说:“文学趋近于抒情的、个人的:各抒己见,不复以古人为绳墨典型。一念一见之微,都是表示个人衷曲,不复言廓大笼”[4]532乃性灵小品文的真谛。他在《小品文半月刊》中同样表示:“小品文所以言志,与载道派异趣,故吾辈一闻文章‘正宗’二字,则避之如牛鬼蛇神”[5]7。林语堂认为闲适和幽默对于小品文也同样重要,此二者与性灵有着至深的关系:“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返归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6]435。在论语派对言志文学的倡导中,性灵、闲适和幽默由是成为其小品文创作的理论支柱,而他们在此方面过多的自我表达,不仅引起了左翼及京派的反感和批判,同时也使得其《论语》的《缘起》中“迫成隐士”的出发点和《人间世》的《发刊词》中“开卷有益”的小品文创作原则退居幕后。
对于论语派的批评主要意在针对他们从晚明中所发现的性灵、闲适和幽默。左翼以鲁迅为首对论语派进行了批评,所持论大抵是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7]591”,从而对他所认为看似性灵的、闲适的、言志的,实则是消极的、逃世的、帮闲的言志派进行批评。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小品文的生机》等一系列杂文,茅盾的《不关宇宙或苍蝇》、周木斋的《小品文杂说》、洪为法《我对于小品文的偏见》等均是左翼文人中批判论语派的有名篇章。这些杂文在批评论语派的同时,把对晚明阐释的重点放在晚明文人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对社会政治的关怀之上。京派同样也不满意论语派,沈从文认为其只不过是“它目的在给人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且“……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8]”,朱光潜也在《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中质疑《人间世》和《宇宙风》,京派的批评更多地指向论语派对幽默的大肆提倡,担心其堕入不够庄重的趣味化甚至是恶趣味之中。
当然,这些批评也和论语派对于性灵、闲适、幽默的过多自我阐释是分不开的。他们的每篇《关于本刊》《编辑后记》中对性灵文学的强调不断加强,尤其是《论语》第六期上林语堂发表的《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呼吁大家写文章应该避免“太积极”。相对于论语派对于文章中现世性、批判性的正经内容的强调,偏重于性灵张扬的个人主义精神更明显地处于首要地位。而这又恰恰是注重社会性和反抗性的左翼文学所最不能容忍的。当双方论争的焦点成了性灵、闲适和幽默,即便论语派有过“迫成隐士”的无奈和“开卷有益”的期许与尝试,也在这场论争中被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过滤,成为鲜明对峙的双峰。
然而,在双方都提高自己的声调,强调彼此的分歧与对立时,不仅是二者文学主张的交锋,其中也包蕴着政治身份和立场的论战。论语派故意压低自己“无心隐居”“迫成隐士”时社会性,加大对毫无立场与不宣传什么主义的张扬,表面看似远离三十年代政治,而实际上却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正如阿多诺所说:“强调作品的独立自主性,这事本身就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性和政治性”[9]76。更何况,当周作人以自由主义的言志派出现在此时的文坛时,就已经把他们的政治姿态包含在其中了。或许相对于文章中具有讽世意义的批判性内容,论语派认为对性灵的呼喊、对言论宽容的强调,以及幽默的心态与闲适的笔调才更能显示他们自由主义的立场。
在三十年代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不同政治力量干预下的文学创作也是对文学场话语的一种争夺。面对左翼和国民党的政治权力,论语派不得不在夹缝中建构自己的文学话语——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言志文论。但正是因为打扮成一副名士模样,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左翼文人的高度警惕。左翼中的不少批评即将周作人等人对晚明性灵的提倡和所谓新文学乃“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追溯视为试图夺取文坛之正统。陈子展在《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中说:“我想怕是他做了这次新文学运动的元勋之一还不够,再想独霸文坛,只好杜撰一个什么‘明末的新文学运动’,把公安竟陵拾出来,做这次新文学运动的先驱”[10]371。林语堂对类似的一些批评予以回击,表明自己提倡小品文并无争夺文坛之正统的野心:“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物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感,他人尽管办刊物专登短篇小说,我能禁止他么?”[11]173不过,即使林语堂坚决否认,论语派试图取得小品文的文学合法性的努力已在文字之间凸显,而他们在这种努力之中所依靠的理论支撑正是性灵幽默,并通过上溯晚明性灵小品的方式从文学史中寻找足以立于经典的力量。
在这番对话中,论语派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文学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在抓住性灵幽默的核心话语的同时,不得不降低他们“迫成隐士”与“开卷有益”中对小品文正经内容和现世性的呼喊。由于论语派对言志派形象的有意建构和实践,以及三十年代政治环境干预下文学论争等因素,论语派的社会性和现世性成为众人遗忘的对象。
二、小品文现世性的生成
其实,在论语派的文学观念中,言志性灵的文学与小品文内容的正经性、现世性并非如论争时那般水火不容。正如《论语社同人戒条》中“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所表明的,他们文学创作重点在于“真”、在于“性灵”,但“真”和“性灵”不是意在超脱尘世甚至羽化而登仙,所谓“老实的私见”指的是立足个人的表达,既可向内表达一己之私情,亦可向外言及社会国家。“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同样也彰显了他们自由取材的主张,但并未有意消解文学的正经性而堕入趣味化的玩乐。即便被世人忽视或误会,论语派在确立了言志派形象的同时,在各种言论和创作中却从未放弃过对小品文正经性和现世性的提倡与实践。
林语堂在《我们的态度》中针对世人将《论语》的幽默误解为说笑滑稽进行回应,他说:“我们不想再在文字国说空言,高谈阔论,只睁开眼睛,叙述现实。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重观察现实罢了”[12]85。论语派反对文章流为空泛虚无之物,提倡写作应专注观察现实,如此才能既不做正襟危坐的道学文章,也不出专为滑稽逗笑之语。《人间世》第2 期的《编辑室语》中“凡一种刊物,都应反映一时代人的思感。小品文意虽闲适,却时时含有对时代与人生的批评”[13]2的说法将论语派闲适的小品文笔调与小品文内容的批判性、现世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林语堂曾表明《人间世》办刊是立足真诚的文学,为中国的杂志打开一条生路,救中国杂志无聊消遣之死相:“西洋杂志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知识,增加生趣。中国杂志是文人在亭子间制造出来的玩意,是读书人互相慰藉无聊的消遣品而已。本刊为要打开此一条路……”[14]16此番表态与吟风弄月的名士派早已相去甚远,他们所提倡的文学是饱含着真诚的态度和现实的关怀,显示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焦虑时既有一种个性的主张又有一番入世的热烈。
在这样的文学主张之下,纵观论语派的创作,虽然有一些文本陷入了单纯说笑的尴尬,可仍旧有不少内容有着浓厚的现世情怀,执着于人生和社会现世,这些内容或是有着幽默也难以掩饰的批判锋芒,或是做到了在闲适笔调中“开卷有益,掩卷有味”。随着三十年代出版业走向成熟、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一个面向所有公民开放性的、由对话所组成的,且具有批判性的公共交流空间也日渐扩展,《论语》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好地运用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启蒙”的功能。《论语》“只谈老实的私见”的文章涉及面不可谓不广,发挥了一份现代报刊的文化职能和政治职能。1932 年的《论语》上《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吴佩孚的名教救国论》《如何救国示威》等文章只看题目便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强烈的批判意味,而《中国何以没有民治》类似于鲁迅《灯下漫笔》般的短文,批判的矛头直指国民性;《法治与脸》中对现代社会仍遗存着的等级制进行讽刺,类似这样的文章以内容而言甚至已经不止于论语派所说的温和而宽容的幽默,而是接近左翼凌厉的讽刺。连论语派自己也对《论语》上文章笔力甚猛的讽刺产生了警惕,《论语》第6期的《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中说:“看来似乎论语想负起移风易俗的重责,每期认定要打倒一位假偶像。这又未免太认真了”[15]209-210。此后的《论语》直白犀利的批判渐少而幽默含蓄的批评增多,或是讽刺“无能校长”“无脑县长”(第25 期征文),或是讨论现代教育问题(第52 期征文),或是分析农民生活(第69期征文),虽不再凌厉却也包裹着讽世的意义,或许这样的写作才更能显示其“迫成隐士”的心态和实质。
论语派的“性灵”并非完全指代晚明的名士风度,其中应该包含着自己的意见与现实的关怀两种因子。读者评论:“觉论语之言,皆他人所不敢说,不肯说的,就是肯说,也不如论语上的痛快,看后只使我连连点头,无其他说话,因为我想说的,论语早为我言之矣”[16]359。他们的文字既有针对三十年代黑暗暴戾环境的批评,也有对于社会风气的评点,还有对于左翼文人的指摘,谐谑与正经之间的漫谈正是他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的实践。
《人间世》上虽也有姚颖《政治上的推与拖》这等辛辣的文字,但“开卷有益”的创作更多地指的是“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2]2,其中内容大抵写山描水、听雨赏花、怀人感事,虽不如《论语》上文章之锋利,但如《今文八弊》(林语堂)、《换一个年头吧》(老向)、《流落在日本的一部中国书》(王贻谋)等文章对日常和书斋生活的描摹也绝不是玩物丧志。《宇宙风》同样“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议论则主通俗清新,记述则取夹叙夹议,希望变成一佥于现代文化贴近人生的刊物”[17]54。论语派这两份专注提倡小品文的刊物在作文上同样以“真诚”为准则,以自由取材为度量。相较于当时文坛那些呼喊浮泛之言,论语派更看重对现实人生的体悟与表现。在《宇宙风》第1 期的《且说本刊》中,他们认为去除虚伪的、道学的姿态,以自由的、宽容的、诚实的态度来对待现实和文学,如此才能拥有“现代的人生观”,人能近情、能现实,方能于国有益。由此看来,在世人虚伪叫嚣的文学工具论中,论语派书写日常生活的闲适小品文是在尝试恢复读者对现世日常的感受力,增加对现代实生活体悟,把人情与自由宽容复归于人,所谓“开卷有益”大抵指此。这种小品文的提倡与实践,表面似乎吐露了逃世的、消极的名士气,也不可否认有不少小品文的确堕入了庸俗琐碎之中,这也难怪左翼会对此大加攻击。但仍有如林语堂、周作人、老舍、丰子恺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作者的一些上乘之作(如陶亢德《二十来岁读者的读物》、莫石《唐人与支那人》、何容《保证人》等)在闲适笔调中闪耀着人文的关怀和光芒,也消弭了晚明小品文中朝代末期的放浪形骸而注入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
三、小品文现世性的传统资源
“无心隐居”而“迫成隐士”的论语派正像周作人所描述的:“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的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18]18。鲁迅也曾表明“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19]538。无论是周氏兄弟所点评的古代隐士和山水田园诗人,还是论语派的“迫成隐士”姿态,背后都有道家思想个性的外形下儒家的精神内核作为底子。当古代士人满怀用世的理想却又四处碰壁、无计可施时,归隐往往是他们共同的路向,看似恬淡超远实则满腔牢骚,隐逸仍不忘“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何况乱如魏晋、残如明末,逃至“药、酒、女、佛”也终不能做到“坐忘”“心斋”,儒家的用世与功利从未被消弭。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代的风云际会与混乱黑暗使每一个有良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不能真正置之度外,论语派在《论语》第一期的《缘起》中所说“《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1]1的创刊缘由已鲜明地体现了他们的功利性与现世性。虽然论语派喜爱的是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个性精神,但他们对于袁中郎用世的热烈亦持有欣赏态度。尤其是论语派在宣告自己的名士身份后仍不时表现出的批判与启蒙的姿态,或许很难说不是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儒家思想的显现。尚不论周作人把左翼判为“载道”的偏激之处,左翼文学中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精神实在是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妙体现;但相比之下论语派所选择的用幽默和暗讽的方式所进行的合法主义的反抗与批判也不能说就不具备儒家现世的精神与效用。
不过,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迫成隐士”后作为本真的“文士”而不在作为斗争的“志士”:“在目下这一种时代,似乎春秋比论语更重要,他或许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之狂澜,跻国家于天平。不过我们这班人自知没有这一种大的力量,其实只好出出论语”[20]46,因此他们在强调“开卷有益、掩卷有味”时,多注重小品文对日常生活的表现。他们对生活现实的关注,对人真情真性的表现,离人生之切近,仍未脱离原始儒家的现世精神。而这与他们欣赏的公安派以及公安派的精神资源之一——李贽的“原儒”紧密相关。李贽反对假道学,但并不反对孔子和儒家,甚至其对人性自然的认同也是他诠释原始儒学的结果。《论语·里仁》中说:“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21]46。虽然有对君子为人道德的强调,但这种强调却是建立在对人欲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孔子之所以“吾与点也”也是欣赏曾点的近情。受李贽“原儒”的影响,公安派的小品文中有着大量表现日常生活现世性的文字,或许晚明异端们的人性与真情正是对原始儒学以人文本的一种复归。论语派多次表明自己对孔子的欣赏,但他们所重视的是“须知孔子是最近人情的,他是恭而安,威而不猛,并不是道貌岸然,冷酷居然于千里之外”[22]22,他们用小品文表现最切实的人生、最真诚的生活,以期消解目下文学中那些呼喊式的虚伪性。论语派在此进一步诠释了“迫成隐士”的身份,试图淡化儒家的功利性而突出其现世性中的人本色彩。
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迫成隐士”和“开卷有益”之中,论语派将原始儒学的意义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完成了文化对译,使原本传统的“迫成隐士”与“开卷有益”之表达具有了现代意味,其中涵盖着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文化资源的融合性理解。
论语派虽然对三十年代的政府大体上是认可的,但不愿对其阿谀奉承,说些肉麻主义的话,更不愿如左翼般推行革命与暴力,可他们对世事又未能完全忘却。既然无法“进”于三十年代“庙堂”之上,也无法真正“退”入山林,他们在守住言论的自由与宽容的基础上,在个性主义的烛照下:“进”以报刊介入社会和文化批评,在杂文中以凌厉之笔出之,笑骂政府和国民性;“退”以小品文笔调书写日常生活,在听雨赏花、人物山水中展现世道人心,又不失去闲适小品文的现世意味,这或许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此番创作姿态,都是他们“迫成隐士”之后试图于世有用又能真实以待的努力。因而,当左翼文学将论语派视为无聊、逃世的文字并认为他们想以此“争得文坛正统”时,论语派虽然进一步举高自己性灵幽默的旗帜,但也不时作出对自己文章的辩解,不断强调小品文的现世性:“在反对方巾气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在介绍西洋文化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这句话也是我自幼念惯‘今夫天下’之遗迹”[11]171,“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23]209”。不以文学为工具而以真诚的态度的写作,才能通过饱含着生活与生命体验的现世性作品沟通读者,从而有益于世道人心。
四、结语
在论语派性灵幽默之下,虚掩着他们文学创作的现世性,而“迫成隐士”与“开卷有益”即是他们对这种姿态的诠释。但现世性又未必与性灵、幽默、闲适之大旗背离,走入“方巾气”的悖论之中,而是在他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真诚的小品文创作态度之下,借以传统资源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既能出之以犀利热烈,又能言之以轻松闲适。因此,他们曾经“用世”和“讽世”的尝试和意义、在“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的号召中为小品文内容的广泛性打开的平台、在“迫成隐士”与“开卷有益”中对小品文创作真诚和现世性的强调,都不应该在既往对论语派及其小品文的固有理解中,堕入“玩物丧志之文学”的印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