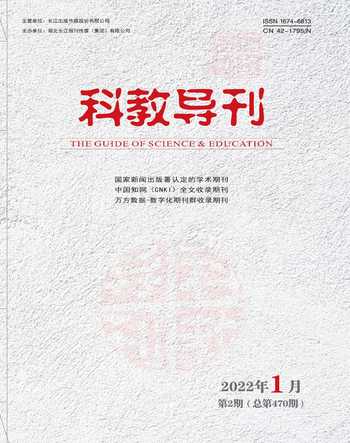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价值指向
何苗
摘要荀子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命题,因其对天人关系的全新界定而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学界多从自然观的角度加以解释,其实这一命题具有浓厚的道德价值意味:荀子思想中的“人”具有双重属性,“制天命而用之”所表达的是以人为主体,以“礼义”为道德评价标准而指向客体——万物,从而赋予万物以价值色彩。
关键词 制天命而用之《天论》;价值指向;礼义
中图分类号:B222.6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j.cnki.kjdk.2022.02.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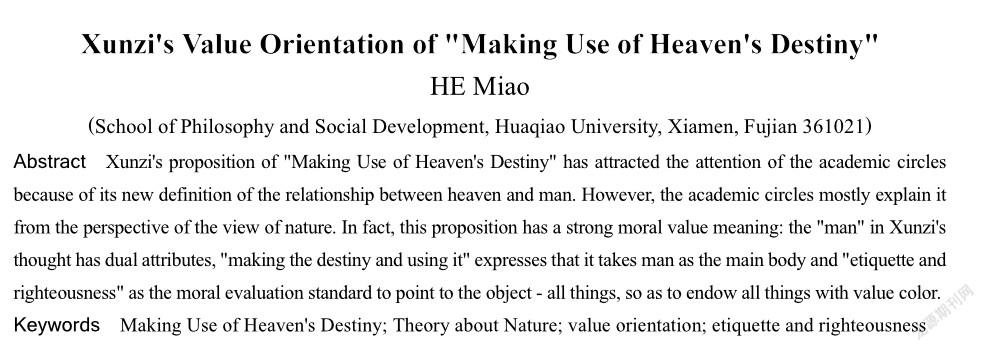
学界关于“制天命而用之”的解读一直存在爭议,其中较为一致的一个说法是人对天生之万物加以合理的安排,即“天生人成”。但在如何实现“人成”的理解上仍存疑,实则“人成”表明的是一种指向性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是人与天生之万物,此万物包括天地人三者,人是指向的发出者,万物为被指向者,“礼义”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中介。人以道德价值判断指向物,并为物定“名”、明“分”,确定物的价值等级,使物具有人以“礼”为标准所赋予的道德价值。
1“制天命而用之”的文本阐发
对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命题的解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主要将这句话引申解释为“人定胜天”,认为其展现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对荀子这一超时代的积极主动思想表示推崇。至近二十年,研究者们已经基本抛弃了这一独断的解释,转而从整体文本着手加以诠释。大致说来,目前学界对“制天命而用之”的解释方式都是将训诂与义理的阐发相结合。
“制天命而用之”一句中,“制”为动词,“天命”为动作的承受者,而“制”前面并无主语,通过《天论》文本不难发现“大天而思之”(《荀子·天论》)整段的重点都落在后半句“孰与”所为,其所探讨的都是人所应当的问题。因此,动作发起者是人。此处的“而”字表示的是递进关系。“用”同样为动词,主语与“制”同。“之”字作为代词,指代的是“天命”。因此“制天命而用之”即是人“制”“天命”并“用”“天命”。
1.1对“制”“天命”的文字理解
“制”展现的是动作的发起者与承受者之间的关系,即“制”与“天命”是互相阐发的关系。
总的来说,对“天命”的解释主要可分为两类。其一以“天命”为“天之所命”,即天所生之万物。杨倞注:“从天而美其盛德,岂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李中生也说:“荀子说的‘天命’,即天所生之万物。”“天命”在全书中仅此一处出现,但在《天论》中还有一处提到了“命”:“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同上)可以看出荀子所说的“命”表示的是生命:人生命的延续“在天”,国家生命的延续“在礼”。因此杨倞等人将“天命”解释为“天之所命”是符合文本逻辑关系的。第二类解释则是将“天命”解释为一种必然性的力量。
关于“制”字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以杨倞为代表,认为“制”字本义为“裁”,表示“若曲者为轮,直者为桷,任材而用也。”也就是要顺从万物的本性,不可妄为。一类是以胡适为代表,以征服、控制、战胜等来解释“制”。还有一类较为特殊,以严灵峰为代表,他看出了控制、战胜天命与前文所说“人之命在天”的矛盾。因此将“制”解为“则”,把“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同上)前后半句从转折的关系变成了顺承。严灵峰的解释虽然解决了逻辑上的矛盾,但并无证据支撑,且与前后文的语义也难以融洽,所以不可取。
总而言之“制”有两解,“天命”也有两解,若只考虑辞章训诂之依据,通过排列组合可以产生四种不同的理解。
1.2对“制天命而用之”的综合理解
后来的学者们意识到要想得到恰当的理解,不仅要对字词的可能含义梳理清楚,还需要将“制天命而用之”与《天论》及荀子对天人关系的定位相联系起来考虑。
同于《天论》篇中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这是目前学界解“制天命而用之”的一个共识。因此对该命题的解释也是能否正确理解“制天命而用之”的一个要点。早期有部分学者认为“天人之分”即“天人相分”,从而将天与人彻底割裂开来,形成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断绝了“天人合一”的可能性。随着荀学研究的深入,现在普遍较为认同的观点是:“分”作“职分”解,强调的是使人明白天的职分与人的职分,做到“不与天争职”。所以学界多将这一命题理解为天生万物之生是一种生命可能性的赋予,天只给予万物以成其为物的可能性,但要实现这种可能性还需要人加以辅助。即“天生人成”。
这种解释从大方向上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若细细探究,便难免产生这样的问题:自然界中的生物都是自生自灭的,即便没有人的参与,种子也可以发芽长大。那么“人成”的具体细节究竟应该作何理解仍然是一个问题。
2“制天命而用之”的义理阐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者们争议的重点一直都放在对“制”和“天命”的解释上,但是却忽略掉了“用”字为该命题所定下的道德价值基调。并且随着近年来,关于《天论》的定位从荀子“论天”的自然观转变为政治哲学的文本,那么仅从荀子自然观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命题就显出不足了。
2.1《荀子天论》的哲学定位及荀子的天人观
《天论》篇着墨最多的是“天”,因此学界多将《天论》篇理解为一篇荀子有关自然世界的认识论及其天人观思想。但回到文本可以看出全文的整体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天;第二部分论人;第三部分提出人在实践时秉持的标准——礼义。
《天论》开篇即指出“天行有常”,表明天是常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上)。“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同上)都只是天不带有主观情感的功能。所以荀子之天是客观的无道德天。人面对天所能做的只是“应之以治则吉”(同上),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就应该逆来顺受呢?这并非荀子的意图,因为承认天的客观性并不等于否认人的能动性,尊重客观规律恰恰是更好发挥主观能动的性前提。
在说明了天的客观性之后荀子进一步考察人和天的关系,以说明人所处的位置。首先是“明于天人之分”,“分”并非代表天与人的绝对对立,而是作“职分”讲。即是要人明白天的职分与人的职分是不同的。荀子认为天有天的道,人有人的道。在这里荀子指出“天职”就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同上)也就是说天赋予万物以生命,万物得以“形具而神生”(同上)。但天的这样一种赋予是不带有主观情感之生。此时的万物虽得以生,但其所具有的只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是客观存在。所以人应该秉持着一种“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同上)的态度,这是荀子对天人关系的一个明确表态,也是《天论》篇的总体基调。
从“明于天人之分”和“不求知天”中都不难看出,荀子谈天,仅做客观的描述,他的目的在“论人”和“论礼”。荀子所表明的只是主观的态度问题,非客观的能力问题。天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人能不能知天,人如何知天,荀子未曾明说,因为在他看来“求知天”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但他说明了人应持有的态度——“不求”。“不求”就是以客观实在的态度对待天,做到“不慕其在天者”(同上)。
那人就只能被动接受上天的恩赐吗?荀子提出人之治有“治之道”,皆是“在我者也”。这个“道”就是第三部分,也是《天论》的最终目的——礼义。因此荀子作《天论》的动意和目的实乃借由对“天”的阐明,使人“明于天人之分”,在明了人在天人关系中的定位后,从而强调政治治道的重要性。
至此,《天论》的整体逻辑线索就非常明晰了:荀子开篇论天,以恢复自然之天;继而提出人在与天的关系中,应保持“明于天人之分”和“不求知”的态度;“制天命而用之”就是在“明”与“不求”的态度中提出的“人职”,“制天命”的方式即是以“礼义”为标准从而“治万物”。人如何能以“礼义”对万物加以合理的安排呢?关键在“用”。
2.2“制天命而用之”中“用”字的价值指向
对“制天命而用之”的解释,经历了“人定胜天”到“天生人成”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最具争议的就是对“制”和“天命”的理解,而忽略了“用”字对“制天命而用之”命题定下的基调。
“用”为动词,本义使用,采用。因此“用”展示出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双向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价值。因为“用”字本身暗含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指向性,物对人有用表示客体对主体而言有价值,或者说是主体赋予了客体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过程。“天生”是天赋予万物以质料因和形式因,成为具体实有之物,但此时的万物仍然属于独立存在之个体,服从于自然客观规律,非处于荀子所关注的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体系中。“人成”则是人为该独立个体设立目的因,同时促使其朝向这一目的方向发展,从而具有动力因,目的就是为人所用。目的即指向,在荀子这里就是明“分”、定“名”,从而建立起物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如此一来,本为客观独立存在的个体就处在了人对外的关系之中,这一关系又是出于人的主观指向,所以被人指向到的物也就具有了人主观赋予的价值。但是这种赋予关系并非完全主观臆断的价值判断,因为荀子所说的人,不是个体主观的人。
2.3荀子论“人”
荀子在《性恶》篇中有一段话可以窥得荀子在谈论天人关系时所论的“人”其实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原文如下:
“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荀子·性恶》)
荀子设想了一个前社会状态,即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从反面论证了荀子所论之人,是处于社会状态的人。荀子虽未直接加以说明,但他想表达的应是当人处在自然状态时,与其他生物并无区别,即自然属性。但人能够从個体集结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从野蛮的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靠的是“明分”。人如何能“明分”,靠的是先王“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礼义代表的是道德价值的判断标准,族群的维系以其为基准。
总而言之荀子所想要讨论的人,是处于社会之中的存在,并且是出于个体而成为外在之客观的人。这种人除了自然属性之外,还多了一重属性——道德价值属性。所以人在实践时,有两种不同的体系,一种是以自然客观的态度认识世界,一种是以人类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为标准看待世界。但这一标准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在于其出发点在人,对于被评价的物而言,评价结果是人主观给予的;客观在于这一标准是出于人内在主观思想但外在客观化的具有普遍性的体系。当人以社会属性的身份对待万物时,即如康德所说“人为自然立法”,是将万物放入人的道德价值体系中加以评价。
3结语
今以“制天命而用之”之“用”字着手,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切入,结合荀子的整体天人思想与以礼为纲领的哲学框架,重新梳理“天生人成”之具体过程,尝试更加细致地把握住荀子“制天命而用之”中所展现的天人关系。
从《天论》文本的定位来说,必须明了的是荀子论天只是引子,其落脚点在人。他将整个世界依据法则的不同进行了两分,一是以自然规律为准则的“天地”,是“天行有常”;一是以“礼义”为标准的人类社会,是“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但是这样一种区分只是为了更好的指导人类实践,并非将社会与自然隔绝。清楚了荀子的意图,就可以明了《天论》作为荀子政治哲学文本的定位,也就能明了礼义作为荀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支柱,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同时荀子已经将天的道德属性抛弃了,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道德依据并非来源于上天。所以人对客观规律之天应当保持“不求知”的态度,对于“天生之万物”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如何“制”?以“礼”。天所生之万物为一客观存在,皆为自然而有,本无形上或道德价值意味可言。但人能在社会关系中通过“礼”确定自己的定位,也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层级。这一价值层级也是儒家最基本的观念,即孔子所强调的“名实相符”。荀子之天与性皆去掉了形上意味,只有作为处在“分”之等级中的人,才因礼义的规定具有相应的价值。也就是说礼起于人,但人反过来又以礼为标准对万物加以价值判定。将礼义向外扩展,推广至整个世界。
总而言之,荀子的“天人关系”线索是天生人,人制定礼义并反过来用礼义对治天地人,以礼义为框架治理万物。“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即表明人为主体,物为客体,礼义为主体对客体确定价值等级之工具,这就是人何以能对物赋予价值。荀子之理论是一个由理性为主导,以具有社会性质的“人”为中心的体系。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战国)荀況.荀子校释(修订本)[M].王天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4](清)杨柳桥.荀子诂译[M].济南:齐鲁书社,1985.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李中生.《荀子》“制天命”新训.学术研究,1994(5).
[9]晁福林.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管子学刊,2001(2).
[10]董祥勇.论析“不求知天”“知天”和“制天命而用之”的逻辑关联.船山学刊,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