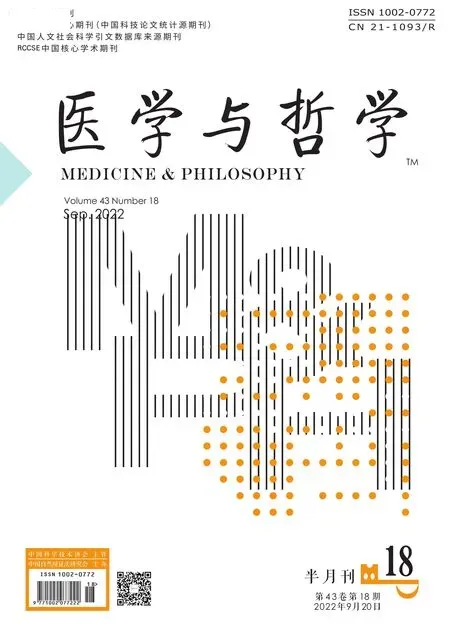《淮南子》形气神的身体理论
谢海金 李良松
成书于汉初的《淮南子》不仅集先秦汉初道家思想之大成,而且融儒、墨、医、法、阴阳等各家思想于一身,其中蕴含的形气神身体理论既吸取了诸家思想之长,又独具汉初思想之特色,是研究汉代身体哲学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1 引庄解老、儒道竞进的思想倾向
汉初,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外之书与《中篇》八卷,并献《内书》二十一篇于汉武帝,“上爱秘之”[1]。东汉高诱为之作注,称此《内书》原名《鸿烈》,经刘向校定后更名为《淮南》,此即今本《淮南子》之名的由来。后因流传之故,《淮南子》原文出现残失,至北宋集贤院校定时仅存十三万余字,是为现今通行本《淮南子》之底本[2]。
自《汉书 · 艺文志》始,历代史志多将《淮南子》归为杂家,近代学者如范文澜等亦沿袭此说。对此,不少学者都作过评议,如陈静[3]认为“列《淮南子》入杂家有理由也有失公平”。高诱认为“其旨近《老子》”,将其思想大旨“归之于道”,近代胡适[4]、梁启超[5]235等赞同此说,称其为“集道家的大成”“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冯友兰[6]早年视其为杂家,后将其归为黄老道家。熊铁基[7]则明确说《淮南子》不是“杂家”,而是“新道家”,亦即盛行于汉初的“黄老之学”。
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与黄老道家在治国思想方面有“天壤之别”[8]183,在对待认识、知识的态度上“背道而驰”[8]193,《淮南子》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之一恰恰是“转变了汉初黄老的思想方向,引庄解老,把黄老治国思想引向了消极避世和个人养生,在汉代开启了道家往神仙道教过渡、发展的方向”[8]214。
笔者更倾向于徐复观的观点,虽然《淮南子》蕴含了丰富的道家思想,但其中的儒家思想的地位“并不次于道家”[9]171,儒道可谓是“平流竞进”[9]175。陆玉林[10]亦从思维框架与逻辑结构两个方面,论证了《淮南子》儒道的分野与整合。
这种引庄解老、儒道竞进的思想倾向,在《淮南子》的身体观中也有所体现。一方面,《淮南子》继承并强化了道家“贵身”的思想,认为身体与天下本为一体,主张“贱物而贵身”[11]701“身得则道得”[11]358。另一方面,它又将道家“贵身”的思想与儒家“修身”的思想混合在一起,如《淮南子 · 诠言训》(下引此书篇章只注解篇名)中的“反己而得”和“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11]466等说法,与孟子“反求诸己”[12]222和“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12]247可谓如出一辙。总之,《淮南子》中的身体观既主张治身养形、修己正人,又追求精神自得、清静无为,整体表现出引庄解老、儒道竞进的思想倾向。
2 形气神和合的身体理论
两汉的核心话题为“天人之际”,各家各派围绕此话题展开论辩,《淮南子》也不例外。其思想特征之一就是贯通天地人,欲究天地之理、解人间之事、论帝王之道。
与天地人系统对应,《淮南子》将人的身体划分为形、气、神三个层次。其中,精神与形体分别禀受自天与地:“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11]219“气”则充溢天地、贯通形神。在生命视域下,三者的关系被概括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11]39有学者用“形气神和合”[13]的说法来阐发三者的关联与互动,颇为贴切。
“形”在《淮南子》中又被称为“形体”“形骸”等,是可见的、具象的、实体的身体器官的总称,是生命的基础,是生命得以维系、生理机能赖以运行的物质性场所。在《淮南子》中,不仅先后出现了耳、目、口、心、肝、脾、血脉、肌肤、骨髓等身体器官的名称,而且对部分脏器的位置与功能的论述也基本符合当时的医理。总体来看,《淮南子》对人身脏器是有所了解的,这是其身体理论的医理基础。
“气”充溢天地、贯通形神,是生命得以产生的本体,也是维系生命的关键之一。《淮南子》认为天地万物都离不开“气”,因而使用了许多与“气”相关的概念,如天地之气、阴阳之气、精神之气等。其中,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四种:“精气”“神气”“血气”“志气”。徐复观[9]224认为“血气”之说最为恰当,指的是“由呼吸之气,引申而为生命中所发出的综合性的力量,或者可称为生命力”。气的流动与感通促成了形神之间的互动与互通、相应与感应。
“神”概指精神,是生命的主宰,是控制器官运转、支使人体活动的中枢。精神是无形的、抽象的、非实体的,宜“形于内”而不可“越于外”,既可聚而为一,又可散布全身。虽然《淮南子》中论述了大量治身与治国的思想,但归根结底,其主旨依旧是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自得”-“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11]36。这其实是道家“贵身”思想的延续与强化。与之对应的是“身得”之说,曰:“身得则万物备。”[11]36在《淮南子》中,“身”不仅指形体,也包含了精神,且“神贵于形”[11]487。因此,《淮南子》论述治身之道时,特别将“养神”置于“养形”之上,如《泰族训》曰:“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11]679
形、气、神不离不杂、互相影响,三者缺一不可,要“各居其宜”,“一失位,则三者伤矣”[11]39。这里的“位”,徐复观[9]226强调了内外之别,他说:“位大别为‘外’与‘内’,形之位在外,神之位在内,气贯通于二者之间。”笔者认为“位”还可以理解为主次之位,神主形次,神制形从。《原道训》曰:“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11]41神主而形从,即为“处其位”,故“利”;形制而神从,则是“失位”,故“害”。要保障形、气、神三者各居其宜,除要做到节制、爱惜与保养以外,还需下一番持静、戒躁的工夫,兼顾养神、和气与平形。此三者正是《淮南子》形神关系理论在养生方面的具体落实与运用。
3 “形”:天人相应,自得于身
3.1 天与人:天地宇宙,一人之身
《淮南子》提出了天地内化于人身、人身外象于天地的观点。一方面,人的身体是一个小的天地,“天地宇宙,一人之身”[11]249,人的身体器官有序运转,就像天地自然有序运行一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另一方面,人与天地相参,“孔窍肢体,皆通于天”[11]126,人的身体形骸与天的自然气象一一对应,如《精神训》曰:“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11]220-221人的精神与形体都禀受于天地,天人之间表现出相似、相应与相通的关系。
上述“天人相应”的思想,亦见于《春秋繁露》《黄帝内经》等书中。《春秋繁露》主张“天之副在乎人”[14]319,《黄帝内经》则明确说“人与天地相应”[15]451。如《黄帝内经 · 灵枢 · 邪客》列举了天地之日月、九州、风雨、雷电、四时等,与人体之两目、九窍、喜怒、声音、四肢等一一对应的关系,从人体的生理结构、诊疗的医学理论等角度,申明了“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15]527的思想。这种贯通天地人的思想取向在之后的传播与传承中得到了改造与发展。
一方面,《淮南子》以贯通天地人为总纲,但“它讲天人感应,以‘精浸相连’为基础,完全立足于自然系统之上”[8]180。董仲舒则赋予了“天人感应”以道德性与伦理性,实现了生理之身与德性之心、自然之天与道德之天的融合,他构建的“身-气-神-意-心”的养生结构[14]452,及其“以中和养其身”[14]444的养生思想,无不浸润着天人相应的思想。
另一方面,中医强调的“三因制宜”,主张对疾病的诊疗方案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变化。这无疑是中医领域对天人相应思想的积极改造与运用,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与辨证治法。以中医经脉为例,《内经》所谓“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15]297,采用的正是“天人相应”的思路,用以说明经脉的存在依据及其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思路符合汉代关于天人、身心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医经脉学说的实践与传承,在临床治疗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不同的经脉,对应不同的月份,因此,随着时间性的日变月移,各条经脉的搏动脉息及其生理功能也会随之变化。这就要求施针时不仅要考虑病症的差异,同时还要兼顾经脉在不同时节的衰旺变化。
总之,汉代天人相应的思想,虽然存在一些牵强附会的时代局限性,但这种将人体与天地进行比附,寻找天地人之间的相似性、对应性、同构性与合一性的思想与方法,在中国的哲学与医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2 地与形:地形之变,心质之别
中医的“三因制宜”认为人的身心状态、体质性格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时令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淮南子》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水”“土”“气”的差异会影响人的身心状态。例如,专论天下地貌特征的《地形训》有“障气多喑,风气多聋”[11]140等论述,总结的是这样的现象:在瘴气弥漫的地方生活易使人嗓喑口哑,而生活在大风之地的人则易耳背耳聋。概而言之,不同的地形、气候、土质、水文与风气,会影响人的性别、夭寿、形态、体质、美丑乃至品行、德性与性格,这是天人相应思想在生理与地理的关系上的具体落实,其规律与原理表现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11]141。
由此出发,《淮南子》将方位与地形联系在一起,归纳了不同地域人群的生理表象与外貌特征。它将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域,总结了“五方人”的体态特征。以东方为例,《地形训》曰:“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长大早知而不寿。”[11]145东方多山川河谷,生活在其中的人一般呈现出头小、口大、隆鼻等外貌体态。结合《天文训》的相关记述可知,《淮南子》不仅继承了先秦以来“五行”与“五方”相配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将其与政治上的“五官”“五色”“五音”等,以及医学上的“五脏”“窍穴”“肌体”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兼顾内质与外貌、融通医学与哲学的思想体系。
《淮南子》的“五方人”与《黄帝内经》的“五态人”可以对照互鉴。二者的划分标准与观点指向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立论依据,且整体都表现出“同”中辨“异”,“异”中求“同”的思路。《淮南子》将天地与人体对应起来,从阴阳五行与内质外貌的关联性入手,对人进行区域性、差异化分类的思路,虽有附会之嫌,但“可以看作是科学地建立地理人类学的先导或最早尝试,对于指导临床辨证治疗和养生也具有参考价值”[16]。
《黄帝内经》也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立论依据,认为人的心质体态有阴阳之分、五行之别。《灵枢 · 通天》立足于阴阳,提出“五态之人”的划分观点。《灵枢 · 阴阳二十五人》则“先立五行”“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进一步将人划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大类,每类又包括五种分型,合为二十五种[15]410-422。这样的划分,实际上只是将阴阳五行作为框架,其核心始终是人的身心特征,最终目的则是指导医疗防治,如曰:“古之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15]460
总之,从人的身心特征与分类的角度来说,《淮南子》重在由“天”论“人”,《黄帝内经》则侧重于以“人”论“医”。前者属于地理人类学,后者属于体质人类学;前者更多是哲学上的思考申发,后者则是为了医学上的辨证施治。二者相映成趣,可以互相参照。
3.3 心与身:心为形主,心为身本
《淮南子》中出现了大量与人的身体有关的概念,除“四支(肢)”“五藏”“九窍”等泛称外,大体分两类,一是实体性的脏器,如耳目口鼻等孔窍、肝脾肺肾等脏腑。二是抽象性的概念,如精、神、意、志、性、情等。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概念-“心”,既是身体的脏器,又是精神的主宰,兼具了虚有与实在、具象与抽象、生理与心理的多重特性。
形体有内外表里之分,外为肌肤、四肢、九窍等,内为五藏、骨血、心神等。内为主、为里,外为表、为用,二者密切联系,如《精神训》所谓:“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外为表而内为里。”[11]219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肝肺胆肾与耳目口鼻之间既存在内与外、主与次的明确界分,又通过“心”的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原道训》总括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11]35“心”不仅具有生理的特性,可以驱使四肢的运动、保障气血的流行,而且具有思虑的功能,能够分辨是非、指导处事。
《淮南子》分别从“主”“制”“知”三个方面,论析了“心”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心为之主,心具有主宰地位。《淮南子》认为“心”不仅是“五藏”之一、“五藏之主”,更是“形之主”[11]226、“身之本”[11]686。从医学上的生理构造来说,人的身体是由诸多脏器构成的,诸器官功能各异、各司其职。《淮南子》结合“天人相应”的思想,对上述医理作了感应式、抽象性、哲学化的诠释,认为人的身躯形体之中“心为之主”[11]221。
例如,着重阐发“君人之事”的《主术训》,不仅论及目、耳、口、足等身体器官的功能,而且格外强调了“心”的作用,如曰:“心之于九窍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11]309“心”虽然不能像九窍、四肢一样视听言动,但身体之动静、耳目之视听,都离不开“心”的指挥与协调,“心”在其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第二,心为之制,心具有制约作用。《淮南子》特别强调了“心”的制约作用:“圣人胜心,众人胜欲……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为之制,各得其所。”[11]474-476圣人与凡人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胜心”,后者“胜欲”。所谓“胜欲”,就是片面地追求身体的各种欲求,陷入“嗜欲”的状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充分发挥“心”的节制作用,如此才能“损欲”而“从性”。
第三,心为之知,心具有认知功能。《淮南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论析“心”具有知觉思虑的功能。正面来说,“心”不仅具有生理性的功能,而且能思考、有知觉,能够知事、知性乃至知“道”,如《修务训》曰:“心知忧愁劳苦,肤知疾痛寒暑。”[11]653人之所以能够有忧乐愁苦的感觉,原因就在于人有“心”,就像人要通过皮肤来感知外界冷暖一样。此外,“心”还能“知人之性”“知事之制”,《人间训》曰:“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筦,谓之心。”[11]586“心”不仅能通过四肢、九窍等器官来感知外界的变化,而且可以由一端而推之八极,将天地之道、万物之理、人事之制都纳于一心,进而知事、知性乃至知“道”。
反面来说,《淮南子》提出了“机械之心”与“心之塞”的说法。“机械之心”应源自《庄子 · 天地》的“机心”之说[17]106,意为机巧诈伪之心。《淮南子》认为“机械之心”会使人“神德不全”[11]14,主张“机械诈伪莫藏于心”[11]245。至于“心之塞”,《泰族训》曰:“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于类也。”[11]689耳、目、口如果塞而不通,会导致人出现聋、盲、喑之病。同理,“心”也可能会出现塞而不通的情况,导致人不能充分发挥“心”的功能与作用,使人变得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不懂变通。
综上,《淮南子》从心为之主、心为之制、心为之知三个方面,高扬了“心”的主导地位,申发了“心”的节制作用,突出了“心”的思虑功能,将“心”确立为了人的身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器官,谓之“形之主”“身之本”。“心”成为贯通身体的表里、内外、虚实的核心概念,耳、目、精、神、意等与身体性范畴都与“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淮南子》的心论“以道为本,由道而言道心,由道心而言天心,由天心而论人心,由人心而论德政”[18]。
4 “神”:至精为神,神主形从
4.1 精与神:精通于天,至精为神
“精”与“神”常被视为一组关联性的范畴,或单独作解,或和合并说。二者作为单字概念,早在《老子》中便已出现,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表述的是“道”的存在情况。至于“谷神不死”“神无以灵”则是在形容“道”的功能。大体来说,“老庄以精说明道的存在,以神说明道的作用”[5]221。《庄子》承续此说,并做出了新的延伸与诠释,如将“精”与“神”连用,提出“精神之运,心术之动”[17]116的说法,不仅使用了全新的“精神”的概念,而且将其与天地与人心联系起来,使其开始具有了贯通天人、沟通心物的特殊内涵。
《淮南子》关于精神的思想继承了老、庄的相关论说。无论是作为单字概念的“精”或“神”,还是和合成为新概念的“精神”一词,都频繁出现在《淮南子》之中。三者的关系颇为密切,具体的内涵又稍有差异。
《淮南子》中的“精”,含义主要有三。(1)作名词用时,“精”指通于内外的某种神秘性的存在。如《精神训》“同精于太清之本”[11]229中的“精”,与《老子》所用的“精”字含义比较接近。(2)“精”与“气”联系在一起,则产生了“精气”之说,如《泰族训》曰:“必自精气所以与之施道。”[11]669(3)作形容词时,则指人的精神状态,如《泰族训》的“精诚感于内”[11]664,指的是“心志完全集中于一点,而无半丝半毫杂念夹杂在里面的精神状态”[9]218。
“神”在《淮南子》中亦有三义。(1)作形容词时,指微妙不测的作用,如《精神训》所谓“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11]222。(2)作名词用时,主要指人的精神,如《原道训》所谓“神失守也”,高诱注曰:“精神失其所守。”[11]40(3)代指人的心,如《诠言训》所谓“神制则形从”[11]487,与《原道训》所说的“心”的作用并无二致。需要注意的是,《淮南子》虽未明确说神就是心,但承认了心与神的密切关系。
“精”与“神”和合而成的“精神”概念,既与二者关系密切,又包含了新的含义。《淮南子》有专篇《精神训》,专讲人的身与心、形体与精神。需要说明的是,“精”“神”与“精神”的内涵在《淮南子》中虽然略有差异,但并不存在截然有别的界线,有时甚至可以通用。例如,“精通于灵府”[11]21与“讬其神于灵府”[11]58中的“精”与“神”可互通。“至精形于内”[11]276与“精神形于内”[11]194中的“精”与“精神”亦互通。
4.2 神与气:精气为人,神气相应
战国末期以来,阴阳五行学说盛行,推动了以“气”为核心的宇宙观的发展,进而逐渐形成了视“精”为“气”的“精气说”。《庄子 · 在宥》所谓“六气之精”[17]95已见此说的雏形,《周易 · 系辞上》的“精气为物”[19]则直接使用“精气”一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氏春秋 ·达郁》所谓“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20],则用精气来比附身体的结构、解释疾病的由来。
到了汉代,各家都或多或少受到“精气说”的影响。《淮南子》直接使用了“精气”或“气之精”等说法,虽然使用频次并不高,但涉及多个方面。一是解释万物之生成,如《天文训》曰:“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11]80二是用以说明人与虫的分别,如《精神训》曰:“烦气为虫,精气为人。”[11]218三是用以阐发感应之机理,如《泰族训》曰:“妖灾不生,非法之应也,精气之动也。”[11]679徐复观[9]217概括《淮南子》的“精气”为“一种特殊纯一的气,流贯于天地及人的形体之中,并成为天与人、人与人及人与物互相感通的桥梁”。
与“精”相对的概念是“神”,二者与“气”相合,又衍生出一组紧密联系却有细微区别的概念-“精气”与“神气”。“神气”在《淮南子》中的涵义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神气”侧重于内在与深层,故曰“神气不荡于外”[11]48;二是“神气”与“精气”略有不同,但都与人的身体和生机密切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神气”之说在传世的先秦典籍中并不多见,但到了秦汉之际,却突然流行了一段时间,贾谊用“神气之所会”来解释“性”[21],王充则用其来解释人的生死[22],董仲舒则用其来解释人的喜怒哀乐。以董仲舒为例,他曾用“日月”“川谷”“神气”来类比人的“耳目聪明”“空(孔)窍理脉”与“哀乐喜怒”,用以解释人体的构成,以及人体与天地的关系[14]355。虽然董仲舒对“神气”并未做出更加详细明晰的解释,但大体可以看出“神气”在董仲舒哲学中是一个颇具神秘性色彩与身体观意味的概念。
4.3 形与神:神贵于形,神主形从
《淮南子》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分别禀受自“天”与“地”,其中“神贵于形”,因而要以神为主、以形从神。如前所述,“形”分内外,内有心肺等脏器,外有耳目等孔窍,这是形体的内外之分。但若换一个参照,将“形”与“神”放在一起比较,则“神”为内,“形”为外,“气”则贯通内外、调和形神。
精神是无形的、抽象的、非实体的,既“形于内”,又可“越于外”;既可聚而为一,又可散布全身。所谓“形于内”,强调的是精神的形成与作用,更多依赖于身体的内在脏器,特别是“五藏之主”的“心”,如《泰族训》所谓“藏精于内,栖神于心”[11]668。《原道训》所谓“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11]23,其中“心”的作用,亦即“神”的作用。
而“越于外”则是在强调精神的作用,可以由内向外扩充,进而影响耳目口鼻等体外器官的运转。《原道训》曰:“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䁝然能听,形体能抗……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11]40人之所以可以视物、听声、言语与思虑,不仅是因为人拥有耳、目、心等形体器官,更在于人可以发挥神与气的作用,使气充盈于器官之中,令精神支使器官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虽然认识到了精神可以“越于外”,但明确反对精神过度的外越,主张“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认为这是“至神”“圣人”的表现。这种主张,同时也符合《淮南子》“以中制外”[11]32、“从外知内”[11]532、“内顺而外宁”[11]668的思想。
为了强调精神内守而不外越的主张,《淮南子》从正反两面做出了论析。它认为耳目口鼻等孔窍是精神的门户,而门户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使精神通过门户而驰骋于外,进而感知外界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与外界之间设置了一道阻隔,避免精神与外界发生直接的、过度的接触。耳目一旦沉迷于声色之乐,就会引发五藏摇动、血气涤荡、精神外越等连锁的身体反应,最终导致人面临旦夕祸福。因此,保养精神的方法,重在“节欲”“反性”“去载”,具体做法包括“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等。总之,人的身体是一个内外结合、形神兼备的有机体,内藏与外官、精神与形体紧密联系、互相影响。
——修身与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