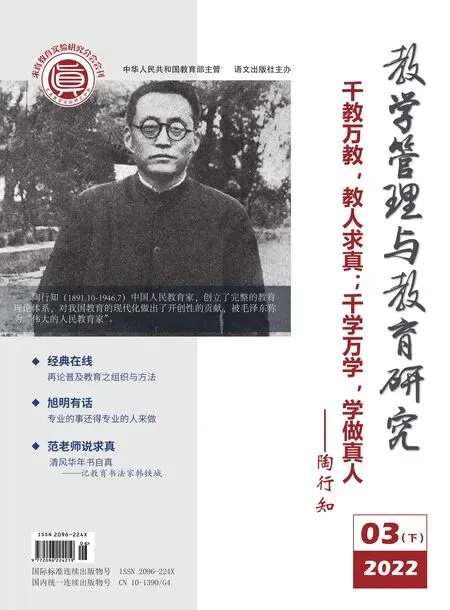再论普及教育之组织与方法
陶行知
组织与方法应该打成一片,才能发出力量。这个道理,我在上一期的本刊内已经略为说明。同时我指出了主张保学、二部制、短期小学诸位先生排斥“即知即传”和“小先生”之错误。现在觉得还有一些意思没有说完,要借这个机会补充出来。
(一)保学采用“即知即传”便一变而成村学、家学。照中国现在的力量,多数县份只能办到一乡设一小学,或一联保设一小学。教育部新近订定每一千人之地设一短期小学,每五个小学区至十个小学区,即五千人至一万人之地,利用一普通小学作为中心小学,这就表示迷信普及学校式教育现在所能达到之限度,所以保学还只是少数地方才能办到。但是如果采用“即知即传”之方法,有了传递先生和小先生之帮助,则乡学或联保学立刻可以分裂成保学。力量能办保学的,如果采用“即知即传”方法,立刻可以分裂而成村学、家学——一村乃至一家是成了一个文化网或文化细胞。
(二)二部制采用“即知即传”便一变而成多部制。现在所提倡之间时二部制或半日二部制还跳不出学校范围,因此很难超过二部——每教师教两级。倘使运用“即知即传”的道理,每教师教一百人,这一百人每人教二人,统共是教了三百人。这样一来,从人数说它是一变而成了六部制,若从教育场所说是一变而成了几十部乃至一百部了。西桥现在一个大先生也没有,六个小先生教六十几个小学生,这六十几位小学生同时又做了小先生教导一百余人,总共是有二百人受教育。它是没有大先生也办成了等于四部制的东西。问它怎么能够办到如此地步,只须采用“即知即传”的方法即能办到。
(三)短期小学采用“即知即传”便一变而成为长期学校。短期小学是一个不幸的名字。它给了大众一个“短命文化”和“学问有止境,并且止得很快”得不良暗示,但我们也不必在名词上推敲。如果短期小学之倡导者,同时提倡“即知即传”“小先生”“传递先生”,那么这所短期小学在质的方面立刻起了变化,在量的方面立刻加倍又加倍。它无须叫学生学了一年便停学,因为免费教人的先生多了许多倍,大家都可以继续求进了。这样一来,短期教育是一变而成为长期教育。
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很快向着殖民地进行。帝国主义之侵略加上了天灾,是不能梦想花许多钱办教育。在这义务教育开始的时候,教育部努尽了力,从国库里只弄到二百四十万元充义务教育经费,加上边疆教育费五十万,庚款八十万,总共只有三百七十万元,分配全国,如何够用?各省自筹之六百八十万,能否筹足已成问题。即使勉强筹足,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无非是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贫困如此,还不采用穷办法,真实令人不解。即使有钱,也当充分采用“即知即传”的原则,另人民自求长进。那省下的钱可以治河、造林、修路……一定要拿来任性挥霍,也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