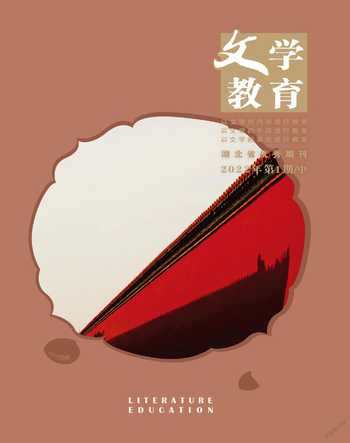生态翻译视域下的谢灵运山水诗典故翻译
高雅仪
内容摘要:谢灵运山水诗的典故蕴含着情景里的哲学思考,翻译能否正确传递典故蕴含的哲思与理念,是能否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交流的关键。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探究译者如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话语建构性和跨文化话语性的基础上,从译者选择的语言、文化、交际三维转换原则角度切入,在典故翻译过程中不断地进行适应性选择,从而创造出“生态优化”的译文,转化文化形象,重塑诗歌意境,传达谢诗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理念,带给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类似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原则 山水诗 谢灵运 典故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中国大力提倡文化对外传播,致力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其中蕴含别致文化美丽的山水派诗歌引起了翻译研究学者的关注。“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刘勰 1958:67)[10]仅此四句就能概括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诗歌的显著特点:用典繁密,说理深奥。因此,谢诗的翻译难度非常大,引起译诗界的关注。
而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自2001年胡庚申提出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被广泛地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所以本文将引用生态翻译学的译者选择视角,深入探讨三维转换原则在指导实际的翻译工作中的可行性,希望能为谢灵运山水诗的翻译工作提供参考和灵感的启发。
一.生态翻译一哲思——生态翻译学理论简述
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生态翻译学的主要内容是以生态学为径,攀登翻译学的高峰。生态翻译学的萌芽,得益于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保护生态的全球性思潮,人类越来越重视生态和谐共生和人类命运担当;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源自于中华悠久文明中儒释道富有哲理的生态智慧,我们既能从中收获经验,也能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奠定道路。
在席卷全球的生态研究浪潮中,翻译界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生态共生,和谐共赢”中觅得一丝良机,相关参考文献也越来越丰富。1988年,彼得·纽马克详细阐述了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与文化关系的主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翻译的生态学特征(Newmark,1988:95)[3]。继前人之智,苏珊·巴斯奈特(S.Bassnett)等学者深入交流、研究,更细致地指出,翻译具有环境适应性与择优生存性,发展出具有生态性质的描述类翻译研究。国际翻译界的新兴生态翻译研究启发了国内学者,而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和《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2013)等著作中,强调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为中心,坚持翻译除工具性之外更具有建构性。而且在描写译学看来,翻译的操控性以及片面性为话语建构性铺平道路。[7][8]此外,翻译还具有跨文化话语性,更不能把文学文本孤立出来,而是要让译文与相关的语篇语境和谐共生,让目的语读者拥有类似源语读者的阅读体验,似乎处在与源语读者相同的生态语境之中。
生态翻译学的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自然选择和译者选择。在译者选择阶段应坚持三维适应性转换原则,可以理解为多维转换,其实质是以三维转换为中心,包括语言维度的适应性转换、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和文化维度的适应性转换。(胡庚申,2013:235)[8]其中,语言维度的适应性转换是指从词汇、句法和语篇的角度看待汉英语言系统的差异,如汉语是一种倾向于意合的语言,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律诗词曲,都没有特别的虚词,大都是实词,引经据典都是点到为止,全靠读者个人悟性和学识;而英语是一种倾向于形合的语言,诗歌的句法结构若非是诗人特意改变,都要使用介词和连词,考虑主谓宾的关系。文化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关注文化交流、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互为异质文化,相同的文化负载物可能会有对立的文化形象,如“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祥瑞,但在西方文化中代表神秘的邪恶力量。交际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关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化解,尤其是谢灵运某些诗歌拥有很多来自儒释道三家的典故,内含多层意义,译者要为高效的文化交流做取舍。
二.穷理观物一诗作——谢灵运山水诗典故来源与特点
“一草一木皆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贴切地形容了寄情于景色的山水派诗人的心境。自东汉末年谢灵运开创山水派以来,众多诗人也开启了观景怡情的道路,但未有人能超越康乐山水诗那充满哲思的一山一水。这不仅是因为谢灵运学富五车、天资聪颖、放浪形骸,还是因为他从儒释道三家中获得灵感,虽然仕途多舛,但他却成为一位自由的山水诗人。
谢灵运山水诗歌的典故主要来源于《诗经》、《楚辞》和儒释道三家的经典著作,具备引经据典、寓情于景、穷理观物的主要特点。他的“山水”既有佛学的三清净,在诗歌的起承转合中兼顾自身修行的“起累-伏累-灭累”,又带着玄言诗穷尽真理不罢休的执着,同时观物之彻底,不仅让读者流连在山水花草之中,而且在美景中潜心问理,上求天文地理,下知为人处世与清净无为,进则为天下忧,退则不为世事所扰。而且,谢灵运喜爱化用《诗经》的典故,使用叠音词和联绵词,侧重情感的抒发,如他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一句就袭用《诗经·小雅·四月》“秋日凄凄,百卉俱腓”。这就要求译者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对哲学深刻的见解。
三.灵活转换一译作——生态翻译学于谢灵运山水诗典故英译的应用
1.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
这个层次的转换主要是因为汉英两种语言的语法体系等的巨大区别,所以译者不得不根据文本语境和目的语文法习惯进行转换,以期达到创作性的翻译效益。这种选择和转化往往是译者运用各种知识和考虑各个方面的结果。一般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具体体现在韵律转换、句法转换和语篇转换三个方面。其中,韵律转换是将原文的韵律模式替换為相应或相似的韵律模式,以达到相同或相似的音乐效果,有节奏和韵脚两个维度的考量;句法转换指译者转变句子等形式结构,来表达原文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态度,又或是把深奥的哲理禅思明晰化,有词序和句式两个维度的顾虑;语篇转换是从生态语言学和功能语法的角度切入的,考虑到汉英传递信息的差异,有主位结构与语篇衔接两个维度的探究。
而典故翻译,从语言维转换的角度来看,顾虑的主要是韵律转换的再创作,即译者需三省自身:“是否能创作新的韵律?”“新韵律能否达到音美、意美和形美的效果?”“目的语读者能否拥有近乎一致的阅读体验?”
例1:
原文:嫋嫋秋风过
译文1:On autumn days the wind goes howling past[2]
译文2:Where autumn winds bluster and breeze[1]
“嫋嫋秋风过”来自谢灵运所写的《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典故出自《楚辞·九歌·湘夫人》“嫡煽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意为树木不堪秋风而落败摧残之貌。谢康乐创作此诗时,心怀感伤,思念故友,寄情于山水之间,缅怀人生苦短,但又因观乎天地险幽、乾坤浩渺,顿悟佛学妙理,明白一切不过凡尘俗世的喧嚣,倒不如游览山水,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超脱自我,与天地共存。“嫋嫋”描写了风动之景,是诗歌景物的一个特写,对于读者的审美体验十分重要。
所以著名汉学家傅乐山(J.D.Frodsham)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创作出译文1的翻译版本,译为英文中的拟声词“howling”。“howl”一词意为怒吼、呼啸,形象地表现了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又有无边落木萧萧而下的场景。而且英文字母“h”的发音类似于一声叹息,一读起来就有一种悲哀的酸楚油然而生,瞬间让读者穿越时空的桎梏,来到那位山水诗鼻祖的面前,一同感受秋风呼啸的情景,心酸而又无可奈何。
而译文2的译者戴维·亨顿(David Hinton)采取头韵的手法,贴近汉语叠音词中“叠”的概念,“bluster and breeze”读起来朗朗上口。而“bluster”和“breeze”都是描述起风的景貌,前者是呼呼大风,后者细微小风,两者并用也能显现出当时狂风乱作的景象。
总结来讲,译文1和译文2在话语重构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前者倾向汉语叠音词中的“音”,后者则是叠音词中的“叠”。两者都是很好的参考译文,为译诗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外,因为汉语偏意合,英语偏形合的差异,各位译者为了英语语法的衔接通顺都加上了介词或连词,如“on”和“where”,体现了语篇衔接的转换。
2.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文化维度上的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始终考虑文化因素,包括文化形象、文化负载词、文学典故与民间习俗,进行适当的转换,以便清晰地传达文化内涵。正因为每个国家或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和生存环境,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负载文化的术语。文化负载词是指体现某一民族独特生活方式的特定文化中的词语、短语或习语,可分为社会类、生态类、物质类、宗教类和语言类。从文化维度的适应性转换来讲,文化形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诗歌中,文化形象以意象的形式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生动的语言,揭示话语对象、行为、情感、思想和经验。意象是跨时代跨国界沟通的渠道,是诗歌的灵魂,可以分为感觉图像和抽象图像等。以下的例子充分展现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学思维的创造性话语优势,通过话语重构带给英文读者不一般的审美体验。
(1)保留源语文化形象
当然,音译和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是常用的经典翻译技巧,如:
例2:
原文:龙蠖
译文:a dragon,a measuring-worm
注释:i Tzu Chuan(B),Ⅲ.The measuring-worm draws itself together when it wants to advance.Dragons and snakes hibernate to preserve. [2]
“龙蠖”出自谢灵运的山水哲诗《富春渚》中的诗句“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而译文出自翻译家傅乐山之手,这里的注释追根溯源,来源于典故出处《易经·系辞下》,即“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一方面,直译能让诗文典故保留异国风韵;另一方面,注释能让读者把握谢灵运为人处世“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哲学思想。然而谢灵运学识高深,用典丰富,几乎是“言出必有典故”,若是整首诗下来都是直译的文化形象加一长串的注释,会不得不打断读者的朗读过程,所以还需要译者具备创新性的文化转换思维,如一些西方学者也会采取异化的手法,通过创造新词的方式来保留其中华文化的独特内涵。下面就是亨顿对于“卜”一字的翻译灵活使用这一手法的举例:
例3:
原文:卜室倚北阜
译文:I chi-sited my house on a northern hill[1]
其中的“卜”即卜居之意,源自《楚辞》名篇《卜居》,字面意思是选择居住的地方,实际是借用来表达诗人对人生道路的抉择。这里的“卜”不同于西方的塔罗占卜,而是中华文化中星象之学,即夜观星象,天地相应,从而选择风水俱佳的居所。所以“卜居”一词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直译为“占卜而居”反而有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
亨顿译为“chi-site”,此译文蕴含着中国道家哲理的新造词汇。《老子》第四十二章有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说阴阳交合,经过灵魂的激荡,洗尽铅华,唯留精髓,从而得到和谐的中和之气,得以滋养万物。阴阳平衡是自然之道,“气”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是阐述宇宙哲理的基本概念,是道家卜卦的原理所在。基于这一点,“chi-site”不失為一个好译文。另外,随着近几年电影《功夫熊猫》在全球的热映,“气(chi)”这一概念渐渐地为外国的读者所熟知,所以“chi-site”能带给读者熟悉又新鲜的感受和更为顺畅的阅读过程,这一异化但又保留对应文化形象的手法激发他们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
(2)转换源语文化形象
为了缩小异国文化与目的语读者的心理距离,译者可采用改变文化形象或者添加熟悉的文化元素,如傅乐山和亨顿对于《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中“乘日车”典故的处理:
例4:
原文: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
译文1:Would that I were the charioteer of the sun!
Only this would bring some solace to my soul.[2]
译文2:O but to set out on the sun's dragon -chariot
and sore —that's solace to nurture my spirit,[1]
“乘日车“语出《庄子·徐无鬼》∶“若乘日之车而游于襄城之野。”经过多个朝代学者专家的解读,“乘日车”意为坐上沐浴在阳光中的车马,乘兴而行,潇洒远游,宛如逍遥的鲲鹏,小小一词体现了庄子自由而不为凡世所累的真人本色。而两位译者都加上了“chariot”,即“太阳战车”,这是一种希腊神话元素。太阳战车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希腊神话中驱车驾马的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使他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为世界带来光明。一方面,这消减了道家文化关于光明的文化概念和自由的人生哲理的显化,可能考虑到这种误解的倾向性,亨顿还加上了“dragon”这个充满东方色彩的名词来修饰日车。另一方面,读者能简单通过阅读来体会异国形象与文化,理解全诗的大概意思,也更能达到文化交流的效益。
总之,无论是文化形象的保留还是变异,只要能达到文化沟通、信息传递的目的,都能让中华文化越来越好地走近世界读者。
3.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
译者在交际维度上的转换往往是为了传达原文的思想、价值观和观念,实现原文的交际目的,这种转换在“译者的选择”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诗歌的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的角度来看,译者能否在译作中重塑原文的意境,以及能否准确传达谢灵运化用哲学典故的多层含义最为关键。意境由承载诗人主观情感的“意”和包含客观景物意象的“境”共同组成,而谢灵运喜用典故,特别是引用《易经》的卦象名,这为诗歌意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等待读者一层层地揭开,需要读者拥有丰富的学识和独特的见解。中国读者若是不了解道家文化尚且在读诗过程中举步维艰,更别提初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读者了。因此,译者可通过含蓄与外露、虚实之间的转换,重构了原文的意境。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译者需点明个别典故的深层含义,准确翻译诗中含义,做到意境重塑和意义表达的明晰化,比如傅乐山《初发石首城》中对“中孚”的处理:
例5:
原文:虽抱中孚爻
译文:Though I still held fast to the lines of Inner Truth[2]
“中孚”字面意思为《易经》的卦象之名:“象曰∶ 泽上有风,中孚”,却深藏着哲思义理。中孚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之一,风泽中孚。“孚”与孵同义,因为鸟卵孵化的时间十分准确,所以有“信”的意义;“中”意思是适合、适宜之意。卦形外实内虚,喻心中诚信,所以称中孚卦,是道家道德的基础,也是儒家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含义的典故,直译或者音译只会让实意虚浮,让人不得其意。所以傅乐山直接把“诚信”这层隐藏的意思显化,喻为“内心的真实(Inner Truth)”并大写,化解读者的阅读障碍,促进文化交流。虽然美中不足的是虚化了易典的文化形象,只能依靠更为详细的注释补偿,但是这样平实的语言风格更贴近原作典故的意境。
傅乐山将典故内涵意外露并加注的技巧同样体现在下面的例子中:
例6:
原文: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
译文: The herb of forgetfulness brought me no consolation.
So now Ⅰshall seek it in silence and solitude.[2]
“寂寞”出自《庄子·天道》中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这里是指道家的理想人格,即自由梦境中的真人本色,清净、无为、不争,暗示谢灵运向往隐居避世的田园生活。而且单独一个“寂”字也脱离不开佛学“起累-伏累-灭累”的禅思。傅乐山将此译为“silence and solitude”,既在語言维度适应性转换中达到头韵的效果,又能传达给读者与世隔绝、万物皆空的道家式“寂寞”。而且增添的注释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对道家哲学思考与概念有了更好的把握。
总结来说,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要求译者作为“递话人”,应该重新建构意境,让读者靠近诗人,也让诗人靠近读者,把握分寸,及时准确传达艰深语言所表现的哲学思考和思想感情。正如谢灵运这般“无典故不成诗,无儒释道不山水诗”的诗作,不应该生硬地把文化当做对外输出的“商品”,而是更应该考虑读者的感受,让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双方的交流中绽放出新的“思想花朵”。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翻译理论,分为自然选择和译者选择两个阶段,本文主要从译者选择阶段的三维原则切入,以谢灵运山水诗为例,探究典故翻译的创新性翻译。本文研究固然是不完善的,但是也有许多收获:首先,生态翻译学充分具备对典故翻译的指导性。其次,译者按照“以译者为中心”的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和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解构了翻译亦步亦趋的奴性与复制性,充分发挥了话语的建构性和翻译桥梁性。
另一方面,本论文研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生态翻译学作为一门新理论,在翻译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特别是国内相关的理论适应性研究和更有说服力的定量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本文以宋朝诗人辛弃疾的作品《贺新郎》中的“玉树琼枝相映耀”一句做为总结,期待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工作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工作者共同努力,交相辉映,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参考文献
[1]David H. The Mountain Poems of Hsieh Ling–Yun[M]. 2001.
[2]Frodsham J D. The Murmuring Stream: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Chinese Nature Poet Hsieh Ling-yun (385-433), Duke of K'ang-Lo[M]. 1967.
[3]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Toronto/Sydney/Tokyo: Prentice-Hall, 1988.
[4]陈琳.从生态译诗论翻译建构性[J].中国比较文学,2019,000(002):122-136.
[5]高培.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许渊冲《琵琶行》英译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
[6]黄莉.谢灵运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及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7]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8]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商务印书馆,2013.
[9]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029(006):11-15.
[10]刘勰.丈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l958.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