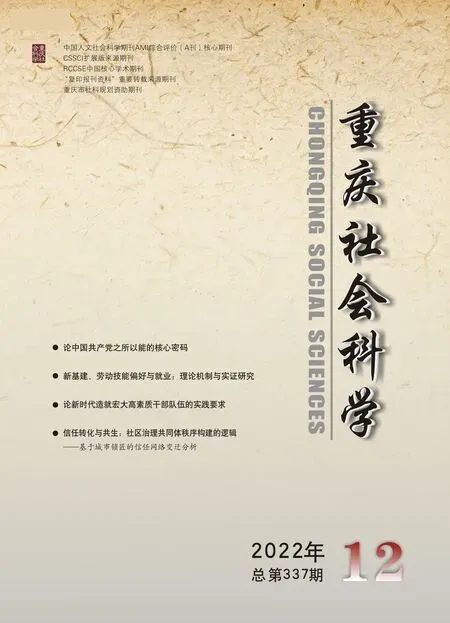《画史会要》作者考辨
周 颖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画史会要》作为明代少有的纪传体绘画通史,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书中对明代画家的考证,堪称明代画史著作中最为完备之作。《四库全书》对其评价是:“其书虽采摭未富,疏漏颇多,而宋、金、元、明诸画家颇赖以考见始末,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画家传中多引以为据,亦谈丹青者所不可遽废也。”[1]民国书画鉴赏家余绍宋虽然对《画史会要》提出了诸多批评,但也认为本书“明代画人传,搜辑颇见勤,至后来考录明代画家者多本之”[2]。近现代文献学家谢巍先生也提出,《画史会要》卷五“画法”一节,收录了很多未见著录的画家之画论,“虽一鳞半爪,然可窥知其所论大概,可资研究明隆庆至崇祯间绘画理论趋向及其发展程度,洵属可贵之史料”[3]420。可见《画史会要》的史料价值是比较高的,是一部明代重要的画史著作。然而,对于《画史会要》的作者认定,至今未有定论。目前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画史会要》的作者为明宗室朱谋垔,而另一种认为《画史会要》的真正作者为明人金赉,朱谋垔不过是托名流布。文献作者的不确定性,无疑影响了学者引用史料的准确性,也有碍于对《画史会要》的进一步研究。今笔者不揣浅陋,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试对此再做详细考辨,以求发掘出《画史会要》的真正作者。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关于《画史会要》作者的几种观点
《画史会要》的作者认定从清代开始便有分歧。康熙四十四年(1705),王原祁等人在奉敕编纂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为金赉撰,续编朱谋垔撰,可见在此之前,已经有两种版本的《画史会要》流传。于敏中等人在乾隆年间奉敕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以及孙星衍嘉庆年间著《孙氏祠堂书目》中都著录为金赉撰。而乾隆年间,纪昀等人奉敕编纂的《四库全书》,清末陈田编著的《明诗纪事》则著录为朱谋垔撰。民国年间,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最早对《画史会要》的作者问题提出了疑问,云:“《画史会要》,五卷,文澜阁四库本。明朱谋垔撰。《佩文斋书画谱》篆辑书目作金赉撰,续编为朱谋垔撰,未详何据。续编今未见,他书亦未见著录。”[2]可见余绍宋当时所见的是四库本《画史会要》,并未见过署名为金赉的《画史会要》,只是对《佩文斋书画谱》篆辑书目中将《画史会要》的作者记作金赉撰表示了疑惑。1925年,莫伯骥先生购得署名为金赉的《画史会要》写本(以下简称“写本”),将其与家藏刊本(即朱谋垔明刊本)进行对比后认为:“此书似是金氏手撰,久而未刻,遂为谋垔托名流布者,故后来唯明人流传写本尚题金氏姓名,特留此以窥破朱氏伎俩。”[4]150傅增湘先生也同样藏有署名为金赉的写本,但他与莫伯骥的看法相反,云:“《画史会要》五卷,旧写本。题 ‘云岩默老金赉敷奇氏撰’,‘颜巷逸人校’......前有自序,言曾续陶九成《书史会要》一卷梓行之,故更为此,则仍朱谋垔所撰。”[5]傅先生认为,虽然写本题名为金赉撰,但因序文中有“曾续陶九成《书史会要》一卷梓行之”,加之傅先生藏有朱谋垔续陶宗仪《书史会要》,故而他认为《画史会要》的实际作者应该为朱谋垔。1949年后,学者们对《画史会要》的作者问题讨论较少,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薛永年先生才再次对此问题进行了关注。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提到:“《画史会要》明清抄本多作金赉撰,《佩文斋书画谱》称‘金赉撰,朱谋垔续编’。近年学者已据松南书舍抄本自序认定为朱氏所撰,成书时间为崇祯四年(1631)。”[6]之后,不少学者都引用了这一说法,但将金赉视为《画史会要》作者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俞剑华在《中国绘画史》中引用史料时云:“金赉《画史会要》:‘画嫘,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7]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附录——历代画学著述明代部分,便列有“画史会要五卷,宁藩支裔朱谋垔隐之著”“画史会要,金赉著”两条,[8]将其视作两本不同的著作。二十世纪末,谢巍先生在莫伯骥先生的基础上再次对此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得出结论为:“金氏之书撰成在前,朱氏乃取之重纂,改头换面有删有补,而以己名付梓。《四库全书》本《画史会要》,显然可知乃取金氏、朱氏两书之长而合为一体,兹本以题署金、朱二人之名为宜。”[3]375-376近年,美术学家韦宾在《中国画学文献史略》中再次提到了《画史会要》的作者问题,他认为“朱谋垔有《书史会要续编》,已见余绍宋《解题》著录,朱谋垔写《画史会要》,与此关系很大。谢巍金赉《画史会要》五卷《考证》辩解《书史会要续编》非朱谋垔作,理由过于牵强,因此,《画史会要》作者问题,仍可深入讨论”[9]。可见,《画史会要》的作者问题依旧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主要原因,是署名为金赉的《画史会要》写本自莫伯骥及傅增湘以后便未见流传,给考辨工作增加了难度。
二、金赉本《画史会要》疑点辩证
认为《画史会要》为金赉所作的学者,主要以莫伯骥先生和谢巍先生为代表。不过,笔者仔细分析二位学者所列出的证据后,发现了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证据非但不能证实《画史会要》为金赉所作,反而增加了其作伪的嫌疑。
莫伯骥先生认为《画史会要》是金赉手撰,久而未刻,遂为朱谋垔托名流布。他列出的论据主要有二。第一,他曾在1925年购得《画史会要》写本,此本前题“云岩默老金赉敷奇撰,颜巷逸人校”,后有金赉表弟跋文,证明金赉确有其人。但是,莫先生在其论述中,并未提供其他材料佐证金赉的身份,笔者翻阅史料,也未发现金赉及其相关的记载。可见,莫先生对金赉其人的身份认定,仅仅是建立在他所收藏写本的署名和金赉表弟的跋文之上的,支撑材料过于薄弱。第二,莫先生列出写本中的文本与其家藏刊本(即朱谋垔明刊本)存在诸多不同(尤其是对明宗室朱多、朱多启火攵、朱统鍡的称呼不同)。为清晰起见,本文特列表于后,将莫先生提及写本和刊本之间的异文部分作一整理与对比,同时列出《画史会要》现存其他版本,以兹佐证。
由表1可见,莫先生所藏写本与刊本之间,存在18处异文,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第一,文字在传抄过程中因形近或音近而产生的差别。如条4、5、6、7、10、11、12。第二,由于传抄中的脱字、衍字而产生的不同。如条1、9、13、17。第三,由于避讳或说法不同产生的差异。如条8、14、15、16。第四,书籍流传时受损而产生的不同,如条2、3、18。莫先生将以上异文视作朱谋垔托名流布金氏著作的关键证据。他认为,因为朱氏为明宗室,所以条14~16中的异文部分,是朱氏为了隐瞒自己托名作伪的事实,将自己包装为《画史会要》的作者而刻意作出的改动。而其他条目中的异文,则是朱氏袭取金氏之作时出现的错漏或作出的改动。但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如条7中,写本将“韦鸥”用墨笔改为“韦鶠”,刊本及其他版本都记作“韦鸥”,如按莫先生所说写本在前而刊本在后,刊本应当与写本一致作“韦鶠”,断不会选择写本认为错误的,已经划去的“韦鸥”之说。另外,条1、4、5、6、9、10、11、12、13、17中的异文都为传抄时产生的,除了写本之外,其他版本的说法都一致。笔者对这些条目中的传主进行考证后发现,刊本及其他版本的记载才是正确的,写本为误记。如果说刊本是抄袭写本而作,那意味着朱谋垔在抄袭的时候,必须对写本中的画家一一进行校订,并且还对条1、17中写本没有的画家进行了补充,这对一位抄袭者来说,似乎于理不合。笔者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写本出于刊本之后,为抄袭之作,误抄或漏抄了上述条目中的画家,才产生了这些异文,而条14~16则是金氏为掩盖身份篡改之故。但笔者也留意到,条2“张僧繇”中,写本比刊本多十余行,且后面多录了十一人;条3“顾野王”写本有而刊本无;条8“胡环”写本记为“山后契丹人”,而刊本则记为“范阳人”,这几条似乎与上述推断有所抵牾。不过,我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朱谋垔刊本在明清易代时曾受到严重毁坏,朱谋垔之子朱统鉷也是四处寻求遗本才能重修此书(详见朱统鉷《重修诸先刻并言》),说明到了顺治年间,朱氏明刊本已经相当稀少,更遑论保存完好的原书了。所以莫伯骥所藏的朱氏明刊本,极可能为受到破坏的残本,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所见明刊本无跋的原因。此外,笔者对比《画史会要》的其他版本,上述第2、3、8三条,重修本、松南本、《四库全书》本皆与写本一致,这更增加了笔者上述推断的可能性。由于松南本和四库本皆确定出于写本之后(因为康熙四十四年前写本已经出现)。如果写本实属抄袭之作,只可能抄袭自朱谋垔明刊本和朱统鉷重修本,鉴于朱谋垔明刊本在入清后已经留存甚少,金赉写本很可能袭自朱统鉷重修本,而本文后面也论证了这种可能性。最后,莫先生还提到写本和刊本均有相同的前序,序文皆有“国初天台陶九成著《书史会要》九卷,余为序一卷,即梓行之”之语。朱谋垔有《书史会要续编》续编传世,但并未见资料记载金赉有此著作。对此,莫先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序号《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七年)1 卷一无“尹长生”一条 有 有 有 有金赉写本(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朱谋垔刊本(崇祯四年)朱统鉷重修本(顺治十六年)松南书舍抄本(清代)共十八行,三百五十四字,下列有袁昂等十一人3 卷一“陈”下列“顾野王”一条 无 有 有 有4 卷一“隋”下列“昙摩拙乂”一条 昙摩拙义 昙摩拙义 昙摩拙义 昙摩拙义5 卷一“唐”下列“尤全”一条 左全 左全 左全 左全6 卷一“唐”下列“裴请”一条 裴谞 裴谞 裴谞 裴谞7 2卷一“张僧繇”一条内容共十余行,后列十一人共四行,后未列其他人共十九行,三百五十四字,下列有元昂等十一人共十七行,三百五十三字,下列有袁昂等十一人卷一“唐”下列“韦鸥”一条后用墨笔改为“韦鶠”韦鸥 韦鸥 韦鸥 韦鸥8卷一“五代”下列“胡环,山后契丹人”一条胡环,范阳人 胡环,山后契丹人 胡环,山后契丹人 胡环,山后契丹人9 “五代”下列“杜,一作措”一条 杜楷,一作措 杜楷,一作措 杜楷,一作措 杜楷,一作措10卷二“北宋”下列“古武卫将军令松”一条右武卫将军令松 右武卫将军令松 右武卫将军令松 右武卫将军令松11 卷二“北宋”下列“李申”一条 李甲 李甲 李甲 李甲12 卷三“金”下列“周兼则”一条 周廉则 周廉则 周廉则 周廉则13卷四“明”无“刘原起,字我用,长洲人”一行有有有有14卷四“明”下列“朱子讳多火翼”一条启攵火 启攵火 启攵火 启攵火先子讳多 先子讳多 先子讳多 先子讳多15 卷四“明”下列“朱多”一条 先从叔多 先从叔多 先从叔多 先从叔多16 卷四“明”下列“朱统鍡” 石城王孙统鍡 石城王孙统鍡 石城王孙统鍡 石城王孙统鍡17卷四“明”无“王显”“许宝”“米万钟”有有有有18卷四“明”下列“张萱官至郡太守”一条张萱官 太守 张萱官 太守 张萱官太守 张萱官 太守
谢巍先生与莫先生持同样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考证。他认为《画史会要》由金赉撰成在前,而朱谋垔则取之重撰,改头换面,有删有补,并以己名付梓。谢先生的论据主要有三点,前两点主要围绕《画史会要》跋文进行讨论,现将两个版本的跋文列于下,以兹备览(加点文字为两则跋文之间的异文部分):
颜巷逸人跋[4]148-149
表兄敷奇氏撰《画史会要》,令予校而录之。兄于丹青家能原本伊始,以及支裔,采摭博而比属精,立诸小传,必甄量品行,后及艺事。兄少负奇志,力自奋于膏粱纨绮中,好苦吟,为《山居百咏》,明枕流漱石之意,故其风寄高脱,驰骤笔墨间。蚤擅旭素之长,更从双钩响榻探得卫、王遗法。登涉之余,即景成图,一时能者,惊服其雅不可及。兄既高介自立,无世俗游,寓苍玉居,吟啸其间,其诗可求而其人不可得而识。著作日富,岁有成刻,兹其庚申夏午告成者是也。
朱 宝 符 跋[10]585-586
宗叔隐之氏撰《画史会要》,令不肖符较而授之梓。叔于丹青家能原本伊始,以及支裔,采摭博而比属精,立诸小传,必甄量品行,后及艺事,则所尚焉者,端自有在,不徒丹青家考镜已也。叔少负奇志,力自奋于膏粱纨绮中,好苦吟,为《山居百咏》,明枕流漱石之意,故其风寄高脱,驰骤笔墨间。蚤擅旭素之长,更从双钩响榻探得卫、王遗法,今则斯邈,宜官皆赴笔端,固草书家一大成也。又移而用之皴斮点擢,无不争妙,登涉之余,即景成图,若李营丘、高尚书、倪迂、米颠,不必专有宗尚,往往任其侔合,一时能者,惊服其雅不可及。雅之属,为清、为古、为流澹而闲远。叔既高介自立,无世俗游。筑寒玉馆,艺大竹万竿,轩楹之际,冷碧萧然。列古彝鼎图史,吟啸其间,或韵人墨士,茗饮燕谈,移日不倦,非其人而以剥啄来,叔为张廌氏矣。叔翰墨名蚤动天下,仕宦吾地者多愿与定交,而固高泄柳之节。其笔可求,其人不可见也。南海苏紫舆公令新建,急一见,叔屏驺从,径入竹中,乃相与把臂。苏好叔草书,临仿数月,惟肖,悦慕若此,竟不因以干牍,亦往往令来不报谢。苏终于官,廉不能具礼。独叔一人经纪其事,曩奔走于令,而数数干牍者迹杳然也。我豫章昔有徐孺子风义千载,而后叔庶几焉。盖叔之制行也,清而宅心也。惟清惟古,则世情都尽,无所于累。为疏淡为闲远,而不能自秘于笔墨之间。余因述画,偶举一二若此。至其孝友之笃,与人交终始不易,禄入赢余,多从施散,不择报也。以若其情,背炎而向于冷,与世人偏其反,而曩剑江胡吉甫跋《书史会要》能备述之。叔著作日富,岁有成刻,兹其崇祯辛未撰也。
首先,谢先生认为,写本跋文中提及“兹其庚申夏五告成者也”,且是书所录明人多为万历和崇祯前后去世,故此处的庚申年应当为1620年而不是1560年,否则书中所录明人一半都不及知闻之。而朱氏刊本已言明成于崇祯辛未年(1631),迟于写本十一年撰成,故在时间上,朱氏具备袭取金氏著作的条件。但笔者认为,谢先生仅仅依据“庚申”二字和书中所录画家的生存年代,就断定写本的成书时间为1620年,显得过于轻率。根据前文我们知道,写本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之前就有流传,故写本作于此前是毫无疑问的。而1705年之前的庚申年除了1620年外还有康熙十九年(1680),虽然写本中未收录明末清初的画家,也不能排除其成书于清初的可能性。比如王毓贤康熙辛未年(1691)所作的同类型画史著作《绘事备考》,所记画家也只记至明正德年间为止,其后不增一人。
其次,谢先生认为,写本有颜巷逸人跋,刊本无跋,重修本有朱宝符跋,且两个版本的跋文中都有“高介自立,无世俗游”之语,而金赉号云岩默老,寓苍玉居,可知其身份为隐士,与“无世俗游”相称。朱氏虽号厌原山人,但其身份为明宗室,且与诗人墨客乃至风雅县令都有交往,实与“无世俗游”之说不符,故朱宝符跋有作假的嫌疑,可能是袭取颜巷逸人之跋,敷陈成篇。不过笔者认为,谢先生此说也不能成立。第一,明代自取别号、法号、道号之风甚盛,上自帝王宗室,下至布衣贱民都以此为尚,例如明武宗自号锦堂老人,世宗自号天池钓叟[11],华山王朱常汛号心源道人[12],景德镇烧瓷工匠昊十九自号壶隐老人,又称壶隐道人[13]等等。仅凭金赉号云岩默老,寓苍玉居,就确定其身份为隐士,略显轻率。第二,“无世俗游”不光可以理解为不与世俗之人游,也可以指与人交往时不涉世俗之事。谢先生将此直接等同于只与隐士交往也显得过于狭隘。第三,两则跋文之中都记有“少负奇志,力自奋于膏粱纨绮中,好苦吟,为《山居百咏》”“著作日富,岁有成刻”,点明了作者出身富贵。如果金赉出身富贵人家,且“著作日富,岁有成刻”,当不至于在历史上被湮没至此。反观朱谋垔,出身于宁藩乐安王府,封为奉国将军,与出身膏粱纨绮相符。第四,宁藩始封王为宁献王朱权,在史学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居常穷究史籍,曾奉勅纂《通鉴博论》及《汉唐秘史》。并且朱权特别注重对后代的教育,曾作《家训》6篇和《宁国仪范》74章,并以此作为族人的行为准则。在朱权的教育下,宁藩家族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出现了不少醉心文史、艺术之人。如瑞昌王府奉国将军朱拱枘、朱拱榣“兄弟二人好学儒雅,而拱榣尤辩博,有智数……拱枘子多炘,拱榣子多火贵并博雅有文”[14]。朱多煴“性澹雅好学……购异书数万卷,耽玩校雠以为乐,终老不厌也。”[15]石城王府镇国中尉朱谋“贯穿群籍,通晓朝廷掌故……暇则闭户读书,藏书甚富”[16]129,曾作《邃古记》《古今通历》《天运绍统》等。弋阳王朱多焜“宽和,喜文雅事”,著有《忠训堂集》[17],且承宁藩祖风,于嘉靖年间刊刻《宁藩书目》。奉国将军朱多炡“自束发被服儒术,多所旁观古图史传记……又明习国家故实,博通当世务”[18],诗文书画无一不精。而朱谋垔所在的乐安王府中,乐安王朱拱椤“以文雅才辩著称,兼精绘事,绘菊石妙绝一时。”[19]谋垔之父朱多“精于史传……家有清晖楼,北眺龙沙,旁窥鹤岭,法书名画盈积几架,春秋晴雨苍润满帘,披卷临玩,怡然自适,善写墨菊,亦喜作仙道人物。子八人,各令习一雅技”。[10]550从叔朱多雅启火攵有诗癖,“苦心琢句,鲜秀自异。有《滋兰堂稿》数卷……写墨竹,醉后颓然,肆笔挥洒,自谓具真草篆隶四法,良足尚也”[10]550。兄朱谋壡工画花鸟,其画有鲁治、周之冕的神韵。朱谋“博学工诗,常曰:‘作诗不根本《骚》《选》,师法六朝以上,终落下格,’故于《文选》一书,熟精其理。行草法《圣教序》,楷法欧阳询,而风神不乏,为世所珍”[20]294。在这种家学环境的滋养下,朱谋垔“著作日富,岁有成刻”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他的著作和刻书见于文献记载的,除《书史会要续编》《画史会要》之外,还有《唐雅同声》《江西宗派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寒玉馆正续帖》等[16]1803,与跋文中所说亦是相符的。
第三,谢巍先生针对莫伯骥先生忽略的序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朱谋垔如序言中所说的一样,有《书史会要续编》一卷行世,而未见金赉有此著作,也不能说明朱谋垔就是《画史会要》的作者。他提到,朱统鉷重修《书史会要续编》时,版籍不存,底稿已失去大半,意味着朱统鉷重修的《书史会要续编》已非谋垔之旧,可能为朱统鉷托父亲朱谋垔之名而作,故不能印证序言所说“余为续一卷,既梓行之矣”。而写本颜巷逸人跋中云金氏“著作日富,岁有成刻”,且“蚤擅旭素之长,更从双钩响榻探得卫、王遗法。”故不能排除其作有《书史会要续编》但未能流传的可能。笔者认为,朱统鉷《重修诸先刻并言》中所说的版籍不存,底稿已失去大半,是针对谋垔所有著作而言,并非专指《书史会要续编》,故不能由此推断《书史会要续编》的藏稿遗失大半。并且朱谋垔除了书画史会要外,还有《分韵唐诗》《山居百首》《钟鼎考文》等已经成刻的著作,而朱统鉷只完成了书画史和钟鼎文的重修,也侧面反映了这三本书的留存情况相对较好的事实。此外,朱统鉷还提到:“庚寅,督学使延昌樊公祖相招,闻而惋惜,慨然捐资五十金,命不肖遘求遗本,补葺故物。而散之四方,藏之经笥者,又安能立致乎?”[20]548已经交代了统鉷四处访求《书史会要续编》散落于各处之遗本进行重修的事实,也是该书耗时九年才得以完成的原因。即便是当时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的藏稿已遗失大半,也不能否认朱谋垔曾经续编《书史会要》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如果金赉真的“著作日富,岁有成刻”,为何现在没有一部留存下来?故谢先生此说过于牵强,并不能成立。
总之,上述学者对于朱谋垔作为《画史会要》作者的种种质疑,如将他们的论据细而绎之,多有偏颇,并不能成为判定朱谋垔抄袭金赉著作,托名流布的切实证据,反而进一步证实了朱谋垔才是《画史会要》的真正作者。
三、《画史会要》作者别证
判断《画史会要》是否出自朱谋垔之手,除了消弭上述疑点之外,还应该从《画史会要》的文本出发。因为作者的身份在他的著作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体现,作者的社会身份以及知识积累不同,必然导致他对社会生活的认知、感受及审美取向有异,表现于著作之中,即会形成言说内容及话语方式的明显差异。本文以四库本《画史会要》作为范本,对其文本进行了仔细分析,确实也在文本中发现了不少证据,可资证明《画史会要》为朱谋垔所作。
首先,笔者查阅《画史会要》的文本,除了前文提及的“先子多火翼”“先从叔多启攵火”“石城王孙统鍡”等几条可判断作者身份外,发现还有许多帮助我们判别作者身份的内容。如卷四“刘廷敕,江右人,善白描佛像人物,游南阳,与吾宗孔炎、子厚善”[10]541。这里所说的南阳孔炎、子厚是指明代唐藩宗室朱硕、朱器封父子,陈田《明诗纪事》云:“硕,字孔炎,唐定王桱六世孫,封镇国中尉……博雅好收藏,书画鼎彝,罗列座右,尝出所藏《唐人理帛图》《东坡山谷像》与王元美品题,鉴别精审,不愧摩天王文孙。诗亦才藻翩翩,在宁国王孙宗良之次……器封,字子厚,硕子,封辅国中尉。”[21]书中以“吾宗”称呼二人,无疑点明了作者的宗室身份。又如“黎民表,字惟敬……每道豫章,必为吾宗舣舟酬和,数日乃去”[10]547。豫章为南昌的古称,朱谋垔的家族宁藩正是分封于此。而在黎民表《瑶石山人稿》中,也的确收录了很多与宁藩宗室的唱和诗,如《朱宗良、用晦、贞吉、巍甫、佳甫、杨懋功、方士功、赵修甫邀集东湖草堂》《朱孔阳携酒舟中因赠》《解维后,方土功、朱贞吉、孔阳追送至龙沙龙光寺,小饮而别》《余徳甫、朱宗良、用晦饯予于滕王阁,文休承继至,分得朝字》等[22]。莫伯骥先生在谈及家藏写本与刊本之间的异文部分时,也并未提及这两条,说明署名为金赉的写本《画史会要》中亦收录了这些内容,这进一步佐证了《画史会要》的作者应为明宗室朱谋垔。至于金氏书中为何会出现这些内容,唯一的解释应当是:金氏在抄袭朱谋垔的《画史会要》时,并未仔细考证书中的内容,而是直接照搬,故而出现了这些讹误。
其次,综观《画史会要》全书,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尊崇皇室、明分等级的观念。我国画史著作中历来就存在“尊皇”的观念,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就对历代帝王的书画爱好和收藏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在卷四画家传记中,虽然收录的帝王宗室画家不多,但在编次上依然将其排在各朝代之首。姚最《续画品》在编次上以“圣艺”为首,“臣工”依次,其余的则是“绪流”。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除了在排序方面把皇帝置于各画家之首,还特意将帝王放在目录之前,与其他画家作出区别。北宋邓椿《画继》则专列帝王宗室画事于前,其后依次为“轩冕才贤”“缙绅韦布”“道人衲子”。这些著作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尊崇皇室的画史观念。而观以上诸书之作者,张彦远出身宰相世家,郭若虚为宋真宗郭皇后侄孙且在朝为官,邓椿家世代为官,姚最为梁太医姚僧垣子,曾任齐王宪府水曹参军,入隋,为太子门大夫,迁蜀王杨秀府司马。他们的皇家和官方背景都相当浓厚,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一致体现出了明显的崇皇和注重等级的观念。《画史会要》中的尊皇观念不仅体现在编次方面,例如将帝王宗室置于卷首,还体现在对帝王宗室画家收录的全面性上,这是前所未有的。《画史会要》卷一中的内容,大部分都引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但在帝王宗室的收录方面,明显较《历代名画记》更为丰富,增加了三皇五帝以及三代时期包括“伏羲”“炎帝”“黄帝”“夏禹”“帝启”等在内的十位帝王。秦朝时期,增加了“始皇嬴政”,西汉时增加了“武帝”“宣帝”,东汉则增加了“明帝”,唐代所列帝王宗室画家达9人之多,且备述更加详细。后面宋、金、元、明各朝也都呈现出这一特点,卷二北宋收录了21位宗室画家,卷三南宋、金、元代共收录19位宗室画家,卷四明朝收录了26位宗室画家,收录人数远超其他画史著作。笔者认为,这正是明宗室朱谋垔的皇家意识在其著作中的体现,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他更加关注那些与他一样具有出色艺术才能的皇室宗亲,为其立传,使其名声能够流传。《画史会要》中的崇皇观念,不止体现于此,还体现在注重叙述入传画家与皇室之间的互动上。这点在卷一至卷四的画家传记中都有体现。例如卷一“齐客”一条:“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10]406叙述了客与齐王一同论画的故事。类似的记载还见于画荚者、宋画史、敬君、画工裔、毛延寿、公玉带、蔡邕、杨修、徐邈、曹不兴、顾景秀、陆探微等画家的画传中。卷二“赵元长”一条:“工释道人物,兼工翎毛。太祖令画驯雉于御座,会五坊人按鹰,有离鞴欲举者,上命纵之,径入殿宇搏画雉,上惊赏久之。曾仕伪蜀,以通天文,为灵台官,凡星宿象纬,皆命画之。”[10]463讲述了赵元长在宋太祖赵匡胤面前展示画技,得到太祖称赞之事。燕文贵、陶裔、牟谷、李雄、元霭等画家的画传中亦有类似与皇室的互动记载。卷三“丁野堂”一条:“善梅竹。理宗因召见,问曰:‘卿所画者,恐非宫梅。’对曰:‘臣所见江路野梅耳。’”[10]499记述了丁野堂与宋理宗赵昀鉴赏绘画之事。梵隆、王振鹏、刘夫人、梁楷等画家传记中亦有与皇室相关的记载。卷四“罗素”一条:“嘉靖中以画游吾宗好事家,时江右画者,止能水墨绰绛,至于丹彩,未有嫡传。乃资之游吴下数年,归而作吕廷振花鸟,设色写生,俱能逼真,山林树石,笔障亦大,然闳堂邃宇中物,非文房清玩。”[10]543讲述了宁藩宗室资助罗素去苏州学习吕纪花鸟画法之事。陈遇、王冕、顾禄、相子先、赵原、陈远、盛著、郭纯等画家亦有与皇室相关的记载。在画家传记中加入与皇室相关的内容,无疑在无形中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即与朝廷或皇室保持密切一致的画家,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能够名留画史。通过这种方式,朱谋垔巧妙地传达了其所设定的优先立传的标准,也潜移默化地为后世画家指明了一个实现途径与努力的方向。当然,这也是朱谋垔崇皇意识的一种体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崇皇观念或显或隐地体现于《画史会要》的全书之中,这也是朱谋垔作为皇室成员在书中留下的印记。正如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言:“任何叙事再现的‘想象’内容都是一种中心意识的幻觉,这种中心意识可以认识外部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结构和进程,将这种结构和进程再现为拥有全部形式连贯性的叙事本身。”[23]通过对事件中的某些材料的删除或不予重视,进而强调另一些材料,通过人物的个性和动机的再现,叙事基调和叙事观点的变化,以及改变描述策略等,历史事件便构成为一个故事。故而,综合上述所列的多重证据,笔者认为,朱谋垔才是《画史会要》的真正作者。
四、结语
《画史会要》是明代重要的画史著作,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文献。《画史会要》的作者自清代起便有两种说法,一为明宗室朱谋垔,一为名不见经传的文人金赉。本文通过校勘金赉旧写本、朱谋垔明刊本、朱统鉷重修本以及松南书舍抄本和《四库全书》本《画史会要》中的异文部分,发现其并不像前辈学者所云能够作为朱谋垔抄袭金赉著作的证明,反而提供了朱谋垔才是《画史会要》真正作者的关键证据。而书籍文本的编排方式、叙述策略以及书后跋文中的一些细节描述,也印证了《画史会要》作者身份为明宗室的事实。故笔者有理由认为,《画史会要》的真正作者当为明宗室朱谋垔。该书初刻于崇祯四年(1631),明末战乱时其成书、底稿与版籍受到严重毁坏。朱谋垔长子朱统鉷为了使父亲呕心沥血之作能继续流传,四处求购遗本,于顺治十六年(1659)完成了《画史会要》的重修工作。而金赉写本《画史会要》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应该是抄袭自《画史会要》重修本,改头换面,伪称为自己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