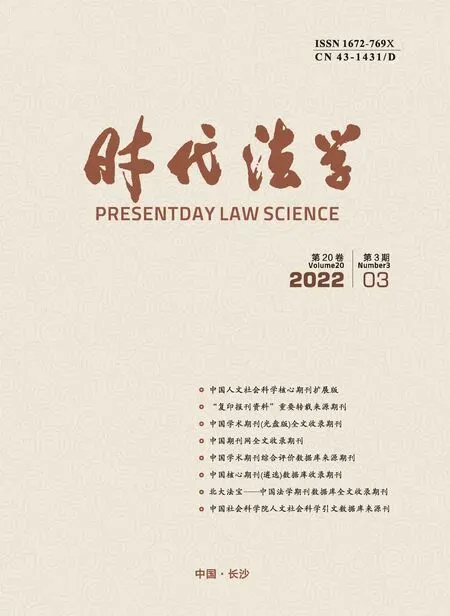论对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的法律规制*
肖姗姗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未成年运动员是指18周岁以下,愿意在专门人员的监督下从事与其年龄相适应的专业体育活动的运动员(1)基于未成年运动员监管的特点,本文所指的未成年运动员,主要是指未成年人专业运动员,并不包括职业运动员、业余运动员。。近年来,未成年运动员被暴力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如2009年我国14岁的足球少年母诗灏被教练体罚致死案、我国举重冠军邹春兰自16岁时起食用“大力补”致不育事件、2016年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性拉里·纳赛尔性侵多名未成年运动员案等。运动员的培养周期较长,其运动生涯几乎全在年幼时开启,如一名体操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大致如此:从12~14岁开始参加全国性锦标赛,15岁开始参加国际比赛,15岁至17岁是体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黄金年龄阶段,成年以后退役。研究表明,运动员的优秀资质越来越呈现低龄化的特点,如在当代体操比赛中,运动员竞技水平的高峰期为14~16周岁,在20世纪60年代时,运动竞技水平的高峰期则为25周岁(2)SeeDavid, Paulo.Children’s Rights and Spor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1999,7(1):53-82.。然而,由于体育训练的高压性、封闭性等特征,未成年运动员长期处于脱离其父母和家庭监护的状态,其极易受到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对此,应当从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现状出发,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基础,完善对未成年运动员的法律保护。
一、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主要行为类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简称UNICEF)于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将暴力侵害未成年远动员权利的行为总结为12类,即基于性别、体型或表现实施羞辱、为取得优异成绩而施加过度压力、将性别视为团队选择或特权的先决条件、身体伤害或性侵害、营养和减肥制度导致未成年运动员饮食失调(如厌食症或其他健康问题)、殴打或其他体罚形式刺激未成年运动员以提高表现、在极端环境中通过强迫冒险造成的伤害、使用兴奋剂或其他能提高成绩的药物、同龄人使用酒精或成瘾药物的压力、利用体育锻炼作为惩罚、拒绝充分的休息和照顾(3)See UNICEF, Innocenti Resource Centre,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Violence in Sport[J]. A Review with a Focus o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2010).。我国学者林琼博士根据实证调研,对未成年运动员的暴力现象予以泛化处理,运用扎根理论将对未成年运动员的泛暴力化行为分为硬暴力与软暴力,并进一步将前者分为躯体暴力和体罚暴力,将后者分为语言暴力、经济暴力、冷暴力与心理暴力(4)林琼.教练员对未成年运动员泛暴力化研究——以福建省为例[D].福建师范大学,2015.3.。本文认为,上述这两类划分模式均过于宽泛,超越了法律的张力范畴,有些行为应被纳入职业道德规范的范畴,如对未成年运动员冷暴力、性别歧视等。法律范畴中的暴力( violence),是指不正当或未经授权而非法使用暴力,违背公众自由、法律或公共权利,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的行为(5)薛波,潘汉典.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404.。结合我国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体罚暴力行为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体罚是指“用罚站、罚跪、打手心等方式来处罚儿童的错误教育方法”(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129.。根据《教育大辞典》的释义,体罚是指“以损伤人体为手段的处罚方法”,同时将留堂、饿饭、罚劳动、重复写字几百几千等行为定义为“变相体罚”(7)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535.。体育学、运动学中的“体罚”概念,显然有别于日常运用于教育学的“体罚”。结合实证研究来看,体育运动中的体罚大多体现为非直接性地身体殴打,其可同于变相体罚,通常通过罚站、罚跪、蛙跳、倒立、扎马步、加量训练等方式对未成年运动员实施大量高强度超负荷训练(简称强迫式训练)、惩罚式训练等非人道训练。
运动员进行重复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其创建自动反应和无故障执行,训练可以发展运动员的耐力、力量、技能或表现水平。持续时间和强度是定义训练活动的两个维度。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运动员所接受的运动强度和时间都应该有一定量的标准,在标准范围内实施体育训练有助于未成年运动员的发展。然而,在许多受欢迎但要求非常严格的运动项目中,例如体操,网球,滑冰和潜水,儿童在很小的时候(通常在4至6岁之间)就被迫接受强迫式训练。对这些年龄尚小、身心发育尚未完全的未成年人,多大的训练强度和多久的训练时间为合适?对此,存在区分合理的训练与强迫训练的困难。毫无疑问,未成年运动员要想在运动中取得成功,就必须付出汗水和痛苦,但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有限性,他们不一定知道或理解这一区别。有证据表明,参与强迫式训练的未成年人为了取悦成年人而努力工作,以至于当他们达到身心极限时,也无法发展出对父母或教练说“不”的能力。然而,一些教练有滥用服从的倾向,要求未成年人绝对服从,并迫使未成年运动员做对他们来说太难的运动。强迫式训练会造成暴力的无限循环,并不值得为了极低的获奖概率而强迫未成年运动员从事超出其身心承受范围内的训练。惩罚式训练主要是指在运动语境下,将体育训练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要求运动员参加。对此,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去理解:
其一,惩罚性训练的定义应该与它所包含的行为相关,而不是依赖于这种行为对相关运动员的影响。因此,惩罚式训练并不要求发生物理或其他形式实质性伤害结果或潜在可能危险。其二,在界定惩罚性训练时,无需考察其目的何在。不论以何种目的为理由将体育训练作为惩罚,都是对运动员的人格尊严以及身心健康的摧残。其三,应该从未成年运动员是否同意及教练施以惩罚性训练的目的两个角度来区分惩罚式训练与合理训练(8)See Ron Ensom,Joan Durrant.Punishment of Children in Sport and Recreation: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J]. Coaches Plan,2010,17(2): 43-44.。一方面,未成年运动员同意从事某些体育训练,以发展他们的能力,而非同意接受以羞辱或惩罚的形式参加训练;另一方面,前文强调的是实施惩罚式训练为行为目标,而此处强调的是教练等主体对未成年运动员施以惩罚式训练的主观目的何在,即他们是为了激发未成年运动员的运动技能,还是为了惩罚或造成身体或心理上的不适。
体罚暴力行为虽然不同于直接外化的身体打击伤害,也不一定对未成年运动员造成医学鉴定意义上的轻伤害、重伤害结果,但对这一群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伤害一点都不亚于暴力打击行为。结合实证研究来看,对未成年运动员施以体罚暴力,不仅可能破坏未成年运动员的心血管系统,造成心率过快、心肌肥厚、心脏肥大、血红蛋白失常等损害结果,同时容易造成未成年运动员骨骼肌肉的畸形发育或骨骼受损,还可能导致未成年运动员因激素分泌增量而致使免疫系统降低或破坏。对未成年运动员实施体罚暴力行为显然有悖于生长发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自然特征,即使行为后果不立马显现,体罚暴力行为将给未成年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身体健康、生命长短带来不可预估的长足危害。
(二)兴奋剂滥用行为
“兴奋剂”被视为阻碍体育运动事业健康良性发展的“顽疾”,也被称为体育赛场的“亚毒品”(9)于冲,陈培.从孙杨案看“兴奋剂”为何“入刑”[J].人民法治,2020(06):46-49.。未成年运动员也未能幸免于兴奋剂的滥用。与成年运动员滥用兴奋剂相同的是,未成年运动员滥用兴奋剂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原因。例如,在体操比赛中,训练者经常鼓励未成年女性运动员在重要比赛前服用利尿剂来减重。在举重项目中,未成年男性运动员通常被要求使用类固醇来增加力量。未成年游泳运动员、短跑运动员和自行车运动员也常被要求滥用药物来增加他们的肌肉量。与成年运动员不同的是,未成年运动员更具可控性。对于教练来说,这非常具有诱惑力,因为未成年运动员把自己的全部信任都寄托在教练身上,而教练却在滥用他们的信任,欺骗或强迫他们服用违禁药品用以提高成绩,有时甚至将这些药品冒充为维生素,但实际上很可能有害于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
滥用兴奋剂的行为违反了大多数体育联合会的现有规定,如果成年人欺骗或强迫未成年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即使在未成年运动员被告知并意识到兴奋剂的性质,这一行为都直接侵犯了其健康权,违反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性要求。滥用兴奋剂将给未成年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如产生药物依赖,导致细胞和器官功能异常,产生过敏反应,损害免疫力,引起各种感染(如肝炎和艾滋病)、心力衰竭、激动狂躁等。滥用兴奋剂的危害主要来自激素类和刺激剂类的药物,药品种类繁多,且处于不断地更新调整中。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许多有害作用只是在数年之后才表现出来,而且即使是医生也分辨不出哪些未成年运动员正处于危险期,哪些暂时还不会出问题。国家、社会、家庭、教练等相关组织和人员都有义务保护未成年运动员免受兴奋剂的伤害。
(三) 性侵害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的性侵害并非仅指《刑法》中规定的强奸罪,应为包括强迫性行为、强奸或性侵犯、猥亵等在内的侵犯未成年人性自主权或身心健康权的行为。有数据显示,在年满18周岁以前,每5个女孩中就有1人被性侵害,每20个男孩中就有1人被性侵害,儿童性侵害的比例在8%~18%之间。体育训练场被视为了性侵儿童的理想场所,因为教练、队医等身份的特殊性,使他们接触儿童的身体成为可能,同时也取得了其父母的同意。由此,身体接触可能会在失当行为与性侵害行为之间产生灰色地带,从而导致信息披露不充分,低估了体育运动中针对儿童的性暴力(2%~8%)(10)SeeLaurie Koller.Sage Sports:Protecting Athletes From Sexual Abuse[J].Oklahoma Bar Journal,2018,89(26):7-9.。从媒体报道的159例体育运动性暴力案件中分析发现,98%的施暴者是16至63岁的教练、教师或指导员(11)SeeBrackenridge C H, Bishop D, Moussalli S, & Tapp J.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abuse in sport: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of events described in media repor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08, 6(4):385-406.。也有调查显示,同伴运动员也成为了性侵行为主体之一(12)See Mountjoy M, Brackenridge C, Arrington M, Blauwet 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consensus statement: Harassment and abuse (non-accidental violence) in sport[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6, 50(17):1019-1029.。此外,在体育运动中,对未成年运动员实施性侵害的行为主体多为男性,女性也逐渐发展成为性侵主体之一(13)Brackenridge C.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violence in sport : A review with a focus o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2010.。当然,无论何种年龄、何种性别、何种类别的行为主体,对未成年运动员实施性侵害的过程通常包括四个步骤,即锁定目标——建立信任——创造独处的机会——实施性侵害行为。
从未成年运动员主体来看,其主要体现为易被性侵害、难以察觉被性侵害和性侵害后难以披露。教练员、队医等专业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有诸多机会与未成年运动员接触,并建立起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未成年人运动员年幼弱小,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加之运动服装的暴露和对教练等专业人士的盲从与依赖,导致其容易成为性侵人员所锁定的“猎物”,极易成为被性侵害的对象。相对于成年运动员,未成年运动员由于性知识的缺乏导致其难以发觉性侵害的发生,甚至成为长期被性侵的对象。如在2016年美国体操队丑闻中,涉案队医以检查、康复的名义触碰运动员的身体,对未成年女性运动员实施性侵害,但诸多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并未及时认清自己是被医疗救治还是被性侵害,甚至在成年后都未察觉在幼年时已被性侵害。未成年运动员性侵害的难以披露性与体育运动的特性密切相关。就有组织性的体育运动来看,未成年运动员在遭受性侵害后并没有正当的性侵害报告程序,其无法寻求适当的帮助与披露机制。同时,性侵害被视为个别主体的问题,而非机构内部发生的问题,通常通过开除性侵害主体的办法以求“息事宁人”。此外,体育运动训练的封闭性和父母对培训机构、教练等人员的盲目信任助长了性侵未成年运动员的火焰,致使未成年运动员没办法或不敢向他人披露自己被性侵害的事实。
未成年免受性侵害的前提条件是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法律承认。相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的性权利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健康利益,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被动性、脆弱性等特点。由于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展尚未完全的阶段,性侵害给未成年人带来的损害是无法预估的。儿童时期的性侵害,是诱发人们一系列心理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如抑郁症、恐惧症、强迫症、恐慌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性障碍和自杀倾向等(14)See Briere J, & Elliott D M. Prevalence and Psychological Sequelae of Self-reported Childhood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 of Men and Women[J]. Child Abuse and Neglect,2003,27(10):1205.。这种身心伤害虽然在成人后会有所缓和,但“污名化”和创伤后的二次适应社会问题将给他们带来无限困扰,亦有在被性侵害后恶逆变为性侵害实施行为主体的情形。因此,加强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成为了解决未成年运动员性侵害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成为了完善未成年运动员法律保护体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除却上述三种主要的暴力侵犯未成年运动员权利的行为外,语言暴力也充斥着体育运动场,贬低压抑、嘲讽挖苦、威胁恐吓、哀求抱怨、粗口谩骂、侮辱尊亲等语言暴力方式十分普遍,伤害了未成年运动员的自尊与自信,导致未成年运动员的性格暴躁,甚至人格变态(15)林琼.福建省教练员对未成年运动员语言暴力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4(4):58-63.。强迫未成年运动员节食以保持体重或抑制发育等情形也为运动场所常见的暴力现象,体育运动员之间的欺凌行为,尤其是年幼的运动员遭受年长运动员的欺凌现象也十分常见。随着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随着体育业的市场化、产业化,一种更加平等、公开、强调教练与队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师徒关系”才是现代体育的主流。类似于家长制的传统师徒关系,师傅权威凌驾于个人权利和隐私之上,未成年人没有反抗的余地,只有服从。一旦反抗或试图脱离,那就意味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何有效地对侵害未成年运动员合法权利的行为予以法律规制,是保障我国体育事业长足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暴力侵害行为法律规制的体系性考察
目前,我国对暴力侵犯未成年运动员权利行为的法律规制主要散见于《刑法》《民法》《行政法》《未成年人保护》《教育法》《反兴奋剂条例》和《体育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并呈现以下特征:
(一)以专门法原则性规定为基础
未成年运动员的主体身份具有双重属性,即运动性与未成年性,对他们的行为规范及权利保护的专门法律法规有《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体育法》作为规制体育活动的专门性法律,对基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可能存在的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如该法第27条明确提出了应当对运动员实行严格、科学、文明的训练和管理;第34条规定了体育竞赛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在体育运动中严禁适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禁用药物检查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严格检查。《反兴奋剂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兴奋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体育运动参加者提供或者变相提供兴奋剂。对于性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体育法》并未有专门性的法条予以规定。但《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多个条文涉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如该法第21条明确规定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41条规定“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
就具体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的法律规制来看,专门法规定了应当以体育社会团体章程中的行业规制和行政处分作为前置处罚手段。如对于体罚暴力行为的规制,前提在于区分体罚暴力行为的适当性与违法性。虽然适当的体罚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未成年运动员的运动机能、有效提高未成年运动员的运动水平,但应当注意该行为是否符合体育训练的限度标准。若超出必要的范围,则构成违法。同时,对于体罚暴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应当通过体罚类型、体罚程度、被体罚运动员的年龄和精神状况、参与体罚的自愿性等四个要素的综合考量。对于此种行为,根据《体育法》第49条、第50条规定,首先应当由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这一特殊主体,则依法给以行政处分。《体育法》对于兴奋剂滥用的行为规制,也可追溯至上述两个法律规范。《反兴奋剂条例》对兴奋剂滥用行为虽设专章规定了法律责任,但从其具体规定来看,仍将行业规制和行政处分作为前置处罚手段,并对特定情形作出了二年或四年的从业禁止规定。对于性侵害未成年运动员权利的行为,专门法并未就这一特殊侵害行为的法律责任予以明确规定,而是将其作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种形式,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9条予以原则性规定,即“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均以抽象的原则性规定为主导,行业章程中通常规定停职、停薪、行政记过等一系列处分方式,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对相关行为违规性与违法性的衔接。同时,也体现了对体育活动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行为的职业性与规范性要求,为规范运动员所在单位责任与教练员责任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二)以行政处分与民事赔偿为补充
除却专门法的原则性规定外,我国对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分,对违法性的体罚暴力行为的具体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行政处分与《民法》中的侵权责任篇中。
行政处分,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对隶属于它的犯有违纪行为或轻微违法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人员的一种行政制裁。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和开除八种。结合实施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我国现有法律体系规定了对教练员等特殊主体的行政处分措施。在实践中,对于具有特殊身份的暴力侵害主体,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如在辽宁省锦州市“教练体罚学生用便池水洗脸”一案中,“便池水洗脸”是一种人格侮辱式体罚,作为专业培养体育人才、负责全市竞技体育训练基础工作的事业单位,锦州市文化旅游体育服务中心就此对涉案跆拳道教练员戴某某进行警告处分,并将其调离教练员岗位;在“江苏宿迁市赛艇队教练体罚”一案中,宿迁市体育局对涉案教练方某作出停职、停薪、行政记过等一系列处分;在“马俊仁强迫队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一案中,前国家田径运动队教练马俊仁被开除出国家队等。上述行政处分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施暴主体再次实施暴力伤害行为的可能性。然而,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教练、训练员的职业禁止问题成为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留白之处。
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一法条确定了风险自担或自甘风险原则在体育运动中的适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运动员对体罚暴力行为自甘风险。对于体罚暴力行为,应当适用一般侵权的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66条规定,民事侵权责任可分为过错责任原则、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体罚暴力行为特征,并基于未成年运动员对教练的严重依赖性与依附性,笔者认为适用推定过错责任更为妥当,即在体罚暴力行为中,推定实施体罚的行为主体具有过错,若其不能证明无过错的,则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若采用过错责任,则忽视了运动训练的封闭性,加大了证明难度,无法及时有效保障未成年运动员的合法权利;若采用无过错责任,则容易造成教练指导员等专业人员的不作为,不利于未成年运动员技能与水平的提升。对于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了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除追究施暴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外,还可比照该法第1197条至1121条的规定追究体育训练机构或管理部门的民事责任。
(三)以刑事处罚为最后保障手段
作为最后一道法律防线,刑法所特有的法益保护机能要求其必须为未成年运动员提供最后的法律保护屏障。在我国的《刑法》体系规范中,对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刑法规制主要体现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
1.对体罚暴力行为的刑法规制
根据体罚实施主体的主观方面差异性,可适用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及虐待罪。在司法实践中,鉴于主观认定的难度,体罚暴力适用于故意类犯罪的相对较少,且过失重伤罪要求达到重伤害的结果,过失致人死亡罪要求达到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在体育训练过程中体育致人伤残、死亡的情形并不常见,因此,过失型罪名的适用也相对较少。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虐待罪的修改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应对教练等人员体罚暴力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刑法修正案(九)》修订之前,我国虐待罪的犯罪主体仅限定于家庭成员,此次修正案在《刑法》第260条虐待罪后增加“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构成要件理论,此罪的客观表现形式通常表现为行为人采用殴打、冻饿、有病不给治疗、强迫进行超体力劳动等肉体摧残手段,以及侮辱、限制行动自由等精神折磨手段,对被害人的身心进行经常性的摧残和折磨,使被害人遭受到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由此,在封闭式训练中,教练取代父母角色,特定情形下成为未成年运动员的被委托监护人,其在监护期间对未成年运动员进行体罚的行为,可构成虐待被监护人罪。对于体罚情节严重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对兴奋剂滥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对于未成年运动员兴奋剂滥用行为的刑法规制,2020年底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对此予以入刑处理,在《刑法》第355条后增加“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这一新罪名,规定“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或者明知运动员参加上述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从这一最新法条规定来看,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提供兴奋剂、组织、强迫使用兴奋剂等妨害兴奋剂管理的行为均被纳入到刑事处罚的范畴,为未成年运动员的公平竞争权与身体健康权免受兴奋剂滥用行为的侵害提供了最后的法律屏障。
3.对性侵未成年运动员行为的刑法规制
我国现有《刑法》对侵害未成年运动员性权利行为的刑法规制主要涉及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这两个罪名在构成要件上有较大的差异,在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上体现尤为明显。《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第236条强奸罪予以修订,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特定主体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予以定罪处罚。结合修订后的这两个条文,我们可以将未成年女性划分为四个年龄层次:
其一,16周岁至18周岁未成年女性。此类女性基于身心发展已基本等同于成年女性,我国《刑法》并未对其性权利予以特殊规定,而是笼统归于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妇女之中。
其二,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女性。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236条后增加一款,作为第236条之一,即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并未完全否定14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权,但是与其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即使取得该未成年女性的同意,亦构成犯罪。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预防和规制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利用法律地位、法律行为或职务上的便利性侵未成年女性。
其三,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女性在刑法上被称为“幼女”。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对奸淫幼女的行为,应当以强奸罪论处,从重处罚。从这一规定来看,奸淫幼女行为的犯罪构成,并不需要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为基础,该罪保护的法益不仅包括了幼女的性权利,同时也侵犯了幼女的身心健康权。由此可知,我国法律是否认14周岁以下的幼女具有性自主权的。对于奸淫幼女的行为,规定从重处罚的同时,《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在公共场所当众奸淫幼女的”“造成幼女伤害的”作为加重处罚情形,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其四,不满10周岁的幼女。《刑法修正案(十一)》对10周岁以下的幼女的性权利保护予以了特殊规定,增加了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五)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对于奸淫10周岁以下的幼女的,应当加重处罚,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强奸罪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女性,对于男性未成年运动员的性权利保护,可依据我国《刑法》第237条之一“猥亵儿童罪”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原本“猥亵儿童罪”规定的“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修改为具体的两种情形,针对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规定4种加重处罚情形,具体包括:(一)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二)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三)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四)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刑法》并未将未成年运动员的性权利予以特殊化处理,但从我国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发展来看,为有效预防教练、医护人员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性侵害未成年运动员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对现有法律体系规定的反思
虽然我国有多个部门法多个法律条文涉及对暴力侵害行为的规制,特别是《民法典》的出台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进一步规范了暴力侵犯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但从体系性方面考察,我国现有的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法律规制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未成年运动员保护理念不足
未成年运动员的双重属性未得以重视,缺乏对未成年运动员权利保护的观念。即使是作为运动员权利专门法的《体育法》和作为未成年人保护专门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仅作出部分原则性规定,鲜有法律条文将“未成年运动员”这一主体予以特殊化规定。未成年运动员具有双重身份属性,即未成年人和运动员。相较于一般的运动员,作为未成年人的运动员,身心发展尚未完全,自我保护意识更为薄弱;相较于一般的未成年人,作为运动员的未成年人,一般在寄宿制体育学校,不能得到正常的父母监护,长期与教练、队医等年龄较长的成年人相处,容易导致其处于服从地位。由于自我保护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薄弱,加之训练环境的封闭性与训练活动的盲从性,导致未成年运动员容易受到他人的暴力伤害。然而,现有的法律规范并未凸显对未成年运动员的特殊保护。未成年运动员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和观念的缺失,导致当前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规制。未成年运动员与家长在暴力侵害事件发生后,大多选择不了了之。然而,暴力侵害给未成年运动员所带来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二)缺乏明确的法律概念
“概念是构造理论的砖石,它是研究范围内同一类现象的概括性表述。”(16)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5.现有法律规范并未对“暴力”“体罚”“性侵害”等与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密切相关的术语予以法律界定。“体罚”一词常出现在体育训练与竞技场中,也常出现在教育教学场所中。然而,“体罚”这一概念并非是规范法学的法律用语,而是属于犯罪学中对现象予以归纳或概括的事实用语。法律规范要求明确性,尤其是作为最后保障规范的刑法,在涉及对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规制中,应当从规范的角度入手,而不能直接搬用犯罪学中所描述犯罪现象时所使用的概念(17)张明楷.刑法学中的概念使用与创制[J].法商研究,2021,38(1):11.。何谓“体罚”?体罚与惩戒行为的界限何在?达到何种程度即构成体罚?《体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均未对此予以明确界定。此外,“性侵”亦为如此,在刑法规范中,有“强奸罪”“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猥亵儿童罪”等罪名,但是对于“性权利”的性质属性,我国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并未加以明确规定,而是将其通归于“生命健康权”。
(三)缺乏对未成年运动员与教练等专业指导人员的权利义务关系规范
未成年运动员与教练等专业指导人员均具有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法律地位,不因指导地位而发生改变。但是,未成年运动员长期与教练、队医等年龄较长的成年人相处时,容易导致其处于服从地位,教练与未成年人运动员的基本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主体扭曲化为“特殊权力——服从关系”,甚至呈现“家长主义”色彩。家长主义一般认为是精英们基于行为对象利益的考量而对其行为或选择作出的干预,其前提条件在于,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并非每一法律主体都能根据自我意志和事实认知作出对自身利益最佳的选择(18)肖姗姗.少年司法之国家亲权理念——兼论对我国少年司法的启示[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39(4):94.。家长主义起源于罗马法中的家父权制度,后家长主义发展为法律家长主义,即国家作为精英的集大成者,为了儿童或精神错乱者的利益,可以允许实施家长式干预。根据少年司法的理论,国家可以基于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而对未成年人的行为实施干预,但禁止个人或单位对未成年人实施家长主义。然而,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缺失,导致“家长主义”作风仍在体育训练、竞技场盛行,如教练等专业指导人员强迫、组织未成年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以激发未成年人运动机能为由加大对未成年运动员的训练力度甚至“体罚”。
如何结合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现状,给予未成年运动员以有效的法律保障,从而更进一步地推动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成为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新时代未成年运动员法律保护的完善
暴力侵害是威胁未成年运动员安全和健康的重要隐患,具有体育特殊性和专业性。在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国家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对特殊主体人员的权利义务边界予以明确,规范职业要求,规定从业禁止制度以降低教练、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员给未成年运动员暴力伤害所带来的风险,从而减少对未成年运动员的暴力侵害,保障未成年运动员的职业安全与身心健康发展安全。
(一)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基本原则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源于英美法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亦有学者将其译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但由于“最大化”“最佳”不符合中文的用语习惯,因此这一概念一直被诟病。2020年10月17日修订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总则第4条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原则,贯穿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方方面面,也为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修订提供了指导,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就明确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未成年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属性要求在《体育法》中必须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因此,笔者建议将总则中的第5条修改为:“国家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对青年、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给予特别保障,增进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在此原则的指导下,确立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中对未成年运动员的特殊保护,为未成年运动员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特殊的保障条件。如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确定未成年运动员的休息权、获取劳动报酬权等。以此原则为基础,指导《反兴奋剂条例》等与未成年运动员权利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订。
(二)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运动员的倾斜性权利
未成年运动员的权利不仅为一种自然权利,也应当为一种法律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不仅包括一般自然人所享有的权利内容,还应当赋予其作为未成年人与运动员双重主体身份的特殊权利,如在有权接受体育训练的同时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有鉴于此,本文将“未成年运动员权利”定义为“依照法律规定,十八周岁以下的运动员在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实践中所产生和拥有的各项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总和”。其中,消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尊重和容忍的权利”,积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给付和作为的权利”(19)周刚志.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中国宪法权利性质之实证分析[J].法学评论,2015,33(03):40-47.。在未成年运动员保护体系中,这一特殊主体处于弱势地位,其消极权利占主导地位,如生命健康权、免受兴奋剂侵害的自由、注册和转会的自由权等。当然,也应当享有一系列的积极权利如受教育权、公平竞争权、获取劳动报酬权、监护权等。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通过修订《体育法》或制定《未成年运动员保护条例》,将未成年运动员的特殊权利落到实处。
1.明确未成年运动员的人格权
在我国《民法典》出台之前,这一类权利被称为“生命健康权”或“身体健康权”。《民法典》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作为人格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第1002条至1004条予以明确规定。其中,生命权包括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身体权包括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健康权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这一系列权利也被《世界人权宣言》所确定,其第3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奥林匹克宪章》更是将保护运动员的权利作为国际奥委会的基本职能之一,明确要求不得实施有害于运动员生命权、身体权与健康权的行为,如要求男女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鼓励消除暴力、反对兴奋剂的使用等。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是人格权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维系整个体育运动发展的生命要素”。这一系列权利决定了未成年人是否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同时也决定了其运动生涯的长短。未成年运动员由于其处于特殊的身心发展阶段,自我保护能力较低,加之常处于脱离家庭与父母的监护和封闭或半封闭的环境之中,因此,其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更应予以重视。
实则,职业安全权和免受兴奋剂侵害的权利,也应当被归入人格权的实质范畴。反兴奋剂使用是每一名运动员的义务,同时也是运动员消极权利的体现。使用兴奋剂具有极大的风险,轻者可导致运动员内分泌紊乱,重者可导致运动员重伤或死亡。对于未成年运动员这一自我保护意识与自我防御意识相对薄弱很多的特殊群体,更应当加强对其反兴奋剂侵害权利的保护。职业安全权这一积极性权利,要求相关部门在未成年人运动员实施体育训练、体育竞技比赛时,应当根据其身心发展特点、参与项目的高难度等,配置适合的、符合安全标准的运动设备、场所及其他必要的条件和保护措施,以保障其训练的安全性。否则,将未成年运动员置于无限的风险之中,给未成年运动员身心所带来的危害结果和潜在隐患将不可估量。这两项职业性权利既是人格权的实质性要求,同时也是未成年运动员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具体呈现。
2.明确未成年运动员的公平竞争权
公平竞争是体育竞技运动的灵魂所在,公平竞争权是未成年运动员享有的最重要的职业性权利。因此,也有学者将此权利称为“职业公平权”(20)钱侃侃.运动员权利的法理探析[J].法学评论,2015,33(01):191-196.。公平竞争,是指在体育竞技比赛中,各相关主体为了争夺有限的体育发展资源(物质或精神)或对自己有利的存续条件,以规则公平为前提,在许可的技术运用范围内,以同样的规则为标准进行裁定的竞争(21)程静静,钟明宝,张春燕.体育竞赛公平竞争的概念与规定性探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04):17-21.。我国《体育法》第37条明确规定了公平竞争在竞技体育中的原则性地位。
未成年运动员的公平竞争权不应当仅限于运动竞技场,其适用范围应当扩大到选拔、参赛、裁判与奖励等各阶段。首先,就训练条件而言,未成年运动员应当享有符合其身心发展特点的训练、表演和竞赛的条件,应当符合人权标准;其次,就参赛资格而言,应当以未成年运动员的运动水平为依据,避免其他不正当利益或其他博弈因素的介入考量;再次,就裁判而言,应当强调裁判员执法和成绩判定的公平,拒绝一切“假球、黑哨”现象,以防对未成年运动员造成精神和物质上的打击。此外,也应当注意对未成年运动员的奖励制度的平等,获得成绩的未成年运动员应当享有与同一俱乐部、同一训练队或同一项目的成年运动员相当的奖励,不能因为运动员未成年的身份而将相应的奖励予以折扣,应根据其实际表现予以发放。
3.保障未成年运动员的受教育权
“在运动员成长过程中,早期的专业化训练迫使其入队年龄越来越年轻化......,为了取得更好的竞训成绩,他们的文化学习时间长期被大量挤占,运动员文化程度低已成为长期存在的普遍现实。”(22)郑丽,曹丽,寿在勇.论“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在校受教育权的弱化与回归[J].体育与科学,2014,35(02):101-104+100.这一现状显然有悖于法律授予未成年运动员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主要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公民均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国家提供教育设施,培养教师,为公民受教育创造必要机会和物质条件。
对于未成年运动员,国家首先应当确保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国家及相关部门,不得以未成年运动员以参加体育训练、比赛为借口剥夺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以体育成绩来取代对未成年运动员文化成绩的要求。国家及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帮助未成年运动员的文化学习,以保证其接受完整、公平的义务教育。当然,受教育权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对于未成年运动员厌恶文化学习,以体育训练、比赛为借口拒绝文化学习的情形,其监护人应当与相关部门相互监督、相互配合,采取积极干预措施,提高未成年运动员对于接受义务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在特殊情况下,对适学适龄未成年运动员采取约束性措施,帮助其完成义务教育。
此外,还应当注意对未成年运动员升学优待权利的保护。我国《体育法》第28条虽然明确规定了“国家对优秀运动员在就业或者升学方面给予优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成年运动员可以获得免试升学的机会。基于教育公平,应当对未成年运动员采用加试或加分的方式,在升学时充分考虑其体育方面的成绩,同时也不忽视对其文化成绩的考核。由此,才能更进一步提升未成年运动员本人、家庭及相关部门对义务教育权的重视,进而提高未成年运动员的综合素质,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固的后备力量。
4.落实未成年运动员的获取劳动报酬权与社会保障权
获取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是国家赋予未成年运动员的积极性权利。体育运动是一项特殊的劳动,运动员是特殊的劳动者,具有专业性与特殊性。体育运动多从未成年幼小阶段开始,通过开发体育潜质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掘其运动机能。运动中的训练、比赛等活动对未成年运动员而言就是劳动,他们有权通过这一系列劳动获得相应的物质报酬。同时,未成年运动员的获取劳动报酬权也应当具有平等性,这一平等性体现在对同工同酬方面,不因年龄差异性而区别对待未成年运动员与成年运动员,未成年运动员应当获得与其运动水平、训练强度等相当的工资、报酬、津贴等。
社会保障权则强调对未成年运动员物质层面的保障。未成年运动员除却获得普通劳动者所享有的社会保险外,还应当享有与其主体特性、所从事的项目特色相符合的特殊社会保险保障。履行未成年运动员社会保险保障义务的主体不仅限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他们所在的俱乐部或运动会的组办者都应当为其购买相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伤残保险和失业保险等(23)陈林祥,李业武.我国优秀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36(3):12-15.。运动伤害是威胁未成年运动员安全和健康的主要隐患。因此,国家有义务要求和监督运动员所属单位建立健全未成年运动员医疗服务和保障制度,并及时、全面地处理运动伤害。同时,应当提供相关的保障制度和具体的措施,帮助未成年运动员受伤后的康复治疗、恢复训练等;或在未成年运动员康复不能或退役的情况下,提供相关的就业和优抚保障。
(三)加大对教练等专业人员的限制性规定
从目前对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人的限制性规定来看,主要体现在《反兴奋剂条例》第39条、第40条对体育社会团体和运动员管理单位相关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运动员辅助人员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或者组织、强迫、欺骗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或非法持有兴奋剂的行为规定了2年、4年和终生不得从事体育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的处罚。然而,对于其他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并未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规制暴力侵犯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
1.扩大从业禁止的适用范围
从业禁止,是指人民法院对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根据其犯罪情况和预防犯罪的需要,禁止其在一定时期内从事相关职业。从现有的对侵犯未成年运动员行为人的规定来看,呈现出主体单一、从业禁止范围过窄等问题。对暴力侵犯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人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加大对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人的限制规定。
其一,扩大适用从业禁止的主体范围。结合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现状,应当将从业禁止的适用主体范围扩大到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人,尤其是性侵行为人,而不仅限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的行为人。从业禁止的主体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因强奸、强制猥亵、猥亵儿童犯罪等被作出有罪判决的人员,还包括因上述犯罪被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人员以及因猥亵,容留、介绍卖淫等涉性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的人员。将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主体纳入到从业禁止的适用范畴,无疑突破了原有刑法中规定的犯罪且被判处刑罚的前提条件,加大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和范围。这也是为了应对目前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严峻形势,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运动员免受性侵害的应有之义。
其二,扩大从业禁止的从业范围。当前对暴力侵犯未成年运动员人员的从业禁止仅限于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的行为人,禁止他们从事体育工作和运动员辅助工作。然而,根据当前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现状,应当禁止暴力侵害主体参与至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单位之中。这里的“接触”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性接触。具体而言,这些工作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等教育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未成年人安置、救助机构;校外托管、临时看护机构、为未成年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以及其他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培训、监护、救助、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审查对象既包括教师、培训师、教练、保育员、医生等直接对未成年人负有职责的工作人员,也包括行政工作人员以及保安、门卫、驾驶员、保洁员和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的创办者、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成员、监事等虽不直接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便利的其他工作人员。
2.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目前,我国多个省市和地区尝试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人员予以信息公开。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举措纳入到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人限制性规定范畴。但是,为了维护违法犯罪人员的正当权利,这种信息公开应当有所限制:
其一,有条件的限制公开。并非对所有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人的信息进行公开,公开的范围限定于对未成年运动员造成了严重伤害的行为人。严重性的判断应当结合被害人的情况以及性侵行为人的情况进行综合判定:一方面,可以考虑对被害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比如身体损伤程度、心理健康情况以及是否剥夺了其生命等;另一方面,对其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再犯的可能性大小、是否具有病态心理以及他人对其评价等进行综合考察评估。
其二,建立全国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人员信息库。在目前强化政法工作信息化的背景下,可以借助政法专用网络和共享平台发展的契机,多部门协同发力,由第一时间掌握信息来源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作为违法犯罪记录的主要提供机关,将各自工作中处理的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案件信息及时汇总并主动录入,再由负责信息管理的部门对相关信息扎口进行形式审核,对于符合要求的统一上传至全国信息库。为了准确识别暴力侵害者,登记的信息内容应当全面,一般应当包括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行为人的基本信息、违法犯罪信息和识别信息。需要登记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住所地等。
其三,制定风险评估机制,决定公开的期限。基于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和社会危害性的整体考量,对不同暴力侵害行为人的再犯风险程度、人身危险性和病态心理进行评估,并以此为依据来进行分级管理。如果暴力侵害行为人在公开期限内没有再次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则可以裁定取消对其信息公开。对不同危险程度的暴力侵害行为人施以不同的信息公开期,进行分级管理。将公开期限分为两档,五年的信息公开期限是原则性要求,终身公开个人信息为例外情况。
3.推进体育行业中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从国家层面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并对强制报告的主体、应当报告的情形,以及未履行报告职责的法律后果等予以明确。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立法层面确定了强制报告制度的法律地位。推进体育行业的强制报告,可以促使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了解自己的报告义务、应当报告的情形以及报告的对象,积极履行报告职责。
其一,规定对体育运动训练相关求职者的强制报告义务。要求求职者在应聘时应当如实告知本人是否有过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促使负有报告义务的体育从业人员了解自己的报告义务,积极履行报告职责。
其二,规定用人单位的严格审查义务。显然,严格规范用人单位的审查义务,相比事后处罚,具有事先预防的优势,在招聘环节就能将有性侵记录的人排除在外。同时,用人单位具有人员排查的便利条件,对于已在职的工作人员是否存在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记录,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辞退。
其三,建立强制报告奖惩制度。对于因及时报案使未成年运动员摆脱困境,让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人受到依法惩治的,应当给予奖励和表彰;对于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如导致犯罪行为持续发生,未成年运动员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的,应当给予相应处分,取消其评优、评奖资格;对于阻止报告的,要从严处罚;对于公职人员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不按规定落实的,应当由监察委员会进行问责。由此,将使报告义务落到实处,进而推动对未成年运动员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伤害救治、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相关举措的完善(24)宋英辉,刘锐玲.强制报告: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水平[N].检察日报,2021-03-21(003).。
五、结语
未成年人运动员的双重属性,导致他们受到暴力侵害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对这一弱势群体予以特殊的法律保护势在必行。体罚暴力、性侵害、兴奋剂滥用等暴力侵害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虽然受到部分法律条文的规制,但实际上并未阻却这一现象的发生。为打破传统的运动员与教练等专业人员不对等的关系,应当从立法层面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运动员原则,对未成年运动员的权利作出倾斜性规定,并从从业禁止、信息公开、强制报告等司法措施入手,加大对这一部分违法犯罪人员的限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