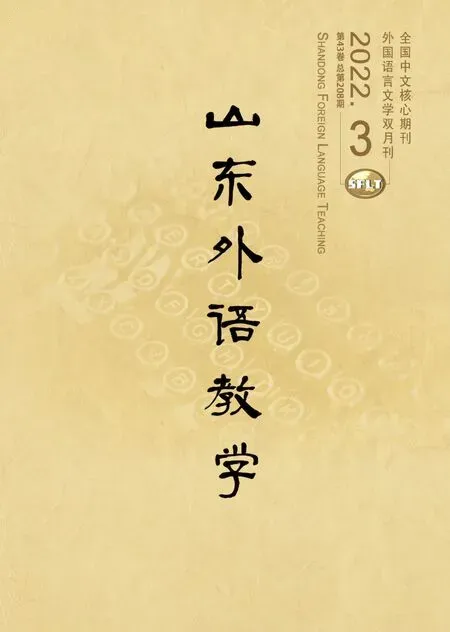《长友诗》的晚清民初之旅
——文化之“诱”与“反诱”
于德英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1.引言
在晚清与西方的被动接触中,语言和翻译在中西文化、科技、军事等诸多领域影响深刻。晚清翻译活动具有传递新知、启蒙思想及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王军平,2020:112)。然而,学界对晚清与西方被动接触之初的译本研究似显不足。作为描写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译本研究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一个译本和其原本的比较研究,另一种是多个译本和其原本的比较研究。梳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或连续历史时期的多译本比较研究,就构成了译本翻译史。译本比较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不同译本的翻译讹误,而是将译本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其接受情形,定位译本规律性的偏移,在此基础上探寻造成这些偏移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总结相应的翻译规律(Toury,1995/2012:31-34,102)。译本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缩影,探究翻译和社会文化的互动。
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的诗歌“A Psalm of Life”自1864年译成中文后,历经多次重译,逐步走向经典化。尽管他的诗坛地位在其去世后急剧下跌,当下朗费罗的世界主义和跨国视野重新获得学术关注(Higgins,2019:193-214)。事实上,这首诗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受到关注。钱锺书(1945/1997,1948/1997)从中西文化和文学比较的角度探讨了186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和晚清尚书董恂的汉译本及文化意义,从而奠定了这首诗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此外,学界对该诗的汉译研究主要有二:一是从翻译艺术赏析的角度(郭著章,1990;喻云根等,1996)、译者研究的角度(彭礼智、刘泽海,2019)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吴赟,2007;黄进、冯文坤,2010)进行译本比较研究;二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冒键,2006;罗文军,2011;郑锦怀,2011)、从功能和影响研究的角度(王文兵,2010)考察该诗在中国的传播。
囿于史料的限制,这首诗歌在晚清民初的汉译研究尚需从文化的维度进一步发掘。本文采用描写翻译研究的范式,以朗费罗的“A Psalm of Life”在同治时期《长友诗》①威妥玛译诗底本、董恂改译本和以威妥玛之名发表在《教会新报》②译诗定本为研究对象,梳理该诗晚清民初的学术接受史,考察该诗译本与原诗以及译本之间规律性的偏移,以此管窥晚清民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场景中译者身份与翻译意图。
2.晚清民初《长友诗》的学术接受史考察
朗费罗是美国十九世纪家喻户晓的诗人。他坚持从美国的生活背景中寻找诗歌主题,其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美国人民积极的清教精神生活。“A Psalm of Life”以年轻人的心对圣经歌者的独白为副标题,四句一节,一共九节。前两节批判基督教此生如梦、死后永生的颓废论调,第三至六节鼓励人们把握现在、实干行动,第七至八节激励人们以伟人为榜样,最后一节号召人们不断收获和追求。整首诗歌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基督教色彩,即唯有此世惜时奋进,方能实现灵魂永生。诗歌以ABAB为韵脚,读来朗朗上口,被誉为“真正美国心脏的跳动”(查良铮,2005:193)。歌颂人生、珍惜当下、积极进取,正是这首诗歌所蕴含的超越国界和时代的人生态度,引发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
“A Psalm of Life”首个汉译本由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于1864年译为散文体,同年由晚清尚书董恂润色修改为七言诗歌。这两个版本于1872年以《长友诗》的题名收录于方濬师的《蕉轩随录》(方濬师,1872/1995:476-478)。译诗定本于1873年以《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的题名发表在《教会新报》11月29日第263期(林乐知,1873/2018:253-254)。对晚清民初《长友诗》的学术史考察,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主要有方濬师1872年《蕉轩随录》所录的《长友诗》、小横香室主人1915年《清朝野史大观·清朝艺苑》所录的《英人威妥玛〈长友诗〉》和玉麟1927年发表在《雨丝》的《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有趣的是,这三篇文献在时间序列上形成后者以前者为基础的学术现象,即小横香室主人的《英人威妥玛〈长友诗〉》依据方濬师所撰《长友诗》而成,玉麟的《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又藉由《英人威妥玛〈长友诗〉》而发。
方濬师在《长友诗》中,开篇借用后汉《东观汉记》收录的犍为郡掾田恭所译莋都夷作《慕化归义》诗三章,引范晔谓“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方濬师,1872/1995:476),阐发蛮夷非我族类却怀有慕义向化之心,其语言文化优越感自不待言。他仿《慕化归义》夷语与华文格式,竖排董恂改译稿诗句,将威妥玛译诗底本小字号分注句下,品评后者底本为“然译以汉字,有章无韵”(同上:477)。在诗稿对比之后,又借引高要苏赓堂示西洋人诗,表达“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同上:478)之文化意图。方濬师在文中记录原诗作者为欧罗巴人长友,误以为长友(Longfellow之译义)是欧洲人。
小横香室主人的《英人威妥玛〈长友诗〉》概述了方濬师的《长友诗》,同样以《慕化归义》三章开首,采用方濬师对两个译本的竖排分注格式,最后附以短评。其所录译诗稿与方濬师所录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短评:“道光时,英国人马里逊善书汉字,西洋人汗得能汉语,略解《鲁论》文义,与威妥玛之能诗,同为徼外同文佳话。今日吾国人好学英法文字,转抛荒本国文,得勿为外人齿冷乎?”(小横香室主人,1915/2009:1032)。编撰者将英人马里逊善书汉字与威妥玛能诗并称徼外同文佳话,对此颇为称许,然而对国人好学英法文字却感齿冷。这种区别对待本国和他国文化的态度,折射了当时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他者文化的保守态度,和方濬师华夏文明“同文远被西洋贾”的文化观一脉相承。
玉麟的《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对威妥玛原译和董恂改译做了品评:董恂改译本“确是正地道的中国七绝”,然而无法据此看出原诗作者;威妥玛译文没有保留原诗的韵脚,将原诗译为“粗浅的散文,但似乎还较改译的七绝能留存一些‘信’”。从“信”的角度出发,董恂改译受平仄字数限制,又运用古典,与“胡译”一类,犯了“那个时代的人难免的毛病”。而威妥玛作为同治时期的外国使臣,“能够这样把原诗之意传达为汉文,实在可说难能可贵”。根据威妥玛的译稿,玉麟推断原诗是美国诗人Longfellow的“A Psalm of Life”,而非欧洲人的诗作。同时,他认为“把诗人的名译义则总觉得极不对”(玉麟,1927:343-345)。玉麟的评判虽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但主要从翻译的“信”这一文本层面的标准衡量二人的译稿,并涉及译名应译音而非译义。
从《长友诗》晚清民初的学术接受史来看,方濬师和小横香室主人的品评均以本土文化为中心。两篇文献开篇以田恭汉译莋都夷作《慕化归义》诗三章,引出威妥玛译稿“有章无韵,请于甘泉尚书”,暗合方濬师《长友诗》中所提道光间略通《鲁论》的西洋人请教高要苏赓堂。董恂将威妥玛稚嫩的散文体裁以富含典故的七言诗,苏赓堂则以诗示西洋人,均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人对西洋人的文学“教化”。苏赓堂诗中前三联“宣尼木铎代天语,一警愚聋万万古。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窄衫高帽款门至,碧眼停观若心醉”(方濬师,1872/1995:478),道尽了对孔子《论语》和圣人御世的推崇,描述了西洋人深受感召、慕义向化的场景,刻画了晚清时期普遍存在于官员文人中的文化优越感。而玉麟的评价,则是以“信”为标准,从文本层面对比两个版本,认为威妥玛的译本更加忠实于原诗。不过,小横香室主人和玉麟都没有提及1873年发表在《教会新报》上的《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
在中西文化接触的初期,译者受语言的限制,翻译中难免出现讹误。抛除由于语言水平不高而导致的讹误,描写这些译本和原诗之间、以及译本之间有规律性的偏移和差异,可从文化的维度阐发这些偏移和差异,从而理解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翻译意图。
3.译本偏移:源语文化导向与本土文化导向
钱锺书依据方濬师1872年的《蕉轩随录》,对威妥玛译本和董恂译本所做的比较,其实是“A Psalm of Life”译诗底本和改译本的比较。第二年,定本《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在《教会新报》第263期发表,传播范围广(林乐知,1873/2018:253-254)。该定本与《蕉轩随录》所载的《长友诗》基本相同,只是“千秋万代远蜚声”中的“代”改为“岁”。有趣的是,这首诗署名为《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但刊载的却是董恂七言绝句版,四句一节、每节隔开竖排。威妥玛译诗定本的谱系流程为:威妥玛“句数或多或少”逐句对译的底本、董恂的“七言绝句”改译本,以及将董恂改译本冠以威妥玛之名发表在《教会新报》的定本。这一谱系看似按照时间顺序自然发生,然而却蕴含着晚清威妥玛和董恂两大外交家的文化意图。
3.1威妥玛译诗底本:源语语言文化导向
与原诗相比,威妥玛译诗底本在三个方面呈现出源语语言文化导向的译本偏移特征。一是在形式和主旨方面,该译本保留了原诗的每诗节四行、共九个诗节的英语诗歌形式,采用逐字逐句翻译的方式,传译出原诗召唤人们珍惜光阴、力图上进的意旨。二是在意象传译方面,威妥玛比较忠实地再现了原诗的意象,如将第四诗节中的“beating hearts like muffled drums”译为“丧鼓之敲”,将第五诗节中的“In the world’s broad field of battle, In the bivouac of life”译为“人世如大战场/如众军林下野盘”等。三是句式方面,威妥玛译文偏向英语句式结构,如他将第二诗节中的“Dust thou art, to dust thou returnest, Was not spoken of the soul”译为“圣书所云人身原土终当归土/此言人身非谓灵也”(方濬师,1872/1995:477-478)。当然,由于汉语水平有限,威妥玛的译文不仅没有传译出原诗的韵律,而且多处句式笨拙不通。譬如,他将“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译为“人生世上行走非虚生也总期有用”,句式冗长,文字直白,解释性翻译不仅没有呈现出原诗简洁明快的风格,也不符合汉语的表述习惯,更遑论汉译稿的诗歌性了。
总体而言,威妥玛译诗底本偏向源语语言文化规范,没有采用汉语的四言、五言或七言等古典诗歌的典律化形式和语言规范。方濬师用“有章无韵”评价该译诗。钱锺书(1948/1997:347)同样对威妥玛译诗评价不高:“不过是美国话所谓学生应外语考试的一匹‘小马’(pony)——供夹带用的逐字逐句对译。”这种以源语语言文化导向的翻译模式,固然有译者受汉语水平所限的原因,但也许有文化方面的考量。目前尚无史料论及威妥玛翻译朗费罗诗歌的原因,唯有从他驻华身份和译文中略窥一二。就驻华身份而言,威妥玛一直代表的是英国政府的立场。1841年随英军侵华,1843年任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翻译,1847年退伍后历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驻华公使等,1858年参与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译者的英方文化立场体现在译本层面,往往更加偏向英语语言文化。
3.2董恂改译本:本土语言文化导向
与原诗和威妥玛译诗底本相比,董恂改译本具有明显的本土语言文化导向。一是采用七言绝句这一古诗典范来改写威妥玛的底本。原诗和威妥玛译诗底本均为九节,董恂改译本采用九节七言诗体,每节四行。董恂用传统的诗体润色威妥玛逐字逐句对译的散文诗体,表现出鲜明的典律化特征。在翻译中典律化的程度越高,则说明译入语文化的强大的文化惯性和译者对译入语文化的高度认同。二是采用大量儒家典故和文化意象来抵消原文的宗教色彩。原诗第三诗节中,“But to act, that each to-morrow / Find us further than to-day”,威妥玛译本直白地翻译为“所命者作为专图日日长进/明日尤要更有进步”,董恂则改写为“人法天行强不息/一时功业一时新”。原诗的主旨是基督教徒应在人世自律上进,从而实现灵魂永生。董恂译本将威妥玛译本直白的语言改写为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他诗节中,董恂改译本亦有多处化用中国文化典故或诗词。如董恂改译本第二诗节“天地生材总不虚”化用李白《将进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第四诗节“无术挥戈学鲁阳”化用《淮南子》“鲁阳挥戈”,“一从薤露歌声起”化用乐府曲调挽歌及曹操《薤露行》中的“薤露”;第七诗节“学步金鳌顶上行”化用“鳌里夺尊”,“已去冥鸿犹有迹”化用汉杨雄《法言·问明》中“鸿飞冥冥”及白居易《范阳张公墓志铭》中“天骥冥鸿”,“雪泥爪印认分明”化用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些本土文学典故和儒家意象将原诗的宗教色彩归化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本土文学典故。
威妥玛译诗底本在形式与意旨、意象传译和句式三个方面的偏移,具有鲜明的源语语言文化特征。而董恂改译稿的七言绝句诗体、中国文学典故及儒家文化意象,消解了原诗和威妥玛译诗底本的文化他者性,呈现独特的本土语言文化导向的特征。单从文本层面难以解释这些偏移,唯有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方能管窥董恂和威妥玛这两位中西官员文人的文化意图。
4.《长友诗》定本:威妥玛和董恂的中西文化之“诱”与“反诱”
威妥玛发表在《教会新报》的译诗定本《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没有采用自己逐行对译、长短不一的散文体,而是采用董恂改译稿的七言绝句体。对于这一行为的文化解读,罗文军(2016:100)认为,这“证明当时西人的确是主动遵守了中国的诗歌规范”。那么,威妥玛为何要主动遵循中国诗歌规范呢?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汉语语言和诗歌功底不足。然而,他选择发表在《教会新报》这一晚清颇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刊物上,也许另有文化意图。而董恂的改译稿同样蕴含着晚清文人官员的文化意图。
4.1威妥玛定本意图:基督教文化之“诱”
威妥玛发表诗歌时没有标注董恂这个改译者。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这首呈现地道的中国儒家文化和丰厚的本土文学典故的七言绝句译诗,可以让中国读者以为中西大同,继而更好地接受基督教的教义?这种推测并非无端,而是有着史实依据。由林乐知创办的《教会新报》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威妥玛译诗定本发表的《教会新报》第263期为例,该期扉页同时标以大清时间(大清同治十有二年岁次癸酉十月初十日)和耶稣降生时间(耶稣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十一月廿九日)。在这一期“教事近闻”“中外政事近闻”“杂事近闻”和“格致近闻”四个栏目中,“教事近闻”占了近一半的篇幅(林乐知,1873/2018)。可以推测,后三个栏目主要以政事、杂事和格致吸引不同的读者群体,这些读者翻开《教会新报》,必然会看到首栏占了每期近一半篇幅的基督教“教事”。间接传教是《中国教会新报》1871年以来主要的传教策略,即通过教授知识、翻译和出版中文刊物,接近中国的知识分子、官员、妇女等群体(贝奈特,2014:206)。而译诗传教则是间接传教的一种具体方式,题目中标注译者威妥玛的英国驻华钦差身份,可以引发晚清文人、官员等读者群体对这首译诗的好奇心。
如果说《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契合了《教会新报》以诗传教的目的,那么在题名中仅标注译者“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而不标注董恂,也就更容易理解了。晚清读者阅读此诗后难免会想象,在“西国”也有诸如“天行健”的儒家精神和“鲁阳挥戈”等中国典故。这样,人为地消除中西文化差异,造成一种中西大同的假象。这首译诗中的文化大同,既暗示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熟知中国文化,暗合当时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又蕴含西方和中国一样有着优美的古诗和相似的文化,召唤国人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如此一来,朗费罗的《人生颂》以威妥玛的译者身份,以董恂的七言绝句这一古诗典范,以《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的题名,以中西文化相似为缘由,成为《教会新报》引诱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基督教教义的诱饵。
4.2董恂改译意图:本土文化之“反诱”
有趣的是,董恂润色修改威妥玛的译诗底本同样有其文化意图。作为晚清外交家、政治家,董恂不懂英语。董恂改译威妥玛译诗底本,固然有受威妥玛所托这一偶然因素,但更引人深思的是其必然因素。
一是对本土文化而言,董恂借助改译稿中惜时图强的诗歌意旨,激励遭受鸦片战争蹂躏的清政府和国人蹈厉奋发。与同时代依然沉浸在大清华夏中心的保守官员相比,董恂与西方人接触多,对西方文化更为了解。1864年他除了改译《长友诗》外,还为丁韪良等翻译的《万国公法》作序。在序言中,他指出:“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董恂,1864/2002:1)由此可见董恂思想的开放性。董恂作为晚清政治家和文人,认为威妥玛底本中“有策励意,无碍理者”(方濬师,1872/1995:477)。“有策励意”正适合激励备受西方列强凌欺的清政府和国人奋发图强。而“无碍理者”是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相契合,这主要表现在董恂改译本中化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鲁阳挥戈”和“鳌里夺尊”等具有儒家思想特征的典故。
二是从中西文化接触的角度来看,董恂借助改译威妥玛的译诗底本,行文化之“反诱”。董恂在润色翻译中,采用本土文化导向的改写策略,用本土的诗学、文化意象和语言规范来消除外来文化的差异性。尽管董恂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思想更为开放,但是在骨子里依然认为西方在文学文化方面不如中国。方濬师在《蕉轩随录》中描写了当时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贬抑心态:“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同上:478)。可以看出,同化西洋人,“反诱”外国人学习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是当时文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普遍态度,也是董恂润色改写的重要目的。董恂不仅在改译稿中蕴含着文化“反诱”意图,而且他本人将这一意图付诸行动。他将改译稿誊写在精美的扇子上,于1865年托由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转送给朗费罗,成为晚清中美文学交流的趣谈。③对于朗费罗而言,这把精美的诗扇为他蜚声海外锦上添花,因此专门设宴庆贺此事。多年后,陈列在朗费罗博物馆的这把诗扇,倒是引发了不少学者游客慕名而去观赏,也算是实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互诱”了。
钱锺书(1948/1997:338)并不赞赏这种文化“反诱”,认为“把我们翻译外国文学的用意倒了个儿……翻译外国文学,目的是让本国人有所观摩借鉴,唤起他们的兴趣去欣赏和研究。”当下,我们以历史同情的眼光看待董恂的做法,一方面肯定他改译此诗以策励国人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对他“反诱”西洋人学习中国文化持辩证的态度。“反诱”西洋人学习中国文化,固然体现了董恂的本土文化优越感,然而相较于同时代晚清官员和文人对西洋文学的淡漠态度,董恂至少展示了对西洋诗歌的兴趣,肯去改译威妥玛的译诗底本。另外,董恂以诗扇为媒介,试图“反诱”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结果却是“送的人把礼物当钓饵,收的人往往认为进贡”(同上:339-340)。不过诗扇倒是引发了朗费罗邀请品赏诗扇的英国人福开森(Robert Ferguson)对董恂书法的兴趣。一百多年后,这把诗扇引发日本和中国学者的兴趣,前往朗费罗故居参观。可见,董恂“反诱”用心大多落空,反而有些许“正诱”的功能了,即引发本国人去观赏陈列在美国朗费罗故居的诗扇,增进了对朗费罗及其诗作的理解,也算是接近钱锺书所倡导的翻译外国文学的用意了。
5.结语
一首小诗的翻译,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仿若水滴大海,溅不起什么浪花。然而,这首诗歌在中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翻译和接受,已逐渐典律化。文学作品在异国他乡的流传,不仅是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更是文化之间的碰撞、交织和融合。恰如张隆溪(2017:111)所言,“无论是探索文学作品流传和接受的历史,还是跨越中西文化差异来讨论某个理论概念,中西比较研究都还可以大有作为。”通过梳理《长友诗》的晚清民初接受史,探讨晚清威妥玛译诗底本与原诗之间的偏移、董恂改译稿和威妥玛底本之间的差异,以及发表在《教会新报》上的《英国驻中国威钦差妥玛译西国名士诗》这一定本的文化意图,可以看出在晚清中西文化接触之初,西洋人和国人借助翻译图谋文化上的“诱”与“反诱”。以史鉴今,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译者身份及其翻译意图至关重要。
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两种语言文化的斡旋者。传统上,人们通常认为译者是作者的传声筒,是原文信息的复制者。然而,《长友诗》译本导向的描写研究表明,译本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文,译者也绝不是原文的传声筒。在选择一个文本进行翻译时,译者必然有自己的文化政治等翻译意图。这一翻译意图会在翻译过程中成为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关键性因素。翻译作为本土和他者断层交界之处,它到底是破坏和征服之举还是意味着转向崭新振奋的本土与他者融合?(Cronin,2011:55)站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译者应该如何选择拟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翻译应该起到什么样的功能?是“正诱”还是“反诱”还是“互诱”?翻译中如何处理本土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同时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这些问题都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探索。
注释:
①“A Psalm of Life”汉译题名有《人生颂》《生之赞歌》《生命礼赞》,本文采用晚清时的译名《长友诗》。
②《教会新报》由林乐知于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办,原名《中国教会报》,1872年8月31日改名《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更名《万国公报》。
③ 钱锺书文章中提及团扇送达时间为1864年。贺卫方在美国见到扇子后,根据扇子的题记时间“同治乙丑仲春之月”,认为这把诗扇于1865年赠送给朗费罗。见贺卫方:《〈人生颂〉诗扇亲见记》,《光明日报》1997年2月5日,后收入《法边余墨》,法律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