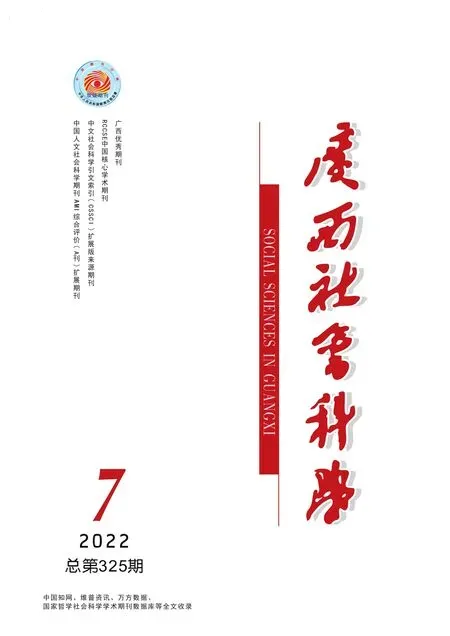论张謇的儒家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江海全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晚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状元。张謇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毕生坚守孔孟之道,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一生创办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典范,又被称为“状元实业家”。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张謇的研究,大都考察其商业、教育事功及政治社会活动,而较少考察其儒家信仰和哲学思想。张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实业成就,但他投身实业的价值定位不在“营利”而在“营志”,在其人生经历和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坚守和践行着“儒家三代理想”的价值追求。用张謇自己的话说“言商仍向儒”[1],这也就意味着他行动上是“商”,精神上仍然是“儒”。故而有学者指出,张謇经营实业,办教育,做慈善只是手段,实现“儒家千年王国”的理想才是他最根本的人生追求[2]。有鉴于此,本文拟将张謇作为一个儒学的“哲学家”来研究,将其置身于哲学家和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探讨张謇的“政、学、业”,以揭示张謇的儒家哲学思想对其成长历程、人格塑造和儒商事功发挥的重要影响。
一、张謇的基本哲学观及儒家哲学论域
关于对哲学的认识,张謇曾经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哲学是高尚的空气。1920年,张謇邀请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南通讲学,他在介绍词中说:“博士于哲学研究有年。哲学之作用最大,能呼吸高尚之空气,而使之附丽于实质之中。此实质之为物,使无空气以为营养,则日就陈腐而无用。故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宣布独立。中国讲哲学之最古者,莫如《易经》;其次则《礼记》亦有所发明。《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3]张謇的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层含义:第一,哲学的作用最大。哲学之于人犹如空气之于人。就像人不能缺少氧气而必赖之以维持生命,国家、社会和个人也不能缺少哲学性的思考和反思,否则就像人缺氧而不能呼吸,日渐陈腐和无用。第二,哲学的品性高尚。张謇之所以用“高尚”一词修饰“哲学”,是因为哲学在道德与伦理上具有崇高性,它涵括最崇高、最高尚的道德与伦理问题。它追求最普遍的道理,探求最广泛的公理与公德。第三,儒学有自己的哲学论域。张謇认为,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的哲学,很多儒家经典都可以归类于中国的哲学,“《易》、《礼记》、《论语》、《孟子》当哲名”[4]。
关于哲学的学科地位以及学习哲学的方法,张謇同样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第一,在哲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的关系上,张謇认为哲学虽然不研究具体问题,但诸种具体学科却离不开哲学,哲学是诸种具体学科的空气和灵光。在张謇的心中,哲学的学科地位最高。兹举以下事例证明:(1)1904年,张謇曾在《师范学校年假演说》中将伦理学、心理学、哲学三个学科排序为:“心理学”高于“伦理学”,“哲学”高于“心理学”。他认为“心理者,进于伦理而渐几于哲学之阶梯也”[5]。(2)1924年,张謇曾在《致美国政府请求以退还庚子赔款酌拨补助南通文化教育事业基金意见书》中提出“文科需办哲学与经史地理四科”[6]。(3)1924年,张謇在《致美国国务院远东局麦克莫里函》中说:“(南通大学)拟建之文理学院将设哲学、国文、历史、地理四系。”[7]可见在张謇的心目中,哲学是文科院系拟将建设和发展的首要学科。第二,关于研习哲学的方法,张謇认为哲学是研究普遍问题的学问,较各种具体科学应该阅读更多的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做到学以致用。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盖学必有体有用,力求为己,非仅笺注传说为也。”[8]“故学求致用,须是博学、慎问、慎思、明辨。”[9]概而言之,我们可以用《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阐述张謇研习哲学的方法,即广泛地学习,仔细地追问,谨慎地思考,明确地分辨,踏实地实行。他曾经提出研究《易经》的三条标准,即“参天道”“明人事”“切于日用行习”[10],这三条标准可以看作是以上方法的具体应用。
二、儒家哲学经典《易经》对张謇的影响
在诸多儒家经典中,张謇最重视《易经》并受其影响最大。他对《易经》的评价非常高,“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者,莫备于《易》”[11]。张謇对《易经》研习最多,13岁开始读《易》,39岁完成了一生中唯一一部学术研究专著《周易音训句读》。他对《易经》不仅用功颇深而且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在张謇的人生经历和职业生涯中,《易经》是其应用最多、实行最多的儒家经典。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阐述《易经》对张謇产生的影响。
(一)《易经》对张謇人格塑造的影响
著名的张謇研究专家章开沅曾这样描述张謇的人格特征:“意志坚定、百折不挠而勇于进取。”[12]这样的描述与《周易·乾卦·象传》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并无二致。自强不息、刚健进取最能体现张謇的人格特征。张謇平时所用花押①旧时文书契约末尾的草书签名或代替签名的特种符号。镌刻着“自强不息”四个大字,他一直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以下仅举一例证明。
张謇初创企业之时,困难重重,并遭受刁难和讥讽,“甚至完全可以说,张謇的所有实业均是在人为的阻力中起步和发展”[13]。张謇曾在日记中记录他与各级官吏打交道的切身体会:“一事一始,上则官绅之谣诼,一影而纯声。下则黠桀之猜疑,强言而弱色”[14],但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激发了他成就一番事业的决心和勇气,锻造出坚强不屈的性格。张謇曾经不止一次在演说中表明自己的这种心迹,“自弱冠至今三十余年中,所受人世轻侮之事,何止百千”,“惟受人轻侮一次,则努力自克一次”[15];“事之艰难颠沛,对于个人,乃为磨炼;对于事实,则为促进。若因艰难颠沛而不为,成于何望?”[16]“将外来横逆当作火熔淬金铁,借以淬我积成君子之资格”,“要有千万人吾往之其,有人扶助要做,有人阻抑也要做”[17]。当时的媒体对张謇的评价恰如其分:张謇“办事则立定脚跟,踏实做去,愈遭挫折,愈求猛进”[18]。
(二)《易经》对张謇儒商事功的影响
李泽厚认为,“《易传》……其中最重要的精神正是‘天地之大德曰生’”[19]。张謇研习《易经》最深的体悟也恰恰表现于这句话,乃至于它成为张謇“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和“应尽的本份”。张謇对“天地之大德曰生”解释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份。”[20]张謇一直秉持这句名言,坚守着儒者“应尽的本份”。
“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张謇的人生宗旨和世界观,张謇整个人生事业都与这一宗旨融合在一起。例如,1899年4月,张謇人生中第一家实业历经四年挫折终于在南通唐闸镇建成投产,他根据《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将之取名为“大生纱厂”,以示他所办的纱厂能够实现济世救民的初衷。日后要扩充盐垦,张謇也解释为“亦不离此宗旨”[21]。根据国内学者的考证,张謇所创“大生”系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97家企业几乎一半的命名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周易》[22]。
其一,命名直接取自《易经》的有21家企业。(1)以“大生”命名的企业共有12家,直接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如通州大生纱厂、崇明大生纱厂、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厂等。(2)除“大生”外,6家企业名称也是直接取自《易经》。例如,广生榨油公司名称取自《易经·系辞上》“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通州资生冶厂、资生铁厂名称取自《易经·坤卦第二》“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大有房地产公司、大中公行名称取自《易经·大有卦第十四》“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中孚盐垦公司名称取自《易经·中孚卦第六十一》“泽上有风,中孚”。(3)直接提取《易经》词组以合成企业名称的有3家。例如,大有晋盐垦公司名称系“大有卦第十四”与“晋卦第三十五”之合成;大豫盐垦公司名称系“大”“豫”之合成,源于《易经·序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大丰盐垦公司名称系“大”“丰”之合成,源于《易经·丰卦第五十五》“丰,大也”。
其二,命名间接取自《易经》的有27家企业。(1)“大生”系统中有24家企业命名间接地来自《易经》,其中“大”作词头的18个,如大兴机器磨面厂、大隆皂厂、大昌纸厂等,“生”作词尾的6个,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颐生酿造公司、颐生罐洁公司等。(2)另有3家企业命名也可以视为间接地取自《易经》。例如,通明电器公司名称之含义取自《易经·系辞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合德盐垦公司名称之含义取自《易经·乾卦第一》“天地合其德”;通遂盐垦公司名称之含义取自《易经·系辞上》“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由是观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已经成为张謇最核心的价值观。“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张謇之“道”,不仅融进了他的思想中,而且和他的整个事业融合在一起,他所创办的企事业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诠释。
三、张謇对儒家“中道”思想的理解和践行
孩提时代的张謇已经接受儒学教育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年仅十岁,就已经掌握儒家经典《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十三岁至十五岁的三年间,他依次读完了《尔雅》《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能做八韵诗,制艺也能成篇。张謇从儒家经典中感悟最深的可能是儒学的“中道”思想。他对“中庸之道”赞赏有加,“夫圣人之道则中焉耳”[23],“孔子之时中,为万世不易之正轨也”[24]。他认为,儒学在中国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并产生如此深远影响,其根本原因就是儒学始终坚持“中道”、不偏不倚,而其他“任何一家之学说,主张稍过,不折于中,未有不流于偏宕者”[25]。
(一)张謇对儒家“中道”思想的领悟
张謇对儒家“中道”思想的领悟融合了孔子和子思的思路。第一,孔子首先提出“中道”思想,其目的是用以规范人的言行。他所谓“中道”就是“执两用中”。孔子把“礼”看作是对“中道”的规定,要求人们的言行符合周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张謇遵循了孔子的思路来理解“中道”思想,他认为:“夫圣人之道则中焉耳,贤者过之而不肖者不及。圣人不能必世无过不及之人,而必不能因有过不及而易中之道。中即事以为权,非执一以驭事。”[26]“人于事物,必与其近己者而好之,而至于有所主张,稍有不慎则过。舜用中,孔子时中,中之施于事于无物,礼义之制裁也。中而时,则礼义之权度也。”[27]也就是说,一般人做事,常因对事物有所喜好而生偏执,将事情做过头,然而圣人遇事权衡,不按照某一条标准驾驭所有的事情,守正而处中,不偏执、不消极,因此圣人做起事情来,从没有做过头或者不及的情形。第二,子思把“中道”的概念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他认为,“中”与“和”乃是宇宙中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遵循这一法则,天地万物得以平衡和谐地发展,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繁荣兴旺。他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张謇将“中和”理解为天地间最根本的普遍法则,恰恰体现了子思对“中道”的理解思路。张謇认为,“世即变而道无时而不存,即中无时而不在也”[28],也就是说,世界虽然是不断变化的,但是道是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的,即“中道”是永恒存在的。此外,张謇还发现,《周易》最丰富的思想也是“中道”:“世变未知所届,唯守正而处中者,可以不随不激。此种道理,《易经》最富。”[29]
(二)张謇的“中道”思想对其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张謇的“中道”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人格特征,而且影响了他的行为方式。张謇研究专家章开沅认为:“张謇沉稳性格也是其所崇尚的‘中庸’思想的延伸。”[30]张謇在日常生活中,为人谦和,注意把握自己的言行分寸,从不嬉言狂语。用张謇日记中的话来讲:“才须晦以养之,谦以益之,否则恐招忌招损。”[31]张謇也曾在一首诗中自嘲:“生平万事居人后”[32]。这与儒家“和为贵”的中庸之道,以及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的告诫是一致的。张謇一向主张温和的行事方式,反对急躁情绪和过激的举动;他主张行事要循序渐进,要“因革损益之宜,第轻重缓急之序”[33]。张謇将儒家“和为贵”的中庸之道继承下来,并在社会运动中贯穿其行为。
其一,张謇坚持缓进的政治改革,主张立宪政治。清末的知识分子都主张变革,但却因为变革的方法和目标的不同而划分为革命派和立宪派。张謇主张走君主立宪道路,反对以激进的革命手段改变中国现状。张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积极公开倡导和投身立宪运动。他希望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和经验,采取合法手段成立国会,制定宪法和建立责任内阁,以此改变封建专制政体。为此,他还组织友人编译《日本宪法》《日本宪法义解》等书籍,进行宣传或者辗转送达内廷,以争取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其二,“和为贵”是张謇与袁世凯合作的基础。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张謇审时度势,毅然放弃了曾经倡导的立宪主张,进而转向共和。张謇在解释自己的这一选择时说:“环视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者,趋势然也。”[34]事实上,张謇这种转变不仅是历史潮流使然,也是受儒家“和为贵”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张謇担心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国家“兵连祸结”、分崩离析。于是,为了使国家尽快恢复统一和秩序,张謇不遗余力参与南北调和,希望尽快求得“和”的局面。
四、张謇礼学思想及其人格修养
张謇非常推崇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告诫他:“处人须时时记定‘泛爱众而亲仁’一语。尤须记‘谨而信’一语。所谓《论语》《孟子》,信得一二语,便终身受用不尽也”[35]。《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必须以“礼”为规范,做到了“礼”,便真正做到了“仁”。《论语·颜渊问仁》中,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最重视“礼”。《论语》中谈到“礼”多达74次,例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好直不好学,起蔽也绞”(《论语·阳货》)等,这些都是在说学“礼”的重要性。孔子认为,礼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如果所有人都按照礼治规定,等差有序,贵贱有等,各处其位,各奉其事,社会秩序就会井井有条。
根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记载:“五年丙寅(1866),十四岁。读《礼》、《春秋左传》……六年丁卯(1867),十五岁。仍从学于西亭,间从璞斋先生问业。读《周礼》、《仪礼》,苦《仪礼》难读,亦不甚了解。”[36]尽管张謇接触儒家礼学著作较其他儒学经典晚一些,但受其影响却比较深。
其一,张謇与孔子一样认识到礼对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张謇写道:“礼者,人之大防。《传》亦有言,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为一人言之耳。一人且不可无礼,而况于十人、百人、千人、万人之众欤?”[37]“盖一人无礼则身危,千万人无礼则国危。”[38]他曾经引用孟子的话抨击当时社会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无礼”行为:“孟子之言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呜呼! 何其言之痛而迫也”[39]。为此,张謇决定从教育入手,在根本上改变当时道德衰败的局面。他常常借开学或者散学时机,对学生宣讲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比如,在《师范学校暑假散学演说》中,他指出:“办事待人,却处处要以仁、礼、忠三字为的。”[40]他为各类学校题写的校训也非常重视德育。比如,他为南通大学纺织专科和商业中学所题写的校训分别为“忠实不欺”和“忠信持之以诚”[41]。他还提出“重德”说:“首重道德,次则学术”[42]。
其二,张謇饱读儒家经典,将儒家伦理人格视为人生完美、高尚和理想的范型,一生践履,时时处处都在按照儒家“礼”待人接物,践行修身。“礼”是儒家最重视的个人修养。孔子将“恭敬、宽厚、诚信、勤快、忠爱”作为“仁”的最基本要求,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便称之为“礼”。张謇在自身的品质修养方面力求做到以上基本要求,“宽以待人”是他的修身实践警言:“盖对人宽,是之为恕……宽以待人,即修身之实践也。”[43]张謇晚年仍然积极弘扬儒学,推广儒学教育。例如,他将海门常乐镇老宅大厅改题“尊素堂”、设“尊孔会”、重修南通的尊孔会等,而且他还将传统儒家伦理人格的内涵赋予时代意义,进行了现代性的转换。例如,他强调:“欲昌明孔学,宜就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八字做起。子为孝亲,臣为卫国,弟为敬长,友为爱人,此属于分际也。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此属于行为也。人能明分际而谨行为,斯尽人道矣。人道尽而后可以进圣贤之域,孔子一身得力处,即在于此。”[44]
五、儒家的义利观与张謇的儒商伦理思想
义利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子及其后儒一贯之主张是重义轻利。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人的行为只要是真情流露,合乎礼,即是至好,不必问结果是否有利。孔子一生行事,亦是如此。子路为孔子辩护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冯友兰用后儒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来解释这句话——“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即“正其谊”“明其道”也;至于道之果行与否,则结果也。“利”也,“功”也,不必“谋”,不必“计”[45]。
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在张謇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阐释。第一,张謇重义,以义为本。张謇的“义”是救民生于“水火”之中的“大义”,营商取利只不过是他实现其“大义”的手段和形式。张謇办厂的动机不能仅仅归结于像一般资本家那样追求资本主义利润,张謇之所以历尽艰辛,筹办工厂,他的动机可以说是爱国与求利相结合,并且还有关心民生苦乐的成分。张謇认为发展民族工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是改变贫困的必由之路。他艰苦创业,使大生纱厂站住脚跟并获得赢利以后就把很多赢利投向进一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中,为改善当地社会经济条件服务”[46]。第二,张謇言利,以利辅义。张謇的“利”是国家之“大利”。他说:“国势日蹙,一息尚存,有一份心力,即当与邦人大夫共谋一份公益。”[47]张謇的“利”还是民众之“公利”,而非个人之“私利”。正如他所言:“鄙人志愿并不在专为股东营余利,实欲股东斥其余利之所积若干成,建设公共事业,为一国立些模范。”[48]由是观之,作为晚清儒商的杰出代表,张謇集近代工业的“重利”思想与传统的“重义”道德观念于一身。他兼顾“义”和“利”,“义利合一”;他将“义”和“利”统一于“振兴中国之大义”之中,他所提倡的“利”是“义”中的“利”,是公利和私利的结合。
儒家的义利观直接影响了张謇的儒商伦理观。首先,张謇虽然从商,但他与当时社会上“志在营利”的一般企业家群体存在截然的差别。利润的追求并不是张謇投身实业之唯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驱动力,而是尽儒者本分,建设新世界之“大义”。正如他在《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中说:“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49]其次,张謇经营实业不是谋个人财富,而是为公众谋利。正如他在《北京商业学校演说》中所说:“人或谓余弃官而营实业,必实业获利有大于居官之所得者;又或谓余已获利数十万金,乃仍集股不止。何耶?当日似以余专为致富计者。余则若专图个人之私利,则固有所不可;若谋公众之利奚不可者?”[50]
张謇认为,企业家应具备的美德是勤勉、节俭、任劳、耐苦。他说:“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51]。在这些美德之中,他特别强调“俭”。“今何独举俭一字为诸生勖?俭可以凝贞苦之心,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52]张謇自号“啬庵”“啬翁”,其中“啬”取自老子《道德经》之“治人事天莫若啬”。“啬”是节俭之意。张謇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待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张謇)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53]
张謇批评当时社会上店主与学徒不平等的役使关系,认为这是我国传统积习:“商店学徒所为捧烟酌茶,对于商店总理,极端服从,甚者且执贱役……外国商店用毕业生固匪若此,然吾国积习相沿,遽欲改之,亦大难事。”[54]张謇认为,企业有管理层与员工之别,但这只是分工和岗位之别,不是役使关系。企业主或者管理层应善待自己的员工,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享用,企业主与员工之间应该建立基本的商业伦理规则。他呼吁:“余甚愿诸君服劳耐苦,凡他学徒所为者无不能为,而独有学理以胜之。絮长比短,可以无往而不得志。诸君要知个人享用,绝无可以过人之理。同此人类,有何理由,而谓吾之自奉可以独奢乎?”[55]
六、张謇儒家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方面,张謇的儒商伦理精神对提升当代企业家群体的道德境界,培养更多的“当代儒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作为儒商典范,张謇一方面具有儒者的才华和操守,另一方面具有商家的睿智与聪慧,他既是儒者的翘楚和楷模,又是商界的豪杰和精英。他由儒入商,以儒经商;言商仍向儒,在商终是儒。与传统儒生从学、入仕有别,商人是其社会身份,实业是其职业,他的儒家理想没有变,他将儒学的道理融入其日常生活和事业中。当代企业家应以张謇为镜鉴和参照,践行张謇的儒商伦理精神。具体而言,应继承和发扬张謇勤勉、节俭、任劳、耐苦的儒商美德,并将其作为长期经营的支撑性内容;遵循社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从事商品交换,积极效仿张謇的“义利合一”“诚信为本”的经营之道;从张謇身上借鉴“经世济民”的胸怀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既要重视企业的经济效益又不忘社会的公益事业,既要有先富起来的勇气又不忘回报社会、造福乡里。
另一方面,张謇的儒家信仰和儒家哲学思想与其人格塑造和儒商事功的关系对当代人理解哲学与人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第一,没有哲学的人生将是盲目的,脱离人生的哲学将是空洞的。如果将人生比作航海,那么哲学就是航海的罗盘。一个人的哲学观通常决定着一个人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的理解,所以张謇一生完成农、士、官、商等不同社会阶层的转变绝非偶然,潜藏其背后并决定其不断抉择的基底恰恰是他的儒家信仰和儒家哲学思想。作为一位儒学“哲学家”,张謇秉承其儒家哲学理念,将易学、礼学等哲学思想融于人生经历和职业生涯中,坚守和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且业绩卓著、泽被后世,因此儒家信仰和理想才是他最根本的人生追求,而儒商事功只不过是他实现儒家理想的手段。第二,一个人需要不断从哲学中汲取前进的动力和为人处世之道。在诸多儒家经典中,《周易》对张謇影响最大。《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张謇儒家理想人格的真实写照。自强不息的人生观是张謇的哲学总纲,也是张謇一生的追求。儒家的“中道”思想不仅影响了张謇的人格特征,而且影响了他的行为方式。张謇对儒家“中道”思想有深刻的领悟,并贯穿其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行为中。他严格按照儒家的“中道”原则待人和处世,守正而处中,不偏激、不消极,顺利化解各种人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