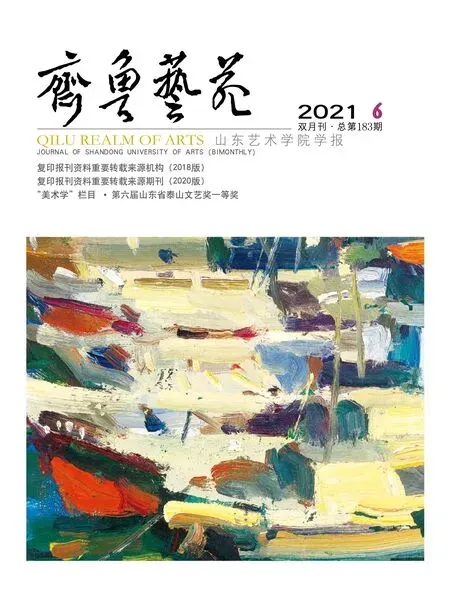从“乾”到“未济”
——攸关中国神话动画电影新现象的哲思
谢 辛
(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学院,北京 100088)
作为中国哲学最为古老的集大成者,《易经》成为君子道德修养的标准。东汉郑玄在《易论》中指出,“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简易”对应了事物发展背后的常规、定律,“变易”指的是超过一定限度的可变性,“不易”则如真理一般恒常不变。简单的三个词,道出“人”之所为“人”的朴素认知。当我们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媒介环境中,去找寻“人”的真正含义之时,回望古代哲学,或许这三个带有“原初性”色彩的词汇已然表明答案。而当我们从对“人”的思考移植于对思考的显现时,就会出现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无法找到那个所谓的“人”之标杆,更可能将其想象为某种“神性”的角色。于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类神话诞生,神话故事亦成为电影类型的一种重要来源。同时,想象与动画对应,动画电影逐渐成为神话的重要载体,《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传统神话故事IP的不断再现、复现,其内核正与我们所说的“人”之意义的探讨对应,又传达而显现出媒介化生存的视听新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想要从技术中抽离出来,对“人”形成再思考的冲动。需指出,本文并非影像文本分析,而是从其内核指向与观者诉求根源的视角,结合东西方哲学的共性议题,进行一次力求贴近“人”之本源的哲思,具体概括为三个关键词:人、物、在。
一、“人”主体:心之所向的“主导性”与“反身性”
如果借用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待第一个关键词,人,即是我们自身,从人自身出发,这一点无可厚非。对人的探讨,可谓万物之本、万法归宗,当下不断奔涌的媒介技术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或许此番改变并非全人类之主动行为,似乎也对应了我们常说的“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的技术主导性,但不管过程如何,这一改变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符合上文所述“简易”的阐释。当下,人们对于人性、神性的思考呈现出何种表征?表征又对望何种“心之所向”?
(一)“人性”与“神性”的互见
孔子将《易经》推崇为群经之首,“周易之精,不在辞之美备,而在序之精当。”其中,“序”即对应“简易”,对人而言,“序”是人性的重要特质,更准确说,是人生运动、联系、发展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一种精神,在人不断上升的时候给予警示,在人陷入困境的时候赐予信心,“序”的阴阳共生,既是平衡,又是“变”与“不变”的互见。正如我们赋予神话故事的诸多神性想象,成为“人”的“替代”,完成一针思想慰藉的醒脑剂。电影,成为“神性”外化的最佳媒介展示,宏大场景的视听呈现为想象赋能,“神性”的解读也从文本(小说、连环画等传统媒介形态)走向影像,从而放大意义的传达。
比如哪吒这一耳熟能详的传统神话故事角色,来源于历史演义中殷商末年陈塘关总兵李靖三子的记载,同时也是先天神灵“灵珠子”投胎。其经历浩劫和磨难之后,终究以佛为父,化解冤仇,逐渐成长为护法神的角色。

图1
而在《哪吒之魔童降生》中,元始天尊孕育混元珠“灵珠”和“魔丸”在投胎时的阴差阳错,却改变了哪吒的出身,甚至所谓命运的安排,契合人类不被打败的奋斗精神。创作者一句“有什么比让观众直接带着‘成见’进入故事,再用作品亲手打破它来得更带感。”[1]进而展现出人性探讨的现实意义,以及上文提及的“再思考”之“再”的深层内涵。
“灵珠”和“魔丸”以蓝色和红色呈现,对应五行之水与火,我们都知道水克火,因此在这部改编版本神话故事中,创作者将传统意义的“水”定胜“火”之顺向隐喻,扭转为“火”之可变性的逆向思考,也就是说,我们期待看到这个小混世魔王的发展,是不变之“火”?还是翻转之“水”?这是盘古开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有关奋斗精神的神话故事的延续,更是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人性”与“神性”的互见,其明晰地指向了欲望本身。
在媒介化生存的时代,人性之欲望不再被掩盖,存在数种可供传播和公开的途径,因此从潜意识上说,传播与公开这一行为本身,很可能成为某种驱动力。作为“灵珠”(善)和“魔丸”(恶)互见的母体,人们常用“纠结”来宽慰内心无法描述却如鲠在喉的感知,其来源与当下流行的网络词汇“内卷”“躺平”“吊诡”等对应。有趣的是,当我们非常清楚“灵珠”和“魔丸”的“共生性”时,却常用言语、行为等外化的表征在现实中尝试逃避,反之,在动画电影中毫无保留地放大。这本身也是“纠结”的,因为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真实与虚拟媒介所谓承载功能的差异,而指向类似阴阳的“合一性”。所以说差异本身很可能不存在,我们无时不刻追寻的更像是一种平衡。当“灵珠”走向极致的时候,物极必反,类似从“升”到“困”的阶段;当“魔丸”的影响力似乎要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时,也正是物极必反,从“困”到“革”,顿悟往往在一瞬间。由此,我们可以将《哪吒之魔童降世》高票房、优质口碑的双赢,看成是一部讲述穷探天理、洞悉人事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学阐述。福兮祸兮,天人合一,当人们能够直面内心“灵珠”和“魔丸”共生的欲望时,也就直面了人性与神性之间那道预设之墙,破壁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从神性中管窥人性,如何从人性中挖掘更为本质(笔者更愿意称之为朴素)的“简易”存在之理。
(二)看得懂的神话故事
从颇具规模的中国动画电影中不难看出,神话故事是其创作的主要来源。业界将神话的直接视听化呈现、神话改编等称之为IP、衍生品、泛化……电影、短视频、手办、cosplay等产品频出,可以说,这本身就是媒介“变易”的表现,“变易”的形式也越来越视觉化、流行化,不断扩充当下可能从多媒介领域获得观看体验的广大受众群体之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文字变为图像、影像的神话故事,既让人看得懂,又在这一看得懂的表象中,赋予其内涵向外延展的可能性。看似自然而然的媒介变革与视听呈现,并非完全取决于技术革新的催生,回望古代哲学,这一点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关联,呈现出人性/神性探讨的杂合性。
看得懂的第一层,是影像的直观观感。有研究者称,《周易》是兴象之源,“‘兴’是看到外物而产生情感的过程……与西方人逻辑的、实证的思维习惯不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更强调直觉,这种直觉又往往借助某些形象表现出来。”[2](P7)直觉、形象等词汇,引入动画电影则转化为与创造力、想象力、艺术性和典型性等特征的对位。古人依靠直觉,依稀洞见“道”的“混沌”,赐其“太极”与“阴阳”属性,所谓感性入手,理性发展,感性与理性的共生,也深度影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演变。因此,我们总能在诸多优秀动画电影作品中,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比如《白蛇:缘起》人妖相恋之凄凄惨惨戚戚,又充满人性对于纯粹之爱的无限憧憬。或许,作为捧着爆米花的观众,总想从人与妖制造的视觉孽恋中,找到某种求变的方式。然而,当我们认定其为“孽恋”的那一刻,即表明结局的某种不可变性:要么,殊途同归;要么,两败俱伤。对于观众而言,孽恋的根源,实际上在于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神话故事而已,此时,人性与神性的探讨,也更趋于被神性不自觉的消解所代替。

图2
第二层则指向了上文所述神性的落地,即从影像中的神话角色与神话故事,感知人性。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例,孙悟空依然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唐僧以乳名江流儿的小和尚形象呈现,这也是其十世轮回的第一世。影片将孙悟空历经劫难的顿悟与江流儿一心向善的点化合一,直指人性的主动/被动救赎。比如孙悟空,始终呈现出急躁、热情、奋进,但又冒进的性格特点,这一点无论是原著还是改编动画,都心照不宣地将展示其性格的另一面作为故事的主线,与之对应的是人生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所要面临的未知征途,在梦想能够照进现实的路上,以孙悟空为类比案例,将人一生中面临的迷茫、坎坷、困境与瓶颈全部展现,神话故事的想象性不断减弱,代入感增强的同时,也让观者从角色性格塑造的正/反角度,思考自身,从而形成神性对人性的映照。通俗的说,我们很容易在近年神话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中,感知某种思想的升华,或境界的通透,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作品能够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佳绩了。

图3
二、物“客体”:媒介化生态的“相关性”与“影响性”
前文所列举的电影案例,基本都以外传、前传等番外形式存在,基于不破坏原著建构的宇宙观的初衷,对故事进行重构,展现出背离“刻板印象”,但又对应了深挖角色性格内核本质的倾向性。同时,也表现出当下人性思考的特征性,虽然从短视频、直播等视听新媒体内容中,我们很难将深度思考与大众娱乐之间进行有效连接,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影片票房/口碑并举的现实,促使某种思考方式的重新回归。这很可能取决于人在媒介化生存样态中所呈现的“物”的相关性。
(一)“物性”与“拜物性”
从海德格尔、鲍德里亚的角度去分析“物”,势必带有不断重复的批判性,而我们以为的现象研究,也不只是直觉,本质上更是批判的。从这个层面上来分析网络给人们带来的“物”之思考,笔者认为批判性很可能被某种朴素的崇拜感、好奇心所影响,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媒介化生存的时代,直觉(或者说是浅层心理)更可能是与“物”对应的最明显特征。
首先提起“物性”,从消费观念角度来看,当下大众已然从物质消费转为心智消费。比如观者对于神话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作品的期待,或许并不源自主动性,毕竟神话故事的刻板印象早已深入人心,更像是随着第一个取得成绩的作品出现,创作者对该类题材投入精力与物力、财力,进行创作的再生产与再接受。当作品出现在院线、网络端之后,观者开始发挥社交网络赋予的主动性,观看、转载、评论、发酵等一系列心智消费行为,其内核又与物质消费勾连,可以说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网络勃发的时代,可能仅表现为切入视角的不同罢了。
其次,当我们剥开“物性”的外壳,探其本质的时候,会发现“物性”的根源实际上指向了“拜物性”。正如神话故事的不断改编,展现出对票房/口碑双丰收期待模式的效仿,其同时也正视了人们对于神话故事这一元文本可挖掘度的“崇拜”。这个词用在此,丝毫不过分,同时结合时代特征,又表现为一定的对应关系,比如与人类/技术、虚拟/现实的某种“崇拜”心理相契合。
物性与拜物性的基石为“物”,我们从其根源上来看,回望古代哲学,按照普遍意义的理解,伏羲发明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尽览“物性”。而我们深入了解发现,比如《周易》第一卦“乾”所对应的“天”,并不只是天空、宇宙等头顶之物,而更像是一种“天”的宏大概念,乾:元,亨,利,贞。元:开始,亨:亨通,利:和谐,贞:正直。其“象征着天:是万物的开始,有亨通的力量,能和谐而有利于物,有光明正大的品格。”[3](P2)由此不难看出,“天”之“物”的理解,在古代就表明了某种抽象性的态度,其指向性很明显,与世界、自然、人的关系直接相关,使得我们对于“天”的理解更趋于制约、主宰的表达。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称,“《易》难看,不比他书,《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4](P1)
而在最后一卦“未济”(水火不容)之前,是“既济”(水火相容)。从“相容”到“不容”,“其有忧患乎?”的疑惑频出,《诗经·大雅·荡》中一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道出“未”的真正含义:一为“未实现”,还需努力;二为“为完成”,还要启示后人。因此,我们或从古人的智慧中,发现其中之妙,那些“简易”与“不易”承载的“变易”,竟全都成为“心之所向”,就像神话故事和神话电影内容所呈现的奋斗精神、顿悟态度与明示警醒,又似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方得始终的感召,总能让我们从对物的崇拜中抽离出来,从物性回归人性,又或许,二者之间的并行关系和排列关系始终没有改变过。
(二)“造物”与“造物者”
结合当下技术发展来看,新现象与人类的创作力正相关。我们从未想过在现实中出现的,或者说在科幻电影中设想的机械人类逐渐成为现实,“造物”的意义凸显。作为机械之“物”的“造物者”,人类经受着时代、社会与自身的考验。再次回看《西游记》IP系列动画电影(也包括真人电影),大圣的自我救赎与成长,对应人对“人”本质的思考,这个“人”在近年的学术探讨中,被延伸为“后人类”。
诚然,笔者不借本文去探讨“后人类”究竟指向肉身之人的机械共生,还是机械人类的情感学习,更想要传达的是,如果我们说“不易”是世界观,“简易”是方法论,“变易”则是试错、通达与发展的路径。在人类不断相信“后人类”来临,并将这种探索未知的态度用固有神话的方式,借动画电影进行传达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有趣(看似与前文所述相悖)的现实:人对于“人”本质的思考,并未因为媒介、技术、文化的转型消解,反而在潜意识中更加增强了这种思考,但与古人不同,思考的环境发生了转变,势必影响思考的对象。如今,我们再思考的对象,不是后人类的“人”,而是“后”,其很可能影响神话电影世界观的再建构,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创作者要对原生IP进行完全相反的改编了。
如今,拜赐于技术变革的力量,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对“物性”和“造物”的亲近感,实际上也就增加了“变易”的诸多可能性,在神话故事的改编电影中,也不难看到除了动画类型、真人扮演类型,还增加游戏等诸多联动形态。比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由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绿洲游戏和十月文化工作室联合出品,定位为角色扮演游戏,其对电影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玩法包括动作和轻量的成长要素;《魁拔》系列手办,则标定“二次元”群体,形成借助动画与“二次元”同构关系而衍生的神话产品。虽然“变易”的形态多种多样,但其“变”之根本,依然与某种内在的“不变”相联系,即基于神话故事的“原生性”,让广大受众借由多重形式不断主动/被动地趋近神话故事的本质。这也可能是一种在“后人类”热议的当下,从“后”回归“人”之思考的方式,对应了从“乾”走向“未济”,进而再次重构的哲学提示。因此,我们或可逐渐明晰一个规律:对于国人而言,思维方式与思考走向的养成,势必基于一脉相承、传移模写、薪火相传式的传承与创新,而其根在国家、民族和中华文化。

图4

图5
三、在“宇宙”:“原点”与“终极”的混沌特征
从“人”与“物”的阐释中,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共生,且始终相伴相生。“人”是“物”的主导者、创造者,同时“物”是人的引导者、影响者。进一步来看,当“人”与“物”共同存在的时候,二者存在之“在”的意义凸显。此处的“在”,不只是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努力研究的方向,更是契合中国古代哲学中“简易”“变易”的第三个层次“不易”。对于当下媒介化生存的我们而言,究竟何为“不易”?神话电影中存在的“不易”,又体现在哪里?
(一)谁在这里
我们从“在”的字面意义来看“在”这里的问题,如果说对于本文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言,最为重要的指向性是“人”,则“人”对应“谁”,“谁在这里”成为这一字面解读的关键点。先来看其表层含义,从神话电影中引用的神话故事来看,经典的、神性的角色“在”银幕中呈现,观者“在”各种媒介载体中观看影像,创作者“在”改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角色和故事为主的IP“在”泛娱乐时代更契合多元发展的要求……“在这里”的“谁”共同完成了“在这里”的矩阵式/网络化的新媒介表征。而回过头看“谁”/“在”的深层含义,又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
第一层“谁”,指的是“人”本身。类似于海德格尔对现象学还原的理解,“把现象学的目光从对存在者的把握——无论这种把握的特征如何——引回对该存在者之存在的理解。”[5]于是,存在者之“在”将我们对“谁”的关注,又转移至“在”本身。也就是说,对“人”、人性、人生理解的笃定性,可以理解为“简易”的规范与标准,“在”所承载的变数则更具有未知性和想象性。但同时,海德格尔也指出,“任何显现都是对人的显现……‘显现’ 的确切含义应当是最贴近人的过程,但最贴近人的并不是人的意识, 而是人的存在;人并非总是处于有意识的状态, 但却始终不能离开存在。显现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理解,人首先在对存在有所作为的过程中理解自身的存在, 对存在的作为是行动;其次, 才是对存在意义的思考。”[6]“贴近”一词,符合当下媒介化生存的受众样态,我们不断贴近对“人”本质的理解的过程,即是对“在”的不断认可,具有“反身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易”在当下,更可能与诸多变化之“人”与“物”之“在”对应,“在”始终未变。这也是近年诸多国产神话电影所传达的内核,其在本文撰写过程中,被反复印证。
第二层“谁”,并没有明晰的对象性,其更像是“在”的主体/客体的统一。笔者认为,倘若我们能够将对“人”与“物”的思考变得可见,对“在”而言,其更像是一种模糊的、似是而非的,趋近符号、精神与梦境的场域。从伏羲所创的阴爻(--)、阳爻(—)来看,两根线的不同排列组合与纠缠态,构成对“人”本质的完整思考,而“在”同理,比照后称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东西方哲学的宇宙观外显。以哪吒为例,当他决定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刻,究竟是“灵珠”还是“魔丸”已不再重要,唯有那些变化的“在”、不变的“在”等客观之“在”,那些“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的精神之“在”,始终影响他的人生。就像海德格尔所述,无需任何“人”或“物”而存在的“在”,是无边界的。这也赋予我们对IP改编、人性思考、媒介环境等以新的启示,“在”的无边界,对应了多元、共享等新词汇所指代的行为指征。
(二)人在哪里
“这里”是“在”,“哪里”亦然,且契合无边界性。海德格尔曾述,“存在者并非处于某种固定的确定性之中,而是处于生活的日常状态和历史性(时间性)中。”[7](P476)当我们用所谓“此在”“彼在”的概念来更进一步阐释“在”的时候,会发现其包罗万象的时空属性在不断显现,具体到神话题材电影,丰富的想象力用打破时空、重构世界等方式,表现与人类生存场域相异,却又充分展现人性的世界。正如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在“存在”上打了一个“×”所做如下解释,“×”的四个边角分别指向了“天地人神”。[8](P65)这也是神话从想象视阈落地为“看得懂”的电影作品的主要特征——天,世界;地,生存环境;人,角色;神,神性、神力的想象。于是,我们会发现这四个字概括了神话电影的主要特征,同时,也为本文所探讨的人、物、在三个关键词标定了指向性,生存之人、生存之物、生存之在构成生存的意义。值得一提,“×”可以理解为对“存在”的否定,当其置于“存在”之上的时候,又带有某种否定之下的奋斗意味,像极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哪吒,打破宿命论的桎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而此时再次回望“简易”,“简”为“坤道”,“易”为“乾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当“变易”表现得越来越多元的时候(也就是媒介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更像是诱惑,人们热衷于触碰诱惑、道德的边界,更享受这种触碰过程带来的潜意识快感,在这个模糊不清的阈限空间中,人们的路径分成了两条:义无反顾地拥抱诱惑带来的沉醉;进行必要的、停滞的思考,再选择出发。对于第二条路径来说,再次出发的方向性就变得更为明晰和笃定。诸如孙悟空、唐僧、哪吒、白娘子等一众神话形象在神话故事中所展现的性格、为人处事的方式和命运的相似性,都旨在对不同时代的人类予以某种强有力的暗示,对应上述两路径的选择性。而这一点,又具有“在”的普遍性。
结语:“多重合一”维度的“变化”哲思
综上所述,东西方哲学对于本文阐释的三个关键词的理解,都指向了“人-人性”的探讨,或许我们在一瞬间想要将其归为某种巧合,又或许这种巧合实际上又因为“指向性”的“共性”而变得再正常不过。三个词,简而言之,“人”是主体,具有“主导性”和“反身性”;“物”是客体,具有“影响性”;“在”是宇宙场,指向物质与精神性的合一、真实与虚拟的合一、天人合一等“多重合一”维度。三个词紧密围绕“简易”、“变易”与“不易”的人生过程,又展示出以“在”为原点和终极的混沌特征。最终,我们借助神话电影为案例的深层探讨,会发现古代哲学对易的本质思考,实际上在于那唯一不变的内核——变化。而我们回头再看,关于从“乾”到“未济”的哲思循环的探讨,势必也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