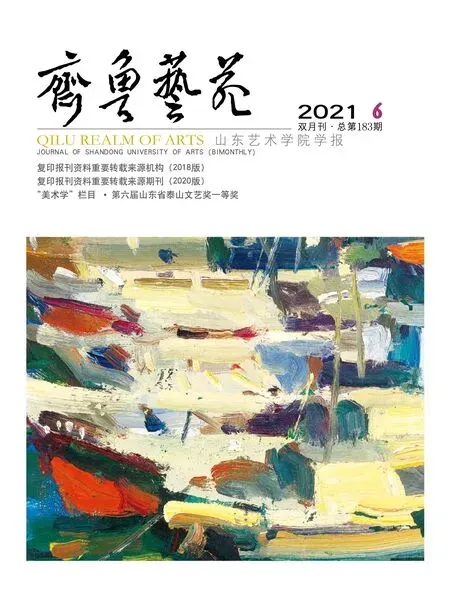中国神话动画电影作品的视觉表达与意义生成
邢祥虎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给国产动画电影打了一剂强心针,并成功“破圈”之后,《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一系列类似作品,相继杀入亿元俱乐部赛道,收割了优异的票房业绩与口碑效应,一次次抬升了国产动画电影创作的天花板,掀起了内地电影市场一波神话题材IP 热。其中《哪吒之魔童降世》累计票房为49.3亿元,登顶2019年度内地电影票房冠军,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票房第二高的单片作品。《姜子牙》累计票房为16.03亿元,成为2020年内地电影票房季军。而这些动画电影作品的豆瓣评分也有上乘表现,最高拿到8.4分,最低也有6.7分,其艺术水准都在及格线之上。
长久以来,国产成人向动画电影一直是内地电影的类型盲区和产品短板,这块类型市场被美国迪士尼、梦工厂、华纳兄弟和日本吉卜力工作室、东映动画等国外电影公司所把持。因此,国产成人向动画电影亟待突围,走出失语状态,亦需要树立起民族动画电影的美学品格。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首的多部动画佳作恰好回应了市场呼声,不仅撬动了成人向动画电影市场,而且还打开了新时代神话题材广阔的创作通道。因此,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国产神话题材动画电影丰富了银幕影像类型,标举了多元化的视觉美学风格,并建构起了吻合时代精神气质的文化症候与传播语境。
一、影像考古:传统文艺造型观念的因袭与挪用
动画电影是与真人电影相对应的一种影片类型,来源于美术片,其制作手法依赖于电脑CG 技术。因此,动画电影是“画”出来,而不是“拍”出来的影视艺术作品。衡量一部动画电影作品艺术品质的关键在于美工设计,也就是人物、场景、道具的概念设计及模型搭建,被统称为动画资产(Asset)。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首的四部动画电影,坚守民族美学立场,积极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艺术智慧和创意灵感,设计开发富有本土审美意蕴的动画资产,带给观众一种国潮体验。这些动画电影有的取材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话故事,有的则取材于《白蛇传》等民间传说,受题材内容影响,其角色设计、场景造型等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中国风格。归纳起来,这四部动画电影的美术设计灵感,大体来源于中国传统典籍、戏曲、出土文物、敦煌壁画等。这些传统艺术元素的加持,深化了动画电影的视觉美学表达深度,也给观众带来了多元审美体验。
首先,中国传统典籍对动画电影美术造型的影响不可忽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外貌造型,虽然与《大闹天宫》的美猴王不尽相同,但其黄棕色毛发、长脸尖下颌、佝偻身躯的模样,基本吻合小说《西游记》的描写:“磕额金睛幌亮,圆头毛脸无腮。咨牙尖嘴性情乖,貌比雷公古怪。”[1](P356)很明显,小说刻画的是半人半猴的形象,有猴性但也通人性。清代《西游记》出现了许多插图绣像版本,如《绣像西游记真诠》《稀世绣像珍藏本:西游记》《新说西游记图像》《彩绘全本西游记》等,这些版本都附有精美的或黑白石印或彩色工笔插图,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孙悟空神通广大、忠正慨然的神情相貌,如图1、图2所示。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动画形象与小说绣像对比来看,二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传统画像的艺术造型观念打破了动画电影的次元壁,深刻影响了孙悟空动画角色的设计与开发,观众最终看到了一个略带桀骜不驯,又有几分侠客精神的“丑猴子”,如图3所示。

图1 《新说西游记图像》

图2 《彩绘全本西游记》

图3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除了孙悟空的形象设计,因袭了传统造型艺术外,化身为玉面书生的反派角色——山妖大王也有迹可循。据该片导演田晓鹏说:“大反派的设计其实是取自《山海经》里对‘混沌’的描述,没有面目、六条腿、很肥胖的身体……完全符合片中的形象。”[2]影片中的山妖大王可以幻化成三种形态:戴帽、散发、肉虫,其中肉虫是他的本来真身。被誉为“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混沌)无面目。”[3](P30)而《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记载了一种异兽——琴虫:“有虫,兽首蛇身,名曰琴虫。”[4](P166)包括《山海经》《神异经》在内的几部富有神话色彩的古老奇书,以其描绘的人神异兽、远古传说等内容,确实为动画电影创作者们提供了想象空间,“《大圣归来》借鉴《西游记》和《山海经》的神仙志怪故事,创造了一个山妖与人类的经典二元对立关系,同时也用 3D 技术造就了一个在故事书中似曾相识过的美好世界与光怪陆离的志怪世界的共存对立。”[5](P161-163)


图4 人面蛇身山神

图5 九尾狐 图6 三首人面山神
《哪吒之魔童降世》有山河社稷图这一桥段,它是太乙真人为培养哪吒成为斩妖除魔的正义之士,而创设的一处修炼仙境,被吸入这幅图的魔童,只好乖乖在此学习昆仑仙术,再也不会逃到外面惹是生非、为害乡邻。山河社稷图的原型来源于《封神演义》,第九十二回“杨戬哪吒收七怪”详细交代了山河社稷图的来龙去脉。此图乃是女娲娘娘所授法宝,助力杨戬降服猴妖袁洪。山河社稷图“如四象变化有无穷之妙,思山即山,思水即水,想前即前,想后即后。”[8](P553)影片将这一幻境奇观予以视觉化呈现,蓝天碧水、五彩植物、苍山劲草、牌坊楼阁,俨然世外桃源。最为震撼的当属片片荷叶托举着的悬浮山景观,哪吒师徒二人乘坐巨大莲花遨游水中世界。导演饺子说:“他的设计概念就是每一片荷叶上都有一个小世界,这个灵感取自于中国的盆景艺术。”[9](P85-87)这样的场景设计,就像中国的山水画,呈现了超以象外的独特意境。
其次,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对动画电影美术造型也有影响。作为大女主,《白蛇:缘起》里的小白造型端庄秀丽、甜美清纯,鸭蛋脸、柳叶弯眉丹凤眼、干枯玫瑰色眼影、粉黛略施、中式复古披肩长发、外加两条细长飘带,极尽女性的灵动与婀娜。白色纱质襦裙,迎风站立,衣袂飘飘,宽大的袖口有如戏曲演员的水袖。通观小白整体的“服化道”美术设计,明显能感觉到她就是戏曲舞台上的青衣附体,如图7所示。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博大精深,舞台效果美轮美奂,《西游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多故事段落都被改编为戏曲曲目,如《闹天宫》《三打》《真假》《金钱豹》《白蛇传》。中国著名美术大师林风眠先生曾创作了数量颇多的戏曲人物画作,其中有几幅画的是《白蛇传》中的人物,如图8所示。林风眠用白描的手法,勾勒了白娘子、小青、许仙三个人物形象,属于典型的仕女类画作,线条流畅饱满,设色淡雅生动,人物神情恬静,具有古典侍女之风韵。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白蛇:缘起》里小白的人设,确实与画笔下的白娘子有几分神似,这也表明动画艺术与戏曲艺术之间的因袭借鉴关系。

图7 《白蛇:缘起》

图8 国画《白蛇传2》
戏曲因素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白蛇:缘起》,也体现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其它几部影片中。在悬空寺一场戏里,山妖大王刚出场时的化妆设计是玉面书生,涂满白色油彩的脸庞是它典型的相貌特征,甫一亮相观众就能快速判断其身份性格——邪恶阴险。这与戏曲艺术化妆脸谱的象征性作用如出一辙。戏曲演员经常用各种颜色的油彩,在脸上勾画出一定的图案,借以表明所扮演角色的性格特征,比如红色代表忠诚勇敢,黑色代表刚正不阿,黄色代表勇猛暴躁,蓝色代表刚强豪爽,白色代表邪恶奸佞,是曹操、潘仁美、严嵩之流。除了扮相所具有的戏曲化特征,影片还通过程式化的舞蹈动作和京腔京韵的唱白,来强化戏曲氛围,山妖大王旋飞高空边舞边唱:“五行山,有寺宇兮,于江畔,而飞檐。”影片把观众似乎带到了戏曲剧院,使其沉浸于“唱念做打”的舞台艺术审美观看之中。与山妖大王一样,《姜子牙》中的九尾狐妖,也以白色脸谱示人。在影片开始的三界大战中,化身王妃妲己的狐妖通体煞白,让人不寒而栗,不由得在心底生发出邪恶、凶险、残暴等视觉感受。而后九尾狐妖被姜子牙的法宝——镇魔宝印降服,而这法宝并非他物,乃是一具白色面罩。被白色面罩封印的九尾虽失去法力,但其魔性不改,仍然是影片的大反派,为姜子牙二次诛妖埋下了伏笔。潘诺夫斯基在早期的电影研究论文中指出,为了让观众准确理解镜头影像的涵义,电影发明了一种风格化的表达方式。“引进一套固定的图像,从外表向观众提供剧情和主要人物的信息,好比皇帝身后的那两个女子,分别手持宝剑和十字架,那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她们代表忠勇和信义。于是,出现了一批可以就其外表、行为和符码化的属性来辨认的典型人物。”[10](P55)根据潘诺夫斯基的研究,动画电影借用戏曲艺术的脸谱化造型方式是“定型态度和定型属性”原则,能够满足观众审美观念的期待视野,与认知概念中的既定图式发生同化。不仅如此,几部动画电影中的其它角色,如蛇母、小青、许宣、江流儿、国师、姜子牙等,人物设计也都有潘诺夫斯基意义上的类型化趋势,包括蛇母吸血鬼般的紫黑色嘴唇、小青美少女战士般的高马尾、许宣仙侠般的装束、国师灭霸般的橡胶头颅、姜子牙耶稣受难般的单薄身躯与风霜蚀刻的蹉跎脸庞、江流儿民间玩偶般的胖头娃娃造型等等。
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十分重视艺术创作活动中的经验价值,认为艺术实践活动中存在某种可套用的“公式”,他称之为图式。“没有一种媒介,没有一个能够加以塑造和矫正的图式,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能模仿现实。我们知道古人把他们的图式看做什么,他们把那些图式叫做准则[canon],即艺术家为构成一个似乎可信的人像不能不知道的那些基本几何关系。”[11](P126)贡布里希进一步以清初传世典籍《芥子园画谱》为例,阐明绘画需要图式的道理,这些图式是完全依赖于前人经验而习得的语汇。动画电影创作也需要图式,事实证明许多导演确实参考了已有的艺术经验与作品。彩条屋影业在制作《姜子牙》时,许多架空时空的场景,都参考了已有的艺术资料,为了呈现归墟、北海、幽都山等场景,团队专门搜集资料了解3500年前的建筑痕迹。《山海经·海内经》描写了幽都山:“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12](P176)影片中的建筑花纹、衣服纹理、道具贴图与材质等各种纹样,也参考了《山海经》。甚至还请了山东临淄的专家去研究姜太公衣冠冢,并邀请专业人士对人物服化道等细节提出建议。此外,《姜子牙》开篇有3分半钟的二维动画,交代封神大战前史,为了创作地道的中国动画,呈现古风效果,主创团队专门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学习壁画艺术,从中吸取创作灵感。《哪吒之魔童降世》里,有一对呆萌可爱的结界兽,其设计原型来源于四川三星堆的青铜文物——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鸟首,导演饺子成功地把出土文物,跨界融合到动画形象之中。
以上创作实践表明,动画电影往往存在一个视觉参考系统,它是一种先在观念,是决定动画形象本质的支架或骨架。但任何艺术活动都不是重复过往,也不是复刻别人,所以图式的作用在于打破图式,在“共相”上建构“殊相”,以美的法则、创新的法则,去支配动画影像创作。正是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首的四部动画电影,因袭与挪用了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并辅以艺术加工与改写,观众才看到了浓郁国漫风的神仙题材动画影片。
二、游观/看进:类型化影像的视知觉心理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像生产方式,实拍电影中的灯光照明、推轨拍摄、摇臂升降、焦点控制等一切笨重庞杂的机械操作,在动画电影那里变成了命令调用、参数设置、菜单选择等鼠标点击动作,电影民工变身为IT码农。软件“画”出了全部镜头影像,视觉表达有了更广阔的创意时空,只有想不到,没有画不到。与真人实拍电影相比,动画电影拥有更加自由的视觉传达手段,影调、色调、镜头运动、摄影角度等视觉语言,拥有无限可能性,可以随意调度,激发出创作者无穷的艺术想象力与表达欲望。面对动画电影影像,观看者被调动起的视知觉心理愈复杂,其观影反应也愈强烈。
从叙事时空转换来看,《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姜子牙》三部影片,涉及了多重时空的变迁,戏仿了公路类型片的叙事惯例,将角色人物的戏剧动作和矛盾冲突,建置于空间位移运动过程之中。《哪吒之魔童降世》则以陈塘关的李府为叙事半径,在相对固定时空内展开剧情,带有家庭伦理情节剧的类型特质。公路片起源于美国,往往以公路/道路为视觉符号,将主人公置于漂泊、流离、行旅状态之中,行走中叙事,叙事中行走,路途上的见闻/遭遇,就是自我认知的告白与陈述。广义公路片的范畴,指涉的是流动叙事空间与建构性思想主题的耦合,“以各种在路上的旅程为主体内容,以道路、旷野、车马和人物移动为影像标志,表现速度与激情、开拓与冒险、逃亡与追逐、爱情与成长以及反抗与救赎诸如此类主题。”[13](P43-47)而家庭伦理情节剧,则是非常古老的电影类型,往往立足于人性道义和伦理纲常,在主人公的人生波折中展开叙事,婚姻爱情、代际亲情、育儿养老、生活琐事、悲欢离合等情感伦常与道德处境,被推向叙事前台,深刻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和理想人格,展现充沛的情感世界,传递惩恶扬善的价值立场。
公路片的影像系统,多以运动镜头为主,强调主观视点的介入,营造“游观”式观影体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场后不久,便用一组运动镜头,交代了法明师父辛勤抚育江流儿的过程。这组镜头多采用横移运镜的方式,横跨春夏秋冬四季,既压缩了叙事时空,又奠定了影像切换节奏的总基调。最后一个镜头定格于苍翠欲滴的层峦叠嶂,一条山野小路蜿蜒伸向远方,路的意象被和盘托出,路途叙事即将开始。首先登场的是“江流儿躲避山妖”桥段,影片调动各种运动方式,构造了“拼命追逐”与“极速逃亡”的剧情模型,身体动作与摄影机动作交织在一起,营造出紧张刺激的视觉体验,影像形式参与到情节内容之中。这种运镜方式爆发力十足,只有动画电影能实现,它不再满足于真人电影里的推拉摇移,而是瞬间运动,急速转接,如果对它进行命名的话,可以称之为“冒险运动”。人物运动和镜头运动轨迹,远远超越简单直线或斜线,而表现为不定向的曲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炮制了超越常规的奇观化影像。而后“冒险运动”屡次被影片使用,譬如“山神大战孙悟空”“孙悟空大战混沌妖王”等片段,镜头时长短、切换快,密不透风,拍摄角度俯仰开合,外加爆炸、烟雾、火光等视效,令人喘不过气来,观影的“本我”情绪,僭越理性“超我”的把关检查而瞬间释放,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快乐原则”被“点燃”,冲动、狂喜、惊奇、自嗨等“非社会化”情绪弥散开来。这表明“冒险运动”不仅是表面的动感,也带有心理和知觉意义,甚至是精神分析无意识的人格属性。
“冒险运动”调动了视线的游观机制。游观也叫动观,是视线追随屏幕内的运动,而不断调整视点的观察技术。游观并非走马观花,而是在散点透视中把握物象、与物神游,将“我”溶入物象之中,使影像沾染上观看者的情感色彩。“动观有助于突现审美主体的实践性,审美活动的主体性、主观性和情感性,也有助于把握审美感知、想象、移情对艺术创造的意义。”[14](P65)美国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认为,运动既可以是实体、纪实的,也可以是风格化、抒情的,但后者无疑更具有“电影化”特征。譬如垂直向上的动作,象征希望、欢愉、权力、权威,反之,垂直向下的动作则象征忧伤、死亡、卑微、沮丧、软弱,纵深上走向摄影机的动作,象征强悍、自信,远离摄影机的动作,象征退缩、软弱、可疑。
《白蛇:缘起》里的“冒险运动”要多一些,体现于“小白大战小道士”“阿宣与小白擎伞飞舞”“白浪滩遇常盘”“小青弑杀阿宣”“小道士大战小白小青”“蛇母大战太阴真君”等几处桥段,这一方面是类型片商业化叙事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影片美学表达的需要。观众在游观体验中,既感受到了正邪双方激烈的对峙,善恶力量的此消彼长,也调动起心理积极性,主动与银幕影像进行深度同化。观众总会站在正面角色的立场上,同情以小白、阿宣为代表的弱者和正义势力,而反抗以太阴真君和蛇母为代表的统治者和邪恶势力,让自己的价值立场,得到想象性解决。“冒险运动”情势越复杂,镜头语言形塑的对峙就越激烈,观众的想象性解决就越彻底。试想如果换用小津式静止镜头,或者长镜头,亦或李屏宾不被觉察的运动镜头,都不可能有效调动起审美张力,也达不到该有的观影效果。与《白蛇:缘起》相比,《姜子牙》里的“冒险运动”要少一些,仅有“姜子牙申公豹大战九尾”“九尾闯归墟”两个段落有复杂的镜头运动,其观影机制也服膺于游观体验,影像上的各种感觉对象,引起了视觉兴趣和视觉好奇。
家庭伦理片的影像系统,偏向于静止镜头对切,景别以中近景见长,剪辑节奏以叙事蒙太奇为主,突出往前和往后的空间深度,观看者的视线,能够长时间驻留于画面某处,形成凝视体验,即“看进”——一种固定视点的观察技术。“看进并未对眼前的对象使用视觉好奇,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视觉经验的修养,在教化的环境中,这种经验把握到了特定的对象。”[15](P188)与游观相比,“看进”依赖影像本身的特殊属性来吸引目光,比如多层景面构成的全景深、多义性的画面主体、有内在趣味的焦点区域等。因此,“看进”钟情于摄影机毫不刻意,甚至会被逐渐忽略的诗意化运动。《哪吒之魔童降世》里有许多“看进”段落,比如“殷夫人分娩”“李靖夫妇见太乙”“海底龙宫敖丙听父命”“哪吒敖丙海边初遇”“李靖求取换命符”等。导演在这些镜头上,并没有安排复杂的场面调度,角色之间建立的是对话关系而不是动作关系,中近景的景别,传递出观众与影像彼此交流的欲望,形成“观众—角色”共同体,角色化身为观众,观众化身为角色。“看进”视线捕捉到哪吒的影像,观众化身为哪吒,在他身上体会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我命由我不由天;捕捉到李靖夫妇的影像,观众化身为夫妇,为人父母的博爱情怀,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替代性满足。这种影像视知觉,已然不是肉体之眼所能把握和控制的,必须传唤观众的特殊的视觉能力——“心灵之眼”(The Mind’s Eye)出场。英国分析美学家沃尔海姆说的很有道理:“‘看进’来源于一种特殊的视觉能力,它所假定的是某物高于抑或超过了‘直截了当’的知觉。”[16](P183)
“看进”和游观互相排斥吗?当然不会。作为发育不充分、崛起较晚的影片类型,中国动画电影,远没有建构起如真人电影般体系严谨、成熟精深、奥义深刻的镜语风格,能被贴上像宫崎骏、押井守、新海诚那样作者导演标签的动画工作者也难觅踪迹。因此,《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四部动画电影并不纯粹,影像风格略有杂糅,有些桥段拼贴了日本动画元素,有些桥段拼贴了美国动画元素,有些桥段拼贴了中国传统线描动画元素。概念风格的游移不定,影响了影片的镜语表达,偏重公路叙事的影片,也有静态场景和固定机位,比如《姜子牙》里的多数镜头,更像是家庭情节剧,观影时“看进”机制占主导地位。偏重家庭伦理叙事的影片,也有“冒险运动”镜头,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遨游山河社稷图”段落,镜头运动犹如过山车般惊险刺激,观影时游观机制,自然就发挥了作用。
三、文化表征:传统IP戏核的现代性改写
与美国动画电影向未来IP取材,习惯“向前看”的创作态度相比,《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国产动画电影向历史IP取材,是一种“向后看”的创作态度。《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取材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白蛇:缘起》取材于中国古代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取材于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向经典大IP取材的好处,在于保证作品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动画电影创作者们站在前人肩膀上,不必担心题材被淹没,最大程度规避票房哑火。但IP越大,改编难度也越大,旧酒不但要装进新瓶子里,还要有点新火试新茶的探索精神,把历史故事巧妙翻新为当代寓言。著名电影艺术家夏衍对电影改编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是相当艰苦的劳动。既然是创造性的劳动和艰苦的劳动,那么,它的工作就不单单在于从一种艺术形式改编成另一种艺术形式。它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但也要力求比原著有所提高,有所革新,有所丰富,力求改编之后拍成的电影比原著更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喜爱,对广大群众有更大的教育意义。”[17](P196-209)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首的四部动画电影,在遵守原作角色名称和人物关系的基础上,大幅度改造甚至颠覆原有人物设定、重新构造剧作故事、架空时空逻辑、重置精神内核、更新人文思想,从各评分平台的数据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改编效果。
从受众定位来看,四部神话题材动画影片,重新定义了动画片的概念,改变了人们对动画片的刻板印象。根据《西游记》等神话故事创作的动画片早已有之,比如《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宝莲灯》等,但这些影片均采取儿童向定位,被视作低幼卡通片,主打合家欢。画风追求喜感、卡通风,情节简单易懂,角色性格扁平化,喜剧性气氛浓厚,没有观影压力。而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首的四部影片,采取成人向定位,情节曲折跌宕、商业化视效、人物心理动机复杂、叙事高概念化、主题思想深刻、观影压力大。典型如《姜子牙》这类影片,其抛出的“救一人与救苍生”这样的复杂主题,远远超出了儿童的理解范围,甚至连成人也无法“破防”。此外,《哪吒之魔童降世》关于正与邪、善与恶的辩证关系,也不是儿童世界的话题,或许只有阅历丰富的成年人,才有足够的智慧来理清个中头绪,并给予完美解释。选择成人向,并非意味着将低幼受众排除在外,事实证明,成人向动画片也有追求合家欢效果的意向。譬如这四部动画片都开发有玩偶角色,《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猪八戒,《白蛇:缘起》里的肚兜,《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结界兽,《姜子牙》里的四不相。作为伴随角色,其功能在于以萌宠造型,俘获孩子的注意力,把他们拉进故事之中,从儿童电影市场分一杯羹。“动画作品既可以是儿童向的,也可以是成人向的,理论上一部动画作品将儿童向与成人向观众一网打尽最为美妙。”[18](P4-16)
成人向的定位必须“文以载道”,以悲剧这种古老的戏剧体裁,来教育引导普罗大众。不可否认,这四部动画电影取材古典文本,场景造型、人物设定、影像风格等方面,皆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痕迹。但影片返本开新,借传统题材之壳,讲述当下故事,直击现代社会群体的心灵,当下人的喜怒哀乐,都能在影像中寻求到寄托与满足。这四部影片都掺杂有悲剧性因素,哪吒被偷换身份、姜子牙被放逐、许宣魂魄消散、江流儿险些丧命。导演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好人蒙难,英雄受辱,制造一出出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剧。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具有净化灵魂的作用:“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此类情感得到疏泄。”[19](P63)怜悯的是不该遭受厄运的人遭受厄运,恐惧的是受难者可能与银幕前正在观影的我们有相似的经历。这是一种特别的快感,它带给观众艺术上的享受和感情上的满足。哪吒为了摆脱“魔童”厄运,一直与以敖丙为首的对立面做不懈斗争,他的遭遇可能就是影院里某些观众生活经历的翻版,哪吒的反抗也鼓舞了观众战胜生活逆境的勇气。姜子牙为了求得事实真相而放弃位高权重的优渥待遇,在别人的不理解中踽踽前行。众声喧哗的当下社会潮流中,我们做的所有事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可,在质疑声中,我们需要自我镇定、自我坚持,多些姜子牙“一根筋”的韧劲。许宣因爱而甘愿变成妖怪,因爱牺牲了生命,他不后悔,因为他相信爱情。犹如工业流水线般高速运转的大都市里,人际疏离、道德解组、个体孤独、理性冷漠,齐美尔称之为“原子化社会”。原子化社会催生原子化生存,大家感慨的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彼此丧失感性温情,就连爱情恐怕也黯然失色。但许宣小白间无功利的纯爱,或许打动了你我,用爱治愈疏离,用爱涂抹生命,用爱对抗沮丧。江流儿不顾弱小身躯,以弱对强,毅然前往悬空寺解救小女孩,他做出决定时是否想到害怕?是否想到死亡?革命战争年代,先烈无惧牺牲,用热血生命涵养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现如今的和平年代,也有风霜雪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也需要英雄主义,也需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我们需要江流儿的精气神,来补信仰之“钙”,永葆不畏前路的时代斗志。四部影片的导演,把悲剧体验感带到观众身边,影像赚取的不是观众哀婉悲伤的泪水,也不是好人没好报的自怨自艾,而是通过剧中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刺激观众,使自己身上潜存的某种优秀品质或正义感得到宣泄,亦或自我反省、吸取教训,培养一种高尚的情操,使人善良。
成人向的定位必须切近成人世界的文化语境,隐喻时代症候,输出成人向的价值观。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首的四部电影,折射了现实世界的热点、痛点,虚拟影像与人生理想形成了互文映射关系。无独有偶,四部电影都采取了创伤叙事,讲述个体觉解、个性解放。孙悟空因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五百年,可以说他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是斗法中的Loser。小白受蛇母派遣刺杀太阴真君,刺杀未果,自己失忆,大脑功能受到伤害。哪吒明明是“灵珠”转世,但阴差阳错被掉包成“魔丸”,与生俱来就带着劣根性。姜子牙被封众神之长,因一时之过被贬下界,幽居北海。四位主人公带着各自的岁月伤痕和心理负担走进观众视线,他们要在观众目光注视下完成自我救赎,进行二次成长。成长既是儿童的权力,也是成年人的权力,比起儿童的生理成长,成年人的心理成长或精神成长,显得更为重要和可贵。因而,成长不应是“青春片”的专利,而是所有叙事影片的母题,如《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触不可及》等。成长意味着祛除迷茫,找回自己,每种成长都不雷同,都值得肯定。《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依靠灵魂导师江流儿的帮助,走出低谷与颓废,及时止损,原力觉醒,再次成长为齐天大圣——神性复位。他的成长轨迹,有点像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因不谙世事而事业受挫,陷入迷茫不能自拔,失败不是堕落的借口,战胜失败才能渡过事业焦虑期。《白蛇:缘起》里的小白,在找回记忆的旅途上,感受到了爱的力量,由妖蜕变为人。她的“治愈式”成长,纾解了现代人焦虑,召唤成长道路上的孤独旅客,敢于回归家庭。《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哪吒,在逆天改命过程中屡屡碰壁,但每一回创伤,都是一次成长,最后他喊出了那句富有解放精神的话“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生活的家庭,缺少父母陪伴,他的成长环境,恰好隐喻了当下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姜子牙》是这四部电影中最为晦涩的,涉及了多重人文主题——众生平等,天下为公;一人与苍生;斩善与除恶。姜子牙的成长是精神性的,具有尼采的“超人”品质。封神大战之后,他自感师尊不公而反抗上天权威和旧有统治秩序,试图构建“人神妖”三界平等的全新价值体系,被放逐人间后也不放弃自我求证,体现出旺盛的生命意志和创造力,在拯救小九的道路上,成长为生活的强者。他或许就是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圣地亚哥,十足的“硬汉”——肉体可以被击垮,但精神永不服输。福柯提出了“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命题——自我如何改造自我:“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到自我的转变,以求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状态。”[20](P49-104)这四部神话题材动画片,用主人公的行动哲学,完美诠释了“自我技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神。
结语
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为首的四部神话题材动画电影作品,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实现了古典文本的现代化视觉转向,与其它题材优秀动画影片一道,共同助推了中国动画电影学派的创新发展。如果把思考视阈再拓宽一下,众多优秀民族风格动画影片的崛起,势必为中国电影学派的成熟壮大而赋能。实践表明,动画电影创作,已然跳出仅聚焦儿童群体的窄众思维窠臼,全龄向产品成为市场主流,越来越多的三口之家、两代甚至三代人,共同走进电影院,同看一部动画影片,这样的观影景观并非天方夜谭。当然某些影片的个别情节与合家欢属性还不适配,折射出电影创作者噱头思维作祟,识变应变能力不足的缺陷。比如《白蛇:缘起》里小白裸露上体与许宣亲热、小白和小青暧昧的“酷儿”倾向。《哪吒之魔童降世》里,哪吒在山河社稷图上撒尿,太乙真人用法术变出一把剪刀,插立在哪吒身前。这样尴尬的桥段,男性观众看了可能会坏笑,但对于女性观众,则显得有些不礼貌、不尊重。但是瑕不掩瑜,有不足说明中国动画电影还未接近天花板,还有提升的潜力。尤其是这四部电影的影像气质、视效呈现、工业化美学品格、艺术表达等方面,已把中国动画电影整体创作水平,从前工业化阶段,带入工业化阶段,借用传奇的神话故事宇宙,安置了现代人的精神诉求,凸显了传统IP 的现代性价值。“对于中国动画创作而言,我们在传承文化基因的同时创造性转化,就是要从过去向现代转化,从神话向科幻转化。”[21](P4-16)时下热映的《白蛇2:青蛇劫起》,将故事时空设定为修罗城幻境,在这个超时空环境里,有机甲、现代建筑、热兵器、末世废土,很显然这是迥异于传统环境的当代场域,传递出追光动画的科幻化转向。因而,包括以神话为题材的广大国产动画电影,在未来的发展中,势必尊重多元化艺术趣味,传递更贴近当代人审美理想的价值观念与人文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