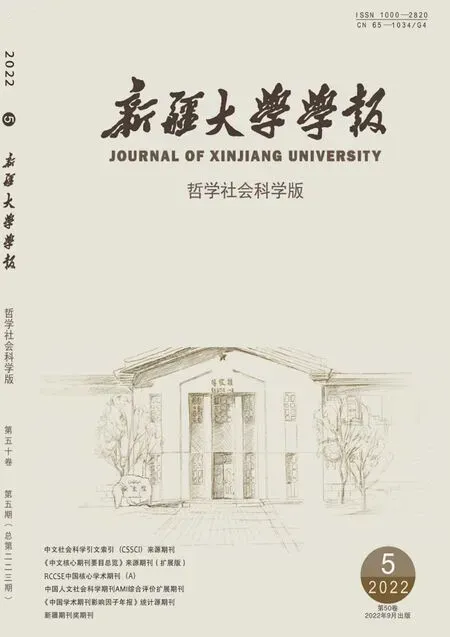唐初(618-639)统治者的西域认知及其经略观*
侯晓晨
(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隋炀帝大业后期,随着国内局势逐渐混乱,浮夸式的西域经略不得不走向末路。继之而兴起的李唐王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不时地与西域地区展开交往。唐代西域经略的研究成果虽然丰厚①唐代西域经略的研究成果,参见林超民《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西部边疆》,《文献》,1986年第3期,第127-141页;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余太山《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王永兴《唐代经营西北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付建河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周德钧《唐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的大战略及启示》,载程喜霖、陈习刚《吐鲁番唐代军事文书研究·研究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李宗俊《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程喜霖《略论唐朝治理西域的战略思想与民族政策》,《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28-41页;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等。,但从认知层面探讨唐初统治者如何一步步走向西域经略,会使一些传统议题焕发出新意。如:唐朝开始经营西域的标志是什么?唐初统治者如何获取西域相关的信息和情报?主要的认知途径有哪些?唐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是怎样的?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探讨贞观十四年(640)以前统治者的西域认知和经略观②“经略” 指 “经营治理” ,词义较 “经营” 丰富。参见祝鸿熹《古汉语常用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67页。本文的 “西域经略观” ,指西域经略的认识、观念和态度,具体指统治者西域经略活动或行为反映出的经略观念。又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平定高昌,建置安西都护府,西域经略意图较此前显著提高,对此后统治者的西域经略影响深远。故本文以该年作为时间节点,而贞观十四年及其以后的西域认知和经略观,限于篇幅,则另文论述。。不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一、唐高祖的西域认知及其经略观
唐高祖与隋文帝在开国局面上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国家尚未统一和北方突厥边患正盛。但就唐初国内割据以及需要结援突厥而言,唐高祖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与险峻。另一个显著的不同,则是唐高祖时期便与传统意义上的西域地区有所往来,不若隋朝至隋炀帝时期才恢复交往。
学者们对唐朝何时开始经营西域有不同的认识。郭锋先生认为唐对西域的经营 “始于贞观四年(630)设伊州之举”[1],作者似是忽略了 “伊州” 与 “西伊州” 的区别。李宗俊先生认为伊吾归唐, “随之唐朝开始了经营西域的大业”[2]。荣新江先生指出贞观六年(632)西伊州改为伊州, “标识着经营西域的开始”[3],刘安志先生也认为贞观六年改名伊州, “开启了唐经营西域的历程”[4]。吴玉贵先生认为唐朝经营西域从贞观十四年(640) “出兵高昌开始”[5],李方先生也认为出兵高昌,唐朝 “开始了对西域的统治和经营”[6]。以上学者所论及的 “经营” ,侧重管理和标志性事件,因而仁者见仁。但从广义上讲,唐朝与西域地区展开官方往来皆可视为经营,因而认为在太宗时期才开始经营西域,未免晚了些。
唐高祖即位之初,即与西域地区取得联系。 “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駃遣使来朝”[7]卷198,5303,记述龟兹国率先与唐朝开始往来,惜两《唐书·龟兹国传》缺乏具体年月。武德二年(619)七月, “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7]卷1,9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唐与西域地区官方来往的事件,不妨将此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开端。
唐朝统治者对西域地区获得的最新的认知,也将通过每一次的使节往来、出兵征伐等方式获取。据统计,唐高祖时期往来的西域诸国或部族主要有:龟兹、西突厥、高昌、罽宾、劫、疏勒、康国、东曹、西曹、安国、石国等,葱岭东西皆有分布。①李锦绣、余太山指出罽宾与劫国武德二年朝献的记载必有一误,参见李锦绣、余太山《〈通典〉西域文献要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0-241页。隋炀帝时期,引致西域,唯罽宾不至②参见刘昫等《旧唐书·罽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9页。文献中关于隋炀帝招致西域不至的记载颇有出入,如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天竺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7页),言 “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 。,而罽宾却在武德二年(619)向唐朝贡。更为引人瞩目的是,武德四年(621)十月, “新罗国、句丽及西域二十二国,并遣使朝贡”[8]卷970,11227。是什么原因导致唐高祖在开国初年即取得接近隋炀帝时期的西域外交成就?
就国内形势而言,武德三年(620)前半年秦王击败刘武周势力,七月开始征讨王世充。武德四年(621)五月,唐军有虎牢之胜,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两大势力相继平定。七月, “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给复一年”[9]卷189,6035。九月,李孝恭、李靖等开始征讨萧铣,次月平定。同时期的北方形势,颉利可汗于武德三年(620)继处罗可汗之后, “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7]卷194上,5155。武德四年(621)三月,突厥寇汾阴、石州,四月,颉利可汗寇雁门、并州。八月,突厥寇代州,经交战唐军失败。九月,突厥又寇并州、原州,唐朝遣将窦琮, “尉迟敬德等击之”[9]卷189,6019-6041。可见该年唐高祖国内统一的进程是相对顺利的,但与北边突厥的关系却相对恶劣,频繁交战。
此时西域的形势,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一方面继承了其兄射匮可汗的政治遗产,一方面自身又 “勇而有谋,善攻战”[10]卷199,5436,是当时的西域霸主。西突厥虽统治西域,却并未对唐朝构成边患,相反,其与唐朝的关系相对友好,明显的表象之一即是已经连续三年向唐高祖朝献。
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大军当发,颉利可汗闻之大惧,复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10]卷199,5436
引文所言 “时北突厥作患” ,与上文所揭示的唐与北边突厥关系相对恶劣一致,而西突厥与唐朝的持续往来,促使唐高祖对其 “厚加抚结” ,共同对抗北突厥,为此统叶护可汗相约在 “五年冬” 发起进攻。虽然这场军事结盟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反映出唐高祖与统叶护存在友好合作的基础。由此,有理由推论武德四年(621)西域二十二国的朝贡事件是得到统叶护许可的,其原因主要在西突厥方面。
此外,史称杨恭仁 “深悉羌胡情伪,推心驭下,人吏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7]卷62,2382,其任职凉州总管在 “武德三年(620)至六年”[11]。又其墓志言 “王化伊始,西域未宾,授公河西道安抚大使”[12]。此时凉州已平, “西域未宾” 或指西域诸国未曾宾服,若推论不误,则西域二十二国的遣使朝贡也可能与杨恭仁的招抚有关。
唐高祖与统叶护的交好伴随着整个武德时期,除了朝贡方面,还体现在双方和亲的努力上。文献记载了两次西突厥请婚:第一次,武德五年(622), “叶护可汗遣使请婚”[8]卷978,11325;第二次,武德八年(625)四月。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上谓裴矩曰: “西突厥道远,缓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 对曰: “今北狄方强,为国家今日计,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 上从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喜。[9]卷191,6107
此次西突厥请婚,《通典》、两《唐书·突厥传下》皆记载是封德彝提出的远交近攻之策,《资治通鉴》记载是裴矩提出的,胡三省注引《考异》言 “今从《实录》” ,表明实录记载的就是裴矩。《册府元龟》记述此事时,言 “于是叶护请婚,帝谓侍中裴矩曰”[8]卷978,11325,这与裴矩武德八年(625)年任职侍中吻合①参见刘昫等《旧唐书·裴矩传》, “八年,兼检校侍中”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08页。但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高祖纪》《新唐书·宰相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页、1629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106页),皆系于武德七年十二月,再依据裴矩武德八年十一月罢为黄门侍郎,则建策和亲时为侍中不误。,再依据《册府元龟》多 “直接移录原始史料”[13]的特点,似可以确定当是裴矩提出②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已经指出诸书记载出入,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原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9页)。另参见薛宗正《伊吾归唐与伊州创置》,载达力扎布《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两《唐书》或是沿袭《通典》的记载。导致杜佑记载出入的原因,可能和封德彝同样向唐高祖提出过唐与北突厥和亲的建策有关,两者行文多有相似。③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封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97页),言 “会突厥寇太原,复遣使来请和亲,高祖问群臣:‘和之与战,策将安出?’多言战则怨深,不如先和。(封)伦曰:‘突厥凭凌,有轻中国之意,必谓兵弱而不能战。如臣计者,莫若悉众以击之,其势必捷,胜而后和,恩威兼著。若今岁不战,明年必当复来,臣以击之为便。’高祖从之” 。
唐高祖原本认为 “西突厥道远,缓急不能相助” ,最终还是采纳了裴矩 “远交近攻” 的建策。该建策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隋文帝时期的长孙晟,其核心要义都是结交 “西突厥” ,以达到威胁北突厥的目的,原因都在于当时北突厥势力强盛,所谓 “今北寇方强” 。唐高祖遣高平王李道立作为和亲使节抵达西突厥时,史言 “统叶护大喜” ,表明统叶护认为与唐朝的和亲也是利己的。然而由于颉利的入寇,西蕃路梗,和亲未果。
事实上,唐高祖与四夷的和亲思想,早在武德二年(619)闰二月时已经有所透露。
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渠搜即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译,美周邦之长算。有隋季世黩武耀兵,万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殚。朕祗膺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其吐谷浑已修职贡,高句丽远送诚款,契丹、靺鞨咸求内附,因而镇抚允合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8]卷170,1890-1891
引文主要表达四方面含义:其一,记述自古以来夷夏的地理分布、文化差异以及先王边疆治理的典范;其二,反思批判隋炀帝的四夷策略;其三,提出悦近来远、 “要荒藩服,宜与和亲” 的策略;其四,结合吐谷浑、高句丽、契丹等的外交情况,使人 “就申好睦,静乱息民” 。针对引文的意义,学者熊德基、骆桂花皆指出该诏书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唐代民族政策的基础,周伟洲先生也分析了诏书思想的理论渊源。④参见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第35页;骆桂花《唐朝制定民族政策的历史原因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第35页;周伟洲《唐太宗的民族观》,载《西北民族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00-501页。
简言之,唐高祖与统叶护可汗通好、军事结盟、和亲等系列举措,清晰地反映出唐高祖联合西突厥抵御北突厥的战略认知。在国内尚未统一、北方边患未宁的形势下,与西突厥的交好不仅可以缓解北方边患,同时取得了与统叶护统治下的西域诸国的交往,可谓一举两得。唐高祖时期对西域诸国的最新认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获取的,这也成为隋唐王朝第一代君主西域认知的重要差异。
二、贞观元年至六年唐太宗的西域认知及其经略观
唐太宗继位后,面临新的西北形势。隋炀帝继位前后,西突厥、北突厥皆有动乱,以此为契机,隋炀帝与传统西域地区重新取得联系。不仅如此,北方边患因始毕可汗的归附与达头可汗的兵败,在隋文帝后期已得到初步的解决。因此,隋炀帝即位后没有显著的西北边患。唐太宗则不同,自隋末唐初以来北方突厥边患仍然延续。如武德九年(626)七月, “颉利又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10]卷197,5392。但是北方形势的转机很快到来。贞观元年(627),阴山以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相率背叛突厥,继而突利可汗因讨击失败与颉利可汗产生矛盾,又其国适逢遭受雪灾。这种种变化,唐朝内部逐渐出现了反击突厥的呼声。直到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君臣平定颉利可汗,北方突厥边患得到较为彻底地解决。与此大约同时,西突厥因统叶护可汗的去世,内部连兵不息,莫贺咄可汗、肆叶护可汗各遣使来朝、请婚,太宗皆不许。西突厥的内乱,不仅导致原先隶属于统叶护的西域诸国等叛离,其自身也 “国内虚耗”[10]卷199,5437。
新的西北形势下,唐太宗与西域地区的互动较唐高祖时期更为频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域认知也更为清晰和多彩。
贞观元年至六年期间,与唐朝往来的西域诸国或部族主要有:西突厥、高昌、何国、康国、帆延、伊吾、龟兹、焉耆、于阗、多弥、安国、东安国等,葱岭东西皆有分布。其中,西突厥和高昌延续了唐高祖时期和唐朝交往的热度。
贞观元年,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时统叶护自负强盛,无恩于国,部落咸怨,葛罗禄种多叛之。颉利可汗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 “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 统叶护患之,未克婚……[10]卷199,5436
统叶护可汗欲再次和亲,却仍然因受到北突厥颉利可汗的阻挠而未果。西突厥和亲使节当中的 “道立” ,正是武德八年(625)四月唐高祖派往的高平王李道立。可见李道立在西突厥滞留近两年,他的归唐虽然没有完成和亲任务,但必定如北周末长孙晟出使突厥一样,带回来大量真实的西突厥内部信息情报。
此时期高昌王更是亲自入唐朝贡。
太宗嗣位,复贡玄狐裘,因赐其妻宇文氏花钿一具。宇文氏复贡玉盘。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贞观四年冬,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7]卷198,5294
据引文,唐太宗继位初,高昌即遣使朝献,麴文泰夫妇与唐太宗互动频繁,不仅礼尚往来,宇文氏也获得赐姓与赐封,转身成为李唐公主。重要的是,麴文泰随时向唐朝汇报西域诸国的动静,俨然成为唐太宗在西域地区的 “情报收集和传递员” 。换言之,凭借李道立与麴文泰的角色作用,唐太宗对西突厥、高昌乃至西域诸国,可以获得相对直接、快捷的西域认知信息。
该时期内关涉唐太宗西域认知的一件大事是张弼出使西域。①张弼墓志的研究,参见胡明曌《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的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文物》,2011年第2期,第70-74页;孟宪实《论玄武门事变后对东宫旧部的政策——从〈张弼墓志〉谈起》,荣新江《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9-220页;谢国剑《唐〈张弼墓志〉释文校补——与胡明曌先生商榷》,《韶关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第94-96页;舒韶雄《唐张弼墓志文字再补》,《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65-66页;吴继刚《唐〈张弼墓志〉释文校正》,《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101-104页;王素《唐麴建泰墓志与高昌 “义和政变” 家族——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二》,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7-164页;荣新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13-118页;等。贞观之始……于时獯丑未宁,边烽屡照,太宗临轩,有怀定远,召公将命,追美凿空。具禀圣规,乘轺迥骛。历骋卅国,经途四万里。料地形之险易,觇兵力之雌雄。使返奏闻,深简帝念。加阶赐帛,宠命甚优。六年……②参见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〇二《张弼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4-227页,另参见前引谢国剑、舒韶雄等学者的补校成果。
针对墓志释文蕴含的唐初与西域诸国关系的意义,胡明曌、王素、荣新江等先生已有阐述,本文略有补充。
其一,王素先生在认定张公瑾贞观元年(627)提出 “突厥可取六状” 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这解开了唐太宗关于东突厥的心结,于是就遣使张弼西域调研,并推测出使时间在贞观元年(627),是 “随同高昌使者返程去西域的”[14]。依据史事,这种推论其实是非必要的,因为作者的立论基础便出现错误。试看以下记载:
贞观元年,(张公瑾)拜代州都督,上表请置屯田以省转运,又前后言时政得失十余事,并见纳用。后遣李靖经略突厥,以公谨为副,公谨因言突厥可取之状,曰……[7]卷68,2507
贞观初,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馈运。数言时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纳。后副李靖经略突厥,条可取状于帝曰……[15]卷89,3756
(贞观)三年,转兵部尚书。突厥诸部离叛,朝廷将图进取,以(李)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以逼之。①参见刘昫等《旧唐书·李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79页。又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李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14页)叙事与旧本传同,但为 “定襄道行军总管” 。两《唐书·突厥传上》记载恶阳岭之战,皆为贞观四年正月。据下引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178-6179页),李靖分别在贞观三年八月、十一月两次受命击突厥。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9页),认为八月属经略,十一月属新命。以上记载虽个别细节上有出入,但李靖出兵突厥自贞观三年开始则是一致的。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丁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以张公谨为副。[9]卷193,6177-6178
据前两段引文,两《唐书》在叙述张公瑾言 “突厥可取六状” 时皆与李靖经略突厥、张公瑾为副一同叙述,而据后两段引文,李靖出击突厥自贞观三年(629)八月始,故张公瑾言 “突厥可取六状” 也应是贞观三年(629)八月左右之事(《资治通鉴》系于三年八月条)。如此,王氏之后的推论不足为据。
其二,对志文中的 “有怀定远” “召公将命” 的理解,王素先生强调了古人用典,认为 “定远” 与班超有关,这有一定道理,但作者进一步认为唐太宗想专门对付西突厥,或显得突兀。据前文对唐高祖以来唐与西突厥关系的分析,西突厥的朝贡、和亲等举措,显示两者的关系较为融洽,且具有战略合作的动机与实践,并不是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而唐太宗继位后也仍然保持交往热度。因此,并不能认为张弼出使具有 “对付” 西突厥的意图。如是,笔者认同吴玉贵先生关于唐初与西突厥关系的分析,即 “不偏不倚,中立观望”[16]293。又王素先生认为 “召公” 指河间王李孝恭,进而认为张弼的出使是唐太宗与李孝恭共同商议决定的。笔者以为这同样是非必要的推论。且不说李孝恭任职过凉州都督、礼部尚书与经略西域关系并不紧密, “召公” 也并非指李孝恭。 “召” 指 “召见”[17]493, “公” 指张弼, “将” 指 “用”[17]181, “命” 指 “命令”[17]266,合起来可试译为唐太宗召见张弼用以出使。王氏的释义或稍显迂回。
其三,荣新江先生通过梳理隋炀帝时期对西域诸国的了解情况,推论《隋书·西域传》所记载的 “二十国” 就是唐初的了解情况, “也是张弼出使西域之前所知道的国家”[18]。作者的推论,显然是忽略了前揭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已经有西域二十二国遣使朝贡的记载。可见,张弼出使前所知西域国家必不限于在其出使后的贞观十年(636)成书的《隋书·西域传》所记载的国家。又荣新江先生依据张弼出使的行程 “四万里” ,结合太宗初年西域诸国朝贡的记载,推论其出使过的国家有:西突厥、高昌、龟兹、于阗、康国、焉耆等。作者的这种比附与联系从结果而言大致是不误的,但笔者想强调,西突厥、龟兹、康国等自唐高祖时期已有入朝的记载,这些国家在唐太宗初年入朝,未必是张弼出使的推动,与具有前期的外交基础、平定北突厥及 “天可汗” 的感召力等因素也有关系。
以上对志文的零星讨论,有助于丰富张弼出使西域的相关史事。 “历骋卅国,经途四万里” 的出使经历是唐开国以来首次重大的西域外交盛事, “料地形之险易,觇兵力之雌雄” 的出使成绩不仅丰富了唐太宗当时的西域认知,无形中也为太宗之后的西域经略活动提供了地理、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情报基础。
随着唐太宗对西域地区认知的增多,也逐渐参与到具体的西域经略事务中。贞观五年(631)康国请归附,被唐太宗拒绝。
太宗谓侍臣曰: “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人甚困。假令于身有益,于百姓有损,朕必不为,况求虚名而损百姓乎!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救。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人?若劳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19]
引文所言广土地、求虚名、劳民的 “前代帝王” ,举近者言之,隋炀帝即是代表。因此,唐太宗从百姓利益出发,拒绝纳康国为属国的虚名。唐太宗同时提出假如康国有难,宗主国尚需附远营救,这样实属劳民伤财。唐太宗提及的 “兵行万里” ,此处 “万里” 乍看似是修辞,形容距离远,实则不然。依据葱岭周边国家距离长安的里程加以类比,则 “万里” 大致相当。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康国附石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6页),言石国距京师九千里,石国西南五百里即康国,则康国距京师九千五百里。康国自唐高祖以来已经数次遣使入唐,唐太宗所言当是建立在其对康国方位、里程认知的基础上提出的。
虽然拒绝康国的內属,但唐太宗还是提倡展开与西域地区交往的。
时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纥干往迎接之。[7]卷71,2548
高昌国,贞观中太宗遣折冲都尉、直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使西域,焉耆王突骑支因遣使朝贡,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8]卷1000,11572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初,焉耆入中国由碛路,隋末闭塞,道由高昌。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上许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9]卷194,6208-6209
据引文,贞观四年(630),西域诸国欲通过高昌王麴文泰入朝的时机一并遣使贡献,唐太宗本已同意,但因魏徵的谏言而终止。第二段引文是第一阶段内唐太宗的又一次西域遣使事件,时间不详,但根据下半句与第三段引文所述焉耆王朝贡并请复开大碛形成的前后联系,则应在贞观六年(632)七月前。焉耆王遣使朝贡,所言开道路、 “便行李” ,具有明显的经济交往需求,①朝贡与贸易的关系,参见王尚达《唐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贡赐贸易管窥》,《社科纵横》,1994年第2期,第64-66页;周伟洲《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59页;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第41-42页;管彦波《论唐代内地与边疆的 “互市” 和 “朝贡” 贸易》,《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第86-87页;孟宪实《大唐 “朝贡” 外交的真相》,《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第78-80页;等。唐太宗答应了焉耆的要求,却也因此导致高昌与焉耆再次交恶。②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言焉耆 “先被高昌寇扰,有恨不给马焉” 。可见高昌与焉耆交恶已久,并非仅因为开通大碛路,故此处用 “再次交恶” 。贞观六年(632),焉耆遣使言状——遭遇西突厥与高昌的袭击。唐太宗据此意识到西突厥的内乱以及高昌与西突厥反叛势力的关系。
唐太宗与安国使节的对话,更能体现出其对经济贸易的重视。
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 “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 诸胡大悦。[15]卷221下,6244
咄陆可汗者,亦称大度可汗。父莫贺设,本隶统叶护。武德中,尝至京师。时太宗居藩,务加怀辑,与之结盟为兄弟。既被推为可汗,遣使诣阙请降,太宗赐以名号及鼓纛。贞观七年,遣鸿胪寺少卿刘善因至其国,册授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10]卷199,5437
安国使节献方物的时间,前半句仅言 “贞观初” ,据后半句唐太宗所言 “西突厥已降” ,当指引文第二段西突厥咄陆可汗泥熟的归附,在贞观六年(632)左右。西突厥内乱及肆叶护可汗卒后,国人于焉耆迎泥熟而立之。泥熟在武德时期便与唐太宗结盟为兄弟,在其被拥立后,遣使诣阙请降,而唐太宗则遣刘善因至其国册封为咄陆可汗。③关于刘善因册封泥熟的时间,刘昫等《旧唐书·突厥传下》,言贞观七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3页)。杜佑《通典》,言贞观七年(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437页)。司马光《资治通鉴》,言贞观六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209页)。或为出发时间与到达时间的差异,参见吴玉贵《阿史那弥射考》,《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第64-70页。由于西突厥势力的减退,其原先控制的西域诸国此时叛离,唐太宗所言 “商旅可行” 表明中西贸易之路不仅畅通,而且获得安全保障。
自击败北突厥颉利可汗,唐太宗被西北诸蕃尊为 “天可汗” ,唐太宗 “四夷俱服” 的政治理想逐渐燃起。
谓侍臣曰: “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9]卷193,6203
据引文,唐太宗与群臣探讨治国理念,其所言 “中国幸安,四夷俱服” ,前者侧重内政,后者侧重外交,体现出唐太宗对中国古代 “华夷一统” 思想的继承。④中国古代华夷思想的研究,参见黄纯艳《论华夷一统思想的形成》,《思想战线》,1995年第2期,第45-50页;彭建英《论我国古代民族观的演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56-62页;何芳川《 “华夷秩序” 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0-45页;薛小荣《华夷秩序与中国古代国防》,《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第140-145页;等。
此外,贞观四年(630),唐太宗首次在西域地区置州。
大唐贞观四年,以颉利破灭,遂举其属七城来降,因列其地为西伊州,同于编户。[10]卷191,5186
伊吾的归附,显然是受到北突厥败亡的影响。唐太宗以其地置西伊州,实行编户制度,之后改为伊州。伊吾作为西域地区的东部 “咽喉” 之一,又是 “商胡杂居”[10]卷191,5185之地,唐朝的掌控,驱除了北突厥势力对该地的干涉,便利了唐朝与西域地区政治、经贸的往来。
简言之,在唐太宗继位至贞观六年(632)期间,不仅有西域诸国的遣使朝贡,也有张弼、揖怛然的出使西域,这些互动成为唐太宗获取西域认知的重要来源。在西域经略方面,从支持通商、册封西突厥泥熟、建置西伊州等事例来看,此时唐太宗对西域事务的参与度逐渐加深,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使节往来形式。如吴玉贵先生所言,唐朝对西域的态度由消极转向积极。①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2页。另参见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认为贞观六年唐朝势力正式介入西域,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34页。
三、贞观七年至十三年唐太宗的西域认知及其经略观
贞观七年至十三年期间,与唐朝往来的西域诸国或部族主要有:西突厥、龟兹、高昌、女国、石国、于阗、焉耆、康国、喝盘陀、疏勒、吐火罗、朱俱波、处月、罽宾、天竺、波斯、安国等,葱岭东西皆有分布。其中,与西突厥的交往仍然最为频繁。
继刘善因之后,唐太宗于贞观八年(634)遣使册立西突厥可汗。
时西突厥国乱,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领左右胄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立咥利失可汗。[7]卷198,5301
(韦)机,贞观中为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设为可汗。会石国反叛,路绝,三年不得归。机裂裳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名为《西征记》。及还,太宗问蕃中事,机因奏所撰书。太宗大悦,擢拜朝散大夫……[7]卷185上,4795
据引文,韦弘机即韦机, “西突厥国乱” 或指泥熟去世。唐太宗遣韦弘机与桑孝彦同往西突厥册立咥利失可汗。由于石国的反叛,韦弘机滞留西域三年,成书《西征记》,记述西域诸国风俗物产。返唐以后,奏书于唐太宗。 “太宗大悦” 的原因之一或是获得了西域诸国的最新信息。
关于册立咥利失可汗,有一点需要补充。《册府元龟》记载贞观 “六年……是年,遣中郎将桑孝彦册立焉耆国王突骑支为咥利失可汗”[8]卷964,11167。与前引相较,不仅时间有误,而且张冠李戴,误将册立同俄设视为册立焉耆王突骑支。可见,《册府元龟》该记载不足为信。
该阶段内西域诸国朝贡相对频繁,唐太宗则较少遣使西域。贞观十一年(637),罽宾遣使献马,唐太宗 “嘉其诚款”[7]卷198,5309,并遣使至罽宾、天竺。同时,唐太宗谈及中夏与四夷的关系,隐含着 “四夷来献” 的政治理想。
贞观中献名马,太宗诏大臣曰: “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徵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长皆来献,此徵力也。” 遣果毅何处罗拔等厚赍赐其国,并抚尉天竺。[15]卷221上,6241
引文所言今天下安、四夷君长来献,是符合当时情形的。唐太宗可以说践行着 “安中夏” 的治国方略。即使贞观九年(635)征伐吐谷浑,也是因其入寇河西、拘留唐使、不顾蕃礼,出于维护河陇安定的需要。虽然这次征讨唐朝的军队首次进入西域地区,但这与西域经略并无直接关系。
该阶段内,唐太宗 “四夷俱服” 的政治理想得到进一步地升华。
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 “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帝奉觞上寿曰: “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9]卷194,6216
贞观七年(633),唐高祖喜见胡越一家,唐太宗祝酒,言 “四夷入臣” ,表现出当时中国与四夷关系的稳定以及唐朝在华夷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贞观十年(636),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唐太宗言: “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无惧。”[9]卷194,6235同样透露出自己 “内安外服” 的政治理想。
除了册封西突厥可汗、与西域诸国使节往来,该时期唐太宗尚没有表现出对西域更多地关注。但随着西域地区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力的兴盛,唐太宗不可避免地参与到西域的局部战争中,由此对西域认知的获取也更为直接和频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事件中。
其一,高昌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力发动对伊州的袭击。
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麴)文泰后稍壅绝之。伊吾先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又与叶护连结,将击伊吾。太宗以其反覆,下书切让,征其大臣冠军阿史那矩入朝,将与议事。文泰竟不遣,乃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7]卷198,5294
学界针对此次高昌与突厥袭击伊吾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分歧。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认为叶护指 “西突厥统叶护”[20]。王素先生质疑《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贞观十三年(639)二月,认为应在贞观六年(632)前,并且指出叶护 “属东突厥阿史那社尔属下”[21],刘子凡先生也认为是 “阿史那社尔的部下”[22]。姜伯勤先生认为叶护指西突厥 “乙毗咄陆可汗所派遣”[23]。吴玉贵先生认为袭击伊吾在贞观十二、三年之间,叶护指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部下 “阿史那步真”[16]323。孟宪实先生认为袭击伊吾在 “贞观十年(636)左右”[24],也认为叶护指西突厥欲谷设部下。
可以看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袭击伊吾的时间。下文将要讨论的高昌与西突厥处月、处密部袭击焉耆的时间,两《唐书·焉耆国传》《资治通鉴》皆言在 “贞观十二年” ,而《通鉴》贞观十三年二月也提及,可见《通鉴》此处显然属于征伐高昌之前对高昌进行追溯性质的叙事。如此,贞观十三年不能视为袭击伊吾的时间,且必然在第二次袭击焉耆之前。此外,《新唐书》记载此事时言 “久之,文泰与西突厥通”[15]卷221上,6221,似是表明袭击伊吾是在高昌与西突厥欲谷设联合以后。又贞观九年(635),北突厥余部阿史那社尔由高昌率众归唐。此后高昌才有可能与西突厥欲谷设联合。因此,笔者以为袭击伊吾的时间当在贞观九年至十二年之间。
伊州被袭击,直接威胁到唐朝的西境安全。唐太宗获知伊州军情的途径,当是通过伊州刺史奏报的,于是下书切让高昌,并征其大臣阿史那矩入朝议事,欲掌握更多的西域信息。但是,麴文泰没有按照要求派遣,而是遣长史麹雍前来谢罪。尽管如此,唐太宗依然可凭借麹雍的汇报,了解高昌、伊吾以及西突厥内部等相关情况。
其二,高昌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势力发动对焉耆的袭击。
十二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7]卷198,5301-5302
又寻与西突厥乙毗设击破焉耆三城,虏其男女而去。焉耆王上表诉之,太宗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其状。[7]卷198,5294
岑仲勉、吴玉贵已经指出两段引文所指为同一事①参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3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2-304页。,兹不赘述。唐太宗获知焉耆被袭的消息,显然是由于焉耆王的 “上表” ,为详细掌握事件来龙去脉,又遣使李道裕前往焉耆。
四、结 语
唐朝建立以后,不久即与西域地区展开交往,并且在武德四年(621)迎来西域二十二国朝献的外交盛况。唐高祖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友好关系的开展,有利于唐朝与西域诸国进行交通往来,双方军事结盟、政治和亲的战略与实践,也有助于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北突厥,缓解唐朝的北境边患,可谓一举两得。
唐太宗并非一开始就有着西域经略的蓝图,而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渐参与西域经略事务的。使节往来、建置伊州、开辟通商道路,无不体现出唐太宗积极的西域经略观。贞观四年(630)北突厥的败亡,唐太宗开始燃起 “四夷俱服” 的政治理想,并且日渐升华,成为其日后四夷经略的思想和理论渊源。张弼出使西域是贞观初年唐太宗西域经略的一件大事,由此唐朝获得了大量的西域地理、军事等相关信息与情报。贞观前期,唐太宗密切关注着西突厥形势的变化,并且选择扶植泥熟系可汗。唐太宗或许深知西突厥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在西域依然有着相当的统治基础,若想进一步经略西域,西突厥是最大的阻碍。
高昌一度是唐朝在西域地区的 “情报收集和传递员” ,贞观中期以后却逐渐走向唐朝的对立面。西域地区发生的两次局部战争,虽与长安相隔遥远,但唐太宗或是征高昌大臣入朝,或是遣使调查,表现出对西部边疆安全的重视。唐朝与高昌此时积怨已深,两国关系的走向,仍然取决于各自统治者的态度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