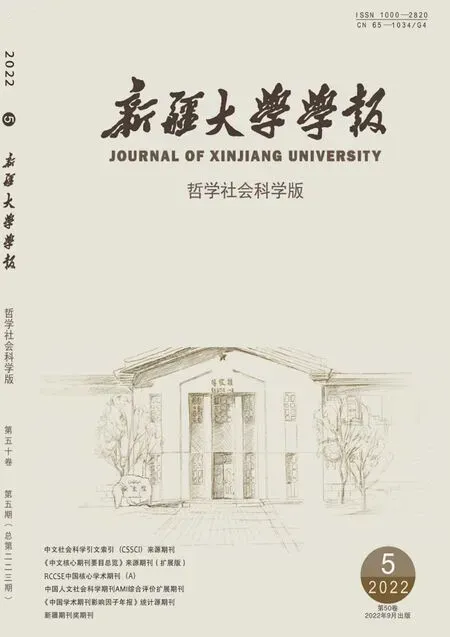告别实质真实?
——对德国刑事协商的制度考察*
李章仙
(中国政法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88)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冲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实质真实在德国刑事程序中仍具有无可减损的重要性,而并非国内某些论者所断言的那样,实质真实已经妥协,或者实质真实已经被刑事协商架空、流于形式。②参见王瑞剑《实质真实主义的妥协——德国刑事协商制度的理论考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56页。无论是德国立法、理论研究还是联邦宪法法院的判解,都一直致力于调和二者间的矛盾冲突。调和的思路便是在坚守实质真实、职权查明等传统刑事法基础原则的前提下,如何审慎地兼顾诉讼效率,规制刑事协商的实践乱象。本文的写作,源于对这种 “权衡之道” 的考察,力图梳理、解读和探讨刑事协商的德国经验,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样本。
二、刑事协商的制度形塑
(一)刑事协商的用语变迁
自20世纪70年代起,刑事协商就以 “潜规则” 的形式在德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初露端倪。③刑事协商一开始是频繁出现在经济犯罪和麻醉药品犯罪的办案实践中,而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展到几乎所有犯罪类型。Vgl.Altenhein/Hagemeier/Heimerl/Stammen,Die Praxis der Absprache in Wirtschaftsstrafverfahren,Nomos,2007,S.20f.但对于应当用哪一个词语来准确地指称这一现象,理论上仍然含混不清。2009年以前,诸如 “交易” (Deal)、 “ 约 定 ” (Absprache)、 “ 协 商 ” (Verständigung)、 “协议” (Vereinbarung)等提法均有出现。2009年,德国联邦议院在立法过程中尝试着对这种 “对话” 的规范性基础和结果寻找合适的表述方式。最终,立法者有意识地选择了 “协商” 这一表述,因为其它的用语都容易让人们产生这样一种不良的印象,即判决似乎是根据 “有合同约束力的条款”①原文为 “quasi vertraglich bindende Vereinbarung” 。具体内容可参见德国联邦议会2009年3月18日所发布的立法意见稿: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gelung der Verständigung im Strafverfahren,BT-Drucks.16/12310,S.8。而形成的。然而,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即便立法者在现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7条c中,明确规定了法官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 “协商” ,但在大多数德国刑事法学者的著述中,更多使用的仍然是 “约定” 一词。他们将 “约定” 作为立法所规定的这种 “协商” 的上位概念(Oberbegriff),用以指称所有让刑事程序得到和睦解决的诉讼形式。因为除了法律所规定的这种 “正式” 协商外,还存在着各种 “非正式” 的程序协商。②例如,检察官和被诉人基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的规定,形成合意后会产生程序停止(Einstellung)。
在中文翻译中,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7条c中表示协商的 “Verständigung” 一词,译者们多用判决协商、刑事协商或者认罪协商来表示,实际上为同义。故本文也不作区分。
(二)刑事协商的制度发展
刑事协商在德国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被德国刑事司法逐步接受和认可的过程。文献层面,一般认为,对刑事协商的探讨最早出现在1982年发表的《刑事诉讼中的协议》③Vgl.Werner Schmidt-Hieber,Vereinbarungen im Strafverfahren,Neue Juristische Wochenschrift 1982,1017ff.和《刑事程序中的和解》④Vgl.Detlef Deal,Der strafprozessuale Vergleich,Strafverteidiger 1982,545ff.两篇文章中。一直到1997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审判第四法庭才在一个基础性判决中,让刑事协商这一 “潜规则” 显性化,并对其诉讼实践施加了明确的法律界限。⑤Vgl.BGH,Urteil vom 28.08.1997-4 StR 240/97,BGHSt 43,195.第四审判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以合意终止程序为目标所进行的 “对话” ,基本上是不违法的,但是否允许这种协商,还要根据一系列的内容和程序条件作判断。该项判决的中心观点在于:第一,原则上,判决协商必须在公开的审判程序中进行。若关于协商的 “对话” 发生在正式的审判程序之外,也必须在正式审判程序中公开提出。第二,刑事协商只有在所有诉讼参与方知晓(Kenntnis)并参加(Beteiligung)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同时,不能损害《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中所规定的被告人的自由意志决定权(freie Willensentscheidung),遵守不强迫自证己罪原则。第三,法庭必须按照《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的规定,基于整个审判程序得出对案件的认知,并在被告人作出可信认罪自白的情况下,允诺其一个刑罚的上限,但并非一个具体的量刑结果。第四,在任何案件中,刑罚都必须与被告人的实质罪责相适应,在刑事协商中也不例外。同时,有罪判决本身不能成为刑事协商的对象。第五,法庭不允许让被告人承诺放弃上诉的权利。⑥Vgl.BGH,Urteil vom 28.08.1997-4 StR 240/97,BGHSt 43,195,204-206.
而后,2005年3月3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庭通过一项裁决,基本上确立了第四法庭所提出的上述指导原则,同时对这些原则作出进一步发展。⑦Vgl.BGH,Beschluss vom 03.03.2005-GSSt 104,BGHSt 50,40.在决定的结论部分,大法庭强烈地主张,要说服立法者对判决协商的合法性、基本的法律要件以及界限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制。同时,立法者的首要任务便是,确定刑事诉讼构架中的基本问题和对判决协商进行制约的法律规范。⑧Vgl.BGH,Beschluss vom 03.03.2005-GSSt 104,BGHSt 50,40,64.
(三)刑事协商的立法化
2009年7月29日,立法者遵循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上述裁定中的建议,将判决协商正式写入《德国刑事诉讼法》。按照立法者的初衷,将刑事协商立法化至少要满足以下三项基本要求:其一,在判决协商程序之外,法庭仍然负有查明案件实质真实的义务。其二,刑事诉讼仍然要遵循公正程序、法庭审理的公开和透明原则。同时,不能损害被告人的法定听审权。这一点不会因判决协商而有所触动。其三,刑事协商的适用不应突破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⑨Vgl.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gelung der Verständigung im Strafverfahren,BT-Drucks.16/12310,S.8.从文本来看,对判决协商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现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7条c中,该条分别规定了以下五项内容:第一,在刑事程序中,对诉讼进程和诉讼结果进行协商具有合法性。但即便如此,也要继续适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4条第2款对案件澄清义务的规定。第二,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后果、判决内容以及与此相关的裁定等。但有罪判决、矫正及保安措施不得成为协商的对象。第三,整个协商程序以法院的告知为开端,诉讼参与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如果被告人与检察官同意法院的建议,协商即成立。第四,法庭不受协商的约束,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可以不遵守其于先前协商中所作出的刑罚承诺。第五,法庭在背离其刑罚承诺时,对被告人负有告知的义务。
除第257条c的规定外,对刑事协商的规制也散见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其它条文中。①具体内容可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4款、第267条第3款、第273条第1款以及第302条第1款之规定。立法者意在用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为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已存在多年的刑事协商寻求立法基础与法律规制。一方面,这些条文需要回应,立法者是否考虑到了在近年来的文献和裁判中,尤其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所提出的各项法律意见。另一方面,其力图针对刑事案件中的协商提交一个全面的、多样化的法律规制意见(Regelungskonzept),以尽可能地为实践中刑事协商的成立和内容提供广泛的适用依据。②Vgl.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gelung der Verständigung im Strafverfahren,BT-Drucks.16/12310,S.8.
“自管模式”在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一般养护工程中的应用实践……………………………………………………… 瞿树林(2-229)
三、刑事协商与实质真实的现实冲突
(一)理论基础的差异
按照德国理论的通说,实质真实的学理基础通常被归结为 “符合论” ,即 “认知与存在相符”[1]。在 “符合论” 的语境下,真实这一概念并非独立于人的认知(Erkenntnis)以外,而是透过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对象)间的关系予以建构。如果认识主体在思维上能够与认识客体取得一致(Entsprechung),则该主体才能在对客体的认知中,获得可以称之为真实的认识。也就是说, “符合论” 给出了判断 “真实” 的标准:当主体的认识内容与客体一致时,该认识即可称为真实。将这一标准适用到刑事程序中,则要求法官对案件的认识要与过去发生的客观的案件事实相一致,唯有如此,法官的认识才能被视为是发现了真实。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实质真实理念。③Vgl.BverfG,Beschluss vom 26.03.1981-2 BvR 215/81,BverfGE 57,250,275.
而刑事协商的理论基础则源于 “交易的真相理论” ,即所谓的 “合意真实” 。合意真实是一种从语言哲学中导出的真相学说。在真相问题的哲学基础框架内,该学说 “从根本上讲是作为符合论的对立学说而存在的”[2]。合意真实理论认为,只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人在内的各诉讼参与方,在审前或者审理程序中,就诉讼进程和诉讼事实进行相互间的讨论和磋商后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案件事实即为真实。此处,诉讼各方不再不遗余力地查证案件在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取而代之关注的是现在能在哪些事实上达成一致。与实质真实是一种静态的真相观相比,合意真实推崇的是一种动态的真实理论,以 “谈话、对话和讨论” 作为其主旨思想。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从程序本身的设置来讲,刑事协商就不太可能与实质真实达成真正的一致。因为在加速程序进行、减轻诉讼负担的同时,若要求继续无限制地坚持实质真实所要求的职权查明原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④Vgl.Altenhein/Hagemeier/Haimerl,Die Vorschläge zur gesetzliche Regelung der Absprachen im Lichte aktueller rechtstatsächlicher Erkenntnisse,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 2007,71(76).
(二)诉讼价值的矛盾
在德国学者看来,实质真实原则服务于两项利益, “既有利于保护被告人免遭错误裁判的侵害,也有助于实现国家对真正实施犯罪行为之人的惩罚”[3]。只有对罪责的确定能达到十拿九稳⑤此处的德语表达为 “mit an Sicheheit grenzender Wahrscheinlichkeit” 或 “so gut wie sicher” ,意指对罪责的认定已经达到一种高度的可能性。的程度时,被告人才允许被定罪处罚。总体而言,在宪法意义上,查清犯罪行为,查明行为人,确定其罪责与刑罚,与对无罪之人作出无罪判决具有同等的重要性。⑥Vgl.Jarass/Pieroth,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Rn.102,10.Auflage,2009.在刑事诉讼中,职权澄清原则 “既是对行为人施加与其罪责相适应之刑罚的基础,反过来也体现了刑事实体公正(materielle Strafgerechtigkeit)”[4]。一项事实不公正的判决结果,不论其涉及的刑罚是严重还是轻缓,都会损害公众对司法的信赖,严重情况下,甚至会丧失公众对法治国的信任。从这一点来看,查明真相可以说是获得公正判决的前提条件。①Vgl.Gerson Trüg,Quo curris,Strafverfahren—Zum Verhältnis der objektiven Dimension der Beschleunigungsmaxime zur Wahrheitsfindung,Strafverteidiger 2010,528(531).
但刑事协商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却在于:当刑事程序可能面临时间和人员的耗费时,应最大限度地压缩证据调查程序。在澄清事实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法官本应通过审判程序这一核心环节来力求查明事实,但由于在审判程序中进行了刑事协商,查明实质真实就会因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合意而放弃,侦查结果和被告人基于侦查程序所作之自白反而成为诉讼的核心。甚至在实践中,当诉讼参与人将几乎所有的诉讼客体都作为协商对象的话, “这种以一致性为特征的协商程序显然就与尽可能查清事实所指向的职权查明原则相悖,甚至与罪责相适应原则间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5]。
(三)司法实践的冲突
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审判、耗时的经济案件诉讼程序,以及普遍增长的刑事案件数量,让刑事诉讼程序的负载进一步加重。以德国警方登记在册的刑事案件数量为例,1980年德国有381万件刑事案件,2009年有605万件刑事案件。到2013年,这一数据有所下降,但仍有596万件刑事案件。案件数量的这种 “井喷式” 增长也可以体现在德国司法人员人事配备的增加上。调查数据显示,1957年联邦德国共有2 421名检察官,1981年有4 361名,到2018年有5 882名。也就是说,在60年的时间内,德国检察官人数的增长幅度超过了100%。②具体数据详见德国联邦统计局2009年数据年报:Statistisches Bundesamt,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09,S.266。德国联邦统计局对德国检察系统2020年的评估统计:Statistisches Bundesamt,Staatsanwaltschaften-Fachserie10 Reihe 2.6-2020。德国司法部2018年的人事统计数据,网址:https://www.bundesjustizamt.de/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Justizstatistik/Richterstatistik_2018.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3.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若回顾德国过去几十年间的刑事司法实践,便可以看到,整体而言, “不论是刑事诉讼本身的程序变化,还是对实质真实这一传统诉讼目标的追求,都导致了德国刑事司法的压力不断增加”[6]。
鉴于此,不论是立法者、法院判决,还是诉讼参与人都在以自身不同的方式缓和这种压力:首先,立法者扩大了起诉裁量原则的适用范围,确立了包括不起诉在内的一系列程序停止的法定理由。其次,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近些年的裁判中越来越倾向于限缩诉讼参与人的证据申请权,以申请人意图拖延诉讼为理由拒绝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调查申请。③Vgl.Gerhard Fezer,Inquisitionsprozess ohne Ende?-Zur Struktur des neuen Verständigungsgesetzes,Neue Zeitschrift für Strafrecht 2010,177(178).其目的在于缓解办案法官的压力,从整体上缩短并加快诉讼程序的进行。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告方)将刑事协商视为逃离诉讼困境、摆脱讼累的 “救命稻草” 。因而,有论者指出,诸如此类的程序操作和传统意义上以依职权 “尽可能澄清事实” 为导向的诉讼程序间,可以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④Vgl.Rolf Hannich,Karlsruher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244,Rn.31,8.Auflage,2019.
四、刑事协商与实质真实的审慎协调
有德国学者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将判决协商立法化,就如同是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Büchse der Pandora)。⑤Vgl.George Küpper,Konflikt oder Konsens?Zur Entwicklung der Verständigung im Strafverfahren,Humboldt Forum Recht 2007,146.由于司法实践中突破条文框架进行刑事协商的现象屡见不鲜,理论的纷争也并未因2009年刑事协商的立法化而尘埃落定。因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需要通过判决的方式来定分止争。2010年和2011年,先后有三个进行刑事协商程序的案件因判决的合法性遭受质疑而被诉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⑥这三项被提起宪法诉讼的裁判分别是:1.慕尼黑地方第二法院2010年3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W5 KLs 70 Js 40038/07),案件被提起上诉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0年10月8日对该案件作出的二审裁定(StR 443/10)。2.慕尼黑地方第二法院2010年4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W5 KLs 63 Js 20750/08),案件被提起上诉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0年11月2日作出的二审裁定(StR 469/10)。3.柏林地方法院2011年3月15日作出的一审判决([503]2 St Js 1194/10 KLs[37/10]),案件被提起上诉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1年8月29日作出的二审裁定(StR 287/11)。提起宪法诉讼的起诉方认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三个案件中的裁定侵害了起诉人按照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和第20条第3款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应当予以撤销。最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经合并审理,于2013年3月19日一并作出判决。①Vgl.BverfG(Zweitens Senats),Urteil vom 19.03.2013-2 BvR,2628/10,Rn.1-132.因为该案件关涉2009年刑事协商立法化的合宪性问题,因而其判决意见被视为德国法领域对刑事协商态度的风向标。本文重点介绍该项判决中关于实质真实和刑事协商的论述,并将该项判决简称为刑事协商合宪性判决。
(一)查明真相的原则性要求
刑事协商合宪性判决共52页。从文本角度分析,以德文的 “真相” (Wahrheit)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话,该词在整份判决书中一共出现了26次。其中,有16次专门提到了 “实质真实” (materiellen Wahrheit)。同时,以德语中的 “查明真相”②此处有五种德文表述:Erforschung der Wahrheit,Wahrheitserforschung,Ermittlung der Wahrheit,Wahrheitsermittlung或者Wahrheitsfindung。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话,该项判决中一共出现了22次。此外,法官依实质事实而衍生的案件澄清义务(rihlihe Aufklärungspflicht)也在判决书中出现了 9次。整体来看,对包括查明真相在内的传统诉讼基本原则的强调,贯穿了该项判决说理的主旨。在判决书的开篇导言部分,第一句话便是:基本法所确立的罪责原则和由罪责原则所引申的实质真相查明义务,不允许法官和诉讼参与人对真相的调查、具体事实的法律适用和量刑原则进行随意的处置(freie Disposition)。③Vgl.BverfG(Zweitens Senats),Urteil vom 19.03.2013-2 BvR,2628/10,S.1.这就意味着,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的一开始便定下了基调:查明真相是宪法层面所确定的诉讼原则,即便是在判决协商程序中,法官和诉讼参与人也不得随意对事实查明进行处置。
在判决书的具体说理部分,即B部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重申: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zentrales Anliegen)在于查明真实的案件事实,否则实体的罪责原则就无法实现。同时,法院明确,将刑事协商进行立法化,并不是要在传统诉讼模式之外,再建立一个所谓的 “合意式诉讼模式” (konsensuales Verfahrensmodell)。相反,立法者将刑事协商立法化的中心目标是,在不损及法官澄清案件事实和形成心证等诉讼程序主导原则的基础上,以符合宪法任务的方式将刑事协商引入现行刑事诉讼法框架内。据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不仅确立了实质真实和刑事协商二者间的位阶关系,而且在判断刑事协商立法的合宪性时,采用了是否损害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和形成心证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刑事协商并未与诉讼传统相 “决裂” ,即便受到了刑事协商的冲击,实质真实原则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此处,或许会有读者提出质疑:既然引入刑事协商的动因是该程序能够在很大范围内缩短诉讼程序、节省诉讼资源,而现在立法者和司法裁判者又坚持要竭力追求案件真相,岂非一种在规范层面自相矛盾的做法?为了避免这种质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已经在这份斟酌刑事协商合宪性的判决中作出了解释:对诉讼中的协商施加限制,并非表明原有法律规范(即257条c第1款)自身存在着不可解的矛盾与冲突,而是一种明确尊重立法原意的体现,即刑事协商要与事实澄清原则、法官自由心证原则相协调。④Vgl.BverfG(Zweitens Senats),Urteil vom 19.03.2013-2 BvR,2628/10,S.31.
(二)以实质真实为导向完善刑事协商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肯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协商的规定并未违宪的基础上,以实质真实理念为导向,对该制度的适用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1.法官依职权澄清案件事实。第一,刑事协商的适用要遵循立法者的释义,与现有诉讼体系相统一,继续追求查明实质真实和发现公正的、与罪责相适应的刑罚。第二,现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7条c第1款中规定,第244条第2款关于法官有义务依职权澄清案件事实的规定不受影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这一规定已经非常明确,其不允许将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法官有义务查明的事实对象与范围作为协商的客体。因此,刑事协商不能成为判决的基础,而仅仅只能在法官基于其所认定的事实形成充分、扎实的心证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决定性作用。⑤Vgl.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gelung der Verständigung im Strafverfahren,BT-Drucks.16/12310,S.13.第三,法官不受协商结果之约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基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7条c第4款之规定,即便法官和参与人在诉讼程序中以协商的方式,就被告人的最终刑罚达成了某种共识,只要法官在后续程序中,发现了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实现罪责原则的新情况、新事实,其就能够 “撕毁” 原有的协商协议,而不受之前协商结果的约束。
2.审查认罪自白之可信性。刑事协商不能撼动法官依职权对案件事实进行查明,还可以理解为,法官要对被告人自白的可信性进行审查。裁判者认为,从字面来看,第257条c第1款除了明确要在协商中继续追求查明案件事实外,还可以引申出两个层次的立法指示:一方面,该规定表明,即便是在进行了协商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纯粹没有实质内容的、形式上的自白,以及一项从未明确、直接阐明其控诉事实的自白,都不能独立作为法官构建其心证的适当基础。另一方面,立法者是想通过这一规定,赋予法官考虑具体个案特殊性的自由裁量权。①Vgl.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gelung der Verständigung im Strafverfahren,BT-Drucks.16/12310,S.30.通常,对自白的审查需要通过审判程序中严格的证据调查来实现。但当某项自白是在以传统诉讼方式进行的法庭审理之证据调查阶段所作出的,法官就能按照普通条文之规定,采用质问(Vorhalte)或文书自读(Selbstleseverfahren)的方式对其可靠性进行常规审查即可。但裁判者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官对自白的审查都不能以与案卷进行纯粹对比的方式进行。②Vgl.BGH,Beschluss vom 03.03.2005-GSSt 104,BGHSt 50,40,49.因为,这种纯粹的对比方式并不能满足《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对法官要将心证建立在整个审判程序基础上的要求。并且,这类自白也没有体现出立法要实现刑事协商透明性和尽可能对以协商结案之判决进行有效控制的意图。③Vgl.BverfG(Zweitens Senats),Urteil vom 19.03.2013-2 BvR,2628/10,S.31.
3.全面的程序控制。按照德国立法者所设定的控制理念(Regelungskonzept),诉讼程序的进行应当让上诉法院有可能对依据刑事协商所作出的判决进行有效的、全面的控制。如此,有助于一审法院有效的适用刑事协商。④Vgl.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gelung der Verständigung im Strafverfahren,BT-Drucks.16/12310,S.10.基于此,裁判者认为,这种有效的控制可以通过广泛的程序透明性、全过程记录以及法官的告知义务来实现。刑事协商进程的透明、公开是对刑事协商进行全面程序控制的前提。只有让协商曝光在公开的法庭审理中,才能为协商过程接受外部监督提供可能。同时,在审理笔录中对协商的内容、程序进行完整的记录,全过程 “留痕” ,可以为上诉法院的全面审查提供依据。此处的全过程记录,不仅包括对程序推进的书面记录,还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对刑事协商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充分的判决说理。此外,为了避免法官因参与协商而有损其中立性,法官就刑事协商的重要事项对被告人负有告知义务。这是德国立法者和联邦宪法法院裁判者对事实法官引导协商程序进行所提出的明确要求。此处的重要事项包括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的刑罚上限和下限、被告人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以及法院将背离在之前协商中所作出的承诺等。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对刑事协商施加告知、记录等规范性要求,以及在条文中明确规定协商程序仍然要适用第244条第2款关于事实真相查明义务的规定,都是为了在法官和诉讼参与人基于协商形成最终裁判的过程中,尽量降低协商会给刑事程序实现宪法所赋予的任务可能带来的风险。⑤Vgl.BverfG(Zweitens Senats),Urteil vom 19.03.2013-2 BvR,2628/10,S.39.
五、回归客观真实——我国刑事诉讼研究的未来走向
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新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正式确立了中国式量刑协商机制。当前,以合意真实和诉讼效率为导向的认罪认罚程序,同样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查明事实真相的诉讼价值和程序理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承袭的是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构造,因此,相较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辩诉交易制度,德国的刑事协商更具比较和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合意真实观的冲击下,如何为查明真相提供有效的程序保障。
(一)坚守客观真实的诉讼传统
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刑事协商 “如火如荼” 的德国刑事诉讼体系中,不论是立法者还是裁判者,对刑事协商的态度都是十分审慎的。其所坚守的底线便是:刑事协商不能突破传统德国刑事诉讼所秉持的基础性原则,尤其是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和法官自由心证的构建。因为这关乎刑事诉讼是否能实现德国基本法所赋予的法治国原则和罪责原则的要求。也就是说,发现真相仍然是刑事诉讼的核心。
与此相似,中国刑事诉讼历来强调 “客观真实” ,要求 “办案人员在诉讼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符合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7]。正如陈光中先生所言,公正与真相是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观。 “真相不明,实体公正难以实现,且程序公正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查明事实真相,保障实体公正。”[8]具体到诉讼认识论领域,就是要坚持客观真实,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兼顾法律真实,做到客观真实同法律真实相结合。①参见陈光中《动态平衡诉讼观之我见》,《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13期,第4-5页。与历史事实相类似,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是客观无法改变的,不能因为主体认识的偏差而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 “事实必然是以真相为前提的”[9]。但近些年来,受当事人主义 “程序真实” 理念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研究中出现了一些 “反客观真实” 理论,客观真实的诉讼价值受到冲击。这种冲击集中反映到当下认罪认罚制度实践领域,即为:认罪认罚案件中,是否要以查明真相为导向,继续坚持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的法定证明标准。对此,不少研究者认为应当降低法定证明标准。②参见谢登科《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第135-143页;高通《刑事速裁程序证明标准研究》,《法学论坛》,2017年第2期,第104-111页。因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由于被告人自愿认罪,减少了庭审举证、质证负担,法庭程序被大幅度压缩。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也相应从以往的实质审查转向书面审理,客观上会降低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其实不然。首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双方对指控事实达成一致,客观上降低了法官在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上的难度,使得该类案件和其他非认罪案件相比,更容易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从而简化程序。但这种程序的简化和更容易达到证明标准只是促进了程序推动方式的转变,而并非在本质上降低原有法定证明标准的要求。其次,基于客观真实的诉讼价值追求,我国的刑事法官负担着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职责与义务。这一点不因庭审程序是否简化而区分适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14条和第222条针对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都适用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之证明标准,因而认罪认罚案件也概莫能外。再次,坚守法定证明标准,要求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也要查明事实真相,并非是阻碍程序简化,平添诉讼累赘,而是主张认罪认罚案件较之普通程序可以适用更为灵活的证据规则。例如,德国刑事协商并未严格遵循直接言词原则,而美国辩诉交易中的传闻证据也具有可采性。通过简化证据规则的适用,同样可以达到简化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目前,不少学者和高层实务部门基本认为:刑事程序的简化实际上是降低证明难度,而非降低定罪的证明标准。③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48-64页;孙长永《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67-187页;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课题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人民司法》,2018年第4期,第4-11页。也就是说,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的证明标准仍然适用于包括认罪认罚在内的所有刑事诉讼程序。
(二)兼顾公正和效率的程序机制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领域已经形成了两种诉讼制度并驾齐驱的格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果说庭审实质化改革是以 “繁者更繁” 为导向,追求真相与公正的话,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追求的则是 “简者更简” ,其效率导向可谓不言而喻。一般而言,在对总量相对固定的司法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时,理想状况是通过 “二八规则” ,将20%甚至是更少的不认罪案件进行精雕细琢,而对其余80%甚至是更多的刑事案件按照简化程序加速处理。由此,形成程序分而治之、互为补充的局面。这就容易让研究者陷入一个误区:与制度上的分而治之相对应,程序的核心价值也要分而治之。换言之,两种诉讼制度所代表的两种价值目标——公正与效率、真相与协商并驾齐驱。在诉讼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将公正与效率并提是大势所趋,但公正与效率二者本身还存在一个价值位阶关系:公正优先,兼顾效率。陈光中先生曾精辟地指出,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离开了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必将是反效率、高成本的,因为图快求多容易造成冤案错案,不仅损害了公正,而且需要花费更多的司法成本加以纠正和补偿”[10]。同理,真相的价值位阶也高于协商。如果将效率作为认罪认罚制度的核心或者单一价值,从而忽视甚至否定查明真相的话,显然在理论基础层面就缺乏正当性。由于基本理念上的认识偏差会让制度的实践效果大大背离预期,以致有不少地方的办案机关,一味追求案件的 “快办” “简办” ,在极力压缩办案时间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漠视被追诉人依法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让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审查流于形式,甚至出现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强迫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乱象。
实践已经充分的告诉我们,在程序 “繁者未繁” 的情况下,一味追求让 “简者更简” ,只会让积弊更深。制度创新只能治标,坚持核心价值才能治本。在两类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公正与效率、真相与协商应当是一种 “分而共治” 的关系。其中,公正与真相仍然是核心价值导向。以此为前提,刑事司法才能 “两条腿” 走路,一方面继续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三)强化检察和司法官的客观义务
在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中,控辩平等无疑占有一席之地。当事人主义国家奉行形式平等,此种控辩平等以形式真实为基础,将严肃的刑事诉讼活动,特别是刑事审判作为竞技场。这套形式平等的程序规则与我国司法职权的配置格格不入,其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戏剧色彩,热闹有余而精确不足。因此,我们应着力思考的是如何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控辩平等。但在论证实质平等的命题时,论者多套用形式平等的思路,将重心完全放在辩护方的权利保障上,着力提倡被告人权利保护和辩护律师的实质性辩护。当然,笔者对此表示十分赞同,但从查明案件事实的角度出发,其实还可以有另一种思路:强化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以及法官的职权查明义务。乍一看,这一提法似乎与控辩平等背道而驰,甚至还会有为了查明真相而 “枉顾” 被诉人基本权利的嫌疑。实则不然。在控、辩、审三造结构中,辩护一方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实际上,不论采取何种制度设计,辩方都无法与控方形成那种理想状态下的绝对抗衡,就算是形式上的程序机会平等也无法实质解决此问题,这一点不可否认。因此,除了要强化辩方自身的权利和地位外,也需要强调控、审两造对辩方的权力加持:一方面,控方的程序目标不是纯粹的胜诉,而是要基于客观义务,竭力收集并查找有利和不利被诉者的事实。另一方面,在当前侦、审信息阻断机制无法成型的情况下,审方绝不能止于消极裁判者的角色,而应克以其职权查明义务,在尽可能掌握所有事实、情节(包括有利被告的事实、情节)的基础上形成心证,以获得有效、全面的程序控制,确立法庭在事实认定上的终局、权威地位。如此,检察官不再是纯粹追求胜诉的原告方,法官也不会是因权力掣肘而只听得一家之言的评断者,孱弱的辩护一方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诉讼照顾,从而实现 “控辩动态平衡” 而非简单的 “控辩形式平等” 。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在奉行形式平等的美国刑事司法中,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也并非是完全消极、被动的。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法官对辩诉交易程序中被诉人认罪供述的审查。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之规定,对于两造在罪名、罪数和刑罚上的磋商结果,事实裁判者并非照单全收,必须发挥审判程序对事实认定、案件办理的终极把关作用。而这一把关的重点内容就是对认罪自白的审查。首先,法官必须了解,被诉人之有罪供述是否出于自愿。此种审查,一方面是为了甄别被诉者在审前是否被违法取证,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为了避免在控方不适当的许诺以及辩方出于辩诉交易所能带来 “利益” 的不当驱使下,案件的办理会背离基本的、客观的事实。其次,法官需要审查,被告之认罪是否有基本的事实基础。即便法官接受了两造之交易结果,但在其作出最后的罪责认定之前,必须查清的一项关键内容便是,是否存在事实之基础能够足以支撑辩诉交易中被诉者之认罪自白。这一规定也广泛为美国司法实务所接受。对此,事实法官可用的审查方式也是多样的。例如:亲自讯问被告人,具体询问检察官,或者是仔细审阅控方所提供的有关辩诉交易情况的详细报告。故,不论是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还是德国的判决协商制度,都主张法官基于案件事实真相而对被告人所作之自白负有审查义务。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简化审理程序,实际上也非常强调程序之简不能代替事实之简,也不能违背案件真相的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