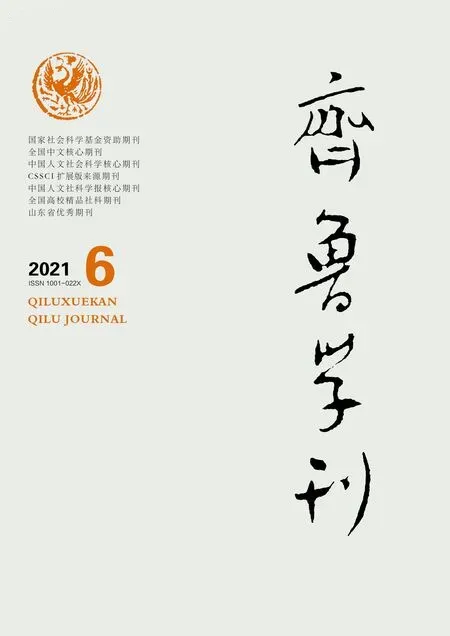戴震论心与理、欲、情的关系
李慧子
(成均馆大学 儒学与东洋哲学院,韩国 首尔 03063)
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本体论上,他继承张载、船山的气本论,认为理并非超越于气而存在的抽象理念,给理与性以天道基础。在人性论上,他继承发展了孟子性善论,用“血气心知”说驳斥程朱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说。在理欲论上,他反对存理灭欲,主张“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1](P9-10)。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同时,也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等著作中,戴震多次论及“气”“理”“性”“欲”“情”“心”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其哲学体系中处于何种位置,彼此又具有哪些关联,是值得厘清与研究的问题。
戴震说:“况气之流行既为生气,则生气之灵乃其主宰,如人之一身,心君乎耳目百体是也,岂待别求一物为阴阳五行之主宰枢纽!下而就男女万物言之,则阴阳五行乃其根柢,乃其生生之本,亦岂待别求一物为之根柢,而阴阳五行不足生生哉。”[1](P82)“生气之灵”是气的主宰,而心乃人身之“主宰枢纽”,决定了人与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一论述足见戴震对于“心”的重视。因此气本论虽然是戴震哲学的重要基础,但人心论也是理解戴震思想的关键。钱穆先生曾指出:“通情遂欲有赖于聪明圣智。”[2](P352)聪明圣智取决于心知,而戴震说达情遂欲是对天理的实现。那么,心知不仅与情欲等人性问题相关,还与天理、伦理制度建构有关。有学者指出,戴震“融情感与理性为一体之‘心’,作为认识能动性和道德主体性的根源,在戴震道德哲学中恐怕要远比‘气’更为关键。这也是以往研究少有关注的盲区”[3]。由此可见,人心论是贯通戴震哲学本体论、人性论与制度论的枢纽,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深入研究。
学界对于戴震理气论、理欲论与人性论的研究较多,但对其心论的系统性研究目前还较少。张立文先生曾分析戴震思想中心的功能,认为心是感知外物的主体,具有思维活动的功能,也是道德意识的实体[4]。也有学者梳理了戴震对心知观的哲学建构,提出“心知的形成本于血气,彰显了戴震气本论的宇宙构架;心知的旨归合于理义,突出了戴震从自然到必然的性善旨趣;心知的发用在于解蔽,搭建了戴震求道之路的知识桥梁”[5]。这些研究对理解戴震心知论具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他们对戴震思想中心与理、情、欲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展开辨析与梳理,无法说明戴震哲学中本体论、人性论与制度论的内在关联。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戴震思想中“心”的功能,以及心与理、欲、情的关系,从而明晰戴震哲学的逻辑框架。
一、心与理之关系:心通理义
戴震认为人性包含欲望、情感和心知三个部分:“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1](P40)他把欲望、情感的产生追根于血气之性,把人之所以能实现仁义礼智归因于心知:“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1](P9)人与动物皆有情、欲,而心知为人所独有的,也是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根本属性。“以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之为善。”[1](P29)戴震继承孔子“天生德于予”的思想,认为“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1](P5),是人认识和实现善性的基础。那么心知何以具有这种实现仁义礼智的“自具之能”呢?
朱子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由此理,便有此天地。”[6](P1)戴震反对朱子把理视为先在于气的绝对存在,他引用先秦儒家经典文献重新梳理了“理”的内涵,认为理并非先天地而生,不能脱离气而存在。理是自然之“分理”“条理”[1](P1)。“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为之委曲条分,苟得其理矣”[1](P12),“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1](P2)。关于理与心的关系,朱子说:“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虚,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6](P2514)又说:“理无心,则无著处。”[6](P85)由此可见,朱子认为在人心之外别有一理,心是承载理的器官。戴震反对朱子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1](P3)的观点,认为这只是朱子的个人见解,并不是至理。他指出在孟子思想中,心能通于理义,就如五官能通于声色气味一样,是人性本然具有的能力,并非是后天赋予的能力。“孟子明人心之通于理义,与耳目鼻口之通于声色嗅味,咸根于性,而非后起。”[1](P6)
孟子只说人心通于理义,但是并没有解释人心何以能通于理义。戴震沿着孟子的思路,从气化宇宙论的角度分析了心知的天道基础。他指出心之所以能通达理义,乃是因为心也是由阴阳五行构成的:“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1](P8)。因为心与天地在形质上是相通的——“人物受形于天地,故恒与之相通”[1](P7),因而人心才能通理义——“理义也者,心之所通也。”[1](P86)戴震由此批评朱子对于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是误读了孟子,强调人心之外并不存在一种超越性的理。“后儒见孟子言性,则曰理义,则曰仁义礼智,不得其说,遂于气禀之外增一理义之性,归之孟子矣。”[1](P6)义理之性并非外在于人性,而是内在于人心,“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1](P7)。既然“人心之通于理义”,非心外别有一理,那么求心就能求理。心与理的关系上,戴震的论述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因为心通于理义,所以心具同然之理、大共之理。戴震认为,理是普遍共理,是万事的准则,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1](P12)他将孟子“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概括为“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1](P3)。他解释“同然”的意思是:“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1](P3)在东原看来,人心具有普遍性的天理,即“大共之理”。所谓“大共”就是善:“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1](P63)“大共之理”就是“有根于心之德”,是“所以衡论天下之事,使之协于中,止于至善”[1](P119)的根据。
东原强调孟子所说的“良能”“良知”,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能力,是“弗学而能,乃属之性”[1](P32)。那么这种“属之性”的“能”就意味着一种必然的实践能力,人具有这种能力就必然会去行善。因此戴震强调每个人都同然具有认识理与实现仁德的心知能力。“有根于心之德,斯有以通夫大共之理,而德之在己,可自少而加多,以底于圣人。”[1](P119)理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知晓与把握的,每个人都能明理、得理,因此圣人与普通人的心灵能力没有差别。“是为得理,是为心之所同然。”[1](P12)不仅如此,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心之功能,“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使“仁义礼智无不全”[1](P28),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在这一点上圣愚也无差别。“所以为同然者,人心之明之所止也。”[1](P85)戴震认为荀子意识到了人心之同然,所以荀子才会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但他批评荀子没有意识到人不仅可以成为圣人,并且能成圣成贤。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7](P353)也正是由于心具有同然之理,人才能用普遍法则去衡量事物和言行是否是正当、合理的,如此人才能不会为偏私所误,不会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迷惑不定,世界不会也因为主观私意而走向混乱。“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1](P28)
第二,心能思,能辨理义。戴震延续孟子“心之官则思”的思想,提出“是思者,心之能也”[1](P5)。心具有天赋的思考能力,因此人能认识和思考天地的规律、宇宙的奥秘,并且能根据天道去制定人间的伦理法则。而人之所以能通于天地之德、德泽于万物,乃是由于心能思。“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见于思乎。”[1](P71)心之精妙体现在它能使人纵观时空,通达天地义理,并且在行事上顺应规律。“心之精爽,有思辄通,魂之为也,所谓神也。”[1](P5)东原解释孟子之所以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乃在于:“心能辨是非,所以能辨者智也;智由于德性,故为心之能而称是非之心。”[1](P105)由于心通于理义、具大共之理,因此心能分辨善恶是非。“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1](P5)理就是万物的条理,具有永恒不易性:“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1](P3);而“义”就是按照天地之理去适宜行事:“如斯而宜,名曰义”[1](P3)。心具有明辨天理、裁断言行是否符合理义的能力。“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1](P3)理义不是人心编造出来的,而是普遍公理,是“不易之则”。“故理义者,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异强制之乎!因乎其事,得其不易之则。”[1](P92)因此,人心能依靠“大共之理”权衡分寸利弊,裁断是非善恶,并使视听言动和于中道。
第三,“心好理义”。戴震注意到人心具有一种天然爱好理义的特性:“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至是者也”[1](P5);“理义非他,课否之而当,是谓理义”[1](P92)。当心灵觉知、辨识到体现天理之节文、符合理义的事情,就能会欣喜、悦纳;当人行事符合理义时,心就会自然产生畅快满足的感觉;反之心灵则会沮丧、难过。“凡人行事,有当于理义,其心气必畅然自得;悖于理义,心气必沮丧自失,以此见心之于理义,一同乎血气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1](P7)心好理义并不是个别人的心理感受,而是心之所同然。正是由于心通于理义,心对于符合理义之事才会欣赏:“举声色臭味之欲归之耳目鼻口,举理义之好归之心。”[1](P91)正是由于心具有好理义的特性,人们才能好善憎恶,社会才能向积极良善的方向发展,仁义才能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戴震从气化宇宙论的角度说明了人心为何能通于理义的问题。他通过分析心具同然之大共理、心能辨理义、心好理义等问题,来说明圣人与普通人的心知能力没有差别,皆能成圣成贤。也正是由于心通理义,人才能认识天地的规律,思考宇宙人生的奥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明辨善恶是非,在利义之辨中舍利取义;才能使视听言动合于中道。可见,戴震并不把心作为客观的认知器官,而是赋予其道德内涵。既然心能通理义,那么人为什么会作恶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心与欲、情的关系。
二、心与欲的关系:以心遂欲与以心节欲
程朱认为太极之理至善至纯,而气质有清浊厚薄之分。“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6](P3)由于欲望来自于气质,欲望有善有不善,因而应在义理之性之中去求理。戴震批评朱子说:“后儒以人之有嗜欲出于气禀,而理者,别于气禀者也。今谓心之精爽,学以扩充之,进于神明,则于事靡不得理,是求理于气禀之外者非矣。”[1](P6)戴震从本体论上打破了气与理的分割,将“理”解释为气之理。如此一来,对于理的追求就不是在气之外。
戴震认为,心不是抽象的空虚之物,而是以血气为物质基础,心不能脱离血气而存在。因为欲望根植于血气,因而以血气为基础的心也会受到欲望的影响。这体现在“其心能知觉,皆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1](P93)。戴震指出,欲望的产生是源于血气,并非因为心:“血气之所为不一,举凡身之嗜欲根于血气明矣,非根于心也。”[1](P92)虽然心是身体的统领者,身体的欲望被心所收摄,但这并不表示欲望来源于心:“耳目百体之欲喻于心,不可以是谓心之所喻也。”[1](P67)心虽能够调动和控制感官,但它并不能代替感官之能:“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为。”[1](P92)因而当欲望过度之时,心通理义、心辨理义的理性能力就会受到干扰,人就会作恶。
戴震反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说明理、欲不是矛盾对立的正邪关系:“非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也”[1](P11);“欲,其物;理,其则也”[1](P8)。欲望本身是一种客观实存,其性质并不是恶的,而理是欲望的规则。他并没有只看到欲望的负面影响,而是肯定欲望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1](P64),“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存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1](P58)。戴震还表明人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人有欲望,而是因为有私欲:欲望并不能遮蔽理,遮蔽理的是私欲。“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1](P9)
戴震批评存理灭欲的观点是用抽象的天理去灭杀人性,背离了先秦儒学的原义:“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1](P58)戴震认为,儒家的仁爱在于“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1](P8),而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的目的并不是让人无欲,而是“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1](P8)。他特别引用了孟子对于必须先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欲求,然后才能让百姓行仁义的表述:“孟子告齐、梁之君,曰‘与民同乐’,曰‘省刑罚,薄税敛’,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1](P10)戴震指出王道之治都能呵护体察人民的情感需求,恰当满足人们的欲求:“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1](P41)
戴震虽肯定欲望的合理性,但他也注意到“言性之欲之不可无节也”[1](P11);“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过”[8](P357),“未当也,不惟患其过而务自省以救其失”[8](P357)。过度的欲望会导致人违背理义做出伤害他人与自己的事情,社会也会因此动荡不安。他认为天理的实现就是对人欲的正确处理,因此主张“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1](P11)。在他看来,要使得欲望的表达合于中道,“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1](P11),就要“依乎天理”[1](P11)。而依乎天理、达乎天理就需要发挥心之作用。这体现在以心遂欲和以心节欲两个方面:
其一,以心遂欲。戴震明确提出“心之所喻则仁也”[1](P67)。心所包含的就是天地之德,就是仁:“天地之德,可以一言尽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尽也,仁而已矣。”[1](P67)仁义礼是天下之共理,智仁勇是实现仁义礼的具体之德,而实现天下共理的核心关键在于心:“仁义礼可以大共之理言,智仁勇之为达德,必就其人之根于心者言。”[1](P119)而心之仁德的实现就是使身体的欲望得以恰当满足:“心之仁,耳目百体莫不喻,则自心至于耳目百体胥仁也”,“心得其常,于其有觉,君子以观仁焉;耳目百体得其顺,于其有欲,君子以观仁焉。”[1](P67)
其二,以心节欲。戴震认为血气、心知不是割裂的,血气之欲、情都受到心的控制:“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1](P92)心灵对身体有统领作用,视听言动都靠心去主宰:“心,君乎百体者也。百体之能,皆心之能也。”[1](P6)心灵能调动知觉和思考能力去感知、认识和理解世界,并指挥身体做出合宜的举动。戴震主张要发挥心通理义、辨理义的理性能力,让欲望得以节制,使得其分寸适当、不过度:“人有欲,易失之盈;盈,斯悖乎天德之中正矣。心达天德,秉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夺之,故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1](P71)人应当保持心灵自省的状态,觉察不适当、不合意的欲念,“欲不流于私则仁,不溺而为慝则义;情发而中节则和,如是之谓天理”[8](P357)。同时,心对于欲的控制要如大禹治水一样,要疏导而不能堵塞:“禹之行水也,使水由地中行;君子之于欲也,使一于道义。”[1](P71)戴震也指出要发挥心之同然的“大共理”能力去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不能以自己为中心:“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1](P75)
三、心与情的关系:以情絜情
朱子认为孟子所说的“恻隐”是“情”:“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6](P91);“盖好善而恶恶,情也;而其所以好善而恶恶,性之节也”[6](P2514)。又说:“性无不善。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说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体本无不善,其流为不善者,情之迁于物而然也。”[6](P92)戴震反对朱子这一理解,澄清四端是心,而非情:“孟子举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谓之心,不谓之情。”[1](P41)他还说明四端皆来自于心:“心则形气之主也,属之材者也。恻隐、羞恶、恭敬、辞让之由于德性而生于心亦然。”[1](P105)
关于性、欲、情、心的关系问题,戴震说:“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徵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徵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性之徵于巧智,美恶是非而好恶分。”[1](P64)欲望是自然人性,也是人生存繁衍的动力。人有了欲望之后人就会产生情感,有了欲望与情感,才会生出机巧与智慧,才会分出好恶。
戴震分析情感具有感通能力:“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1](P64)正是因为人有情感,人与人之间才能彼此感知与沟通,而情感的感通能力藏于心中。心能对外界的刺激产生知觉反应:“夫事至而应者,心也。”[1](P9)而这种知觉反应是人所有的感官能力中最强大的:“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曰觉,思之所通曰知,百体能觉,而心之觉为大。”[1](P90)正是由于心具有知觉能力,人才会怀生畏死,人与人之间才能彼此共情与理解,关心和帮助才得以可能。孟子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7](P237)戴震认为,人之所以当看到他人处于危难、苦痛时而心生恻隐、怵惕,就是因为心有知觉、有情感,能觉知冷暖悲欢,能换位感受他人处境。“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侧隐之心?”[1](P29)这种知觉能力是心本身固有的,并非心外别有一物操控人的想法与言行:“然则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焉藏于心’也。”[1](P29)因此,心的知觉能力是人与人、万物发生关联的基础,也是道德产生的基础。
戴震认为情与理并不矛盾:“情者,有亲疏、长幼、尊卑感而发于自然也。理者,尽夫情欲之微而区以别焉。使顺而达,各如其分寸毫厘之谓也。”[8](P357)理不是压抑情欲的工具,而是要对不同层次的情欲进行区分,让适当的情欲得以满足,让过度的情感得以节制和疏导,“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1](P2)。如果为了维护凝固的礼法规范而让人舍弃、压抑情欲,那么这种理就不是普遍公理,就是偏私的意见,就会伤害人心。
戴震认为,理中包含和体现了情,理与情无法割裂:“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1](P1)当一件事情符合理义时,情感也能得以恰当显现。如果只是一味要求人必须符合理义,但却不让情感得以表达,那么这种要求就是不合理的。戴震区分“必然”与“自然”之则,旨在揭示理义并非外在于人性,而是基于人性之自然。他批评荀子没有意识到礼法的必然法则其实也是出于自然人性:“知礼义为明于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极则,适以完其自然也。”[1](P32)理义的目的是为了呵护和实现人性,并非要压抑与排斥情。
在戴震看来,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与《大学》中所的“所恶”,皆是“人之常情”,而“常情”中包含着常理:“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尽于此。”[1](P4-5)人之所以会有“所不欲”、“所恶”的“常情”,皆是因为遇到违背“常理”的事情,因此是“不言理而理尽于此”[1](P5)。宋儒后学所主张的“舍情求理”不仅不能体民之情,还会伤害民心:“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1](P5)那么如果使得情欲有节,又能呵护民心民情呢?戴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以理节情”的同时,也要“以情絜情”,而“以情絜情”的关键乃在于心。
人之所以能以情絜情,是由于心中存有“常情”和“常理”。“今日理在事情,于心之所同然”[1](P5),个人之情是普遍人情的体现,因此用我之情去絜矩他人之情,才能理解与体谅他人:“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以我絜之人,则理明”[1](P2)。只有絜矩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人才不会因一己之偏私而伤害他人:“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1](P2)只有超出一己之私,用普遍共通的情感去体谅与理解别人,人的起心动念与视听言动才能符合理义,没有差池:“以情絜情而无爽失,于行事诚得其理矣。”[1](P2)
戴震希望通过调动人心所具有的大共之理去“以情絜情”,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与互助。“诚以弱、寡、愚、怯与夫疾病、老幼、孤独,反躬而思其情,人岂异于我!”[1](P2)因此,“以情絜情”不仅需要发挥心之辨理义、节情欲的理性能力,同时也需要发挥感性的情感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戴震认识到道德情感‘未有不悦于理义者,未能尽得理合义耳’,为了避免情得理不得的情况,除了感通移情能力之外,还有‘能明于必然’的理性裁断能力,只有将感通移情与理性照察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情理兼尽,实现自然与必然的统一。”[3]
戴震澄清孟子“乃若其情”的“情”不是情感的意思,而是实情之意。实情包含生活的真实情景,也包括人的欲望、情感与心知。“今曰理在事情,于心之所同然。”[1](P5)“理在事情”就意味着情、欲、心知之中都体现着理,在“情之不爽失”之中就体现理的流动。戴震澄清圣人之学并不是绝情去欲,而是让人明理行善:“无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绝情欲以为仁,去心知以为智也。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1](P53-54)由此可见,心不仅能让欲望、情得以适当展现,也能使其符合理义、分寸适当:“是心之明,能于事情不爽失,使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1](P3)既然心是体情、遂欲、达理的主宰和枢纽,那么如果心不发挥作用,人即使有再好的资才也不能通情达理,仁义礼智就不能实现。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心的功能呢?
四、论心知的实现
戴震认为,造成古今之人不能行仁义的根本原因是私与蔽。私是对情欲的无节制追求,而蔽是指心知不能发挥作用。“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1](P9)私欲一旦兴起就会使情感有所偏移,而过度的情欲会干扰心知之能。心知一旦被遮蔽,就无法发挥其辨理义、节情欲的能力,人就会做出违背礼法规范的失德之举,也就无法通达和遵循理义:“心有所蔽,则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1](P9)心受遮蔽还会“必害于事,害于政”[1](P1)。因而只有人的欲望不私、情感不偏、心知不蔽,才能通达理义、实现仁义礼智:“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智也。”[1](P41)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私”“不偏”“不蔽”呢?
第一,运用心之思考能力去除私欲、意见对于心知的遮蔽。戴震提出“解蔽,斯能尽我生”[8](P394)的思想,强调心知对于明理、达情、遂欲的重要性。去除私欲并不是让人无欲,而是使心无私慝。如果一种思想只是让人灭除欲望,但不能清除人们头脑中偏见,那么这就不是圣人之学。“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1](P57)要想解蔽,首先要发挥心灵的思考能力。心之思不仅体现在对外在现象与规律的思考,还体现在心有自主意识,能切己体察、反躬自省。“返观内照,近于切己体察,为之,亦能使思虑渐清,因而冀得之为衡鉴事物之本。”[1](P16)“解蔽”就是要运用思考能力,去除偏见和个人意见对真理的遮蔽。人在认知方面最大的危险就是“蔽而自智”,即用自以为是的观点和主观意见当作普遍真理。“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1](P3),“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1](P9)。人一旦任性由己、自以为是,就会产生悖谬的想法。而之所以会出现误解、误读与误判,就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的把握真实的情况。所以如果想要避免“任其意见”所导致的谬误,就要“使人自求其情”,即不带偏见与私意地了解、探求客观实情。
第二,学问资于道德。戴震认为,由于人分得的阴阳二气不齐,所以“成性各殊”,在先天资质上有所差异。“物之得于天者,亦非专禀气而生,遗天地之德也,然由其气浊,是以锢塞不能开通。”[1](P86)但是后天的教化与修为能够弥补先天之不齐,每个人通过后天的努力都能成为圣人。“人之血气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齐,得养不得养,遂至于大异。”[1](P8)他通过说明下愚可移而鼓励人们不要放弃教化与修为:“至下愚之不移,则生而蔽锢,其明善也难而流为恶也易,究之性能开通,非不可移,视禽兽之不能开通亦异也。”[1](P30)戴震提出学问对于心知的养护和提升最为有益:“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1](P6)学问能扩大心量,去除遮蔽,让人从昏昧变得明智:“以心知言,昔者狭小而今也广大,昔者阊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养也,故曰‘虽愚必明’。”[1](P8)通过后天的学习,也可以使心要保持“察”的觉醒、明辨状态,如此才能不受情欲之蒙蔽:“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1](P5-6)
第三,不能仅靠个人修养去保护心知之能,社会也要建构合情合理的制度去体察民情,满足百姓的生活欲求,从而促进心知的实现。礼是依据天理秩序而制定的人间法则,“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1](P48),因此人通过践行礼法就能将外在的规范、条理内化为身心的秩序。礼不仅能促进人伦关系的睦融洽:“礼者,天则之所止,行之乎人伦庶物而天下共安。”[1](P72)礼也能让人获得智慧:“若夫条理之得于心,为心之渊然而条理,则名智。故智者,事物至乎前,无或失其条理,不智者异是。”[1](P94)设立礼法的目的是“治天下之情”,使人的言行变得恭敬、谦让、谨慎,让情感的表达恰当、适中:“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1](P49)礼法的惩罚作用还能让人“明乎怀德怀刑”[1](P77)。戴震指出,礼既是“至当不易之则”[1](P56),也是“动容周旋中礼”[1](P49),是人们在人伦日用的交往互动之中不断展现的动态的、适当合宜的行为规范。因此不能用凝固化的制度去裁断复杂的现实情况,更不用僵化的礼法规范去裁制人心人情。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戴震思想中,心是达理、体情、遂欲的枢纽,具有通达理义、辨别是非、好善憎恶、知觉感通的能力。血气和心知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性。欲望、情感来自于血气,而仁义礼智源于心知。由于心由二气五行构成,在形质上与天地相通,因此心能通于理义、心具同然之大共理。也是由于心以血气为基础,也会受到欲望、情感的干扰和遮蔽。理与欲、情并非正邪关系,“理是情之不爽失”,“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达情遂欲也是理的体现。但是过度的情欲也会遮蔽心知,让心不能辨乎理义,从而做出破坏理义规范的失德之举。因此,心应当保持辨夫理义、节制情欲的理性能力,也要用同然的“大共之理”和知觉感通能力去“以情絜情”,让人的情感得以呵护,也让人与人之间彼此友爱互助。戴震“将人的本质置放在一种交感性的血气、心知上,并在此血气、心知上建立一种絜情的人伦之道。血气与人伦的双重性不但构成了人的本质,它也构成了群体共享的道德基础”[9](P271)。心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心之功能的发挥决定了理、欲、情的实现。而人要全面发挥心知之能,使得情欲有节而合于理义,就要从三个方面努力。在个体层面而言,要运用思考能力去除私欲、意见对于心知的遮蔽。在修养功夫层面而言,将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目标,要通过学问与修为弥补先天资质上的不足,使得心知“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从社会层面而言,国家要建构合情合理的礼法制度去保护人民的情感、满足百姓的基本欲求,并促进心知之能的提升,从而让仁义礼智得以实现。因此,人心论在戴震哲学中起着勾连本体论、人性论与制度论的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