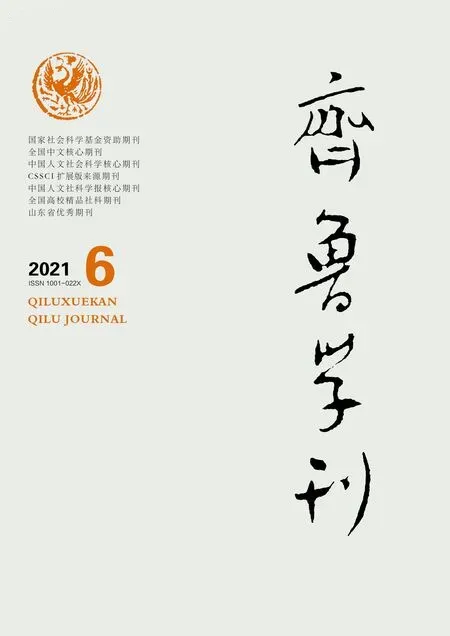生存的美学维度与文学记忆本体内涵的阐释
沙家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素质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450002)
基于创作主体的文学记忆研究,重在关注作家记忆对文学生成的意义。文学书写是对个人或人类生存经验的书写,文学创作始终参与人类记忆的重构。所以,作家选取什么样的记忆,直接影响着文学内涵的轻重与深浅。实质上,人是记忆存在物,记忆与人之生存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往往有各自不同的生存观,进而有不同的生存论。基于生存的多维性、苦难性和符号性等人之生存的一般性特征,以及美是人类的肯定性精神价值和积极情感的有意味的感性呈现,笔者认为:美学意义上的生存特征应是生存的多维向度、生存苦难的美学升华及生存符号的诗意栖居[1](P317-327)。这种状态就是“合于人性的或人应该如此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生存或生存状态便是美”[2](P45)。基于生存的美学维度,文学记忆的本体内涵承担了以穿越时间的方式追求生命的完整、以苦难性记忆承载生命的厚重、以诗意的记忆符号安放“存在”之灵魂的叙事功能。立足当下消费时代或后现代现实语境,秉持文学记忆本体的美学维度,我们能理性考量现代人类活动的得与失,客观评判作家对记忆资源的选择给文学带来的诸多影响,帮助作家及时纠偏负面的生存观念,使生存记忆的文学书写无愧于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以穿越时间的方式追求生命的完整
记忆首先是个时间范畴。戴望舒在《我的记忆》一诗中,以亲情拥抱的方式把“记忆”视为忠实的老朋友。可以想见,戴望舒在与其“记忆”照会时是多么幸福和惬意,纵然可能有伤感存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细究起来可以发现,这是因为诗人以穿越时间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所在。穿越时间正是作家的一种存在方式,作家潜意识地遵循生存多维性的时间连续向度,以“现在”为基点追忆往昔,用想象和情感使“记忆”审美化,作家从中获得了生存论意义上的领悟及生命的跃迁。
首先,在想象中重构生命的过去。人的生命之河“不舍昼夜”地流动,那些逝去了的岁月里,有着人曾经的甜蜜、忧伤或挣扎,人们不可能与之隔绝,但我们只有通过想象穿越时空,以回望的方式与之“亲密”接触。以想象的方式追忆往昔是人的无奈之举,但恰恰是在这种方式中,人们能有选择地重构生命的过去,让生命之流不至于断裂。一般说来,个人常常重构的是童年、故乡,或成年之后的人生往事。
童年是一个人最初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遭际,是生命出发的地方,是“属我”的私人空间,虽然短暂但意义非凡。童年记忆是作家写作的原始起点,童年经验构成了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独特的童年视角是作家观察人生和社会的有效窗口。古今中外最让我们感动并充满温暖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关于童年记忆的深情书写作品,我们会从中体察到作家的真实生命存在。鲁迅的童年书写就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童年经验”构成了鲁迅创作中重要的写作资源,他的“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朝花夕拾》安放着鲁迅诸多童年记忆,这些积淀在作家心灵深处、不能忘怀的记忆,负载着作家深沉的思考,传递给我们温暖和感动。鲁迅正是在其童年书写过程中,完成了他生命的再体验和重构。
当然,想象童年一般要进行精神还乡,因为故乡与童年往往是一体的,都是生命的原点所在,因而,故乡是一个人重构生命过程中不可绕过的精神领地。故乡安放着作家的灵魂,是作家精神成长仪式启动的地方,作家自从离乡之后就无意识地把精神扎根于此了。所以,书写对故乡的依恋情结,找寻生命根源的依据,就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掀开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学史画卷,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书写故乡的优秀诗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还乡”为母题的作品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很多现当代作家在谈到其创作资源时,都要提及故乡的精神滋养。沈从文说他“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3](P29),莫言说“我的肉体生活在北京,我的灵魂生活在对于故乡的记忆里”[4],等等。可见对故乡的想象式回望,对于作家心灵归宿和和生命记忆的重要意义。同时,作家在回味自己的童年时光时,不仅仅是怀恋故乡,更多的是咀嚼和回味人生往昔的酸甜苦辣或坎坷经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往事书写是一种复杂而又丰富的文学现象,这些往事多是底层的苦难生活,或文人的怀才不遇与仕途坎坷等,作家对这些往事不是机械地再现,而是加以审美化选择和重塑,并在追忆的过程中赋予其新的价值,从而实现生命意义的再生与飞跃。
其次,从历史记忆中汲取人类前行的力量。重构生命的过去实际上就是重构“我”的个人记忆,但人是社会存在物,故也是要重构“我们”的集体记忆,以此获取更丰富的生存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过程是一个记忆共享的过程,通过分享“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向全人类发言。文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是由人的历史属性决定的。人之历史,是人自我解读的历史,是“我向性”的历史,此时的历史已具有主体的自觉意识,个体或群体记忆的历史化就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强调主体精神的参与作用,如体验、观照和领悟,这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思维过程。有了这种历史意识的烛照,那些“本来的历史”才会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意识的注入会增强文学记忆的历史底蕴,帮助人们汲取历史记忆中的积极因素,从而让人类更有力量、充满希望地前行。有了历史意识, 我们或因忏悔而批判,或因忧患而展望。如此,我们才能沉入历史,在历史中寻找智慧,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关键钥匙;讨论史事,多一些维度和眼光,着眼于宏大历史,也不忽视私历史,以此来填补历史的空白。作家有了这种历史意识的品质,其创作会更富有深度和力度,其作品才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证和写照。
第三,遗忘“过去”,从对“现在”的关注中开创未来。不管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我们务必承认这些都已经成为不可挽留的过去,并且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过去”是以“现在”为参照而存在的。人活的就是“现在”,“现在”是人存在的第一要素,是人真实性、现实性的集中体现;当我们在向后看追忆往昔时,一方面在特意“记忆”,另一方面也在“遗忘”。“记忆”和“遗忘”共生共存,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住,人必然要有选择地进行经验重塑,这样“记忆”就以筛选的方式淘汰掉无价值和无意义的东西,留下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在这里,“遗忘”的规律在起作用。我们发现,“记忆”指向的是过去,“遗忘”指向的也是过去,只不过“过去”的内容不同而已。所以,为了“现在”要“记忆”过去,也要遗忘“过去”。“留住”记忆,遗忘“过去”,都是为了“现在”的前行,进而去开拓未来。就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而言,认真地关注“现在”、关注“当下”,才是切切实实的,只有把握住现在和当下,未来的筹划、构想和实现才不是空话。以清醒的“现实”精神面对“当下”的生活,我们才能明白自己最需要做的是什么,社会责任的履行和使命的担当才不致成为空中楼阁。从这方面说,文学的“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秉承“从现在做起”的理念,诊断自我或社会的病理,以开具疗救的药方,文学的价值也就由此体现出来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鲁迅,他给我们树立了一座真正把握“现在”的精神丰碑,他的创作表现了鲜明的“现在”时间意识。鲁迅意在强调以“过程哲学”来寻找通达未来的现实道路,而不是沉醉于“朽腐”的过去和向往于“虚妄”的未来,这里作家秉持的是“清醒现实主义”[5](P37)。鲁迅“清醒”的不仅是“现在”,而且还有“过去”,可以说正是在对“过去”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才有了他的这种执着于“现在”和“当下”的人生哲学。所以,他的作品底蕴非常丰富,给人更多的是警醒。
二、以创伤性记忆承载生命的厚重
人生追求是无止境的,人的生命往往在挑战和超越中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挑战极限和超越自我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因此,人生的过程必然会面对种种无奈、挫折甚至是失败,人会为此感到痛苦、忧郁、孤独、伤感甚而绝望,人的生存苦难性决定着人在流逝了的岁月中会有诸多创伤性记忆痕迹存在。创伤性记忆是人的心灵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人的生命的厚重感和悲怆感。因此,作家的创伤性记忆书写,承担着书写人的心灵的厚重和悲怆的使命,他们把某种创伤性记忆留存下来,是用一己的心灵之痛来成就文学的“悲剧的诞生”。戴望舒在《我的记忆》中提到,“记忆”在他“寂寥”时会“密切拜访”他,这里的“寂寥”暗示着诗人因曾经的心灵伤痛而生发起一种“创伤性记忆”,或是甜蜜的忧伤,或是忧伤的甜蜜,这些正成为诗人重要的写作资源,《雨巷》中那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正是作者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的化身。
文学是一种“苦闷的象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说明了诗人身遭不幸而情感郁积,最终不得不愤而书、屈而鸣、穷而后工的道理。李贽认为:“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6](P312)王国维指出《红楼梦》可谓是“悲剧中之悲剧”[7](P123),都是同样的道理。总体上,中国古代文论家主要谈及的是作家的人生经历与其创作动机、创作潜能和作品影响的关系,但不管提出什么样的论说,都把文人感情的郁结、怨愤、痛苦看作是创作的重要资源。无论是“发愤著书”,还是“不平则鸣”,诗人的书写往往是基于其内心深处的创伤性记忆,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即是对这种创伤性记忆书写的最好的概括。
中国文学中的创伤记忆书写,还表现在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叹和忧愁。时间如流水,昼夜不停息,孔子发出了“逝者如斯”的慨叹。后来的作家留下了诸多沉郁、悲凉或豪壮的诗篇,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8](P42)的忧患;有“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9](P36)的惋惜;有“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10](P5)的苦恼;有“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11](P96)的忧愁;有“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12](P66)的悲伤,等等。这里有着诗人对时间流逝的深邃的哲学洞见:“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13](P1183-1184)——时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14](P243)——时间的不可逆转性;“今朝零落已可惜,明日重寻更无迹”[15](P330)——时间的瞬逝性。时间的无情,生命的苦难遭际,这一切让诗人常常沉入对往昔生命的感喟之中。曾经的记忆就这样充满伤感地缭绕于诗人的脑际,记忆由此也让诗文本身释放着美丽的光华。
相对而言,创伤性记忆的生成更多的是社会苦难因素所致,比如魏晋时期就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灾难催生了人的“自觉”,也催生了文的“自觉”。一次次险恶的政治迫害,一个个家庭毁灭无存,一桩桩不可预期的苦难,带给诗人深广而深沉的人生喟叹、恐惧和哀伤。于是我们可以理解,“竹林名士”表面上的放荡不羁、风流倜傥,实质上内心却无比孤独、苦痛和烦恼,甚至颓废。阮籍一句“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16](P312)仿佛让我们听到了诗人那种孤独煎熬时的愤懑心跳以及对理想知音的深情呼唤。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13](P902)一句,说尽了古人登高望远的苍凉和悲壮,那往事如烟的诸多回忆,世道艰辛的深沉体验,壮志未酬的无边痛苦,历史兴亡的反思慨叹,积郁成忧的失落之感,全然在“登台”之后的一瞬间喷涌而出,抒发了一种博大沉厚的孤独感。这里的“回忆”应该是一种创伤性记忆,这种记忆让诗人心中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虽然豪壮但绝不悲痛。或许正是由于诸如魏晋名士等诗人的创伤性记忆的共鸣和感召,尤其是这种高洁心灵的烛照,才有后来无数人文精英知识分子自觉地担当起对自由生命的真诚呵护,或谋求国富民强的积极参与之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留下某种创伤性记忆。“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家以敏锐的感悟力和记忆的穿透性,对历史造成的精神创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是因为经过了“伤痕——反思——寻根”这样的心路历程,历史造成的创伤性记忆才成就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韩少功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抛到了穷乡僻壤,这一段经历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深刻的“伤痕”记忆,这种“伤痕”记忆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成了一代人“心灵创伤”的标志。韩少功把这种“伤痕”记忆的成因归结为“多因了苦难”,“时光总是把苦难渐渐酿出甘甜,总是越来越显示出记忆的价值”[17](P16)。
从心理学角度看来,创伤性记忆不单是个体欲望无法实现带来的生理上的伤痛,也不完全是政治或自然灾难给人的躯体造成的伤害,而是在这些外在苦难因素作用下人的心灵遭受的更深层的痛楚和创伤,这种创伤在文学创作中是经过主体审美升华后所沉淀下来的一种审美经验。所以,进入文学中的创伤性记忆具有主体超验的性质,它已化为一种精神,其底色是“冷”的、沉重的,但因负载着对生命、对人类命运的关爱,故会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产生“炽热”的感动。强调创伤性记忆的审美价值,是为了凸显文学从生存的苦难性出发的励志意义,但并不是说不再书写那些美好的快乐的“暖色调”的记忆。实质上,文学创作中的“冷”记忆与“暖”记忆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因为真正的人生欢乐背后常常依托着一种透明的、穿透性的“忧愤之思”或“悲剧精神”,往往是那些充满“悲剧精神”的作品更能给读者带来独特的愉悦感。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诗人就是一个闷闷不乐的人,他在内心郁积着深深的愤怒,却能靠他那构造独特的双唇,使得通过它们的呻吟和哭泣声变成让人欣喜若狂的音乐。”[18](P3)由此看来,作家的神圣使命就在于他必须直视人类生存的苦难,必须对人以及人类在抗争苦难过程中所遭受的心灵痛楚作出敏锐的观照与判断。要之,作家应以这种“难度写作思维”[19]回归悲剧意识,营造种种生命的感动,这是文学审美价值呈现的一种重要路径。
三、凭借诗意的记忆符号安放“存在”之灵魂
如果以上回答的是“为什么记忆”及“记忆承载着什么”这两个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如何记忆”或“凭借什么来记忆”的问题,亦即“记忆的媒介”是什么的问题。戴望舒的诗《我的记忆》告诉我们,诗人记忆的媒介或载体可以是“烟卷”“笔杆”“粉盒”“木莓”“酒瓶”“诗稿”“灯”“水”等日常物品,这些日常物品常常以一种符号的形式成为诗人进入回忆的“诱因”。所以,从生存的符号性物品出发,我们能发现记忆得以生成的媒介所在。在此,笔者认为,作家记忆的媒介主要集中在“象”和“言”上,当然也包括身体等元素。
首先,感性的“象”。《周易·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的解释是“得意而忘象”。在古代中国,不管是“言—意”,还是“言—象—意”,都把“意”放在根本地位,“言”和“象”只是表达“意”的手段和工具而已。这些基本上可看作是中国古代人对文学文本层面的认识。就“象”特质的现代阐释而言,“象”应该是外在的、客观的、视觉可观的,所以“象”在视觉思维作用下,经主体想象、情感和理解等心理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意象”,这里负载着作家复杂的审美经验。所以,“象”成为作家传达审美经验的工具,此时的“象”已成为人精神的载体、自由心灵的栖息地,文学正是立于此而获得了“超越”的特质,故文学是“超象的”[20](P175)。作为精神载体的“象”成为一种工具,也可以说是一种“媒介”。作为文学记忆媒介的“象”,具体是指可观可感并有作家审美经验凝聚于此的“物”——自然景物或社会事物。所以,那些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自然景物、沉睡多年的古代遗迹“断片”,以及丰富多样的日常物品、公共节日场景、民俗仪式等都可纳入有关“象”的文学记忆媒介范围之中。
自然物象及日常物品会经常成为文学记忆的媒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母题”意象与自然万物密切相关,有着明显的生态寓意,日、月、山、水、花卉、鸟兽等等,都可以入诗入画,在文学书写中被赋予诗性气质。事实上,近在眼前的自然物象往往会成为作家情思飞扬的“关联物”,作家据此借“物”起兴,或睹“物”思人,或借“物”怀“古”,记忆中那些与此相关的甜蜜或忧伤往事会浮现在眼前,此时的“物”已经具有象征或暗示意义,成为记忆生成的“诱引”和传媒。鲁迅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吃过的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等蔬果,这些食物成为他“思乡的蛊惑”[21](第2卷,P230);夏丐尊案头放置的“钢铁假山”——这个“‘一·二八’之役日人所掷的炸弹的裂块”——因时常让他想起那些民族屈辱的历史,而成为他“最有重要意味的东西”[22](P107)。这样的“蔬果”或“钢铁假山”已成为作家记忆的媒介,它们以特有的意味打开了作家记忆的大门,成为安放作家记忆和生命的载体和媒介。相对个人记忆的载体和媒介而言,历史遗迹、公共节日场景和民俗礼仪,更多打开的是集体记忆之门,彰显着族群和公众团体的共同记忆,因而具有文化记忆的叙事功能。历史遗迹经过岁月的沉积或淘洗,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给人带来时间的冲击感,那些历尽沧桑残留下来的遗迹“断片”更易让人进入历史的时空隧道,作家在古迹、文物中所遇到的是已经被遗忘的灵魂,记忆的复活使过去的灵魂返归,与当下的心灵相遇或共鸣,作家的生命由此获得了新的升华和再生。
其次,抽象的“言”。相对于感性的“象”,抽象的“言”是不可忽视的记忆媒介。我们知道,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存在”的家,凭借语言符号来把握世界的文学,其描写具有无比的广阔性和丰富性,这一点相对于重于感官经验的“象”来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文学有“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据闻一多先生考证,汉语中的“诗”字有3层含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23](P185)按照这一观点,“诗”在最初阶段是为了“记忆”,因此,“诗”首先是记忆的载体和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本身就伴随着回忆,语言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记忆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正如哈布瓦赫所说:“每一个(被理解的)词语,均伴之以回忆。不存在没有词语对应的回忆。我们谈的是浮现于脑海之前的回忆。正是语言,以及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习俗系统,使我们每时每刻能够重构我们的过去。”[24](P290)
“诗”与“言”会以记忆媒介的方式让我们记住个人和民族的过去,也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距离而回到“安放”着个体或集体记忆的地方。海外华侨或远离大陆的作家们对作为母语的汉字相当敏感,看到汉字他们会有回乡的感觉,使用汉字书写会唤起他们的“乡愁”记忆。诗人余光中在《听听那冷雨》中写到:“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25](P248),字里有“土”,“土”承载了华人所有的记忆和希望。同时,“雨”打在土地上激起了一种特别的“土腥气”,那“腥气”让地上地下的记忆皆蠢蠢蠕动,于是诗人存封多年的“记忆”复活了,并随着“雨”打泥土的音乐旋律一起飘扬开来……遥远的“记忆”可能象“雨”一样冰冷而潮湿,但怀乡本身却是很温暖的。由此可见,延续汉字的生命力也就是延续着我们个体的真实存在及我们民族的未来。
第三,诗意栖居于记忆符号。纵然感性的“象”和抽象的“言”因其自身的优越性成为文学记忆的媒介载体,但最终在“意”被表达后还是被“忘”了——文学因这种“忘”的“超越性”而具有独特持久的艺术生命力。然而,最终的“象”和“言”并没因此被抛弃掉,而是仍然客观地存在着。这里的关键是作家以想象和情绪的逻辑使这些媒介载体迭映上了主体自我的色彩,此时“象”与“言”已以符号的方式成为主体记忆的媒介:“符号的记忆乃是一种过程,靠着这个过程人不仅重复他以往的经验而且重建这种经验。想象成了真实的记忆的一个必要因素”[26](P81)。另一方面,主体诸多情绪中的情感心理因素对载体的变形和重塑起到更大作用,因为,“艺术是情绪记忆的生动表述”[27]。由此,作家以善于感受的心灵,用身心去怀抱和体验这些客体,使之成为渗透了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并最终使自我个性在这些客体上得到了确证和实现。此时的媒介载体应该真正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当然,这其中的“意味”并不单纯是个人情性,还包括更多的社会内容。事实上,那些记忆媒介之所以具有这种丰富的“意味”,从生存哲学上来讲,是因为人、尤其是作家的生存在本质上是诗意的,作家是以诗意的方式把自己存在的灵魂自由地安放于此。人虽然现实生存上充满着苦难,但内在心灵深处却无比渴望自由,即诗意的“栖居”。在这里,“栖居”的不仅是在感性的“象”上,也在抽象的“言”中,因为语言是灵魂得以安放的所在。
余论
基于生存的美学维度,建构文学记忆的本体内涵,意在从人之生命内核处窥视记忆的本体特征。但作为文学艺术创作资源的记忆本身不是始终隐藏于内,而是要复活出现在当下,记忆主体必须以“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与“过去”进行照面。于是,“记忆”来到了眼前,介入了我们的生存现实。由此,文学也介入了现实,在对现实的言说中,发挥着它应有的功用。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文学的本质不仅仅在于强大的想象力,而且还在于勇敢的介入。戴望舒在《我的记忆》中描述的“记忆”情态,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他的“记忆”在与眼前的媒介发生了对接后,一切都近在眼前,“过去”的现实介入让诗人感到无比惬意,同时诗人也以这种“介入”的方式观照着周围世界。记忆的复活,文学的介入,彰显出文学记忆的诸多功能:见证历史、认同身份、审美怀旧、疗救伤痛和启蒙人性等。反过来说,一旦作家基于诸多负面性的生存状态——相对于多维性的断裂,相对于苦难意识的及时享乐,相对于诗意符号栖居的单调和乏味——来重塑记忆,记忆的美学功能丧失,那么文学就有可能失重,变得浅薄或轻浮,文学危机也就可能成为时下人们最为担忧的精神现象之一。事实上,在消费文化渐趋盛行的时代,越演越烈的商品化、技术化以及工具理性,造成人和种种现实存在的严重异化,使得人的生存观念与现实的冲突日益激化,生存不堪重负,生存的美学份量弱化,随之而来的是对记忆资源的选取偏离了基本的价值准则,文学记忆的美学功能淡化,文学正遭受着空前的压制,文学危机似乎就近在眼前。如何激活记忆的美学功能,如何彰显文学的时代力量,帮助作家纠偏负面的生存观念,正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难题。或许,基于生存的美学维度来建构文学记忆本体内涵的价值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