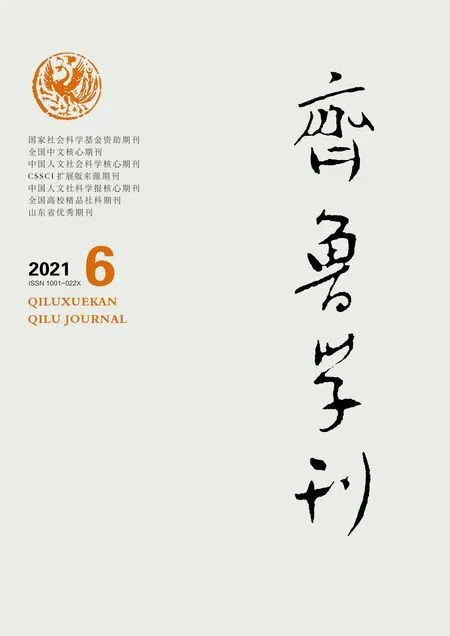南宋佛寺文中的山水、乱离书写及理学蕴涵
李晓红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佛寺文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慧远所作的《庐山记》和《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两文一叙安世高神庙,一涉石门精舍,均记山川气象与游赏逸兴,为后世佛寺文创作奠定了绘清景、叙佳游的基调。北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则确立了佛寺文的基本范式,一篇之中往往涵盖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寺内建筑、人物事迹等基本要素。唐朝时,段成式《寺塔记》及其他寺碑文崇尚辞藻,一改质朴笔法,为佛寺文增加了新的色彩。递至宋代,在多种因素的促发下,佛寺文创作臻于全盛,据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计有佛寺文两千余篇,其中佳构众多,作者囊括僧俗名流。目前学界对北宋佛寺文已有研究,如赵德坤、周裕锴《济世与修心:北宋文人的寺院书写》[1]等,但对南宋佛寺文尚少关注。南宋佛寺文对山水胜域、时代变局、理学思潮等有多方面的反映,具有重要的文学和社会文化价值,本文对此试作探讨。
一
对于寺院地理位置以及寺内建筑的描写,是佛寺文创作中的一大传统,这类书写在南宋佛寺文中亦频繁出现,且极富观赏性,其中又尤以对山巅水涯之秀丽风景和雅聚同游之畅意骋怀的描绘最为动人。事实上,印度早期佛寺祇园精舍、竹林精舍就已经融入了山水园林成分,也就是说,自有佛寺起,山水即是佛门建筑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借助大自然的灵山秀水,澄澈心识,返照本心,体会湛然佛理,一直是僧徒日常修行中的重要内容,是以宋人赵抃有“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次韵范师道龙图》)之叹。正因一众名寺都择址山野密林,所以南宋佛寺文频频模山范水,更有通篇描绘山水之作,即便有些作品不专意于描写寺院环境,其叙述寺庙地理位置时也往往会对自然环境进行概括性描述。
在南宋佛寺文中,山水幽姿常用来点缀文华。王铚《包山禅院记》称寺址依山傍水,“烟云生于步武,阴晴变于几席”[2](第182册,P180),景色秀丽宜人;刘宰《白云精舍记》状寺院之景曰:“水光山色,上下澄鲜,暮霭朝霞,迭来献状” [2](第300册,P156);释仲皎《梅花赋》赞寺中美景云:“孤山寺侧,玩回雪以无殊;却月观前,学凌波而不浅”[2](第182册,P313);郑清之《拨赐田产记》亦图绘寺景:“负城阙而挹湖山,宅幽宾胜,足以囊括云水,颐指烟霞”[2](第308册,P256);洪迈《重建佛殿记》篇首即叙紫金寺优越的地理位置:“真能雄跨东南二百州,如宸章所表揭者。千帆下来,万客鳞萃,鱼龙之所凭怙,人天之所宾悒,古今推胜,无得拟议”[2](第222册,P79)。此类只言片语的山水描写,亦足以动人心目。
当然,一句话的点染往往无法穷尽寺中的山水妙韵,南宋佛寺文中最常见的是大段的景语勾勒,如杨万里《永新重建宝峰寺记》称赞此寺“饮山之翠,纳山之光,领山之要,里之人乐游焉”,并对山峦有聚焦式的描摹:“远而望之,俨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委,秉珪佩玉,坐于庙堂之上,使人一见而敬心生焉。迫而视之,澹乎若岩岳幽人披薜荔,带女萝,餐菊为粮,纫兰为佩。”[2](第239册,P349)比喻形象生动,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释道虞《妙严院碑记》先精心图画周遭环境:“步西北岗,登斗峰,山高千尺,松植万株。山之巅有蟾蜍之窟,山之腹有松桧之树,山之根有壻谷之水”,后赞寺院“地望爽垲,卜筑奇胜,疏筠翠柏,烟笼云霭,面揖斗峰,在目睫许。嘉木千寻,断崖万仞,灵禽韵美,野草花香。四顾山川,风景佳丽,殆胜地也” [2](第302册,P419)。释宝昙《仗锡山佛记》对寺内山水有移步换景式的呈现:“径雪豆而西四十五里,皆层峦叠嶂,颠崖悍石。行人被榛莽,踏沮洳,践蛇虺,登危陟险,始即山之趾焉。山断溪横,北岸林光溢目而为秀发……涉桥而北,一亭岿然……自亭而上历十八折,杉松荟翳,如在青罗布障中行。至二十里云,一池靓深,出墙阴才数十步武耳。”[2](第241册,P182)寺内佳景一一现于目前,使人顿生亲临目睹之感。
相较北宋而言,在南宋佛寺文中,通篇写景之作大为减少,但亦不乏佳构,释道璨的《饮绿阁铭并序》颇有代表性,其云:
闰藏主结阁湖光山色间,请铭。予摭东坡语,扁曰“绿饮”,又从而为之铭。铭曰:谓绿可饮,山高奈何。山果高哉,嫩绿浮波。夜雨新霁,晓光融液。翠如泼醅,不压自滴。倚阑一笑,和风薰人。呼吸咽嗽,百体皆春。松在屋头,竹在屋角。招之斯来,汝酬我酢。踏月打门,客何人哉?我醉欲眠,君去勿来。[2](第349册,P368)
山间之空翠,在王维诗里尚无具体观感,只道可湿人衣,在道璨笔下则可视、可感、可饮。视觉中的绿色化为味觉之良醅,使人仿佛置身翠色漫天、伸手可掇的饮绿阁中畅饮天地精粹,其巧思妙感,有东坡风致。除苏轼之语外,道璨此篇还化用了辛弃疾、陆游、陶渊明、李白等人的成句,可谓调遣随心,运化无痕。“和风薰人”“百体皆春”等语营造出的圆满境界以及与松竹为伴的空寂心态,更为文章增添了禅的韵味。这种美的境地,恐怕唯有长久居寺、潜心世外之人才能领悟,僧人们以虚静的心灵观照自然时,所得之景往往超越世俗。豫章大梵寺名动天下的青屏列岫 [2](第357册,P99)、北山鲍家尼庵名倾京城的梅屏[2](第298册,P224)以及天池雪屋韶禅师“凿池引泉,环以幽花细竹,夷犹其间” [2](第349册,P406)的明月庵概皆类此。无怪乎周紫芝在评价僧人的山水作品时赞道:“乃知其幽深清远,自有林下一种风流。”[3](卷2,P675)叶谦《明因教院记》、幸元龙《超果寺水石记》等亦通篇写景,笔调清嘉,但与道璨作品相比,似乎少了那么一些佛禅境界,文中更多的是对自然山水的客观呈现,这也是文人和僧人在模山范水时普遍存在的差异。
写景之外,南宋佛寺文中还包含游目骋怀的成分,这类内容常与山水景色的描绘同时出场,情景交融,意趣盎然。王日益《崇寿院敕额跋》记载了与朋友远眺寺景的佳趣:“暇日领客登眺,溪桥横卧,野木旁拱,倒景流光,下上相属。前峰后巘之奔伏,远洲近溆之分合,霁日阴云、朝霞暮烟之开敛吞吐,莫不尽于几席之上,穷天地之奇变,遗氛埃之浑浊,长啸激烈,谷应水涌。”[2](第301册,P322)程珌在为净慈山报恩光孝禅寺所写的寺记中亦提及僧俗雅聚的诸般妙处:“或偕释子道人,俱度风篁之岭;或与高人胜士,同登月桂之峰。或忘归而屡宿石桥,或乘舆而独瓢冷涧,或遇葛翁于北坞,或逢仙许于南泉,或赓遵式之留题,或听智僧之长笑,或近见法真之张宝帐,或遥瞻释遇之上骊峰。”[2](第298册,P130)曹勋为赏山水之胜、云霞之鲜建造了清隐庵,并延请僧师照看,他的记文中亦有大段游目丽景、剖抒心怀之语:“每梅雨霏空,断霞照晚,清风拂水,白月在波。樵歌渔唱,递发于烟云之中,轻帆短棹,往来于菰蒲之末。至若中宵月好,微澜不兴,湛若琉璃,碧浸百里,不知身世在尘埃间也。”[2](第191册,P87)字里行间满蕴着超逸之趣。此外,光孝寺为唐相房融所建的笔授轩,能仁寺为黄庭坚所建的清凉轩,本觉禅院为苏轼所建的三过堂,乃至上镌陆游长短句、张孝祥书法的甘露寺多景楼,也皆为僧俗雅聚高会、品题岩壑的专门场所。这些作品无论是记众人伴游的吟啸,还是写孤身独赏的悠然,都呈现出一种高雅的格调,大自然的山水在澄澈灵魂的观照下被赋予了优美的风神。
南宋佛寺文也多描写寺内的诸般创设,虽然南宋国势不及北宋,但当时佛寺依然维持了表面上的繁荣,各地寺宇梵宫壮如王室,规模宏大,此种情况正如陆游《法云寺观音殿记》所述:“予游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往往历数百千岁,虽或盛或衰,要皆不废。” [2](第223册,P116)轮奂宏壮之外,在南宋佛寺文的书写中,此时寺院的形貌似乎高度趋同,览千寺如同观一寺。阅读此时的佛寺文,常会看到对寺内构造的套路化描写,如刘克庄《重建九座太平院记》叙寺内建筑曰:“未几,曰殿,曰钟楼,曰经阁,曰罗汉堂、大士堂、僧伽堂、祖堂,曰法堂、僧堂、寝堂,曰方丈,曰官厅,曰庳堂,曰郁密寮、卢隐寮、寿寮,曰浴院,曰门,曰庑,起乙卯冬,讫己未春,俱复旧观。”[2](第330册,P305)朱舜庸《方山上定林寺之记》中的描写大致相类:“无何,有殿以奉佛,有堂以会法,有室以安众,以至门庑庖湢,莫不毕具。”[2](第319册,P273)不仅文人这样描写寺院建筑,僧人如释居简、释道璨等在佛寺文创作中也多是这样处理。大势虽如此,南宋佛寺文中还是塑造了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佛门建筑,陈宜中《大仁院佛阁记》写该寺有镌刻洞石而成的七百余尊罗汉像,又建宝阁覆盖其上,远远望去,“轮奂崔巍,如在碧落”[2](第352册,P462),观者油然而起欢喜之心。陈宜中声称这是他经行四方见过的最杰出的佛阁,目眩神骇之余,不禁赞叹不已。楼钥《天童山千佛阁记》称寺内新建七座阁楼以安放千佛,阁成之后,“自下仰望,如见昆阆,梵呗磐钟,半空振响。徜徉登览,四山下瞰,河汉星斗,如在栏槛”[2](第265册,P27)。尤袤《轮藏记》写寺院寻常规制外,又称“上为毗卢遮那,宫殿楼阁充满虚空境界中,为善财参五十三善知识,因地下为八大龙神舒爪运肘之势,其外覆以大殿,广容其藏”[2](第225册,P243),经过之人无不动心骇目,以为是神力所致。
寺周山水与寺内创设在很多时候是无法作截然区分的,楼钥《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中所绘图景即是如此:“余尝登含晖之亭,如踏半空,左眺云海,视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历历如指诸掌,真绝景也”,“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十年,犹属梦境”[2](第265册,P32)。能让作者在二十年后仍感觉历历在目,并时时见诸梦境,可见其山水形胜之佳,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二
南宋之世一直笼罩在靖康失国和四郊多垒的阴影中,处境较北宋更为艰难。于外,金、西夏、蒙古等国始终虎视眈眈,南宋朝廷与金人作战多以失败收场,在与蒙元的较量中更是惨罹亡国灭祀之灾;于内,南宋百姓不堪科敷之扰,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方外佛寺成为安顿身心的极佳场所,人们纷纷逃到佛寺躲避战火,消解苦痛。然而,在陆沉、板荡的乱世中,佛寺也时常被战火波及,大量寺院化为丘墟,世外佛寺亦染世间乱离底色。南宋佛寺文中的乱离书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描绘了战争对房屋、城郭的破坏,也展现了战乱对士人心灵造成的创伤,同时还表现了仁人志士呼唤中兴、奋起抗敌的爱国情怀。
金兵的侵凌,使宋廷遭遇了“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4](P76)的灾祸,南渡以来的战火、流离书写频见于佛寺文。曹勋《仙林寺记》称作为帝王驻跸之地的临安就屡遭战火:“建炎及绍兴间,三经戎烬,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复井邑。”[2](第191册,P85)陆游《泰州报恩光孝禅寺最吉祥殿碑》称泰州地区亦经历了数次战祸:“自建炎后为盗区战场,中虽息兵,然犹鬼啸狐嗥于藜莠瓦砾中,自官寺民庐,皆略具尔。未几,复有绍兴辛巳虏祸,前日之略具者,又践蹂燔烧,涤地而尽。”[2](第223册,P178)李纲《邵武军泰宁县瑞光岩丹霞禅院记》记录了福建泰宁县战后的惨状:“今年(建炎年间)春,盗起邻郡,余徙长乐,未阅月,邑遭兵火,焚爇殆尽。”[2](第172册,P217)祖大武《广严寺记》中提及叛将李成对江左地区的侵扰:“至建炎间,李成以巨盗寇掠江左,蹂践殆遍,其凶徒尝囤聚于寺南之二十里。”[2](第325册,P288)释居简《钦山禅院记》描绘了荆湖地区战后的凋敝景象:“建炎末,荆湖南北列刹烬于贼,环千里为盗区”,“时人命如叶,州郡闭关自固,坐视剽掠焚荡,方迂辨曲谈,聊忍须臾”[2](第298册,P364)。释道璨《崇寿寺记》对理宗时期波及湖北、浙江、江西三省的战争场面有所记录,称“时开庆元年秋,狂寇偷渡江许,伏黄州,十一月袭寿昌,犯兴国,窥南康。豕突深入,建昌当贼衢,受祸甚烈”[2](第349册,P367)。刘辰翁《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禅寺记》则描绘了吉州衰败零落的情形:“会当干戈,南北纵横,岁俭人饥,豪右衰落,施者犹丐,工价腾涌,官无阖庐,败不遑救;又于其间楼船驾海,斩伐百祀,六合为炉,铁牡欲飞。”[2](第357册,P188)文中所载不仅是吉州一地的状况,也是南宋末世图景的写照。南宋建国以来,战争不断,且波及地域十分广阔,又以南渡初期和南宋末年最为集中,其间既有南宋朝廷和金、元等国的大规模战争,又有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以及部分官军的叛变、劫掠。战争的阴霾长久笼罩,使南宋人始终摆不脱关于战乱的伤痛记忆,郁结在心,发而为文,这正是南宋佛寺文中出现大量乱离书写的主要原因。
世外佛寺其实也难逃战火的冲击,正如释道璨《崇寿寺记》中所言:“西北用武,征调繁兴,江淮间无不废之寺。”[2](第349册,P367)释正觉《僧堂记》亦有相似的记述:“建炎之末,人病乱离,湘汉江淮,兵火燔掠,尊宿丛林,没芜十八九。”[2](第183册,P3)大量佛寺在无情的战火中化为灰烬,又如孙应时《法性寺记》称“建炎庚戌,是寺毁于兵,大士有灵,栖塔仅存,余皆瓦砾之场也”[2](第290册,P93);释希颜《重建圣寿教寺记》称“于是初经建炎兵火之后,寺宇焚荡,瓦砾填委,蒿艾萧条,春禽昼呼,鼪鼯夜啼,已为榛莽之墟。僧徒休足之地,皆编茅以弊风雨”[2](第183册,P376);涂禹《重修澄心寺佛殿碑记》亦载“建炎乙酉,北虏乱华抵江右,寺空于一烬,缁徒鱼惊鸟溃”[2](第306册,P51)。佛寺文创作以佛寺为主要关注点,寺院毁于兵火之事遂被频频提及。
战争造成的人口伤亡往往更令人触目惊心。叶梦得《建康掩骼记》叙建炎兵火之事甚详,金兵入城后诛杀老弱,大肆屠掠,纵火烧城整三日,战火过后,建康城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其云:“凡驱而与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于烽镝敲搒者盖十之四。城中头颅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伤残宛转于煨烬之间,尤有数日而后绝者。”[2](第147册,P336)南宋朝廷收复建康后,高宗下令收敛死难者遗骸共计八冢,尸骨全体者四千六百八十七,肢体不全者七八万,建康城内原有的十七万人口或逃或亡,几成空城。洪迈《重建佛殿记》中也写到了生灵涂炭的情况:“当绍兴之季,戎马饮江、暴骨堆莽。”[2](第222册,P80)当时战争之惨烈,昭然可见。洪适《水陆疏》对大量百姓死于非命、曝尸荒野、无人收葬的惨状亦有展现:“或家屠于剧盗,或命绝于凶年,或析骸于灶觚鼎耳之前,或蹀血于车轮马足之下。豚无掩豆,若敖氏之鬼长饥;爪不表犀,冥漠君之冢何在?”[2](第214册,P159)除剥夺生命外,战争还给尚在人世者带来了许多生存困难。冯檝《净岩和尚塔铭》中描绘了兵戈过后寺僧缺粮以致饿死的惨状:“时以襄汉才复,百里绝人,荆榛塞路,虎狼交迹,山顶僧行散逃馁死,所存不过百数,日餐野菜橡糜以度朝昏,供利阻隔,屋宇堕颓,庄夫耕具,十无一二。”[2](第181册,P153)受施主供养、与战争距离相对较远的僧人们尚且四处散逃,饥馁至死,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更是可想而知了。
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需要抚慰,从南宋佛寺文来看,人们安抚心灵、疗愈创伤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求助佛的力量,通过重建佛寺、做法事等超度亡魂,安顿生者。叶梦得《建康掩骼记》中提到高宗皇帝下令由城中五处佛寺总揽收葬骸骨、超度亡魂之事,这场大规模的掩骼活动在朝廷和寺院的通力合作下得以完成:天子亲下诏书,朝廷拨付相关款项、派出专门官员监工,礼部特批度牒,寺院总揽葬事佛仪[2](第147册,P336)。李纲《潭州荐阵亡水陆疏》对南宋朝廷出面邀请僧人为阵亡将士做法超度之事也有所反映[2](第172册,P328)。佛门僧人及民间向佛信士亦有自发为战火中亡魂收骸骨、做法事的举动,释法忠《南岳山弥陀塔记》称此塔为信士郑子隆集合众檀越之力为“阵亡疫死者”所建,惟愿拯济亡魂,往生净土[2](第174册,P98)。李弥逊《宣州泾县铜峰瑞应塔记》中也提到普现居士在兵戈初定之后,辗转各地,收葬遗骸,做法事以济众生:“(普现居士)所过名山,饭僧百万众,供幽明水陆几二百会,募众诵经三百万藏。开华严场,结会一百万人。”[2](第180册,P347)曹勋《战场立经幢记》中的“经幢”亦是湛然居士为战场上丧于白刃的忠魂所做,他希望通过创立经幢、刻佛经呪的方式,让这些亡魂拔离痛苦,托生净方[2](第191册,P90)。朝廷还出资建立了一系列带有救济性质的场所,供年老体弱以及战争中肢体受到损伤的人群居住,并延请僧人代为照管。这些场所名目不一,诸如居养安济院、养济院、安养院、寿安院之类。
在佛法度化之外,南宋的仁人志士还有另外一种疗愈战争创痛的方式,即提振精神,直面痛苦,呼吁抗金杀敌,高扬爱国情怀。岳飞的佛寺文极具代表性,他的佛寺文中均激荡着一股抗击金人、恢复中原的豪情:
余驻大兵宜兴,缘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2](第196册,P350)
余自江阴军提兵起发,前赴饶郡,与张招讨会合。崎岖山路,殆及千里,过祁门西约一舍余,当途有庵一所。问其僧,曰:“东松”,遂邀后军王团练并幕属随嬉焉。观其基址,乃凿山开地,创立廊庑,三山环耸,势凌碧落,万木森郁,密掩烟甍,胜景潇洒,实为可爱。所恨不能款曲,进程遄速。俟他日殄灭盗贼,凯旋回归,复得至此,即当聊结善缘,以慰庵僧。绍兴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飞题。(《东松寺题记》)[2](第196册,P351)
岳飞奉旨趋阙,复如江右,假宿幽岩,游上方,览山川之胜,志期为国速欲扫平黠虏,恢复舆图,迎二圣于沙漠,辅圣王无疆之休。绍兴三年十月初三日题。(《乌石寺题名》)[2](第196册,P352)
这三篇作品均写于南宋初创、兵戈未息之时,岳飞经过佛寺原为憩息、游目,但他所思所想无不与抗金杀敌有关,其殷殷爱国之诚,于方外之地亦未尝有一刻暂歇。文中满溢的英雄气,对恢复故土的高度笃定和执著追求,无疑会对在战火中失去家园和亲友的人们有着巨大的激励和安抚作用。相对而言,做法事超度亡灵对当时之人的心理创伤来说是一种消极的疗愈;岳飞等英雄人物的抗金壮举和报国热情,则会给广大民众带来直面痛苦、摆脱困境的勇气和力量,能起到一种更为积极的疗愈作用。
在南宋社会,与岳飞怀有同样报国热忱、立志北定中原的不乏其人。史浩《刘忠显公祠堂记》高度赞扬了刘韐在靖康之难中誓死捍卫疆土的忠义之举,热切盼望早日廓清中原,可以到北方的刘韐祠堂瞻仰示敬。此文作于乾道五年(1169),史浩时任尚书右仆射,他的这一愿望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心声。岳飞之孙岳珂在《重修忠简宗公功德院碑记》中也抒发了“二圣之不还,中原之不复” [2](第320册,P368)的沉痛慨叹。袁甫《衢州光孝寺记》通过对“孝”的阐释,指出“中原赤子,久苦烽燧,版图未归,仇耻未刷,卧薪尝胆,亟思报复,以慰祖宗在天之灵,此志未尝须臾忘也”,并称此孝“塞天地,横四海”[2](第324册,P35)。裘由庚《云盖龙寿禅寺复田记》更是勉励该郡宰邑“北望中原,志清河洛,得时与位,挈舆地而归本朝,使乃祖忠简公义不臣虏之志,一伸于六七十载之后,则功烈伟矣”[2](第334册,P439)。林希逸《重建永隆院记》则对徒洒亡国之泪、却不将“恢复”之事付诸行动的南宋官员提出了辛辣的批评:“吾国士夫能洒新亭之泪,而未能还洛阳之钟簴,湖山豢佚,若以为固然。” [2](第336册,P28)凡此种种,或慷慨激昂,或痛心疾首,皆可见南宋士人丹心为国的赤诚。
南宋高僧也多有爱国言行,大慧宗杲阐发了“菩提心即忠义心”(《示成机宜》)[5](P912-913)的思想,在当时禅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南宋佛寺文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方外僧人在战火兵戈中坚毅、果敢的身影。冯檝《净严和尚塔铭》记载了建康兵火中净严和尚以淡定从容的风范护卫了整座城池的事迹,其时,城中缺粮,敌寇扬言屠城,净严镇定自若,节食分赡大众,且佛事不辍,最终“(贼寇)攻既不利,而曰城中果有异士,遂引去”[2](第181册,P153)。周必大《赣州宁都县庆云尒禅师塔铭》也记载了尒禅师的英勇、慈悲之举:“会齐述婴城叛,缁素宵溃。师曰:‘我去,寺必墟。’止不动。阅百二十日,贼屡欲纵火加害,师随机解免,舍匿士庶千计,亦赖以全。”[2](第233册,P169)这些僧人能够在危难时分挺身而出,既是受到了大慧宗杲忠义爱国思想的感召,其实也是危急状况下迫不得已的举动。
三
理学自诞生之初即持排佛态度,北宋理学家们的排佛态度尤其坚定,从未给寺院撰写过只言片语以寄褒奖之意。南宋以降,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理学家收到寺院邀约,切实参与到佛寺文的创作中。在一千多篇南宋佛寺文中,理学家创作的大致有四百余篇。这些作者的阵容不可谓不强大,杨时、胡寅、邓肃、朱熹、杨万里、楼钥、陆九渊、叶适、魏了翁、真德秀、林希逸、刘辰翁等理学名家皆在其中。此外,一些虽说不上是理学家但受理学浸润的文人也频繁在佛寺文中宣扬理学观念。这使得南宋佛寺文中洋溢着浓厚的理学气息。
理学家的佛寺文虽对佛门创设以及僧师德行有所表彰,但感慨所系、主旨所归往往都落脚在理学上。总体来看,南宋佛寺文中的理学蕴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基于儒家立场誉美佛事。出自理学家之手的佛寺文大多是在寺院再三邀请下创作的,供刻石记功之用。寺院为了得到名士的记胜翰墨,常有跨越千里、精诚求文之举,又常有亲朋助请之“增上缘”,此外,很多僧师与求文对象素有私交,这就使得那些本不情愿创作佛寺文的理学士人也不得不勉力为之。南宋理学家的佛寺文中占比最大的内容是对合乎儒家道义的释门诸事的褒奖,但理学家们往往会在文章开头或结尾处亮明儒者身份。胡铨《新州龙山少林阁记》称“余非学佛者,与浮屠之说绝不通晓”[2](第195册,P365),写作此文只不过是为了嘉奖寺僧乐闻儒道;罗颂在《古岩经藏记》中称“抱周孔之书而熟味之,以究夫性命之极。万一有所自得,而后考佛之书,取其与吾儒合者,明著焉以授之,庶乎其有补”[2](第254册,P351),他为寺院撰记乃因佛书与儒家之旨有相通之处;曾丰《重建华严寺记》文末称:“释学,予不知也。概如俨以吾道,不负其师,所属近孝,盖可书也。况复诿曰:为国祝颂近忠,为民祈祷近义”[2](第278册,P2),他应允作记也是因为佛门内敬师、祝颂、祈祷之事与儒家的孝、忠、义等理念相合;陈亮之所以为普明寺置办田产并撰文记事,“亦以见买田之议非溺于因果,而出于天下之公心也”[2](第280册,P63);吴柔胜《正觉寺记》亦称“夫释氏之学,儒者不能知”[2](第290册,P229),他因嘉奖僧师德行之坚忍才为之作记;刘宰《京口正平山平等寺记》文末亦明言“余儒家者流,口不读释氏书,既为清识其始,复为清诵所闻。若曰命之矣,则三纲五常之所以维持斯世者”[2](第300册,P98),他作记文实因佛说与儒家伦理同有维持世道之效;王应麟《广恩崇福寺记》亦称记寺非为徼福,而是“君子谨终追远,无不用其极”[2](第354册,P321),佛经《大报恩篇》就多与儒家孝义相合。由以上例证可见,对儒者身份的强调是南宋理学家佛寺文的一个特点,尤其是南宋中期以后,此一特点愈为明显,这当与其时的理学发展状况有着内在关联。南宋中期,理学经朱熹、张栻、陆九渊等大儒的发扬已然成为南宋学术思想的主流[6],其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后,更是流布天下,沛然莫之能御。因此,南宋佛寺文中出现了越来越繁密的儒者身份声明以及越来越坚定的儒家立场表态。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理学家的佛寺文里,一些普通文人的作品中亦是如此。
其次,贬佛崇儒,抬尊理学地位。除对佛门事体有所肯定外,贬佛的言论在理学家的佛寺文中亦相当常见,叶梦得《胜法寺轮转藏记》批评佛寺奢靡:“佛法自汉入中国,即与其言皆来,然未尝若是侈也”[2](第147册,P339);胡寅《云庄榭记》对佛学之汗漫颇有微词,称作记是为了“晓夫吾党之溺于荒诞幻而不复致诘者”[2](第190册,P62);车若水《塔灯记》对燃灯一夜花费三万铜钱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暴殄之罪”[2](第346册,P204);安刘《钱塘南禅资福院创建佛殿记》称孔子居于陋巷而儒道愈发光大,而佛门创设蠹民伤财,难怪被视为异端[2](第350册,P17);韩元吉《景德寺五轮藏记》斥轮藏之奢殆如儿戏[2](第216册,P21);叶适《法明寺教藏序》讥“浮屠以身为旅泊而严其宫室不已,以言为赘疣而传于文字愈多”[2](第285册,P169),难以自圆其说;李昴英《净慈释刺血写经赞》认为刺血写经的举动是“妄中之妄”[2](第344册,P107)。朱熹高弟陈淳在《不允隆兴寺僧传经疏》中对佛学的批评最为全面、辛辣,其曰:“自三纲九法斁沦,而别派殊宗躏蹂,大抵化人导世,急于觊果邀功,视奉亲敬长为度耳闲谭,把诵佛持经为切身重事,需事畜之资以颐涂偶,剥塞墐之用以贲空庐。颠之倒,倒之颠,厚者薄,薄者厚,蚩蚩者浑如大寐,明明者亦被冥驱。恬习成风,迨至今日。”[2](第296册,P74)归结起来看,南宋理学家对佛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蠹民、虚妄、背弃人伦等几点上。
以实言之,贬佛实为抬尊理学地位的一种途径。除“攻乎异端”之外,理学家们还在佛寺文中直接表达对圣贤之道的赞颂。张九成《海昌童儿塔记》对儒家诸圣传承道学、拯世救民的功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具在人心,觉则为圣贤,惑则为愚不肖。圣人懼其惑也,乃著之六经,使以义理求;乃铭之九鼎,使以法象求。簠簋俎豆、火龙黼黻以发之,钟鼓筦磬、琴瑟芋笙以警之,清庙明堂、灵台辟庸以行之,使人目受耳应,心竦意萌,恍然雾披,豁然冰泮。乃知千圣虽往,此心原不去,万变虽经,此心自有余。”[2](第184册,P151)曾丰《圆觉庵记》称赞孝宗皇帝以儒家经典《周易》《孟子》注解佛经:“孝宗以孟子之觉觉《易》之圆,以《易》之圆圆孟子之觉,合而为《圆觉经注》” [2](第278册,P23),他担心个中真义不为后世理解,故作记以说明之,其抬尊儒道之意甚明。宋末谢枋得更是在《凤林新建莲堂疏》中直接说出了“天怜像教,托儒教以扶持”[2](第355册,P129)之语,尊理崇儒之意溢于言表。显而易见,此时的儒学已十分兴盛,与张方平之时的“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 [7](P113)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最后,涵养德性,阐发理学命题。在南宋佛寺文中,展现德性修养的内容非常多见,杨时《养浩堂记》通篇论浩然之义:“予尝论养气之道,以谓体、心、气、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于无,则天地与我其一乎。夫天地,其体也;气,体之充也。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理固然矣。”[2](第125册,P17)真德秀《跋钱文季少卿维摩庵记》称“其言维摩诘非有位者也,而能视人之病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禄,乃不能以民病为己责,是诘之罪人也”[2](第313册,P179),除“维摩”二字之外,其言略无佛意,旨在砥砺爱民之操行。尤袤《雪巢记》尤为个中佳篇,“雪巢”是其友林景思在佛寺内的居所,命名缘由为“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将视其虚以存吾心,视其白以见吾性,视其清以励吾节,视其幻以观吾生,即知少壮之不足恃,富贵之不足慕,贫与贱者不足以为戚”[2](第225册,P246)。尤袤对朋友的这番话以及朋友的品行都极为称赏,并在此基础上点化出了陋巷瓢饮而乐在其中的儒家道德境界。
南宋佛寺文中探讨理学命题的议论性文字更是处处可见,周行己《新修三门檀施舍名衔序》开篇即阐理:“理有默定之分,事无适然之合。人之所作,乃天之所为;物之所起,乃时之所至。古今一道,上下同流。是故逆数可以知来,前识以之垂记。符节之同,毫厘不忒。”[2](第137册,P152)后文则是在此论调基础上展开的进一步申述。胡寅《衡岳寺新开石渠记》亦于篇中阐发物、道之用以及诚心正意之说:“物无不可用,用之尽其理,可谓道矣乎,非邪?”“天地之内,事物众矣。其所以成者,诚也。实有是理,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实有是事,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2](第190册,P58)。在这大段理学论说之后,方才约略涉及寺内事体。曾丰《重兴院记》亦于文末畅发立志为善以“寓吾之大”的议论[2](第278册,P6)。叶适《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则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对战后百姓吝于布施的行为表示理解,认为“抑异以安俗,退夷而进华,又义之所出也”[2](第286册,P84)。总体而言,从南宋初年一直到南宋中期,理学家创作的佛寺文中虽常掺杂性命之说,但议论的部分尚比较克制,楼钥、杨万里、陈亮等兼具文学家身份的理学家更是创作出了一批语言精警、议论斩截的佳作。到了南宋末年,林希逸、李昴英、黄振、姚勉、刘辰翁等人的佛寺文中,议论说理的内容大为扩张,几乎每篇佛寺文中都有大量的理学论说,而议论的范围却非常狭窄,多集中于理、道、性、心、仁、孝等理学概念。以黄震《龙山寿圣寺记》为例,该文百分之八十的篇幅都用在了对“实”的阐发以及对庄列之学的攻击上,文末还称“若今人心之病,孰大于谈虚”[2](第348册,P272)。南宋末年的佛寺文中出现如此密集的关于理学命题的论说,与其时理学被确定为官方哲学的发展进程是相吻合的。随着理学地位一起提升的,还有士人对理学进行阐发的兴趣,但对理学思想进行过度阐发,无疑会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宋濂所谓“宝庆之后,文弊滋极,惟陈腐之言是袭,前人未发者,则不能启一喙”[8](第7册,P2180),即是对南宋末年文学受理学过度影响之弊病的极佳概括。
除理学家外,一般文人的佛寺文中亦具有丰富的理学蕴涵。贺允中《应心泉记》称“夫通天下者一气,备万物者一诚”,文中还多有“仁”“心”“尼夫之雨”“瓢饮之乐”[2](第182册,P46)等理学语汇。何熙志在高度肯定理学地位的同时也对佛学予以认同,其《潼川府牛头寺罗汉阁记》称“吾儒至诚不息,而终至于配天地、覆载万物,若合符节矣。何独于释氏而疑之?故并书以祛后惑”[2](第200册,P339)。李纲《报本殿记》虽为赞美佛殿而作,但“报本”之名实出于儒,其间提到了儒家的“礼”“祭祀”“仁”“义”等诸多概念,称“凡祭祀之间,所以仁鬼神者,皆推其本而报之,仁之至、义之尽也”[2](第172册,P200),此之谓“报本”。张浚《重修鼓山白云涌泉禅寺碑》开篇即以理学议论入文:“天下之事未有为而不诚,诚而不至,充尽夫至诚之道,犹不能有克成者。”[2](第188册,P144)这是以儒家的至诚之道为佛门的修寺之举张目。将理学定为官方哲学的理宗皇帝在其《天竺广大灵感观音殿记》中亦有理学论说,如“心者何,仁是也” [2](第345册,P410)。陈羍《重修石建寺碑记》一文极短,但还是给说理留下了足够的篇幅:“中兴美名也,而中者末之渐,兴者衰之复,日中则仄,阳极而阴,理固然也。” [2](第358册,P25)在一般文人的佛寺文中,说理的成分也是随着理学的发展呈日趋稠密之势。及至南宋末年,陈著、李涛、家之巽等人的佛寺文中常有大段的理学议论,其程度虽不及同一时期理学家的佛寺文那么夸张,但也是非常显著的。
佛寺文发端于东晋慧远的《庐山记》和《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经《洛阳伽蓝记》和唐人寺碑文的发扬,至宋而臻于全盛。南宋佛寺文数量多、作者众、质量佳,其间既有高文典册,又有优美辞章,对南宋社会生活有多向度、多层面的反映。南宋佛寺文内容丰富,山水清音、佛门建筑、乱世图景、理学蕴涵等均被收纳于其中。南宋佛寺文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是宋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