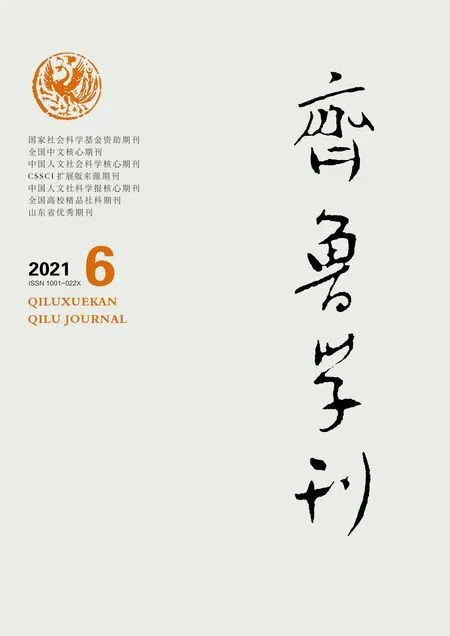古代史家责任意识探析
陈娇娇,张秋升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原因有多种,政治的需要、史官和史馆制度的设置及完备、整个社会“史”文化氛围的浓厚,等等皆是。若从治史主体——史家(1)本文所用“史家”一词,涵盖任职官府的“史官”和私家修史的“史家”。为行文方便,一般以“史家”涵盖二者。角度来说,首要的就是史家强烈的责任意识。责任是人们分内应做之事,责任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分内之事的自觉意识,是自觉做好应做之事的精神状态,通常也称为责任感,崇高的责任感可以称为使命感。史家的责任意识就是史家对史学工作的自觉认知和主动担当的精神。
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是良史的基本品质之一,是历代史家自我反思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官、私史学中均有广泛表现,可以说贯穿于史家考史、撰史、评史的各个环节,涉及到史学自身和历史本体的诸多方面。虽然古代史家没有对此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相关的言说和在治史实践中的体现,却是相当丰富而普遍的。对此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特质、发展机制和持续兴盛的原因。惜迄今人们没有给予系统的梳理、归纳以及专门的分析,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专门探讨者尚付阙如。其中涉及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瞿林东《史学与“良史之忧”》一文,从忧患的角度论述古代史家的社会之忧和史学之忧,未正面论及史家的责任意识[1];杨翼骧、乔治忠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一文,“申明修史的责任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篇幅较小[2];瞿林东《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一文,较多涉及了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但主要关注的是其社会责任方面,也不是专题性讨论[3];孔祥成的《论“国亡史成”》一文,重在论述“国亡史成”的理念,亦非全面论述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4];许兆昌将周代史官的职事归纳为从记事到统军作战等共35种,分为6大类:文职事务、馆职事务、礼职事务、史职事务、“天”职事务和武职事务,但没有从治史主体的角度论及史官的责任意识[5](P99-108);罗炳良《良史之忧:史学批评范畴的时代特征》一文,只是将“良史”作为一个史学批评范畴,将其内涵进行了历时性的论述,亦非专论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6];陈其泰《“名山事业”:史家强烈的使命意识》一文,只是列举了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魏源等例子,对其使命意识没有深入剖析[7];时培磊《中国古代史学“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探析》对史家责任意识也涉及不多[8]。
古代史家大多将治史看作一件严肃而崇高的事业,因此,他们要求治史者对史学事业应勇于担当并认真负责。这里面包含有史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的史家甚至为了写史而不畏强权,冒着生命危险,记述真实的历史,表现出浩然正气的史胆和献身精神。史家责任意识的形成可追溯到三代时期的史官。作为官府里的官员,三代史官职责明确,分工清楚,承担着 “君举必书”、记事记言、掌管典册等职守,尽职尽责,而且所记之史,讲求“书法”,遵循一定的规则。晋董狐不畏强权,“书法不隐”,记下“赵盾弑其君”,因而被孔子誉为“良史”;齐太史兄弟三人因写下“崔杼弑其君”而被杀,而其弟和南史氏依然勇往直前,最终记载下了崔杼弑君的事实。董狐和齐太史是三代史官尽职尽责的典型代表。
至孔子以私人身份担当史官之责,便开启了后世私家治史的责任担当进程。孔子生当春秋末年乱世之中,为拯救世道人心,匡扶礼坏乐崩的衰世,而自觉担当起史官的责任,修《春秋》以救世,即孟子所说“孔子惧,作《春秋》”[9](P155)。于是,这种责任意识便由官职之守,扩展成私家所持所为。孔子修《春秋》不但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同时表征了其史学责任感。《汉书·艺文志》谓:“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10](P1715)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亦谓:“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因鲁史以修《春秋》。”[11](P204)因载籍残缺,伤斯文之坠而修史,充分说明了孔子的史学责任感。
孔子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学责任意识,均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在后世史家身上,这两种责任意识往往是合而为一的。至汉司马谈以太史令未成史而自责,司马迁更是秉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自觉担当,撰写《史记》。此后,官私修史者都共同强化着治史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学责任意识,直至后来,史家发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强烈呼声!
那么,古代史家治史责任是什么?其责任意识表现怎样?这些责任意识的成因又有哪些?我们将分而论之。
一、古代史家的治史责任
三代史官的设置以周代史官最为完备系统,分工明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各有其责。概括而言,周代史官的职责有起草公文、宣读文件、记录时事、保管文书、制历颁朔、担任宗教活动职务等。之后,史官职能范围逐渐缩小,渐归于纪事一种。但纪事的同时,又有对历史的善恶评判。孔子修《春秋》不但记载了春秋242年的历史事实,而且贯穿着“微言大义”,以“义”为标准,评判历史,“惩恶而劝善”。总体而言,古代史家治史责任有二:记录历史、惩恶劝善,亦即承担着史学责任和社会责任。
对于史官职责,元代胡祗遹做过详细的说明。他在《国史院厅壁记》中系统梳理自古以来史官的职责,认为史官职责范围存在由宽到窄的变化,古之史官负责的事务较多,身兼数职,“盖主记录、明历卜。故凡邦国计簿,及天官、历律、典则、礼仪皆兼之”。汉代史官除纪事外,仍兼有天官职能,后来“专以纪录为职,余皆不与焉”。即使是专司纪录之责,依然范围较广:“上自祖考受命之圣神,天子之一起居、一话言,大臣百官之一举措、一应对,皆得耳闻而目见,退而书于册。下及礼乐刑政之美恶,遐方异域之服叛,列国风俗之疵美,天象、地质、日月、星辰、风云之征变,山林、川泽、水火、草木、百物之妖祥,闾里欢戚之声容,云林隐逸之奇特,与夫忠臣孝子、节妇义夫,以及弑逆之恶,莫不详悉隐显、原究情伪而备书之”,这是我们见到的对史官纪事职责范围最详细的说明。胡祗遹还进一步指出,史官的职责不仅仅限于纪事,他们还担当着惩恶劝善的责任,即“不溢美、不隐恶,核实昭直,善足为法,恶足为戒。藏之金匮,秘之石室,人主不可得而观。诛奸谀于九原,发潜德于冥漠,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史官之职也”[12](P249)。
胡祗遹史家责任论渊源有自,只不过他说得更加具体完备而已。北齐柳虬在《史官密书之弊疏》中即指出,作为史官责任有二:一是记事,二是监诫和教化:“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13](《柳虬传》,P681)唐朝刚刚建立,唐高祖就下诏修史,在《唐高祖修五代史诏》中,就明确了史官的责任:“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4](《令狐德棻传》,P2597)以记事和惩劝为史官的基本职责。宋王钦若等所修《册府元龟》亦有对史家职责的论述:“广记备言,国史之职也;章往考来,《春秋》之义也。夫司记言动,纟由绎编简,为一代之典,源千秋之训,固宜书法不隐,叙事可观,研思覃精,间不容发。”[15](P1612)“广记备言”自然无所不记,但“《春秋》之义”“千秋之训”亦不可忽视,这同样是强调记载历史与评判历史的统一,从而发挥历史的惩劝功能。
关于史家之责,唐代刘知几认识颇深,因他在史馆修史长达二十余年,耳闻目睹了史官的种种表现,他本人也“职思其忧,不惶启处”[16](《史通》原序, P1)。他指出记载历史、使善恶昭彰是史家的职责:“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16](P220-221)这是存史、诫世的责任。与之相连,留存善恶记载,前提是区分品类、鉴别善恶:“亦有厥类众伙,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16](P172-173)这是对善恶区分的责任。他进一步指出:“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恶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16](P175)所以,区分善恶、分别品类、载入史册、诫世示后,都是刘知几心目中的史家之责。
对不能尽责的史官刘知几给予了谴责:“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16](P185)北宋王钦若等也认为不负责、不称职的史官应该受到惩罚:“若乃司载笔之官,昧叙事之方,徒淹岁时,空索编简,或纟由绎之靡就,或颁次之无文,昧进旷官,盖可惩也。”[15](P1615)。对于高度负责的史官,刘知几则积极歌颂:“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16](P180)
史书的论赞是古代最基本的评判历史的形式,明末毕懋康认为,写好论赞是史家责任所在,“匪义弗可为史也。匪义而史,箕敛之薄书而已”。因此,对于论赞之义的阐扬不可不慎:“诸史为载物车,而论赞为照人镜也。”[17](毕懋康《二十一史论赞》序,P535-536)明代胡应麟也说:“夫史之论赞而岂苟哉?终身履历,百代劝惩系焉。”[18](P131)因其为百代劝惩所系,故必须谨慎。
史家之责,责任重大,对此古代史家亦有明确的论说。南朝刘勰认为史之任要“负海内之责”,清人钱大昕说史之书乃“千载之书”,足见史家既要对天下负责,又要对千秋万代负责,其责任重大不言而喻。刘勰说:“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11](P208)所以,绝对不可任情失正。钱大昕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齮齕前人,实以开导后学。”[19](《廿二史考异·序》,P1)所以,史家之责是从空间上对海内天下、从时间上对千载万世所负之重责,它不应偏私于某人或某些人,不应只面对过去或现在,还要面对未来。这样的责任不仅重大,而且崇高。
面对记事、惩劝等史家的基本责任,古代史家表现出了强烈的治史责任意识,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二是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以下我们将依次述论之。
二、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
留存历史是史家治史的第一步,也是后世官私修史者首要的工作。早期史官的职守,被孔子继承并赋予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后世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史家的责任意识被反复阐述和一再强化。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古代史家责任意识的表现。
其一,从史家自我言行来看,多数史家都有很强的存史意识和修史诉求。
从孔子惧而作《春秋》,到明末谈迁一介寒儒矻矻著史,再到清代王鸿绪撰写篇幅浩繁的《明史稿》,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立意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精神及行为不绝于书。
孔子强烈的存史责任意识,不仅表现为他对董狐“书法不隐”的高度赞扬,而且更体现在他晚年编订《春秋》上。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9] (P155)指明了孔子以修史来整饬世道人心的强烈责任感。《春秋》成,“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20](《孔子世家》,P2353),则又说明了孔子修《春秋》的态度是多么认真!
董仲舒和司马迁也对孔子修《春秋》的责任感深有体会:“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子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0](《太史公自序》,P4003)
汉代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对存史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临终前,他对儿子司马迁谆谆嘱托,先从其祖上为太史,祖职即有撰史之责说起,要求司马迁“续吾祖”;又道及汉武封禅自己不得跟从的遗憾,进而要求司马迁:“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殷殷期盼,溢于言表。最后司马谈说到自己即将离世而修史不成的遗憾和恐惧:“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作为一位负责任的史家,将自己不能修成史书看作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可见其责任感之深之重。司马迁决心继承父志,完成这一崇高使命,故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并主动担此重任:“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20](《太史公自序》,P4000-4002)他还将自己能否尽责上升到是否犯罪的高度:“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坠先人所言,罪莫大焉。”[20](《太史公自序》,P4005)在遭受宫刑之后,司马迁的责任意识变得尤为强烈:“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10](P2733)又云:“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0](P2735)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司马迁撰史的高度责任心、伟大使命感和为史学献身的精神。
东汉蔡邕自言著《汉记十意》“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会臣被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躯朽腐,抱恨黄泉”[21](《蔡邕列传》李贤注引蔡邕上书,P2004),故获罪之后,依然“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21](《蔡邕列传》,P2006)。这充分说明蔡邕有着强烈的留存历史的责任意识。东晋常璩“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反侧惟之,心若焚灼,惧益遐弃,城陴靡闻”[22](《序志》,P894),故发奋著《华阳国志》,也是唯恐华阳历史湮没无闻。北宋司马光修史的责任感尤其强烈,面对史籍浩繁,皇帝无暇阅读,历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他批评正史之繁冗,立志写出简略有效的史书:“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23](《进资治通鉴表》,P9607-9608),用以“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并深感此事“功大力薄,任重道悠”[24](P468)。欧阳修指责五代史书记载的残缺和驳杂,担心这一时期的历史泯然无传,起而重修历史:“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废之际,岂无谋臣之略,辩士之谈?而文字不足以发之,遂使泯然无传于后世。”[25](《宦者传》,P458)故而“慨然以此自任”,“潜心累年而后成书”[25](陈师锡《五代史记序》,P1050)。南宋李心传“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不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26](《序》P1),终于写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成为后世了解和研究宋史的必读经典。
以上所列,都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史家对修史的高度责任感。这样的责任意识逐渐发展,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国亡史存的重大责任理念。金国被蒙古灭亡后,元好问以“国亡史兴,己所当为”的信念,声言“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欲自撰金史[27](《遗山先生墓铭》,P394)。这种存史的责任感不但为史家、文人所接受,甚至作为军事统帅的董文炳也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28](《董文炳传》,P3672)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观点,是对历史的高度重视,证明这种责任意识亦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明末清初,有两位私家修史者的强烈存史责任感特别让人感动,一是《国榷》的撰者谈迁,二是《明季南略》《明季北略》的撰者计六奇。谈迁自幼家境贫寒,博学重史,痛感于陈建《通纪》中的种种错漏,在物质条件极为贫乏的条件下,靠借阅或抄录的方式积累史料,意欲勒为一编,写出信史。明亡之后,出于对“国灭而史亦随灭”[29](《黄宗羲谈君墓表》,P6225)的深深忧患,怀抱故国情怀,孜孜二十余年,大功即将告成时,书稿突然遭窃,谈迁痛不欲生,“悲悼者累月”[29](《朱一是谈孺木先生墓志铭》,P6223)。后决意发愤重写:“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29](《国榷》义例,P8),终于在顺治八年(1651)完成新稿,而距其初修之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了。明清之际的计六奇与谈迁的经历非常相似,亦出生于没落的书香门第。明清之际的天崩地解,山河破碎,使他无意于仕途,而寄情于南明历史。他遇到史料,就废寝忘食地抄录:“纵览凝思,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晨夕勿辍,寒暑无间。宾朋出入弗知,家乡米盐无问。”[30](《跋》,P524)并表达了自己修史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责任感:“天下可乱可亡,而当时行事,必不可泯。”[31](《自序》,P1)终成《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传诸后世。
清修《明史》,官、私史家均表现出积极的责任担当,在野的戴名世面对“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的状况而慨然担当,“鄙人无状,窃有志焉”,立志纂修《明史》[32](《与余生书》,P2),而王鸿绪在雍正年间进呈的310卷《明史稿》,更是志存明代历史的强烈责任感之表现。
其二,从史家劝谏朝廷修史来看,建言修史彰显了史家的责任担当精神。
古代史家立志自己修史,反映了他们强烈的修史诉求和责任担当,而在特定时期他们积极建言朝廷修史,也是其责任担当精神的一种表现。有的人虽然未必自己修史或参与官史撰修,但他们对存史的责任感却同样强烈。
东晋王导出于对纂修国史的责任心,劝说晋元帝重视修史:“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33](《干宝传》,P2149-2150)他不但建言备设史官,而且推荐干宝等人来纂修历史。
隋灭唐兴,历史巨变,更激发起人们对修史的重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作为史官的令狐德棻就建议修撰前代史,表达了修史的强烈责任感:“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14](《令狐德棻传》,P2597)。令狐德芬表达了大乱之后一代史臣对修史的深深关切,显示了强烈的责任感。史家不但对纂修前代历史充满了责任感,而且对当朝历史的及时记存编修,也颇为关注,如唐崔梲《请修史疏》即说:“且言异代,犹恐弃遗,况在本朝,岂以湮灭!臣尝闻宣宗缵承大业,思致时雍,旰食宵衣,忧勤庶务。十余年之内,可谓治平。于时史官,虽有注记,寻属多故,辇辂省方,未暇刊修,皆至沦坠,统临之盛,寂寞无闻。伏思年代未遥,耳目相接,岂无野史,散在人间,伏乞特命购求,十获五六,亦可备编修,冀成一代之信书,永祚千年之盛观。”[34](卷851,P8941)反映了一个史家对当世史料寻访搜集意义的高度敏感和“冀成一代之信书”的高度责任感。
北魏和元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其统治者也如汉族统治者一样,重视历史及史书的纂修。不少史臣或史家出于对历史的留存史迹的责任感,也上书建议纂修史书。北魏李彪上书高祖:“秘府策勋,述美未尽。将令皇风大猷,或阙而不载;功臣懿绩,或遗而弗传。”[35](《高祐传》,P1379)表达了对史迹湮没不传的担心。元太宗六年(1234),金灭亡不久,刘秉忠便以“国灭史存,古之常道”为据,提出修《金史》之建议,“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28](《刘秉忠传》,P3691)王鄂本是金朝状元,早在忽必烈时代,就请求设立国史院,并进言:“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兴者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人而可公故也。”[36](P41)他建议修撰辽史和金史时说得更为具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37](P239)刘秉忠、王鄂的建议反映了一代史臣对修史的责任意识,他们的“国灭史存”“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也成为了后世史家责任意识的象征语。
元顺帝时期的危素建议修辽、金、宋史时说:“古之君子何贵于史哉?以其君创业于初,守成于中,失国于终,故后世之为君者考其所以兴,监其所以亡,其仁明可法,其昏乱可戒。其臣之忠良正直、奸险佞邪,故使后世之为臣者思以彼就此焉……昔人有言:可以亡人之国,不可以亡人之史。盖记载其一国之政者,其事小;垂监于万世之人者,其功大故也。则三朝之史,不可以不修也审矣。”[38](P149-150)危素从鉴戒的角度强调了修史的重要性。
苏天爵是元代著名的史学家,所著《国朝名臣事略》是元代私修本朝史的代表作。他有一篇关于本朝功臣列传纂修事宜的折子,其中写道:“古者史官所以论著君臣善恶得失,以为监戒者也。钦惟圣朝龙兴朔方,灭金平宋,遂一华夏,而阀阅勋旧之臣,谋猷才能之士,苟不载之简策,何以垂示方来?夫祖宗大典,既严金匮石室之藏,而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诚为阙典。然自大德以来,史臣屡请采辑,有司视为泛常,讫今未尽送官。”[39](P444)对本朝功臣列传纂修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指陈,并对修史以垂示未来寄予了盼望。
其三,从史家对治史责任的评说来看,不论是责评他人还是自责,都传达出史家存史的担当精神。
从对史家治史能否尽责、是否尽责的评说中,亦可看出古代史家对存史的主动担当精神。这些批评既有对他人的评论,也有对自我的反思和自责,一般对不能尽责、没有尽责者给予贬斥,自责者则表现出深深的内疚。
唐代韩愈任史官修撰,曾经有《答刘秀才论史书》一文,他提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34](卷554,P5610)的说法,表达了作为史官推脱责任、不能直道修史的犹豫与担心。柳宗元读后,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认为既为史官,位居其位,就当思直其道,尽职尽责。柳宗元明确申明史官的责任:“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他强调“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史官只有尽职尽责,“孜孜不敢怠”,才能使历史记载“庶几不坠”,并认为史官“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40](P807-809)。真正的史官,是不需要别人督促的,应有自觉担当的意识。
史家所表达的未能尽责的惭愧,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史家责任意识之重。明代何瑭在《史职议》中写道:“伏以有官守者,则思修其职;有言责者,则思尽其忠。此人臣之大防,而古今之通谊也。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睹内外百司各有职守,而史官独若无所事者,朝参之余退安私室,于国家政务无分毫补益,犹且月受俸钱、日支廪给。既失官守之职,难逃尸素之讥。每念及兹,不胜惶愧。”在表达了自己的深深愧疚之后,何瑭又对史官不能记录时事、留存历史表示忧虑:“臣谨考:古者,王朝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我祖宗设修撰、编修、检讨,谓之史官,俾司纪录,法古意也……不知因循废坠始于何时……方今山陵既毕,政治维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职于久废,敕令修撰、编修、检讨直史馆。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论列、大政事之因革驰张、大臣僚之升降拜罢,皆令即时纪录……史职既修,国典斯备。”因而希望朝廷将久已废弃的史职恢复起来,让史官负起责任,以保障留存国典。最后他说:“上则圣君贤臣、嘉谟嘉猷不至有所遗落,下则憸夫小人惧遗万世之讥,亦有所惩戒,不敢纵恣为恶。公则明朝廷无虚设之官,私则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体甚便。”[41](P467-468)只有历史记载完备,才能发挥历史的惩恶劝善的功能,发挥历史的应有作用。
明代另一位史臣张位也有与何瑭《史职议》相类的文章,题曰《史职疏》,在该文之中,张位认为,“夫当职而不能举,守官之耻也”,“臣闻左史记动,右史记言,故当时圣君名臣经世之迹,炳然侈于后观。历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时,尚设起居注官……今国史之员虽设,其名存其实废矣”,表现出对史官建置的重视和对当时史官名存实亡现状的忧虑。最后,张位对历史不能被记载、修史无专责从而造成野史流传等问题,表达了深切关注:“臣顷备员纂修,切见先朝政事,不过檃栝章疏之存者纪之。若非出于诏令,形诸建白,则近者以无据而略,远者以不知而遗。中间精神脉络,每每不相联贯,致使圣代鸿猷茂烈,郁而未章,非所以媲前徽而光后范也。旧闻史氏中,亦有随所睹记暗疏之者,因事无专责,往往中辍。纪载既失其职,徒令野史流传,淆乱失真,甚亡谓也。”[42](P4430)
三、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
信史是中国古代史书的最高境界,也是发挥其社会功用的基本前提,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是史家责任意识的突出表现。那么,什么是信史呢?
清代的毛奇龄和朱彝尊都强调,修成“信史”是史家的责任。毛奇龄说:“千秋信史,所贵核实。故曰不遗善,不讳恶,又曰劝善惩恶比之赏罚。”[43](P95)他重在强调“核实”,即历史的真实,这是惩劝的前提。朱彝尊则说:“国史者,公天下之书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44](P277)他强调公正,不偏私,即历史评判的标准。实际上,古代所言“信史”应具两个基本的内涵:一是求真实录,一是公正无私。古人对信史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而在具体的议论中,人们会各有侧重,或二者兼具,或二者取一。
其一,求真实录的治史取向。
史学的求真仍需从孔子那里寻找源头。孔子曾称赞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影响深远。班固将司马迁《史记》评价为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0](《司马迁传》,P2738)的确,司马迁的《史记》贯穿着实录精神。黄帝以前的历史在当时的许多典籍中有不少记载,但是司马迁却认为那些描写茫昧不实,故而不取;《山海经》中记载了不少神怪,他也一概斥之于史书之外;对未知史实,他亲自访查,实在不可知者,便阙疑不写。自此之后,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理念便深入人心,求真求实渐成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南朝刘勰强调史书贵“信史”,其信史之信,重在真实。刘勰对史家不能实录的原因作了分析,同时也强烈谴责了虚妄的历史:“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近略远,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11](《史传》,P207)年代的久远和爱奇的心理大大损害了史书之信。
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写了《直书》和《曲笔》两篇,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实录精神,并第一次将一个史家是否采取实录的写史态度与人品密切联系起来:“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16](《直书》,P179)这意味着能否修成信史,与史家道德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北宋王钦若等在《册府元龟》中也强调信史:“传曰:书法不隐,又曰不刊之书。盖圣人垂世立法,惩恶劝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渎货而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蔑记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而厚诬,宜当秽史之名,岂曰传信之实。”[15](《不实门序》,P1613)事实的不符、评论的不公,当称作秽史,怎能叫作信史!欧阳修在《论史馆日历状》中说到:“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诫,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45](P1251)直书不隐正是信史的基本要求之一。
南宋李焘撰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他曾上奏说:“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省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46](《经籍考二十》,P1637)对史书纷错难信的遗憾是其修史的动机,其追求信史的责任心跃然纸上。吴缜鉴于《新唐书》存在“善恶多相异之辞,纪传有不同之事”等等现象,自我担当,考证勘误《新唐书》,撰成《新唐书纠谬》,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非常强烈。他还说道:“臣虽至愚,常切私愤,从吏之暇,披卷以寻,岁月寖深,瑕纇愈见。”[47](P162)又可见其自觉担当之切。
明遗民王鸿绪出于对历史的负责,追求历史的真实:“野史之增饰,家传之附会,亦往往有之,若著之正史,则不得不核其实,以示百世无惑,不敢刻,亦何敢滥也。”[48](P584)乾嘉时期的求真精神则发展为实事求是的理念和态度。乾嘉学派以钱大昕为代表,他明确标举“实事求是”的理念,提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49](P421)他说:“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49](P396-397)又说:“史家记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50](P350)钱大昕等考史学家,常常博引旁证,参互搜讨,以探求客观的事实真相。以上均是追寻信史的典型表现。
古代史家的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史家坚守史官职责上。这里有一典型事例可以说明史官是如何坚持职守维护历史真实的。起居注在古代专记人君言行动止,史官为了防止记载的失真,往往拒绝人君亲览。唐太宗虽为明君,但却多次欲观起居注,史官均予拒绝。朱子奢曾上表言及此事,指陈唐太宗亲览起居注的不当,认为君主若是明主尚且无害,“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51](《史馆上》,P1301)后数年,唐太宗又对史官褚遂良提出观览起居注的要求,褚遂良认为起居注对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并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51](《史馆上》,P1301)反映了褚遂良的忠于职守观念,以免因人君的干预而导致了历史的失真。唐文宗也想亲览起居注,史官魏謩指出:“陛下但为善事,勿谓臣不书。如陛下行错忤,臣纵不书,天下之人书之……由史官不守职分,臣岂敢陷陛下为非法?陛下一览之后,自此书事须有回避。如此,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14](《魏謩传》,P4569)魏謩坚持了自己的职分,保持了历史的真实。
信史必须真实、必须直书实录的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深谙中西史学的著名学者汪荣祖说:“顾中西史家,俱以存往迹为己任。”[52](P235)又说:“往迹虽存,苟非实录,则亦殆矣。故史之优劣,决之于信度之高低耳。”[52](P236)在他的心目中,信史的基本要求就是实录。
其二,公正无私的评史信念。
求真实录之外,古代史家还注重历史评判的公正性,而偏私导致历史评判的不公,故而被历代史家所痛斥。
东晋史家袁宏,“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恐“前史缺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今之史书或非古人之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53](《后汉纪·自序》,P1-2),《后汉纪》就是在这种忧虑心境下写成的。唐代史家李大师出于自觉的修史责任意识,意欲重修南北朝各代史,他“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54](《序传》,P3343)。李大师是基于南北朝各自偏私,不能做到公正书写历史,故而要重修南北诸史。“没齿之恨”说明他对修史的高度负责精神,而他修史的自觉担当精神传给了其子李延寿,在其死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李延寿完成了父亲的夙愿。
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对史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李焘对隐晦篡改事实、以私意变乱是非的修史现象极为愤慨,建议重修《徽宗实录》,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徽宗一朝大典,治忽所关最大,若不就今文字未尽沦落,尚可着意收拾,同力整顿,日复一日,必至是非混乱,忠义枉遭埋没,奸谀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55](《职官》,P2789)忠义与奸谀颠倒,是历史最大的不公,他将之定为史官犯罪!李焘私修《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是基于对秦桧奸佞误国、淆乱国史的愤慨及对历史公正的追寻,史家称其“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56](《李焘传》,P11914)。但其慨然担当又非草率行事,而是“网罗收拾四十年”而成[46](《经籍考二十》,P1637)。辽道宗统治时期的耶律孟简不但有修“国史以垂后世”的存史责任意识,而且极力强调信史:“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57](《耶律孟简传》,P1456)
在古代史学史上,私人修史者出于责任心而校正国史之失的现象比较普遍。明代的焦竑说:“古天子诸侯,皆有史官,自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与贪而曲笔,虚美隐恶,失其常守者有之。于是岩处奇士偏部短记,随时有作,冀以信己志而矫史官之失者多矣。”[58](P67)他反对虚美隐恶,希望校正史官之失。黄省曾则对《实录》所及偏私不公、敷衍塞责的史官痛加挞伐:“作俑之人无其智,又无其才,且或挟妒嫉之私,存祸殃之惧,故缩避含糊,草草应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59](P811)清代钱谦益痛恨曲笔以欺天下的史家,甚至大加诅咒:“其或敢阿私所好,文致出入,曲笔以欺天下后世,不有人祸,必有天刑。”[60](P1244)
四、古代史家责任意识的成因分析
与记事、惩劝等史家的基本责任要求相一致,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表现为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和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那么,这些责任意识的形成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有三:一是帝王的需求与支持,二是史家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三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转化。
其一,帝王的需求与支持。
古代帝王重视历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大都以史为政,治理国家,发挥历史资治的功能。史官、史馆的设置是他们重史的突出表现,诏令修史也是史学史上的常有现象,他们自身对于修史大都有较强的责任意识,甚至亲提史笔,撰写历史。所以,帝王的需求和支持是史家责任意识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我们从帝王修史诏令中来分析这一问题。
孔子修《春秋》是个人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司马迁写《史记》虽说是太史令职责要求,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私人行为。班固写《汉书》是个人私撰到官修的一个过渡,反映了帝王对历史越来越重视,故而东汉开始选择人员东观修史,而汉末荀悦的《汉纪》就是皇帝直接命令的结果。此后,帝王与史学的关系日渐紧密,下诏修史成为历代帝王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
北魏虽为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所建,但对历史的重视不亚于汉族统治者。魏太武帝曾经下诏令崔浩修史:“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惧不能负荷至重,继名丕烈……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也。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35](《崔浩传》,P912)反映了魏太武帝对史官之阙职、史事无记载的关切以及赋予崔浩修史之责的殷切之意。
唐高祖开国之初即下达《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并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14](《令狐德棻传》,P2597-2598)阐明了史官记事的重要作用,表达了对历史湮没的痛心,强调了修史的责任。唐太宗的《修晋书诏》,对《晋书》的修撰同样表达了强烈的责任感:“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遂使典午清尘,韫遗芳于简册;金行曩志,阙继美于骊騵;遐想寂寥,深为叹息。”[61](P467)因为十八家晋书的修撰者才非良史,事亏实录,故唐有重修晋史的责任。
一统时代的帝王强调修史的意义,分裂割据时代的统治者也是如此。唐末五代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即使是地狭祚短的小政权的统治者,也多重视历史,表现出修史的责任感。如后唐末帝李从珂《令修撰实录制》:“然而致理之绩,虽已播于颂声,纪事之书,尚未编于史氏……其实录宜令史馆急速修撰呈进。惟务周详,勿令阙漏。”[34](P1151)后晋高祖石敬塘在《令修唐史敕》中说:“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咸阙。今耳目相接,尚可询求。若岁月寖深,何由寻访?”[34](P1182-1183)五代时期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本朝和前朝实录的修撰和续修,表达了存史的责任意识。
宋太祖下诏修五代史,在《修五代史诏》中说:“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62](P555)命令委派专人,专司其职,完成修史。宋仁宗表彰《新唐书》修撰者的敕书中则说:“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贤臣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坏成败之迹,晦而不彰,朕甚恨之。”[63](P385)其修史的责任心也是相当强烈的。
元顺帝时编纂辽、金、宋三史,《修三史诏》云:“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57](《修三史诏》,P1554)也是唯恐历史散失,诏令修三史以垂鉴。
明朝刚刚建立,明太祖就下诏令开局修撰《元史》:“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原殆将百年……时号小康……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64](P212)宋濂在《进元史表》中说明太祖“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65](P47),在《吕氏采史目录序》中说明太祖“慨然悯胜过之亡,其史将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65](P50),都反映了明太祖朱元璋本人有着非常强烈的存史垂鉴的修史愿望和责任意识,他对史臣也提出了相应的的责任要求。
清代《明史》的纂修,历时近百年,几代帝王都极为重视,国史院检讨汤斌上奏所言颇有代表性:“我皇上御极初年,命史臣纂修《明史》,诚可见于国可废,史不可灭也。”[48](P640)康熙帝要求史臣负起责来,修好《明史》,强调“作史昭垂永久,关系甚大,务宜从公论断”[48](P545),“《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朕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48](P548)。表达了自己对修史的高度责任感。而当时的史官也积极呼应皇帝的提倡,如徐乾学说:“不可虚美失实,又不可偏听乱真,愿以虚心核其实迹,庶免佞史、谤史之讥。”[66](P428-429)
可见,至少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的修史诏书如出一辙,可谓形成了一种模式,均表达了他们对修史的强烈的需求和要求史臣尽职尽责修史的观念。这些修史诏令表达了帝王对修史的高度重视,他们对史官提出了很高的责任要求,并因此影响着史官的修史方向。
其二,史家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
古代史家责任意识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自身所职之事的重要性有理性的、清晰的认知,史家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是其责任意识形成的认识前提。古代史家普遍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表现有二:一是历史功用之大,二是史权之重。
在中国古代,史家普遍认为历史的功能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包括两类具体作用,一是鉴戒,二是教化。正因为古代史家对历史功能有高度的认识与关注,他们才对治史这一活动不敢轻忽,其责任感也由此产生。
自周初“殷鉴”思想提出之后,汉初过秦,又有“秦鉴”之论;孔子修《春秋》,惩恶而劝善,教化世人。东汉末年的荀悦认为史学的作用有:“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67](荀悦《汉纪序》,P2)这类认知结论渐成模式,至唐代刘知几已发展为系统的理论认识。
刘知几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上至帝王,下至黎庶,对于功名无不汲汲追求,以图不朽,不朽的唯一途径就是载入史书,史书应区分善恶,惩恶而劝善,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故而史书之重要,进而史家责任之重大,尽在情理之中:“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6](《史官建置》,P280-281)又说:“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16](《直书》,P179)唐代杜佑有着非常明确的史学经邦致用的理念,李翰《通典》序中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68](P1-2)群迷用史,不能奏效,故杜佑《通典》出。
历史因其功用之大而显得极为重要,朝代越是往后,人们越是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明代丘濬将历史的重要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由历史之重要延伸到史职之重要。在《大学衍义补》中,丘濬说:“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然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69](P63)历史不可一日或缺,史官所任是万世之事,故而其责任极为重大,是非、公义全系于斯。嘉靖年间的陆深也在《史通会要》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自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70](P133)在他看来,重史职已经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理念和做法。
因历史之重要,所以史职备受重视,而史权自然极为重大。古代史家对于史权的认识非常深刻,故而使得史家不由得生出强烈的治史责任意识。宋代苏辙说:“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又说:“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71](P1346)他认为史权是圣人制天下是非的三种权力,并将史权与天权、君权相并列。明末毕懋康则说:“夫史有天道焉,人主不能夺,柄臣不能改。曹好曹恶不能乱史者,万世之耳目也。”[17](P534)因为史有天道在,所以人主权臣对它都不能左右。这已经有史高于君的意味。到了清代的汤鹏则更进一步,将史权置于天权、君权之上:“是故权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天之权掌生杀,君之权掌黜陟,史之权掌褒讥”,“是故天不兼史,史兼天;君不兼史,史兼君”[72](P300),从理论上将史权抬至最高权力的地位。而李维桢也说:“史官之权,重于帝王。帝王止赏罚一时,史官则荣辱千载。”[73](P156)
正是基于历史功用之大、史权之重,所以才有龚自珍如下决绝的论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74](P22)龚氏之语,虽不免夸张,但由此而衍生出了史家责任意识甚至使命感,则是不争的事实。
其三,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古代的士人具有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儒学产生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这种意识被一再提倡和强化。作为士人群体中的一类,史家的忧患意识便转化成了治史的责任意识,这是儒家忧患意识在史学中的具体表现。史家的忧患意识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现实社会的担忧,对史学的担忧和对史官的担忧。
从孔子修《春秋》始,以史担当并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便代代传承。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忧惧而作《春秋》,强烈忧患意识化作孔子修史以救世的社会责任感。正如彭忠德所言:“‘孔子惧’正是孟子史学评论的深刻和高明之处,因为这三个字强调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75](P205)清代龚自珍则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74](P7)
史家的忧患意识不仅表现在对现实社会的关切与担心,还表现在对史学现状的深切关怀上。刘知几身为史官,目睹了史馆种种弊端,怀着对史学事业的敬畏和忧惧,退而私撰《史通》,言行之间,都透示出对史学的殷殷之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他说:“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16](《自叙》,P271)《史通》的成书,以及其中对史家责任的界定,对史家责任意识的强调,大都来自于刘知几对当时史学现状的深深忧虑和思考。
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还表现为对史官这一职务的担忧,相关的言说比比皆是,大而言之,一是担忧史职之废,二是担忧史才难觅。唐代魏征等指出:“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76](《经籍志》,P992-993)三代史官的精神丧失已久,魏晋以下,写史者素养很差,导致所修史书虽数量不少,但往往不能真实传达历史人物的信息,造成了史书记载失真,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唐代史官朱敬则上《请择史官表》,首先强调了史官的重要性和人才的缺乏:“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风,资其笔削;三王盛事,借以垂名。此才之难,其难甚矣。”其次表达了自己对史官人才选择的忧虑,体现出了对朝廷选拔史学人才的强烈的责任感:“伏以陛下圣德鸿业,诚可垂范将来,傥不遇良史之才,则大典无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今若访得其善者,伏愿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更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则天下幸甚!”[51](《史馆上》,P1298)
忧患意识刺激并强化了史家的责任感。明代骆问礼说:“臣闻史职之废也久矣,诸臣之建言亦不一而足矣,而卒未有议行之者……四海之广,何患无才?朝廷之大,何爱一官?而事固有动而不相害者。况今面奏之典既行,则圣君贤辅、嘉言懿动,必有超今迈古者,不可不纪述其详,光显其实,以传一时之盛。而一二奸邪情状,亦有当备之,以鉴今而惩后者。宋神宗有言:人臣奏对,有颇僻谗慝者。若左右有史官书之,则无所肆其奸矣。斯言也,有以哉?……臣愿陛下察古人重史之意,求祖宗设官之心……故史职不可不修也。”[77](P5162)当官方不注重修史的时候,往往就有史官或史家忧心忡忡,上表奏疏,敦促人君或统治者重视修史。这些都是史家忧患意识的突出表现,落实到具体修史过程中上,便转化成了史官的责任意识。
结语
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既保障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历史评判的公正性。主体的责任意识使得过往历史不坠于地,抑制了毁灭历史、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等现象的发生几率。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史家的这些责任意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上述现象的发生。由于历史观和史学观的局限,古代史家载笔记录时有其特殊的取舍标准和书写方式,特别是在评判历史方面,虽然明言追求公正,但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史家不仅不可能完全做到他们自己预设的目标和推崇的原则,而且这种目标和原则本身就可能对全面反映历史真实造成某种障蔽。尽管如此,古代史家强烈的治史责任意识和天道史职所在不畏强御勇于担当的精神,对今天的史家来说,应该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