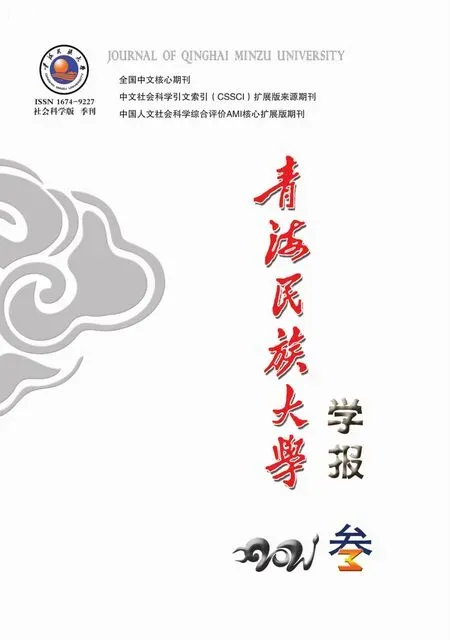“么些先生”的文化实践
——李霖灿的纳西族民俗研究
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650031)
李霖灿是近现代驰名中外的学者,曾任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于1939 年与纳西文化结缘后,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此研究,被纳西人民亲切地称为“么些(MO-SO)先生”。纳西族学者杨世光这样评价这位“么些先生”,“他不断把他的著作寄赠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寄赠纳西文人学者和乡亲。是他以半个世纪如一日的毅力和执着,第一次使祖国的纳西东巴文化跻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给海峡两岸共同的纽带上增添了一道绚彩,架作海峡两岸空间的一座无形而又实在的金桥”。[1]李霖灿对纳西民族文化的研究得到了纳西人民的认可,1994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授予他“丽江县荣誉公民”的称号。
20世纪30年代—80年代,李霖灿陆续发表的著作有《黔滇道上》(1939)《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4)《么些标音文字字典》(1945)《么些经典译注九种》(1967)《金沙江情歌(云南歌谣调查)》(1971)《么些研究论文集》(1973)《么些族的故事》(1976)等。1956年3月受到美国华府国会图书馆之邀,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的东巴经书,1958年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么些经典》一文,向世人介绍了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为东巴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歌谣、故事、节日、民间信仰等民俗的方方面面,在近代民俗学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王铭铭认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方式非常重要,却被现代的青年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忽视,他倡导对社会科学的“人的无名化”之成因进行反思,并提出“人生史”这个概念,认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究,最好是选择一个重要,却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关心相关文献,进行相关口述史或口承传统(如传说、传闻、谣言、访谈)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有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制作某一‘history of a life’。”[2]可见“人生史”是有别于“集体人生”的研究,而是选择在社会文化史上做出贡献的个体,特别强调挖掘那些被人们所遗忘的杰出人物的学术成就。历史学家钱穆也曾谈到:“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3]李霖灿在纳西学界、边疆民族研究以及民俗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1949 年后由于他离开大陆,远离曾经熟悉的田野调查点,他所研究的学科和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语”的境地。李霖灿正是王铭铭所言的“重要,即并非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从他对纳西文化的研究可见一代学人在多民族共同意识下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认同与建构。
由于李霖灿在纳西族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20 世纪80 年代后陆续受到学者的关注。郭大烈的《李霖灿与纳西东巴文化》、[4]和少英的《纳西文化研究的拓荒者与奠基者——李霖灿》、[5]杨福泉的《绿雪歌者——李霖灿与纳西东巴文化》、[6]李明珠编辑的《李霖灿教授学术纪念展》。[7]这些论文从李霖灿生平以及对纳西族文化研究方面都进行了论述。遵循上述学者对李霖灿的研究和评价,本文进一步梳理李霖灿在民俗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心系丽江纳西族民俗文化
李霖灿(1913-1999),生于河南省辉县百泉的书香之家。母亲在他幼年时逝世,父亲以开饮食店维持家用。虽然生活艰辛,但父亲热爱生活的态度时刻影响着他。在他1950 年5 月《父亲大人的故事》手稿中写到,他的父亲善于讲故事,常常引得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围在他周围,他自然也从父亲那里听到很多故事。[8]父亲对他的影响,使得他后来对纳西族东巴经中的故事有极大的兴趣。李霖灿高小毕业后,在开封市第一师范工作的三哥资助下,考上了河南第一师范。师范毕业后在李剑晨老师的推荐下报考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校艺术氛围浓厚,大师云集,思想活跃。在校学习的5 年时间为他日后研究东巴象形文字、艺术鉴赏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抗战时期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先后搬到浙江诸暨县、江西贵溪县、湘西沅陵,后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组成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39 年按教育部安排迁往云南昆明。李霖灿与几个同学相约步行到昆明,途中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昆明后,李霖灿根据沿途的考察经历,于1940 年在《大公报》(香港)出版了《黔滇道上》,文中记录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艺术、地理地貌、博物生态、民风民俗等内容。多年后李霖灿之子李在中对这一时期的材料进行整理后再次以《黔滇道上》一书出版,并增加了李霖灿由贵阳步行到昆明的日记,以及李霖灿当年为“边疆艺术考察团”所写的田野调查报告及相关文章。[9]李霖灿到昆明后,与好友李晨岚相约去拜访古琴手郑颖荪时,接触到纳西族的象形文字,郑颖荪向他们介绍这些文字记录的是纳西族故事。李霖灿想到这些比美洲红印地安人的图画文字要美丽、要完备得多的象形文字竟然书写的是故事,便下定决定一定为这一项文字学上的国之瑰宝贡献此生。[10]李霖灿对纳西文化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李霖灿到昆明后,在学校成立了“高原文艺社”,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沈从文听说后,主动约文艺社成员们到家中畅谈。李霖灿与沈先生交谈时提到了在黔滇道中所见的精美绝伦的苗族服饰,这时沈从文马上拿出奥裔美籍学者J.F.洛克的东巴文化研究著作进行介绍,经沈先生这一介绍,就更促使了李霖灿要去丽江走一趟的决心。不久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滕固计划对边疆艺术进行调研,李霖灿主动申请并获得经费支持。他于1939 年6 月到丽江,按计划两个月的考察很快就结束了,他不得以只得暂时离开丽江。这次调研让他对纳西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也产生了对纳西文化进一步调查的决心。同年11 月他又迫不及待地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高才生李晨岚再次来到丽江。这一时期,李霖灿写了一系列描写纳西族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的游记,在沈从文的大力推举下发表于《今日评论》,获得微薄的稿费贴补生活费用,后来这些论文收入在《神游玉龙山》[11]《雪山·碧湖·喇嘛寺》[12]并在大陆出版,散文中记录了目前丽江许多著名的旅游胜地,这是了解纳西古王国重要的文献资料。据李霖灿回忆,“沈从文老师一再提醒我们,老百姓的智慧,深湛而有撼人心弦的地方,当脱去士大夫阶级的浅薄傲慢而转为积极的学习研讨,一一都具体呈现在我面前”。[13]后来李霖灿也多次提到沈从文是他走入民间的思想启蒙者。1941 年7 月,李霖灿收到董作宾和李济写来的电报,邀请他加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并支持他继续研究纳西族文化。从这时开始李霖灿的民族调查身份得到正式的认可,并得到民族学家凌纯声的指导,“凌纯声博士是我作么些民族研究的启蒙导师,他受李济博士委托,曾为中央博物院(实在是为我)拟定了一份滇西民族调查及采集计划。这项由他亲手写成的计划书中,第一项就是么些民族的调查,不但路线注得明明白白的,而且把调查时注意的要点一一谆谆解说,于是这本计划书就成了我调查么些民族的启蒙课本。在丽江工作时随身携带,如今还珍藏于行箧之中,纪念我作科学研究的初步”。[14]有了中央博物院的经费支持和科学的调查指导,李霖灿的研究就更加深入和细致了。当他接触到大量东巴经典后,发现东巴经典中记录的一程又一程的地名,有可能就是纳西族的迁徙路线,决定进行追踪调查。1942年初,他由丽江向北渡过金沙江,到中甸县的北地,后来经调查考证后发现这里是纳西族的东巴教和东巴文字发源地。李霖灿在这里遇到与他志同道合的东巴和才,并答应做他的向导同他一起探寻纳西族的祖源地。他们一同追寻到宁蒗设治局属的永宁土司地界中,同年 8 月返回丽江。1943 年 9 月 1 日,李霖灿与东巴和才一同离开丽江,到迁至四川李庄的中央博物院汇报调查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迁至李庄的研究机构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随同研究机构到来的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李方桂、张琨等一大批学者,一时学术大家云集,人文荟萃,成了战时的文化中心。李霖灿到李庄后在语言学家张琨指导下对记录的纳西族经典和语音系统进行一一校正,东巴和才作为发音人,三人在一起工作了三个多月,记录了二十本经典,二十个故事和许多日常应用的语言。1944 年,《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列入中央博物院人文馆专刊之二出版,次年又出版了《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共收录2121个纳西象形文字,共208页。《么些标音文字字典》收录了2334 个标音符号,列举了最常见最常用的音字简表,共347个符号,内有异体字104个符号,其中17个字有分音调的趋势,在书后附有依照字型笔划排列的索引,字典把当时写法繁多杂乱的纳西标音文字进行了归纳。再版时两本字典合二为一,命名为《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2001),这本字典是纳西文化研究者和少数民族语言学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李霖灿对纳西族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涵盖纳西民俗的方方面面,通过分析李霖灿纳西族民俗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到各民族民俗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吸收以及融合的过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下多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系统阐释东巴载录民俗的历史记忆
李霖灿认为纳西族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智慧,非同小可,不说教而讲古,手法异常高明。因为大人小孩,都喜欢听故事。”[15]纳西族的故事都收藏在东巴经典中,有对哲学的思考,也有对生活的启示,更有对民族历史的记忆。李霖灿并不满足于只做收集工作。“时日渐久我便看出收集故事虽然不是一件大事,可也不见得那么简单,只靠舌人通译终不是一个彻底的办法,首先便须自己通悉那几百册象形文字的经典。好在自己在艺术学校学过几年绘画,描写大雪山固然是束手无策,但对付经典上这几个鸟兽虫鱼却还游刃有余,于是就向‘多巴’递了门生贴,像小学生样‘天地玄黄’来认识描画么些人的千字文。由文组句,看画会意,近一步就想涉猎他们的经典。这一来麻烦可就大了,文字关系语言,经典牵涉宗教,一转再转这场大梦就飘扬到民族学各个部门中去了。”[16]从此就开启了李霖灿纳西族民俗文化的调查之旅。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追溯祖源地的习俗。人们由于迁徙或其他原因不能返回自己的故土时,仍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回归故里,因此人们会把沿途的路名记下来代代相传,记忆迁徙路线就成为族中某一些人的责任,纳西族传承者自然是东巴们。没有文字的就口耳相传,有文字的自然会将这条迁徙路线笔之于书,纳西族的东巴经中就记录了不少的地名。在众多的经典中,“祭祖”和“开丧”这两类经典引起李霖灿的注意,“祭祖”是把祖先由祖源地接到家来祭拜,“开丧”则是送亡灵回到祖源地的仪式。这两项仪式都需要东巴背诵一系列的地名,李霖灿还发现这些地名与其他经典中的地名不谋而合,东巴们大多能指出距离家一两天路程的地方,这也说明地名的真实性。纳西族地区民间还流传着,丽江县巨甸乡巴甸村有个叫和文裕的东巴,他曾以“起祖”“开路”经典里所记载的路线去追寻过纳西族的祖源地,一直探索到无量河中游一带,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才回到丽江。可见,当地也曾有东巴与李霖灿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更加坚定了李霖灿探求纳西族迁徙路线的信心。
纳西族的起源地和迁徙路线也曾有学者做过研究,1936 年,陶云逵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上的《关于么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17]是较早关注纳西族迁徙的论文,陶云逵认为纳西族最早是起源于西北康藏一带,但文中大多是根据史料进行推测,实地调查材料较少。1931 年约瑟夫·洛克(Joseph·F·Rock)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了这一带的地图和许多精美的照片。李霖灿认为陶先生的论证为他的实地考察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而约瑟夫·洛克对他了解无量河上游及贡噶岭雪山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两者都对迁徙路线考察提供极大的帮助。
纳西族的“起祖”路线在纳西语中称为祖先迁徙路线,即民族迁徙路线。1942年,李霖灿挑选了鲁甸县和世俊大东巴给束家写的一本祭祖经典作为主要参照本,并查阅多部经典后,根据经典上的提示绘制出102个地名的地图。经典中的神话给予了李霖灿很多的启示,如《敦与庶的故事》[18]讲到,在最早的时候,天地还没有开辟,日月星辰都还没有出现,还没有修起巨那茹罗神山。《分寿分岁的故事》[19]再次提到巨那茹罗神山已修好,从北边来了洛神(相当于所谓的阳神),从南边来了色神(阴神)。他们两人在山顶上相遇,那时的世界刚刚开辟,一切生物的寿命都还没有规定,因此就商议要为世间万物分寿分岁。李霖灿认为,这些神话中说得很清楚,这座人工修成的神山是人类通向天界的通道,可以推测为纳西族的祖源地。那下一步需要证实的就是神话中的巨那茹罗神山在什么地方,李霖灿仍然从神话中去寻求答案。当时在丽江以口头形式广为流传着一个《青蛙和乌鸦的故事》[20],故事讲述神人九兄弟去开天,神女七姊妹去开地,九兄弟懒惰,七姊妹勤快,最后是天小地大。老始祖某莉敦召集大家商议如何处理。大家都想不出办法时,神人就派乌鸦去请青蛙来想办法,不一会儿乌鸦回来,它说想到办法了,把大地折叠起来就好了。正当大家都夸赞它聪明时,青蛙出现了,青蛙说,这个办法是它告诉乌鸦的,这让乌鸦无地自容,同时也恼羞成怒,叼起青蛙准备吃了它。聪明的青蛙告诉乌鸦,它的肉是咸的,要放在水边的石头上,边吃边喝水,可乌鸦刚把青蛙放在石头上它就逃走了。李霖灿推测,从地理环境来看,这则故事很可能是创作于现今木里境内无量河一带。这一带是横断山脉的边缘,站在这一带的高山上看,可见山浪层叠,真有把大地折叠起来的感觉,而其他纳西族地区则没有这样的地形,神话中讲到大河中的石头,也只有这里最明显,因此无量河一带较有可能是纳西族的老家。《么些族的洪水故事》[21]中讲到,洪水从山顶上崩出水来,老虎跳不过,深谷变成泥潭,水獭也游不得,山峦重沓大水忽起的一幅图画,很像是“山洪暴发”的样子。唯一的幸存者瑳热莉恩藏在革囊存活下来。李霖灿认为洪水神话中描述的就是西康境内无量河峡谷地带。无量河是自北向南流的一条大河,于金沙江N 字大湾的北端注入金沙江。这条河流的峡谷地带是纳西古文化开拓的重要区域。住南边的纳西人,如丽江阿喜石鼓一带,用的是木船;住东边的,如永宁泸沽湖上,用的是独木舟,都不曾使用这种古老原始的革囊。但在叙述洪水冲天的故事中,他们却仍然说是革囊浮水,才使人类有了硕果仅存的孑遗。由此可见,这项古老传说的起源地点,当与革囊的地区近而与木质舟船的地区远。他当时调查时从木里境内俄丫地方过河到永宁土司地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革囊。李霖灿的论证体现了口头文学和民俗文化对历史研究的互证性方法。
纳西族民间仪式中的方位感,也从侧面反映出民族迁徙地。纳西族是一个喜欢占卜的民族,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占卜的民族。民间故事讲到,他们的占卜方法来自四面八方。东到川康交界处大凉山的牛牛坝,北到青海的果洛,西到西藏的拉萨及印度,南到大理昆明,从地域上的四至,也可以推测到纳西族古代文化区的中心是无量河一带,而不是在今日的丽江等处。[22]
李霖灿认为虽然仅从东巴经和民间仪式中对迁徙史的叙述,不能确定这是纳西族的起源地,但从这些资料中至少可以证明纳西族曾在一定时期内住在无量河及贡嘎岭大雪山附近,然后再由这里向南方迁移。根据丽江东巴的文字记录和永宁盐源东巴的口头背诵,可以确定纳西族的一支是由无量河向南迁徙的,因此,神话中的巨那茹罗神山,可能就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贡嘎岭大雪山。
李霖灿以神话和仪式推断出纳西族的祖源地后,他从丽江西北区出发(鲁甸的白罗岔),经中甸、永宁、木里到无量河边,只要渡过无量河向北走7 个地方就可到达神话中所说的巨那茹罗神山,但由于当时无量河一带正在闹匪患,无奈只得在无量河边止步。[23]李霖灿虽然没有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但沿途的调查使他获得了不少的民俗文化资料,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纳西族的迁徙路线进行论证。纳西族在无量河上游一带是自北向南迁徙的,到无量河的中游一个叫索洛的地方分两条路线迁徙,一支走向东地,经木里、永宁来到盐源、盐边一带,一直到西昌附近,这是没有发明文字的一支。另一支仍向南行,沿无量河的流向,一直到金沙江N字大湾的北端,无量河流入金沙江,他们又追溯金沙江来到中甸县属的北地。在这里“多巴教”(东巴教)得以发扬光大,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经典就有三百多本,使北地成为“多巴教”的圣地,至今仍有“不到北地,不成多巴”的俗谚。到北地之后,他们仍继续向南行,在打鼓地方渡过金沙江,迁徙到丽江,即从现今纳西族的大本营,再向南到达鹤庆县交界的地方,与民家(白族)相遇后不再向南迁徙,而是取西北方向经石鼓镇、巨甸镇、鲁甸县,到达维西县境,这可能是明代末叶后纳西族人新开的殖民地。有文字和没有文字的纳西族在他们迁徙的下游没有再会合在一起,所以形成现今一支有文字、另外一支没有文字的地理分布现象。李霖灿能对纳西族的迁徙路线做出如此详细的论证,与现代学者对田野调查反思时,提出的“将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24]理念相一致的,这也是提高田野调查的水平与质量的有效路径。他对纳西族迁徙路线进行调查时,详细地梳理和阅读了多部纳西族象形文字经典,将经典与各地民俗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纵向的历史分析与横向的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探讨史料记载较为匮乏的纳西族历史是一种可以借鉴的办法。
三、推动纳西族象形文字规范化,助力口头文学传承
民族语言文字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记录着不同民族的生活实践,蕴含着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25]纳西族不仅有丰富的口头文学,还有独具特色的象形文字和标音文字,虽然李霖灿只收集到3 本标音文字的经典,但对研究纳西族文字意义重大。纳西族民间故事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故事情节还引人入胜。李霖灿给予纳西民间故事高度的赞扬和肯定,“么些故事不仅只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已,简直有点像圣经的文体,又有点像托尔斯泰所记的俄国民间故事的情调呢!节奏如此爽朗,词句如此委婉,结构如此曲折,只须随手记下,便都是动人的绝妙好词,合起来一看,便是一篇欲同希腊神话争美的边民故事”。[26]纳西族文字的出现在促进口头文学传承的同时,也促使口头文学的内容更加完整和丰富。
李霖灿从1939年初夏到丽江后不久,就对纳西族象形文字产生了兴趣。他认为学习文字需先学习语音学,在丽江调查时先后通过书信向方国瑜、葛毅卿请教过语音知识,回到李庄后,得到傅斯年的允许,又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组内,与张琨学习了3 个多月的语言学知识。1944 年4 月《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出版,一年后又出版了《么些标音文字字典》(1945)。纳西族文字字典的出版,标志着向文字的规范化方面发展。语言学家们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济在序言中写到道:“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问题的人,已日渐增多了。要认识这些问题的真面目,最要紧的似乎是应该听说他们的话,读他们的书(假如有的话)入手。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如民族学、比较语言学,自然更应该走这一条道路。人类虽说是用文字用惯了,但创造一种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中,并不是常见的事。有了这件事,无论它出现在地球上哪个角落里,都值得若干人钻研一辈子。”[27]李济既肯定了纳西族语言文字在人类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又看到语言是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鼓励青年学者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时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董作宾赞扬李霖灿的纳西族象形文字研究是“譬若积薪,后来居上”,并认为纳西族象形文字为研究甲骨文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28]
纳西族象形文字主要用于东巴经的书写,书写是为了更好记忆的需要,口头文学和东巴经典两者在传承过程中相辅相成,促进了纳西族口头文学的传播。洪水神话是各民族都具有的一种神话类型,也正因为纳西族的洪水神话有文字进行记载,在李霖灿看来更生动有趣,“么些用图画文字记录下来的,在全世界尚没有比么些文更完备更意趣横生的样本。洪水故事极有价值,就故事的本身论,情节极为曲折复杂而动人,在我看到或听到的洪水故事中尚没有见到这样的好材料”。[29]杰克·古迪(Jack Goody)谈道:“书写文学从来不是简单记录已有故事,神话或故事总是在‘抄写’过程中,随着一系列新文体的出现,以及旧文体的修改而发生变异。在某一历史时刻,书写能让人们把口头记忆作为回忆此类作品的方式,这类记忆的角色其实还有所提高。”[30]可见,由口头到书写是对讲述文本完善的过程,在书写的过程中会附带着书写者的情感,使文本内容更具有书面文学色彩则需要在口头文学上的再创造,反过来又促进口头文学的发展。纳西族象形文字出现后,东巴经书已成为东巴口述的附带记录,东巴们通常在记诵东巴经书后,不再看着经书大声阅读出来,而是口头叙述,口头叙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对书面文本再创作的过程。李霖灿对纳西文字典的编撰工作,促使纳西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形成一套书面记录传统,推动了纳西族民间文学的传播和传承。
四、探求纳西族民俗传统的多元文化融合
纳西族的经典是为了服务于民间信仰而存在,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不仅仅只是此目的,正如马凌诺斯基所认为的那样,宗教的功能,即由分析宗教如何与其他社会活动发生关系而服务于人类。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是适应个人及社区的一些深刻的——虽然是派生的——需要的。[31]宗教信仰不能离开社会生活而单独存在,李霖灿对纳西族经典的研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把民间信仰放在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调查研究。李霖灿在调查中特别注意收集经典,他在纳西族地区调查的4年时间里,共采集到的象形文字经典1230册,标音文字经典3册。这些经典体现出民族的智慧,是民族的百科全书,更能体现出多民族“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
纳西族的《洪水神话》中讲到,洪水过后仅存的男主角瑳执莉恩,娶得天女翠海苞波后,生三子,分别是后来的古宗(西藏人)、么些(纳西族)、民家(白族)三族。从纳西族“共母”神话可以看出各民族之间是“兄弟关系”,具有“血缘”亲情。“共母”神话是一个无价的精神源泉,反映各民族“和而不同”“不离不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取向,对调适民族关系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文化意义。
纳西族不仅是占卜的民族,而且还是一个善于学习占卜的民族,“对干支的学习来自于汉人,一种炙羊髀骨看兆文的占卜方法来自于凉山倮倮族人(彝族);掷骰子占卜法来自于民家人(白族);打竹片卦来自于栗粟人(傈僳族);抽线图片卦来自于古宗人;鸡胫骨卦来自于鲁鲁人。他们不仅学,而且学得很到家”。[32]善于学习的民族也是善于交流的民族,纳西族对占卜的学习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纳西族在经典和口头都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神通广大的大神多巴神罗为了不受鬼的侵扰,需要古宗人的巫师,民家人的巫师和么些人的巫师共同为他念经做斋,才能保他平安无事。此类神话反映出纳西族社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深蒂固,像多巴神罗这样的大神的力量也是有限的,需要与其他各民族共同合作才能战胜困难,体现了纳西族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叙事和族群记忆,巩固和强化了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交流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事实。
结 语
李霖灿在纳西族地区调查是以当时民俗为根本,关注活态的民俗事项和生活意义,因此,他特别注重田野调查,强调文献资料与民俗生活的互渗互证的关系,强调民俗的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谱系。他的研究没有运用过多深奥理论,对纳西族民俗文化研究都是以身历其境的体验和直接的文化接触为基础,他在实地研究方面的积极推介对增进文化了解与交流都具有开拓性意义。他在纳西族地区的实地考察中,运用参与观察法,以“局内人”的视觉去观察、体会和理解纳西族文化,在调查中与纳西族民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我们呈现了负有“温情”的田野调查。
李霖灿在纳西族地区的四载时光,收集到经典上千册,为纳西族保留下来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以田野调查来解读纳西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方法,对民俗学者具有启示性,纳西族象形文字书写的经典是散漫速记式,要明白经典内容需要对东巴文解读和了解纳西族的民俗文化,通过田野调查来解读这些经典就变得至关重要。为了调查纳西语言文字、民间习俗,他寻访纳西族迁徙路线、拜访当地东巴人、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他在调查过程中始终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他者文化,让自己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与他们感同身受,理解他人的理解,尊重他者的文化,当时丽江纳西族地区由于受到汉化的影响,大多数民众对纳西象形文字持鄙弃态度,把象形文字称为“牛头马面”,李霖灿与东巴交流时给予象形文字充分的肯定和认可,东巴都没有想到他们的文化竟然受到汉人的赞许,一个个都对李霖灿心存感激之情。他带着“温情”做田野调查,他与纳西族知识分子周汝诚、大东巴和文质以及调查助手东巴和才等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田野中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得他的调查更加深入,材料更加真实可靠。
随着学科建构的发展,分支学科不断出现,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也变得多元化,多学科相互借鉴已成必然趋势。从李霖灿的学术历程认识到,民俗学的调查研究只有掌握了多学科知识,才能以多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李霖灿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出于对图画的敏锐力,当他第一次在古琴手郑颖荪先生处看到东巴象形文字写成的经典时,便下定决心为文学上的国之瑰宝贡献此生。此后又在沈从文和董作宾两位大师的帮助下,指引他走上纳西族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之路,他在调查和研究方法上受到过凌纯声指导,语音学方面,曾向方国瑜、葛毅卿、张琨等人请教并学习过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正是李霖灿善于学习的精神,使得他不拘泥于某一学科领域的方法来调查研究纳西族民俗。他的研究实现了现代学人知识应用的本土化,对民俗学现代学科理论的建构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