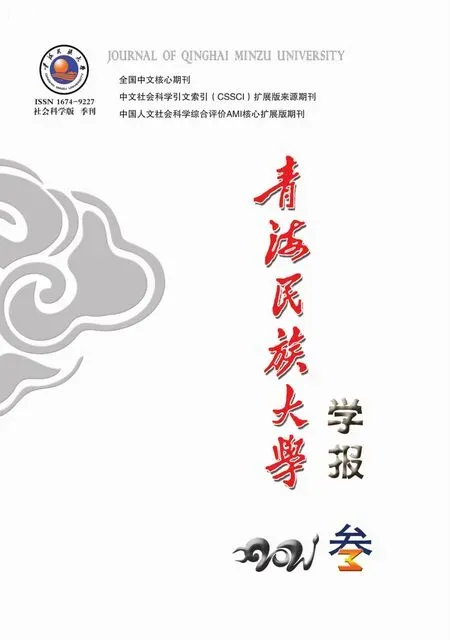发现女性:论于式玉藏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贡献
郑 莉 张慧敏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610065)
埃德温·阿登纳(Edwin Ardener)认为女性常常处于相对沉默或是失语状态,她们的世界观同以男性为主的权力团体存在差异,这使她们的发言权受到约束[1]。在人类学中也是如此,人类学家或是男性,或是接受过男性偏见训练的女性,无一例外都处在男权文化的覆盖范围内[2]。因此女性在早期人类学中始终处于隐身状态,不管是作为研究人员还是研究对象,女性在人类学学科的概念和理论中都位居边缘或是直接缺席。[3]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一些广为人知的女性人类学家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以外,人类学不乏其他女性的参与,尤其是男性人类学家的妻子[4],然而一直以来,她们的贡献总是被忽视、被掩盖。
于式玉就是这样一位被低估了的女性人类学家。于式玉拥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具有语言天赋,擅长文献目录,又愿意开展实地调研,不仅协助丈夫李安宅进行学术研究,其自身也致力于边疆考察研究和藏区教育事业,著述了许多相关文章[5]。于式玉比李安宅更早来到、也更晚离开拉卜楞,对拉卜楞及其周边游牧地区进行了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考察,清晰地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该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境。但相对而言,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思想近年来逐渐受到了较大的关注,而于式玉的研究大体上还依附于李安宅,其学术独立性尚未取得足够重视。[6]于式玉的作品因与当时的经典民族志有所差异而没能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但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为藏学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探索带来了很多启示和范例。她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对边疆教育事业的投入促进了汉、藏民族之间的交融与团结,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追溯于式玉的学术和人生,不仅能让我们对当时的涉藏地区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也让我们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女性视角、经验和贡献有更多的认识。
一、于式玉生平与学术简介
于式玉教授(1904-1969),女,汉族,山东临淄县人,曾任华西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是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李安宅教授的夫人。她早年考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学习音乐,又入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文史。1930 年在日毕业后,回国与李安宅完婚,后就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兼任北平国立女子文理学院日文、日本史讲师。1938年,于式玉去往甘肃,不久又在拉卜楞地区设立当地第一所女子小学,还帮助当地成立卫生所。1942 年离开拉卜楞后,在华西大学任华西边疆研究所任研究员兼社会学系副教授。1943 年底,于式玉与蒋旨昂前往川西理番黑水地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整理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1950 年,于式玉随李安宅一起作为藏文化专家参军进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8 军研究室工作,投身于昌都、拉萨等地的教育培训、文化沟通工作。于式玉转业后,同李安宅一起在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工作,后调往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1969年,于式玉因病去世。
199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收录了20 篇于式玉的文章,这也是她唯一的藏学专集。[7]《文集》是于式玉在抗战年代亲自前往甘南和川西北涉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后的心得合集,包含了于式玉对边疆地区的宗教生活细节、妇女的生活史、民间文艺、风俗民情等的考察和著述。李绍明认为《文集》有三个特征:一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二是揭示了当时涉藏地区存在的社会问题,并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及当局者的忽视;三是对藏族的宗教和民间文化、风俗习惯进行了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考察和分析,弥补了当时藏学人类学研究的某些缺失之处。[8]《文集》立体详细地呈现了边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性格等社会文化、精神图像,由此可窥见于式玉对涉藏地区社会所作的考察研究的学术、社会价值,值得当今人类学者吸收和借鉴。本文就《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做一些探讨。
二、于式玉的主要研究方法及特点
(一)以功能主义把握“他者”文化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民族志范型以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为主导,融合马林诺夫斯基的生理、心理需求——文化满足功能主义,并以中国的历史学派加以补充和修正。[9]功能学派认为需要将文化当作一个合成体来研究,抓住文化各要素的主要社会功能[10],并从社会文化体系的现实意义角度出发,去探寻世界观、文化的整体结构和内在功能。研究人员需要走出书斋这座“象牙塔”,在田野中开展比以前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常用的观察记录更加深入且系统的研究,[11]不仅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初步观察,更要弄清楚它的功能和作用,将理论与田野工作进行知识性的贯通。李安宅作为功能学派的译介者之一,从中汲取学术养分、批判继承了不少学术思想,这从他对祖尼人和藏区的实地研究中可窥一二。于式玉虽未系统接受过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的训练,但身处功能学派为主导的时代背景下,加之受到李安宅的影响,于式玉的藏学研究也带有明显的功能主义特点。她对为何要研究寺院布施这一问题的解释是,寺院在涉藏地区有着诸多功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的中心。看不见寺院,便看不见这一切;看清楚了寺院,藏民的全体动态,也就能知其梗概了”。[12]布施一方面是寺院维持生存的经济来源,一方面也是藏族对宗教虔诚信仰、替来世积聚福田资粮的体现。同时,在当时的涉藏地区,除了喇嘛和尚能够诵读佛经从而识字,普通百姓很少能够读书识字,可见在缺乏正式学校的部分涉藏地区,寺院还承担了教育的功能,“小孩要认字,唯一办法即是当喇嘛”。[13]在民俗方面,于式玉分析了藏族婚礼风俗的经济功能,“本族内不论哪家娶媳妇,各家的妇女都要盛装艳服到那家去唱喜歌酒曲。唱完一曲,便向当家人要钱……要得的钱是大家的,交给头人,算公款的收入”。[14]这种应酬往来,是部落生活的习俗,是“社会先于个人”原理的体现。此外,于式玉在《黑水民风》中还分析了“跳锅庄”的文化功能,跳锅庄一方面是边民社会对“锅庄”的敬意表达方式,一方面是“庆祝新谷入仓”的庆祝仪式。可见观察总结出文化的内在机制与主要功能,是把握“他者”文化的重要方法之一。[15]
(二)近似“深描”的阐释性描述
虽则于式玉的藏学研究带有功能主义特点,但她并非以单纯局外人的角度,使用跨文化的透镜对当地土著文化报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于式玉怀着对藏族同胞真挚的热爱之情,学藏文、说藏语、吃糌粑、住藏房等,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于式玉深深地融入进了藏民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从文化内部去研究和理解文化,因而在她的民族志中,人类学家与藏族之间存在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密切互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于式玉笔下,民族志不再仅仅遵循和追求科学、理性,而是透过公共符号深入藏族的内心世界,去观察他们的世界观、精神和感知。这样的民族志写作手法,显然不仅仅关注文化功能,还关注地方性文化中社会行为者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情感。[16]于式玉的这种研究和写作方法,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解释人类学是20世纪70年代继文化人类学之后,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卓越影响力的一个流派。格尔茨认为文化的分析并非如同实验科学一般探求普遍规律,而是作为解释科学去探寻意义,他主张“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民族志方法。“深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深度描述,而是在解释之上具有理解性的描述,不仅需要对田野中的现象进行客观的记载,“描述”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一个对文化所在的世界观、人观和社会观背景进行解释、说明和理解的过程。[17]例如于式玉在《拉卜楞寺祈祷大会的布施》一文中对百姓对宗教布施的态度及造成这种宗教布施行为的社会心理做了透彻的分析:
轮到一次,人们为了面子,为了光荣,为了替来世聚福田资粮,把日省吃俭用的积蓄,都贡献出来,不知再过多少辛苦经营才能恢复一点元气他们生产方式与技能不改善,恐怕怎样辛苦经营,元气也永远难恢复起来。
所受的痛苦,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恨起来的时候怨前世业果不好,因此极力设法想下一辈子得到解脱。而就不得不努力为来世集聚资粮。因这种关系,把现世看做苦海,离了现世就可超生乐土。所以不惜把今生所有的都为来世的缘故而布施出去,自己各处乞讨也无不可。这样看起来,他们今生的苦恼是甘心情愿吗?自然不是。(引自《文集》第11-12页)
宗教布施表面上是百姓对宗教的信仰,实则是百姓对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希望。在这样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并非如同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只将文化当作是躺在手术台上等待解剖的躯体,[18]而是一个对藏族社会及藏族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文化精神有着充分尊重和深入理解的人类学家。在解释人类学正式诞生之前,于式玉在对涉藏地区的研究中便不自觉地使用了接近于“深描”的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研究强调“全观性”的宏大叙述结构,将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黏合起来,并梳理出具有人类共通性的社会规律与理论,从而达到社会秩序的控制与稳定。而于式玉则并未完全陷入功能主义对文化的模式化和简单化,她深入研究对象之中,致力于从地方性文化的自身特性去挖掘和理解宗教行为、风俗习惯背后的意义,强调涉藏地区社会复杂的专门性和情景相关性,注重文化“被分享的意义”,在文化的环程中实现文化交流。
(三)性别自觉下的女性经验呈现
田野调查很难做到完全的性别中立,研究者的性别身份会使他或她的田野调查过程或多或少被打上性别特征的烙印。[19]早期的人类学家多数是男性,所调查的对象也是男性,研究方法也以男性活动为中心,女性则居于从属地位,是被建构的“他者”。1848年至1920 年,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其后,女性主义人类学逐渐发展。[20]女性主义人类学更侧重研究女性和社会性别,将女性眼中的世界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展现出来,并两性关系作分析探讨,“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 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21]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很难说于式玉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但女性身份让于式玉具有一种性别自觉的特征。这种性别自觉源自女性独有的、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使女性能够表达和解释对社会实在的独特观念,从而让于式玉在关注领域、研究方法和书写路径上都与同时期的男性人类学家有所不同。虽然于式玉的研究并未挑战当时的主流人类学研究范式,但的确弥补了当时中国的藏学人类学研究中个女性视角的缺失。
1.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
多数传统研究脱胎于男性经验,仅着眼于男性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22]人类学经典著作中虽不乏对女性的记载和描述,但她们的生活记录在被世人所看见之前已接受了男性的过滤和解释[23]。于式玉作为女性考察者,从女性经验视角出发,着眼于与她朝夕共处、共同生活的藏族妇女,对同时作为文化创造者和生产实践者的她们进行分析,描述和研究了许多妇女问题。于式玉对边疆民俗风情的考察细致入微,这通常是男性研究者不宜“走进现场”或者不受重视之处。[24]于式玉研究了多是藏族妇女参加的“坐娘乃”、藏族妇女的梳发、藏族妇女的宗教地位、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等,她还不吝惜笔墨重点讲述了同院的藏族女性万慕错的生活史。于式玉的研究并非仅仅展现社会事实,还意在深入挖掘事实背后的社会文化观念。例如她细致入微地观察和考究了拉卜楞藏族妇女的梳发行为,并描述了她们在生命不同阶段的发型及不同阶级女子发型配饰的差异。事实上,同时期的其他内地旅行者也曾关注到拉卜楞的女性群体。明驼认为拉卜楞具有“母系社会”的特质,因为“藏族女子只娶不嫁,生产的活计均由女子承担,婚姻关系破裂男子只需离开女方住宅或帐篷”。[25]葛赤峰则考察到藏族认为女子必先修成男身才能修行佛法,进而推断出藏族妇女地位远不如男子。[26]与上述隔岸观火式的“他者”眼光不同,于式玉在涉藏地区生活时,以女性的主体身份与藏族妇女融为一体,消解了研究主位和客位之间的对立,她深入细致地观察和呈现出藏族妇女自然的生活图景,而不只是让他们生硬地回应研究者的研究问题。
2.重视个体叙事
所谓科学研究中的客观资料与普遍定律,均建构于特定的社会性别、阶级、文化、历史与权力体制[27],启蒙思想遵循具有普遍性的“宏大叙事”,将作为人的个体掩盖在了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之下,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具有意义。当时对涉藏地区的诸多研究,多从区域观照的整体视角入手,上升至宏观结构层面去探寻和讨论族群、地方、国家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28]于式玉虽未完全脱离这种“整体主义”式的研究特征,但她极大地关注了被研究者的个体经验叙事,注重实际的个体在实际中开展的现实活动,强调当事人的经验,并从他/她们的经验、角度了解社会现象。在《麻窝衙门》一文中,于式玉对“头人审官司”的描写主要由一场具体的官司展开,在审官司时,头人苏永和“见诉讼人那种不胜恐慌的样子,等他说到一段落时,便借机哈哈大笑起来”,“趁着空气松动,他便命娃子拿出咂酒来赐予告状的人,用这种方式缓和他们恐惧而紧张的心理,同时使他们感到头人和悦可亲”。通过对这些官司中苏永和与诉讼人的互动描述,展示了苏永和能够一统黑水的独特治理模式。于式玉对苏永和着墨颇多,详细描写了苏永和借助姻亲和血缘关系达到政治上扩大统治范围的做法,塑造了一个“坚强沉毅”“深谋远虑的边民领袖”形象。传统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备受功能主义的影响,对“当地人”形象的描绘多是面目模糊,但实际上,将行动者置于中心的民族志同文学作品一样有着通过塑造人物来直指人心的作用。[29]研究者所描绘的是另一个族群的生命、经历与见解,绝不能用学术语言来替代当事人的生活语言,更不能用学术语言居高临下地驱使当事人的主体声音。[30]文化从来不是独立于个体的神秘统一体,带来变化的力量存在于活跃的个体之中而非抽象的文化之中。在于式玉的研究中,黑水头人苏永和、麻窝夫人高丽华、活佛嘉木样、同院妇女万慕错等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展现了宏观社会结构下的微观个体形象。
(四)以民间音乐透视涉藏地区文化
自马林诺夫斯基在特布里安群岛开创出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田野研究以来,人类学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更为注重探索不同民族的各色文化特性。西方的音乐人类学也受到了人类学思潮的影响,开始在异国他乡的田野中寻求对异文化音乐中特殊性的解释,而非像比较音乐学时期那样仅在实验室或书斋中开展研究。[31]就民族音乐学而言, 由于“音乐事象在一定的空间内,无时无刻不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32]因此研究此种“动态的生命力”成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重要和核心内容[33]。音乐作为“他者”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正如于式玉在《文集》第70 页所写:“文艺是社会的产品,民间文艺更是与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拿一个歌来研究,可以找出当地文化的水准。什么风俗道德,什么人情世故,生活状态,都不难反映在里面。”[34]于式玉早年曾在日本东洋音乐学校学习音乐,后又在日本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文史,这段经历使她对边疆地区文艺的考察显得如鱼得水,例如她对拉卜楞涉藏地区民间文学的研究即是从当地民歌入手。在不常使用文字的藏族中,民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礼仪生活、祭祀生活、节日庆典生活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于式玉对拉卜楞藏区流传的酒曲、情歌、神曲、工作曲和游戏曲的歌词和曲调进行了记载,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她敏锐地观察到拉卜楞涉藏地区除了本地固有的歌曲,还传入了康藏地区的流行歌调。[35]于式玉还简要分析了民歌歌词中的意象,既有地理概念、自然现象、人物形象和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信仰对象等。民歌被归属为“集体的认同”,它不具有个体作曲家,它的基础便是成员共同分享的音乐系统和共同记忆,作为一个集体有机体的生命系统和认同系统。[36]对拉卜楞涉藏地区民歌的研究,能够让我们获得该地区音乐和文化的真实认识和客观评价。
三、于式玉的边疆服务及对民族团结的追求
人类学自诞生起就怀揣着对人类社会有用的期望,然而长期以来,主流人类学的学术志趣都是理论研究,而非实际应用。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学科的分支之一,它力求把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方法和研究成果运用于改善人类社会生活和解决社会文化问题,从而使人类社会朝着更健康、更进步的方向前行。[37]于式玉十分注重将调查研究工作与服务工作相结合,她曾表示,“当时我的理想是通过服务进行研究,通过服务研究来培养,使服务、研究、训练合一体”,这也是李安宅当时的主张。[38]
于式玉认为大多数藏族生活贫困的原因,一是遭受民族歧视政策和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二是贫苦藏族的低文化素质阻碍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39]所以于式玉一方面呼吁政府要重视藏民的贫困问题,一方面力求在行动中为藏族赋权。在藏族传说和佛教经典中,女性是“罗刹”,在灵魂上比男子低一级,同时在社会中,妇女无权过问部落对外事务和宗教祭祀事务等,但“一切劳动的工作都是担在妇女的肩头之上”“一个藏民女孩子,在家庭之中,她可以是个主人,也可说是个奴隶”。[40]可见,虽则相较于同时代受到封建礼教的汉人妇女,藏族妇女已属较为开放的群体,但其仍处于男权社会之下,无法拥有和藏族男子相同的各项权利。作为亲历辛亥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女性学者,于式玉对男女平等有着执着的追求,力图从教育层面帮助藏族提高文化知识以促进性别平等,将研究成果直接应用、服务于社会。当于式玉在拉卜楞看到旧城里的小学只限男子入学,且无专门的女子学校的时候,她认为“在世界这样进步的时候,未免有点畸形”。于是她创办了拉卜楞寺地区第一所女子小学,并义务教学四年。他们1939年申请拨地建校,1940年4月建成“拉卜楞女子小学”,宫保错任校长,于式玉做主任。第一天到校学生仅18 人,时隔不到一月便有40 余人,待1942年于式玉离开时已有一百三四十人。[41]这是拉卜楞地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女子学校,甚至被认为是“在任何藏族地区,这也是第一所,是专为藏族女孩子设立的”学校[42]。于式玉在拉卜楞的创学经历,为其后于昌都创办东学和小学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于式玉在文化教育上做到了理论和实践合一,她投身边地、推动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务实和坚韧精神是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于式玉在边地教育工作实践中十分注重藏族的国家认同问题,认为“要使边民认识国家,了解国家,促使他们了解的步骤,便是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灌输他们的现代常识”。[43]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于式玉通过教育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显示了她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把握,[44]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 语
科学并非价值无涉,它产自具有自我意识的科学家们,而个体的科学意识会受到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传统知识论中的内容、方法论和实践都围绕着男性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以男性价值观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于式玉作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中的重要女性,对她的研究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一窥当时如火如荼的华西学派中的女性书写。于式玉从功能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又不自觉地结合了解释性描述方法,以女性视角呈现了女性经验和微观个体叙事,同时她的音乐和文史学习经历使她对涉藏地区文艺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于式玉为社会留下了优秀的早期民族志,呈现了早期涉藏地区的社会事实,为我国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早期建设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追溯于式玉的学术人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女性视角、经验和贡献有着整体关照和更多思考。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45]于式玉在学术研究之余,还致力于将自己的知识和理论直接应用、服务于社会,她长期投身于边疆民族事业和社会教育事业;拉卜楞女子小学为近代边疆教育事业的初步转型做出了一定贡献,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护祖国统一、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于式玉的人类学研究不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立体的拉卜楞宗教和世俗社会,也为如何从多层次多角度观察和建设新时代的涉藏地区社会提供了对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