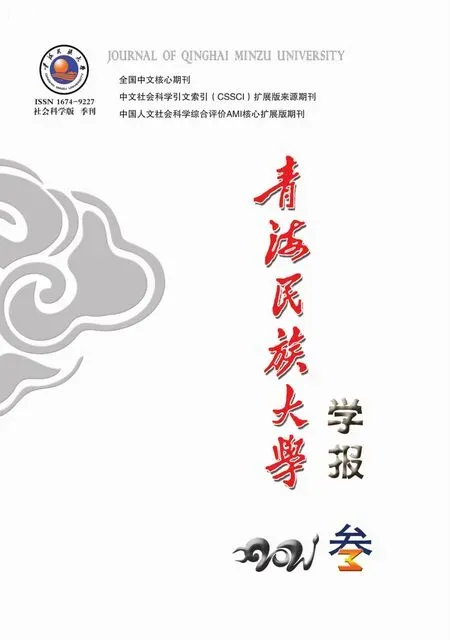新西兰毛利人“豪”(hau)的人类学解读
——以《毛利人与现代性:鲁亚塔拉之死》为中心
李丽琴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810007)
深圳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杨中新在其《毛利人口及其祖先探源》一文中,从人种、人口、经济、文化、语言、遗传、考古等方面对毛利人祖先的渊源进行了详细考证,认定新西兰毛利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国的百越民族。[1]根据《环球时报》1998年8 月23 日的报道,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著名分子系统科学系钱伯斯(Chambers)教授在研究时将毛利人血液中的DNA 信息与世界各地其他人种的遗传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后宣布:波利尼西亚人和毛利人的远祖来自中国的台湾岛。[2]新西兰原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也持有相同观点,他于2006年7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上说:“毛利人是中国人!新西兰的第一批居民是中国人的后代,基因证据显示毛利人起源于中国。”[3]
对于新西兰的毛利人,中国学者们大都对其文化给与了极高的关注,包括诗歌、战舞、美术、语言等,但是对于新西兰早期毛利人“豪”的研究十分少见,鉴于此,本文基于人类学家安妮·萨尔蒙德(Anne Salmond)的论文《毛利人与现代性:鲁亚塔拉之死》,通过对新西兰毛利人“豪”(hau)的人类学解读,以期学者们能对起源于中国的毛利人的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人类学家安妮·萨尔蒙德(Anne Salmond)在她的论文《毛利人与现代性:鲁亚塔拉之死》中详细地叙述了19 世纪初在新西兰一位叫鲁亚塔拉的位高权重的年轻的毛利族酋长从与欧洲人的接触到互赠物品直至受到欧洲人带来的所谓“恶灵”(auta)的搅扰而死,失去了“豪”(hau),即“生命之气”。鲁亚塔拉的死真的是因为欧洲人带来的恶灵吗?“豪”难道在万物与人类中都存在吗?馈赠的物品包括思想的交织、文化的混溶都存在“乌图”(utu),即“回报”吗?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曾阐述,文化不能视作一堆偶然集合的“特质”。因此,在新西兰毛利人的文化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事实,“豪”必须结合“乌图”和“恶灵”这两个要素,才能更好地解释“豪”。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偶然连接,而是紧密相连且缺一不可。本文试图借助人类学中的功能分析法,在以鲁亚塔拉为代表的毛利人与欧洲传教士互动的布局下,对这三个密切相关的文化要素进行分析,透视新西兰毛利人的“豪”在其生活中的文化隐喻及功能。
一、人类学视域下的“豪”“乌图”与“恶灵”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不能视作一堆偶然集合的‘特质’,只有可以比较的要素才能相提并论,只有相合的要素才可以归入一个调和的整体。”[4]毛利语“豪”(hau)的字面意思是“空气”,在毛利文化当中,“豪”被解释为“生命之风”(wind of life)或“生命之气”(the breath of life)。从对“豪”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豪”是出于直接的人体需要,具有强制性。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最早在他的经典文本《礼物》中展开了对毛利人“豪”的人类学讨论。他认为毛利人的“塔翁加”(taonga,珍贵的物品)都是“马那”(mana,神力)的媒介,把本不属于自己的“塔翁加”占为己有,这个“塔翁加”就具有了“豪”(hau,赠与物之灵),会给自己带来厄运。莫斯认为“豪”的产生促使人们在物质交换中有义务进行物物交换。
但是萨尔蒙德认为莫斯对“豪”的阐释只停留在了表面,她认为新西兰毛利人的“豪”实际上起源于他们对宇宙的认识。毛利人特·科胡拉于1854年记录了关于毛利人的这首宇宙圣歌:
升腾于生长之源,
思想源于升腾,
心智源于记忆,
渴望源于心智。
知识有了意识,
它居住在微光之下,
普(黑暗)出现了,
黑暗为跪拜而来,
黑暗为跳跃而来。
密实的黑暗可以感觉,
这黑暗可以触摸,却看不见,
这黑暗以死亡而告终。
首因源自于虚无,
拥有虚无,
解脱束缚的虚无,
生长的豪,生命的豪,
留在了空旷的空间。
大气出现了,
漂浮在大地之上的天空,
漂浮在我们头顶之上的广阔天空,
留在了红光之下。
月亮出现了,
我们头顶上的天空,
留在了光芒之下,
接着太阳出现了,
光芒万丈,
照耀着天空。
晨曦、清晨、正午,
天空洒下了白昼的光辉。
接着陆地、诸神和人依次出现了。[5]
在毛利人看来,言词承载着无比的力量。从这首神秘而又朴实无华的圣歌里,萨尔蒙德推论出:在新西兰毛利人的文化当中,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万物与人类都是由“豪”形成的,“豪”这一生命之气(the breath of life)产生了光界下的万物。毛利人的首领通过血统承载着祖先们的“豪”,与祖先们的塔普(tapu,禁忌)和马那(mana,神力)一样,“豪”存在于整个亲族当中。
根据萨尔蒙德的调查,在早期毛利人的文化观念当中,所有外来物品、生物和人员都附有超自然的“恶灵”;“恶灵”的力量会损害毛利人的“豪”,因此需要有“乌图”;“乌图”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通过摧毁这个“乌图”所附有的“豪”,使得生命之气得以恢复,在此情形下,“乌图原则或等价回馈在个体与群体间就产生了互惠交换,乌图原则也朝着平衡的方向发展。”[6]然而萨尔蒙德又强调,在乌图原则的互惠关系打破或者说拒绝进入互惠交换的情况下,毛利人的“豪”就有可能被摧毁,个人或群体将遭致厄运。根据毛利人的宇宙观,以及他们自古就有的“恶灵”和“乌图”的观念,不难看出这三个文化要素有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
二、鲁亚塔拉与欧洲传教士
(一)鲁亚塔拉
鲁亚塔拉在新西兰毛利人的历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新西兰岛屿湾的一位年轻的部落首领。尼古拉斯,这位曾与鲁亚塔拉一起航行并在鲁亚塔拉的家乡进行传道的英国自由移民这样描述鲁亚塔拉:“精力非常旺盛,高个子透着威严,肌肉发达,面部表情丰富。我毫不犹豫地说:‘他的仪态风度充满了尊严和高贵,似乎有意让当权者感到卑微,他的眼睛明亮闪动似乎不是普通人的双眸,他在族人中的威望越来越高。’”[7]
在尼古拉斯的眼中,鲁亚塔拉是一个纯洁和纯粹的人,他比文明人强壮和敏捷,同时他又比文明人低劣和愚昧。
据萨尔蒙德的叙述,鲁亚塔拉1805年在悉尼的约翰逊港口登上了欧洲的捕鲸船,当了一名水手,远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行捕鲸活动。1806年,鲁亚塔拉在悉尼下船,并在这个地方遇见了欧洲传教士塞缪尔·马斯登(Samuel Marsden),他们的相遇成为了毛利人和欧洲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8]二人于1807 年分别乘船赴伦敦,马斯登赴伦敦招募去新西兰传道的传教士,而鲁亚塔拉则是想在伦敦见到乔治三世国王,因为“这样面对面的见面”(be kanobikitea)在毛利人的生命中是重要的,如果没有相见,那么“豪”不可能通过领袖的问候实现群体间的交换。[9]然而,鲁亚塔拉并没有实现他的愿望,1809年当船只到达伦敦时,船长并未允许他下船,反而殴打和凌辱他,并把他转移到了运送犯人去南威尔士的安妮船上。在安妮船上,鲁亚塔拉遇到了准备前往悉尼的马斯登夫妇及其家人,马斯登夫妇一路上一直照料鲁亚塔拉直到他恢复了健康。至此,鲁亚塔拉和马斯登的“豪”混溶到了一起。
当安妮船到达悉尼的杰克逊港口之后,鲁亚塔拉和马斯登一起下船并去了马斯登的农场。在这里鲁亚塔拉学会了种植谷物,特别是小麦,并学会了一些英语,对欧式的其他东西学会的更多。紧接着,他和三个毛利人伙伴坐上了一艘捕鲸船,船主答应返回岛屿湾。然而,当船到达岛屿湾时,船主拒绝让鲁亚塔拉和他的伙伴上岸,相反,这船开到了诺福克岛,在这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并被遗弃。鲁亚塔拉在诺福克岛上生活了几个月后,安妮船到达了诺福克岛,船长让他坐船返回了杰克逊港口。
鲁亚塔拉的航行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毛利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同时也验证了以尼古拉斯为代表的欧洲人对毛利人所抱有的种族歧视,即,他们是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劣等野蛮人,可以随意支配和控制,欧洲人这种天生的优越感促使他们不断地想去征服欧洲之外的“荒蛮之地”。
1811 年鲁亚塔拉终于回到了岛屿湾,并将在马斯登农场学到的小麦种植技术、建筑技术教授给了自己的族人。1814年鲁亚塔拉以翻译的身份和几位欧洲传教士以及他的叔叔乘船去了悉尼的约翰逊港口。1815年鲁亚塔拉和他的叔叔将马斯登传教团带回到了新西兰岛屿湾。回到岛屿湾之后,鲁亚塔拉病倒了,按照族人的说法,鲁亚塔拉将欧洲人的“恶灵”带回到了岛屿湾,毛利人认为把他们的“豪”和欧洲人混合在一起的代价是致命的,[10]“恶灵”吃掉了鲁亚塔拉的“豪”。1815年3 月3 日一大早,鲁亚塔拉死了,正如宇宙圣歌所说,他的“豪”升腾到了生长之源。
(二)欧洲传教士
《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第11篇引用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段表述,“在她(欧洲)长期以来保持的优越性,让她忍不住把自己装扮成世界的情妇,认为其他人类都是为了她的利益而生的。男人爱慕她,就像深刻的哲学家直白地赋予她的居住者自然优势,并且言之凿凿地说,在美国的所有动物和人种都是堕落的——甚至狗在我们的环境里呼吸一会儿也会停止吠叫。欧洲傲慢自负的事实已经不胜枚举。维护人类的荣誉,教会这个自以为是的哥哥谦虚地认为是我们的分内之事。”[11]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美国换成新西兰,或是所有欧洲人未曾到过的地方。
1769 年至1770 年,英国海军军官、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环绕新西兰南北两个主要岛屿航行,绘制了海图,作为太平洋上波利尼西亚三角区域之一的新西兰被纳入了世界版图,库克随后写出了有关毛利人情况和新西兰适合开拓为殖民地的报告。1777 年,在他的航行报告发表后,猎捕鲸鱼、海豹者,伐木者和其他寻求暴利的欧洲人纷至沓来,从此作为新西兰原住民的毛利人与欧洲世界联系到了一起。毛利人与欧洲人不断发生的战斗对当代毛利人乃至新西兰社会带来的后果无法估量,但是,正如萨尔蒙德所描述的那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双方走到了一起,这就是毛利人渴望欧洲的货物,而欧洲人垂涎毛利人的资源,如包括土地在内的海豹、鲸鱼、木材、亚麻、猪和土豆。
在鲁亚塔拉与欧洲人的交往中,英国牧师塞缪尔·马斯登是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正是他俩的深度交往改写了新西兰毛利人和欧洲人的关系,也正是马斯登于1815 年鲁亚塔拉死后在新西兰成立了第一所基督教会,标志着基督教正式传入新西兰。
据萨尔蒙德在论文中的叙述,马斯登在18世纪80年代被艾兰协会选为后备的神职人员,经过培训,他成了杰克逊港口的助理牧师,定居在了这个流放地,在这里他成了地方法官、富有的农民、首席牧师以及伦敦布道会塔希提岛布道的赞助人。[12]马斯登1805年在杰克逊港口遇到了鲁亚塔拉的近亲特帕希(TePahi),1806 年又遇到了鲁亚塔拉,这两次相遇或许让马斯登看到了毛利人的精神世界,他曾这样写道:“他们的精神就好像一块没有开垦的肥沃土地,仅仅需要合适的提升方式就能使他们与文明国家相称。我知道他们是食人族,一个野蛮的种族,充满了迷信,完全处在黑暗王子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我知道让他们真正摆脱残酷的精神枷锁和痛苦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十字架上救主的福音。”[13]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维护国家荣誉,教会这个自以为是的哥哥谦虚地认为是他们的分内之事”,马斯登决定去新西兰传道,并开始欢迎毛利人到他的家里做客,1807年2月,他坐船到英格兰征募赴新西兰传道的牧师。[14]
1814年马斯登把从英格兰招募的两位传教士派到了新西兰,一位是年轻的校长托马斯·肯达尔,一位是木匠威廉姆·豪尔,这两位传教士成了欧洲教会在新西兰的代理人。1815年马斯登和另外两位传教士制鞋商约翰·京以及自由移民尼古拉斯也乘船来到了新西兰。作为知识分子,这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带着欧洲自有的优越感、傲慢和自负,“响应着欧洲的‘一般常识’,即理性和真理是与基督教和文明生活密切相连,而野蛮生活却与愚昧和迷信相连”,[15]带着文化偏见开始了他们在精神家园用“文明”去征服“野蛮”的布道旅程。
三、“豪”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萨尔蒙德的论文里,她一一详细地用事实来探讨“豪”的具体表现形式。“豪”出现在不同的人或物中,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即“生命之风”“生命之气”或“赠与物之灵”。
从新西兰毛利人的宇宙观来看,万事万物皆有“豪”,生命之气产生了光界下的万物。“豪”在表现形式上包括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和混溶。
(一)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换和混溶的“豪”
1.鲁亚塔拉与马斯登的“豪”
可以说,从1806 年起到1815 年鲁亚塔拉过世,鲁亚塔拉的“豪”就与马斯登的“豪”紧紧交织在了一起。1806 年,鲁亚塔拉在悉尼遇见了英国牧师塞缪尔·马斯登,这次相遇成了历史上毛利人与欧洲人关系的转折点,促使马斯登产生了去新西兰传道的想法。1809 年6 月,他们在伦敦的安妮船上再一次相遇,对于马斯登来说,他认为是上帝在暗中帮助了他,为他去新西兰传道铺平了道路,而对于毛利人来说,这二人的“豪”在此已经混溶在了一起。鲁亚塔拉接受马斯登的邀请去了他的农场,在这里他学会了种植谷物,也学会了一点英语,对欧洲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根据埃尔佛雷德·克罗斯宾的观点,[16]作为文化个体,鲁亚塔拉也善于进行跨越文化的转换,他乐意接受欧洲高度便携的文化复合体,诸如欧洲的农业种植技术、建筑风格,并将其传播到自己的土地上。当他带着这些文化回到新西兰后,他在小山坡上修建了欧式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这也是新西兰“镇”的雏形,他还教自己的亲族如何种植小麦,并写信询问马斯登如何将小麦变成面粉,于是马斯登随船带给了鲁亚塔拉一个钢制磨粉机,一个煎锅和一个传教团。此时,他们彼此互相交换的“豪”处于互惠平衡状态,也就是说,乌图原则或者等价回馈在个体间产生了互惠交换,从而在宇宙关系网络里乌图原则也在朝平衡的方向发展。即便在鲁亚塔拉临终之前,他也特别叮咛族人待自己的小儿子长大一点后再将他送到悉尼的孤儿学校,使其在欧洲人中长大。由此看出,鲁亚塔拉是一位极富理性的首领,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欧洲人的文化,他愿意让自己的后代接受欧洲文明,也愿意让后代的“豪”与欧洲人的“豪”混溶在一起。
2.鲁亚塔拉与乔治三世国王的“豪”
1769年10月9日,詹姆斯·库克船长率船队带着礼物成功登上新西兰的土地,并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宣布拥有对新西兰的主权,至此开启了新西兰的被殖民历史。
在萨尔蒙德的论文里,她特意提到了鲁亚塔拉于1806年乘捕鲸船去悉尼,然后打算去伦敦亲自面对面地拜见乔治三世国王,因为这样面对面的见面(be kanobikitea)在毛利人的生命中是重要的,如果没有相见,那么“豪”不可能通过领袖的问候实现群体间的交换,[17]通过领袖的问候可以增添个人或群体的生命之气,这或许是鲁亚塔拉想见英国国王的目的。然而,当鲁亚塔拉1809年到达伦敦时,船长并未允许他下船,拜见英王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3.鲁亚塔拉与欧洲人之间的“豪”
随着传教团进入新西兰,鲁亚塔拉与马斯登之间处于平衡的“豪”被打破,这就预示着互惠关系的平衡崩溃了,[18]因此,“豪”联带着运气的好坏,毛利人相信“豪”里拥有不可见亦不可算的力量。与“豪”伴随而来的是“乌图”,这二者之间具有隐形的义务和强制性关系,而且它们也满足了个人机体的需要。“豪”“乌图”及“恶灵”在毛利人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若“乌图”中含有“恶灵”的话,就会给人带来种种不吉利的命运。
当鲁亚塔拉把马斯登和他的传教团从杰克逊港口带到新西兰几周后,他生病了,“他得病让他的族人联想到和欧洲人接触尽管很吸引人但是也往往充满了危险”。[19]毛利人认为是欧洲人的“豪”与鲁亚塔拉的“豪”混溶在一起,招致“恶灵”开始吞噬鲁亚塔拉的“豪”。在毛利人看来,欧洲人拥有自己超自然的“恶灵”,它们的力量可能会危害到毛利人。萨尔蒙德在她的论文中提到,欧洲船长把他的手表掉进了毛利人港口的海水里,当地人认为正是由于这个邪灵才爆发了传染病。[20]欧洲人以及他们的东西比如船只、枪支、铁器、动物、植物以及随身用具包括手表在内对于毛利人来说都附有超自然的力量,[21]这些超自然的力量会摧毁毛利人的“豪”。
萨尔蒙德在她的论文中描述到,鲁亚塔拉病倒之后,马斯登和欧洲传教士带着药物和食品去看望他,但是鲁亚塔拉的亲族认为他们的探望会打破毛利人的禁忌,因此拒绝传教士的探望,在马斯登用大炮威胁鲁亚塔拉的亲族后,他们允许了传教士进入鲁亚塔拉的隔离区,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毛利人禁忌被打破,导致鲁亚塔拉的亲族认为欧洲人的“恶灵”进入了鲁亚塔拉的身体并住了下来。在传教士们拜访之后的那天夜里,一颗流星划过鲁亚塔拉的家乡朗伊奥拉的夜空。第二天鲁亚塔拉就神志不清了,祭司告诉他的家人“恶灵”以蜥蜴的形式进入了他的身体,吃掉了他的呼吸(或者“豪”)和重要器官。[22][23]
正如莫斯在《礼物》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礼物之灵”的灵力保障人们自愿自觉肩负“回赠的义务”。[24]鲁亚塔拉在临终的前几天,得知马斯登和传教士要离开新西兰时,他吩咐妻子们赠送给他们上好的席子和一头猪,并让她们退还马斯登他们赠送给他的各种东西,包括放在身边的一对手枪。这不仅表明,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鲁亚塔拉履行了回赠的道德义务,同时也表明,作为部落的首领,鲁亚塔拉的“豪”直接影响着自己亲族的“豪”,他此时不再保留欧洲人赠送给他的物品,即“乌图”,将欧洲人的“恶灵”还给了他们,以此换取家人和亲族的平安。
(二)毛利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相互交换和混溶的“豪”
事实上,除了以上形式之外,不同文化之间的“豪”也在彼此交换着,混溶着,这就是跨文化。从1806 年鲁亚塔拉与马斯登的邂逅,到鲁亚塔拉生病直至死亡,毛利人的文化与欧洲人的文化就在不断地跨越彼此的界限进行着混溶和碰撞,不同文化当中的生命之气也在互换和排斥。
毛利人自身所固有的、独特的、延续几百年的文化创造与欧洲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宇宙论”就是它们的代表。毛利人认为,宇宙是以原始能量的突然爆发开始的,生命之气产生了光界下的万物,它强调生命的整体性与相互依赖。可在基督徒的叙述中,神的灵运行在空中,创造了宇宙的万物,欧洲人的宇宙观强调的是生命的分层与独立。在尼古拉斯和鲁亚塔拉一起航行的旅途中,鲁亚塔拉向尼古拉斯讲述了毛利人的信仰和宇宙观,尼古拉斯想当然地认为毛利人对宇宙的理解是错误的,欧洲的传教士们作为欧洲文化在新西兰的代理人,急于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传播到这块精神荒莽的土地上,好让野蛮人得到上帝的救赎。
毛利人的文明与文化是否和欧洲文明具有文化交流的障碍,即“铁幕”?事实证明,毛利文化与欧洲文化的“豪”虽然经历着排斥和碰撞,但是从一开始,毛利人和欧洲人还是能够彼此商议建设性的协议。[25]
鲁亚塔拉在马斯登的农场学会了农业种植技术和英语,并将其传播到了自己的土地上,而马斯登派去新西兰的传教士也学会了毛利人的语言与生活习惯,特别是鲁亚塔拉在自己传统的部落社区按照欧式的风格建立了“镇”。按照人类学家卡尔·G·西伊科维齐的观点,这显然是受到西方影响的结果,作为毛利人的缩影,鲁亚塔拉已经吸收了欧洲文化的“豪”。
四、“豪”“乌图”与“恶灵”的文化隐喻与功能
“豪”“乌图”与“恶灵”这三个文化要素似乎构成了“豪”得以存在的体系。要是有人给你赠送了礼物,你却不回报,或是回报的东西带有“恶灵”,那么你就伤及了对方的感情,甚至可以伤到对方所代表的群体的感情或命运,导致关系破裂。因此,“豪”是早期毛利人赠送礼物环节中整个群体必须重视的力量,它具有强迫性。
而“乌图”具有象征性。例如欧洲人的手表掉入海里,因此给毛利人带来了“恶灵”,引起了疾病,那么“手表”就具有了象征性,它象征着不顺和邪恶及超自然的力量,同时,“豪”与“乌图”似乎又具有了交感性,但是这种交感性在今天来看,它们只是人为的联想,为的是满足人们心理机能的需要。
“豪”“乌图”及“恶灵”有一种功能的和经验的真实性,因为当一物赠出之后,这一物就有了“豪”,随之就有对方给你的有形或无形的回报,即“乌图”。当这“乌图”给你带来不好的结果时,“乌图”就带有了“恶灵”,这一系列的完整反应并不是传统的,可对于毛利人来说又是经历过的,故而又是真实的,这一完整性社会事实又使个人或群体重新调整他们的行为。
出现“恶灵”后有无补救方式?三者能否互相转换?损坏对方赠与的东西,昔日的恩情、友谊,或热心被蹂躏,愤恨的诗歌,破坏的祈祷,无情的咒骂,故意和恶意的虚伪,这些举动不是传统的,而是自然而然的,他们都是“恶灵”出现后的补救方式。在毛利人的文化中存在两种重要的仪式和“豪”有关,一个是旺阿伊(whangai)仪式,就是将敌人首领的头发献给祖先,借此把敌人首领的“豪”让诸神吃掉;另一个仪式是卡伊(kai)仪式,把被征服的敌人首领的尸体在食人肉仪式上吃掉。[26][27]如果成功地进行了报复行为,亲族的“豪”也可以恢复。[28]
同时,“豪”“乌图”和“恶灵”这三者可以互相转换。根据萨尔蒙德的叙述,鲁亚塔拉死后,他的大老婆也随即上吊而死,他们的尸体此刻变成了“恶灵”,在三天的禁忌之后,鲁亚塔拉和他的大老婆的“豪”才会离开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右眼变成了世上活着的灵魂,他们的左眼变成了天上的星星”。[29]对毛利人来说,鲁亚塔拉的“豪”又回到了它的源头,鲁亚塔拉的死是“豪”的平衡关系的破裂,最后又通过死后三天的禁忌仪式使得这种破裂的平衡关系得以恢复,鲁亚塔拉的灵魂又获得了生命。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在朴素的人类心理上,或者说在生理上,有一种自然的对于死亡的反对,觉得死原不是真的,或以为人还有一个灵魂,而这灵魂是永生的等等,都是由于一种否认个人毁灭的深刻需要而产生的,这种需要又不是一种心理的‘本能’,而是为文化,合作,及人类情操的生长所决定的”。[30]鲁亚塔拉的灵魂获得了生命也体现了毛利人朴素的宇宙观,即,他的灵魂又升腾到了生长之源。
当然,“乌图”也可以转化为“恶灵”。当尼古拉斯拿走了马斯登赠送给鲁亚塔拉的手枪,即“乌图”,并把它扔进火里的时候,手枪爆炸后砸到了尼古拉斯的头,让他失去了意识,鲁亚塔拉的亲族认为这是手枪所附带的“恶灵”惩罚了尼古拉斯。
结 语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对价值观的定义,[31]毛利人的“豪”“乌图”“恶灵”的整体性社会事实明确体现出了毛利人的价值观。当毛利人送出一物或得到一物后,便产生了“豪”,因此也产生了需求。他需要有“乌图”,这是一个稳定的平衡交换,当这种稳定的平衡交换被打破后,“恶灵”就出现了,他的“豪”也相应地遭到了破坏,对个人或群体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毛利人为了消除这种“恶灵”带来的影响,会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手段,即,摧毁“乌图”。
正如毛利人的宇宙圣歌所叙述的那样,所有的生命和万物皆有“豪”,一切之间皆存有交换,互相影响。在今天的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和欧裔白人的文化依然在不断地冲突与和解,彼此之间的“豪”已混溶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