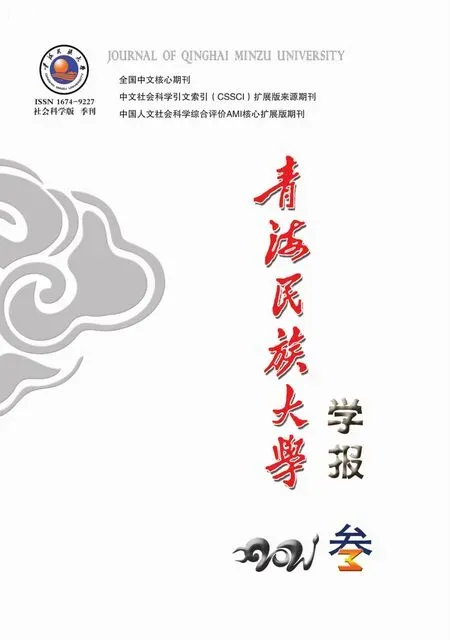延续与变革
——清代嘉峪关长城功能辨析
邓 涛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嘉峪关是明清时期的长城雄关,连接甘肃和西域,是明清两朝经略西北边疆的重要支点。关于清代嘉峪关的功能及其战略地位,以往有部分研究涉及。有文章研究涉及清前期嘉峪关的功能转变;[1]有文章研究涉及清代嘉峪关以西地区的移民与城镇;[2]有文章研究涉及清人对嘉峪关区域属性的认知;[3]有文章研究涉及嘉峪关在清朝西北丝绸之路中的地位。[4]综观以往研究,依然有以下研究空间:一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清代嘉峪关长城的军事功能以及清朝对嘉峪关的维修;二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清代嘉峪关地区的内地和边疆双重属性;三是关于清代嘉峪关在西北边疆经略中地位的研究还有深化的空间。
一、明清嘉峪关沿革及清人对嘉峪关的认知
由于嘉峪关在明后期和清初时一度为中原王朝疆域的边缘等原因,清人对嘉峪关及其周边地区区域属性的认知具有复杂性。
(一)明清时期嘉峪关地位变迁
洪武五年,明朝击败盘踞甘肃的北元势力,统一河西走廊地区,“以嘉峪关为限,姑置敦煌于度外焉”。[5]由于彼时北元势力依然出没在甘肃周边地区,明朝无力完全遏制,故相比汉唐和元朝,明代甘肃地区的流官体制有所内缩,在嘉峪关外实行羁縻卫所制。永乐时,明朝曾在嘉峪关外的哈密设立卫所,但并未在哈密长期驻军。嘉靖时期,由于吐鲁番东侵,明朝放弃了在嘉峪关外的经略,“诸番内徙,但以关为中外之巨防”,[6]明朝的西北边疆正式内缩到嘉峪关一线,嘉峪关的军事战略地位提升。
明清鼎革之后,清初嘉峪关以西地区依然为边外地。康熙朝之后,随着清代西北边疆拓展和甘肃地区行政变革,嘉峪关地区战略地位亦随之发生变化。左宗棠曾评价,“窃维甘肃地处西北边荒,旧隶陕西行省统辖,康熙年间拓地日广……”,[7]即相比明朝和清初,康熙朝之后的甘肃辖区得到了扩展。具体如下:一是“康熙二年以陕西右布政使驻巩昌,分领巩昌等四府,五年改为甘肃布政使司,移治兰州,是为省会”,[8]原先的甘肃右布政使逐步过渡为甘肃布政使,清代甘肃行省的版图初步奠定,原明陕西布政司、陕西行都司、陕西都司部分区域得到整合。康熙四年,在全国的政区改革中,“凤阳巡抚、宁夏巡抚、南赣巡抚俱裁去”,[9]而“以宁夏、平、庆裁归甘属”,[10]陕西布政司部分辖区划归甘肃,使得原明甘肃镇和宁夏镇合为一体,清代甘肃区划雏形已现。在这个阶段,嘉峪关是甘肃辖区的最西侧,也是清朝疆域的最西侧,依然是疆域的边缘。二是康熙末年、雍正初时,随着清朝开始经略嘉峪关以西地区,甘肃辖区开始向西北延伸,沙州、瓜州故地纳入清朝版图。乾隆朝实现大一统之后,新疆东部府州县在行政上受陕甘总督节制,亦受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统辖。这个阶段,嘉峪关开始从疆域的边缘转变为疆域的腹地。
(二)清人对嘉峪关及其周边地区区域属性的复杂认知
在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前,嘉峪关多被视为边地与内地的分界线。如乾隆十三年,甘肃地方官员提到:“甘郡内地,粮价虽贱于安西……”[11]在地方官员看来,相比嘉峪关以东的州县,嘉峪关以西甘肃安西地区并非内地,嘉峪关具有了界限边地和内地的地位。随着清朝西北边疆的拓展,乾隆朝时,嘉峪关从清朝与漠西蒙古对峙的前沿变成了大一统后疆域的腹地,清朝君臣也越来越将嘉峪关视为内地。《清朝文献通考》评价清朝统一新疆后的嘉峪关“至嘉峪关左右已居腹地,又无俟多兵驻守”,[12]认为甘肃以西、以东皆为腹地。彼时,清朝君臣将嘉峪关视为内地或腹地较为普遍。《(光绪)肃州新志》提到包括嘉峪关在内的肃州地区,“本朝开辟新疆,遂为腹地”。[13]但是,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后,将嘉峪关视为边地与内地分界线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如道光五年道光帝提到:“安西、玉门、敦煌等处设处关外,情形与内地不同……”[14]认为甘肃嘉峪关以西地区并非内地,嘉峪关以东地区为内地。林则徐被遣戍至新疆时路过了嘉峪关,他曾赋诗:“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15]认为嘉峪关是中原和非中原的界限。清末时,魏光焘在诗中提到甘肃嘉峪关:“天然万里中西界,独立三边缥缈楼。”[16]认为甘肃嘉峪关是中原和西域的界限。清末时,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曾在甘肃探查,提到时人对嘉峪关以东和以西地区的情感,认为长城并没有失去象征意义,如果中国人远行出嘉峪关,就会伤感,甚至潸然泪下。[17]
清人将嘉峪关视之为边地与内地的界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源于嘉峪关的历史地位,即从明朝至清初,嘉峪关大部分时段是中原王朝西北边境所在之处,是清朝疆域的边缘。彼时,嘉峪关以西地区为藩部地带,如“布隆吉尔、沙州原系蒙古地方”,[18]所以,在清朝统一嘉峪关以西地区之后也有人沿袭此前说法和印象,将关外视为边地或边疆。二是源于嘉峪关自身的形制特点。即嘉峪关除了关城,还有蜿蜒的边墙,清人经嘉峪关前往安西或者新疆,需要在嘉峪关接受官兵的盘查,是直省民人出边至安西或新疆的最后一道关禁,因此造成部分清人将出边、出关视为离开内地。三是源于嘉峪关以西地区的地理风貌特征。嘉峪关以东地区为河西走廊,农耕文明已经在此扎根多年,人烟相对较多,农耕相对发达,而嘉峪关以西的“安西、玉门颇多沙瘠”,[19]地理相对荒芜,部分地段除了稀疏的驿站,大多百里无人烟,造成清人出关后陷入一种对异域的陌生感,进而造成他们将嘉峪关以西地区视为边地。四是源于嘉峪关以西地区流官体制扎根较晚。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嘉峪关以西地区虽然设有卫所,但府州县体制尚未扎根。清朝统一新疆之后,虽然在嘉峪关以西地区逐步实行了府州县体制,但总体来说,安西地区的府州县相比内地分布更为分散,在行政建置和城市建设上同嘉峪关以东地区差异较大。
二、清代嘉峪关长城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军事功能
关于长城的定义,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所采用的定义为:长城是指连续性的墙体(包含关城),[20]不包括长城周边的营堡、墩台等设施。明代长城建设同北边局势密切相关,明清史料中多将长城称为“边墙”,即“犹长城之遗,而讳其名耳”,[21]故下文主要以“边墙”一词指代长城。早在明初洪武朝时,明朝便十分重视北平以北隘口的防御,此后又经历诸朝,到嘉靖朝时,东自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基本成形,主要防御对象为鞑靼、瓦剌、吐鲁番等。明清鼎革之后,由于清朝在入关前统一了漠南蒙古即明代鞑靼部一部分,故学界多认为清朝不修长城或无修长城的必要。这一论断总体是对的,康熙帝在漠北蒙古归附清朝之后曾提到:“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22]综观整个清代,清朝确实基本不新修长城,但是并不代表不维修长城。明清鼎革之后,清初藩部地区特别是青海蒙古对甘肃的威胁依然存在,故清廷曾通过修筑边墙的方式,防御青海蒙古。康熙五年,青海蒙古“蜂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23]对甘肃地区造成了直接威胁。因此,甘肃地方“修筑边墙,首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止”,[24]通过维修扁都口至嘉峪关的边墙来隔绝青海蒙古。有研究提到,清初“清朝高度警惕,加固了西水关至嘉峪关一段的边墙”。[25]但结合此后的相关史料可知,彼时清朝对扁都口至嘉峪关边墙的维修相对有限,原因是“但既绌于费用,复又艰于工资”。[26]
康熙二十九年,清朝同漠西蒙古在距离北京几百公里的乌兰布通草原爆发大战。此后,噶尔丹虽然兵败退居漠北,但依然不时威胁清朝的漠南和甘肃地区,因此,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命川陕总督佛伦巡视陕西和甘肃地区的边墙。之后,佛伦上奏提到:“陕西自肃镇嘉峪关北边,以至宁夏贺兰山起处,俱系土筑边墙……请于明年渐次修补。”[27]为应对漠西蒙古的潜在威胁,清廷决定对包括嘉峪关地区在内的边墙进行分步维修,其原因即如相关研究所言:“朔漠每有军情,长城毕竟是一道现成的屏障。”[28]清前期,清朝对嘉峪关边墙的维修是常态化的,《(光绪)肃州新志》记载清朝对嘉峪关的维修,“顺治、康熙以来,时加修葺”。[29]
清末同治朝时,陕甘和新疆地区爆发了反清事件,而嘉峪关成为清朝隔绝新疆起事军和甘肃起事军的建筑依托,也因此遭到了战争的破坏。《(光绪)肃州新志》记载:“同治四年,逆回叛乱,关门不启,往来游贼,致毁边墙而入,今军旅肃清,长城缺口完缮如故。”[30]由于嘉峪关边墙成为阻碍回民起事军的建筑,故边墙被毁。清朝在恢复甘肃地区的秩序之后,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提到:“嘉峪关附近边墙坍圮甚多……嘉峪雄镇,最为西路第一要隘,当此关陇全境肃清,本应及时补修完好。”[31]从此段论述可知,同治朝西北动乱之后,嘉峪关长城损毁颇多,虽然清朝彼时修复嘉峪关长城有便于盘诘行旅、稽查税务的目的,但强调“当此关陇全境肃清”这一特殊时段,反映了维修嘉峪关长城亦有存续其军事功用的目的。光绪时,清朝同俄国交涉伊犁事宜,张之洞主张对俄强硬,提到“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终不至掣动全局”,[32]亦将甘肃嘉峪关视为保卫内地直省的首要战略要地。
三、清代嘉峪关长城是融合内地和边疆的纽带
除了军事功能,我们也要看到,清代嘉峪关的非军事功能是居于主要地位的。随着民人经嘉峪关出口至安西和新疆定居,嘉峪关越来越具有融合直省和藩部的象征意义。
(一)清廷总体鼓励民人由嘉峪关出边谋生
清代时,清朝在蒙古、东北等区域总体实行封禁政策,对不同族群实行分割式管理,以维护自身统治,但清代移民经由嘉峪关迁往新疆是持续的,嘉峪关长城不是民族之间的绝对界限,而是融合与交流的纽带。
甘肃嘉峪关以西的安西地区,“本朝初,为边外地”,[33]人烟罕见。康熙后期,为应对漠西蒙古威胁,清朝开始组织兵民赴安西地区屯垦。康熙五十五年,针对此前一年漠西蒙古侵扰哈密事宜,清朝开始打造嘉峪关至哈密一线的军事防线。在关外驻军,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军粮供应问题,因此,当年清朝规定:“自嘉峪关至达里图,可耕之地尚多,肃州之北口外金塔寺地方,亦可耕种,应遍行踏勘,募民耕种……俟收获之后,人民渐集,酌立卫所。”[34]边外民人的聚集是清朝在边外设立卫所等建制的重要前提。康熙末年时,甘肃嘉峪关外“赤金卫、柳沟所等处,曾募人种地”。[35]雍正初时,清朝又命驻扎嘉峪关外的绿营余丁在安西领地耕种,官给耕牛及种子。雍正二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上奏提到:“肃州之西桃赉河、常马尔鄂敦他拉等处俱膏腴之地,应令民人耕种[36]”。雍正四年,清朝以敦煌地区“人烟甚稀,不成村落,乃招甘肃皋兰等县物业穷民两千四百户开垦屯种”[37],组织甘肃民人向嘉峪关以西沙州地区迁徙。雍正七年时,甘肃嘉峪关外安西、沙州的等地,“屯垦民户今年到者统计共有二千四百零五户,屯种既广,树艺益繁”。[38]
清朝大一统之后,陕甘总督文绶奏请改革嘉峪关的关禁政策,提到“应请每日晨开酉闭,以便农民商贾前往关外,广辟田畴也”,[39]鼓励民人赴关外和新疆开垦田地。同时,彼时出关手续也开始简化,文绶提到此前嘉峪关关禁稽查较严,“不免守候稽延之累”,[40]因此建议“进关者仍行盘诘,出关者听其前往”,[41]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农民前往关外屯住。此后,该议得到批准。嘉庆时,全国范围内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甘肃地区,土地贫瘠,“小民口食维艰……”,[42]清朝曾制定措施鼓励甘肃民人出口谋生,即“莫若劝令贫民出口觅食……或地方官量为佽。[43]彼时,清朝对于甘肃民人出边特别是向西赴安西和新疆谋生是不反对的,甚至制定政策鼓励出边谋生,促进了甘肃人口向嘉峪关外流动。《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一书提到清朝统一新疆后不久,新疆地区就有不少定居的甘肃人了[44]。
(二)嘉峪关内外行政体制的一体化
随着民人出关在嘉峪关以西地区屯种定居,为清朝在嘉峪关以西地区设治奠定了基础。康熙三十六年,清朝统一哈密回部,从嘉峪关至哈密一线实际上为清朝的疆域范围,但彼时清朝尚未在该区域设治。康熙五十四年,漠西蒙古侵袭哈密,康熙五十六年,漠西蒙古侵占西藏。由于嘉峪关以西地区为漠西蒙古通向青海蒙古和西藏的要道之一,因此清初为应对漠西蒙古的威胁,开始关注嘉峪关以西地区的防御和治理,即“厄酋作逆,出师征讨,嘉峪关外渐加修复”。[45]明朝经略关西七卫,也有应对蒙古的目的,即如《甘肃通史·明清卷》一书所言:“明朝设立关西七卫的主要目的就是隔绝蒙古和西番,拱卫西北边疆……。”[46]
康熙五十七年,清朝在嘉峪关以西地区“置靖逆卫及赤金卫,兼设同知……又置柳沟所,兼设通判治之”,[47]流官卫所体制开始突破嘉峪关,深入到嘉峪关以西的藩部地带。雍正二年,清朝在布隆吉尔地方置安西卫,并设安西镇总兵官和同知;雍正四年增置沙州卫并升柳沟所为卫;雍正五年,升赤金所为卫。明朝在嘉峪关以西虽然设立了卫所,但未长期驻军,且卫所官员多为藩部首领,卫所的羁縻特点较为明显。清朝在这些地方恢复卫所,但设有同知管理,且卫所下的人民多为关内移民,行政体制同清初的甘肃实土卫所十分相似,不具有羁縻特征。《(光绪)肃州新志》记载了康熙后期至雍正朝嘉峪关外卫所的设置,“嘉峪关外西边鄙之地及敦煌全郡,渐次开屯设卫……”。[48]清乾隆朝实现大一统之后,安西地区的卫所陆续改革为府州县,如乾隆二十五年,“以西域平定,裁卫所……以沙州卫置敦煌县”,[49]标志着嘉峪关以东和以西地区在行政体制上的日益均质化。
四、清代嘉峪关是沟通直省和西域的交通枢纽
《西域图志》提到嘉峪关是“西域新疆门户”[50],认为嘉峪关的地理交通地位重要。
(一)藩部通过嘉峪关与内地驿站连为一体
甘肃是清朝直省连接新疆的交通要道,也是人员、物资的中转地,亦是清朝驿站的重要节点。乾隆朝时,甘肃通往内地直省的交通线,一是经由陕西、宁夏至甘肃,二是经由陕西直接往甘肃,[51]但二两路均在嘉峪关汇合,为直省驿站体系的端点或终点,体现了嘉峪关的交通地位。清朝也因战事需要,一度在甘肃临时新增军塘,嘉峪关则是军塘的重要节点。如乾隆十九年清朝出兵漠西蒙古之时,“因西域军务,甘省口内自肃州至宁夏之花马池,安设正、腰站七十六塘”,[52]嘉峪关为起点。道光四年时,清廷同新疆的奏折和寄信往来,皆通过军站,分南北两路,其中西路从北京昌平军站起,经过山西天镇、陕西榆林、宁夏花马池,出嘉峪关。清末时,清朝常设的军报站主要分为两路,一路经张家口出边接阿尔泰军台,为北路,一路沿山西、陕西、甘肃至嘉峪关,“接军塘,以达西路文报”,[53]即内地驿站与关外至新疆的军塘在嘉峪关过渡和切换。
此外,嘉峪关亦是清朝在关外后勤补给的重要起点。从清朝收复新疆的角度看,嘉峪关是清朝后勤补给线的重要一环。同治十一年,清朝在筹备出关进军嘉峪关以西和新疆时提到:“将来出关,数千里长途……出关后军食如何设措,饷运如何疏通。”[54]因此命左宗棠筹备自嘉峪关至新疆用兵前线的后勤供应线。
(二)清末新政中嘉峪关交通地位重要
光绪十五年,陕甘总督上奏提道:“拟设西安至嘉峪关陆路电线,以速边报。”[55]并得到清朝批准。清朝修建经由嘉峪关的电线,主要是出于经略新疆的目的,即“将来接至新疆,则东西万里一律灵通”。[56]清末时人曾提到甘肃嘉峪关在清朝经略新疆上的重要交通地位,认为俄国铁路逐渐向东延伸,出兵新疆相比清朝从嘉峪关调兵更快,“一旦新疆有事,华兵虽强,迟不敌速”,[57]因此,主张修建从嘉峪关到新疆的铁路,以巩固西北边疆。尽管通往新疆的铁路当时并未实现,但反映了时人对嘉峪关交通地位的关注。就清朝修建铁路的动机而言,“约分为二,内地则计懋迁,边地则重征调”,[58]即修建通往边疆的铁路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陲。彼时由嘉峪关往新疆的铁路并未建成,但光绪朝时内地经由甘肃嘉峪关通往新疆的电报线路成功架设,使得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经略能力增强,有研究认为随着经由嘉峪关的甘肃至新疆电报线路的开通,“甘肃遂成为西北的通讯枢纽”。[59]
五、嘉峪关是清朝管理西北朝贡贸易的依托
基于嘉峪关的重要交通地位,嘉峪关成为清朝管理朝贡贸易的重要区域。
(一)嘉峪关在清代朝贡管理上地位重要
康熙朝前期人梁份曾评价嘉峪关在明末和清初西北朝贡贸易中地位,“关则嘉峪,通西域贡道,顺则以宾来庭,逆则以绝交关路”。[60]早在明朝时,明朝即将嘉峪关作为管理西北朝贡贸易的依托,而梁份生活的时代,清朝尚未统一青海蒙古、哈密以及新疆,西北藩部入京朝贡皆需经嘉峪关并在嘉峪关接受检查。如顺治十三年,清朝下谕给吐鲁番时提到:“着五年一次来贡,进贡人员入关不得过百人。”[61]甘肃地方需在嘉峪关查核贡使人数。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朝中后期,外国部落如哈萨克、浩罕、巴达克山等部皆同清朝建立了朝贡关系,[62]而这些贡使赴京,多经由甘肃嘉峪关。《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漠南蒙古科尔沁、扎赉特等部的贡道从山海关出入,土默特、喀喇沁等部的贡道自喜峰口出入,而西域哈密、吐鲁番、南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的贡道,从嘉峪关出入。此外,中亚的巴达克山、哈萨克、安集延等部落,“贡罽刀、马匹,或三年或间年,贡无定期,贡道由嘉峪关。”[63]可见,虽然清代长城关口皆有迎接和查核贡使的功能,但相比张家口、山海关等长城关口,嘉峪关所接待的藩部和外国更多,任务更为繁重,是清朝管理西北藩部和外国贸易的首要地区。
(二)嘉峪关与清朝西北互市贸易
在大一统前,互市贸易有助于维持清朝同藩部之间的关系;在大一统后,有助于促进疆域范围内民族交易市场的形成。有研究认为清代时,“昔日浴血厮杀的长城关口易为熙熙攘攘的贸易市场”。[64]
一是嘉峪关本身为贸易征税或盘查之所。乾隆二十年,清朝击败达瓦齐、统一漠西蒙古之后,下令允许商人直接同漠西蒙古贸易,“于哈密以东之布隆吉地方,招集商贾同通事评定物价,于嘉峪关盘验稽查,量定税则抽税”,[65]嘉峪关有征收互市货物税的功能。此外,由于“嘉峪关为内外往来咽喉,盘诘最易”,[66]故该关是清朝查禁违禁贸易品的依托。乾隆后期,沙俄在恰克图不时同清朝产生纠纷,乾隆五十四年,清朝决定通过限制同俄国的大黄贸易以“制俄”,规定“嗣后大黄一种……即陕甘两省,亦只当于嘉峪关、榆林等处,加意查察”,[67]嘉峪关是清朝查禁大黄贸易的依托。
二是嘉峪关是进行互市贸易的依托。雍正初和乾隆初,皆为清朝同漠西蒙古关系相对缓和之时,也是互市贸易频繁之时。乾隆四年,清朝初步规定了漠西蒙古熬茶使者赴藏路线,即“由桥湾一路进嘉峪关,从肃州、甘、凉经庄浪出西宁口”,[68]嘉峪关是漠西蒙古使者的必经之处,而嘉峪关所在的肃州成为互市贸易之所。漠西蒙古进贡使者在经嘉峪关在肃州贸易,虽非常制,但清朝一再破例允许,原因便是“进贡夷人所带牲畜货物,准其赴肃交易者,实由柔怀远人、恩施格外”。[69]乾隆十一年,清朝规定了漠西蒙古赴肃州的贸易流程,使者抵达哈密后,“马驼货物先令起行赴肃,其牛羊暂留卡外牧放”,[70]由哈密绿营护送监督,之后可分几个方案,其中即包括漠西蒙古使者的货物提前在哈密议定价格,由肃州绿营“领商出口迎收”,[71]或是先不必确定贸易价格,由肃州商人“亲自出口议价”,[72]此两种方案,嘉峪关外的近边地区在互市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 语
从以上论述可知,清朝统一漠西蒙古之前,嘉峪关及其周边边墙的军事防御功能并未完全丧失,反而随着漠西蒙古的崛起及其势力抵达嘉峪关边外地区,嘉峪关及其周边边墙成为清朝御控漠西蒙古的前沿区域。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后,嘉峪关的军事功能逐步丧失,但是清末西北动乱之时,嘉峪关及其周边边墙遭遇了兵燹,嘉峪关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再次凸显。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清代嘉峪关长城的非军事功能是占主要地位的。随着嘉峪关以西地区逐步纳入清朝统治,随着直省民人相继出嘉峪关赴安西和新疆地区谋生定居,嘉峪关越来越起到融合内地和边疆的作用。为经略安西和新疆,清朝在嘉峪关的关禁管理上提供各种便利,促进直省民人赴边外开垦谋生。同时,清代嘉峪关是内地驿站系统与边疆台站系统的交接点,是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清末时,清朝亦十分重视经由嘉峪关通往新疆的电线及交通建设。此外,嘉峪关是清朝管理西北藩部及外国朝贡使者的首要之区,是清朝管理内地同新疆贸易的依托,一方面清朝在嘉峪关征收相应的贸易税,另一方面,嘉峪关边外近边地区是清朝同藩部互市贸易的重要场域。清代嘉峪关的多元功能反映了随着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巩固,直省边缘地区日益成为融合直省与藩部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