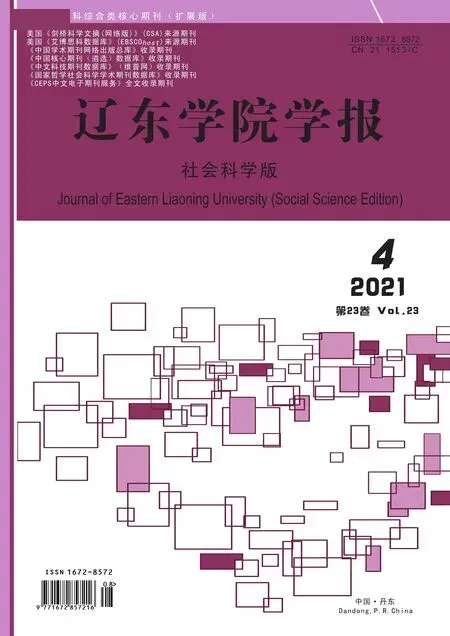斯蒂芬的自性化之路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荣格心理学解读
曹 颖
(辽东学院 外国语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3)
荣格将自性化定义为一个人成长为心理上“个体”的过程,即一个独立的、看不见的统一体或“整体”。自性化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自性化的过程中,个体应该学会整合自我意识、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无意识中的各种原型。在原型中,个体应该主要处理他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情结和自我等[1]258-262。《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借助刻画主人公斯蒂芬的精神成熟过程,即自性化过程,呈现了一位既受制于文化传统又渴望自由解放的爱尔兰青年艺术家的自我变迁。作者乔伊斯在勾画斯蒂芬个性发展的过程中折射出爱尔兰民族个体身份对实现民族解放的渴望,这对爱尔兰民族及其文学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斯蒂芬的自我意识
基于卡尔·荣格人的心理学理论,心理是由独立又相互作用的三个主要系统构成的,即自我意识、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无意识。自我意识作为意识领域的核心,是形成对自我的认同感及连续性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的构成要素为思想、记忆与个人所能意识到的情绪[1]46-49。
斯蒂芬是乔伊斯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人物。《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意识流手法的使用,恰到好处地揭示了斯蒂芬的心路历程。在小说的第一章,年幼的斯蒂芬只能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他所生活的世界。作为一个孩子,由于对事物的因果关系缺乏洞察力,所以他的情感经历常处于纷繁混杂之中。后来,当斯蒂芬成长为一个迷恋宗教的少年时,他就能以一种更明了、更成熟的方式来考虑问题。因此,连接小说段落之间的结构也似乎比小说开头更加条理化,思维也似乎更逻辑化。斯蒂芬变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周围的环境。但他仍盲目地笃信教会,他强烈的内疚感和对宗教的痴迷,使他在思考问题时仍不够理智。只是在小说最后一章,也就是在斯蒂芬上大学期间,他似乎才真真切切地变得理智起来。在小说的结尾,乔伊斯把斯蒂芬描绘为一个在情感、智力和艺术上都日臻成熟的人。
斯蒂芬的自我意识,即他意识的主体,我们可以通过对他早期经历的分析来发现。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很小的时候就与周围的人——同学、家人甚至同胞区分开来。在接近成熟的时候,他在追寻着成人的大问题答案:人生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在斯蒂芬很小的时候,他就展现出了对艺术的热爱,尤其是用词的艺术出现在了他早期的自我意识中,这也说明了斯蒂芬在同龄人中的与众不同。斯蒂芬在年少时,对学校里多兰神父不公正对待自己的愤怒和反抗表明了他内心的导向。这种内心的导向也为他将来拒绝做一名神职人员、离开爱尔兰追求艺术家的自由铺平了道路。少年时代的斯蒂芬是个好孩子,他牢记父母的忠告,言行一致。母亲告诉他“不要和粗野的男孩说话”,父亲建议他“不要对人吹毛求疵”。然而这个成长阶段已经过去,让位于一个自主甚至可能是叛逆的阶段。在这个新世界里,首先是克朗戈斯·伍德教会学校,其次是贝尔维迪中学,他以一种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作出决定,远离了他安全和温暖的家。斯蒂芬开始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安全的外部世界找到位置,学会应对周围和内心日益增加的冲突。当对生活感到不快时,斯蒂芬通过对浪漫的想象和情绪与欲望的发泄,表现出他对社会不满的倾向。当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信仰不符时,他能够反省并找到补偿的方法,这显示了他的智慧与人生哲学。在斯蒂芬成长的初期,这种自我意识对他未来的爱情观、宗教观、社会观以及个性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斯蒂芬的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理论是荣格较为独特的理论之一。荣格认为人的本性的所有构成要素是与生俱来的,这些先天的要素不是由个人的成长环境创造的,而是从环境中带出的。在荣格提出的理论中,三种原型可以用来分析斯蒂芬的集体无意识,即人格面具、阴影和阿尼玛[1]289。
人格面具的膨胀。人格面具是出于适应环境或个人便利的原因出现的个性要素。如果某人在各种情境(如工作、家庭等)下戴着某种面具,即是一种人格面具。人格面具是自我意识的“公共关系”部分,它可以让人们在各种情境下较为轻松地社交[1]324。斯蒂芬的人格早在他在克朗戈斯·伍德寄宿学校求学的时候就显现了出来。试图掩盖弱点,让他人关注其优点,斯蒂芬尽力适应着外部世界,并尽他所能在学校表现出色。这也表明他的人格面具早在学校期间就一直在膨胀。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名字恰好有逃离之意。斯蒂芬的同名人,希腊神话中的巧匠迪达勒斯成功地逃离了克利特岛的迷宫,但他的儿子伊卡洛斯最后坠海而死(1)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同名人,是希腊神话中的巧匠,依靠自己的才智,用蜡制成两副翅膀,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一起逃离了囚禁他们的克利特岛迷宫。迪达勒斯成功地逃离了,但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翅膀被融化了,最后坠海而死。。迪达勒斯与伊卡洛斯在斯蒂芬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因为斯蒂芬的父亲也姓迪达勒斯。乔伊斯借助神话传说,暗示斯蒂芬必须一直平衡他逃离爱尔兰的欲望和高估自己能力所带来的危险——这种举动就如同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为了降低匆忙逃离的危险,斯蒂芬便在大学滞留了一段时间,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美学理论。之后,他才打算离开爱尔兰,认真地开始写作生涯。在小说第五章的第三部分,斯蒂芬看到了那些飞翔的鸟儿。这些自由翱翔的鸟儿恰恰暗示了斯蒂芬现在已是一个羽翼丰满的艺术家,此刻也正是他逃离爱尔兰的最佳时机。通过阅读乔伊斯插入文中的许多祷文、歌曲和拉丁文片段,可以推测出斯蒂芬当时的精神状态。当斯蒂芬是个小学生时,乔伊斯使用了一些稚嫩但又很诚恳的祷文。这些祷文说明即使一个小孩对宗教教义一无所知,但他可能还是笃信宗教的。当斯蒂芬感到罪孽深重在教堂祷告时,乔伊斯插入了一长段拉丁语祷文,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只是在机械地诵读,却无丝毫相信之意。在斯蒂芬上大学期间,同学们常常用拉丁文开玩笑:他的朋友经常把诸如“让血腥的世界和平吧”等一些口头语翻译成拉丁文。他们发现译成拉丁文后,语言听起来特有意思。这样诙谐地使用拉丁语,不仅对年轻人所受的教育是一种嘲讽,而且对教堂里呆板僵化地使用拉丁文来祷告也是一种讽刺。这些语言方面的小笑话表明斯蒂芬对宗教的态度已不再那么严肃。小说临近结尾时,乔伊斯从爱尔兰民歌《Rosie O’Grady》中选取了一段歌词,这首歌不但带给斯蒂芬一种祥和、平静的感觉,而且也反映了斯蒂芬打算摒弃爱尔兰传统文化。贯穿整部小说的祷文、歌曲以及拉丁文都构成了斯蒂芬的生活背景。
阴影的觉醒。人们不喜欢或宁愿忽略的自身特点聚集在一起即构成了荣格所说的阴影。受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它是意识领域最容易理解的情结。荣格不认为情结是没有优点的。在他看来“有光才会有阴影”。也就是说阴影在平衡心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阴影,个人就会变得浅薄与过分在意他人看法,成为行走的人格面具。正如冲突能够推进小说情节,光与阴影对于个人成长也是不可或缺的。当一个人真正成长时,他必须正视其阴影,并试图平衡阴影与人格面具的关系[1]283。斯蒂芬人格的对应部分——阴影,觉醒了,这是当他受到肉体欲望的困扰,并因此对所犯下罪行感到恐惧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之家成长起来的斯蒂芬,最初的家庭环境使他对教会的道德准则坚信不疑。在他青春年少时,懵懂的欲望使他陷入罪恶的深渊之中,常常寻花问柳,对宗教熟视无睹。虽然他放任自流,但他也总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有悖于教规的。接着,阿纳尔神父的说教促使他重新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但他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成了一个近乎完美、极其虔诚且狂热的宗教信仰典范。斯蒂芬最终还是意识到这两种生活方式——极度的堕落和极度的虔诚,不但都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他不愿过那种颓废放荡的生活,也不愿过那种严厉而苛刻的天主教徒的生活,因为他认为这种苦行僧式的教会生活会阻碍他体味作为一个人而应有的全部生活。斯蒂芬的阴影虽然困扰着这位即将成年的青年,但是对斯蒂芬的人格发展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斯蒂芬成功地在内心世界的阴暗面和光明面之间保持了平衡,这一点在他个性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阿尼玛的出现。阿尼玛被认为是一个男人心灵中的异性原型,一种投射在他潜在伴侣身上的理想化形式。这种心理原型来源于个人及女性的经历。以幼年时同母亲的经历为始,试图平衡男性对性别的片面性体验。与阴影相似,阿尼玛有被映射的倾向。不同于阴影的是,它更倾向于以理想化的形式被映射。男性在潜在伴侣身上对自己阿尼玛的影子的寻找解释了一见钟情的现象[1]154。当斯蒂芬第一次真正爱上海滩涉水的少女时,他的阿尼玛在小说中首次出现。当斯蒂芬与女孩邂逅时,他终于下定决心去拥抱生活,颂扬人性。对他来说,这位少女是纯洁、美德的象征,是完美生活的写照。“他的喉咙由于渴望大声喊叫,都憋得发疼了,他要像高飞的鹰鹞一样喊叫,响彻云霄地喊出他随风飘去的喜悦。这是生命对他的灵魂发出的喊叫,而不是充满各种职责和绝望的世界发出的粗暴而无味的喊声,也不是呼唤他到圣坛前去终日进行那些无聊活动的非人的声音。片刻狂野的飞翔已使他获得彻底的解放,他的嘴唇勉强抑制住的胜利的欢呼,几乎撕裂了他的头脑。”[2]235(引自第四章第三部分)小说第四章结尾所描写的这位美丽女孩的出现,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斯蒂芬的自性化进程。
三、斯蒂芬的个人无意识
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源于个人成长与集体无意识的互动。在他的心理学原型理论中,个人无意识即无意识的第一个层面,包括压抑的记忆及短暂遗忘的信息。荣格无意识的第一层具有重要而有趣的特征,即可以将一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形成心理要素,称为情结。换而言之,情结即是关注于某个特定概念的思想、感情及记忆,并且它在个人自性化的过程中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情结强烈地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因此往往具有原型元素。在一个健康的个体中,情结可能是平衡片面的自我意识的关键,从而使个性得以发展[1]201。我们通过分析斯蒂芬情绪和身体上的抑郁,以及他的三个主要情结(父亲情结、母亲情结、英雄情结),可以发现,斯蒂芬情绪与身体上的抑郁导致了他行为的改变,他的情结甚至改变了他在即将成年时的人格发展进程。他对周围人的态度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都与他的情结有关。
在斯蒂芬童年时,读者已了解到他控制自己情绪爆发与艺术表达的重要性。如:“啄掉他的眼睛,快道歉”的克制,宣言与新教小女孩艾琳结婚导致的母亲与家庭女教师丹特的道德惩罚,以及喜欢野玫瑰主题的歌曲等。可以说,他对反叛与自由的喜好虽然不是与生俱来,但早在童年时就萌发了。斯蒂芬在克朗戈斯·伍德教会学校上学时,关于爱尔兰政党领袖帕内尔这个敏感话题成了家人在圣诞晚餐上激烈的、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通过争论,斯蒂芬意识到受难是对自由的追求中难免要作出的牺牲。这也是斯蒂芬本人的处境,他认为英雄会被其祖国爱尔兰摧垮。他开始变得冷漠与愤世嫉俗。不久他生活中崇敬的宗教信仰也开始幻灭。斯蒂芬的转变表明他开始成熟,不再好奇与天真,他开始更多的反思,以使自己融入外部世界。读者通过他的反思有机会窥视他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的情绪抑郁及最终内心冲突的解决。
与斯蒂芬的情绪抑郁相比较,更痛苦的是他的性抑郁。当他企图协调好自己的生理欲望与所处环境下天主教严格教义的矛盾时,他与都柏林妓女有了第一次性的体验,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和罪恶感。他曾一度置自己的宗教信仰于不顾,纵情于淫逸堕落的罪恶之中——频频去寻花问柳。接着,在一次为期三天的僻静灵修中,斯蒂芬听到了一系列关于罪恶、伦理和地狱的说教。他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从此这位年轻人便决定重新投入到圣洁虔诚的天主教徒生活之中。他渴望沉浸在对宗教信仰的持续忠诚中,这证明了他害怕给自己一点空闲的时间,以防某种冲动的弱点会出现。很明显,斯蒂芬意识到他的本能是无法成功抑制的,他的自我感官会在任何时候被释放出来。他的愤怒是最明显的罪恶倾向,这导致斯蒂芬对自我救赎的追寻,以此在面对不断的诱惑时,恐惧感有所减弱。
荣格心理学中的母亲情结不仅是个人与现实中母亲经历的结果,而且还受到他心灵中“母亲”烙印的影响。对斯蒂芬来说,母亲与父亲不同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沉重的情感负担。在他早期与女性的关系中,他总是因难解的内疚感到窒息。性冲动的本能渐渐被压抑。母亲、丹特、圣母玛利亚、艾琳都是他早期生活中有个人情感的女性。然而掺杂在这些情感中的是对女性魅力向往的内疚。粉红色的都柏林妓女,她床边的娃娃及自信的母性平复了斯蒂芬的恐惧,造成了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身体和精神上对她的崇拜。有人认为这是创作的终极行为。母亲在斯蒂芬离开之前表达了她的期望,把他的情感发展到艺术理想主义的水平。最后,斯蒂芬感谢母亲的期望,并认真对待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可能性,就像对待艺术世界给他的灵感一样。在斯蒂芬的无意识中,他的母亲情结通过直觉,在困境时将女性与温暖、安全感联系在一起,在迷茫时与罪恶、诱惑联系在一起。
荣格认为父亲情结是一组与父亲的形象与经历相联系的情感色彩的概念。在男性中,积极的父亲情结会产生对权威的轻信,以及在所有精神信条及价值观前有明显的屈服的意愿。一般来说,父亲情结是通过人格面具的协同作用及阴影的面貌表现出来的[1]396。斯蒂芬的父亲西蒙,由于理财不当,致使整个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在与查尔斯大叔一起度过一个夏季之后,斯蒂芬得知家里已提供不出可供他返回克朗戈斯继续求学的费用,他还获悉他们将移居都柏林。此时,斯蒂芬认识到了父亲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他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命运的变化无情使他感到了生活的窘迫与痛苦。在转学贝尔维迪中学前,父亲与克朗戈斯的两位神父讨论了斯蒂芬在学校受到惩罚一事。当看到斯蒂芬紧张痛苦的神情时,他们笑得都很开心。在斯蒂芬的眼中,这是父亲的背叛。父亲肤浅的建议及对过去没完没了的回忆证明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斯蒂芬只能从学校的神父那里找到榜样,但他又一次失望了。乔伊斯在描述斯蒂芬被选中做牧师并与教导主任探讨这一决定时,运用一些宗教意象讽刺了将“宗教召唤”变成一种所谓的荣誉(如:教导主任的站姿、探身的姿势、精心设计的笑容、拨弄百叶窗的绳索、阴影中的脸、对牧师穿着及秩序的嘲笑等),这让斯蒂芬感到震惊与尴尬。斯蒂芬开始意识到那些充满热情的人被爱尔兰实际的“父亲”背叛了。帕内尔被他的朋友背叛,自己被父亲和那些自以为是并视为榜样“父亲”背叛。这一认识为斯蒂芬在小说结尾作出过一种新生活的决定奠定了基础。
英雄作为荣格理论的原型母题,涉及克服障碍与实现特定目标。英雄体现了一个人无意识的自我,在经验上是所有原型总和的展现,因此它包括父亲与智慧老人的原型[1]516。在斯蒂芬·迪达勒斯的例子中,障碍是那些内在或外在阻碍他充分发展价值的因素,实现的目标是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完全自由。斯蒂芬的姓迪达勒斯与希腊神话中的巧匠同音。斯蒂芬的名字让人们想起圣徒斯蒂芬(2)见圣经《使徒行传》。斯蒂芬是七名基督教执事之一,也是第一位殉道者。他对自己信仰的辩护激怒了犹太听众,被乱石砸死。。主人公的名字与英雄的关系不言自明。斯蒂芬离开主任办公室后,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这意味着斯蒂芬拒绝了母亲(宗教)与父亲(鲁莽、不负责任)两个世界的束缚,去创造更好的新生活,一种未来有希望的新生活,这样的举动更像一个英雄。斯蒂芬在大学的学习,让他感到无限的知识给他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可能性。艺术家斯蒂芬在文字的欣赏与实践中脱颖而出。现在,他意识到神秘工匠的精神与他的命运息息相关。内心叛逆的男孩斯蒂芬已死:就像年轻的伊卡洛斯被淹没,伟大的艺术家斯蒂芬诞生了——就像神话中擅长创造新事物的英雄迪达勒斯。
四、斯蒂芬的自我个性实现
荣格认为自性化是心理成熟的过程。自性实现是个性发展的终极目标。斯蒂芬经过前两个阶段的个性发展,即人格面具、阴影及阿尼玛等心理学原型的个性化及个人无意识的觉醒,个性发展迎来了最终阶段——自性实现。自性实现首先要以充分的个性化为前提,然后与自我(即意识的中心)相互配合,在经过自我与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协调后,最终达到自性实现[1]251-252。对斯蒂芬来说,其自性的实现就是挣脱各种束缚成为艺术家。
在斯蒂芬成长的整个阶段,可以准确地说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平衡的人,非常清楚他的无意识。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他的自性化似乎是成功的。在小说结尾几行,斯蒂芬表明了他的愿望:“在我的灵魂的熔炉中,铸造出我的民族还没有创造出来的良知良能。”[2]364斯蒂芬认识到他的社会将永远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正是这个社会塑造了他的独特个性。一旦他创造性地表达他的观点时,他也同时转达了整个社会的心声。即便斯蒂芬放弃了传统的社会参与形式,抛弃了其社会成员的身份,但他仍想着要通过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服务。
在整部小说中,乔伊斯有意地散布了他对爱尔
兰现实的讽刺。他在描述社会语境时并不关注对国家的批判,因为小说的中心主题是斯蒂芬的成长,他是一位潜在的年轻艺术家,在个人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束缚。虽然斯蒂芬想逃避政治,但他还是在不停地思考着爱尔兰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爱尔兰民族是一个屈从的、恭顺的民族,他们能容忍外来者的统治。上大学时,在与教导主任的交谈中,他发现甚至连爱尔兰人讲的语言都是借用英国人的。“我们两人谈话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原来是他的语言,后来才变成了我的。像‘家’‘基督’‘麦酒’‘主人’这些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和从我嘴里说出来是多么不同啊!我在说这些词儿和写这些字的时候可能并不感到精神不安。他的语言对我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的生疏,对我它永远只能是一种后天学来的语言。那些字不是我创造的,我也不能接受。我的声音拒绝说出这些字。我的灵魂对他这种语言的阴森含义感到不安。”[2]264斯蒂芬对爱尔兰附属地位的理解对他后来成为艺术家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这种理解促使他决定摆脱自己的祖辈们所接受的“枷锁”。从斯蒂芬与达文的交谈中,我们能觉察到斯蒂芬迫切希望摆脱爱尔兰传统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第二,这种理解让斯蒂芬痛下决心,用他的艺术来表达爱尔兰自治的要求。由于使用的是英语这门借用的语言,所以他决定采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写作。这种新文体将不仅独立于英国之外,而且还要忠实于爱尔兰民族。
荣格个性发展的心理学视角不仅为理解乔伊斯自传体小说中主人公所经历的转变提供了新的方法,也给出了探寻像爱尔兰社会对爱尔兰艺术家的意义这样的问题的线索。小说中,乔伊斯有意分散了对爱尔兰社会现实的讽刺,因为他的小说重点是斯蒂芬——一个潜在的青年艺术家的成长,而不是腐朽与令人窒息的爱尔兰社会环境。然而只有更好地理解困扰这位潜在的爱尔兰艺术家的因素,才能全面理解他个人发展的各个阶段。尽管有限,但是乔伊斯提供的关于爱尔兰社会的信息仍然暴露了这个国家令人窒息的气氛。爱尔兰的宗教、政治及传统文化均可以被认为是阻碍这个国家及人民发展的因素。因为宗教对爱尔兰的深刻影响,追求自由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渴望国家独立的政治领袖帕内尔的悲剧意味着希望的丧失。斯蒂芬周围如此悲观的气氛更好地解释了他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抛弃祖国、家人和朋友的决定。对许多读者来说,自我放逐的决定似乎是斯蒂芬的一种背叛,然而这种选择是他亲眼看见和亲身经历的一系列背叛的结果,这些背叛是他在“爱尔兰父亲”身边长大的过程中亲历的。当他最终意识到与艺术上的“父亲”的联系时,也就是神话中的“迪达勒斯”,毫无疑问他会像“迪达勒斯”与“伊卡洛斯”追求自由一样,走上逃离冰冷、腐朽的牢笼之路。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