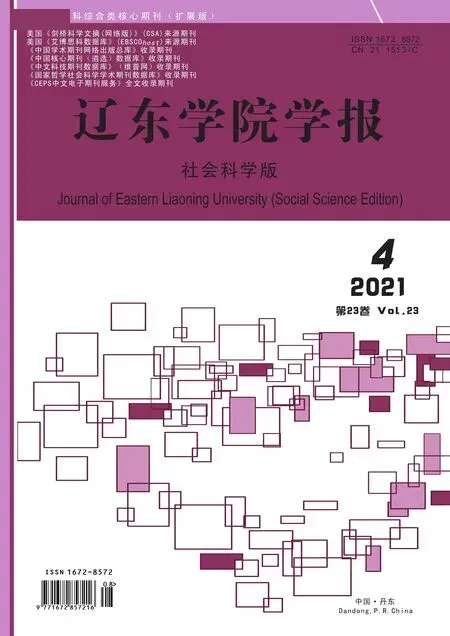贞下起元:对《老子》“礼”之精义的阐释
齐小建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从文化学角度观之,邹昌林认为“礼”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礼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1]14礼有一种独特的表意功能,是一种特殊的负载工具,在文字出现之前,远古文化信息全由礼来承载,故可说“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据邹氏所说,秦汉之际是“礼”之新旧交替时期,以此为界分为古礼和今礼。所谓古礼,具体是指五帝之礼和三王之礼。三王之礼源于五帝之礼,孔门儒学之礼继承三王之礼尤其是周礼而来,古礼为源,儒礼为流,本文所言“礼”特指文化学上的古礼,非儒门倡导之礼。
一
在邹氏看来,古礼的核心是宗法分封制,到春秋以后,作为社会基础的宗法分封制发生巨变,古礼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并没有就此消失,故古礼中有着某些不受这个核心制约而又能够影响整个文化发展方向的因素存在。邹氏认为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们在生产上或其他方面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基本是这个核心左右不了的。二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这是在这个核心形成以前就存在的,以后也无法改变,这也是这个核心所基本左右不了的。”[1]192由此方可窥见古“礼”最深层之精义:“礼”不仅统摄上古时代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其中包蕴的一种作为人禽之别、文野之别的独特精神内核。到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则为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开出了独特药方:“自然”“无为”“贵柔”“贵言”“虚静”“处下”等等。本文抽绎出《老子》文本所蕴藏的这些深刻思想,寻绎它们与古礼中所蕴含精神内核的独特关联之处,试图从一个新的维度与视角来理解《老子》一书对“礼”的真实立场与态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特征是“周文疲弊”“礼崩乐坏”,其结果就是古礼由原来统一的整体分化为礼义与礼仪两个层面,即分离为“义”与“仪”。三代是纯正古礼时代,春秋是僭礼、变礼时代,至战国进入对礼的反思时代。诸侯之间连年征战,社会巨变引起了当时思想家对礼的反思与怀疑,怀疑的结果就是对待礼的态度出现两种倾向:重仪与重义。“古礼之制度和精神,仍为这个时代的学术界和学者们所记录、整理、阐发义理而保存下来”[1]33,质言之,战国时“重义理”的社会思潮,促成了当时思想家对礼之义理的探赜与阐发。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间论礼的集大成者,尤重古礼探源。正如邹昌林所言:“《礼记》并非仅仅是《仪礼》的注脚,而且是对古礼的继承和发展。尽管本身不无瑕疵,然古礼之精神,全靠着《礼记》的阐发,才得以充分发掘出来。”[1]44我们再看郭嵩焘的观点,在《〈礼记质疑〉自序》中说:“凡《戴记》所录,皆发明二经之义趣者也。二经所未具,亦常推广而补明之。而其文或参差互见,或繁复相抵,或引起一端而辞有偏胜,或殊其旨要而义实兼通,其言列国时事,多与左氏异同,要以发明《春秋》之义例,以著礼之大经。诚欲上考古礼,必此之为涂径也。”[2]21此处不是本文的重点不再赘述。据此我们便以《礼记》作为阐发古礼之义理的可靠文献。
二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3]887-888
可见,礼的最初形成起源于人类的日常饮食,饮食可以直接或间接表达某种情感。洪文郎说:“人对于鬼神和死者,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情感,所以必须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来传达内心的不同感受;因此,各种不同的‘礼’也就由此产生。”[4]45由此可见,礼的起兴之物是人的情感,礼本于对人情之节制。《礼记·礼运》《礼记·问丧》也贯穿了这种思想。后世学者承袭了这种观点。孙希旦《礼记集解》曾言,“有所抑而不敢肆,谓之撙;有所制而不敢过,谓之节。……凡事不可以无礼,故君子必恭、敬、撙、节、退、让以明之。礼主其灭故也。”[5]10礼来源于对人情的节制。李安宅指出:“礼的起源,自于人情。……明礼之道,是要用恭敬、撙节、退让的。”[6]7-11我们还可以举具体例子来分析,《礼记·檀弓下》:“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7]361洪文郎解释:“因为在丧礼中,孝子面对亲人的死亡,心情是极为悲哀的,所以为了不使孝子因此而哀伤过度,反而损坏了父母所赋与的身体,就必须要用一些礼节来节制孝子的悲哀,让他们能面对这种突然的变故。”[4]47邹昌林说:“礼起源于对人的情欲的节制和规定性。”[1]66笔者同意这种说法。
域外学者对此问题也得出类似结论。凯伦·阿姆斯特朗发现中国先秦及战国时期有一种精神的诞生:“礼仪官员们也试图抑制狩猎活动,将其限制在一个谨慎划定的季节。……克己、节制和有度成了时下的格言,无论你做什么,都有一种恰当的方式。……君子依照礼仪的精细规则而生活: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8]123-125“战争变成一场精美的盛典,由谦恭和克制所支配。”[8]157马克斯·韦伯也说:“跟古代伊斯兰教的封建武士所有的热情与狂放比较起来,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性的自制、内省与谨慎的特色。尤其是,我们会发觉到,所有热情的形式,包括欣喜在内,都受到压抑……”[9]218可见,“节制、克制、谨慎”是国内外学者对礼的古老本质功能的共同认识。
到儒礼时代,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与家国意识,强调礼的教化功能与乐的感化功能,通过“乐”来唤醒人内在“仁”本性,使之外化为礼,用礼来节制人对欲望的追求。质言之,节制精神尤其是对情感的节制,可说是古礼向来的精神要义与重要功能。检阅《老子》一书,老子对圣人的“寡欲”要求正是对这种节制精神的充分发挥和演绎。
冯友兰说:“《老子》以为人生而有欲,欲占人生中一重要地位。”[10]76人之有欲无欲,相当于社会间的有名无名。有欲,又要想种种方法来满足其欲望,满足欲望的方法越多,人越满足而人欲越不能满足,人必受其害。老子的建议是与其设种种方法来满足欲望,不如从根本上寡欲,而寡欲方法之一就是减少兴起欲望的对象。《老子》有言:“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11]8,“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1]45,“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11]91这三章老子都是说寡欲,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目的是让其民“实其腹”“弱其志”。
老子“寡欲”的观念也并不是绝对的,人为了生存需要绝不会毫无欲望:“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11]190所以说老子本意并非是要绝对地灭绝人欲,而是要奉劝统治者:“去甚,去奢,去泰。”[11]76在老子政治理想里,圣人在治国理政时要除去那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措施法度。理想的统治者往往能够顺应自然、不强制、不苛求,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老子认为“寡欲”和“无为”是二合一的,他眼中圣人的“寡欲”表现为以下几方面:“无为”“贵言”“绝学”“虚静”。
老子的“无为”主要从政治角度展开。李泰棻说:“妄为病在于‘欲’,不见可欲,则自已矣,所以首先作到寡欲,这是必要的。”[10]241统治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能做到“寡欲”自然就不会妄为,就能做到尊重事物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不会胡作非为。《老子》一书,除了三十七章中以“无为”来描述“道”以外,其他内容凡是谈到“无为”的地方,都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的。“寡欲”即是“无为”,陈鼓应指出:“老子提倡‘无为’的动机是出于‘有为’的情事。‘有为’一词是针对着统治者而发的。”[10]394老子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要求统治者“无为”。“有为”即“有欲”,“无为”即“寡欲”,可见“寡欲”在民即个人修养,在君即政治素养。老子极力呼吁为政者要“无为”,是因为他看到充满个人私欲的当政者不足以有所作为,却偏要妄自作为,结果给老百姓带来战争与灾难,所以在老子看来统治者“寡欲”“无为”才是理想国家唯一釜底抽薪的办法。老子也说:“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11]183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替大匠斫木头,非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会闹出乱子来。
老子本着以民为本的立场,要求统治者“无为”。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11]184国家和人民难于治理的真正原因是,统治者没有尊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依据历史经验来治理国家,肆意伸张个人的意欲,蚕食税赋,加强少数人的利益,扩张统治阶级的权力,任意蹂躏人民,强作妄为。老子看到“有为”之政的祸害已经很严重,所以他才感叹:“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1]149-150统治者为满足私欲给老百姓的禁忌束缚太多,法令森严,赋税杂多以致民不聊生,所以老子站在以民为本的立场上呼吁统治者“无为”,这样便能达到老子理想的社会。
“贵言”是老子“无为”观念的具体表现。“贵言”,“悠兮其贵言。”[11]40按照马叙伦的解释,“悠”即是“不言或无声之意”,“贵言”,表现在“少言”与“守中”。老子“贵言”的原因是“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11]147老子心中最高层次的“知”是“常”,而“常”是默会而成,非常规的知识,不能名言的知识。而此时的统治者“不知常”,他们欲“有为”必有言,即他们制定政策发号施令就掺入了个人私欲和喜好,那这样的法规政策绝对不是“真知”,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如此执政,必会将人民大众置身于水深火热。故老子要求统治者“少言”,学习历史经验,制定治国良策。另一方面,老子推崇“守中”:“多言数穷,不若守中。”王弼注:愈为之则愈失之矣。按楼宇烈意,“数”作“速”,“中”,即守其空虚无为之意[11]14-16。统治者政令繁杂、朝令夕改反而更加使人困惑,更行不通,不如保持内心虚静,不“妄言”。可见,“多言”“妄言”和“无为”是相对的,“言”也即是为的一种,所以说“贵言”是“无为”的题中应有之义。
老子的“绝学”是针对人的内在性情而言。智慧与知识也是欲望的对象,所以老子也要人们“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若能使民众绝学,不追求社会智慧与自然知识,也断绝人们通过知识与书本去认识社会、扩大视野、追求名利、满足更多欲望的途径,将“欲望”的对象及其追求途径从根本上铲除,便能使人固守自然本性而不起伪心。老子认为,圣智、仁义、巧利三者不是出于人的本心而是社会产物,与人的自然本性抵牾,所谓“智慧出,有大伪”,非出于内心的事物都是属于伪,故老子建议人们认清世间真与伪,从内心必须绝学弃智,回归本性,守住真朴之心,杜绝欲望。人的内心“绝学”方可使君主“自然”、民众“自化”。这是老子根据当时社会状况而引发的独特思考。
“绝学”与“虚静”互为因果,但“虚静”是老子更本质的要求。正如老子要求:“致虚极,守静笃。”[11]35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陈鼓应说:“老子用‘谷’来象征‘虚’,‘虚’这个观念应用到人生方面的时候,它含有‘深藏’的意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上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深藏若虚’,这和半瓶子满就摇摇晃晃的情形,刚好是一个对比。”[10]397老子谈“静”,也是在政治立场上来立论,“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11]123“正”通“政”。老子喻示统治者学会“藏”而不是“放”。老子以为君主内心清静方能统治天下,故老子才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11]91老子的“清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因为老子早就发现古圣人就是这样做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1]150老子以历史经验告诫当世统治者,统治者性情清静而不纵欲,社会才能走向安定富强。
“静”与“燥”反,“静”与“重”同。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11]69可见,静与重相关,持重者则静,老子贵“静”亦贵“重”,尤其是强调作为一国之君,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能够保持“静重”。但老子看到当时的统治者正好和他的理想是相悖的: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随意地发动战争,践踏礼乐制度,他们没有“以民为本”的政治意识,没有“清静稳重”的政治作风。所以老子认为“清静”也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应有的品质。综上,老子在统治者个人性情与政治作风两方面的“寡欲”要求具体表现为“无为”“贵言”“绝学”“虚静”等几个方面,而“寡欲”正是古礼之“节制”精神的具体“复现”与当代“演绎”。
三
远古时代人与禽兽的区分,也即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标准主要有二:一个是“别”,另一个是“让”[1]205。别即区分、区别,让即礼让、敬让、尊让。观之《礼记》,“礼让”无所不在,“礼让”精神贯穿整个古礼之中。
为什么说能不能礼让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呢?因为古礼在形成之初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防止人际间的争夺杀戮,人类能够通过一定的礼仪、规范、制度,即人与人的礼让精神,来调节和防止相互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动物身上只存在本能,绝没有相互调节关系的能力。故是否具有礼让精神,尊礼而谦让,就成了人与禽兽的重要分界线,人类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便开始踏上文明的进程。所以“让”在古代才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它成了古礼的重要基础,成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色之一,礼让精神成就礼仪之邦。
“礼让”精神在先秦古籍中多有体现,尤其贯穿《礼记》一书。《春秋榖梁传·定公元年》有言:“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12]317《左传·昭公二年》有言:“卑让,礼之宗也。”[13]1588《礼记·乡饮酒义》有言:“尊让、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杨天宇解释:“尊重、谦让、清洁、恭敬,是君子接交的原则。君子互相尊重、谦让就不会争执,清洁、恭敬就不会怠慢,不怠慢、不争执就会远避打斗争吵了。不打斗争吵,就不会有暴乱的祸害。”[14]822-823杨天宇认为礼让是初民的重要品质之一,“让”的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的“斗辨”、“暴乱”。《礼记·曲礼上》有言:“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杨天宇说:“是以君子态度恭敬、凡事有节制、对人谦让,这样来体现礼。”[15]2-3《礼记·祭义》有言:“致让,以去争也。”[14]616杨天宇说:“使人讲究谦让,用于除去争纷。”《礼记·乐记》云:“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14]476杨天宇解释:“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庄敬恭顺,是礼对人的节制。”可见,“礼让”精神是礼之义理最基本的品质。
西方学者也发现了古礼的这种礼让精神。阿姆斯特朗在《轴心时代》一书中考察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圣人尧、舜、禹的优良品质和感人事迹,发现他们的时代是最重“德”的时代,而“礼让”“谦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品德。正如阿姆斯特朗评价尧、舜、禹:“他们是有度、谦逊、克己和恭敬的典范,这些品德正是‘礼’欲培养的。”[8]127可见,“让”也是五帝时代的“德”的重要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说“礼让”“不争”是礼的第二要义与重要功能。我们可以再看李约瑟的考察,他说:“葛兰言却从神话和民俗学的观点对这个概念做了彻底的考查,其结论是:‘馈赠’(potlatch)的风俗在中国远古社会中一定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按照这种风俗,一个首领的威望取决于他在定期或季节性的聚会上所能分赠给全体部族的食物或其他物品的数量。在中国,由谦让和退让而得来的不可思议的美德、社会声望以及最后的‘面子’,已成为这个文化中的统治因素。……倘若这种传统起源于‘馈赠’习俗的话,那末,它在道家著作中就得到了最高的表现,尽管它不是道家所独有的。”[16]68-69我们考察《老子》发现,它从三方面体现了这种“礼让”精神。
其一,《老子》道德上的无私体现了礼让精神。老子言:“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11]19这是说,圣人总是首先考虑到他人的利益,首先受益的反而是自己,圣人总是将自身置之度外,自身反而得到了保全,这正说明是无私成就了自己。无私变成有私,馈赠别人,成就自己。这是老子独特的思想观念。老子又说:“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11]172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往往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损人伤己,善于人才使用的人常常能放低姿态,居人之下。这就是退让、不争的品质,尊重历史规律,传承自古以来的好生之德,没有耀武扬威,没有大开杀戒,心中有天下而无私心,梁启超把它叫作“无私主义”,就是教人将“所有”的观念打破,无“私”则无“争”。
其二,《老子》政治观念上的不争体现了礼让精神。《老子》有言:“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11]85胡适把老子这种观念叫作“不争主义”。关于老子的“不争主义”,罗素说这句话是专门提倡人创造的激情与冲动,认为老子哲学是最高尚最有益的哲学。罗素说:“人类的本能,有两种冲动:一是占有的冲动,一是创造的冲动。占有的冲动是要把某种事物,据为己有,这些事物的性质,是有限的,是不能相容的……这种冲动发动起来,人类便日日在争夺相杀中,所以是不好的冲动,应该裁抑的。……创造的冲动正和他相反,是要某种事物创造出来,公之于人,这些事物的性质,是无限的,是能相容的……这种冲动发达起来,人类便日日进化,所以这是好的冲动,应该提倡的。”[10]53-54罗素认为老子的不争观念潜含着“创生”的思想。老子在《老子》一书末尾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11]192老子这种观念是对时势的匡正,因为老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兵火连年的时代,诸侯互相杀戮,小国自身难保,百姓生灵涂炭,所以老子“保民”而“不争”,“不争”倡“创造”。老子传承礼让、不争的精神,又以此为基础提倡人的创造、创新精神。
其三,《老子》中“道”的柔的性质体现为礼让精神。老子有言:“弱者,道之用。”[11]110创造性、创生性正是老子“道”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子“道”的创生性虽然是“柔弱”的,但这种创生性却能绵延不绝地作用于宇宙万物的。陈鼓应说:“‘道’在创生过程中所表现的柔弱情况,正是‘无为’状态的一种描写。”[10]399“道”之柔弱品质是宇宙万物可以顺其自然自我生长、自我发展、自我成就的前提。“贵柔”是老子的又一独特观念。
《老子》还有言:“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11]185陈鼓应说:“老子在经验世界的事物中找到论据,用以说明‘坚强’的东西是属于死亡的一类,而柔弱的东西是属于生存的一类。”[10]399老子发现活人的身体是柔软的,死人的身体是僵硬的,自然界的动植物都是如此,所以老子总结道,“柔弱”的事物必是生机盎然,“坚强”的事物则即将毙命,这是老子从宇宙万物的自然发展规律总结的。“坚强者”锋芒毕露,至刚则易折,不可长保,“柔弱者”懂得谦虚礼让包容,暗藏生机,方绵延不绝。“坚强者”的力量是抗“性”的,“柔弱者”的力量是随“性”的,而老子眼里天下最柔弱、最随“性”的莫过于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11]187“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11]120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这柔弱并不是柔弱无力的意思,其中却含有无比坚韧不拔的因素。老子由“水”的物理性质还提出了“处下”的观念,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1]20老子最喜欢用“几于道”的水做比喻,水有居下、不争、利物的特点。
综合三方面,《老子》中“无私”“不争”“贵柔”“处下”的观念正是古礼“礼让”精神的当代展现,“让”的精神“成德”“立国”,直至“道之用”。
三王时代,“公有”天下已变成“私有”国家。春秋战国,是人民最苦难、道德最败坏、社会最动荡的时代。此时老子以特有的史家深邃智慧,以拯救人类的大慈大悲之心,对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一套彻底消灭这种灾难的完整思想体系。而通过本文可以得知这一套完整的思想观念,其实是源自对人类“古礼”文化精神的一种“复归”。这种“复归”不是对往昔的简单重复,而是事物前进运动的一种形态,通过“复归”,形成了更深刻的思想观念:将古礼最基础的精神理念升华为一套完整的关于人类的思想学说。老子讲自然之道的最终目的还是回到了解决人间的现实社会问题上来的。
冯天瑜说:“民族传统的反思和人类当代意识的追寻(或曰世界新声的摄取),是建设现代文化的两大依据,是新文化成长的两个相反而又相成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当代意识的追寻有赖于传统的反思,传统的反思又不断接受当代意识的启迪。此所谓‘用现代批判传统,用传统格义现代’。总之,新文化的构建遵循着‘文化重演律’方得以运行。”[17]361文化重演即是精神文化层面对古人某些思想观念的“重演”。从本文分析可得,老子“复古”以求“新变”,返古开新,按“文化重演律”言,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返祖现象”,本文所述的《老子》中的精神就是对古礼精神的一次“回复”与“重演”,它促使蹒跚的“古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了蓬勃的“青春”。在某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老子》是古礼在春秋战国之时的“贞下起元”之书。另一方面,我们以历史主义态度观之老子思想和古礼文化精神之间的深刻联系,便可得出一种阐释老子思想的新视角与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