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变迁及其当代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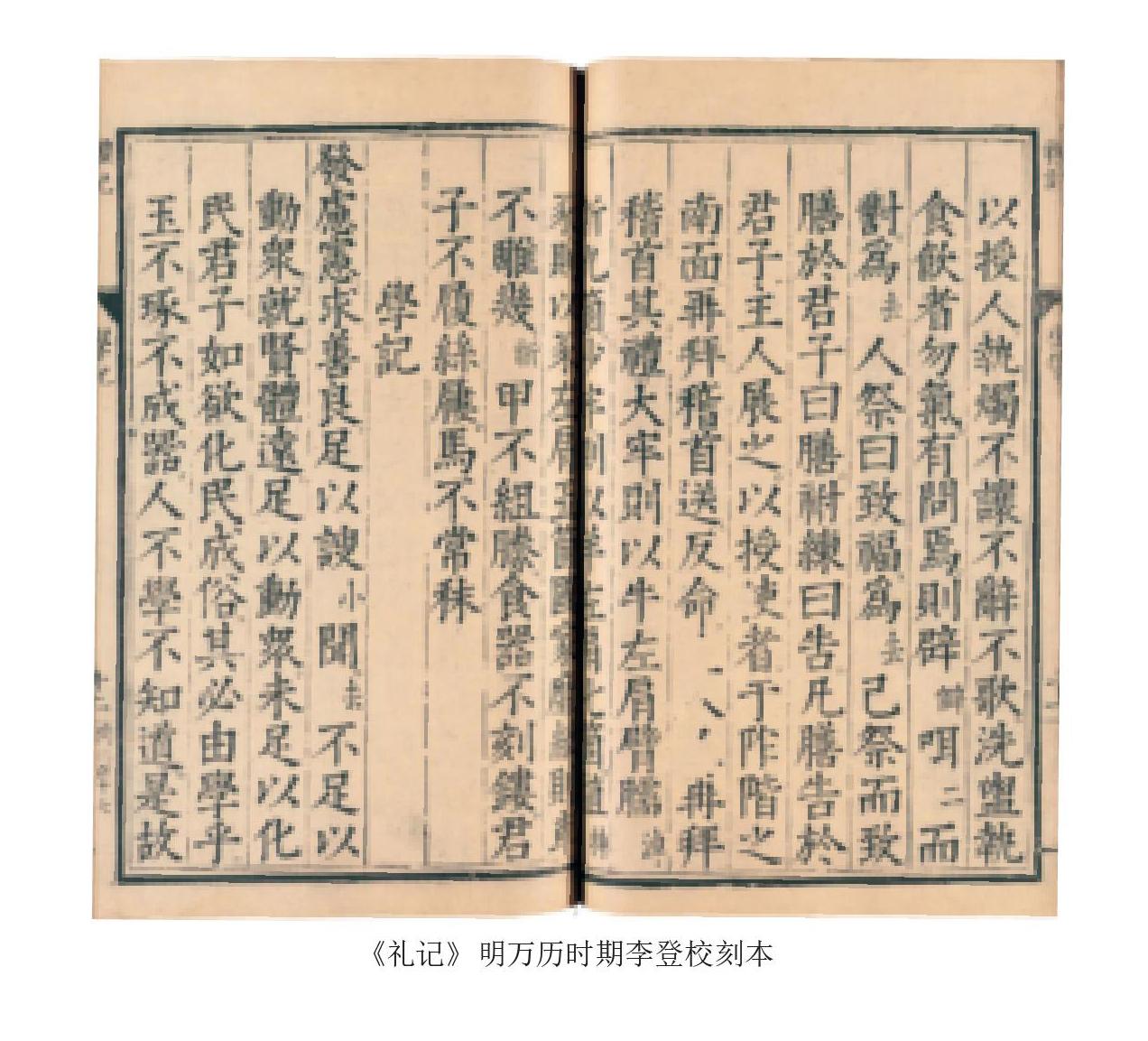
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礼记》虽然成书较晚,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充分体现、揭示了儒家的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观。
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礼记》是一部非常特殊而且非常重要的经典著作。它全面、集中、系统地论述、阐释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礼记》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价值。
《礼记》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变迁
《礼记》本来不在儒家经典之列。在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礼》是《仪礼》十七篇,而不是《礼记》四十九篇。《礼记》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为辅助诸生研习《仪礼》而编纂的一部礼学文献汇编,是对《仪礼》的补充和阐释。终西汉一代,《礼记》都不在经典之列,只是作为《仪礼》的附庸而存在。到东汉末期,经学大师马融、郑玄先后为《礼记》作注,《礼记》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到曹魏时,朝廷甚至将《礼记》正式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到唐代孔颖达等奉诏编纂《五经正义》时,《礼记》更是喧宾夺主,直接取代了《仪礼》“五经”之一的地位,完成了对《仪礼》地位的超越。
《礼记》为什么能够由“记”升格为“经”,并从《仪礼》附庸的地位完成对《仪礼》“五经”之一地位的取代和超越?这主要取决于《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性。相较于《周礼》《仪礼》而言,《礼记》全面、集中、系统地论述、阐释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等。可以说,儒家的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在《礼记》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示和阐释。正如清代学者焦循所说:“《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序》)
《礼记》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厚而广博。上自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准则,都在《礼记》中得到多方面论述和阐释。《礼记》四十九篇较系统、完整地记述和阐释了先秦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诸礼,而且对其他先秦文献较少记述的封国制度、爵禄制度、封禅制度、明堂制度、宗法制度、昭穆制度、学校制度等也有较详细的记述。从学术体系说,《礼记》四十九篇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礼记》四十九篇是我们探寻先秦历史文化必经的津梁,对于我们学习和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礼记》的当代价值
《礼记》不仅在儒家经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礼记》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价值。下面我们就以《礼记》的一些篇章为例来讨论《礼记》的当代价值。
《礼记·礼运》集中体现了儒家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价值。它所提出的“大同”“天下为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至今影响犹在。它以孔子的口吻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同”社会理想,并从不同维度论述了礼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礼制的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通过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化描述,展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和社會理想。
《礼记》许多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礼乐文化“和”的精神及其重要意义。《礼记·儒行》明确提出“礼之以和为贵”,体现了儒家礼乐文化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崇尚和追求“和”。这里所谓的“和”,包括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基本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了儒家学派主张通过“礼”的实施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思想。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主张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都应当自觉接受“礼”的约束,当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求大同存小异,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安定有序、和谐发展的局面。
《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两篇对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影响特别深远,因而宋代大儒朱熹将这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大学》所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分解和阐述,从多个向度揭示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而《中庸》从揭示天、命、性、道和教的关系入手,说明“道”原于天(天命)而内在地具于人(性),人应以“慎独”的修养工夫,时时体现天道(教)。这可以被看作是对“内圣”的形而上学化的揭示。《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和《中庸》提出的“不偏”“不易”、中正、平和的为人处世之道,激励着我国古代众多学人努力修身养性、弘扬社会公德、积极入世,兼济天下,服务于社会。毋庸置疑,《礼记》所倡导的“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对于我们当今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礼记·学记》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篇教育学专论,也是世界教育史上较早集中系统地论述地教育问题的教育学著作。宋代理学家程颐非常推崇《学记》。他说:“《礼记》除《中庸》《大学》,唯《学记》最近道。”《学记》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的教学经验和教育理论,既对当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缺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又提出了许多合理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意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学记》认为教育不仅是对文化知识的传承,而且应该把思想品德的教化置于首要地位,从而通过道德教化达到移风易俗、治国安民的目标。显然,《礼记·学记》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教育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总之,《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集中体现、阐释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修己安人”的思想,亦即“内圣外王”之道。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导向性作用。它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思想和学术价值,而且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历代《礼记》注本
《礼记》自西汉编纂成书后,即得到了历代学人的普遍重视和推崇。对其进行研究注释者,代不乏人。现今传世的最早、最权威的注本是东汉郑玄的《礼记注》。郑玄的《礼记注》摒除今、古文门户之见,博综兼采,择善而从,要言不烦,又多真知灼见,从而使《礼记》大行于世。唐朝初年,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奉诏撰定《礼记正义》。孔颖达《礼记正义》采用郑玄注,基本坚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整合南朝皇侃《礼记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礼记义疏》,为《礼记》作出新的权威注本。孔颖达《礼记正义》迄今仍是最权威、最常用的《礼记》注本。
南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礼记》学著述当推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本书卷帙浩繁,采择广博,除了引用郑注和孔疏之外,还博采其他经说一百四十二家。元代最有代表性的《礼记》学著述是陈澔的《礼记集说》(与卫湜《礼记集说》同名)。与卫湜《礼记集说》相比较,陈氏此书的特点是精练,要言不烦,甚便学人。明代科举考试,指定陈氏《礼记集说》为考试标准用书。明代的《礼记》学著述当以胡广《礼记大全》和郝敬的《礼记通解》最有代表性。《礼记大全》是胡广于永乐年间奉敕编撰,处处体现了宗宋学之取向。从治学方法上看,《礼记大全》仅采纳成说,于文字、名物、制度等皆无考证,体现了明人空疏的学风。郝敬《礼记通解》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礼记》学著作,对郑玄的《礼记注》多有驳难,并提出许多新见。
清代影响最大的通释全经的《礼记》学著作者当推乾隆“三礼馆”撰定的《礼记义疏》、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和朱彬的《礼记训纂》。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礼记义疏》兼采汉、宋,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打破了元明以来宋学对《礼记》学的垄断。孙希旦《礼记集解》通例是先引郑玄之说,次引孔颖达之说,再引述宋、元、明、清诸儒之说。由此可见其汉、宋兼采的治学特点。朱彬的《礼记训纂》与孙希旦的《礼记集解》一样,皆是汉宋兼采之作,没有门户之见,不仅多征引郑玄、孔颖达及王念孙、王引之、江永、刘台拱等汉学家的成果,亦多采宋学之释义。
此外,当代出现了多种专门以帮助今人学习《礼记》为目的以现代汉语译注《礼记》的著作,如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杨天宇的《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吕友仁与吕咏梅的《礼记全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钱玄等人的《礼記》(岳麓书社2001年)、王文锦的《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吕友仁的《礼记讲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丁鼎的《礼记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这些用现代汉语撰写的译注《礼记》的新著各有千秋,共同特点是简明易读,颇便于初学者使用。
丁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