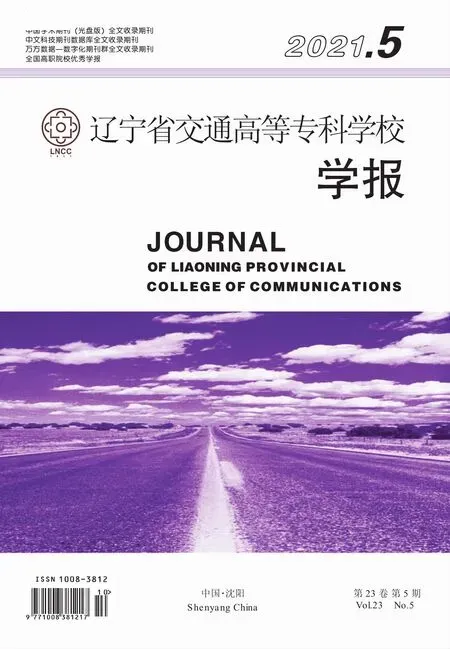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困境与深化
孙金超
(南通大学,江苏 南通 226000)
为了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首先需要明晰 “放管服”的科学内涵: “放”,即简政放权,强调政府重新定位角色、持续下放行政权力,控制、纠正和弥补其在高校管理上的越位、错位、缺位问题; “管”,即放管结合,主张以技术创新推动政府监管职能及管理体制个性,以促进其职能转型; “服”,即优化服务,要求政府减少对高校行政审批干预,提升供给服务质量,将传统“统治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而言,“放”为前提、 “管”为基础、 “服”为目的,三者层层递进、 “三位一体”。现阶段,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仍面临着渐进式与激进式改革冲突、速度与质量效益矛盾等一系列困境,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管就死、一死再放”等情况屡有发生,因此,有必要立足“放管服”改革难题,深刻思考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
1 当前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面临的困境
1.1 放权力度递减
受“高权管制”传统的影响,政府对不同类型及层次的高校的放权力度、 “放管服”改革态度不尽相同,这导致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放权、监管状况呈现出复杂图景。一方面,放权口径缺乏统一标准, “双一流”高校或部属高校被假设为具备健全的自治自律机制,此类高校简政放权力度较大,而其他院校简政放权幅度、步调呈显著差异性;另一方面,权力下放的范围不甚统一,放权力度也呈逐级递衰趋势,多地有关部门针对高等院校所需下放的权力仍未彻底下放,或权力下放不对口,或力度不足,或放小、放虚却不放大、放实,诸如此类问题严重阻碍了“放管服”改革进程;除此以外,广泛号召的放权始终处于“放” “收”摇摆不定的尴尬境地,政府将高校办学自主权视为权力施与,每次放权后又逐步收回去,精简机构编制时再重新将权力下放,这导致简政放权无法真正落地,加上权力下放未考虑高校承接能力,引发政府权力“放不下”、高校“接不住”的矛盾[1]。
1.2 监管真空扩大
放与管乃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因此,要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必须做到放管结合、放管同步,一手抓“放”、一手抓“管”,做到 “放手”而不 “甩手”, “出手”而不 “失手”,实现 “管”的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高效性。然而,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习惯于以审或以罚代管,这难免导致有关部门权力重复、审批流程繁冗、过程盲目随意,高等院校不得不疲于繁冗的审批工作,无法全面投入教育管理工作,还有多地部门过分强调事中、事后监督与管理工作,认为不审批即无职责,担心放权时政简了、权放了,管理也随之乱了。除此以外,权力下放后政府有关部门未及时依循变化动态调整工作,教育部门监管、执法等水平也未及时跟上高等院校监管职能需求,难免引发监管 “真空”,管控不到位问题出现。
1.3 服务职能泛化
优化服务是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基础上持续深化的结果。近年来,各地院校虽然在教育服务改进优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服务水平低下依然是常态,服务职能的推进仍受到诸多阻滞,无益于“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一方面,服务意识薄弱,多地政府并未意识到行政的本质在于服务,片面将管理视为服务,这导致高等教育领域重管理轻服务问题严重;另一方面,服务职能泛化,高校肩负着教学、科研和服务职能,这三大职能关系无疑对高等院校教育服务的适配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高校教育服务职能范围过度拓展、功能过度夸大等问题严重,这不仅对高校政策教学秩序产生了冲击,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还导致科研活动中功利性价值取向泛滥,致使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失衡[2]。
2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深化路径
2.1 以精准放权为目标,强化“按需放权” “差异放权” “协同放权”
现阶段,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关键在于推动“管、办、评分离”,实现“放管服”的有机结合,明晰政、校、行、企各方定位及关联,以精准下放权力为基本目标,着力解决“放”什么、怎么“放”、 “放”给谁三大核心问题。其一,注重按需放权。简政放权要有大局观,做到上下联动、左右衔接、协调放权,既要考虑放、管、服,又要考虑地区及高校承接能力;既要关注主要矛盾,又要把握关键环节,认真研究、细分已明确下放的权力事项,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聆听多方呼声,精准对接师生所盼、高校所需,遵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基本原则,做到按需放权,推行高校“点单式”放权模式,实现简政放权的精准性。其二,强调差异放权。政府要统筹考虑各地区、各院校的特点及要求,出台有针对性的倾斜政策,面向条件成熟的地区及“双一流”、高层次院校进行学位点布局及优先放权,针对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薄弱的院校则要进行学位授权扶持,通过有差别、有层次的差异放权,促进全国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均衡发展。其三,强化协同性放权。政府要积极推动关联、相近等审批事项的融合,明确放权清单、具体流程及方法,加强分工责任制、监督追责制等建设,实现全链条同步“取消”或权力“下放”,强化“放管服”改革的综合效应,持续拓展改革的受益面[3]。
2.2 以有效管理为导向,强化“分类管理” “绩效管理” “质量管理”
针对监管不到位、监管真空持续扩大等问题,关键是要面向放管结合的基本要求,以有效管理为导向,强化 “分类管理” “绩效管理”“质量管理”,全面激活高等院校的办学活力,持续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其一,探索分类管理。分类管理既涉及政府层面,又涉及高校定位及发展实际,既要参考借鉴国际优秀高校分类体系,又要与我国国情、高校教情相符,因此,要立足全局系统谋划、统筹协调,构建完善的分类管理体系,对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及发展目标进行科学定位,强化政策制定及执行的针对性、精准性,克服其同质化倾向,打造差异化办学理念与风格,在不同层次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其二,加强绩效管理。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长远目标,强化管理的质量、结果、参与、服务、成本及效益意识,通过绩效目标设置、考核指标设计、绩效数据收集及反馈、绩效评价主体及方法选择,绩效结果反馈及使用等,全面建构绩效管理体系,统筹评价办学绩效与质量,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指挥棒”效应。其三,注重质量管理。为了强化管理的有效性,还需积极探索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参与的质量管理模式,立足办学水准、教育水平、产出绩效等展开评价,建立评价反馈响应与公开问责机制,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激励、诊断功效,形成集教育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的权力结构运行机制[4]。
2.3 以优质服务为基准,强化“协作服务” “人性服务” “智慧服务”
针对服务意识薄弱、服务职能泛化等问题,关键是要以优质服务为基础,强化“协作服务”“人本服务” “智慧服务”,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责和使命,切实“服”出民声。其一,注重协作服务。 “放管服”深度改革离不开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因此,要在政府主导下,强化政、校、行、企等的参与,为了优化服务,政府要结合现代治理理论,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将协作理念引入治理之中,通过政府、高校、社会三方联动,构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改革合力,推进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配套设施建设,为高校内涵式发展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创设完善的体制机制环境。其二,提供人性服务。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关键是要使服务接地气、人性化,既要注重完善高等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构建效率高、成本低、过程透明的政务服务平台,又要加快精简审批手续、缩减办理周期,提供同质量、同标准、并联审批及容缺预审,尽可能实现“线上常态化办理”,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增强广大师生的获得感,还要注重构建职责分明、分工明确的协同工作制,规避重复、多头、过度检查,就科研服务而言,要将科研人员从会计角色中释放出来,为其营造更好的科研环境。其三,探索智慧服务。要积极引入“互联网+”技术,打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高校、高校与高校间数据共享难题,全面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 “互联网+校际共享”改革,为高等教育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服务,持续提升服务效率及其透明度[5]。
3 结语
综上,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的“先手棋”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当头炮”,顺应了社会各界对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期待、新诉求,对于全面助推国内高等院校内涵式发展意义深远。值得思考的是,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政府放权“放不下”、高校“接不住”,政府监管“不合理”、高校 “不适应”,政府服务 “不到位”、高校“不满意”等多重矛盾仍存在,因此,有必要以精准放权为目标,面向管理效率、服务水平等要求,积极探索高校教育“放管服”改革深化路径,以助推高校的内涵式发展与建设。